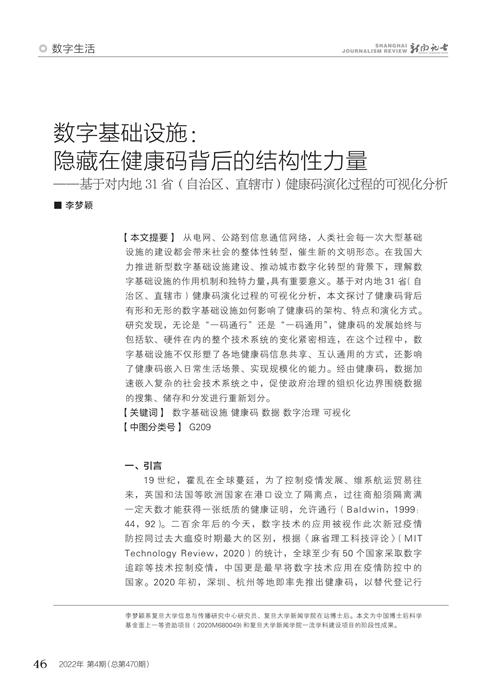数字基础设施:隐藏在健康码背后的结构性力量
——基于对内地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
■李梦颖
【本文提要】从电网、公路到信息通信网络,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社会的整体性转型,催生新的文明形态。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和独特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内地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本文探讨了健康码背后有形和无形的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了健康码的架构、特点和演化方式。研究发现,无论是“一码通行”还是“一码通用”,健康码的发展始终与包括软、硬件在内的整个技术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形塑了各地健康码信息共享、互认通用的方式,还影响了健康码嵌入日常生活场景、实现规模化的能力。经由健康码,数据加速嵌入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之中,促使政府治理的组织化边界围绕数据的搜集、储存和分发进行重新划分。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 健康码 数据 数字治理 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209
一、引言
19世纪,霍乱在全球蔓延,为了控制疫情发展、维系航运贸易往来,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港口设立了隔离点,过往商船须隔离满一定天数才能获得一张纸质的健康证明,允许通行(Baldwin, 1999:44,92)。二百余年后的今天,数字技术的应用被视作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同过去大瘟疫时期最大的区别,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0)的统计,全球至少有50个国家采取数字追踪等技术控制疫情,中国更是最早将数字技术应用在疫情防控中的国家。2020年初,深圳、杭州等地即率先推出健康码,以替代登记行程信息和健康状况的纸质表格(深圳特区报,2020)。此后,健康码在全国迅速铺开,截至2020年12月,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相较于传统的管理方式,健康码“无需接触”、“动态更新”、“更便捷和安全”(方兴东,严峰,2020)——集中展现了数字技术的优势,但也可能带来更严峻的数字鸿沟、数据滥用和个人信息泄漏的问题(彭兰,2020;宁园,2020),对现有的法规和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许可,2020)。还有学者指出,健康码不仅关乎治理创新、社会公平或隐私保护等议题,更直接指向人的生存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预示着“肉身人向数字人的关键转化”(吴冠军,2020),人、物、实体空间等各个面向的数据经由健康码直接影响身体的自由行动,“开启了媒介介入社会的新型方式”(孙玮,李梦颖,2021)。
可以说,已有的讨论为理解健康码个案的丰富意义及其所展示的数字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嵌入,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和观点。但大部分研究将健康码看作“既定之物”探讨其社会影响,而忽略了技术及技术物本身的特性和演变过程。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健康码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高覆盖率、高使用率,还逐步形成了以省级健康码为单位,以国家级平台为中介转换的基本架构;无论是企业、机构自行开发的防疫信息登记系统,还是核酸检测、疫苗接种情况查询等新的防疫手段,都依托健康码展开;对大部分人而言,健康码已成为出行的必要条件,健康码的“系统故障”、“使用异常”往往会造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极大不便。这些变化都标志着健康码已从早期的“电子信息登记表”,演化成为疫情下人员流动管理的基础性系统。健康码如何发展成为今天的结构和样态?哪些因素影响了其发展逻辑?数字技术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提出引入“基础设施”的分析概念和方法,通过追溯和比较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码的发展过程,理解影响健康码结构和样态的关系和力量,尤其关注健康码背后有形和无形的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形塑了其演化的方式和特点。本文所指的数字基础设施,既包括服务器、数据中心、基站等使数据可以流动的物质性技术系统,也包括网络协议、数据标准、政策法规等维系其运作的机制和规范。第一,研究将健康码看作动态的、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的系统,以健康码的推广、互认和更新过程为研究对象,追溯健康码发展成为全国性人口流动管理基础性系统的过程;第二,从健康码的技术原理及其所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入手,理解其运行方式和演化逻辑;第三,从健康码个案探讨数字基础设施的独特性。如果说基础设施是形塑社会变迁的基础性物质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社会的整体性转型(Plantin & Punathambekar, 2019),那么数字基础设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健康码的个案如何刷新我们对于基础设施力量的理解?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和独特力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研究:从“寻找共性”到揭示“独特性”
“基础设施”通常指高速公路、电网、通信网络等组织日常生活的“大型技术系统” (Hughes, 2012:45),它们提供了“使其他物、人、思想得以流动的网络”(Larkin, 2013:328)。美国社会学家Susan Leigh Star在其极具开创性的论文《基础设施的民族志》中总结了基础设施的基本特征:区别于一般性技术系统,基础设施广泛共享、无处不在,其规模和影响范围超越单一的事件或地区;除了规模庞大,基础设施深度嵌入社会技术结构,并且融入日常实践当中,就像人们大多注意水龙头而忽略背后的水管一般,基础设施通常隐藏在其他活动的背景中,往往在其出现故障时,基础设施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才会显现(Star, 1999:380-382)。
传统基础设施研究沿承了科学科技研究(STS)和技术史研究的思路,主要关注水、电网、通信网络等大型基础设施如何形成、演化,以及这个过程中政经力量与技术的互动关系(Sandvig, 2013:96)。过往研究发现,想要自上而下设计大型基础设施通常难以成功,基础设施的形成通常始于一项新技术的发明,而新技术一旦开始应用,会适应和调节不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并演化出纷繁复杂的异质系统——在铁路、电力、互联网等的发展早期都曾出现许多相似但不兼容的设备和系统(Edwards, 2016:340)。往往需要作为中介转换机制的“网关(gateway)”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技术设备也可能是通用的协议或标准,让各地的系统能够灵活转换、协同运作,并融入日常操作惯例中,新技术才可能真正演化成为基础设施(Plantin et al., 2018)。换而言之,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的、物质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Edwards et al., 2007:4),它既集中反映和体现现有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又会形塑日常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和体验(Dourish & Bell, 2007)。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一系列“提供了计算和网络资源”的硬件、软件、技术标准等,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特点在于其能够“搜集、储存和分发跨越多个系统和设备的数据”(Constantinides et al., 2018)。有学者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通常围绕“数据”展开,常见的问题包括由谁管理、控制、使用数据,如何形成关于搜集、分享、储存数据的惯例等等,也因此,网络协议、国际数据标准等转换机制对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形成尤为重要(Edwards et al., 2007:31)。可以发现,基础设施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抽象出基础设施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点,将研究者的视角指向“网关”、“标准化”等基础设施形成的关键环节,为理解大型技术系统的力量及影响提供了一系列概念和方法。但由于其目的在于“寻找共性”,在这个脉络里,让数据得以流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让水、电得以流通的水网、电网并无差异,其对于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同其他基础设施的不同考察不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崛起,尤其是谷歌、脸书、微信等“基础设施型平台”(van Dijck et al., 2019)的快速扩张,基础设施一词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视野。以Jean-Christophe Plantin等(2018,2019)为代表的学者提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基础设施研究和平台研究这两个不同路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巨头越来越具备了传统基础设施无处不在、普遍使用的特点;另一方面,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往往意味着开放其架构和治理框架,这个双向的过程也被称为“平台的基础设施化”和“基础设施的平台化”。从这一视角出发,有学者以亚马逊、淘宝等具有代表性的平台为个案,探讨互联网平台如何渗透甚至替代原本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基础设施,突出监管和治理平台的挑战(Constantinides et al., 2018;段世昌,2021)。由于研究的落点在于商业平台巨头和公共基础设施在社会功能上的交叉或冲突,恰恰消解了不同平台本身的技术特点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独特性。
新近的应用程序研究(App Studies)则从软件研究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物质—技术”(Helmond, 2015)的方法路径:通过分析软件界面设置、解析其数据接口及流向、分析程序包等技术文件内容的历时性变化,揭示程序的设计原理和思路,突出其所勾连的多元主体和物质基础设施(Dieter et al., 2019; Gerlitz et al., 2019)。可见,软件研究是从应用程序本身的特点和架构着手,追溯其“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为基础设施研究提供了补充。受到这一路径的启发,本研究将综合基础设施研究和软件研究的视角,通过分析各省健康码的技术更新过程,追溯健康码的形成、演化过程,从数据的搜集、汇聚、分发入手,理解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和力量。
三、研究方法:可视化分析
研究搜集了2020年2月到2021年3月之间(覆盖各省健康码上线后一年的时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健康码相关的政府文件、技术标准说明、用户协议及相关媒体报道,借助RawGraph等开源数据可视化工具,系统性地分析健康码的演变过程。
首先,研究对早期各省健康码的基本状况进行梳理、统计和分类,根据地方主管部门类型、技术开发方、技术标准、申领方式等指标,勾勒出不同地方健康码的差异和关联。第二,运用扎根方法的思路,对各省级健康码历次版本更新内容的说明进行编码,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其历时性变化,以理解各省健康码的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北京健康宝”为例,继2020年3月1日上线后,分别于同年3月17日、6月25日,推出了“北京健康宝2.0版”和“北京健康宝3.0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20)。针对每一次技术更新,北京市经信局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更新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以2.0版为例,除了解决“早高峰时期登录异常”、人脸识别验证时常需“重复刷脸”等问题,这一版本的北京健康码增加了“他人代查”和“环京通勤人员使用”两项新的功能(北京日报,2020)。于是,在分析编码时,北京健康宝2.0版本的更新内容被标记为“技术优化”、“他人代查”和“环京通勤人员使用”。以此方法研究对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健康码共计53次版本更新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编码,并借助RawGraph等可视化工具,纵向把握全国健康码的历时性变化,横向对比不同省份健康码的演化过程,理解健康码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第三,尤其关注健康码跨省互认的技术原理和物质性基础:基于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各级政府文件、健康码技术说明等资料,分析健康码互认的关键技术环节,和原有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关系等问题。
四、差异与整合:重塑地方管理架构
2020年1月起,健康码作为一种新的数字技术和管理机制开始在全国推行,其建立过程勾连了各地原有的管理架构和治理机制,亦卷入了不同类型的利益主体。如图1所示,早期各地健康码的主管部门类型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负责公共卫生和健康工作的卫健委部门、大数据管理局等数据治理部门以及省营商局等政务服务部门;在技术开发方面,除了人们比较熟知的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大巨头,中国电信、浪潮、华为等大型国企和科技公司亦参与了多地健康码的开发,此外,由各地政府控股或长期合作的地方数字服务企业,包括数字广西集团、数字重庆、吉林祥云等,也主导或参与了本地健康码的开发和运营。
这种地域间的差异直观地表现在了各地健康码技术设置和申领方式的不同上。以颜色分类为例,除了最早由杭州推出的“红、黄、绿”三色码,有近三分之一的省级健康码采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方式,比如,天津健康码是“红橙绿”三色,广东粤康码只区分“红绿”两色,而贵州健康码则用了“红黄绿橙紫”五色对人群进行分类。此外,健康码申领方式亦不相同。总体而言,健康码的申领渠道有四种:省级一网通办App、支付宝、微信,以及专门的健康码应用(见图2)。首先,一网通办App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申领渠道——有22个省份都提供这一申领方式,其中,在吉林、宁夏和福建三省,一网通办App是其早期唯一支持的申领方式,这三地的健康码也都是由本地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其次,支付宝和微信的覆盖率相似,分别有18和19个省份支持通过这两个平台申领,其中,由阿里巴巴协助开发的健康码通常只能通过支付宝申领,而仅支持微信申领的情况主要有两种,或是由腾讯协助开发其健康码,或是由本地科技公司负责改造已有的政务微信公众号作为新的健康码申领入口,这既体现了两大平台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又突出了微信对政府公共服务渠道的深度嵌入;最后,还有两个省份——甘肃、陕西,在疫情期间推出了专门的健康码应用,这既可能受到分管部门的影响,也可能同各地原本的治理数字化程度相关,这两个省份都由当地卫健委部门负责开发健康码,于是将原本提供医疗服务的小程序或客户端改用作健康码申领,如甘肃使用的是卫健委开发的“健康甘肃”App,在疫情之前,这一应用的主要功能是支持预约挂号、门诊缴费、检查报告查询等,而其省级政务服务应用“陇政通”于2020年初才刚刚推出,尚未整合医疗相关服务。
可以说,早期健康码纷繁复杂的样态集中反映了各地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和权责安排。具体而言,当涉及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疫情防控时,负责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卫健委部门和以大数据管理局为代表的政府数据治理机构之间,如何界定职责。自中央于2015年、2018年先后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来,各省都尝试从机构设置上推进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设立数据治理机构。但是,各地数据治理机构的隶属模式、组建方式和职责划分不尽相同,有的已成为单独的政府部门,负责整合统筹全省的数据资源,有的则隶属于省办公厅、发改委等部门,负责建设政府网站、发展数字产业等(黄璜,孙学智,2018)。当各地需要对疫情迅速反应、在短时间内推出健康码时,这些数字治理结构和职能设置上的不同,立刻凸显出来:仅就健康码的主管部门而言,既有像上海、贵州等由已独立运作的大数据中心统筹运营的,也有像山西、甘肃等由卫健委的信息化部门主导的,还有像黑龙江、宁夏等地由承担本省大数据建设的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政府办公厅等部门承办的,这些差异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数字治理方面不同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化安排。
第二,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的关系。在健康码的个案中,这主要指地方政府同提供数字技术服务的企业的关系。通过梳理健康码的技术开发方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企业都参与了我国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并形成了不同的合作模式:有的地方是由深度参与了当地数字政府建设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负责开发健康码,比如,此次设计“粤康码”的“数字广东”公司,由腾讯联合三大运营商共同创立,从2017年起即开始负责广东省的数字化改革项目(数字广东,2020),类似的,承办浙江、海南健康码的阿里巴巴长期参与两地数字政府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海南日报,2019);也有的是参照传统电子政务项目的招标方式,向本地的软件开发企业采购需要的服务,比如,设计八闽健康码的是“根植福建”的企业长威科技(金融界,2021),该公司2017年参与了福建省政务服务App闽政通的开发,此次健康码也先是在闽政通上推出,一年后才逐步支持支付宝和微信申领。可见,各地所涉及的技术服务企业的类型、参与程度和合作方式都不尽相同,并且大多是基于过去数字政府建设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和模式,这些区别也都呈现在了此次健康码的开发当中。
而随着健康码的应用和推广,原本的政府管理架构和数字治理机制开始改变。各地开始加速搭建面向本地居民的一网通办App,以及支撑省内跨部门协作的一网通办平台。如图3所示,全国大部分省份自2019年起陆续推出省级政务服务应用,其中,近四分之一的省份,是在疫情后才上线本省统一的一网通办App。比如,内蒙古“应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于2020年3月“紧急上线”了“蒙速办App”的试运营版本,主要功能即提供健康码申领,此后才逐步完善了其他政务服务功能(内蒙古日报,2020)。河南省2021年发布“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年)实施方案”,首当其冲的是建立全省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项目和政务云,目标是在“2022年年底前初步建成省一体化协同办公平台和移动端‘豫正通’”(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
同时,尽管健康码上线初期,主要根据各地原本疫情防控的管理架构由某一部门负责其开发和运营,在健康码上线后,这种安排迅速发生改变。随着健康码整合的数据类型越来越多,各地往往需要多个条线、多个部门围绕数据的整合、储存和交换重新商讨组织的方式和架构。以山西为例,当健康码需要接入本省一网通办应用“三晋通”并对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时,主导健康码开发的省卫健委须与负责本省一网通办平台的省政务服务中心、智慧政务项目组等进行协作和数据联网,并就健康码的运营维护重新划分职能(山西智慧政务,2020)。类似的,黑龙江省为了推出“龙江健康码”,“组织公安、卫健、民政、通信管理等多部门协同配合,腾讯公司软件研发,合力攻坚”(哈尔滨新闻,2020)。
这些调整并非疫情下的暂时性安排,而是推动了政府组织架构和职能划分的制度性变化。过去仅在省工信委下设置了大数据相关职能的陕西省,于2021年正式成立了省政务大数据局和大数据中心,并定位为“省政府直属正厅级一类事业单位”,负责统筹全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陕西日报,2021)。而在疫情前就已经成立了大数据局的河南省,则是重新明确各级、各部门在“数据采集、汇聚、储存、共享等环节”的职责边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同时推动全省数据向统一的平台归集(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2020)。这意味着,尽管疫情前各地数字治理的组织架构和方式各不相同,未来都趋向通过专门的数据治理机构和统一的一网通办平台及应用进行统筹。此外,正如有学者已注意到的,健康码的开发显著区别于政府网站建设等传统电子政务项目,对于大数据、云计算能力有更高的要求,还涉及协调多个部门、以用户为导向等方法和理念上的差异(史晨,马亮,2020)。这意味着,尽管各地大多基于过去数字政府建设中已形成的合作关系和模式选择开发健康码的企业,但未来将越来越倾向有数字基建能力、可以参与整体架构设计和持续运维更新的企业。可见,健康码不仅带动了政府治理系统的加速数字化转型,还带来了新的权力关系,打破了各地行政管理的组织化边界,促使行政管理架构围绕数据的收集、处理进行重新划分。
五、“一码通用”与“一码通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的功能拓展
随着健康码的推广和疫情防控需求的变化,自健康码上线后,大部分省份都对其健康码应用进行了多次更新,尽管更新频次和拓展方向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各省健康码的更新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码通行”、“一码通用”、“技术更新”。“一码通行”,主要指同健康码能够成为人员流动管理基础性系统密切相关的功能,包括家人代领、老人码、离线码、线下场景、省内码统一、全国跨省互认等;“一码通用”,是指拓展健康码的功能,将健康码应用到管理疫情间人口流动以外的领域,最典型的包括同就医凭证、公交乘车码等进行整合,以及增加核酸检测结果查询、疫苗接种情况查询等功能;最后,“技术更新”是指云上数据迁移、系统升级扩容、统一数据接口、界面优化、增加申诉反馈等功能。
如图4和5所示,“一码通行”是最常见的一类功能更新,尤其在健康码上线初期,各地都较为密集地更新了相关功能。大部分省份增加了“家人代领”健康码的选项,通过这些新增功能,儿童、老年人等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等的群体都被纳入了健康码的管理范围;同样常见的,还有规范和整合线下使用场景,包括规范健康码的申领流程和使用场所,以及将不同机构和企业原有的进出人员管理系统接入健康码,由此小区、单位、商场等不同场景都被纳入其管理范围;最后,统一省内的健康码使用、建立跨省互认转换机制等,更是健康码系统得以标准化并真正实现全国“一码通行”的关键环节。这些功能更新对于扩大健康码的用户规模、覆盖各类社会群体、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使之成为人们身体跨越地域边界的通用凭证至关重要。
如果说“一码通行”的功能更新旨在提高健康码的覆盖率、使用率及对日常生活的嵌入度,“一码通用”方向的拓展则是试图将健康码应用到疫情人口流动管理以外的领域。从图4中可见,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频繁升级健康码的功能,并且持续开发新的使用场景,包括同地铁码、公交码、医保凭证等实现“一码通用”;同时,自2021年初以来,各地健康码陆续新增了查看核酸检测结果或查询疫苗接种情况的功能,尽管同疫情管理相关,但是否包含这类功能不影响健康码发挥其管理人员流动的核心作用,也属于“通用”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一码通行”还是“一码通用”,健康码的发展始终与包括软件、硬件等在内的整个技术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健康码更新的第三类主要内容即为“技术优化”,既包括网络、服务器、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也包括重新组织和搭建新的技术架构、标准和协议,优化界面设计和用户体验等。健康码的推广和功能拓展既受到各地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又驱动了后者的升级改造。以贵州为例,“‘贵州健康码’小程序上线第一天使用人数突破54万,访问量超600万次……为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已经部署了云服务器近400台、云数据库50台、存储50TB、独享带宽及系列云安全服务”(云上贵州,2020)。同样,在海南,健康码上线不到一周,申领人数即超过百万,达到原系统可承担的流量峰值,于是当地政府“紧急扩容升级”带宽和服务器,以支撑健康码系统的运作(海口日报,2020);还有的省份在疫情期间紧急搭建了新的政务云,待硬件升级完成后进行健康码系统和数据的迁移(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20)。
此后,疫情的每一次变化或是新功能的上线,都是对数字基础设施新的挑战,并且随着健康码的深入使用,每一次“程序卡顿”、“加载异常”、“系统故障”也都意味着对日常生活更严重的影响。2021年8月初,当山东出现本地疫情时,健康码的查询量峰值达到60.96万人次/分钟,8倍于前一工作日,造成系统崩溃,于是当地紧急下线了代表完成疫苗接种的金色健康码以减轻网络带宽和服务器的负担,同时,扩容网络带宽、增加服务器(健康山东,2021)。可见,健康码的使用对于支撑各地政府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各地在短时间内加大相关投入,而随着储存和处理海量数据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种投入将始终是处于进行中、未完成的状态。如果说,在疫情之前,各地政府的数字化程度不一、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力度不同,那么疫情后,尤其随着健康码的使用,各地的数字基建则整体进入了持续增长阶段。
六、标准、接口和可编程性:搭建全国性的健康码系统
数字基础设施不是单纯地支撑健康码的稳定运行,更影响了健康码全国互认的机制和方式,塑造了今天健康码系统的形态和架构。在健康码推行早期,各地主要根据用户自主申报的数据以及自己制定的赋码规则进行制码,到2020年3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建立了本地的健康码,但各地健康码的判定标准、适用场景和对应的隔离措施都不尽相同,频繁出现跨省流动受阻、重复隔离的现象,如何实现互通互认成为当时最大的难题。起初,跨省互认主要通过省与省之间签署互认合作协议实现。2020年3月14日,四川省同广东、浙江、重庆等10省市签署了《推动务工人安全有序返岗合作备忘录》,同意“相互认可双方出具的健康申报证明(健康码)”,并要求相关单位落实这一协定,不再要求来川务工人员留观或隔离(四川省人民政府,2020)。类似的,贵州和重庆、浙江和海南以及长三角地区都比较早签署了区域性互认协议。同时,各地纷纷呼吁拒绝地域歧视,尤其对于持湖北健康码的离鄂人员,应一视同仁,绿码放行。
然而,健康码的互认不只是人的沟通(包容和互信),也不只是行政系统的沟通(行政令要求的互认),更需要不同地区数字系统的沟通,而数字系统的沟通需要特殊的“语言”,涉及数据格式、接口、模型的标准化。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其跨地区互认的实现是通过沟通协商“健康码的制定标准及人员管理措施”;搭建能够安全交换数据的管道——“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共享数据——“每日定时上传红、黄‘健康码’数据文件,分别提供绿色‘健康码’的查询接口……日均交换红、黄码人员信息量100余万条”(澎湃新闻,2020)。
此后,一方面,各地逐步取消了市、区级健康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疫情防控码管理便利人员出行使用的通知》的要求,“原则上各省仅保留一个统筹建设的健康码”,也就是说,在各省内基本形成了更加高效的、由中心统一控制的健康码系统。另一方面,在统一了各个省内的健康码使用后,这个纵向整合的过程没有再继续延伸,全国“一码通行”并没有以一个“全国健康码”替代所有地区码的形式出现,而是维持了以省级健康码为单位的基本架构,相关数据的储存和处理都主要依托省级数字基础设施完成。“只有当一个个在地的、由中心控制的系统连接到可以分布式管控和协调的网络中时,真正的基础设施才开始形成”(Edwards et al., 2007:7),也就是说,“基础设施不是一个系统,而是(系统的)网络或组合”(Edwards, 2016:340),而连接不同的系统、让其可以灵活转换的关键装置,正是“网关”。在健康码的个案中,全国性的平台、数据标准和新冠数据库,正承担了这一“网关”的角色,协助健康码的跨省互认。2020年3月起,各地开始按照统一的国家标准——《个人健康信息码参考模型》、《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格式》、《个人健康信息码应用接口》,将防疫健康信息目录数据汇入国家平台。截至2020年4月初,“贵州健康码”向国家平台推送数据1211.86万条,入库总量在全国31个省区中排名第9(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2020);辽宁报告该省14个市汇聚并上报国家“防疫健康数据”1476.3412万条,入库766.9523万条(辽宁日报,2020)……这些数据汇聚成了实时更新的“国家防疫重点人群数据库”。当涉及异地健康码申领时,各地可调用国家数据库的“访问接口”查询相关信息,并在各自的系统中完成数据校验、比对和制码,从而实现转码。
由此,一个以省级健康码为单位,以全国性的平台、数据库和数据标准作为“网关”的全国性人口流动管理基础设施形成了。在国家层面,仅需支撑基础数据库的运行,而非协调全国所有省份、所有部门相关数据的储存和分析;在地方层面,通过国家发布的查询接口即可以调取其他省份的实时数据,既无须为本地服务器增加额外的负荷,又可以根据本地防控需求和赋码规则实现转码,同时,即便个别地区健康码系统偶发故障,也不会影响全国其他地区。这种分布式的架构体现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健康码系统结构的影响,如今以省级健康码为单位搭建的健康码系统,正是试图在数字基础设施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取得平衡。
最后,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形塑了各地健康码信息共享、互认通用的方式,更通过其“可编程性”,影响了健康码渗透进日常生活场景、迅速实现规模化的方式。医院、学校、博物馆、企业等不同类型的场所,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对于需要亮码还是扫码、核验还是登记,以及相关信息的类型、颗粒度、时空范围等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出现本地病例时,有的场所不仅查验健康码的颜色,还需要能够录入地点、实时体温、核酸检测结果等信息的应用和设备以及供管理端使用的应用程序等。而数字技术最基本的属性在于其“可编程性”(马诺维奇,2020:47),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于计算机领域,意指软件应用可以通过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I)让外部开发者在其架构和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需求创建新的应用,从而扩展其本身的功能和使用范围(Plantin et al., 2018)。以上海为例,2020年3月,上海“一网通办”上线了随申码的开放平台(文汇报,2020),在上海注册的企业和机构不仅可以通过“单位张贴码记录查询接口”,核查和登记员工及访客的健康码状态,还可以根据疫情防控的需求申请“使用随申码验码接口开发通过扫码枪、扫码器读取人员防控核查的应用程序”,并实现在自己的应用程序内直接跳转到随申码页面。类似的,广西健康码建立之后,整合了广西当地不同企业和单位开发的疫情扫码防控应用,所谓“整合”不是直接替代现有的管理系统,而是通过提供“H5、API接口等形式对外开放应用”,支持不同场景、不同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接入和开发自己的管理程序(广西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2020)。尽管调用健康码的接口需要向政府申请,可拓展的功能和应用也须在疫情防控的范围之内,但健康码通过提供一定的“可编程性”,吸引不同类型的主体使用同一平台,而非创建分散的、标准不一的防疫信息系统,从而达到规模化的效应。这些新的场景和应用所生成的数据又会再次“哺育”健康码系统,帮助地方政府第一时间了解疫情的发展情况。
七、结语:数字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力量
19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的比喻横空出世,有意将快速发展的数字通信技术同构筑城市文明基础的硬件系统相联系(Edwards et al., 2009)。30年后的今天,由光纤、基站、云服务器、传感器、数据中心、算法等硬件和程序构成的“巨大的”、“渗透到一切之中”(陆兴华,2021)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形成,其规模和影响也早已超出了原本高速公路——快速传输信息——的意象。2021年末,西安健康码短时间内数次崩溃,引发了防疫工作的混乱和日常生活的极大不便,并最终导致大数据局官员被问责,再次凸显了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财新,2022)。
通过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在健康码系统形成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经由健康码,数字基础设施加速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促使政府管理的组织化边界围绕数据相关的实践进行重新划分;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协同运作,需要通过网络协议、数据标准、数据接口等机制进行“数字沟通”;数字基础设施的性能、架构和“可编程”的特点,更是形塑了各地健康码信息共享、互认通用的方式,影响了健康码嵌入日常生活场景、实现规模化的能力。这都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可被视作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数字基础设施让大规模数据的收集、储存、传输、流转成为可能,同时又为这种可能性设置了明确的界限和规则。不同系统间的连接转换都需考虑存储空间、数据标准、接口、编程等计算和网络技术的特性和语法,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有着自身权力的结构”、迫使其他系统的运作和交互都“考虑它的法则”(费里德里希·基特勒,2008:118);第二,数字基础设施是驱动其他系统重新组织和配置的动能,通过将数据加速嵌入到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当中,推动生成新的结构和关系,在健康码的个案中,这种力量集中体现在其打破了行政管理的组织化边界、推动了政府管理架构和工作流程的系统性变化,可能打开新的治理方式和形态。
由此,本文推进了关于基础设施的讨论和研究:第一,区别于大部分研究主要在比喻的意义上用“基础设施”强调数字技术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本文引入基础设施的理论和概念,展示了通过聚焦网关、标准、规模等基础设施的关键特征,可以为理解当下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极具价值的视角;第二,突出数字基础设施的独特力量和作用机制,从可编程、分布式等数字技术的特性出发,聚焦数据相关的一系列实践,揭示了当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嵌入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时,将驱动政府组织架构和治理方式的整体性变化。随着数字基建的加大投入,以及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型计算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各个面向都将产生剧烈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回应Geoffrey C. Bowker 和Susan Leigh Star(1999:34)的历史性呼吁——“倒置视角”、关注隐藏在技术背后的基础设施,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领域推动生成的新的结构和关系,对于理解当下的数字革命及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北京日报(2020)。“北京健康宝”2.0版上线。检索于http://www.gov.cn/xinwen/2020-03/18/content_5492625.htm,2022.1.21。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20)。市经济信息化局介绍北京健康宝3.0相关情况。检索于http://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2006/t20200625_1932609.html,2022.1.21。
财新(2022)。西安“一码通”一月内两度崩溃,谁之责。检索于https://www.caixin.com/2022-01-06/101826373.html,2022.1.21。
段世昌(2021)。从“寄生”到“共栖”——淘宝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新闻记者》,(7),86-96。
方兴东,严峰(2020)。“健康码”与正在浮现中的智能传播新格局。《未来传播》,(5),2-13+120。
费里德里希·基特勒(2008)。硬件:一个未知的本质。载西皮尔·克莱默尔编著,《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广西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2020年3月8日)。八码归一,广西健康码正式上线。检索于:http://www.gkq.gov.cn/yw/gkqyw/202003/t20200330_124849.html,2022.1.2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2020)。贵州“健康码”成功对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检索于http://dsj.guizhou.gov.cn/zfxxgk/fdxxgk/dsjyytg_5619967/202004/t20200402_55766961.html,2022.1.21。
哈尔滨新闻(2020)。龙江健康码来了:一次申报全省通行 自证健康 亮码通行。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92084,2022.1.21。
海口日报(2020)。海南健康码系统进行扩容升级。检索于http://www.haikou.gov.cn/zfdt/hkyw/202002/t20200224_1491109.html,2022.1.21。
海南日报(2019)。数字海南有限公司成立 推进我省政务信息化应用。检索于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tingju/201911/1e096ec4fadc46129fa3b1da95966be4.shtml,2022.1.21。
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2020)。河南省大数据中心在郑州揭牌。检索于https://dsj.henan.gov.cn/2020/04-01/1311778.html,2022.1.21。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年)实施方案的通知。检索于https://www.henan.gov.cn/2021/10-09/2324519.html,2022.1.21。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20)。河南省“健康码”系统成功迁移中华黄河飞天云。检索于http://www.henan.gov.cn/2020/04-27/1350507.html,2022.1.21。
黄璜,孙学智(2018)。中国地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初步研究:现状与模式。《中国行政管理》,(12),31-36。
健康山东(2021)。山东回应健康码故障、金色码下线:因短期查询量激增,已恢复。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875085,2022.1.21。
金融界(2021)。长威科技二闯IPO,这次能否走出福建省?。检索于http://stock.jrj.com.cn/ipo/2021/03/23081832199189.shtml,2022.1.21。
辽宁日报(2020)。辽宁发放800余万张防疫健康码。检索于http://ln.people.com.cn/n2/2020/0410/c378317-33938505.html,2022.1.21。
陆兴华(2021)。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诺维奇(2020)。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日报(2020)。上线100天,“蒙速办”App走进内蒙古千万家。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7928192,2022.1.21。
宁园(2020)。健康码运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制。《法学评论》,(6),111-121。
彭兰(2020)。“健康码”与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现代视听》,(6),1。
澎湃新闻(2020)。长三角地区健康码率先互认:摩擦系数降低,就会促进经济发展。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93302,2022.1.21。
山西智慧政务(2020)。“一部手机三晋通”APP成功上线防疫健康信息码。检索于https://www.meipian.cn/2rgmxsdo,2022.1.21。
深圳特区报(2020)。全国首个凭“码”出行城市,深圳全面实施人员通行认证管理。检索于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0-02/15/content_22866170.htm,2022.1.21。
陕西日报(2021)。省政务大数据局和省政务大数据服务中心挂牌成立。检索于http://www.shaanxi.gov.cn/xw/sxyw/202107/t20210714_2183050_wap.html,2022.1.21。
史晨,马亮(2020)。互联网企业助推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健康码与“浙政钉”的案例研究。《学习论坛》,(8),50-55。
数字广东(2020)。数字广东公司成立三周年探索数字政府建设“广东模式”。检索于https://www.digitalgd.com.cn/news/4515/,2022.4.22。
四川省人民政府(2020)。关于认可广东、浙江等10省市健康申报证明(健康码)的通知。检索于http://www.sc.gov.cn/10462/c102278/2020/3/14/386d0b277abf47dfac0462adc4561e97.shtml,2022.1.21。
孙玮,李梦颖(2021)。“码之城”: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探索与争鸣》,(8),121-129+179+2。
文汇报(2020)。上海“一网通办”升级“随申码”,为企业负责人开放了一个“特殊通道”。检索于http://n.eastday.com/pnews/1584291115016476,2022.1.21。
吴冠军(2020)。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9),115-122+159。
许可(2020)。健康码的法律之维。《探索与争鸣》,(9),130-136+160。
云上贵州(2020)。贵州健康码”系统正式上线云上贵州大数据集团精准助力我省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检索于http://gzw.guizhou.gov.cn/xwzx/qyzc/202002/t20200225_51580708.html,2022.1.2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2728645.htm,2022.1.21。
BowkerG.& Star, L. (1999).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MA:MIT Press.
Baldwin, P. (1999).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nstantinidesP.HenfridssonO.& Parker, G. G. (2018). Introduction—platforms and infrastructures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9(2)381-400.
DieterM.GerlitzC.HelmondA.TkaczN.van Der VlistF. N.& Weltevrede, E. (2019). Multi-situated app studies: Methods and propositions. Social Media+ Society5(2)1-15.
Dourish, P.& Bell, G. (2007). The infrastructure of experi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frastructure: meaning and structure in everyday encounters with spa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34(3)414-430.
Edwards, P. N.JacksonS. J.Bowker, G. C.& Knobel, C. P. (2007). Understanding infrastructure: Dynamics, tensions, and design. Report of a Workshop on “History & Theory of Infrastructure: Lessons for New Scientific Cyberinfrastructures”. Retrieved from http://hdl.handle.net/2027.42/49353.
Edwards, P. N.Bowker, G. C.JacksonS. J.& Williams, R. (2009). Introduction: an agenda for infrastructure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10(5)364-374.
Edwards, P.N. (2016). Downscaling: From global to local in the climate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In: Harvey, P.Jensen, C.B.& Morita, A. (Eds.)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Routledge339-351.
Gerlitz, C.HelmondA.NieborgD. B.& van der VlistF. N. (2019). Apps and Infrastructures: A Research Agenda. Computational Culture-A Journal of Software Studies(7).
Helmond, A. (2015).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 Social Media+Society, 1(2)1-11.
HughesT.P.(2012). The Evolution of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in: Bijker, W.Hughes, T.P.& PinchT. (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MA: MIT Press45-76.
Larkin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327-343.
Liu, C.& Graham, R. (2021). Making sense of algorithms: Relational perception of contact tracing and risk assessment during COVID-19. Big Data & Society8(1)1-13.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0)The Covid Tracing Tracker: What’s happening in coronavirus apps around the worldRetrieved from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12/16/1014878/covid-tracing-tracker/2022.1.21.
Plantin, J. C.Lagoze, C.EdwardsP. N.& Sandvig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20(1)293-310.
Plantin, J. C.& PunathambekarA. (2019).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platformsand politics. MediaCulture & Society41(2)163-174.
Sandvig, C. (2013). The Internet as infrastructure. In: Dutton, W. H.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86-108.
Star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3(3)377-391.
Van DijckJ.PoellT.& De Waal, M.(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李梦颖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20M680049)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