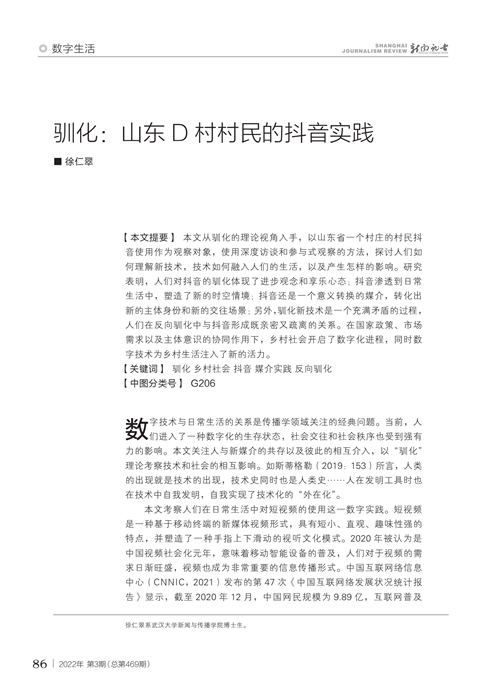驯化:山东D村村民的抖音实践
■徐仁翠
【文本提要】本文从驯化的理论视角入手,以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村民抖音使用作为观察对象,使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探讨人们如何理解新技术,技术如何融入人们的生活,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表明,人们对抖音的驯化体现了进步观念和享乐心态;抖音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塑造了新的时空情境;抖音还是一个意义转换的媒介,转化出新的主体身份和新的交往场景;另外,驯化新技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人们在反向驯化中与抖音形成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在国家政策、市场需求以及主体意识的协同作用下,乡村社会开启了数字化进程,同时数字技术为乡村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驯化 乡村社会 抖音 媒介实践 反向驯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传播学领域关注的经典问题。当前,人们进入了一种数字化的生存状态,社会交往和社会秩序也受到强有力的影响。本文关注人与新媒介的共存以及彼此的相互介入,以“驯化”理论考察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影响。如斯蒂格勒(2019:153)所言,人类的出现就是技术的出现,技术史同时也是人类史……人在发明工具时也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了技术化的“外在化”。
本文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短视频的使用这一数字实践。短视频是一种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媒体视频形式,具有短小、直观、趣味性强的特点,并塑造了一种手指上下滑动的视听文化模式。2020年被认为是中国视频社会化元年,意味着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人们对于视频的需求日渐旺盛,视频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21)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55.9%。此外,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如今,短视频以强势力量占领农村市场,中老年人成为新兴且庞大的用户群体。根据田野观察,农村群体对短视频的依赖程度体现出较强的黏性,用短视频来打发时间已成为农村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随着视频在技术功能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阐释农村群体和视频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更显必要。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遵循Couldry提出的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将媒介理解为实践,而不是文本或生产结构。实践研究要求提出开放性问题,询问人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理解在做的事情,研究者应该避免先入为主的理解(Couldry, 2004)。本文聚焦农村语境,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关注技术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从实践的立场考察短视频如何融入人们的生活,以及主体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一、文献回顾
“驯化”一词最初指驯服野生动物,后来被用于分析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塑造,关注技术为什么以及如何出现。Silverstone等人提出家庭作为一种“道德经济”的模式,系统地探讨技术如何从物质和符号两方面双重连接到人们的家庭生活中去。驯化包括四个重要阶段:占有、客观化、合并和转换。占有(appropriation)指一件物品离开商品世界和等价交换的广义系统,被个人或家庭占有;客观化(objectification)强调技术使用的空间维度,指新技术在家庭环境内的摆放位置,并且其展示的意义被人们用来呈现自己的品位,以进行阶级区分;合并(incorporation)强调技术使用的时间维度,指媒介具有时间转换功能,例如人们将媒介融入日常安排,以媒介时间来维持家庭惯例;转换(conversion)是一个跨越内外边界的过程,指技术定义了家庭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跨越人工制品与意义、文本和技术的边界,将家庭成员转换到更广泛的社会中去(Silverstone et al., 1992:18-22)。
驯化理论的基本特点包括:强调技术与人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其中,主体为技术赋予人为的印记,而技术也对家庭文化和互动模式产生影响;驯化理论考察人们的行为实践,同时也采用动态的、迭代的方法检验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驯化还以微观视角勾连更大的社会结构和媒体消费语境,聚焦主体在与技术协商过程中的意义生产。
20世纪90年代的驯化研究关注家用的电视和电脑,后来的研究发生了诸多转向,体现在分析对象和语境迁移两方面。首先,驯化研究的分析对象包括技术和使用者。研究者们将驯化概念应用于不断涌现的新媒体技术之中。Haddon(2003:51)启发人们思考移动手机如何被驯化,消费环境和手机如何相互影响等问题;Quandt和von Pape(2010)建议研究媒体生态系统的驯化,关注不同媒体之间的共存和竞争;根据移动媒体的发展,Hartmann(2013)提出了“媒介移动性”(mediated mobilism)的概念。驯化研究还从物质实体转向非物质实体,例如驯化算法(Leong, 2020)、驯化约会软件(Wu, 2021),以及考察社交媒体和即时消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De Reuver et al., 2016)。对非物质实体的驯化研究为本文打开了新的思路,使笔者注意到一些新出现的媒介形态,例如短视频。此外,使用者研究体现了从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到个体消费者的转变(Haddon, 2003:52-53)。具体细分研究对象,包括青少年(Guan et al., 2019)、老年人(De Schutter et al., 2015)、老年移民(Khvorostianov, 2016),以及对特殊群体的研究,如中国男同性恋者驯化约会软件(Miao & Chan, 2021)。个体的媒介使用体现了现代化和全球市场发展带动的个体化消费趋势。其中,相比于被视为新媒体主要用户群体的年轻一代,中老年人作为数字移民,尤其是乡村中老年人,与信息通信技术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
其次,研究者们关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技术驯化和文化塑造。驯化研究起初以家庭为边界,后来转向家庭之外,关注工作场所和当地社区(Helle-Valle & Slettemeas, 2008)。还有一些学者将视角转向国家语境,不仅关注理论所源起的英国,还注意到非西方国家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包括中国西南小镇家庭驯化互联网(McDonald, 2015)、阿根廷人驯化WhatsApp(Matassi et al., 2019)、欧洲老年人驯化手机(Nimrod, 2016),以及瑞典休闲中心的数字媒体驯化(Martnez & Olsson,2021)。大多数研究没有点明国家在驯化过程中的角色,仅关注社会层面个体的媒介使用。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对技术的驯化无法忽视国家这一主体的力量。另外,“反驯化”(dis-domestication)、“反向驯化”(reverse domestication)和“再驯化”(re-domesticating)等概念拓展了驯化理论的应用语境。驯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也并非总是成功的。当原有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作用就必须被重新评估(Haddon, 2003:46)。尽管不同概念的内涵互有交叉,但是它们强化了驯化是一种互动过程,一种与主体有关的行为实践,并启发了本文对驯化过程的考察。
短视频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体现出内在的矛盾,表现在主体建构和文化表达两方面。在主体方面,短视频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自我表达平台,促进了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沙垚,张思宇,2019),呈现和建构了小镇青年多元的形象(刘胜枝,安紫薇,2019)。与此同时,短视频也导致了农民屏幕成瘾、孤独感强化、家庭冲突频发(刘天元,王志章,2021)。在文化表达方面,短视频促进了乡村亚文化的表达和文化认同(刘娜,2018),重构了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周敏,2019),促进城乡边界的消解和文化拼接(曹钺,曹刚,2021)。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乡村亚文化或被主流收编,或被商业话语消解(刘娜,2018)。在社会层面,短视频再生产了既有的城乡关系(张敦福,路阳,2021),塑造了中国的城乡二分法和城市文化的主导地位(Liu, 2020)。沿袭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功能主义取向,较多文章讨论了短视频对人们乡村生活的形塑或重构。研究者们认识到短视频对人们的双重影响,倾向于探讨技术的功能,并发人深省地提出一些隐忧。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对实践过程的关注不足,仅强调了静态的因果联系,而忽视了技术与使用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中国学者还以勾连的视角分析了短视频的使用,从生活器物、文本内容、空间场景三个层面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短视频实践(何志武,董红兵,2021);从技术文本、空间场景与主体行动三方面探讨短视频在乡村抗疫实践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意义的生产(周孟杰,吴玮,2021);分析陕西省村民借助短视频平台获取信息,将个体与乡村社会和外部世界勾连起来(吴琳琳,徐琛,2020)。笔者认为,勾连理论细化了技术使用的多个维度,以工具观探讨人与技术的互动,在强调技术角色和主体能动性的同时未能将人们的行为理论化。
本文关注作为技术使用者的人,将主体拆分成观看者和展示者,认为他们协同生产了观看和展示的公共空间,为短视频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可能。另外,本文将人们的媒介使用范围分为私人空间—公共空间这一组关系维度。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技术驯化从家庭向乡村敞开,镶嵌于“家庭—村庄”的结构之内,重塑了新的私人和公共界限,这是一个流动的跨越边界的过程。驯化实现了人对新技术由外向内的占有和使用,以及由内向外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在跨越内外的过程中,技术和乡村语境实现紧密的互动。
通过梳理,本文以驯化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抖音这类短视频如何嵌入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经验。研究问题具体表述为:人们如何看待抖音这一新技术,如何驯化抖音?在驯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根据驯化理论,人们对抖音的使用,包括占有、客观化、合并和转换四个过程,同时人们以反向驯化来平衡生活。本文以一个乡村现实的个案研究,致力于素描社会转型期内的农村群体。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抖音这一媒介形态作为分析对象,原因有二:第一,抖音是一款短视频社交软件,在中国当前的短视频行业中位于第一梯队,占据优势地位。根据《2020抖音数据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0年8月,抖音日活跃用户数突破6亿。第二,根据田野观察发现,相较于快手、西瓜视频等视频软件,山东省这一村庄内的人们普遍使用的是抖音App。
新媒体研究较多在城市语境内开展,而对乡村语境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旨在对农村的数字实践进行细致的本土描述,以管窥中国农村的局部现实。本文的田野地点为山东省诸城市林家村镇大桃园村,该村位于中国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带,户籍人口1390人,1.8860万亩地,380亩山场。随着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年轻人普遍外出求学和打工,因此大桃园村也呈现出空心化的趋势,留守人群主要是“50后”、“60后”和“70后”。选择该村作为田野地点主要是因为大桃园村的家庭宽带和个人智能手机普及率较高,使用抖音成为村内的普遍现象;同时笔者的老家紧挨大桃园村,有着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对村庄内的人和文化较为熟悉,有助于快速进入田野展开研究。
笔者于2021年7月10日至8月31日在大桃园村进行一个多月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采用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访谈到40位经常使用抖音的研究对象。为保证受访者的差异性,笔者在性别、年龄、职业、软件使用时长等方面有意做出区分,包括男性16人,女性24人,年龄范围在35—73岁之间,使用抖音的年限在1年7个月到3年之间。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根据拟定的问题展开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均大于30分钟,并有针对性地回访了部分受访者。所有访谈均得到受访者同意,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以1—40的编号来表示。此外,笔者有意观察他们刷抖音时的神态、肢体动作、姿势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并关注他们的抖音账号,观察他们发布的视频、给他人的评论和回复。
笔者以录音和笔记的形式整理访谈资料并以主题分析方法进行“概念—类属—主题”的归纳整理。访谈和数据分析过程同步进行,当访谈到第40个人时,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类属,笔者便停止资料收集。数据分析过程为:首先提炼出资料中的关键概念,不断比较,通过概念间的相似或相异性,归纳出更高一层次的类属;再通过类属间的比较和连接,提炼出核心主题。本文结合驯化理论,调整行文框架,突出了乡村语境的特点。
三、占有:进步观念与享乐心态的融合
“占有”指技术的获得,以及新技术对人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人们如何谈论它。手机和抖音作为一种私人归属物,一般被视为“谁”的手机,登录了“谁”的账号,但是乡村社会出现了一种共同占有的形式。对抖音的驯化是一种多主体共享的实践活动,例如二手手机在家庭成员间的流转,选择一部旧手机作为家庭内刷抖音的设备,家庭成员共用一个抖音号。数字化生存的现实向我们表明: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你如何理解技术,就会如何理解人(吴国胜,2009:2)。对抖音的占有,体现出使用者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动机,表现为人们的进步思想和享乐心态。
技术未来主义者认为,新技术的到来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乌托邦景象的实现,并将新技术与现代性和现代秩序勾连。成为“现代”,指急切地、强迫性地进行现代化,抛弃早期的错误观念,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保持未定的状态(齐格蒙特·鲍曼,2017:4)。在乡村社会里,人们将使用新技术与进步、时髦、开放等概念联系到一起,表现出对新技术的积极态度:
“跟着社会走”是人们普遍的观念。人们在浏览视频时能学习到一些实用技能,包括医疗养生、农业种植、家庭矛盾调解等,因此玩抖音关系到人们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人们也将玩抖音的人看作更先进、更开放的人,而没有接触过抖音的人是封闭的、落伍的人。在驯化新媒介时,人们将传统的农村社会与现代性结合起来,并树立起一道区隔乡村群体内部的分界线。
理解人们占有新技术的方式,必须了解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农民对新技术的接纳,不完全是自发行为,而是与国家大力推进“数字乡村”政策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有关。自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两份文件提出“数字乡村战略”开始,国家一直积极推进农村互联网的普及,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家庭宽带的铺设、经济型智能手机的使用以及手机流量的降费,这一信息系统链条的完善促进了抖音在大桃园村的普遍使用。在一系列国家行动中,农村逐渐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也受到农民们的青睐。
每一种工具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即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或者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尼尔·波斯曼,2019:12)。短视频具有情感的偏向,使人们能够在虚拟世界里逃避现实的烦恼和压力,获得无深度的简单快感:
农民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一种新媒介,而是积极、能动地展开数字实践,并以此构建村庄的闲暇生活,寻找生活的意义。在国家的政策推动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方位地带动了中国乡村的发展,其中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带来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不仅提高了农业效率,还为农民创造出更多的闲暇时间。如今,闲暇时间的日常化与新的娱乐方式彼此契合,构成了数字时代新农村的生活风貌。人们居住在一个现实与虚拟交叠的生活场景中,实现了视频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视频化。另外,全球市场的流动带来个体主义的消费观念和自我意识,人们推崇享受生活。当前的中国农村正在深度转型,重大的社会变化塑造了国家整体的精神面貌,影响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心态,也反映出乡村发展的新态势。农民对新技术的采纳,体现出人们的自我定位,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心态和观念变化。
四、客观化:空间场景的生产与竞争
“客观化”强调新技术在生活场景内的摆放位置和相应的文化品位,而场景则包含移动的空间和媒介生态系统。在人们的数字生活中,手机的物理位置表现为随处可及性,随着场景的嵌入生产出多样的生活空间。另外,抖音的多媒体属性还使其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占据优势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手机和抖音作为一种人们的伴侣媒介,与其他物质实体一同构成人们日常活动的场景。人们常将手机放在家内任意位置,可能是灶台、饭桌或窗台。当人们迈出家门后,手机便放置在衣服口袋或包里:手机以其移动属性塑造了社会空间内的多个媒介场景,例如在灶台旁一边做饭一边刷抖音,斜躺在农村的土炕上刷抖音,又或者在户外随手打开抖音。作为一种被放置的资源,手机和抖音自然地嵌入个体的生活中,创造了人们彼此间观看和表达情感的方式。新技术的出现生产出了另类的生活空间,是人们对空间的无意识改造,更是一种空间实践。
抖音依托于手机这类移动媒介,具有多种技术可供性,包括广泛性、精准性、社交性以及多媒介性等优势。从整体来看,抖音融入原有的媒介生态系统之后,给电视和微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抖音还满足了注意力稀缺下人们对信息的非嵌入要求:人们对抖音内容“走马观花”式的观看方式,与劳动过程相契合,因此无意中为抖音在媒介系统内树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五、合并:媒介时间与社会时间的耦合
“合并”指新技术嵌入家庭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当一项新技术成为日常安排的一部分时,便失去了神秘感,也意味着驯化的成功。在当前的媒介化社会里,媒介与人的深度连接,使彼此互为对方的延伸。通过耦合媒介时间和社会时间,抖音实现对日常生活任意时间段的嵌入。
刷抖音日益成为人们打发闲暇时间的首选,填充进人们固定的生活安排中。人们的生活作息被媒介所牵引,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表现为媒介时间自然地与生活节奏交融在一起:
抖音通过算法给用户推荐感兴趣的内容,使人们在指尖刷一刷的操作下,进入到一种“心流体验”中。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2019:64)。媒介在延伸人体的某一部分时,也会削弱或“截除”其他部分,导致其他感官的“麻木”。田野观察发现,人们休闲时会坐在街道两侧刷抖音,无视响亮的外放声音。在家庭聚会中,人们坐在土炕上,也会各自找个位置以舒服的姿势刷抖音,保持沉浸式的感官投入状态。间或有人挑起话题,简短地聊一阵后又沉浸到自己的视觉世界中去。在刷抖音的过程中,人们脱嵌于当下的社会场景,实现感官的重组和一种专注的时间投入。戈夫曼的“自涉入”概念认为,个体的身体或与其相关的客体,常常是他涉入的对象,尤其是一些指向自我的、自我专注的人体活动(2017:65-66)。刷抖音作为一种自涉入的快乐实践,使人们在视觉和听觉中享受一场感官盛宴。概言之,抖音视频实现了物理时空和虚拟时空的互嵌,在用户的身体和感官环境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连接。
“媒介记忆”(media memory)指利用或通过媒介塑造关于过去的共同记忆,以及跟媒介有关的记忆(Neiger et al., 2011:1-2)。在驯化抖音的过程中,人们将这一视频平台作为展示自我的工具,记录日常生活和重要的生命事件。作为一个承载着意义的媒介物,抖音汇聚起一个乡村的媒介记忆,并构建了一种历史叙事。
“上抖音”通常是他们表述这一行为的话语,也是一种与身体相关的实践。人们通常在抖音这一虚拟空间中记录自己的生活,包括日常劳作、乡村风貌、特殊日子等:人们还喜欢上传乡村的集体活动和个人生命事件,比如村内舞蹈队排练的片段,以及人们在结婚、生子、升学、生日等时刻相聚的场面。
通过个体记录,关于乡村的媒介记忆被生产出来,而生产者是未经专业训练、自己摸索习得的一些农村中老年人。人们在抖音短视频中的公共参与和表达,是一种平民的记忆生产,不仅带来了集体性的地方视觉景观,还构造了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史。在见证和再现生活的媒介实践中,拍摄和上传视频成为一种社会仪式,在网络中宣扬平民的立场,共享和强化了展示自我的合法性。人们在抖音中完成仪式化的展示,使媒介时间与社会时间深度耦合。
六、转换:新主体和新乡村的意义生成
“转换”涉及新技术怎样成为人们身份界定的一部分,并在公开场合中展演出来。人们将短视频作为连接外部的窗口,对短视频的驯化实现了家庭/个体与乡村的意义转换,生成了新主体和新乡村。
抖音促进了乡村内私人生活的变革,塑造了以参与者和网络微名人为代表的新时代主体。短视频使人们习惯于屏幕中的生活,虚拟共在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基于此,短视频促进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曾经“沉默的大多数”如今拥有了记录自己和他人的权力,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潘祥辉,2020)。
拥有抖音之后,人们会主动关注身边人的动态,参与到熟人的生活中去。本文称他们为“积极参与者”:抖音算法通过用户的授权可以定位到具体的位置,并且推送同一区域内人们发布的视频:抖音以位置信息激发了村民们凝视他人的主体意识。在凝视与被凝视之间,人们穿梭于不同的生活空间内,通过观望、参与的方式来拉近彼此的距离。作为重要的可见性媒介,抖音使人们进入到一个多数人看多数人的“对视社会”,彼此窥视(刘涛,2015),并建立起一种周身环绕的亲密感。
另外,短视频这一新媒介带来了人们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改变,促进了许多农村微名人的出现:借助美颜、道具、文字和音乐等功能,人们上传自己唱歌、跳舞和模仿他人的视频。在抖音上的自我表露和个人表演,拓宽了人们的交际圈,还使经常上传视频的人成为本地的网红:抖音还构成了一个情感的空间。通过整饬后台并检查前台的表现,人们完成了对虚拟空间内“想象的受众”的情感劳动,由此带来了人们对自我的物化:通过从视频中挑错来实现自我核查,主体与媒介对应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人们的劳动成果也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并反过来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
人们无时无刻打开手机刷短视频的行为已成为一种媒介景观。抖音在家庭和乡村之间的跨越,以流动的方式为乡村群体打造了一个融合了血缘、地缘和虚拟友谊关系的地方共同体,同时也为个体创造了专属私人空间。如梅罗维茨(2002:7)所言,媒介可以容纳和拒绝参与者,既能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带来排斥和隔离,能加强“他们和我们”的感觉,也能消除这种感觉。
抖音以“同城”和“通讯录推荐”的功能让可能认识的人彼此关注,促进了半熟人社会内人们的相互联系。此种线上的熟悉感也将网友们发展成为线下的熟人:Elias提出“型构”(figurations)概念,指个体与他人进入一种相互编织的过程,伴随着一定的社会秩序,人们之间建立起相互拉扯、相互制约的关系(1978:116)。抖音里的行动者也构成这样一张网络,观看者和展示者之间互相成就,互有关联,组成了一个本地共同体。在共同体内,人们积极维护一种“副社会交往”的互动规范,包括回关、点赞、评论等管理好友的策略。“有关必回”、认真给对方评论是人们对线上交往原则的共识:人们以点赞与回赞的互动结构来维护一种“泛好友”的关系。
另外,抖音为人们开辟出专属的私人空间,带来原子化的媒介使用:驯化抖音是一种个体的媒介实践,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人们可以随时遁入私人空间里,实现私人空间对公共空间的强势入侵。田野观察发现,无论是在家庭内还是街道两侧,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短视频总会时不时地闯入人们之间。个体与抖音之间构成了一组空间上的具身关系,而与空间内的其他人构成他者关系。在抖音这一排他性的空间内,个体主动地与人群隔离开,参与到指向私人事务的社会情境中去。人们固然可以共存于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内,但若实现两者间的切换,需要一个质询或召唤,而突然的召唤带来的是短暂的迟疑和迷惑。
七、反向驯化:使用者与抖音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
驯化过程不总是顺利的,包含了人们对新技术的排斥和选择性使用。本文将“反向驯化”视为驯化过程的一部分,相关策略包括撤回和减少技术的使用(Karlsen & Syvertsen, 2016)。区别于主体拥抱新技术这一驯化过程,反向驯化指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对新技术持抵抗和退缩的态度。研究发现,人们的媒介使用始终受到劳动和身体状况的限制,因此人们会主动地反向驯化新技术。
积极、自主的调整策略,意味着人们有意识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以避免技术破坏正常的生活实践。
抖音的长时间观看一定程度地损伤视力,因此人们只能间歇性地使用抖音。人们对抖音的驯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由最初的十分入迷转变为与抖音保持既亲密又刻意疏远的关系。人与技术的深度连接构成了技术的自我隐退,但是当技术出现故障时,显著性、突兀性和无可回避性就使得“上手之物”变为“在手之物”(戴维·J·贡克尔,保罗·A·泰勒,2019:124-130)。而抖音带给人们身体上的知觉也直接影响着用具的在手性,使技术以突兀的方式显现而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这种反思和驯化行为均体现了使用者的能动性。
Scheerder等人(2019)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互联网的发展不太感兴趣,也没有太多反思性的立场。但是本文对边缘人群的自主意识持肯定态度。事实上,部分人群能够意识到抖音带给生活结构和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并有意地减少、调整对抖音的使用,体现了农民从长久生活经验中生发出的实践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使用抖音的习惯性操作中,人们没有注意到新技术带来的异化力量。正如学者们所言,人们在认识抖音时展现出极大的理性限度,终归无法摆脱技术对自身的操纵与影响(李红艳,冉学平,2020)。
八、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抖音为例,考察了乡村群体对短视频的理解,短视频如何融入乡村,以及带来什么影响。研究发现,人们对抖音的占有体现出进步观念和享乐心态,这与数字乡村政策和社会变迁有着密切联系。抖音渗入日常生活的结构,建构了新的时空情境,不仅生产空间场景、争夺媒介系统内的优势地位,还通过耦合媒介时间与社会时间,促使人们开拓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抖音还转换了新的主体身份,促进积极参与者和微名人的出现,并塑造了乡村共同体和私人空间这类新的交往场景。此外,人们对新技术的使用还体现出一种矛盾的行为,表现为在反向驯化中与抖音形成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
本文以中国乡村的新媒介使用拓展了驯化理论的应用语境。首先,在中国的乡村现实中,人们的新媒介驯化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体现了“家—乡村—国家”一体的机制。对驯化理论的理解还需要结合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例如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变迁带来人们进步主义观念和享乐心态的融合。第二,乡村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提醒我们注意驯化主体内部的差异性,例如观看者和展示者之间各自不同的行为实践,以及新技术使用对乡村群体内部进行的界限区分。第三,Silverstone等人的“驯化”理论重视家庭内的道德经济,而本文更侧重乡村的休闲文化实践。传统乡村与现代新媒介技术之间的相遇和碰撞,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驯化过程中,农民群体的自洽逻辑,使他们过着舒适和随性的生活。
媒介批评家们一贯反思新技术带来的影响,诸如对电视和手机等媒介泛娱乐化倾向的控诉。此类娱乐有罪论的观念也延续到短视频中,然而本文更赞同马克·波斯特(2000:6)对现代型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的批评,即未加深入地考察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这一类态度会妨碍研究者探讨媒介对人们而言的巨大吸引力,也不能真正地理解媒介和人。当前乡村群体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已然是一种大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视频成瘾的负面影响,而要考察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探究人们驯化媒介的动机和相关策略。农民在闲暇生活中驯化新媒介,体现出人们能动的主体性和内嵌于乡村社会情境的生活哲学。
本文关注日常生活的新媒体实践,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展开回答。抖音的情感偏向对乡村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异化效果?在驯化抖音的同时,用户无意中完成了数字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乡村群体如何看待免费劳动和隐私泄露?此类问题有待后续探讨。■
参考文献:
曹钺,曹刚(2021)。作为“中间景观”的农村短视频:数字平台如何形塑城乡新交往。《新闻记者》,(3),15-26。
CNNIC(2021)。《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最后访问:2021年9月18日)。
戴维·J·贡克尔,保罗·A·泰勒(2019)。《海德格尔论媒介》(吴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抖音短视频(2021)。《2020抖音数据报告》。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444630236_120543798(最后访问:2021年9月18日)。
欧文·戈夫曼(2017)。《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何志武,董红兵(2021)。短视频“下乡”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重构——基于一个华北村庄的田野调查。《新闻与传播评论》,74(3),14-23。
李红艳,冉学平(2020)。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凸显”——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思考。《新闻大学》,(2),94-101+122-123。
刘娜(2018)。重塑与角力:网络短视频中的乡村文化研究——以快手APP为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6),161-168。
刘涛(2015)。美图秀秀:我们时代的“新身体叙事”。《创作与评论》,(12),92-94。
刘胜枝,安紫薇(2019)。呈现与建构:直播、短视频中小镇青年的形象分析——以快手、抖音平台为例。《中国青年研究》,(11),37-43。
刘天元,王志章(2021)。稀缺、数字赋权与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基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田野调查。《中国农村观察》,(3),114-127。
马克·波斯特(2000)。《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19)。《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55周年增订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尼尔·波斯曼(2019)。《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
潘祥辉(2020)。“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国际新闻界》,42(6),40-54。
齐格蒙特·鲍曼(2017)。《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2012年版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贝尔纳·斯蒂格勒(2019)。《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沙垚,张思宇(2019)。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新闻与写作》,(9),21-25。
吴国胜(2009)。《技术哲学讲演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琳琳,徐琛(2020)。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勾连”:陕西省×家村村民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10),135-139。
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敦福,路阳(2021)。城市社会学视野下土味文化与城乡关系再生产——基于布迪厄的误识理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3(2),91-97。
周孟杰,吴玮(2021)。三重勾连:技术文本、空间场景与主体行动——基于湖北乡村青年抗疫媒介实践的考察。《中国青年研究》,(1),78-86+111。
周敏(2019)。“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中国青年研究》,(03),18-23+28。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14(2)115-132.
De Schutter, B.BrownJ. A.& Vanden Abeele, V. (2015). The Domestication of Digital Games in the Lives of Older Adults. New Media & Society17 (7)1170-1186.
De Reuver, M.NikouS.& BouwmanH. (2016). Domestication of Smartphone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A Quantitative Mixed-method Study.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4 (3)347-370.
Elias, N. (1978). What is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uanC. Y.Tang, J. M.& Wang, M. (2019). The Family Politics of New Media Domesticati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Mobile Phones’ Influences on Rural Adolescents’ Socialization in a Central Chinese Tow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0 (1)1-19.
HaddonL. (2003). Domestication and Mobile Telephony. In J. E. Katz (Ed. )Machines that Become us: The Social Context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New BrunswickNJ: Transaction.
HartmannM. (2013). From Domestication to Mediated Mobilism.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1)42-49.
Helle-Valle, J.& Slettemeas, D. (2008). ICTs, Domestication and Language-games: A Wittgensteinian Approach to Media Uses. New Media & Society10 (1)45-66.
Karlsen, F.& SyvertsenT. (2016). You Can’t Smell Roses Online Intruding Media and Reverse Domestication. Nordicom Review, 3725-39.
Khvorostianov, N. (2016). Thanks to the Internet, We Remain a Family: ICT Domestication by Elderly Immigra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Israel.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16 (4)355-368.
Leong, L. (2020). Domesticating Algorithm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cebook Users in Myanmar. Information Society36 (2)97-108.
Liu, KZ. (2020). From Invisible to Visible: Kwai and the Hierarchical Cultural Order of China’s Cyberspace. Global Media and China5 (1)69-85.
MartinezC.& Olsson, T. (2021). Domestication Outside of the Domestic: Shaping Technology and Child in an Educational Moral Economy. Media Culture & Society43 (3)480-496.
Matassi, M.Boczkowski, P. J.& Mitchelstein, E. (2019). Domesticating WhatsApp: Family, FriendsWork, and Study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21 (10)2183-2200.
McDonaldT. (2015). Affecting Relations: Domesticating the Internet in a South-western Chinese tow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18 (1)17-31.
MiaoW. S.& Chan, L. S. (2021). Domesticating Gay Apps: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of the Use of Blued Among Chinese Gay Me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6 (1)38-53.
NeigerM.Meyers, O. & Zandberg, E. (2011). On Media Memory: Editors’s Introduction. In M. Neiger, O. Meyers & E. Zandberg (Eds)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NimrodG. (2016). The Hierarchy of Mobile Phone Incorporation among Older User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4 (2)149-168.
QuandtT.& von Pape, T. (2010). Living in the Mediatope: A Multimethod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ociety26 (5)330-345.
Scheerder, A. J.van DeursenA. JAM& van Dijk, J. AGM. (2019). Internet Use in the Home: Digital Inequality from a Domestication Perspective. New Media & Society21 (10)2099-2118.
Silverstone, R.Hirsch, E.& Morley, D. (199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In R. Silverstone &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London: Routledge.
WuS. W. (2021). Domesticating Dating Apps: Non-single Chinese Gay Men’s Dating App Use and Negotiations of Relational Boundar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43 (3)515-531.
徐仁翠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