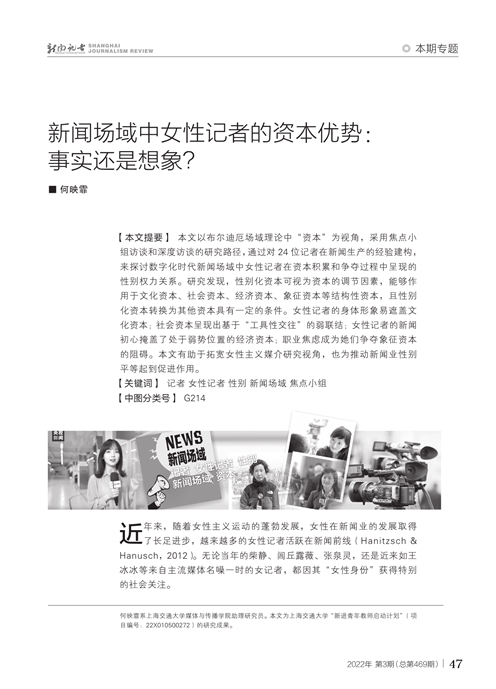新闻场域中女性记者的资本优势:事实还是想象?
■何映霏
【文本提要】本文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资本”为视角,采用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的研究路径,通过对24位记者在新闻生产的经验建构,来探讨数字化时代新闻场域中女性记者在资本积累和争夺过程中呈现的性别权力关系。研究发现,性别化资本可视为资本的调节因素,能够作用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等结构性资本,且性别化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本具有一定的条件。女性记者的身体形象易遮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呈现出基于“工具性交往”的弱联结;女性记者的新闻初心掩盖了处于弱势位置的经济资本;职业焦虑成为她们争夺象征资本的阻碍。本文有助于拓宽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视角,也为推动新闻业性别平等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记者 女性记者 性别 新闻场域 焦点小组
【中图分类号】G214
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在新闻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记者活跃在新闻前线(Hanitzsch & Hanusch, 2012)。无论当年的柴静、闾丘露薇、张泉灵,还是近来如王冰冰等来自主流媒体名噪一时的女记者,都因其“女性身份”获得特别的社会关注。
记者职业对于女性而言,在“表达沟通能力、形象气质、富有同情心、易于被采访对象接受”等方面具有天然的性别优势(Van Zoonen, 1998;尤红,2020)。相比较其他行业常出现男女比例的失调,当下新闻业的女性进入门槛已经降低,女性记者队伍愈发壮大(ASNE, 2016;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9),甚至连新闻报道在主题上也逐渐趋向“软性化”风格,呈现出符合女性传统的文化期待(Van Zoonen, 1998;王海燕,2012),这些现象似乎都在指向女性比男性更能胜任记者这份工作。但在看似光鲜热闹的表象下,上述推断究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种职业
想象?
有研究表明,新闻场域过去镶嵌着明显的性别逻辑,女性记者的职业发展比男性更为艰难,所面临的职业挑战不仅是因为她们在工作中的表现,而且因为她们的性别本身(Gill, 2007:20; de Bruin, 2000)。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曾视“性别”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新闻场域被视为权力场的一部分,其权力关系又能决定人们行动(本森,内维尔,2017:3),这为阐释性别权力关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布尔迪厄,2017:52; Djerf-Pierre, 2005)。基于此,本文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资本”为研究视角,聚焦一线记者的新闻生产经验,通过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获取一手材料,并将女性记者看作是持有各类资本的行动者,她们不断争取“资本”兑现,目的是实现“资本”增值,以此来审视新闻场域中性别权力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构型”。场域决定了人们行动的基础,场域中的行动者(agents)所处的相对位置和各种资本之间分配的关系,都被加注了各种规则、权威和价值观(本森,内维尔,2017:7-8)。若以不同场域相交或重叠的方式,能够重构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并重塑行动者的身份。
新闻场域是各种不同力量之间博弈的场所,它用权力结构的隐喻代替了新闻编辑部这一物理空间,更好地展现了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布尔迪厄,2020:180)。随着中国媒体机构的转型,学界开始将“新闻场域”作为分析工具来阐释中国新闻生态和行动者的变化。在张志安(2018)看来,主流化媒体转型中的新闻场域与政治、经济、专业控制因素相互影响。曾丽红(2014)将中国调查记者看作是新闻场域的行动者,并从话语惯习、场域结构配置、资本去探讨他们的角色实践的深层逻辑。陈立敏(2021)认为作为行动者的前媒体人通过“职业惯习的延续、创业资本的获取”的方式参与到新闻实践中。
同样,研究者们也常用“场域”和“资本”概念去探讨微观层面中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机会和职场生存逻辑,用以解释新闻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譬如,Tsui和Lee(2012)研究发现香港女性记者之所以离开新闻业,原因在于女性记者所在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之间相互叠加而产生冲突。Djerf-Pierre(2005)指出,女性记者可利用自身资本种类和数量来制定相关的策略,与男性记者一同竞争。Zuiderveld(2011)发现非洲新闻机构中,成为媒体精英的女性记者可视为一种积极的资本,但大多数女性记者集中于中下层,构成了新闻机构的“天鹅绒贫民区”。
可见,资本是一种稀缺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有效资源。场域内蕴藏着各种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等。文化资本是文化能力的体现,包含教育文凭、职称、文化能力和文化品位等内涵;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总和,包括社会关系本身以及关系所带来的资源集合体;经济资本指财产资源可直接转换成金钱,通过产权的制度化方式得以传承和保障;象征资本又被称为“符号资本”,指被制度化公认的、被合法化的权威、地位和名望(本森,内维尔,2017:7)。同时,不同资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文化资本可间接转化为其他三种资本,但竞争与转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象征资本往往联合其他几种资本,凸显其整体资本实力,象征资本的强势能使其他资本产生直接交换(本森,内维尔,2017:7-9)。
场域又是各种力量斗争、协商的场所和结果,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领域若想拥有一席之地,必须具有该领域最有价值的资本(McNay, 2000:4;本森,韩纲,2017)。因此,如果想要成为场域强势的竞争者,需审视自身原来的位置,并调整行动策略参与到资本的争夺中,构建自己独特的职业生涯(Moi, 1999)。
沿着布尔迪厄的思路,Djerf-Pierre(2005)和Moi(1999)认为性别也可以看作一种特定形式的资本,故称为“性别化资本”。通常,象征资本依赖于人们的感知和评价,而性别文化又塑造了这种感知和评价。在男性话语为核心的父权制文化背景下,性别差异被看作一种“象征暴力”。因此,在一定条件和情境下,性别化资本可视为一种正向或负向资本,影响着记者象征资本的积累。然而,对于女性新闻工作者来说,性别通常表现为负向资本,这时容易抵消女性记者的文化、社会、经济等资本,或需要通过获得其他形式的正面资本去弥补这种负向资本。正如Djerf-Pierre(2005)的发现,处于中上阶层以上的瑞典女性记者,其文化和社会资本水平都远高于男性,足以抵消性别化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
过去学者们主要从不同时期女性记者的职业特征去研究。宋素红(2003)认为始于晚清后的中国第一代女性新闻记者为了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实现了自我身份与角色意识的结构性转变。冯剑侠(2012)指出民国时期第二代女性记者被外界看成是“交际花”或“无冕皇后”的职业身份。陈阳(2006)发现改革开放之后,媒体转型中的女性记者易受到“职业意识、职业常规和新闻生产的体制情境”的影响。也有学者从女性记者的职业发展障碍去研究。王海燕(2012)认为随着市场化传媒机构规模不断扩大,促使女性工作者数量增加,但否定了新闻业走向女性化趋势的观点。王海燕(2016)进一步指出女性调查记者的职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的原因是“社会建构、职场建构和自我建构”三方面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所致。North(2009)发现美国女性进入新闻行业的时机与男性大致相同,但她们的职业生涯却非常短,更容易离开新闻业。闾丘露薇(2021)发现香港女性记者性别意识不强,新闻业中仍然存在着结构性性别不平等。另外是从工作与家庭之间关系去研究。研究发现,女性记者长期受制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容易引发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角色冲突,生育后的女性记者常出现职业焦虑(Tsui & Lee, 2012; Kim, 2006; Rivera, 2007)。最后是从女性记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去研究。有研究表明,女性记者在新闻编辑部总是处于边缘位置,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或性骚扰,为了不降低自己的专业形象,这些女性记者选择保持沉默(Sooyoung & Davenport, 2007;全媒派,2018)。
综上,部分研究背景发生在中国之外,由于全球范围内性别平等程度不一,性别呈现出的社会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因素都渗透到新闻领域中,因此,亟需深入中国新闻机构女性记者的新闻生产经验,来探讨新闻场域中性别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此外,既有研究大致都在前数字化时代进行,忽略了技术赋予新闻业的时代变化。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以“采编、制作和发行”为基本新闻生产流程正逐步实现数字化(Tandoc & Ferrucci, 2015),记者的新闻生产节奏、工作方式、工作量等新闻常规的感知发生着变化。因而,本研究的前提是在数字化的语境下,并结合男性记者样本作对比,将男女记者置于互动平等的关系之中,让性别概念更具参照性。鉴于此,数字化时代中国女性记者的身上,这种基于性别化的资本如何被看待或被使用?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对其他结构性资本构成促进或抵消?都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二、研究方法:焦点小组与深度访谈结合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以焦点小组访谈为主、深度访谈为辅。焦点小组访谈是一种自然无结构的小组座谈形式,针对某一主题展开自由讨论,以获得细节上的描述性数据。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激发参与者的灵感以及带动议题的讨论氛围,从自由的小组讨论中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通过对受访者所表述的观点进行观察与分析,能表明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内在意涵,更好地补充、扩展和深入挖掘数据之外更深层次具体的影响,也有助于研究者产生分析性主题(方蒸蒸,程晋宽,2017)。
本次焦点小组访谈于2020年4月至8月之间进行,通过滚雪球方式进行招募,招募对象为从业经验超过三年的记者和编辑,主要来自报社、杂志社、通讯社、电视台等媒体类型。参与者共有24人,包括12位女性记者和12位男性记者。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文末附录,编号女性为“F”,男性为“M”。
为了避免异性记者在场时不愿透露内心真实看法,本研究将同性记者放在一组,以便加强同性记者之间的话题沟通。首先,确认线下和线上2个焦点小组测试室,将6名男性参与者为一组,6名女性参与者为一组,共4个焦点小组,其中,有两个小组需在线上的微信群进行讨论;其次,研究者作为焦点小组的主持人,先介绍本次小组讨论的主题、研究目的、数据用途以及匿名化的处理方式,然后让参与者们填写基本情况,如年龄、教育程度、单位信息、从业时间等信息;再次,围绕“男女记者双方在采访中的优势和劣势”等话题展开讨论,平均每组访谈约为40—60分钟。在讨论中,每个参与者都需积极发言,主持人会根据现场发言情况随机点名,以此保证焦点小组的讨论质量。每当一个问题讨论结束后,主持人会以“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吗”进行提问,如果没有,则再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在结束焦点小组后,研究者与焦点小组中部分需要再深入讨论的参与者单独进行约30分钟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以此获取焦点小组中未深入展开、更有价值的信息。
三、“权力的游戏”:女性记者的资本积累过程
“场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的较量是基于‘资本’的逻辑”(本森,内维尔,2017:5)。当女性记者携带初始资本入场后就开始了不同数量和种类的资本积累过程,而性别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对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结构性资本产生促进或抵消的作用,最终决定了女性记者在新闻场域的关键位置。
首先,学历是进入新闻行业的第一张“入场券”。文化资本作为记者积累资本的初始位置,须通过长期的个人努力才能获得。研究发现,女性记者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同等学历条件下仍然会优先录取男性,反而加剧了女性之间的竞争:(F02)
其次,文化资本与天然的“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女性记者的新闻专业水平往往会以“女性身体”去建构,如女性形象、女性气质(温柔、细致、善于沟通、亲和力、同理心),使得她们一开始就能迅速与受访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不易被拒访,还能获取更多的采访机会,甚至她们可以利用自身外貌的优势,增加其择业便利:(F10)
然而,若一份职业过分强调以“青春”为特征,也会为女性记者带来困扰,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这也是为什么女性记者的职业生涯和“吃青春饭”的职业特征紧密关联,而男性记者普遍认为是“越老越吃香”。此外,女性记者在采访异性时,容易被言语调侃或窥探隐私,如F03曾在采访中被受访者介绍相亲对象,她只能尴尬地婉言拒绝。
再次,文化资本还凝结在新闻作品的价值,体现于记者的新闻能力、新闻专业知识水平等。由于新闻记者职业的特殊性,需经常外出采访去求证消息来源并获取新闻线索。对男性记者而言,会有“体能”上的优势,如“灾难性报道”。在采访时更强调专业权威性,在遇到拒访时一般不会放低身段,反而会据理力争,敢于提一些敏感、攻击型的问题,或继续寻找其他受访者,来取得可靠的信息。但他们也抱怨自己缺乏女性外在优势而被拒访:(M06)
文化资本在转化其他资本时具有隐蔽性。例如,一位国内名校毕业的记者F04,加入了一家知名财经媒体担任记者,作为新进入者,领导建议她可以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机构和群体环境中受益,挖掘学历优势背后所带来的隐藏社会资源。尽管一段时间后她并没有与受访者形成强互动,也没有获得收入和职位方面的提高,但她认为采访资源的开拓反过来再次促进了文化资本的流动(如拓宽视野、扩充知识面、为新资源开辟机会)。
甘斯(2009:146)认为记者和消息来源有着“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体现在特定的“采访线”(beat)或负责特定类型的报道。因而,新闻场域中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从业者的采访条线和媒体资源,以及拥有的各种人际关系、地位、信誉等。
Putnam(2000)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及其相关的互惠规范,可分为“桥接”(Bridging)和“凝聚”(Bonding)。“桥接”强调社交广度,具有包容性,有利于拓宽交友圈。“凝聚”强调社交深度,人际关系更牢固。研究发现,这种通过“采访”积累的人际关系建立的社会资本,呈现出由弱到强的联结关系:“以媒体平台名义建立的工具性交往、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工具性交往、以个人名义建立的情感性交往”。工具性交往强调社交广度,记者尽可能拓宽人脉,获取各类采访资源。情感性交往强调社交深度,记者为受访者提供长期的情感支持,形成一种强联结:(F09)
第一阶段,以媒体平台名义建立的工具性交往中,由于采访频次低,记者和受访者之间是一种趋于松散的“弱联结”,双方因工作需求而产生交集,但这种关系只有暂时的,一旦记者失去身份头衔,双方链条就自然断开;第二阶段,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工具性交往,是一种“由弱到强”过渡的联结,记者的专业口碑经过长期沉淀,逐渐受到外界认可和信任,但双方关系可能还是停留在长期合作的对公关系,为了保持新闻客观性,记者和受访者彼此都会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公事公办、公私分明”成为大部分记者主要社会交往方式;第三阶段,是以个人名义建立的情感性交往“强联结”关系,记者和受访者互动加深,形成情感纽带,此时双方以“趣缘”和“情感”为联结成为可能:(M3)
同时,社会资本的强势可以转换为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如果一位记者通过积累采访资源来增加自身的社会资本,拓宽记者的人脉关系,日后为记者提供职业转型机会,有利于记者“资源兑现”。尤其是采访到“有名望”的采访对象,更强化了文化资本(新闻专业能力)和象征资本(如“有面子”):(M12)
女性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女性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媒体平台名义的“工具性交往”,呈现出一种“弱”联结。性别观念在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中相互交织,造就了女性记者不同的性别意识,决定她们差异化的交往方式。若采访对象的性别多为异性,女性记者在与受访者互动过程中会出于自我保护,有意地设定一些界限。而男性记者虽未能在最初与受访者迅速建立关系,但在后期交往中,却因同性别无障碍的沟通,更容易建立紧密关系。
F07和她的丈夫都是记者,他们供职于不同的媒体机构。谈及社会资本的积累上,她认为自己很缺失。而她的丈夫长期与采访对象交往紧密,特别注重维护与他们之间关系,私底下经常交流很多行业信息和观点。在他们结婚宴请当天,F07的丈夫还主动邀请了曾经采访过的朋友。在她丈夫看来,受访者也可以成为私密朋友,为他建立起新的社会纽带。(F07)
第二,女性记者往往缺乏进入非正式的社交网络的机会。出差对于记者来说是家常便饭,免不了一些交际应酬,男性可以通过“一起抽烟和喝酒”作为互动式开场,但如果与受访者接触只能以“喝酒才能完成信息获取及社交”的方式,则会让女性记者受到很多阻碍,也会让新闻采访踏入“失范”的边缘。实际上,女性在人际交往的不顺畅并非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不是不能喝酒,而是没必要喝酒”(F10),女性记者常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喝酒,而一部分男性也认为“女性喝酒”违背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可能让外界误以为她们是撇开“家庭责任”去参与交际与应酬,容易受到家人的指责:(F06)
第三,婚姻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联系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而女性价值的体现可通过丈夫已有地位来增强自己的社会资本(谭琳,李军峰,2002)。如果产生有声望的姻亲关系,既是一种社会资本,又可能提供象征价值(布尔迪厄,2017:121)。对于一些女性记者来说,记者是比其他行业更能快速积累人脉资源的职业,这也为她们结识另一半提供新的契机,通过婚姻关系可以再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资本:(F11)
新闻行业的收入待遇整体在走向衰落。有数据显示:超过八成的记者月收入在1万元以下,近六成的一线新闻记者表示“收入待遇”因素将会是离开新闻业的主要原因(美通社,2016)。即便记者再有饱满的新闻热情,一旦不能“酒足饭饱”,也无法支撑他们的“新闻理想”:(F04)
研究发现,男性记者背负更沉重的家庭经济压力,更看重一份职业的薪资。当他们认为记者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经济资本出现匮乏时,便会选择离职。M08来自于一家体制内媒体,他从某重点大学毕业后跟随女朋友来到了北京,当时他作为应届生可以申请北京的户口指标,但需要与用人单位签约5年时间,否则违约需要缴纳赔偿金,但在这五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在某个城市扎根立足之后(如“拿户口”),记者对经济资本也有着持续的期待:(M08)
有研究从77份媒体人在互联网(2003—2016年)发布的离职话语中,发现男性明显占多数(胡沈明,胡琪萍,2016),且多数离职媒体人选择通过传媒创业等方式获取创业经济资本(陈楚洁,2018)。可见,男性记者的离职动机与经济资本的缺乏息息相关:(M05)
与此同时,女性记者坚守初心,怀揣着强烈的新闻理想,总是将新闻工作看作一份重要使命,而不是一种获得个人财富的方式。F12毕业于一所国内顶尖名校,非常热爱新闻事业。毕业后她从一家广州的知名媒体回到上海工作。在她看来,来自头部媒体的记者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对于同等学历其他行业来说,记者收入相对偏低,之所以还有这么多学习新闻专业的学子放弃优渥薪资来选择做记者,大多源于对新闻的热爱,但这种热情会因现实条件而不能持续。她坦言自己是上海本地人,加上女性的身份,暂时不需要考虑太多经济压力,才能支撑着她一直做记者:(A12)
另有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女性记者涌入新闻界的人数虽在递增,但女性长期在决策层中代表性不足,集中于中下层的她们收入实际上比男性少(Ross, 2004; Beam & DiCicco, 2008)。总体而言,在传统媒体衰落的背景下,尽管记者整体收入下滑是影响男性记者离职的关键因素,而女性记者选择保持原有工作状态或许因为更看重新闻理想,但这些表面现象都无法改变女性在新闻机构整体收入偏低的事实。
新闻界的竞争实际上是象征资本的竞争(Carlson, 2015:67)。Schultz(2007)指出新闻场域中的象征资本主要表现为“专业经验、职务、新闻条线、新闻奖项”等。Djerf-Pierre(2007:43)认为“成功、声望、地位以及构成‘好’新闻的标准”,都能决定新闻业的话语权。研究发现,女性记者对自我职业认知与晋升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由于性别因素带来的职业焦虑,影响着她们象征资本的得失。
第一,父权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性别刻板印象,一方面会让女性记者容易卷入“性别气质表演”,既要扮演迎合男性审美趣味的角色,又要扮演自我客体化的角色;另一方面会让女性在获得成功后受到外界“凝视”。外界默认女性领导容易被家庭牵扯精力,或留给别人“软弱”的印象(如“好说话”),或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如“女强人”)。女性记者想要在新闻业取得成功,要么依附男性,要么成为“男性”,女性不得不承受沉重的性别压力和角色偏见,甚至性别偏见就存在于女性群体,她们常作为男性的“同谋”参与性别权力的斗争中:(F05)
第二,生育职责仍是女性记者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家庭等因素叠加,女性记者的职业生涯比男性更短,触及职业天花板的年龄更早,男性记者便会趁机“弯道超车”,不断积累比女性记者更多的工作经验,获得比女性记者更多的象征资本:(F09)
对于很多女性记者而言,选择记者工作最主要因为时间灵活、能兼顾家庭生活,但媒介融合策略带来新闻工作节奏的加速,新媒体端需要保持24小时在线状态,迫使女性记者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不断重叠,她们的私人生活时间不断被侵蚀,即便在家里也要跟进报道、更新新闻快讯,而无法全身心照顾孩子。此外,部分新闻机构也对记者的数字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让他们更新自身数字化技能和数字素养,但女性记者由于年龄增长和繁忙的家庭事务,令她们无法脱身去学习,进而造成内在的无助感:(F02)(F08)
第三,女性记者对自我职业认知产生“认知不协调”。新闻场域中的女性记者性别意识普遍不高,她们在评估自身能力与实际获得某种资本竞争力时容易产生出“认知不协调”,会造成她们“言行不一”。在看似“公平”的名义下,有些新闻机构将“奖项”作为一种“替代性”补偿,纳入女性记者正面的象征资本中。(F02)但竞争意识薄弱的女性记者对自我认识仍处于“被动”状态,在她们看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F03)和踏实工作(F01)比拥有职业晋升空间更重要。与此同时,她们认为职业晋升只与个人能力有关系,与性别无关。单论“能力”来说,很多女性记者认为自身实力并不逊于男性记者,但在竞争某些职位时,女性记者开始否定自己,并以“自我劝服”和“情感疏离”的途径去缓解因认知不协调带来的不适。由此可见,在性别权力争夺中,当负面的性别化资本最大化时,是无法有效地转换其他资本带来的效应,女性记者也会被边缘化:(F01)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为理论基础,全面阐释了新闻场域性别权力之间的关系,总结了数字化时代作为行动者的女性记者的新闻生产经验和生存逻辑,侧面展现了中国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数字化时代带给记者新的挑战,“技术赋能的媒体趋势、新闻常规的多重调整、公共与私人空间重叠”等一系列变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性记者适应媒介转型环境中的能动性(生存空间挤压、平衡家庭关系等)。此外,尽管中国的女性记者数量和地位不断提高,但她们自身的性别意识普遍不强,不易察觉到新闻场域中负面的性别化资本,忽略了可能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这与前人发现有所相似(闾丘露薇,2020)。可见,女性记者的资本优势,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想象。
首先,性别化资本作为资本的调节因素,能够作用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等结构性资本,潜移默化地嵌入女性记者资本积累过程中。其一,从文化资本来看,女性记者的知识储备及文化程度往往通过“消费身体”呈现出来,实质遮蔽了她们的新闻能力,削弱了她们的职业口碑和新闻可信度,易给受访者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并采取“无能力预设”,即:外界看待女性记者天生缺乏驾驭“重要新闻”的能力,或常被贴上“美女记者”而不是“专业记者”的标签。其二,从社会资本来看,女性记者能很快与受访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通过婚姻的方式改变自身的阶层地位,但却与受访者形成一种基于“工具性交往”的“弱”联结,并没有像Djerf-Pierre(2005)所说“早期的女性记者拥有很多的社会资本”。其三,从经济资本来看,女性记者虽然保持初心,坚守新闻情怀,但却因职位偏低而导致整体收入偏低,实质掩盖了她们所处的弱势位置。其四,从象征资本来看,女性记者对自我职业会产生“认知不协调”的职业焦虑,即:自身专业能力和竞争意识不成正比,并在晋升发展的过程中受制于外在“传统性别文化规训”与内在“家庭职责”的影响,导致她们对未来职业发展信心不足,在职场中逐渐自我边缘化。
其次,在不同场景下,女性记者将自身负面的性别化资本转换为其他资本的成本、难度和机会都有所不同。性别化资本转为其他资本具有一定的条件,当负面的性别化资本最大化时,女性记者资本数量和种类才显得不足,其他资本难以抵消负面的性别化资本,其拥有各种资本之间的“低转换性”难以为她们赋权,致使她们向权力争夺的过程中需克服重重阻碍,这些因素都无法弥补因性别问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Moi, 1999; Djerf-Pierre, 2005)。
最后,本文拓宽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视角,弥补了性别传播现有文献的不足。女性记者已成为一种职业想象,为更多女性职业发展赋能。女性记者作为内容生产者,能够生产和传播出更多与女性有关的新闻内容,为其他女性发声,潜在地影响了新闻场域内在的性别意识的传递,有利于向外传递并鼓励更多女性受众,对新闻业性别平等起到促进作用。
本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焦点小组中,虽然参与者在发表观点时容易激发其他参与者的灵感,但由于参与者的从众心理,总是认同和强化“前一个人的观点”,不易挖掘到个体内心深处真实想法和独特性经验,当场仅讨论出一些记者共性层面问题,后期只能通过深度访谈加以补充。此外,面对近几年媒体人纷纷离职转型的现状,性别对于媒体创业者的资本积累有什么影响?他们在传统新闻场域所积累的资本对他们创业又有哪些促进作用?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曾丽红(2014)。中国调查记者行动实践的社会学分析——一种媒介场域的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7),48-52。
陈楚洁(2018)。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媒体创业叙事与创业者认同建构。《新闻记者》,(3),4-22。
陈立敏(2021)。从“记者”到“积极行动者”:前媒体人的新闻参与研究。《新闻大学》,(5),66-80+123-124。
陈阳(2006)。我国新闻生产的影响机制之研究:以妇女新闻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71-77。
方俊奇(2019)。论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所形成弊端的破解之道及对其象征资本的再思考。《法国研究》,(1),33-42。
方蒸蒸,程晋宽(2012)。焦点小组访谈”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意义。《外国教育研究》,(6),19-25。
冯剑侠(2012)。“无冕皇后”还是“交际花”:民国女记者的媒介形象与自我认同。《妇女研究论丛》,(6),59-64。
赫伯特·甘斯(2019)。《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沈明,胡琪萍(2016)。个体身份转换与行业规则的塌陷——以2003—2016年媒体人离职告白为例。《编辑之友》,(12),63-69。
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2017)。《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张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罗德尼·本森,韩纲(2017)。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新闻与传播研究》,(1),2-23。
闾丘露薇(2021)。我们还需要讨论性别平等?——香港记者性别意识探讨。《传播与社会学刊》,(57),29-52。
美通社(2016)。《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检索于https://www.prnasia.com。
莫妮卡·德夫-皮埃尔,刘霞(2014)新闻学的性别——20世纪新闻业的性别构成与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S1),90-93。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7)。《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20)。《关于电视》(许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媒派(2018)。《中国女记者骚扰调查》。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180323/20180323A08OYN.html。
宋素红(2003)。近现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新闻与传播研究》,(2),41-47+93。
谭琳,李军峰(2002)。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基于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观点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4),5-11。
王海燕(2012)。对媒体商业化环境下“新闻业女性化”的质疑——探究女性新闻工作者追求性别平等的障碍。《新闻记者》,(12),26-33。
王海燕(2016)。女性调查报道记者的性别迷思——社会刻板印象建构的视角。《新闻大学》,(4),19-26+149。
尤红(2020)。女记者职业生涯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与省思——以电视女记者为例。《当代传播》,(1),61-65+81。
张志安,汤敏(2018)。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新闻与写作》,(3),56-65。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017)。《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检索于http://www.zgjx.cn.2018。
ASN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 Editors Newsroom Diversity Survey, 2016.
Carlson, M.LewisS. C. (2015).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de BruinM. (2000). Gender,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1(2)217-238.
Djerf-PierreM. (2005). Lonely at the top: Gendered media elites in Sweden. Journalism, 6(3)265-290.
Djerf-PierreM. (2017). The gender of journalism: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the fie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dicom Review, 81-104.
GillR.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nitzsch, T.HanuschF. (2012). Does gender determin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views? A reassessment based on cross-national evi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3)257-277.
Kim, Y.BaeJ. (2006). Korean practitioners and journalists: Relational influences in news selectio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2(3)241-245.
McNay, L. (2000). 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Moi, T. (1999).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books. google. com.
North, L. (2009).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industry change and the effects of neoliber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0(4)506-521.
Putnam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RiveraR. L. K. (2007). Culturegender, transport: Contentious planning issues.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ulleti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76)117-121.
Schultz, I.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tic doxa, news habitus and orthodox news valu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190-207.
SooyoungC.DavenportL. D. (2007).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Korean newsroom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3)286-300.
TandocE. C.Ferrucci, P. (2015). A tale of two newsrooms: How market orientation influences web analytics us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suiC. Y. S.LeeF. L. F. (2012). Trajectories of women journalists’ career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Studies13(3)370-385.
ZuiderveldM. (2011). Hitting the glass ceiling- gender and media manage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3(3)401-415.
何映霏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新进青年教师启动计划”(项目编号:22X01050027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