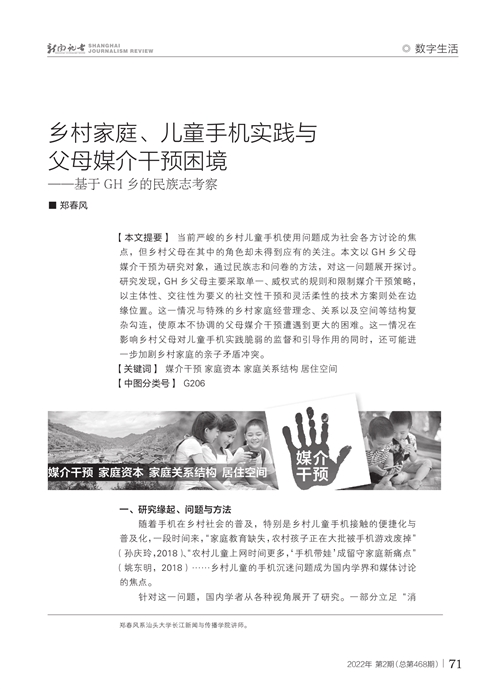乡村家庭、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困境
——基于GH乡的民族志考察
■郑春风
【本文提要】当前严峻的乡村儿童手机使用问题成为社会各方讨论的焦点,但乡村父母在其中的角色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GH乡父母媒介干预为研究对象,通过民族志和问卷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GH乡父母主要采取单一、威权式的规则和限制媒介干预策略,以主体性、交往性为要义的社交性干预和灵活柔性的技术方案则处在边缘位置。这一情况与特殊的乡村家庭经营理念、关系以及空间等结构复杂勾连,使原本不协调的父母媒介干预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一情况在影响乡村父母对儿童手机实践脆弱的监督和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乡村家庭的亲子矛盾冲突。
【关键词】媒介干预 家庭资本 家庭关系结构 居住空间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缘起、问题与方法
随着手机在乡村社会的普及,特别是乡村儿童手机接触的便捷化与普及化,一段时间来,“家庭教育缺失,农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机游戏废掉”(孙庆玲,2018)、“农村儿童上网时间更多,‘手机带娃’成留守家庭新痛点”(姚东明,2018)……乡村儿童的手机沉迷问题成为国内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焦点。
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从各种视角展开了研究。一部分立足“消极儿童”的理论预设,如乡村留守儿童因为亲情关怀缺失而导致的手机需求、依赖甚至沉迷(郑素侠,2012 & 2013;莫梅锋,王旖旎等,2014),以及娱乐化的手机使用等,成为相关研究最为常见的逻辑归因与判断。另一部分则超越“消极儿童”与“问题化”的理论预设,将研究重点转向乡村儿童如何主动、策略性地使用手机媒介来应对成长的环境变化,以及如何通过情境化的媒介实践,将手机嵌入自身的成长经验等方面(李艳红,刘晓旋,2011;胡翼青,何乔,2010)。还有部分学者从家庭结构(冯强,马志浩,2019)、媒介化亲职(胡春阳,2012 & 2019;王宇,陈青文,2019)、数字反哺(周晓虹,2000 & 2011;洪杰文,李欣,2019)等视角来探讨乡村儿童的手机媒介实践问题。
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少有研究专门关注乡村父母在应对于儿童手机实践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及其相关状况。本文立足特殊的乡村家庭结构,从父母媒介干预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乡村父母采取了怎样的干预行动,这些干预行动在乡村家庭场域又面临怎样的结构性条件与难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志方法,选取江西赣南地区的GH乡作为田野调查场域。GH乡是笔者家乡,密切的社会联系和熟悉的在地情境,既有利于民族志调查的开展,又能对当地社会状况以及更为聚焦的儿童现象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现时—历时性的把握,从而为笔者在民族志考察与“返乡书写”之间建立有机的知识生产过程(刘楠,2018)。此外,GH乡作为典型的处在剧烈转型中的中部偏远乡村,对本研究议题也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笔者于2019年8—11月期间对GH乡下辖的QS、ZY、WZ等村落的父母媒介干预与儿童手机实践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民族志考察,同时在2020年7—8月进行了补充性考察。
本文结合使用问卷调查作为辅助方法。问卷数据可以与民族志材料相互支持,并扩展田野调查。GH中学是GH乡唯一的一所中学,主要面向乡内各村落学龄儿童,因此是笔者问卷发放的理想场域。GH中学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前身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仁义书院,一直未中断办学,因此也与GH乡社会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历史性情感与制度性连接。近年来,GH中学在校生每年维持在七八百人左右,是GH乡青少年最集中的地方。考虑到问卷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笔者于2019年11月12日在GH中学初一至初三进行了分层问卷发放:在七年级发放问卷58份,回收有效问卷47份;八年级发放问卷61份,回收有效问卷55份;九年级发放问卷56份,回收有效问卷51份;共计在GH中学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153份。
二、文献综述
随着手机等传播新科技在儿童群体的大规模普及,如何正确引导儿童的媒介实践,以趋利避害,成当代父母面临的共同难题(Livingstone et al., 2017)。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国外学界出现一股研究父母干预(parental mediation)儿童媒介实践的浪潮,其中聚焦的关键问题是父母如何管理和干预儿童的媒介体验(Haddon, 2013;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整体来看,相关研究认为父母干预策略因儿童年龄、媒介素养、教育、对传播新科技的风险感知、社会经济地位等差异化因素而不同,也会对儿童造成不同的社会后果(Khurana et al., 2015; Nikken, 2018)。
目前国内对父母媒介干预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一直以来,这一问题或隐或显依附在关于儿童媒介接触、使用及其效果的相关研究中(赖运成,李瑞芳,2019;姜博,徐军华,2019),或被裹挟在媒介素养的研究框架中(路鹏程等,2007;刘勇武,2010;陈梦晖,2017),作为一个附属性议题出现。近年来,相关针对性的研究开始出现。如张煜麟(2015)对社交媒介时代亲职的研究从侧面涉及了父母媒介干预的内涵,陈青文(2019)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上海市父母的媒介干预,曾秀芹等人(2020)系统梳理了中外语境中父母媒介干预研究的发展脉络,归纳了父母媒介干预的方式、效果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等,并对该议题的本土化研究提出了若干意见。曾秀芹等指出,“如何将父母媒介干预从抽象命题转变为具体实践研究”(曾秀芹等,2020:63),是当前国内父母媒介干预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而这也是本文的理论起点。
相比之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国外学者归纳了父母媒介干预的不同类型,如有学者归纳为社交性途径(social approach)、制定规则和设置使用限制(making rules about and setting restrictions)以及技术性解决方案(technical solutions)三种常见类型,而且他们的研究显示父母整体上更倾向采用社交性途径,有近四分之一父母从不干预他们子女的传播新科技使用(Kirwil et al., 2009)。也有学者将父母干预策略归纳为积极型干预(active mediation)、限制性干预(restrictive mediation)、共同使用(co-use)和监督(monitoring)四种类型(Zaman & Mifsud, 2017)。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互动限制(interaction restrictions)、监视(monitoring)、渠道限制(access restrictions)、共同使用式的监督(supervision with co-use)、技术性干预(technical mediation)和阐释性干预(interpretative mediation)等六种策略(Symons et al., 2017)。
同时,有学者更加深入探讨了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父母干预的差异化建构作用。如Kirwil等人(2009)探讨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不同社会语境对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差异化的影响。Dedkova和Smahel(2020)则从社会生态学视角,具体考察了积极型干预(active meditation)和监视(monitoring)两种策略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父母的性别、媒介技能、帮子女解决媒介问题的能力等因素,影响了积极型干预策略的内涵及其采用,但对监视性干预策略影响不大。他们进一步指出,父母干预策略不是固定不变的流程,而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不断被重构;它不仅受单个的亲子情况影响,同样受到其他亲子情况或其他看护者的影响;它不仅受稳定的家庭特征和亲职风格的影响,同样也是现实和即时语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作为父母媒介干预对象的儿童手机实践
对于乡村父母媒介干预问题的讨论,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其对象——乡村儿童及其手机实践的基本情况层面。儿童手机实践对父母情感与认知判断的冲击,是乡村父母媒介干预行动的现实逻辑起点,也是相关讨论的经验前提。
(一)日益普遍的乡村儿童手机实践
当前,乡村儿童手机实践现象日益活跃。从图1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到,从初一到初三不同年龄阶段的GH乡儿童群体,拥有1部及以上手机的比例均达60%左右,各年龄阶段情况基本持平,这一情况足见手机在GH乡儿童群体中的普及程度,以及乡村父母媒介干预所面对情况的普遍性。其中还有一定比例儿童拥有2部及以上的个人手机。从调研情况来看,部分儿童为应对父母与老师缴没而做“备用方案”,成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随着儿童成长特别是进入初三年级,部分父母对学习不理想的儿童媒介干预的放松甚至悬置,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为“备用方案”的第2部手机的必要性,从而使得这一比例在初三年级反而出现大幅下降。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乡村父母媒介干预的某种特定逻辑。
在儿童手机使用时长的调查中,除个别儿童在问卷中特别指出不玩手机外,绝大多数儿童都在手机上花费了一定时间。具体从图2可以看到,每天在手机上花费1小时及以上时间的各阶段儿童均占到七成以上,花费3—5小时及以上时间的儿童整体也占到一半左右。同时可以发现,在1—3小时、3—5小时以及5小时以上等各使用时长段中,儿童占比与其年龄之间整体上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儿童年龄越大,在相关手机使用时长段所占比重也越大。手机使用时间是父母媒介干预的一个关键目标,因此父母媒介干预在这种相关性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了怎样的结构性作用?也就成为一个有待厘清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调查数据(见图3)显示,手机游戏成为近50%儿童手机实践的主要内容,约70%的儿童手机主要用于刷视频和听歌等线上娱乐项目,这些活动普遍被认为不利于儿童学习和成长;相比之下,只有30%左右的儿童手机实践涉及学习内容,20%左右涉及日常人际联系。可见,GH乡父母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综上可以看出,在日常交往与玩乐情境中,手机身影在GH乡儿童群体中已变得无处不在。相比以往电视、便携式磁带播放器、MP3/MP4播放器等,可以说当前手机实践不再是GH乡儿童生活世界的边缘现象。特别是图2、图3所展现出来的儿童高比例的长时间及娱乐化的手机实践状态,更是日益成为GH乡家庭无法回避的亲职难题。这一情况在凸显GH乡父母媒介干预问题急迫性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当下媒介干预策略整体性的低效甚至失效状态。至于乡村父母媒介干预为何出现这一状况,则正是本文要重点阐述的问题。
(二)乡村儿童“问题化”手机实践的代际效应
在这一背景下,GH乡父母似乎都有与之不快甚至惨痛的故事和记忆,或关于自身,或涉及邻里,由此造成的亲子间新的不信任甚至冲突关系,进一步形塑了乡村家庭亲子间的代际情感责任结构,正如下面访谈对象讲述的:
那个孩子,做完作业不去休息,就盯着他妈妈的手机,躲在房间里玩。那段时间学习成绩降到了班上三十多名……去年暑假我还和他干了一架。(访谈对象A,父亲,2019.09.19)
实际上,手机作为复媒体(polymedia)(Madianou, 2014),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责任境况(new condi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手机媒介社会化过程牵涉着特定、具体的道德责任议题,在这些议题上,主体越来越需要为他们的媒介选择与实践行为负责,他们对于恰当使用负有更为直接而不可推卸的责任。手机实践的道德分量(moral weight)由此日渐凸显出来(Madianou & Miller, 2012;Gershon, 2010;Madianou, 20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从家庭代际视角可以清晰看到,乡村儿童手机实践与亲子代际间的责任认知与道德评判存在着密切勾连,这某种程度上成为乡村父母媒介干预直接的情感基础。
在GH乡父母认知中,手机问题的严重性使之不同于便携式播放器、MP3/MP4等无关紧要的“小孩玩的东西”或学习辅助用品,特别在讨论子女或谈及乡里儿童的学习和成长问题时,手机更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GH乡儿童的媒介实践史上,媒介第一次被提高到与其成长具有直接而重大关联的层次,儿童之于家庭、父母的成长责任,更加显在而频繁地呈现在其日常手机实践中:
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外面扒拔(辛勤工作),不都是为了他!要食要着(穿),我俩什么会给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天天拿个手机窝在房间里,门也不开,饭也不吃,书也不去读……不拿手机给他,他说就去跳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访谈对象B,父亲,2018,05)
父亲B在向笔者倾诉儿子的一次成长危机时,满腔气愤、无奈和不解。GH乡盛传着许多类似的故事,而B的倾诉同样反映着GH乡父母在涉及此类事件时的普遍情绪:他们在看待手机与脆弱的子女成长这一看似简单但实际复杂的关系问题时,很少把自身放置到这一现象和过程的责任框架中,而更多是认定子女在哪里或什么时候学坏了。这样,一方面之前一直处在边缘和被遮蔽的关于媒介与儿童成长—培养之间潜在的伦理责任问题,突然以一种可见而迫切的问题化形态展现在乡村社会面前。如当乡村父母谈论子女的学习或成长议题、特别当出现消极迹象时,他们会习惯性地迅速将之与“玩手机”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的因果关联。可以说,这是前手机时代的乡村儿童媒介实践所没有遭遇过的沉重的成长伦理压力。另一方面,手机媒介实际上促成儿童成长—培养责任在儿童与父母之间不均衡的代际分布与流动。父母一般以能为子女提供更加殷实的经济与物质条件作为自我评估亲职履行状况的主要标准,因而在涉及儿童成长与手机媒介之间的伦理追责时,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将自身从中抽离出来,儿童则几乎担负起手机媒介消极效应的所有道德责任。
四、GH乡父母媒介干预策略的现状
上文讨论的乡村儿童手机实践对家庭代际责任结构的重塑,在现实层面进一步影响着亲子代际行动逻辑。对于一直相对稳定的乡村父母范畴而言,不可控的儿童手机实践及其后果,无疑使他们遭遇到全新的亲职难题。这一情况赋予父母媒介干预行动充分而迫切的情感基础,并内在促成对子女手机实践的现实干预行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结合Kirwil等人(2009)的理论,从社交性途径、制定规则和设置使用限制以及技术性解决方案三个层面展开更为具体的讨论。
(一)以威权式管理为主导的使用限制
理论上而言,乡村父母同样具有实施上述各种媒介干预策略的可能,但受社会语境、教育水平、媒介素养、家庭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Sasson & Mesch,2014),呈现出其特殊的一面。正如Kirwil等人研究发现的,处在传统的集体主义氛围社会语境的父母,或不进行干预,或倾向使用限制性规则或技术性限制策略(Kirwil et al,2009),在GH乡也明显发现,父母采取的媒介干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制定规则和设置使用限制,其中又以相对单一的威权式管理或不介入干预为主。
单一的威权式管理是基于父母传统权威想象而建构起来,并由此得以实施。这种干预策略虽然难以较好应对日益复杂的儿童手机实践,但在乡村意义结构中仍占据独特位置。这一策略内部又存在两种不同的具体方式。一种是持续性的、威权式的使用限制及规则。在这种方式中,儿童手机实践受到父母持续而系统的强制性限制,父母也常因此而倍具成就感。“我在屋下(家里)就不让他玩(手机),现在读书的时间我是都不让他玩。”(访谈对象C, 母亲,2020.07.21)一位母亲在谈及儿童玩手机问题时自信地说道。
但这种情况在GH乡其实并不多见。天天玩手机成为当前GH乡父母口中对子女玩手机问题最为常见的描述,而对于自身应对,他们则多表示平时没时间管,也就不管了,也经常可以听到他们气愤地讲述自己在某个时间、某一场景实在无法忍受子女玩手机的问题,而做出摔门、训斥、体罚、砸手机等极端行为。可见,虽然GH乡儿童的手机实践呈现出频繁而持续的普遍特征,但父母的行动回应却是非持续性的。上述情况在父母媒介干预层面则表现为一种有别于上文的更为常见的偶发性的强制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多发生在因儿童玩手机而引发的冲突情境中,正如D的丈夫对儿子玩手机时的暴怒情形所显示的那样:
家里小孩日日玩手机,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老公也气得要死,也管不住他了。有天晚上,我那个仔(儿子)拿我的那只手机反锁在厕所里玩。他说你再要玩,再不听话,我就要打死你。一气之下,我老公把厕所门都打烂了。(访谈对象D,母亲, 2020.07.21)
(二)难以达成的社交性和技术性方案
因特定的乡村情境,加之GH乡父母整体不具备必要的媒介素养基础,社交性和技术性干预策略处在整个媒介干预体系相当边缘的位置。
首先,在社交性方案方面,在GH乡这种相对传统的乡村亲子关系情境中,儿童被视为“小孩子”,儿童的生活世界相应被贬低性地视作“小孩子的事”,以至于排除在家庭正式的日常事务议程之外;相比之下,只有大人们“日日在外面累死累活做事”(访谈对象E,父亲, 2019.09.17),“辛辛苦苦外面扒拔”(访谈对象B,父亲, 2018,05)才是家庭“正事”,这种不对等的代际主体身份及行动意义,与社交性方案内部所要求的平等交往逻辑之间构成了根本性对立,从而在基础层面挤压着社交性干预方案在GH乡家庭领域展开的结构性空间。即使在一部分相对年轻的父母群体中会有实践上的尝试,但也由于“交流的失败”,多面临着无法达成的困境:
我说你上午学习,做好作业,你说要玩,那下午让你玩。当面说得好好的,一转背人不在,他马上又玩起来了。(访谈对象D,母亲, 2020.07.21)
同时在围绕手机使用(如手机系统与功能设置、App使用等)、网上事务(如缴纳费用、网购、信息注册等)等发生亲子交往的情景中,上述情况也并未出现本质上的改变。这种沟通多以子女向父母进行知识输送的代际反哺形态展开,而且在GH乡,这种家庭代际反哺事件多围绕父母迫切的事务性议程展开,完成待办事项成为主要目的,大多父母并未将其视为学习和提升手机素养以更加有效干预和引导子女手机实践的机会。在这种普遍情境中,代际反哺的媒介化亲子交往活动及其单向的媒介知识流动,并没有在GH乡父母群体反向形成共同参与、引导儿童手机实践的意识与行动,也没有为这种意识和行动创造结构性的机会。
其次,在技术性方案方面,GH乡大多数父母对智能手机操作系统都不甚熟悉,不了解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干预和引导子女的手机实践。在最为常用的手机密码设置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GH乡父母开始启用手机密码设置,但这种技术干预手段对儿童与手机做一刀切的隔断处理,儿童经常能通过学习、联系等诸多日常“正规事由”以及对父母手机使用有意识的暗中观察等,轻易突破其使用封锁。“(设置手机密码)都试过了,能保几天吧,他看你开手机,没几天就试出来,换都换不过来。”(访谈对象D,母亲, 2020.07.21)而手机系统中的“家长模式”、手机软件中的“青少年模式”等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技术干预方案,GH乡父母普遍不会使用:
F(教师):你的手机设置学生模式吧,设置了学生模式后,手机有很多应用和游戏就用不了了,有些设定的网站也上不去。这个只有家长才能控制。
D:这个我不知道,哪有这个功能?在哪里,你帮我看一下。
总体来看,GH乡父母对子女手机实践采取的是一种断裂的、不协调的媒介干预策略,偶发性的、威权式的强制性规则和限制方案成为其主要内容,而以主体性、交往性为要义的社交性方案和灵活的技术性方案则处在边缘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儿童手机实践产生的家庭亲子交往关系也主要被引导至控制—反抗的单向维度中展开,并大多以冲突和矛盾的形式呈现在GH乡家庭中。
五、乡村父母媒介干预遭遇的特殊困境
父母媒介干预及其内在结构受到特定社会语境的深刻影响,父母媒介干预的现实效应则同样需要通过特定社会结构条件才可以实现。正因为如此,父母媒介干预和特定社会情境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立足GH乡特定的家庭现实情境,可以发现乡村家庭的经营建设理念、庞杂紧密的特殊关系结构甚至最为日常的家庭生活空间的变化等,都在不同层面对乡村父母媒介干预的决策及行动造成复杂、显著的影响,而且在诸多情境和条件中,上述因素对父母媒介干预行动造成了明显的干扰和冲击。
(一)乡村家庭经营理念对干预动力的分化与消解
儿童作为家庭单位的主要成员及行动者,其活跃的手机实践与父母的家庭现实经营谋划及实施,正发生日益频繁的交织和碰撞,并对作为整体性的家庭经营现状及预期产生重要影响。作为父母的回应性举措——对子女日常世界的干预和引导行动,必然遵循和渗透着其特定的家庭经营建设理念,另言之,乡村父母特定的家庭经营建设理念在基础层面形塑和影响着父母的媒介干预行动。
21世纪以来,之前缓慢而相对均衡发展的GH乡家庭,从经营理念、策略到实际的家庭经济水平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快速的差异化发展趋势。正如桑格利在剖析当代家庭剧烈转型时发现了家庭资本结构转换这一关键逻辑,家庭资本也成为我们观察GH乡家庭这一历史性过程以及正发生其中的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口。
“尽管拥有财产的数量至关重要,但世世代代,家庭资本结构(经营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与其数量相比,变化要更大”(桑格利,2012:20)。与传统的农业经营资本及模式相比,促成文化资本的转换成为GH乡家庭经营更为关键的方向。但对于大多数GH乡父母而言,面对日益超出自身理解和掌控范围的社会境况,除了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之外,主要只能依靠子女教育来实现。儿童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乎能否打破与超越乡村个人与家庭命运世代机械的复制与传承链条,并进一步改变世代“耕田”或打工的“乡下人”身份。乡村儿童在家庭建设工程中实质上肩负了更重大的职责。但与此脱节的是,他们实现这一职责的通道却非常狭窄,即一般只能通过高考,而不像城市家庭的关系资本,个人在音乐、舞蹈、绘画等其他才艺,同样可促成这种转换。
正是在这种逻辑中,GH乡父母媒介干预与子女学习成绩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学习成绩好,则父母对子女手机实践相对敏感,而施加持续而严格的干预;他们的事例也经常成为家人、亲戚以及其他熟人持续讨论的对象,自觉专注地学习、对手机有节制的接触、父母不让玩手机等话语及内在行动要求,伴随着“会读书的孩子”形象弥散在乡村熟人社会关系圈层中,他们的手机实践就处在这种被他者营造的高光形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熟人关系压力之下。相反,如子女学习成绩不理想,虽然在年龄较小阶段,他们同样受到父母的严格控制——父母认为子女学习之所以不理想,手机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控制甚至杜绝玩手机,成绩就有大幅提升的预期——但随着年龄增加,父母一旦认定他们“不是学习的料”,文化资本转换面临失败或破灭,他们会倾向果断放弃对这一道路的坚持,转向更加实际的选择——子女早点毕业,打工挣钱,务实谋划经营资本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子女手机实践可能带来消极后果的担忧随之释放,媒介干预随之明显放松,甚至放弃。这一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解释了上文图1、图2中所讨论过的一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学习好,则父母干预多;学习差,则父母干预少”这一简单行动逻辑背后,反映出的实质是当前乡村家庭经营建设理念及其支配的家庭行动逻辑对“儿童存在”的普遍性价值和意义的狭隘化、甚至变相否认。这在日常生活层面集中表现为父母以及家庭对儿童态度以及行动方式的功利性与断裂性,上文中父母媒介干预的简单二元逻辑突出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说,当前GH乡的家庭经营理念在根本层面分化和消解着父母媒介干预行动所需的持续稳定的动力机制,本来作为一项日常行动领域的媒介干预,被日益分化成为一种断裂的、非此即彼的权宜性应对举措。
(二)家庭关系结构对干预平衡性与统一性的冲击
乡村父母媒介干预处在特定、具体的家庭关系结构中,这种关系结构也在诸多情况下对父母媒介干预造成直接的干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GH乡家庭在形式上发生着核心化与小型化转型(王跃生,2013)。核心家庭的关键指标不在于成员规模,而是关系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家庭事务处理方面的独立性,从这个层面看,实际家庭状况与户口登记的家庭情况经常存在不一致的地方(Xu & Xue, 2017:16)。在GH乡,户口分家并没有带来实际家庭生活层面的分家,“分户而不分家”、两代同堂仍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而且与城市不同,GH乡两代同堂的现象本身就承立在上一代多子家庭的叠加效应基础之上,即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夫妇本身来自多子女的大家庭。这样,两代同堂就意味着两三个甚至更多小型化核心家庭的叠加,而形成一种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的超大规模的跨代际家庭。
在这种家庭中,一方面,多个夫妻家庭的儿童相应聚集,交织着多重的同辈亲属关系;另一方面,儿童也被嵌入与其他成员庞杂交织的代际关系网络中。手机在组织与重构这种家庭关系的同时,其“物品”本身的流转与驯化也处在这种不可控的多重关系节点之中,儿童手机问题被导向一种不稳定的代际流动状态。
以笔者调研的G(父亲)的家庭情况为例,G有一弟一妹,三人均已成家,且都已育有子女。G和弟弟各育有一儿一女,妹妹育有一子。在现实条件下,这种核心家庭很难独立承载乡村转型引发的各种结构性压力。在笔者调研的2019年及前两年,G三兄妹及配偶都外出务工,子女都交由在家务农的父母隔代抚养。形式上小型化与核心化家庭的维系,在功能以及关系上仍高度依赖传统乡村“大家庭”模式的支撑。
在当下这种“大家庭”中,年轻一代父母对子女情感有着强烈而感性的需求,手机的即时语音和视频通讯功能则很好契合了这点。正如G家庭所展现的,祖辈、父母与子女睡前饭后的手机视频语音聊天成为常态。但手机媒介在承载乡村儿童在核心家庭与“大家庭”之间分合转换的同时,又衍生出新的儿童手机问题:
这几个孩子,我做事一回来就围过来,扒我的袋子(索要手机),管都管不住……有一次,我们寻了他们两个一下午,到处都找遍,就找不到,我们都快吓死了。结果他们两个躲在二楼的床底下玩手机。他们还聪明,拿排插接线,一边充电一边玩,你说这个怎么管!(访谈对象H,祖母, 2019.10.27)
从G母亲H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较之小型化核心家庭,“大家庭”内部儿童的聚集带来了手机实践需求在家庭场域的叠加,其面临的媒介干预压力无疑也相应叠加。与多个夫妻家庭亲职向祖辈转移相呼应,乡村父母的媒介干预职能也出现代际转移。如G三兄妹务工外出时,除了告诫子女不能整天玩手机之外,他们往往更寄希望于他们的“老父母”,嘱咐他们“平时管严一点”、“手机之类不要随便放”等,但作为子女媒介干预的主体,自身却处于实质性的缺席状态。除平时视频通讯时偶尔苍白无力的口头警告之外,他们并无更多实质性的措施,与子女围绕手机而展开的频繁而艰巨“日常斗争”,其实都落到了祖辈那里。可以说,G家庭中媒介素养最为欠缺的祖辈却承担着媒介实践干预最多的职责。当寄宿家庭并非直系祖辈,而是其他旁系亲属的时候,在亲疏远近与责任程度相匹配这一朴素的传统关系原则作用下,这种被转移的媒介干预则处在更加微弱的境地。综上言之,这种结构极大冲击了父母媒介干预所应对的代际关系及职责的平衡性,而这种平衡又是确保父母媒介干预有效性的一个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多节点的家庭关系也使儿童手机实践日益超越父母掌控的边界,并潜在性地破坏着父母媒介干预体系的内在统一性。如G抱怨的那样,“我是能说得住(管得住)一点……我妹妹一回来,手机啊、平板啊,什么都给他们玩,那是玩得一天到晚的”。如图4的调研数据显示,在获得个人手机之前,大约25%的各年龄阶段儿童可以从其他家庭或亲属成员那里获得手机。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一情况甚至更为普遍。与此同时,在儿童手机问题上,家庭年轻成员总体抱以更加开放的态度,而且很多时候,这是他们向儿童展现亲情给予的重要形式,而儿童也更乐于和敢于向年轻家庭成员索要手机。因此,乡村父母媒介干预要面对的不仅有日益超出他们理解和掌控的儿童范畴,同样还有这种庞杂家庭关系有意无意的频繁介入与掣肘。
(三)家庭居住空间结构对干预时空条件的阻断
除上述层面,作为家庭基本要素的居住空间结构同样对父母媒介干预产生着重要影响。家庭空间结构的变化,潜在性地成为GH乡父母媒介干预所要应对的另一个特殊难题。
“作为一个越来越被牢牢嵌入儿童的概念空间与物理空间,‘家’的空间实际上当然并不总是一个理想空间:这个空间的规则和纪律与学校和城市的规则和纪律一样,对许多儿童而言都是有疑问的”(詹姆斯等,2014:48)。的确,作为儿童生活中心的家的空间,其实充斥着父母的监视和权力问题,而这又建立在父母对“家”空间的控制上,即儿童对家庭空间的使用以及在其中展开的日常活动,常受到父母监督与控制。因此,父母媒介干预通常表现为父母与子女围绕媒介问题而在家庭实体空间进行的日常控制与斗争的过程。家庭空间常规排列以及家庭成员对空间经验一旦发生变化,父母媒介干预面对境况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在2010年以前,GH乡传统的“家”一般为一室一厨一厅的双层土坯房构造。第一层为生活空间,二层为储物空间。其中,生活空间一般又分为厨房、餐厅、厅堂(类似客厅,但普遍兼具家庭祭祀的功能)和卧室等基本生活功能区。在空间分配上,一般做饭、用餐共用一室,厅堂和卧室各占一室。一个家庭一般共用一间卧室,部分成员较多的家庭,则会在二楼另收拾一个房间作为卧室。一些居住条件紧张的家庭,则没有设单独的厅堂。
这种居住结构将各成员差异化的生活笼统聚合在整块而无个体边界的家庭空间中,各自的日常生活也都全面展现在彼此的视野中。这种空间塑造的家庭生活对于儿童,在营造共同情感之外,同样具有限制性。这种家庭空间权力结构给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和控制带来了方便,从饮食到起居,父母可以对包括媒介实践在内的儿童家庭生活进行全面而通透的观察与控制,其所达到的程度甚至能看到全景监狱的影子(福柯,2003)。
随着乡村发展,土坯房作为落后标志,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首要处理的对象。2012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要求“加大以土坯房为主的农村危旧房改造力度”,赣州市随即启动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改造范围逐步扩大至所有土坯房。在政策强推与政策补贴的双重推动下,GH乡全面拉开土坯房改造的序幕,并在较短的三四年内,在全乡境内迅速完成了改建要求。
GH乡全境范围内的家庭空间结构在短时期内随之发生剧烈变化。首先,新建砖式平顶房在居住空间方面得到了大幅优化与扩展。之前一室一厨一厅的土坯房,被单层建面为三室甚至四室一厅的砖式平顶房替代,而且新建房一般都建有两至三层。因此,GH乡家庭的物理子空间普遍扩展至六室二厅至八室二厅之间。其次,更重要的是乡村家庭空间开始出现个体化与私密化趋势。随着家庭空间的相对充裕,普遍出现了一个专属的儿童物理空间——独立的儿童卧室。
家庭居住空间的细分,本质上也是人行为的细分和私人时间的分化(北本正章,2020)。一方面,以儿童卧室与父母卧室的相互分离为基础,父母与儿童在家庭日常生活层面开始发生分离,父母逐步对子女私人化的卧室空间产生明显的边界感;另一方面,“卧室的门”将儿童个体空间从家庭公共生活中剥离出来(Livingstone, 2002:112),也从父母无处不在的空间监视和控制中抽离了出来。父母对儿童在独立卧室空间内的媒介实践逐步失去控制,儿童诸多被认可或不被认可的手机实践,都逐步退入或整合进私密性的、由“门”隔离的个人卧室空间。在此,乡村父母媒介干预遭遇到一种特殊之“门”。
虽然父母还是会干预甚至训斥儿童在卧室中的玩手机行为,但已无法再像共处同一卧室时代那样实现无处不在的直接监视和控制了。“去年他们俩经常在晚上十二点一点起来,偷偷拿他妈妈的手玩,在自己房间里一玩就玩到晚上三四点”(访谈对象A,父亲, 2019.09.19),在儿童没有“自己房间”的时代,A遭遇的这种干预困境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此可以看到,父母对子女的权力运作机制所需的连续空间时常因卧室之“门”而被中断,儿童卧室空间正逐步成为乡村父母媒介干预与父母权力机制中的一块“飞地”。在这个意义上而言,GH乡父母媒介干预遭遇的困境,本身就是乡村家庭空间权力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而GH乡儿童手机实践不断出现的问题化趋势,其实也是父母在家庭空间中对儿童控制与整合走向失败的一个侧面印证。
六、结语
当前活跃的乡村儿童手机实践日益与其命运发生直接而重大的关联。乡村儿童媒介实践的这一深刻转型,冲击着乡村亲子关系原有的代际情感与责任结构,儿童承担着更大的关于“成长”的媒介责任。这种责任的代际不均衡流动,成为以威权式的规则和限制为主的乡村父母媒介干预的关键情感支撑及合理性基础。同时,乡村父母这种媒介干预策略又与特殊的家庭经营理念、关系以及居住空间等转型复杂勾连,进一步冲击原本断裂的媒介干预策略及效应。
客观而言,本文仅是一个细小的切口,其可能的意义与其说发现乡村父母媒介干预的新内涵,不如说在于提醒在城市中心主导社会知识生产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关注乡村父母媒介干预以及乡村儿童媒介实践议题的特殊性,而不是模糊或简单化城乡社会关系及其语境差异,忽视乡村父母媒介干预的独特境况,提出去情境化意见、结论或矫正措施。可以说,正是这种特殊性赋予了乡村父母媒介干预问题独特的复杂性,这是我们讨论乡村父母媒介干预问题的起点。至于如何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就乡村父母媒介干预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方案,则将是本文后续推进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日]北本正章(2020)。《儿童观的社会史:近代英国的共同体、家庭和儿童》(方明生译,沈晓敏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青文(2019)。新媒体儿童与忧虑的父母——上海儿童的新媒体使用与家长介入访谈报告。《新闻记者》,(8),15-25。
陈梦晖(2017)。在媒介的边缘游走和融入——评《在乡村望世界:中国乡村青少年媒介素养研究》。《新闻爱好者》,(8),112。
冯强,马志浩(2019)。科技物品、符号文本与空间场景的三重勾连:对一个鲁中村庄移动网络实践的民族志研究。《国际新闻界》,(11),24-45。
[法]弗朗西斯·德·桑格利(2012)。《当代家庭社会学》(房萱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路鹏程,骆杲,王敏晨,付三军(2007)。我国中部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比较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红安县两地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3),80-88。
洪杰文,李欣(2019)。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国际新闻界》,(10),50-74。
胡翼青,何乔(2010)。传播与城市的想象——以燕子河镇儿童为例。《当代传播》,(5),17-20。
胡春阳,毛荻秋(2019)。看不见的父母与理想化的亲情:农村留守儿童亲子沟通与关系维护研究。《新闻大学》,(6),57-70。
胡春阳(2012)。寂静的喧嚣,永恒的联系:手机传播与人际互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姜博,徐军华(2019)。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状况调查分析。《图书馆研究与工作》,(9),73-78。
赖运成,李瑞芳(2019)。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109-112。
刘勇武(2010)。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媒介素养教育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8),46-47。
刘楠(2018)。学者返乡催生乡村传播研究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3)。
李艳红,刘晓旋(2011)。诠释幸福:留守儿童的电视观看——以广东揭阳桂东乡留守儿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1),70-78。
[法]米歇尔·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莫梅锋,王旖旎,王浩(2014)。青少年手机沉迷问题与对策研究。《现代传播》,(5),133-137。
孙庆玲(2018)。家庭教育缺失,留守少年陷网游漩涡——不能让农村孩子被游戏废掉。《中国青年报》,(9)。
王跃生(2006)。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6-108。
姚东明(2019)。庞丹阳,张涛.农村儿童上网时间更多,“手机带娃”成留守家庭新痛点。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03/c_1123220147.htm。
曾秀芹,柳莹,邓雪梅(2020)。数字时代的父母媒介干预——研究综述与展望。《新闻记者》,(5),60-73。
[英]詹姆斯,[英]简克斯,[英]普劳特(2014)。《论童年》(何芳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张煜麟(2015)。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青年研究》,(3),48-57。
郑素侠(2012)。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57-160。
郑素侠(2013)。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参与式行动的视角。《现代传播》,(4),125-130。
周晓虹(2000)。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社会学研究》,(2),51-66。
周晓虹(2011)。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6),109-120。
AnqiX. & Yali, X. (2017). Family Structure. In Anqi, X. , DefrainJ. & WenrongL. (ed). The Chinese Family Today. New York: Routledge.
Dedkova, L. & Smahel, D. (2020). Online Parental Mediation: Associations of Family Members’ Characteristics to Individual Engagement in Active Mediation and Monitor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 (8)1112-1136.
Gershon, I. (2010). The Breakup 2. 0.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ddonL. (2013). Mobile Media and Children.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1)89-95.
Khurana, A. , Bleakley, A. , Jordan, A. B. & RomerD. (2015).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Internet Restriction on Adolescents’ Risk of Online Harass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44(5)1039-1047.
Livingstone, S. (2002). Young People and New Media: Childhood and 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London, UK: Sage.
Livingstone, S. & HelsperE. (2007). Gradations in Digital Inclusion: Children, Young People and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9(4)671-696.
Livingstone, S. , lafssonK. , HelsperE. J. , Lupiánez-VillanuevaF. , Veltri, G. A. & Folkvord, F. (2017). Maximizing Opportunities and Minimizing Risks for Children Online: The Role of Digital Skills in Emerging Strategies of Parent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782-105.
MadianouM. & Miller, D. (2012). Polymedia: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Digital Media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6(2)169-187.
MadianouM. (2014). Smartphones as Poly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3)667-680.
NikkenP. (2018). Do (pre)adolescents Mind about Healthy Media Use: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al MediationDemographics and Use of Devices.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2(2).
KirwilL. , GarmendiaM. , Garitonandia, C. & Martinez, G. (2009). Parental Mediation. // LivingstoneS. & Haddon, L. (Ed. ). Kids Onlin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for Children. Portland: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SymonsK. , Ponnet, K. , EmeryK. , WalraveM. & HeirmanW. (2017). A factorial Validation of Parental Mediation Strategies With Regard to Internet Use. Psychologica Belgica5793-111.
SassonH. & MeschG. (2014). Parental MediationPeer Norms and Risky Online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332-38.
Zaman, B. & Mifsud, C. L. (2017). Editorial: Young Ghildren’s Use of Digital Media and Parental Mediation.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11(3).
郑春风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