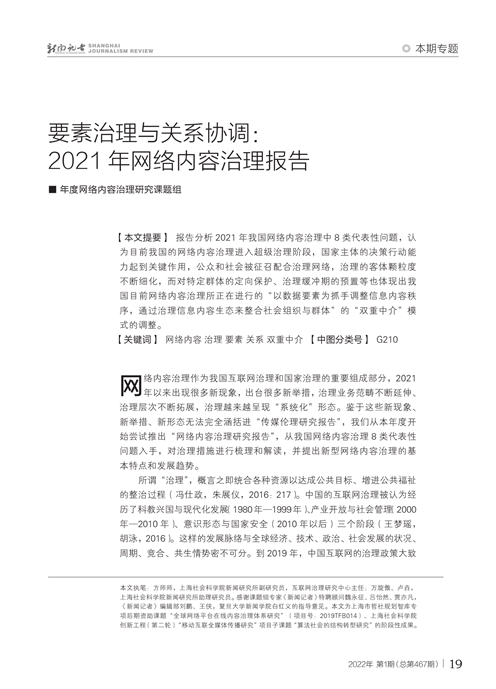要素治理与关系协调:2021年网络内容治理报告
■年度网络内容治理研究课题组
【本文提要】报告分析2021年我国网络内容治理中8类代表性问题,认为目前我国的网络内容治理进入超级治理阶段,国家主体的决策行动能力起到关键作用,公众和社会被征召配合治理网络,治理的客体颗粒度不断细化,而对特定群体的定向保护、治理缓冲期的预置等也体现出我国目前网络内容治理所正在进行的“以数据要素为抓手调整信息内容秩序,通过治理信息内容生态来整合社会组织与群体”的“双重中介”模式的调整。
【关键词】网络内容 治理 要素 关系 双重中介
【中图分类号】G210
网络内容治理作为我国互联网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以来出现很多新现象,出台很多新举措,治理业务范畴不断延伸、治理层次不断拓展,治理越来越呈现“系统化”形态。鉴于这些新现象、新举措、新形态无法完全涵括进“传媒伦理研究报告”,我们从本年度开始尝试推出“网络内容治理研究报告”,从我国网络内容治理8类代表性问题入手,对治理措施进行梳理和解读,并提出新型网络内容治理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
所谓“治理”,概言之即统合各种资源以达成公共目标、增进公共福祉的整治过程(冯仕政,朱展仪,2016:217)。中国的互联网治理被认为经历了科教兴国与现代化发展(1980年—1999年)、产业开放与社会管理(2000年—2010年)、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2010年以后)三个阶段(王梦瑶,胡泳,2016)。这样的发展脉络与全球经济、技术、政治、社会发展的状况、周期、竞合、共生情势密不可分。到2019年,中国互联网的治理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政策理念从“政府管理”到“共同治理”,政策体系从“垃圾桶模式”到“问题导向”再到“战略布局”,政策过程从重“事前控制”到平衡“事中—事后控制”(黄丽娜,黄璐,邵晓,2019)。
2020年3月1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实施,这被认为是我国自接入互联网以来专门针对网络传播内容制定的最全面而系统的规范性文件(易前良,唐芳云,2021)。何为“网络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指出,“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以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为目标,开展的弘扬正能量、处置违法和不良信息等相关活动”。“规定”以《网络安全法》等为依据,就网络内容“提倡”、“禁止”、“防范”三方面做出列举,为网络内容治理提供了系统指引。
近年来,以《网络安全法》①为基础,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②随着对“全平台网络传播秩序”加强管理,网络领域以习近平总书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为指导,对不断以新的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出现,扰乱网络空间良好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特别是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生态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大治理工作力度。“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③“由治标为主向治本发力的工作定位,围绕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的工作主线,重点强化专项整治和基础管理,实现网络生态治理由局部治理、分散治理、应急治理向全面治理、系统治理、日常治理转变”。④
2021年是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的重要年份。诸多部门或单独、或联合对网络生态环境进行集中整治行动。其中如国家网信办牵头进行的2021年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⑤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安排部署的“新风2021”集中行动⑥等。行动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的核心任务——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整治春节期间网络环境,打击网络水军、流量造假、黑公关,治理算法滥用行为,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规范网站账号运营,整治PUSH弹窗突出问题等。历次“清朗”、“净网”等专项行动都取得了较强的治理效果,几十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被关停,豆瓣网、新浪微博等网站、社交媒体被约谈,平台上的违规“头部账号”被依法处置。2021年1月到11月,全国共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53621亿条(图1 图1见本期第20页)。
从治理理念的不断明确,到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再到行动实践的频繁精准,以及对社会力量的征召发动等,我国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呈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
第一,网络内容治理既是互联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新领域。其中网络强国思想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⑧是两大重要的前置条件。网络强国思想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我国互联网发展治理问题的重大成果,……是我们党管网治网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引领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庄荣文,2021)。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则体现为让互联网技术成为执政资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使其从“最大变量”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增量”。⑨
第二,我国的网络内容治理实践具有鲜明的综合性与延伸性特点。互联网通常被分为三个层次:底层的物理层(包括电缆、智能终端、传感器等物质设备)、中间的逻辑层或代码层(包括互联网协议、应用软件等逻辑规范)、上层的内容层(包括文本、语音和视频等符号系统)(Benkler, 2006:383)。Domanski(2018:11)提出互联网治理的四个层次模型:基础架构层、技术协议层、软件应用层以及内容层,相当于对“中间层”进行了拆解。有学者在分析我国的在线内容治理时,考虑到“内容治理实际上是对信息传播行为的制度约束”,因此仅做了“技术层”和“内容层”区分,前者是基础设施,包括物理层和代码层的互联网协议部分;后者指对代码层中各种应用软件的开发与使用,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内容(易前良,唐芳云,2021)。对照我国网络内容治理框架来看,治理的范畴和层次在结构上不是拆解和细化,而是覆盖面更广,包括甚至不限于对技术层的标准制定、对平台企业的责任要求、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治理,以及网民的互联网使用规范等。
有研究认为,我国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平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维护个体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解决之道在于维护公共利益,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属性,具体策略是建立“政党和政府主导—企业高度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治理模式(朱瑞,2021)。落实到中国当前的情况,还存在现实中真正塑造和规范互联网运行方式的种种实践。
网络内容治理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系统”形态。之前较多研究认为,平台是“系统”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旨在组织用户之间(包括企业实体和公共机构)进行交互的一种可编程的数字体系结构”(席志武,李辉,2021),平台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实质性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但是在国内网络内容治理格局中,以平台为体现形式的互联网企业既是治理的一个层次或环节,同时也是被治理的对象,平台的治理主体身份仅在其作为“治理代理”时成立。因此,本报告尝试将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的整体看作一个“生成中(becoming)的系统”。卢曼认为,社会或社会系统外在于每一个其中的具体行动者,有其自身的逻辑,保持一定的封闭性。系统中最小的分析单元不是个体,不是行为,而是沟通(Kommunikation)(Luhmann, 1998:13)。同时,系统的复杂性通过结构来调整,即“对能容纳的可能环境条件”进行选择,不断将外部多样化、异质性的行动者卷入和吸纳进系统(卢曼,2008/2013:183)。在系统内,不同的行动者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这也是保持系统运行的动力来源(阮晓眉,2011)。
由此,本报告尝试改变通常限于“内容层”对于网络内容治理的结构与范畴的划分,取径在具体情景中“谁”(治理主体)—“如何”着手(治理实践)—获取“什么”(治理效果)的思路,强调社会现实是被共同“选择”实践出来的,而这种选择又是如何与系统的期待相符合的。我们尝试从2021年我国网络内容治理领域众多事件中选取8类代表性问题,以更小的分析单元——传播(communication)切入,聚焦更为抽象的分析角度——要素治理和关系协调,这势必考察涉及“代码层”或“技术层”意义上的“网络内容治理”。
一、网络内容的要素治理:数据化、数据滥用与平台数据主义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第六条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范畴,与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并列。数据,按《数据安全法》定义,“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第三条)。
数字化和数据化是智媒时代在线内容生产、消费、挖掘、流通的核心特征,社交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一个以数据和元数据(metadata)价值为基础的“数据驱动社会”。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测,到2023年,中国的数据量将达到40ZB,其中超过80%是非结构化的数据。⑩
数据化(datafication)是平台运行的三大机制之一(何塞·范·迪克,孙少晶,陶禹舟,2021),基于海量不同平台生成的元数据曾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副产品。但一方面这些元数据并非价值无涉,而是通过平台“有目的”服务被提取出来的(boyd & Crawford, 2012),另一方面,随着元数据逐渐可以被挖掘、丰富和重新利用,数据在网络的不同层次中皆可作为动力资源发挥作用(杨洸,郭中实,2021)。在智能传播所涉及的技术层和内容层中,有数据参与的内容挖掘与生产、用户精准画像、个性化信息推荐、智能信息感知等将人—信息—场景连接起来,完成闭环。
在对数据无限追求的同时,随着5G技术的普及,企业数据将成为中国数据的主流。在2021年的网络内容治理中,我们发现以对数据要素进行治理而间接对内容进行治理的形态,即通过治理“数据”这一市场要素来规范和调整网络内容生态秩序。这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出台、App治理中基于数据保护的界面互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伪造的社会风险,以及超级平台链接的互通互联等。
(一)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治理的“中国方案”
2021年8月,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9月,网信办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12月31日,《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出台,发布部门扩至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四家,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这个“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算法治理的2.0版本,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方案”。[11]【解读】随着算法与国家、社会、个体之间不断关联日益融合,这一泛在的推促性技术(nudging technology)(Thaler & Sunstein, 2009)可以跨越地理空间,折叠时间序列,将自然的、社会的、人与非人“对称地”关联起来,网络效应“召唤”出更多基于行动的参与要素,经由算法技术形成互联。在算法驱动的推荐系统中,所有的数据组合形式都要通过算法输出,并与技术逻辑、数据集结构、应用场景等关联。算法治理面临两组核心矛盾:第一是对于作为系统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OPP)的技术装置(Callon, 1986),如何识别出算法自身潜在的技术—社会风险;第二是对于算法技术的使用,如何在风险控制与推动应用中找到适合平衡点。此“规定”可以看作是一次对我国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廓清,显影出目前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政策矩阵”。
比对先前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对算法推荐的管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首先,对算法的规制更加突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科技伦理的审查提上议程;第二,治理主体分层定位更加明确,其中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治理与监督管理工作,电信、公安和市场监管等联合成为治理主体,地方与之相对应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的相关工作;第三,对于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新增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针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反垄断和适老化的要求,同时完善了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条关于申投诉流程与投诉举报内容;第四,强调算法推荐服务的提供者要配合管理部门开展安全评估和监督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数据等支持和协助;最后,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处罚力度有所加强。
对于算法驱动的中介技术而言,一个需要着重关注的要点是其具有结构性的“固向强化”效用(Feezell, Wagner & Conroy, 2021)。在此“规定”中,我们可以从管理导向、动员能力、权益保障、场景适用四个层面发现对算法进行治理、与算法进行交互的特点:
第一,在法律层面落实“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要求。[12] “规定”将坚持正能量、禁止推荐违法信息、落实主体责任等,列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最重要规范,同时在信息安全、模型数据管理时要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
第二,尤其关注算法的传播和动员能力。“规定”多个条文涉及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按2018年《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信息服务,还广泛涉及开办论坛、博客、微博客、聊天室、通讯群组、公共账号、短视频、网络直播、信息分享、小程序等信息服务或者附设相应功能。“规定”不但重申涉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要依法取得许可,在服务过程中不得生成合成虚假新闻信息或者传播非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并且对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出了备案要求,通过立法技术将对算法的监管延伸至逻辑层和代码层。
第三,针对用户面对算法的无奈地位,此次“规定”一个备受瞩目的规范是“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要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用户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第十七条)。该条款赋予用户脱离被困在算法里的主控权,可以“以退为进”自主决定是否采用算法推荐服务,以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13]之前很多服务应用已经允许用户自主选择是否采用算法推荐服务,但其过程往往比较复杂,不易实施。现在“规定”对于用户可退出算法推荐服务的规定,不仅是要求用户对于是否采用算法推送可以自主选择,同时对算法的价值导向、计算过程、模型选择、数据应用等均做出要求,实现全流程覆盖。
第四,数字接口与用户贴近的场景适用。“规定”主要针对的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即算法技术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方面的应用。虽然对于算法的定义和边界有多种划分方式,算法“弥漫”在计算机与网络设施的固件、硬件、系统、应用、服务的多个层面和多重连接之间,但是“信息服务”却是和人、和用户最为贴近,最直接相关的交互界面。因此可以说,“规定”主要针对的就是与用户的在线信息获取与接触直接相关的算法技术与应用服务,比如搜索引擎、推荐引擎、精准广告等。
前举七部门的“指导意见”为完善算法治理设立了三年期限,可以预见“规定”在实施过程中还将进一步改进、发展。
(二)彰显信息内容基础公共服务地位的App治理
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清粉软件违规调用通讯录、不全授权就不能用,要求删除个人信息被拒等问题,3月21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明确了39种类型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使用时所需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App运营者不得因用户不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使用App基本功能服务。4月26日,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了“知情同意”、“最小必要”两项重要原则,从事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有关主体违反要求的,依次按通知整改、社会公告、下架处置、断开接入、信用管理流程进行处置。11月,工信部还印发了《关于开展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已经收集的个人信息清单和与第三方共享的个人信息清单,在App二级页面展示。
【解读】根据中国信通院(2021)《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个人信息保护治理白皮书》显示,截至2021年9月,我国App在架数量达274万款,第三方应用商店在架分发总量达到2.0164万亿次。截至2021年11月,App专项整治行动共开展21批、对5406款App发出整改通知,公开通报对于2049款整改不到位的,下架540款。对于App侵害用户权益的专项整治行动共开展5批,累积通知539款违规App进行整改,公开通报145款,下架11款。其中排名前4位的问题分别是私自收集个人信息(20%)、账号注销难(16%)、过度索取权限(15%)和私自共享给第三方(14%)。
一般来说,对于App治理的分析和解读都会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切入,这也是2021年为了准备和配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在网络内容治理方面的重要举措。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中对不同类型App所必须收集的个人信息的规定可以发现,其实大量传统意义上与信息内容相关的App服务类型——比如新闻资讯类、网络直播类、在线影音类、短视频类、电子图书类、浏览器类、拍摄美化类、远程会议类等,都无需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这表明,如果用户不需要其他增值服务,这类App无权索取用户个人信息。
虽然规定如此,但违规情况并不罕见。根据上述信通院“白皮书”显示,恰恰是“教育学习类、金融服务类、新闻资讯类是违规最多的应用类型”(中国信通院,2021)。当前,用户的数据问题已经从单纯的“个体信息”和隐私保护的单一维度扩展至“个体权益、企业竞争和生产关系”三个维度(戴昕,2019)。对于数据的所有权、企业对基于用户数据新技术的创新性使用、数字社会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资料如何在使用和保护上找到平衡,不同路径的观点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研究分析了数字平台与用户之间经济关系的三种路径——“作为劳动的数据”模式、基于订阅费改革的用户付费论,以及基于用户数据劳动的集体转移支付路径——认为“从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数据议题,需要将其与全球数字竞争格局、数据驱动型经济、国家大数据战略、产权制度创新等政治经济议题结合起来考察”(徐偲骕,李欢,2021)。
“数据价值释放的重点不在产权配置,而是更应关注流通规则”,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工作。[14]对不同App类型就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范围所进行的规范,是从源头上对“数据石油”应当如何进行采集和分配进行的约束。而与信息内容相关的App至少在这个方面,公共服务的属性相比商业增值,更加处于基础地位。
(三)预防滥用人脸识别导致“深度伪造”风险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助力社会治理和疫情防控的同时,开始快速渗透到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2021年“两会”上,人脸识别再次成为热议话题。央视3·15晚会曝光了科勒等品牌的门店,通过摄像头的人脸识别管理系统,在未经进店用户知晓和允许的前提下为每一个通过者建立ID,并进行用户数据分析。在广泛关注和呼吁下,人脸识别管理规制措施陆续跟进实施。3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收集、使用个人生物特征等敏感信息的,应当逐项取得消费者同意”。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物业服务企业以人脸识别作为进出唯一方式;未征得个人同意搜集、处理人脸信息;未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人脸信息安全导致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等行为,均认定为侵犯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与人脸识别数据相关的涉及“深度伪造”的问题也是2021年网络内容治理的重要方面。2021年3月18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加强了对语音社交软件和涉深度伪造技术的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尤其是“加强对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相关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管理”。[15]6月11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要求“社交软件、网站、论坛等互联网平台要严格履行信息发布审核的主体责任,全面清理平台上发布的涉摄像头破解教学、漏洞风险利用、破解工具售卖、偷拍设备改装、偷窥偷拍视频交易等摄像头偷窥黑产相关违法有害信息”。[16]【解读】国家标准GB/T38671-2020《信息安全技术远程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将“人脸识别”定义为“以人面部特征作为识别个体身份的一种个体生物特征识别方法”,其通过分析提取用户人脸图像数字特征产生样本特征序列,并将该样本特征序列与已存储的模板特征序列进行比对,用以识别用户身份。[17]2021年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脸信息列入敏感个人信息。[18]人脸识别的社会风险涉及数据、算法和应用三个环节,包括隐私侵犯、群体歧视、识别错误、数据滥用等(曾雄,梁正,张辉,2021)。人脸识别或者“刷脸”的风险不限于“把人认出来”的身份识别过程,而重在通过人脸验证/人脸辨析进行的其他关联分析,从纯粹的身份识别机制转换为识别分析机制(韩旭至,2021)。
而在公共场合未经个人同意通过技术手段暗中搜集人脸信息的做法不仅构成了对自然人人格权益的侵犯,这样搜集、泄露、交易的数据还会为“深度伪造”提供生产资料。此次在对摄像头偷窥等黑产的集中治理工作中就发现,在18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视频监控云平台发现了SQL注入、越权操作等高危漏洞,对联网摄像头的全面排查中发现4万多个弱口令、未授权访问、远程命令执行等漏洞,取证处置的有500余个,约谈了4家存在隐私视频泄露的视频监控App厂商,并督促其完成整改。[19]“深度伪造”(Deepfake)是依托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和模型自动生成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的技术(王禄生,2019),其过程首先需要进行广泛的人脸数据搜集,然后借助软件进行特征提取,为下一步的机器深度学习提供数据资料。深度伪造背后的支撑是深度学习算法,深度学习算法依赖海量训练数据,用于训练的真实数据越多,合成的音视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就越逼真,即便是专业软件和鉴定人员也很难识别。
“深度伪造”的危害性在于,它让“眼见不一定为实”,破坏人们赖以辨别真伪的方式,一键式的操作让伪造“平民化”。国外近年来已经出现多起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给明星换脸、生成网红的色情内容,以及出于政治目的假造公众人物演讲视频的案例;而长期真假内容边界的模糊还会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媒体、社会、政体的不信任,引发社会伦理危机和负面连锁效应(赵国宁,2021)。
数字公用事业与传统公用事业的重要区别在于:数据化作为权力来源,不仅有赖于算法、技术和非人类等自然资源,而且更关键和更密集地依赖于人类自身(Chen & Qiu, 2019)。2021年对深度伪造技术的治理,表现出对人脸识别技术滥用的社会后果与现实影响力的关注,尤其涉及舆论和社会动员能力的时候。要具体考察“技术在何种场景下以什么目的如何被使用”依然是技术—社会治理中对“技术没有善恶,但绝非中立”风险的重要的判定方式。
(四)推动数据可携带与互操作性进行平台反垄断
9月9日下午,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要求,9月17日前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在9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布会上,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表示:“无正当理由来限制网址链接的识别、解析和正常访问,应该说严重影响了用户的体验,也损害了用户的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20]《反不正当竞争法》在2017年修订时,已就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列出禁止专条(第十二条)。主管部门一贯注意依法保障网络通畅运行,维护用户合法权益。早在工信部提出要求之前,4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就曾联合召开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强调应“严防网络平台企业实施系统封闭行为,确保生态开放共享”。[21]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限流、屏蔽、商品下架等方式,减少其他经营者之间的交易机会。9月13日,腾讯、阿里、字节跳动回应了工信部整治要求。
【解读】“平台位于我们生活的中心”(Gehl & McKelvey, 2018)。中国社会对现代化、全球化的追求构成了数字平台兴起的政策基础(段世昌,2021)。范·迪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平台:一种是中介平台,一种是行业平台。前者是组建其他基础平台和应用程序的生态系统,也可称为超级平台(super platform),后者则是为特定行业和市场提供垂直服务的平台(何塞·范·迪克,孙少晶,陶禹舟,2021)。
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铭刻物质性与数字物质性(束开荣,2021),而平台的逐渐“基础设施化”则表现为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从原有体系中脱嵌出来。通过对平台历史(platform historiography)的梳理发现,平台开放与垄断的“一体两面”体现在其“从连接器到工具箱,再到行业生态的开放进程与从数据到基础设施,再到产业融合的垄断指控,平台企业以数据做链接,以基础设施搭建工具,在模糊的产业边界中构建行业生态的策略投射”(毛天婵,闻宇,2021)。
Srnicek(2016)认为,垄断是平台的DNA。平台的垄断问题来源于其滥用数据垄断,而平台间的链接屏蔽体现出平台的垄断趋势。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平台“二选一”行为不是“本身违法”,但利用用户对于平台中介的高度依赖性所进行的强迫排他行为会严重妨碍市场竞争(王晓晔,2020)。平台通过海量的多样化数据搜集分析,将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能有效把握市场的动态运行规律,更精准有效地施行各项竞争行为。通过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平台企业能够凭借已经积累的数据优势,维持和扩大市场力量,提高市场进入壁垒,降低市场有效竞争。
平台的互联互通,其核心问题在于推动用户数据的可携带性和平台间的互操作性,建立平台间的无障碍连接,实现数据互操作和开放生态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个人信息可携带权,按照通常理解,应该包括数据主体有权从数据控制者处获取个人信息副本,以及请求数据控制者直接将其个人信息传输给另一实体。对于用户来说,“互操作”可以在不同数字服务之间进行相互通信,增强用户的协同工作的能力,让不同平台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互补性的操作。“互操作”可看作是用户基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依法行使的合法权利,这也可看作是通过规范数据权利来间接治理信息传播生态。
二、作为关系协调的内容治理:在政府—行业—平台—用户之间
在社会治理的理论中,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以及“持续的互动”(沙垚,张思宇,2021)。在文化/传播治理中更要注重“多元行动主体”的“互动合作”(王前,2015)。之前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具有“政企发包制”特点,即政府将网络事务的具体治理权发包给非公有制企业,并附加高强度的负激励,同时自己保留监督权和奖惩权。这样既规避了产权安排的约束(平台为非公有制单位),也节省了直接管理平台的治理成本,当然它以政企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为前提(于洋,马婷婷,2018)。还有学者认为,政府限于多种原因难以对互联网做到精细化管理,只能借助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介力量,尝试进行间接控制。在这种治理格局中,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实际上能够发挥裁判乃至替代性决策的作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信息流动的“守门人”,在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主体地位,它有能力也有义务对其平台上所产生的犯罪风险进行前置性防控,这是网络平台提供者承担主动审查义务的正当性根据(敬力嘉,2017)。
鉴于网络内容治理目前所呈现的综合性和延伸性特点,本报告尝试不预先设定行动网络中的“主体”是谁、身份如何,而是从“关系”的结构形态出发,“识别”在具体的语境和场景中被征召进入网络的行动者,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带来了哪些能动与可能性(Latour, 1996)。
(一)突出公众账号管理中的平台责任与自媒体身份
2021年1月25日,国家网信办对2017年《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公众账号管理规定”)作出修订后发布实施。10月26日,网信办又就2015年《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信息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做出修订发布征求意见稿。前一个规范性文件业已生效;后一个尚属征求意见文本,但从中可以看出主管部门的意图走向。
此次“公众账号管理规定”修订是顺应“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呈现出专业化、组织化、商业化等诸多特点”,[22]依据《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强调打击虚假信息、虚假流量等违法违规行为”。[23]新规共23条,包括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内容和账号管理主体责任、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信息内容生产和账号运营管理主体责任、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分级分类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及行政管理等条款。而“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的修订则重点关注账号身份的真实性问题,要求平台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保证注册账号的真实与合规。
【解读】国家信息中心2020年4月发布的《2019中国网络媒体社会价值白皮书》显示,中国传媒产业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其中互联网传媒占据了传媒业市场的八成。传媒产业发展进入大众自媒体传播时代,“网络媒体作为技术创新和融合变革的先行者,既有责任引导网民的理性追求、促进网络空间的理性回归,又有动力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扩大正面影响来提升自身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24]此次对“公众账号管理规定”和“账号名称管理规定”的修订,突出对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公众账号运营者“双重身份”的确定。通过对内容安全(导向性、真实性、合法性)、账号运营安全(依法、文明、规范)以及禁止行为(虚假冒名注册、违规采编新闻、制造虚假舆论、恶意营销诈骗、抄袭伪原创、煽动网络暴力、非法买卖账号等)三大方面的廓清,这两项规定将负责和维护在线内容生产生态的责任落实到平台和自媒体上。
“平台既是一个市场,又是一个企业”,这种独特的组织结构“至少在人类商业文明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冯建华,2021)。平台的双重属性使其难以找到市场公共利益与企业私人利益的平衡方案,这是平台治理遭遇困境的根源(李良荣,辛艳艳,2021)。在“国家—平台—社会”三方治理格局呈现“私有制属性,社会化监管”的特征下,对公众账号运营者的双重身份的确认,更加强调在主管部门和平台监管的结构性上,公众账号运营者的能动性可行的边界与禁忌。
而平台的“主体责任”在配合“账号名称管理规定”时更加得以彰显: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签订协议,提供真实身份信息,遵守平台内容生产和账号管理规则、平台公约和服务协议。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在注册账号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负责监管六类假冒、仿冒、捏造名称的网名不得使用。[25]对于为何要落实、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身份,在10月20日国家网信办部署推进的“清朗·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思路中可以看出端倪:清朗专项整治行动的目标,是要“强化统筹协调,进一步加强账号注册、使用和管理全流程动态监管”。而对于这个目标,平台处于关键性位置——对于账号注册、使用和管理的全周期动态进程,平台具有无可取代的后台基础设施属性。由此可见,在治理的权限上平台的主体责任更为重大。这也可以对照理解9月16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的意见》,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网站平台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10个具体工作要求,目的就在于指导督促网站平台补短板、强弱项、提水平,确保网站平台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二)短视频乱象的运动式治理与治理常态化
根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73亿,使用率接近90%,日均使用时长达120分钟。[26]短视频已成为最受网民欢迎的新兴信息传播方式之一。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发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乱象不断: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部分用户为了蹭热度、博流量,借东京奥运会运动员恶意炒作、营销谋利,受到平台处罚和封禁;因短视频走红的“拉面哥”、“菜馍老奶奶”等草根网红被卷入流量漩涡,频遭身心干扰、利益裹挟和权益侵犯;为博眼球恶意编造散布疫情谣言,“随手拍”短视频成为涉疫谣言的主要源头;小红书向用户推送未成年人身体隐私短视频,围观的评论、弹幕中存在性暗示……
2021年1月8日,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称2020年共接到900余条举报线索反映抖音平台传播色情低俗信息。北京市“扫黄打非”办指导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对“抖音”平台进行了约谈,对抖音做出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责令立即改正有关违法行为。
【解读】短视频制作者作为“数字灵工”,具备就业灵活、创意灵气、市场灵捷的特点。抖音、快手等平台通过直播和短视频拍摄创造的“灵工”新业态,融合创意、创新、创造等新形态,成为平台经济时代新的工作范式(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
强调视觉化、碎片化、场景化和直观体验(陈世华,陈佳怡,2021),短视频因其特殊的文本特点和叙事逻辑,复杂的内容产销关系以及独特的生产运营模式,在塑造媒介市场新景观的同时,也出现一系列失序现象。[27]2007年出台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对于如今大量低门槛、个体化、碎片式的UGC短视频内容,难免捉襟见肘。治理规则落后于社会乱象是一种常见现象,运动式治理成为一种选择。运动式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以“元治理者”的身份推动企业形成合乎公意的“个体自治”(肖红军,李平,2019)。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国家推行社会改造的愿望十分强烈,同时拥有强大的道义合法性和权力(冯仕政,2011)。在愿望、合法性和权力三种因素的共同驱动下,国家不但倾向于而且能够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改造社会所需要的资源,形成以弘扬正气为中心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属于事后治理的范畴,且仅通过运动式治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杜绝乱象。从组织的角度来看,运动型治理与常规型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双重过程和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既相互矛盾,又互为倚赖,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在常规治理之外,运动型治理发挥的是一种“纠偏”的功能(周雪光,2012)。除了主管部门监管外,相关平台行业的自律日益发挥重要作用。2019年1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与《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两件行业规范出台,明确了内容先审后播、优先推荐正面内容、积极引入主流媒体和党政军机关团体账户、建立总编辑内容管理负责制度和审核员队伍。2021年11月29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严管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网络表演,并对借助未成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间或者短视频账号,或者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等吸引流量、带货牟利的账号依法予以严肃处理。这些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对短视频内容的治理从运动式向常态化的过渡(曹钺,曹刚,2021)。
(三)对未成年人网游沉迷的“数字断连”保护
2021年6月施行的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列有“网络保护”专章,其第七十四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第六十八条规定新闻出版、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都负有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开展宣传教育,监督网络服务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义务。8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7月,国家网信办启动的“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其中第七类问题就是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问题。
不过“防沉迷”措施遭到干扰和暗中抵制:租号、借号、买号、利用断网等破解“防沉迷”的方法和教程在网上传播甚广。9月6日,话题#花33元租号打2小时王者荣耀#冲上热搜。据央视新闻报道,网络上可以通过租号、买号等途径绕过监管无限制玩网游,游戏账号租卖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在某购物平台,输入“手游租号”等关键词便可以轻松查找到大量的租号商家。有商家在销售过程中非但不主动核实买家的年龄情况,甚至将“无防沉迷”作为卖点之一。9月8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对腾讯、网易等重点网络游戏企业和游戏账号租售平台、游戏直播平台进行了约谈,要求其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深刻认识严格管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解读】游戏成瘾(game addiction)的概念源于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但是网络游戏高度沉迷(high engagement)有别于网络游戏成瘾(Charlton & Danforth, 2007)。高度沉迷的特征是频繁游戏,并伴随轻微过度游戏的症状,而成瘾除了具备高度沉迷的特征之外,更有过度游戏的危害性表征:比如行为的凸显(沉迷)、抵触(自我矛盾或与他人冲突)、退缩和复发。借鉴青少年酒精、药物、赌博成瘾的研究对青少年网游成瘾的抑制性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只有兴趣转移和父母监控与网游成瘾呈显著负相关,经济开销之类对于网游成瘾影响则很小(胥正川,2009)。
尽管与其他传统媒介相比,游戏玩家多被认为是“积极受众”,但在游戏内他们仍处于被动地位,玩家并不能真正对游戏世界的发展进程进行掌控。玩家的绝大多数行为仍是按照游戏设计者的预设而进行的。相比成为“越轨玩家”,更多人更关注如何在已有设定的规范下实现自己的目标。游戏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技术,当沉浸在游戏内容时,人们的注意力既不在外部世界,也不在技术本身,而是被困在游戏内容为其所创造的想象世界中,游戏世界与外部世界成为两个平行的宇宙。游戏虚拟情境设置背后隐藏更多的是游戏设计者的意图,其目的在于保证虚拟空间的完整性和封闭性,以此赋予玩家游戏行为合理性。玩家与游戏角色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李彪,高琳轩,2021)。
成瘾是一种“过度连接”的问题。美国科普记者迈雅·萨拉维茨(Maia Szalavitz)认为,成瘾是“一种被奴役或者被束缚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愿选择”,成瘾是一种学习障碍,通过特定的学习路径达到心理学上的目的,这一过程会让成瘾行为变成自发的具有强迫性的行为(萨拉维茨,2021:8)。而对于成瘾的刻板印象,强化了社会从法律、文化和社会观念上的偏见。
虽然通过强制的“数字断连”可以使得技术使用者全部或部分放弃连接功能,但对未成年人网游成瘾的监管更是一种基于时空—行为的战略控制。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中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要求重点排查解决网站平台防沉迷系统问题漏洞,解决“青少年模式”入口不显著、识别不精准、专属内容不够丰富、应用效果不佳等问题,进一步优化模式效能,着力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最初游戏防沉迷要求是所有的网游玩家需要身份验证,然而当时的防沉迷系统并没有与公安系统联网,网上的身份信息泄露现象泛滥、身份证生成器随处可见。而后各大游戏厂商收紧了防沉迷举措,未成年玩家用父母的身份证注册游戏的案例屡见不鲜。直到国内部分游戏厂商实行了“宵禁”、“夜间巡航”、“人脸识别”、“识别定位”等措施,大部分未成年玩家才真正有效地被监管起来。但是类似人脸识别的技术成本较高,目前只有少数游戏大厂全面接入该系统,仍然有大量小厂游戏不具备监督、监管、监控用户的能力。可以看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合作、监督。技术层面只是提高了未成年人的准入门槛,但引诱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的因素依然存在。
(四)启动对“饭圈”乱象的“协同共治”
2021年4月底,一段“大量乳制品被倒入臭水沟”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这些乳制品都是粉丝为了给爱奇艺出品的综艺节目《青春有你》第三季选手“打投”应援用的,按照节目规则,粉丝买得越多偶像“出道”的几率越大。由于这些乳制品根本喝不完,于是被白白倒掉形成大量浪费。5月4日,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青春有你》第三季后续节目录制。这一事件掀开了“饭圈”乱象的一角,成为国家网信办“清朗行动”治理“饭圈”的直接导火索。
6月15日,国家网信办启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打击5类“饭圈”乱象行为:一是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等行为;二是“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人肉搜索、侵犯隐私等行为;三是鼓动“饭圈”粉丝攀比炫富、奢靡享乐等行为;四是以号召粉丝、雇用网络水军、“养号”形式刷量控评等行为;五是通过“蹭热点”、制造话题等形式干扰舆论,影响传播秩序行为。8月27日,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规范粉丝群体账号,严禁呈现互撕信息等十条工作措施。
【解读】所谓“饭圈”,通常指因某位明星而集结和行动的有组织的网络社群。“饭”是Fan的音译,“圈”即圈子,也就是一定规模的粉丝由于共同兴趣有组织性地汇聚在一起。传统粉丝的追星行为会被认为是个体的、情绪化的、即时的行为,而当前“饭圈”的追星作为一种集体行动,更加具有组织性、职业化、利益关系(陈丽琴,2020)。根据《粉丝经济4.0时代白皮书》显示,从2018年至今,粉丝经济已经进入4.0时代,粉丝团体具备较强的组织力、传播力与造势力,粉丝在营销活动中的助推力成为不可或缺的传播战略之一,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情感连接进化为养成式追随,粉丝的话语权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甚至拥有部分决策权(Admaster & 新浪社会化营销研究院,2019)。
分析此次整治“饭圈”乱象的行动和通知可以发现,其针对的“乱象”主体,不完全是“粉丝”个体,还涉及如明星经纪公司、职业粉头、营销公号、社交平台等组织与机构;治理的对象,不仅有在线的符号文本生产,还有大量个体行为和群体行动。在经典的流行文化理论中,粉丝文化经常被认为具有“观看”和“阅读”属性,粉丝对偶像是一种单向的“追随”。新技术和数据化的引入使得偶像和粉丝之间存在着“关系劳动”——为保持热度,偶像会通过与个体保持“越界”的亲密感而建立起自身的权威(Bonifacio, Hair & Wohn, 2021)。通过多种技术、在多个平台同粉丝展开多层次的互动,关系劳动中的偶像类似一种“微名人(microcelebrity)”,它与传统名人最大的差别在于,微名人凭借其可接近、相似性、互动性等特征,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真实、亲密的互动交往,与传统名人相比,微名人的模仿成本较低(汪雅倩,2021)。已有研究发现,用户会去模仿他们喜欢的微名人的生活,由于社交媒体能够提供及时的互动,这种模仿范围会越来越广,且越来越深入。对社交媒体微名人的渴望可能会促使年轻用户过度关注外在形象,甚至出现盲目模仿、自我迷失(Wilcox, Kramer & Sen, 2010)。而粉丝通过双向互动,也开始更具参与性和嵌入性,通过对数据、文本、社群、商业关系等的介入式“操作”,粉丝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性和话语权,甚至可以“决定”偶像的“养成”。
一般认为“饭圈”文化具有以下属性:从个体维度看,粉丝依据异质性偏好选择进入“饭圈”,具有物质性和筛选性等特点;从群体维度看,粉丝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子群体,他们各司其职,构成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生态圈;从组织维度看,粉丝的角色分工、组织形态与运作模式展示出了清晰的规则体系和等级结构;从文化维度看,“饭圈”已经形成内部专属的话语体系与运作规则(吕鹏,张原,2019)。而经由粉丝的“操作性”所带来的饭圈文化并不意味着文本的消逝,而是转化了文本构成与消费的方式(崔迪,2021)。
“操作性”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可以使粉丝通过技术接入形成广泛的商业连接,而这种连接可能被技术霸权与资本力量驱使,同时引发技术滥用与情感断层问题。通过干预各类平台的数据设定,对偶像和特定内容的显现进行调节,粉丝的这种“操作性”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单向追随或者双向互动,更像是一种“技术行动”。“饭圈”对偶像的劳动付出与购买消费不再遵循平等与自愿原则,而是带有道德束缚性的必须义务(刘海明,冯梦玉,2021)。8月12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饭圈”乱象愈演愈烈的背后,是资本以流量变现的商业逻辑——“以矛盾造热度,以热度换流量,以流量谋利益”。仅将“饭圈”视为一种以青年族群为主的文化圈层将会忽视“饭圈”的消费内涵。而网络过度使用、网络隐私侵犯、网络暴力冲突等问题(黄楚新,2021),映射出中国青年文化的多样态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不确定性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品位断层和媒介素养断层(吴炜华,张海超,2021)。
因此从治理的角度上来说,“饭圈”乱象所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粉丝个体的文本生产与介入行动,也包括群体行动和商业模式,还包括创意行业、娱乐产业的规范与生态。对于“饭圈”乱象的治理体现出政府部门与企业平台的“协同共治”特征,这样的模式在未来还将成为更加长期、持久与常态化的监管体系。
三、总结与讨论
随着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媒体在极大提升新闻传播效能的同时,也因引发了颠覆性的传播变革而对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在行政驱动的制度惯性下,网络治理的理念和手段仍难以完全脱离传统媒体时代宣传工作的管理思路与做法,盘根错节的“多头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带来的产物(冯建华,2021)。之前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网络社会与传统物理空间的区别,沿用传统物理空间的法律治理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思考网络社会的治理问题(郑智航,2018),一度造成互联网法规政策纷纷出台,规则重叠、规制冲突等弊端(周妍,张文祥,2019)。网络空间多头并置、相互交错的密集式立法立规,不仅难以提升法律实施的整体效果,反而推动立法层级及其威慑力的不断加码。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风险,只要将风险控制在社会承受范围内,适当的风险不但无甚大碍,反而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处处力求消除风险的社会,其结果只能是停滞不前(劳东燕,2007)。
Domanski(2018)曾经对于互联网的治理层次提出过政策设计“三步走”:即对于每一个层次,都可以问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治理这一层?谁来治理?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三个问题的指向,也即通俗话语中的对于互联网的治理如何“管得住,管得好”。詹姆斯·斯科特(2019)从国家视角进入,对人类社会的改善项目提供过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即可以从社会可供性、意识形态特征、国家决策与行动能力,以及公民社会基础进行分析。由此来看2021年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具体政策和实践的话,可以发现有若干鲜明特征:
第一,我国的网络内容治理进入超级治理阶段
前期发展积累的技术可供性与社会对于技术的接受扩散度为治理提供了前置条件,“中国互联网之所以能在初期就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深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耦合,更重要的,它是20世纪世界经济体系运作的必然结果”(王梦瑶,胡泳,2016)。对于超级平台的反垄断、对短视频内容的运动式治理、对社交媒体头部账号的治理、对“饭圈”技术行动的规范等,治理对象均是社会结构中的主干、头部、海量的“庞然大物”。这些超大型、超级事物的出现与成立,有赖于我国互联网自引入以来狂飙突进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手机等智能设备的发展和普及,甚至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线上生存、生活渐成常态,这些都对超级平台的生成和流量向头部集中的趋势产生影响。由于当前我国互联网内容治理不仅限于传统技术意义上的“内容层”,范围和形态都更加复杂丰富,因此超级治理的对象是数据化、数据中心主义,以及其所带来的资本与秩序问题。
第二,国家主体的决策行动能力起到关键作用
基于中央层面的实施的治理主体(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等)不再是“九龙治水”各司其事的分散治理,对治理客体的联合行动、协同治理集结和发动起整个治理系统;各地网信办和配合单位在执行层面通过对上负责、绩效考核的形式,进一步落实来自中央层面的治理协调任务。比如,在2021年1月31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加强全平台网络传播秩序管理》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管窥作为共同参与治理的行动者的来源和分布:
北京网信办、上海网信办、广东网信办负责同志以及央视网、澎湃新闻、腾讯公司、新浪微博、哔哩哔哩、斗鱼直播负责人作了发言。中央新闻网站、中央新闻单位新媒体部门、地方新闻网站负责人,商业网站、应用程序、浏览器、微博客、音视频、网络直播、搜索引擎、即时通信工具、论坛贴吧、信息分享、公众账号平台等各类商业网站平台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网信办负责同志,中央网信办相关业务局(中心)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这并不是最全的列表,也不一定每次治理行动都会动员全部行动者参与,但这标记出了覆盖政府职能部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社交媒体、商业网站、应用程序等多种类型来源的“治理行动者网络”,而在层次上,除了中央直属单位和部门,地方和相关业务部门也参与部署会议。这些“异质”的行动者汇聚在“全国网信系统”这样的网络结构中,每一个既是网络中的节点,又是节点自身能动性的体现。
第三,征召公众和社会配合治理实践施行自律
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上线三周年之际,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文明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和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于9月1日联合发布了《“抵制网络谣言共建网络文明”倡议书》。倡议书提出了“严守传播秩序、完善治谣格局、辟除网络谣言、共建网络文明”四点倡议。这些一方面要求公众及其所进行的行为,比如开办公众号、在线发言等,需要履行法律法规义务,不得从事和进行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公众需要配合“好市民”的要求,比如App治理工作小组发动群众对违规App进行检举举报,国家网信办12377网站开设举报专区欢迎网民参与到网络“清朗”专项行动中来等,均对公众社会的配合进行了动员。此外,2021年33家互联网平台联合签署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反垄断自律公约》,百家游戏企业签署《网络游戏行业防沉迷自律公约》,近百家网站平台签署《互联网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建设文明网络生态承诺书》,《网络游戏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互联网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团体标准发布等,实际上是通过发动社会力量,通过行业自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同治理网络、共建网络文明的局面。
第四,网络内容治理的客体颗粒度逐渐细化
在国家网信办6月7日组织召开的“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网络”的专题会议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治理模式的若干重要特质:首先是问题导向的精准打击,此次专题会议治理的对象是“境外赌博集团利用网络对我招赌吸赌行为”,所以采取的精准打击对象是“涉赌推广链”,既包括网络直播、短视频、网络阅读、婚恋网站及贴吧社区等暗中植入投放的吸赌信息,也包括提供有偿推广服务和传播涉赌有害信息的网络平台;第二是诉诸技术源头治理,对为网络赌博活动提供服务的区块链平台及衍生平台应用、服务器托管、网络云存储、通讯传输、VPN服务、CDN加速强化企业监管;第三是线上线下广泛协同,夯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社会举报监督,引导互联网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加强企业内部风险规范管理,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形成长效工作合力。细化治理客体颗粒度的趋势在未来还将进一步强化。
此外,2021年的网络内容治理还体现出一些新变化,比如着力对特定群体的独特需求进行定向保护,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防沉迷,对应用程序的适老化调整,改善老年群体、残障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等。2021年有些文件先发布“征求意见稿”,虽然征求的范围和效度相对有限,但相比之前的直接出台,预留出社会讨论和接受的缓冲期。由于目前网络治理的结构呈现泛化和边界模糊的特征,传统的权威管理和共同治理模式需要创新,“以数据要素为抓手调整信息内容秩序,通过治理信息内容生态来整合社会组织与群体”的“双重中介”模式是当前我国网络内容治理正在进行的探索和调整。■
注释:
①本文依照通行习惯,在法律名称中省略国名。
②至今,网络领域已经形成以《网络安全法》(2016)、《电子商务法》(2018)、《数据安全法》(2021)、《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个“决定”(2000、2012)和若干其他法律中适用于网络的规定为主干,数十件专门的和其他适用于网络的行政法规以及数十家主管部门发布的诸多部门规章组成的网络法律体系,还有大量规范性文件。2021年出台的除上述两部涉网专门法律,还有行政法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部门规章《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用户公共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还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③人民日报(2019)。《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062181034138166 & wfr=spider & for=pc。
④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中央网信办召开全国网络生态治理工作座谈会》。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4/21/c_1620581583568723.htm。
⑤包括春节网络环境(2月4日)、饭圈乱象整治(6月15日开始为期2个月)、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7月21日)、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8月27日)、移动应用程序PUSH弹窗突出问题(8月27日)、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10月18日)、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12月23日)。
⑥包括“护苗2021”、“净网2021”、“秋风2021”专项行动。
⑦新华网(2018)。《习近平: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4/21/c_1122719810.htm。
⑧中国政府网(2014)。《习近平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检索于http://www.gov.cn/ldhd/2014-02/17/content_2610754.htm。
⑨人民网(2020)。《庄荣文:让互联网从“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最大增量”》。检索于http://it.people.com.cn/n1/2020/0716/c1009-31786367.html。
⑩产业信息网数据中心(2021)。《过去10年,全球数据量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50%》。检索于https://www.chyxx.com/data/202104/944168.html。
[11]中国网信网(2022)。《专家解读|平台算法治理制度的中国方案——〈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解读》。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2-01/05/c_1642983970927235.htm。
[12]新华社(2019)。《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检索于http://www.gov.cn/xinwen/2019-01/25/content_5361197.htm。
[13]《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做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做出决定。
[14]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21)。《〈“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解读》。检索于http://www.gov.cn/zhengce/2021-12/01/content_5655197.htm。
[15]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加强对语音社交软件和涉深度伪造技术的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3/18/c_1617648089558637.htm。
[16]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的公告》。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6/11/c_1624994108997096.htm。
[1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0)。《GB_T38671-2020信息安全技术远程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检索于https://img.tezhongzhuangbei.com/file/20201201/9379c348eeafa45ae7f4c9a7a206aebd.pdf。
[18]《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19]同注释16。
[2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国新办举行“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布会图文实录》。检索于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6830/wz46832/Document/1712363/1712363.htm。
[21]财新周刊(2021)。《互联网反垄断大戏连台》。检索于https://weekly.caixin.com/2021-04-23/101697652.html。
[22]法制网(2021)。《国家网信办发布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新规》。检索于https://china.gov.cn.admin.kyber.vip/xinwen/2021-01/24/content_5582219.htm。
[23]新华社(2021)。《国家网信办出台公众账号管理新规?剑指虚假信息、流量造假》。检索于http://www.gov.cn/xinwen/2021-01/24/content_5582211.htm。
[24]国家信息中心(2020)。《2019中国网络媒体社会价值白皮书》。检索于https://www.ndrc.gov.cn/xxgk/jd/wsdwhfz/202004/P020200414717451252380.pdf。
[25]中国青年报(2021)。《国家网信办: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六类情形被禁止》。检索于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027/c1004-32265556.html。
[26]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21)。《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470596893_100065199。
[27]12426监测中心(2020)。《2020年中国网络版权监测报告》。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435421088_120054912。
参考文献:
AdMaster,新浪社会化营销研究院(2019)。《粉丝经济4.0时代白皮书》。检索于 https://www.dx2025.com/archives/58348.html。
曹钺,曹刚(2021)。作为“中间景观”的农村短视频:数字平台如何形塑城乡新交往。《新闻记者》,(3),15-26。
陈丽琴(2020)。饭圈女孩“进化”的行动逻辑与“共意”建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140-150。
陈世华,陈佳怡(2021)。狂欢与沉寂:短视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传播》,(6),133-138。
崔迪(2021)。探索流行文化研究的新进路。《中国社会科学报》,检索于http://ex.cssn.cn/gd/gd_rwhd/gd_ktsb_1651/szjy/202111/t20211119_5375831.shtml。
戴昕(2019)。数据隐私问题的维度扩展与议题转换:法律经济学视角。《交大法学》,(1),35-50。
段世昌(2021)。从“寄生”到“共栖”——淘宝平台如何走向基础设施化。《新闻记者》,(7),86-96。
冯建华(2021)。刑法介入网络信息治理的背景、路径与边界。《新闻界》,(9),65-74。
冯仕政(2011)。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1),73-97。
冯仕政,朱展仪(2016)。政治社会学研究述评——以国家治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韩旭至(2021)。刷脸的法律治理:由身份识别到识别分析。《东方法学》,(5),69-79。
何塞·范·迪克,孙少晶,陶禹舟(2021)。平台化逻辑与平台社会——对话前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主席何塞·范·迪克。《国际新闻界》,(9),49-59。
黄楚新(2021)。警惕资本裹挟下的“饭圈”文化对青年的影响。《人民论坛》,(25),36-40。
黄丽娜,黄璐,邵晓(2019)。基于共词分析的中国互联网政策变迁:历史、逻辑与未来。《情报杂志》,(5),83-91+70。
敬力嘉(2017)。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以网络中介服务者的刑事责任为中心展开。《政治与法律》,(1),50-65。
劳东燕(2007)。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3),126-139。
李彪,高琳轩(2021)。游戏角色会影响玩家真实社会角色认知吗?——技术中介论视角下玩家与网络游戏角色互动关系研究。《新闻记者》,(5),67-82。
李良荣,辛艳艳(2021)。论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双重属性。《新闻大学》,(10),1-15+117。
刘海明,冯梦玉(2021)。数据至上的“饭圈”乱象反思。《青年记者》,(11),40-42。
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一项劳动控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7),42-58+127。
吕鹏,张原(2019)。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中国青年研究》,(5),64-72。
迈雅·萨拉维茨(2021)。《我们为什么上瘾》(丁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毛天婵,闻宇(2021)。十年开放?十年筑墙?——平台治理视角下腾讯平台开放史研究(2010-2020)。《新闻记者》,(6),28-38。
尼克拉斯·卢曼(2013)。《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Robert J. Domanski(2018)。《谁治理互联网》(华信研究所信息化与信息安全研究所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阮晓眉(2011)。鲁曼的沟通运作:一个去人文主义化的转向。《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3),1-37。
沙垚,张思宇(2021)。作为“新媒体”的农村广播:社会治理与群众路线。《国际新闻界》,(1),120-137。
束开荣(2021)。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新闻记者》,(2),39-50。
王禄生(2019)。论“深度伪造”智能技术的一体化规制。《东方法学》,(6),58-68。
王梦瑶,胡泳(2016)。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现代传播》,(4),127-133。
王晓晔(2020)。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现代法学》,(3),151-165。
王前(2015)。理解“文化治理”:理论渊源与概念流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6),20-25.
汪雅倩(2021)。从名人到“微名人”:移动社交时代意见领袖的身份变迁及影响研究。《新闻记者》,(3),27-39。
吴炜华,张海超(2021)。社会治理视阈下的“饭圈”乱象与文化批判。《当代电视》,(10),4-8。
席志武,李辉(2021)。平台化社会重建公共价值的可能与可为——兼评《平台社会:连接世界中的公共价值》。《国际新闻界》,(6),165-176。
肖红军,李平(2019)。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管理世界》,(4),120-144。
胥正川(2009)。网络游戏成瘾的动机及抑制性因素作用的实证研究。《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3),308-314。
徐偲骕,李欢(2021)。平台V.S.用户:谁该向谁付费——数字平台与用户之间基于数据的经济关系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5),25-43+126。
杨洸,郭中实(2021)。数字新闻生态下的信息失序:对数据主义的反思。《新闻界》,(11),14-21+31。
易前良,唐芳云(2021)。平台化背景下我国网络在线内容治理的新模式。《现代传播》,(1),13-20。
于洋,马婷婷(2018)。政企发包:双重约束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基于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研究。《公共管理学报》,(3),117-128。
詹姆斯·斯科特(2019)。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国宁(2021)。智能时代“深度合成”的技术逻辑与传播生态变革。《新闻界》,(6),65-76。
郑智航(2018)。网络社会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二元共治。《中国法学》,(2),108-130。
庄荣文(2021)。网络强国建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学习《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求是》,(3),检索于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2/01/c_1127044103.htm。
周雪光(2012)。《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9),105-125。
周妍,张文祥(2019)。移动互联网下的传播变革及其社会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165-172。
朱瑞(2021)。数字化崛起:中国互联网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结构与动力。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中国信通院(2021)。《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个人信息保护治理白皮书》。检索于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11/P020211119513519660276.pdf。
曾雄,梁正,张辉(2021)。人脸识别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策略。《电子政务》,(9),105-116。
Benkler, Y.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nifacio, R.Hair, L.& Wohn, D. Y. (2021). Beyond Fans: The Relational Labor and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f Creators on Patreon. New Media and Society1-20
boydD. & Crawford, K.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15(5):662-679.
CallonM. (1986)“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196-233.
CharltonJ. P.& Danforth, I. D. W. (2007). Distinguishing addiction and high engagement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game play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3(3)1531-1548.
ChenJ. Y.& QiuJ. L. (2019). Digital utility: Datafication, regulation, laborand DiDi’s platformization of urban transport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6.
Feezell, J. T.Wagner, J. K.& Conroy, M. (2021).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algorithm-driven news sources on political behavior and polariz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6)1-51.
GehlR.& McKelvey, F. (2018). Bugging out: darknets as parasites of large-scale media objects. MediaCulture & Society41(2)219-235.
LatourV. B. (1996).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Soziale Welt, (47)369-381.
Luhmann, N. (1998).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Band 1. Suhrkamp.
Srnicek, N. (2016).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CA: Polity Press.
ThalerR. H.& Sunstein, C. R. (2009).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York, NY: Penguin.
WilcoxK.Kramer, T. & SenS. (2010). Indulgence or self-control: A dual process model of the effect of incidental pride on indulgent choic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8(1)151-163.
本文执笔:方师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万旋傲、卢垚,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感谢课题组专家《新闻记者》特聘顾问魏永征、吕怡然、贾亦凡,《新闻记者》编辑部刘鹏、王侠,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白红义的指导意见。本文为上海市哲社规划智库专项后期资助课题“全球网络平台在线内容治理体系研究”(项目号:2019TFB014)、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第二轮)“移动互联全媒体传播研究”项目子课题“算法社会的结构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