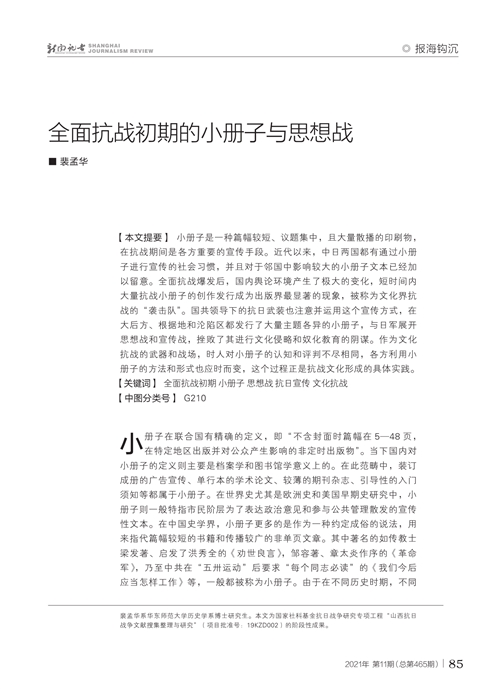全面抗战初期的小册子与思想战
■裴孟华
【本文提要】小册子是一种篇幅较短、议题集中,且大量散播的印刷物,在抗战期间是各方重要的宣传手段。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都有通过小册子进行宣传的社会习惯,并且对于邻国中影响较大的小册子文本已经加以留意。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舆论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短时间内大量抗战小册子的创作发行成为出版界最显著的现象,被称为文化界抗战的“袭击队”。国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也注意并运用这个宣传方式,在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都发行了大量主题各异的小册子,与日军展开思想战和宣传战,挫败了其进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的阴谋。作为文化抗战的武器和战场,时人对小册子的认知和评判不尽相同,各方利用小册子的方法和形式也应时而变,这个过程正是抗战文化形成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全面抗战初期 小册子 思想战 抗日宣传 文化抗战
【中图分类号】G210
小册子在联合国有精确的定义,即“不含封面时篇幅在5—48页,在特定地区出版并对公众产生影响的非定时出版物”。当下国内对小册子的定义则主要是档案学和图书馆学意义上的。在此范畴中,装订成册的广告宣传、单行本的学术论文、较薄的期刊杂志、引导性的入门须知等都属于小册子。在世界史尤其是欧洲史和美国早期史研究中,小册子则一般特指市民阶层为了表达政治意见和参与公共管理散发的宣传性文本。在中国史学界,小册子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约定成俗的说法,用来指代篇幅较短的书籍和传播较广的非单页文章。其中著名的如传教士梁发著、启发了洪秀全的《劝世良言》,邹容著、章太炎作序的《革命军》,乃至中共在“五卅运动”后要求“每个同志必读”的《我们今后应当怎样工作》等,一般都被称为小册子。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情境下对小册子的定义也有不同,因此笔者从以下两方面来确定小册子的范畴:一是尊重历史意见,原则上首先采纳时人对小册子的理解和定义;二是以1964年联合国定义中的短篇幅、非定时、有影响等原则为参考标准,以此筛选能被称为小册子的文本。必须承认,与产生于全面抗战前后庞杂繁复的史料相比,这样的处理思路仍然不够严谨,因此笔者暂时摒弃其他议题的小册而集中关注宣传性小册。
胡适曾将《独立评论》活跃的五年称为“小册子新闻的黄金时代”(胡适,1956:502),这里的“小册子新闻”实际上指的是杂志期刊,罗志田对此有深入研究,他指出“五四后的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杂志的兴起”(罗志田,2003:308)。樽本照雄在研究新小说时也有“清末是一个由近代印刷术支持的杂志时代”(樽本照雄,2002:1)的说法。不论是始于清末还是五四,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杂志时代”确实被广泛关注,它与报纸一道取代了清议,成为当时舆论最重要的载体。这彰显了思想史的研究旨趣,杨国强认为通过各种文本播扬派生的观念要比政治制度更富有支配力和笼罩力,这种直摄人心的力量催动了“近代中国更深层面的新陈代谢”(杨国强,2018:38)。与知识人群体相对的,普罗大众在激变时代的处境也为学者关注,其中李孝悌对上海、西安两地戏曲改革进行实证研究时,已经专门对《革命军》、《醒世钟》等小册子的弹词体裁作了文本分析,并指出这可能是日后各种“走向民众”(李孝悌,2001:242)运动的先河。王汎森也指出,“在一波又一波、各式各样的运动时,真正可能对一般人产生影响的,不一定是长篇大论,更多是改写的、删选的小册子,几张传单,还有几句琅琅上口的新名词或新口号”(王汎森,2017:104)。
由此看来,“杂志时代”发端之际已有小册子的悄然流布,而全面抗战后杂志的“黄金时代”告一段落后小册子反居其上,各种社会群体短时间内集中出版了大量宣传性的小册子文本,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界的显著现象。一些既有研究中已经对此有所涉及,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作为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加以论述,涉及图书出版与审查、舆论变动、抗战文学,以及根据地的出版事业发展等,其中多是利用了小册子资料的实证研究;①二是作为中日思想战的一个面向进行关注,这主要体现为材料的搜集整理,如《华北治安战》中就收录了大量相关史料,近年则以唐立国对日军思想战文本的收集研究为最值得注意的成果。②
小册子作为史料被广泛地使用,是其史料价值的证明,但是以此为中心的专题研究难得一见。实际上早在一战结束之后,日本政府就已经设置了相关的宣传机构,策划对华思想战。侵占东北得手后,又积极部署全面侵华战争,其中陆军省出版的数本小册子被认为是“战前宣言”,对中日社会都产生了强烈震动。面对日方精神征服的企图,中国也有所应对,抗战宣传小册的创作发行是其中的重要面向。全面抗战初期小册子出版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是出版史上罕见的现象,前有生活书店的“黑白丛书”、上海杂志公司的“大时代丛书”,后有国共两党的各种抗敌宣传小册,仅初步统计即有上百种。这些小册子资料是中日思想战交锋的见证,却未见专文探讨,本文关注抗战初期宣传小册子的产生发展,以就教于方家。
一、“飞如蝴蝶”:战前中日的小册子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体战”概念的出现,为政府控制和引导舆论提供了合法性,各国都意识到了宣传对于战争胜败的深切影响,并相继成立专门负责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的公共信息委员会、英国的宣传政策委员会、德国的外部事务中央办公室等等。日本也成立了数个宣传机构,为策动侵华战争营造舆论环境,包括陆军省新闻班、外务省对华情报部、海军省军事普及班等等。其中以陆军省新闻班最为活跃,由其策划出版的数本小册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对宣传小册有所留意,但政治上长期的分裂境况使得难以有统一的宣传规划,因此小册子出版活动多是民间行为。
(一)全面侵华前夕日军的小册子出版
1934年10月1日,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制的小册子《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出版,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与冲击”(郭廷以,1986:943),这也是十四年抗战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小册子文本之一。此小册共分五章,论及国防观念变迁、国防力构成要素、国际形势、国防强化应注意的方面,以及国民觉悟等。总的看来,此文本是军方推进其军国主义思想,为将政府和社会绑上战车进行“总体战”的一个宣言。在日本,政财及新闻界对此的讨论不胜枚举,新闻班和文化同盟甚至专门记录了相关的评论、讲演和座谈会。③军部由此透露出的野心使议会受到极大触动,双方的矛盾一度演变为所谓的“小册子问题”,直到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在议会向首相冈田启介作出所谓“解释”之后才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此事对两国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日本议会的妥协和退让使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侵略战争的轨道。中国方面对此事的认知也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此册发表于记者会上,共计印刷有16万册,国内很快便有人译为中文发行,可见有以下版本:1.敬慈译,刊于《国闻周报》;2.张孤山译,刊于《军事汇刊》;3.冯白桦译,中央航空学校出版;4.译者不明,人民印务局出版,共22页;5.译者、出版方不明,共51页。④笔者未见的版本可能更多。其间一个显著现象是译介传播之快,如冯白桦版仅五天就译毕付印,这首先是因为此册在日本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一本小册子的刊出,正好像一个大量爆弹的抛出一样,对于政府各部、政党、全国言论机关、全国的学者争论界思想家等方面,都激起了波浪壮阔的大影响,赞成的与反对的大影响”。得益于这些译者对政治空气的敏锐察觉和积极的翻译工作,这本小册很快为国内所知,并引发了不亚于日本的舆论震动。
报刊作为最重要的舆论场,对此小册的反应最大。《大公报》的评论首先注意的问题就是“日军部何以发表一小册,即足以震动日本全政局之势力乎”(大公报,1934)。作者认为军部在表面上代表了日本多数民众的利益并拥有震慑政府的武力支持,小册中鼓吹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蛊惑了前者,否认资本主义的内容又威胁了后者,使军部的战争掠夺政策成为一个备选项,而这无疑“将使世界大战之期日益接近”。《东方杂志》同样感到战争的危险,“日本军阀这几年来大声疾呼一九三五年之危机,想把整个的日本向着战争一途迈进”,此册或会帮助军方扫清财阀掣肘,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一天天的迫近”(作舟,1934:3)。此外如《中央日报》、《时报》、《民报》等主流报纸都有报道。
实际上,陆军省这本小册直接针对的并非中国,而是针对日本国内不赞同进一步进行军事扩张的政经界势力,是一种对内的“思想战”。据唐利国研究,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发行于1934年2月的小册子《思想战》是日本官方最早系统论述思想战问题的文本,之后鯉沼忍在1935年所著的《论对华思想战》和内阁情报委员会编写的《国防与思想战文件》,则都涉及了同时开展“思想战”以彻底征服中国的内容。
(二)国内的小册子出版与早期思想战
其实在思想战的说法系统形成之前,日方已经对宣传品对政局能起到的作用有所留意,其中小册子就是重要的一部分。如1920年日本国会讨论对华问题时,就提到“《国耻小史》不过为一小册子,然第一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实赖于此册子之力也,愿内阁诸公勿以片纸而置诸度外也”。⑤《国耻小史》是沈文浚所编,出版于清末的小册,内容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欺侮。而在日方看来,此书不但助辛亥革命成功,且将警惕日本的思想深埋中国人心中,影响深远。
日方对中国的小册子出版有所留意,中国也有人在观察日本社会上的小册子流行,尤其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各种文本。作为日本在东亚最大的战略对手,苏维埃俄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思想上对其造成了威胁,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的突出表现就是小册子的大量发行。李大钊曾描述黎明会在日本的活跃,“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的攻击之列。他们天天宣传,天天游说,这儿一个演说会,那儿一个讨论会,这里立一个杂志,那里创一所日刊。公共结合以外,他们还有自己本着他专究的学理择选的问题。今天一个小册子,明天一个小册子,散布传播飞如蝴蝶”(李大钊,1919:312)。
与李大钊的观察类似,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依赖小册子的输入和传播,1920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所查禁的83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品多是小册子。中共成立后,也有意识地利用这种形式的印刷物进行“宣传战”,如1922年中共发布了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小册子各五千份,政治宣传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陈独秀,1922:49)。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负责的国民党宣传部议案中有“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的丛书小册子”;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攻击中共的先声是戴季陶所著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最终导致国共分裂(杨奎松,2008:61-87)。之后的五卅运动、历次反围剿、西安事变等重大事件中,也都有各方编辑发布的小册子流传,以作宣传。所以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小册子在国内已是一种常见而必须的舆论手段,“传单、摺本和小册等的宣传品,在一种运动中往往用得最多,而发出的数量也很可观。凡一种范围较大,并且和全社会有关系的运动,它所发出的宣传品往往在万数以上,使社会人士对此事能有所认识”(梁士纯,1936:47)。
因此中日两国中小册子都是常见的宣传手段,在双方关系紧张时,小册子的发布往往会牵动对方的神经,前文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就是一例。实际上,日军部已经在定时发布小册,以向社会传递其观念和意图,在此册最后一页还公布了已经发布的10本小册之目录。之后由日本军部发行散布,并为中国报刊报道的小册主题包括纪念日俄战争三十周年、号召全民国防、讨论燃料问题、鼓吹“海上自由”等。其中最著名的则为1935年9月,时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所作《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一般认为这是标志着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进入高潮的信号。⑥日方小册子确实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关注,这些文本散发出的威胁恐吓之意,更使中国社会认识到日军的侵略之心而有所防范。因此在鲤沼忍看来,日方此时的对华宣传是失败的,他所撰的《论展开在北支政策上被遗忘的文化工作和思想战为当务之急》提出要以更隐蔽的方式瓦解中国的抗战心理,这也是之后日伪实施宣传战和奴化教育的理论指导之一。
对日军业已展开的宣传攻势,中国方面并非毫无准备。在华北地区,中共一直重视抗日宣传工作,“当时,党的工作内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步深入,重点是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抗日救国会员”(张君,2015:294)。在西北,红军向各地方武装大量散发抗战小册,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白区,地下党通过小册子制造舆论,声援和营救被当局抓捕的进步人士。同时通过各个地下印刷厂、中国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等机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全民族抗战,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小册子。国民党通过行政系统分发《救国理论》,并且将小册子的编订作为指导民众工作的方法。至于社会人士和团体产出的各类小册更多,“小册子是宣传最好的工具,而又是最易普遍传播的刊物”(大路社,1936:3)。“飞如蝴蝶”的小册子意味着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宣传手段。
二、另一个“黄金时代”:文化界的小册子取向
胡适将《独立评论》活跃的五年间(1932—1937)称为“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本质上通过期刊的出版发行,以较低成本获得较大话语权的时代。“当时排字工价不贵暨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胡适,1956:502)。但是1938年之后各项物料价格飞涨,如纸张进口量减少了近七成,需求量却因为宣传品的大量印发而增加,使得价格翻倍,《独立评论》便难以经营了。胡适所言的“小册子新闻”实际上就是固定出版的期刊,淞沪会战之后,作为重要文化市场的沪宁地区政治环境发生变动,许多同样性质的杂志被迫停刊,于是胡适认为杂志的黄金时代已然终结。与此同时,以抗战宣传为主题的宣传小册子大量出现,这又宣示了另一个“小册子黄金时代”的到来。
(一)小册子出版量的爆发式增长
“‘八·一三’的炮火,把上海书店的老板们吓慌了,将《光明》、《文学》、《中流》、《译文》,爱读的杂志相率停刊。然而替代了这些杂志的是更多的小册子”(郭沫若,1938:93)。出版家张静庐对此现象有更详尽的描述,他以从业者的敏感性指出,全面抗战初期国内出版界的一大变化是小册子大量出现。“抗战初期的出版新书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通俗的小册子,为要向民间普遍的推销,高深理论固然没有人理解;售价方面,在战时购买力当然薄弱,也力要求低廉。——生活书店出版的黑白丛书战时特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大时代丛书,都是实例。一种是有时间性的,或为全国民众注意力所集中的某一事件,如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新闻纪事体的小册子,和诗歌戏剧等单行本,一窝蜂就出了十几种,虽是多少不免浪费,但需要的倾向很明显的显露出来了。此外,过去视为神秘性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张静庐,1938:192)。
正如郭沫若和张静庐所注意到的那样,小册子的爆发式增长是全面抗战初期的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其原因是抗击侵略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在这样的氛围中,宣传和鼓动便是文化界参与抗战的主要方式,“由于纸张的缺乏和印刷所的破坏等原因,或因战事的紧张,平时的悠长型的作品已无处发表的缘故吧,都全变成极薄的小型的东西,内容也完全战事化,变成它本身就是煽动性的小册子式的东西”(增田涉,1938:104)。悠长型的文学作品出版减少,杂志“黄金时代”结束,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内文化界的转向,这直接表现为宣传小册子的腾起,时人对此现象评价不一。
在抗战救亡作为绝对的舆论中心时,其他主题的出版物大为减少,由此可能造成对其他重要议题的关注有所缺失。邹韬奋认为,“我们自抗战以来,物质上的损失与毁弃,我总觉得不要紧,那些书局里没有新的伟大的译述,直叫人焦心。而一般人热烈的只去读那些浅显的抗战小册子,证明大家已经因战争而放弃了对于学问深刻的研究”(邹韬奋,1938:525)。邹韬奋并非反对抗战小册子的宣传作用,他一直认为只要有贡献于国家民族,“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贡献的大与小,原本就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邹韬奋,1936:693)。他在此表达的是一种担忧,抗战宣传挤占了其他议题的空间,尤其是“对于学问深刻的研究”这个空间。其实不只是学术研究的空间被侵占,当时整个社会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抗战上,“记得在抗战初期,那时最流行的读物是有关抗战的小册子,一切都挂上抗战的招牌,说一声‘与抗战无关’也便可构成一种罪状”(赵超构,1944:524)。
对抗战小册子本身也多有议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其内容和主题趋同化,导致彼此之间“差不多”的诟病。“显现在我们眼帘之前的,是无数五花八门的杂志,是无数各种不同颜色的小册子,这应该是一个多么可喜的现象。可是随着来的,却是一个极其严重危机的事实,这一事实完全在表现刊物内容的‘差不多’和读者对象的重复上”(黄操良,1938:1)。这应当是文学界始自1936年底“反差不多运动”的一种延伸,沈从文批评一些作者“记着时代而忘了艺术”,生产一些公式化的低质量作品,进而与反对者以《大公报》为阵地形成了“广泛的笔战”(月报,1937)。茅盾也不满报刊界政论大同小异的现象,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仍未改观,“上海各报当然同伸义愤了,然而除了义愤以外,对于当头难的国难作具体建议者,似乎还是很少;依然是‘差不多’”(茅盾,1937:17)。除风气使然外,黄操良认为“材料荒”是小册子内容趋同的主要原因,这个来自作者的意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二)文化界对抗战小册的大讨论
也有人对小册子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认为这种宣传性质的浅显读物出版没有意义。“七七事变”之后吴宓南下长沙临时联合大学,行至汉口时拜访《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季鸾方与战地归来之青年会谈。客去,宓致其诚悃,而鸾仅作抗战之乐现论,劝宓读新出之抗战小册子。宓颇失望”(吴宓,1937a:255)。这里的“诚悃”应当就是吴宓对于抗战前景的悲观论断,实际上,他之前与陈寅恪讨论时已经流露了类似的态度:陈认为中国国贫民弱难以速胜,不如保全华南悉心备战以待将来;而吴宓更加悲观,“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吴宓,1937b:169)。在他看来即使应战也只会失败,而砥砺奋进、一雪前耻的机会非常渺茫。对此时的吴宓来说抗战前途未卜,区区几本小册无法左右战局,因此才会对张季鸾的建议感到失望。
与之相对则是热烈赞扬抗战小册子的声音,他们认为小册子是极好的宣传材料,应当大力提倡。时任通俗读物编刊社主任的王真,出版发行的抗日读物多达“三四百种,数千万册”,他曾以《五百大刀队》等三种读物为例论述“新酒装旧瓶”的宣传作用。“上面三种新读物两家书局一年七十万册,假设一个读者讲授给五个听众,那已到三百五十万民众要受我们的影响了”(王受真,1935:21)。这种“一个读者讲授给五个听众”的表述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中国的文盲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在战前一份针对开封大相国寺书市的调查直言,“事实上,大众对于读物是没有阅读的机会的,而且他们就根本上不能阅读什么读物。因为大众是文盲。大众对于读物的领受和理解,不是利用他们的眼,而是利用他们的耳”(张履谦,1934:111)。这个面向最广大民众的书市中80%以上的书是弹词唱本和神怪传奇,并且多数读者并不购买,只是租读或在摊前付费读书。喜峰口抗战的几本读物正是利用了传统弹词的形式和既有的行销网络,以极低的售价打开了市场,才得以广泛传播。
至于抗战小册主题“差不多”的现象,也有人持乐观看法。潘梓年在其主编的《抗敌救国丛书》前言中说:“大家为的都是抗战,都是要追正确的抗战理论,学习进步的抗战技能,所谈的问题和所得的结论,怎能不‘差不多’呢?如果真的差得多了,那才是怪,才是要不得。”并认为这些抗战小册子很有前途,“不但不多,而且还不够呢”(任淘,1934:1)。张申府也认为抗战小册子仍有发展空间,“自抗战以来,定期刊物与小册子是出了许多。在量上,在质上,都够了么?内容是不是都充实?意见是不是都正确?是不是都已得到了充分的流通?是不是有的地方,有的群众,还大感觉读物的缺乏”(张申府,1938:49)?所以仍可进一步地鼓励和提倡。
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方略中报纸仍是最重要的工具:“书籍、小册、传单、标语,固然在宣传工作之应用上,往往极有价值,可是最重要的工具,还要推报纸,因为报纸对读者的影响是自动的有恒的”(宣传部,1938:8)。而对文化界来说,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国内舆论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主旋律,各种媒介短时间内都将关注点归于一处。与战争进程相关联的是国土沦丧和生计日艰,报纸期刊已然难以承载激愤的社会情绪,于是创作出版小册子成为时局激变下文化界的自发行为。得益于其发行的时效性和议题的集中性,小册子在全面抗战初期一度取代了杂志,由此形成了另一个属于小册子的“黄金时代”。
三、从“袭击队”到“正规军”:中日的思想战和宣传战
包天笑将抗战时期的小册子称为“文化界的袭击队”(包天笑,1937),这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出文化界作为思想和舆论战线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小册子是其重要的武器;二是表明全面抗战初期集中出版的大量小册子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起到了“袭击队”的作用。随着正面战场数次会战的结束,抗战由战略防守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出版界骤然而兴的小册子现象显得后继乏力。其中原因是多样的,比如京津、淞沪等出版业集中的地区相继沦陷,战争导致的资本匮乏和物流中断,以及敌人在沦陷区的文化管制和奴化教育等等。与此同时,国共两党所属的宣传机关开始重视小册子在思想战上的作用,并各自展开行动。
(一)国民政府与正面战场思想战攻防
日军的小册子宣传战略首先被用于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上。《密勒氏评论报》认为日军的宣传攻势甚至要比军事攻势更为猛烈,“战事爆发之后,日本的宣传品,飞速的印行出来,差不多两倍于其在华所投炸弹的数量”(汪宁士,1938:379)。文中列举了《和平的满洲国》、《如何给予日本均等机会》、《日本为何而战》等9种面向外国的英文小册子,驳斥了其中的谎言和狡辩。这些宣传物是日方争取有利国际舆论环境的一种策略,虽然其中不少是冠以驻外使馆甚至首相名义撰写发布,实际上均需通过军部的审核,所以这些小册无疑是日本“总体战”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这些文本的目标受众是英文世界的读者,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所以这类小册往往避重就轻、颠倒黑白,妄图抵赖其侵略实质。如日本驻美大使馆出版的《日本为何而战》中,污蔑中国的文化界抗日行动是“虚构的宣传”,对其屠杀中国平民的行径绝口不提,反而称日军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Jap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37)。不过日方的掩饰和谎言往往被轻易识破,不论是官方还是名义上的中立通讯社,散发给欧美的小册都没有换来日军所希冀的国际舆论环境,反而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些印刷品也“只有扔进废纸篓完事”(拜亚斯,1939:939)。
在沦陷区、大后方和根据地,思想战线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则更为激烈。四川、云南等大后方虽未被日军大规模侵占,但早在战事初起时就被日本的宣传小册子渗透,“到现在,他们竟将宣传品混入到我们的后方来了,据说是连成都也发现了这种小册子。你看,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的建立沦陷区域的文化工作,而敌人却已经在我们的后方做起文化宣传来了,这是极所惊骇的”(抗战文艺,1938:162)。在日军业已侵占的地区,其宣传部门发布的小册子数量更加庞大,种类更加多样,内容更是明目张胆地“攻心”和劝降。这些小册有的是日本浪人在利益驱动下,借日军淫威进入学校强买强卖,“各校因为避免麻烦,差不多都买一二份”(欣晓,1937:224)。有的是假冒中国立场编写“种种煽惑之邪说,似是而非”,印刷散布,蛊惑民众。有的是在进行集会时,由汉奸组织散发,如1938年6月北京的一次敌伪集会中,除以百万计的传单标语外,还有一万部小册子专门向“各学校、各团体分发”(新闻报,1937)。可见这些小册子都是由日军有计划地产出和传播,在定位上是与武力战、经济战同样重要的。
与之相对的,中国方面的抗战小册子作为“文化界的袭击队”虽在初期取得了瞩目成绩,但只靠文化界自身的力量难以长久与日方相抗衡,于是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对此予以重视。在《战时对外宣传大纲》中,小册子就是对外宣传的五种方式之一,在一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布了11种小册,共计有近70万册。由军方和政府组织出版的战争理论书籍中,外军利用小册进行宣传的战史开始更多地被翻译介绍,其中最多的是与国民党军交流较为密切的德国军队。比如同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的《战时国家总动员》中,记载了一战期间德奥小册的印刷之多、分配之速。德国将军麦舍的名言“五十万小册比一百吨炸弹更有效力”(罗敦伟,1938:46)被一再引用,甚至传播的具体方法如“散发小册子则嘱令散给上车的旅客,不要散给下车的旅客,因为下车后阅读的机会少,弃于地下了”(李茂秋,1938:190)都有所涉及,可谓详致。针对日军以空投和邮传为主的传播方式,国民党政府指派各级政治部分别做出应对措施,以“积极防止敌伪反宣传品的散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15)。同时各地政府也利用既有的行政体系,通过散发抗战宣传小册鼓舞民众斗志。
(二)小册子与中共领导的敌后宣传战
与重庆政府治下的大后方相比,中共活跃的沦陷区和根据地是思想战、宣传战的中心战场,也是日军进行文化攻势的重点目标。就日军的宣传小册子来说,对华北投入了远多于其他地区的精力和资源,“敌伪出版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宣传小册子,仅在华北,就有一二百种之多。南方的材料,得到的很少”(文化教育研究会,1941:158)。其主题五花八门,有反国民政府和国共合作的、宣扬“中日亲善”的、反对“欧美同盟国”的,预设的读者群也不尽相同,如针对儿童的《小鸟》、针对女性的《怎样作中国的新女性》、针对青年的《大日本青年致中国青年书》、针对农民的《告中国农民》等。这些小册多用“生动的笔调、艺术的手法”,借俗语或唱本等底层人民乐见的形式,捏造事实进行奴化教育和劝降宣传。在历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还重点针对教师和村民,制作了袖珍小册供“在学校与各村庄举行讲话之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1942:9)。
中共一向重视宣传工作,“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环境十分艰苦,但出版报刊和小册子的工作没有停止过”(周保昌,1983:1),长期处于各种恶劣环境中更使中共对书刊的创作、出版和传播有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是根据地的文化中心,也是印刷出版中心,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同时中共还要求各地要各自创办印刷所,石印、油印、铅印并用,“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中共中央,1939:46)。在这个指示下,周恩来从读书出版社中抽调工作人员,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创办华北书店,店址设在辽县桐峪镇,“用油印、手工刷印等办法翻印了几十种小册子”(范用,1983:32)。这些小册包括揭发敌军虚假宣传的《莫中敌人的奸计》,劝说伪军反正的《给日寇压迫下的伪军》,以及直接面向日军士兵的《日本士兵之出路》等。之后在技术条件和宣传需要发生矛盾时,还一度暂停和合并了一些刊物,转而出版小册子。重庆政府也对敌后的思想战有所支援,其中就包括了针对沦陷区群众编写防止投敌的小册,并输送各种宣言和演词的小册子至游击区等。得益于这些工作,日军妄图从精神上征服中国的思想战计划,比在战场上的失败来得更快。“最近,首创东亚联盟理论的日本石原莞尔中将,在其《欧洲大战之进展与中国事变》一文中,提起了思想战,坦白承认了日方对于渝方的思想战还十分落后,因之渝方对其彻底抗战之宣传,终于还涂布着不可动摇的魅力”(何海鸣,1942:35)。
但是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此阶段的小册子相较其他宣传方式,虽然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国统区,广播和电影成为更有效的宣传方式;在根据地,壁报和各地的小报也蓬勃发展起来。从被俘日军的反馈来看,广播和传单起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而受小册子感召的并不多见。实际上,1943年敌伪组织“新民会”颁布的需要禁止发行的《抗日图书目录》中,仅有38种标注为小册子,其比重仅为被禁书目总数的1%左右。⑦同时,他们也不再重视对华进行小册子宣传的工作,“(日方)小册通常不大见到,只在敌伪认为有扩大宣传的需要时,始刊印此类小册”(秉中,1942:29)。
二是不论创作者如何计划,小册子的真实受众从来都不是广大民众。这固然有流通渠道难以达到乡村社会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无疑仍是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实际状况,“虽然有些比较通俗的小册子,小报和画报,但由于发行不普遍,依旧停留在大都市里,内地的大众依旧没有福气拜读……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绝大多数的大众还是目不识丁,还是听不懂一个最粗浅的名词”(林淡秋,1937:26)。打破这道阻隔在大众与文化之间的长城,最重要的方法是开展大众教育,提高识字率。虽然各方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通过各自的方式着手解决,但是大规模消灭文盲是1950年代之后才得以实现。此前的“大众文化”和“通俗读物”,实际上是能被多数“知识人”所接受认可的文化和读物,小册子有这样的潜力,但通过小册子影响大众仍是借助了这些知识人作为中介,远没有达到创作者所期望的“献给大众”的效果。
但不论如何,在全面抗战初期文化界的抗战小册子“如雨后春笋般随地怒茁”之后,重庆和延安都对此有所关注,并将小册子作为实施文化抗战的一个面向。在武装抗战、经济抗战的配合下,日军的“思想战”计划未能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反而使一些日军士兵在感召之下产生了厌战反战心理,这也预示着侵略行为的最终失败。
四、余论
在全面抗战初期,团结御侮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民众需要一种主题鲜明,兼备通俗性和时效性,并且价格低廉的出版物,于是抗战小册子成为出版界最好的选择。各大书店以抗战为主题的各种小册子如火山喷发一般大量出现,仅一年间即达上百种,出版量动辄数十万,这也成为文化抗战的先声。此后,中国军队和日军的宣传机关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战,双方出版的各种小册子是交锋的重要武器。与文化界自发的出版活动相比,由军队出版的小册子是各自宣传战略的一部分,主体内容有更强的针对性,发行渠道有更强的组织性,受众身份也更加明确。于是侵略者出版奴化教育、精神征服的小册子,与中国军队出版反对侵略、坚持抗战的小册子,成为这一时期双方思想战的重要面向,并最终以日军的失败告终。
小册子作为抗战乃至历史研究的史料,都不能算是“新材料”,但是如何认识和利用,进而围绕小册子深化既有研究应当被重视。近年来,各种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出版如火如荼,不论是深藏民间的契约文书,还是散落国外的档案密册,都一批批得以付梓面世,这是史学研究从未有过的一个材料极大丰富的年代。资料既多、获取又易,这样便利的研究条件下,“趋新”似乎成了避免同质化研究的一种选择。不可否认,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是深化研究的强大驱动力,但不能因为一味求新而忽略了对既有史料的挖掘和解读。实际上,在诸如宗教史、美国早期史、欧洲城市史等领域,小册子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以此为中心的讨论屡见不鲜。而在抗战研究中,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和利用小册子,就是为了避免本末倒置,片面重视材料之新而忽视了研究路径之新、方法之新的一个切入点。
抗战小册子的兴起和发展,实质上是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互动的过程。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大量出版和随处可见,是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文化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是文化抗战的先声,同时也是许多亲历者在历史情境中对“抗战文化”最直观的感受。对小册子的创作者而言,文化抗战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化界自己的事情,启示、发动和引导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抗战队伍中才是他们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抗战不是精英的而是大众的,由此形成的抗战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大众化的烙印。随着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小册子被文化界以外的群体运用起来与侵略者进行思想战,与其他形式的宣传手段一并成为文化抗战的武器,而体裁内容更加多样的抗战文化也得以形成。
通过抗战小册子,也提醒我们避免历史研究中因为“下意识”和“想当然”导致的误判。有关现代中国公共领域、舆论环境和大众文化等议题的讨论已经非常深入,其中报纸和期刊都是重要的关注对象,透过这些文本审视社会变迁中民主化和大众化要素也是常见的研究思路。在谈论到小册子时,这些理论和概念似乎也是比较适用的分析工具,但这看似合理的路径可能反而是“下意识”和“想当然”的陷阱。实证之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小册子在创作之时确实一度面向基层的普通民众,但预设读者群和实际受众并不重合,小册子并未直接对最基层的广大民众产生影响,其内容更多地依赖“知识人”作为中介来传播。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思想战”中,宣传小册子作为交锋的武器和战场,各方对其认识也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它在战前是各方惯用的宣传手段,在全面抗战初期是中国文化界的“袭击队”,之后则成为思想战的重要一环,因此对小册子历史作用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
注释:
①抗战文化的研究讨论中多是已小册子作为具体资料来运用的。早期有金冲及:《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22页;近年有王海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红色图书”出版发行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4期,第4-13页;王天根:《抗战语境中舆论场域重组及其历史省思》,《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第11-14页;徐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②这些资料包括: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唐利国(编)。《思想战与文化宣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吕彤邻(主编)。《美国眼中的中共宣传资料》。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荣县档案馆(编)。《荣县抗战宣传档案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③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档案中,有大量对此的记录,如:陸軍省新聞班(著)。《「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に対する評論集》。亚洲历史资料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C14020009200。日本防务省防务研究所藏。《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座談会の速記》YD5-H-特249-66。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講演会の記録》YD5-H-特228-660。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④具体为: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敬慈译)。《国闻周报》1934年11月11日。日本陸军省新闻班(著)。《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张孤山译)。《军事丛刊》(14),1-14。《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策》(冯白桦译)。南京:中央航空学校。《国防本义与其强化之提倡》。广州:人民印务局。《国防之本义与增强国防之提倡》。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检索于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detail.htm?fileCode=ffe40ec56da24922a9ca16ed29cf497e&fileType=ts。
⑤北洋政府外交部在处理巴黎和会后的山东问题时,留心收集了一些国内外舆论反应,合归为“山东问题国内外官民意见”册,其中有日本国会的一次会议记录,参见《日本国会对华问题及青岛问题借款问题之讨论由》03-33-157-01-013。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⑥具体目录见:《小冊子「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の強化第1分冊》。亚洲历史资料资料中心公开日本防卫省档案C14020008000。日本防务省防务研究所藏。各报评论包括:《日再发陆军小册子》,《京报》1935年2月25日。《日俄战争三十周年纪念,日陆军将发小册子十万册》,《新闻报》1935年2月25日。《日海军部小册子鼓吹海上自由》,《大公报》1936年5月6日。
⑦这些记录主要来自于日军俘虏,参见:日本官兵对我方对敌宣传影响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史料丛编》(第一辑第68册)(第478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参考文献:
拜亚斯(1939)。中日对外宣传的评价(逸君译)。《血络》1939年4月15日。
包天笑(1937)。文化界的袭击队——小册子。《救亡日报》1937年10月17日。
秉中(1942)。《敌伪宣传内幕》。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陈独秀(1922)。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大公报(1934)。日军部国防小册所表现之日本经济问题。《大公报》1934年10月16日。
大路社(1936)。《炮火下的活动》。上海:国防常识出版社。
范用(1982)。一个在白区的出版社——记读书生活出版社。载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出版史料》(第一辑)(第24-4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郭沫若(1938)。抗战一年来的文化动态。载寸喁(编著)。《抗战建国第一年》(第93-95页)。重庆:七七书局。
郭廷以(198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至二月份》。台北:国史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粉碎“敌伪反宣传”宣传要领及对策》。汉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何海鸣(1942)。东亚联盟的必然性。载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上海分会宣传科(编)。《东亚联盟论文选辑》(第35-44页)。上海: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上海分会。
胡适(1956)。丁文江的传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7卷)(第401-5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1942)。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宣传计划。《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171),9。
黄操良(1938)。《日本对华侵略战的代价》。上海:大众出版社。
抗战文艺(1938)。建立沦陷区的文艺工作。《抗战文艺》1938年12月26日。
李大钊(1919)。新旧思潮的激战。《晨报》1919年3月4日。
李茂秋(1938)。《全面抗战方略》。南昌:生记印刷局。
李孝悌(2001)。《清末下层的社会启蒙运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梁士纯(1936)。《实用宣传学》。上海:商务出版社。
林淡秋(1937)。《抗战文化与文化青年》。上海:上海杂志公司。
罗敦伟(1938)。《战时国家总动员》。汉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罗志田(2003)。《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
茅盾(1937)。“差不多”。《新闻记者》(第1卷),(3),17。
任淘(1934)。《抗战中底军事动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汪宁士(1938)。日本的宣传小册子。《文摘·战时旬刊》,1938年3月18日。
王汎森(2017)。《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近代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受真(1935)。再论“为什么要把新酒装在旧瓶里”。载顾颉刚(编)。《通俗读物论文集》(第18-23页)。上海:生活书店。
文化教育研究会(1941)。《敌我在宣传战线上》。文化教育研究会。
吴宓(1937a)。吴宓日记1937年11月17日。载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第255页)。北京:三联书店。
吴宓(1937b)。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载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6册(第169页)。北京:三联书店。
欣晓(1937)。奴化教育(天津通讯)。《抗战·抵抗三日刊》1937年10月6日。载谢忠厚等(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第10册(第22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闻报(1937)。敌散印小册子竟假借国民党立场。《新闻报》1937年10月28日。
宣传部(1938)。《抗战时期宣传方略》。汉口: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杨国强(2018)。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65。
杨奎松(2008)。《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月报(1937)。编者记。《月报》第1卷(4),858-859。
增田涉(1938)。一个日本作家的中国抗战文学观(晓奏译)。《文艺(上海)》第2卷(4),104-107。
张静庐(1938)。《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杂志公司。
张君(2015)。抗战初期冀中党组织的活动与抗日武装的创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1937》(第293-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履谦(1934)。《民众读物调查》。开封:开封教育实验区出版部。
张申府(1938)。《我相信中国》。上海:上海杂志公司。
赵超构(1944)。剧名之鸳鸯蝴蝶化。《赵超构文集》第2卷(第52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
中共中央(1939)。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等(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
周保昌(1983)。新华书店在延安初创时期。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史料》编辑组(编)。《出版史料》(第二辑)(第1-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邹韬奋(1936)。工作的大小。《生活日报》1936年6月18日。韬奋基金会等(编)。《韬奋全集(增补本)》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邹韬奋(1938)。《再厉集》。上海:生活书店。
樽本照雄(2002)。《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贺伟译)。济南:齐鲁书社。
作舟(1934)。从史蒂尔的预言说到日本国防小册。《东方杂志》1934年11月31日。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37). What is Japan fighting for: the truth about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Japanese Association of San Francisco1937.
裴孟华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山西抗日战争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9KZD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