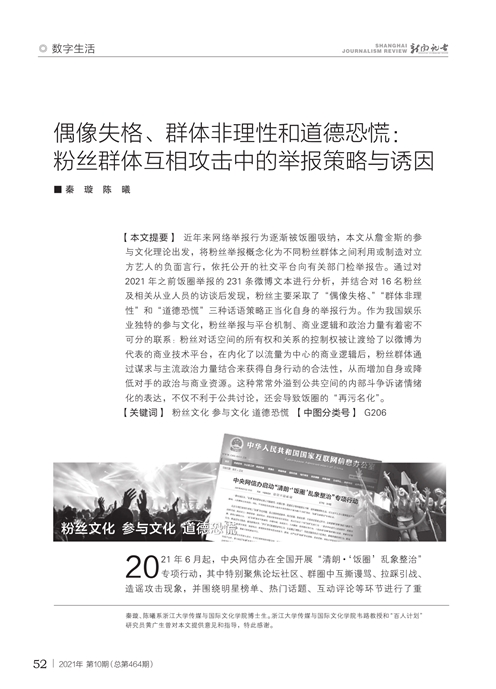偶像失格、群体非理性和道德恐慌:粉丝群体互相攻击中的举报策略与诱因
■秦璇 陈曦
【本文提要】近年来网络举报行为逐渐被饭圈吸纳,本文从詹金斯的参与文化理论出发,将粉丝举报概念化为不同粉丝群体之间利用或制造对立方艺人的负面言行,依托公开的社交平台向有关部门检举报告。通过对2021年之前饭圈举报的231条微博文本进行分析,并结合对16名粉丝及相关从业人员的访谈后发现,粉丝主要采取了“偶像失格、”“群体非理性”和“道德恐慌”三种话语策略正当化自身的举报行为。作为我国娱乐业独特的参与文化,粉丝举报与平台机制、商业逻辑和政治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粉丝对话空间的所有权和关系的控制权被让渡给了以微博为代表的商业技术平台,在内化了以流量为中心的商业逻辑后,粉丝群体通过谋求与主流政治力量结合来获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从而增加自身或降低对手的政治与商业资源。这种常常外溢到公共空间的内部斗争诉诸情绪化的表达,不仅不利于公共讨论,还会导致饭圈的“再污名化”。
【关键词】粉丝文化 参与文化 道德恐慌
【中图分类号】G206
2021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在全国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特别聚焦论坛社区、群圈中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现象,并围绕明星榜单、热门话题、互动评论等环节进行了重点整治。时隔两个月,中央网信办于8月27日再次要求进一步加强饭圈治理,严禁平台呈现饭圈粉丝互撕信息。为此,微博对多位明星的极端粉丝采取了强力制裁措施,多家明星工作室陆续发布理智追星倡议书,号召粉丝理性讨论。
回望饭圈发展,因为个人喜好的排他性和不稳定性,粉丝群体既可能因为共同的兴趣集结,也不可避免地会因此产生矛盾与争吵。过去,这种争吵多采用言语辱骂的方式对其他明星及其粉丝进行攻击。而近年来,网络举报策略逐渐被饭圈吸纳,成为饭圈“掐架”的手段之一。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不得捏造或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但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和娱乐性使网络信息难以得到有效把关,一些粉丝往往利用这种方式对他人进行恶意诽谤或打击报复,进而干扰监督机制的正常运行(熊光清,2014)。面对新的“互撕”形式,最直接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粉丝举报的产生,这些举报又存在什么样的特点?
当代的粉丝研究多承袭费斯克和詹金斯关于生产性粉丝的观点,从积极正向的视角出发研究单一粉丝群体的内部运作,因而难以解释不同粉丝群体之间的“爱恨纠葛”。更重要的是,只要粉丝群体建立在对商业化作品的共享性回应之上,它就并非完全自治的,在商业平台很少被限制和管理的背景下,粉丝参与的意义需要进一步反思(Jenkins et al., 2016: 1, 141)。换言之,当下的粉丝参与与网络平台、商业利益和主流话语之间的交织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一脉络下,本文希望进一步思考这种另类的粉丝参与文化与媒介平台、商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即四者如何互相吸纳、融合?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整个饭圈生态乃至公共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将粉丝举报概念化为“不同粉丝群体之间利用或制造对立艺人的负面言行,依托公开的社交平台向有关部门检举报告的行为”。通过聚焦微博上公开发布的粉丝举报文本,试图揭示这类举报的特点、话语策略及其社会形构,藉此了解他们参与此类行为背后的原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詹金斯的参与文化理论。
一、文献回顾
(一)粉丝、饭圈与参与文化
虽然“对特定的人或事物拥有强烈兴趣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粉丝”(Shen et al., 2019),但当代意义上粉丝(fans)的出现与大众文化及电子媒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胡岑岑,2020)。他们通常被理解为与流行文化内容有深度接触的个体,并经常通过流行文化内容维护自己的身份,饭圈(fandom)则是作为个体的粉丝围绕共同兴趣所形成的亚文化群体(Brough & Shresthova, 2012)。在粉丝概念出现的初期,这一群体往往被大众媒体描述为痴迷的、离经叛道的、危险的狂热分子。在大众传播学研究中,也有病态化粉丝的倾向(Jenson, 1992)。加里(Gary)等人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粉丝文化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试图为原本被定义为负面的粉丝群体正名,并为他们的行为赋予一定积极的意义;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对20世纪90年代新媒体发展的回应,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粉丝群体如何利用各种媒体积累文化资本、建构身份认同;第三阶段的研究将分析范围扩大到不同类型的受众,将粉丝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探讨粉丝的情感特征(Gray, Sandvoss & Harrington,2007)。
作为第一阶段的重要研究者,亨利·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一书中提出“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他认为文化消费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对原始文本进行重写、批评与挪用的参与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参与文化”的内涵经历了一系列流变:在最初的研究中,“参与文化”仅仅用来描述形态模糊的文化生产和通过社会交换所建立起来的饭圈(fandom)(Jenkins et al., 2016:2-3),但通过对过往研究的回溯,詹金斯认为,饭圈实践可以产生集体智慧,为更有意义的公共文化铺路,蕴含着从文化消费走向政治参与的可能(Jenkins, 2006a)。比如,美国最早的有关同性恋权利的内容其实出现在科幻发烧友编写的杂志上(Gaber & Paleo, 1983);麦当娜的粉丝通过相互支持在社会中表达共同的女性赋权主义思想(Fiske, 1989);酷儿群体(Gaylaxians)通过写信游说而成功地在电影《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置入了一个同性恋角色(Tulloch & Jenkins, 1995)。这意味着,饭圈不仅仅是草根文化生产的基地,也是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空间(Jenkins et al., 2016: 155)。至少在美国的语境下,年轻人从饭圈中习得的技能、能动性、合作意识和组织结构,可以使参与式媒体文化转化为参与式政治文化,最终促进社会进步(Jenkins, 2006b)。张玮玉以中国在线翻译社区的历史发展和结构布局来考察这一论点,发现粉丝活动可以从寻求娱乐转移到知识共享(Zhang & Mao, 2013),并在后续研究中提出了“粉丝公众”(fandom publics)的概念,认为这种趣缘群体的政治性不比其他的社会构成弱(Zhang, 2016)。
整体而言,随着饭圈规模的扩大以及结构和运作模式日渐正式化与复杂化,粉丝形象经历了一个“去污名化”的过程。研究者在意识到粉丝群体强大的消费意愿与消费力的同时,也注意到他们作为行动者在公民教育(Zhang & Mao, 2013)、公益活动(孟威,2020),以及网络爱国主义行动(刘海龙,2017)等公共参与实践中的潜能。但近些年来在微博、豆瓣等趣缘社交平台上频繁出现的粉丝互掐现象似乎在暗示,所谓的“参与文化”不能被局限在积极正向的参与中。现有的粉丝研究多以这种乐观的视角研究单一粉丝群体内部运作(郑欣,2007;朱丽丽,韩怡辰,2017;王艺璇,2019),鲜有涉及与其他同类型粉丝群体的交流、互动甚至是矛盾,因此无法解答他们对偶像的“爱”如何被扭曲为资本增值和维护霸权的工具。
(二)黑粉(anti-fan)与粉丝掐架
当我们继续对粉丝的“爱”给予关注时,也不能忽略它的对立面——“仇恨”。加里认为,对黑粉(anti-fans)和非粉丝(non-fans)的研究能对媒介文本的互文性和粉丝的情感参与有更进一步的了解(Gray, 2003)。黑粉虽然本质上不是粉丝,但他们也会积极地对不喜欢的文本或流派发表意见,并通过构建社区将不满进行转化。?这种分裂会出现在各种媒体文本中,随着互联网让黑粉得以协调并聚集,黑饭圈会越发壮大(Gray, 2005)。
在中国,最常见的黑粉往往是反对某个明星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在线上对艺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负面宣传、恶搞、攻击和谩骂,在线下则进行恐吓、伤害性的人身攻击。有时,这种攻击还会蔓延到有影响力的个体粉丝,并引发不同粉丝群体之间的“战争”(陈晨,2017)。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粉丝间的争吵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情绪发泄,为固有的排他心理找到了宣泄出口(付晓光,宋子夜,2017)。此外,部分策略性的掐架活动具有社群动员的作用,可以强化粉丝内部的身份认同。这种掐架并不是饭圈文化中的非理性行为,可能是一种调动成员情绪、围绕共同目标而展开行动的团结机制(杨玲,2020)。随着粉丝经济的繁荣,同类型、同人设或同期偶像之间资源竞争加剧,很多粉丝掐架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家的偶像获得更多资源(吕鹏,张原,2019),在此期间许多商家和个人常常通过平台营销刻意煽动粉丝的狂热情绪,导致骂战升级(洪培琳,2018;张婧,2019)。明星和经纪公司一般并不排斥黑粉和这种粉丝间的骂战,而是利用这种冲突所带来的曝光率成为最终的受益者(陈晨,2017)。可惜的是,上述研究多从思辨角度出发,缺少经验研究的支撑。
网络行动是包含国家、市场、公民社会、抗争文化与跨国行动等多种力量动态互动的结果(杨国斌,2013),基于网络的粉丝行动也不例外。饭圈固然有其自身的管理规范和运行逻辑,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内部的行为模式和话语体系在逐渐“出圈”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外部政治话语、互联网生态、媒介环境等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形塑。只研究粉丝与偶像、粉丝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并不足以阐明中国的粉丝文化机制(尹一伊,2020),当“不理智”和“脑残”等标签被再度用来描绘粉丝群体时,本研究试图突破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粉丝内部进行观察的窠臼,通过对不同粉丝群体之间愈发频繁的掐架行为进行研究,与詹金斯等人所推崇的“参与文化”进行对话,并回答如下问题:
1.当举报日益成为饭圈掐架的方式,这样的粉丝举报存在什么样的特点?粉丝们主要采取了何种话语策略?
2.这种另类的粉丝参与文化与媒介平台、商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四者如何互相吸纳、融合?
3.粉丝举报对整个饭圈生态乃至公共生活可能产生何种影响?
二、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以“粉丝”和“@共青团中央”为关键词在微博上进行检索并收集相关文本。之所以从微博中收集,是因为作为目前饭圈内使用范围最广、方式最多元的社交平台,粉丝数超过50万或月均阅读量大于1000万的大V用户数量接近5万,远多于其他平台(李慧,2018)。而2016年以来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使中国共青团系统的微博成为年轻人尤其是以女性粉丝群体为代表的“小粉红”?群体聚集地(吴靖,卢南峰,2019)。作为连接中国共产党和年轻人的纽带,@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目前已拥有1556万粉丝,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粉丝在举报过程中会优先@共青团中央。
需要强调的是,粉丝群体在进行此类举报行为时往往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在特定时间内发布类似信息,因此存在大量重复文本,平台在主动屏蔽相似结果后共呈现相关微博645条。鉴于本研究主要侧重总结粉丝举报的话语策略而非用户画像、社会网络分析或进行情绪倾向分类,因此研究者未再对微博上的文本进行全量采集,仅利用Python抓取了呈现结果中早于2020年12月31日23:59发表的微博共计353条,随后两位研究者又分别进行人工筛查,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本,最后得到有效微博231条。对文本的整理和归纳主要借助了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并在此基础上依照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不断地比较(Glaser & Strauss, 1967)形成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从原始数据提炼出概念和范畴,从而回答问题一与问题二。
为了进一步回答研究问题,在结束以上两步的材料收集后,研究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对共计16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行业报告显示,追星群体中女性占比高达86%,95后占82%(艺恩数据,2021),可以说年轻女性是该群体的绝对主力军,因此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也呈现出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特点。此外,研究者在选择访谈对象时还尽量涵盖不同粉龄和追星地区(见表1)。访谈时间自2021年1月持续至2021年2月,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录音形式记录。
三、粉丝举报的特点
文本显示,最早可追溯的粉丝举报出现在2017年,主要涉及说唱歌手PGOne吸毒和游戏主播卢本伟直播引导粉丝冲突。此后相关微博数量波动不大,直到2020年后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这些文本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仅涉及中、韩地区的明星及其粉丝群体
所有举报文本涉及的均为中、韩两国的明星及其粉丝群体,其中以中国为主,完全不涉及日本和欧美饭圈。这与不同地区的追星模式有关:
2008年以后,以K-POP(Korea-Pop的简称)为代表的韩流2.0借助数字媒体和移动经济在亚洲境内得到广泛传播(Shim & Noh, 2012)。随着技术的发展,流行音乐市场打破了过去唱片加演唱会的传统产业链,数字音乐市场成为音乐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艾瑞咨询,2020),流媒体音乐平台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正在变得愈发密切,艺人和粉丝通过流媒体互动而产生的数据流量成为娱乐市场的重要筹码。东亚地区便是这种产业结构变化最明显的地方(Zhang & Negus, 2020)。中国偶像行业和数据粉丝实践的同步增长与韩流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的流行文化还主要依赖港台地区的输入,时至今日则体现为向韩国学习,基于工业化、流水线模式高效生产和迭代偶像。2018年被称为“中国偶像娱乐元年”,在借鉴韩国电视节目推出的《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取得巨大成功后,国内出现了一批新兴偶像经纪公司,即使是过去以日系养成为主要运营模式的老牌经纪公司丝芭传媒和时代俊峰,也从2020年开始向选秀节目输送练习生:
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最快的方法就是模仿和学习。内娱的应援?什么的都在学韩娱。搞应援色、应援的口号、上班图、下班图、路透,还有做物料、送工作人员礼物,这些不是都是从韩国来的吗?(访谈对象A)
但是,与流量、数据相伴而生的不仅仅是作品、荣誉和代言,还有一起生根发芽的恶性竞争与黑粉文化。在韩国,最出名的粉丝竞争与初代偶像H.O.T.有关,该团体开启的应援文化传承至今。上世纪90年代,韩国媒体将同期组合水晶男孩塑造成H.O.T.的竞争对手,间接导致了两组合粉丝之间长期争吵和冲突(Kim, 2012)。近年来,这种竞争从线下蔓延到线上,形式也从群体斗殴延伸到诽谤与造谣。比如女团IZONE的在美韩裔粉丝通过泄漏隐私的形式对他人进行威胁,要求他们对其他女团和组合进行持续的、有组织的网络造谣与性别羞辱,从而影响被攻击对象的社会口碑与形象。这些案例与中国饭圈近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掐架和举报行为有着同源关系,其实质是粉丝在帮助偶像明星与同类型、同人设或同时期的艺人进行口碑和资源的争夺:
这些爱豆就是靠流量而不是作品活着的,他们本家是这样,对家也是这样。但是欧美那边儿没有这样的爱豆文化,主要还是靠好歌、好电影、好作品活着,也就没必要搞这些(举报、掐架)个东西。即使真要吵架了,那些欧美明星也会自己下场,根本轮不到粉丝,但是韩娱和内娱的经纪公司不会让偶像和爱豆开口。(访谈对象G)
(二)关于韩国艺人和粉丝的举报以政治主题为主
虽然举报文本会涉及明星及粉丝的言行举止、价值观等各方面问题,但涉及韩国地区的文本主要以经济公司或个人涉嫌辱华、反华、破坏外交关系或粉丝不爱国爱党等政治性议题为主。
这种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排他行为过去多表现为饭圈外部对内部的敌视。在十几年前韩流文化刚刚进入中国时,很多网友认为哈韩一族不爱国,用“脑残”称呼这些追星族。以“脑残不死,圣战不休”为口号,在百度上通过刷帖、爆吧?等方式对哈韩群体展开大规模言论攻击,这场被称为“69圣战”的网络狂欢事件将双方矛盾带入了大众视线,自此之后韩粉“沦为追星链底端人群”(网友:肥嘟嘟左卫门),此次事件也成为“韩粉人人喊打,夹着尾巴做人”(网友:未注销)的开端:?
其实每个圈子的粉丝都很疯狂,但是喜欢韩星就会涉及到国家层面,……(黑粉)经常攻击追韩娱的粉丝,而通过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更好地达成他们的目的。(访谈对象D)
这种策略逐渐被饭圈内部学习吸收,成为群体间互相争斗的武器,通过指责其他偶像或明星及粉丝反华、辱华来达到打压的目的。
(三)关于内地艺人及其粉丝的举报以道德主题为主
虽然内地的偶像产业文化承袭了韩国娱乐产业的特点,但和涉及韩国地区的文本主要以政治性议题为主不同,涉及内地艺人及其粉丝的举报文本,以偶像的言行等道德问题为主,民族、宗教等政治性议题夹杂其中。
研究抓取到的微博文本可追溯到2017年的两个事件。第一件是说唱歌手PGOne出轨知名女明星后被网友曝光其有吸毒史,以及部分PGOne粉丝不知紫光阁是什么,奋而“网暴紫光阁”。首先,PGOne幽会有夫之妇引起网友对其伦理道德层面的批评;其次,网友曝光PGOne成名前吸毒,违反了我国法律,认为有吸毒史的明星没有资格引导青少年粉丝;接下来,由于媒体微博@紫光阁批评PGOne歌词低俗等,引发粉丝“网暴紫光阁”,并误以为紫光阁是一家饭店,引起舆论对其粉丝无知和非理性的讨论。另一典型事件是举报游戏主播卢本伟在直播中教唆粉丝辱骂他人,也聚焦在卢本伟本人的言行不能正确引导粉丝、其粉丝无理性这两点上。
四、粉丝“战争”中的举报策略
为了形成切合研究对象的扎根理论,本研究在对收集到的微博文本进行逐词逐行的初级编码和具有指向性的聚焦编码后,最终形成可以指向举报策略的三大核心编码:“偶像失格”、“群体非理性”和“道德恐慌”。其中,“偶像失格”借用自饭圈用语,专指偶像所作所为不符合规范,因此失去了做偶像的资格;“群体非理性”针对粉丝群体,强调他们缺少能动性,容易被人“利用”和“操控”;“道德恐慌”则指通过强调其他群体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来合理化自身的举报行为。
(一)偶像失格
过去,饭圈所谓的偶像失格主要指明星在上升期谈恋爱、不认真营业、和粉丝或素人私联等有违职业规则的行为。近年来,如果偶像明星被曝出有吸毒、抽烟、骂人等违背社会日常规范的行为也会被认为“失格”。这种针对偶像明星个人负面问题的举报在文本中频繁出现,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批评个人品行不端,如“抄袭”,学生时期“打同学、骂老师”,在疫情期间“虚假捐赠”等;其次是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经纪公司或艺人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等;第三类指偶像明星存在违法犯罪情节,如吸毒、造谣、无证驾驶等。
此外,2020年3月11日《检察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漠视社会责任的偶像都是失格的偶像”,关于“粉丝行为,偶像是否应该买单”的饭圈争议由此成为大众探讨的话题。因此,一些举报文本也将“无法正确引导粉丝”作为偶像失格的表现进行批判,如“粉丝发表民族分裂言行时,偶像没有给自己的粉丝树立正确的三观”、“艺人推出新作品时不仅没有理性引导,反而以圈钱为荣”、“作为公众人物不约束自己的粉丝,放任粉丝造谣”、“眼睁睁看着粉丝发疯失控”等。
(二)群体非理性
勒庞认为,群体冲动易变、偏执专横且往往容易受到暗示。群体情绪的易传染性使理智、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尽管勒庞的相关论述被学者批评“悲观而且独断”(刘海龙,2020:64),将大众看为乌合之众给了我们一种虚伪的正义感(威廉斯,2011:377,383),但勒庞与弗洛伊德式的论断成为“群体非理性”策略的理论武器和“真理性参考”。这一策略将粉丝群体简化为勒庞式的“乌合之众”,并忽视粉丝的主动性和多样性特征,强调他们是狂躁的、无底线的,受艺人或利益团体的“操控”和“压迫”。
这种话语策略具体可以体现在五个维度。第一种是非理性认知,其中最常见的是邪教隐喻和洗脑隐喻,认为其他粉丝群体在追星的过程中已经“走火入魔”,被“养蛊洗脑”,“印小册子搞宣传,在公交车上写口号,无时无刻不在传道”。第二种是非理性消费,为了让偶像在各方面都能有更好的成绩而过度消费,进行数据造假,贷款购买专辑甚至非法集资,“教唆未成年人氪金”等。第三种是不爱党爱国,往往指粉丝有疑似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污名化政府或党媒等行为和言论,例如“侮辱一线抗疫人员”、“改编对国家和人民意义重大的歌曲”、“污蔑党媒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第四种是公私不分,指粉丝在追星时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比如举报粉丝“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上班时间公器私用,用政府账号造谣其他艺人”,教师将个人的追星好恶带入课堂,借此“为明星引流”。第五种是品行不端、违法犯罪,其中最常见的是批评粉丝“辱骂”、“造谣”、“网络暴力”,除此之外还包括“涉黄”、“歧视”、“内部霸凌”等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群体非理性”主要针对的是粉丝群体,但这些举报文本会特意强调“××(艺人)粉丝”的标签,其实质还是通过批评粉丝在追星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来损毁相关艺人的美誉度。
(三)道德恐慌
“道德恐慌”是在前两种策略的基础上,对“偶像失格”和“群体非理性”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强调,从而提高相关艺人应该受到惩罚或被封杀这一论断的论证力度。科恩指出,“社会似乎会时不时地遭遇一些道德恐慌时期。某种状况、事件、个人或群体会凸显出来,并被视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的一种威胁”(Cohen, 1972:1)。但实际上,“这种假定的威胁规模或严重程度往往要远远大于真实的威胁”(Thompson, 1998)。因此,“道德恐慌”也被看作是一种过度的社会反应(Young, 1971)。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和社会控制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所谓的“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s)往往选择一些极端的例证并罔顾其他事实而径直得出结论(胡泳,2011)。
当下制造道德恐慌的媒介从传统媒体转变为社交媒体,因此恐慌的蔓延范围和影响力大大扩张。更重要的是,这种制造道德恐慌的行动者不再只是传统的新闻媒体和警方、法庭等机构,过去作为“被讨伐”对象的粉丝自身也不断放大对其他粉丝群体可能造成的恐慌。
这种恐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上都有所体现。微观层面主要强调所谓的氪金和团队“洗脑”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影响,包括“向未成年人灌输错误的消费观、价值观、伦理观”,因为受到偶像明星的“荼毒”和“教唆”会“出口成脏”,甚至可能“动手打人”,从而“动摇国家的根本”。中观层面上,一方面声称其他粉丝群体通过制造性别、民族对立来“增加团体仇恨”、“污染饭圈环境”,另一方面要求对她们认定的劣迹艺人进行封杀和集体抵制,否则会“严重影响网络秩序”、“污染网络环境”。宏观层面则体现在对公共安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风气的破坏,例如主播在直播时骂人“完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艺人在疫情期间不能有效管理粉丝是“罔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维护偶像的粉丝“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成为破坏社会的工具”。
五、举报何以流行?
和过去的追星文化不同,当代“粉丝”身份是互相融合的,他们既是某人的粉丝,又属于公共议题的参与者,同时是政治的关注者。在平台机制、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影响下,追星、公共参与和政治生活融合成新的场景,从而制造出这一看似动荡不定的粉丝参与
行为。
(一)困在流量的漩涡里
电子媒介混合了原本以个人资本为边界的社会场景,形构了新的社会场景。为了适应混合的场景和信息系统,人在表演时产生了与戈夫曼有较为明确界限的“前后台行为”不同的“中台”行为(梅罗维茨,2002:46-48.)。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将娱乐、公共议题参与、人际交往、商业竞争等不同的社会机制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平台,形成多个崭新的、融合的场景,并随之产生了场景的新秩序和符合新场景的个体行为。
在本文的讨论中,明星粉丝“举报其他艺人及其粉丝”也是一种“中台”行为。如果说上一代饭圈的核心特点在于“文本中心性”(崔迪,2019),如今的饭圈实践则变成“以数据为中心”。以微博为代表的的现代媒介技术向发起举报的粉丝展示了一套“真理”:谁的话题流量高、谁的议题更严重,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重视度。不同平台和媒体对艺人提供了各种流量评价方式,例如微博超话榜、各大媒体在年末通过人气投票选出的“最具影响力艺人”,都是对粉丝活跃度和黏性的量化指标。以明星势力排行榜为例,该榜单除了对微博的阅读量和互动数进行统计,还涉及对明星社会影响力的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数据,一是提及明星的微博阅读量,二是相关明星的搜索量。为了让自己的偶像赢得更多关注,粉丝们需要依照其逻辑,使自己追捧的偶像在这类评选机制中有更多“可见性”,这也直接导致了饭圈内部“打榜组”、“数据组”的出现,通过这种看似自愿的行为承担起推广者的角色。
与通过打榜证明自身忠诚度和活跃度从而实现流量这种正面可见性不同,粉丝举报的主要逻辑是对其他明星产生负面可见性,但其本质还是不同粉丝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流量争夺。
首先,通过媒介获得可见性可以在公共场所获得某种存在或认可(Thompson, 2005)。在微博平台,用户 “转载”或“评论”对信息的扩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到信息传播的广度(高承实,荣星,陈越,2011)。更多的流量就意味着更大的可见性,粉丝通过在互联网公共空间发表大量同质性的举报文本,无论内容真假,只要流量够大,就可以覆盖关于该明星的正面文本,使其不可见:
粉丝掐架一般就是控评啊,要么就是在热搜里洗广场?啊,然后发一些对方的黑料,或者发自己的澄清,然后两边互发。如果黑料和这种举报文案压过对方的澄清文案,那就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胜利了。(访谈对象J)
其次,偶像明星的粉丝往往基数大、活跃度高,在社交平台有很强的消费意愿和宣传能力,因此一旦与社会、政治话题产生联系,会在短时间被大量浏览。对于参与“战争”的粉丝而言,这是让对家负面信息“破圈”最快速有效的办法。其中,营销号与同矩阵的其他账号成为将不同平台、偶像和粉丝的最新消息进行搬运、加工的娱乐信息中转站,依靠粉丝量和快速引流成为角逐的战场。除了收取艺人红、黑通稿的佣金,微博广告共享计划是其收入的一大来源,即依靠相关信息所得到的阅读量、互动量等流量获得平台的激励金。黑粉往往利用这些营销号的影响力扩大负面信息的“可见性”;与之相对,所涉艺人的粉丝将不得不发布正面评论“对冲”,降低负面信息的可见性,从而在短时间给予营销号大量流量,使其从中获取微博平台的激励金:
流量明星之所以是流量明星,是因为他本人有比较高的识别率,可以快速生产流量……这个话题人物和庞大的群体一旦与意识形态之类的话题结合,就会产生非常大的KPI,他们就是指望着这个事情出圈引起关注。(访谈对象O)
平台是有立场的,但是微博并没有在引导一个健康和谐的社区氛围。我们都很明确,作为饭圈的一部分,微博现在做的就是明星的生意,靠明星维持着整个平台的流量。粉丝和明星各自安好是无法给微博带来流量的,所以它就纵容那些营销号、那些引战的东西去填满社区,大家你来我往,自然就产生了巨大的流量场。(访谈对象A)
虽然粉丝并没有“对技术麻木”(麦克卢汉,2019:6),尽量保持着能动性,但面对一整套强势的技术逻辑,他们依然充满矛盾心理,将对话空间的所有权和关系的控制权让渡给以微博为代表的技术平台,困在其中无可奈何:
其实不管是明星还是粉丝,大家都是被玩弄的棋子而已。虽然我们有一系列反黑流程,非常复杂非常累,但最后也是营销号赚钱……这对于我们自己来讲也是非常烦恼的事,但又必须得去做这些事。因为这些营销号所进行的恶性比较会直接出现在你的广场上。我觉得这种(现象)才是真正需要进行网络整顿的。(访谈对象D)
(二)“打倒对手”的商业逻辑
粉丝举报的商业考量主要出于以下两点。首先,大量同质举报文本在提升明星负面内容可见性的同时,明星及其粉丝的名字在统计机构的数据收集中也成为了“关键词”。负面词汇与明星关联度的上升意味着艺人舆情风险的提高,因此还可以阻止他们获取商业资源:
现在已经造成一种印象,跟××的合作是有麻烦的,关联的负面东西越多,品牌会觉得找你有风险,尽管品牌会需要KPI和ROI,但品牌形象不是一时出来的,他们也会找其他人。对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访谈对象N)
其次,通过将艺人及其粉丝拉入社会、政治议题,可以使粉丝因为陷入恐慌而不敢生产流量或进行消费,艺人在商业竞争时所持有的“粉丝资本”便会随之缩减,从而在竞争中落后,就像访谈对象M说的:很多事件其实也是在PUA和吓粉丝,让大家离开。
“流量”不仅仅是技术逻辑的关键,也是粉丝经济商业逻辑的核心。流量明星的粉丝群体基数大、活跃度高,不仅能在短时间产生大量流量、奉献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主动消费的意愿也很高。这种以粉丝为基础,得到市场认可和利用的资产被看作是偶像的“粉丝资本”。“粉丝资本”不仅给商务合作伙伴带来了可观的潜在经济收益,还可以为他们省下宣发费用,导流新的消费者,并使产品“破圈”。因此,“粉丝资本”越高,越容易获得商业资源。
为更有效地寻求粉丝帮助安排宣发,多数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都会通过设置粉丝运营岗位来和粉丝组织保持联系。在与经纪公司的互动中,不少粉丝通过共情把自己当作“经纪人”,在内化了上述商业逻辑后自发行动。这些行动中不仅有加强偶像“品牌建设”的正向活动,也包括打击对手的举报行为:
盘子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为什么要合力打倒木秀于林的人,因为没有他以后还有其他人可以上,她们哥哥就能捡漏了呀。(访谈对象P)
(三)“拥抱主流”的粉丝文化
霍尔等在研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青年在战后发展出来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时,之所以强调“亚文化”而不是“青年文化”,就是要将其和主流的青年文化区分开来。如果说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粉丝文化还能够被涵盖在传统亚文化研究的“抵抗”和“收编”路径下,随着@共青团中央、@央视新闻等开始用饭圈行话与粉丝接触,粉丝组织越来越倾向归依主流话语,传统亚文化研究的“收编—被收编”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粉丝与官方话语的互动。
表面上看,这种互动经历了从“去污名化”到“互相利用”的过程。上文提到,69圣战后,以追捧韩国明星爱豆为代表的粉丝群体口碑坠入低谷,成为“脑残”、“非理性”、“不爱国”的代名词,但近几年的一系列网络爱国主义运动则使粉丝群体和原本反对追星文化的网民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握手言和。因为长期在社交平台上参与与偶像明星相关的网络辩论,“迷妹们”形成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成熟的组织架构(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虽然2016年和2019年的两次“出征”都使用了“控评”这种有争议的饭圈操作和“翻墙”这种有违网络管理规定的行为,但依然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赞扬和爱国网友的支持。如@共青团中央曾转发《守护最好的阿中!饭圈女孩出征“开撕”香港示威者》,对此表示鼓励。
这些出圈的粉丝现象改变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关系。在被官方肯定的同时,一些饭圈行为被正当化,举报也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主流话语则把饭圈文化与主流价值观、舆论引导有机嫁接(黄典林,2020),试图通过挪用饭圈的行话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例如宣布推出虚拟偶像、在直播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施工场景时添加打榜功能、邀请“最美女记者”王冰冰担任主题团课主持人等。此外,在出现影响范围较广的饭圈事件时,以@共青团中央为代表的主流社交媒体会发表评论,与粉丝互动、为事件定性。如定性某明星的粉丝雇佣星援APP为其偶像“数据造假”。相关研究还发现,在网络行动中,粉丝群体往往难以完成跨群体的动员,反而是@央视新闻等传统主流媒体担任了观点提供、引发大规模网络扩散的角色(崔凯,2020)。
因此,对于举报主体而言,其动机主要来自以下两点:首先,主流话语有管束饭圈的先例。PGOne被举报后@共青团中央曾发帖称该公众人物可能“触犯国家的相关法律”,新华网则评论其“遗臭万年”、“不配拥有舞台”,央视网、新华国际等微博官方账号也纷纷转发。随后,PGOne的公开演艺活动暂停。其次,在考虑政治机会的同时灵活调整行动方式(Ho & Edmonds, 2008),利用舆论来打压对手。通过日常的媒介活动,粉丝群体习得了一定的媒介运作知识,懂得调动各类媒介资源。对于他们来说,官方话语的加持是党同伐异的理想手段,因为一些共意性(consensus)运动往往容易获得体制的默许与支持(郭小安,杨绍婷,2016)。虽然并非所有举报都会被注意,可一旦被体制内社交媒体点评,对于被举报者来说就是巨大的打击,这也是内娱的独特性所在:
从共青团表扬饭圈出征之后,粉丝举报开始频繁地和它(共青团中央)扯上关系。这种行为不是在学韩国,而是中国粉丝群体自创的一套逻辑。因为饭圈女孩在中国一直处于底层,被表扬之后就觉得被肯定、背后有靠山、做事也更有底气了。(访谈对象E)
总体而言,粉丝群体希望利用举报打压其他艺人的粉丝群体,而体制内社交媒体在平衡整个饭圈的同时达到了维护主流价值观的目的。但这种表面上的互相利用掩盖了饭圈的文化运行逻辑被笼罩在政治逻辑下的实质。粉丝们对举报机制的使用和依赖实际上强化了对主流话语权威的认同,这种柔性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饭圈“泛意识形态”的趋势,即“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而忽视其内在的文化性和科学性”(俞婷,丁俊萍,2019)。粉丝们为了维护明星爱豆,必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强调个人的政治身份,表达政治立场:
不管是明星还是粉丝都要政治正确,就像公祭日或者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需要发声明、禁言、黑头像一样。一些吧主或者站长可能觉得没必要,但是为了不影响自家爱豆必须这样,因为不这样做就会被(别人)骂。(访谈对象E)
六、走向公共的饭圈战争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粉丝的组织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同粉丝群体在知识生产和公益活动方面凭借高效的行动力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例如2020年疫情期间,不少粉丝向武汉支援疫情物资,得到了网友和媒体的赞许。但是,饭圈当下一些交往方式和圈层形态并不利于公共讨论,反而只是在反复的争吵中消耗激情和耐心(崔迪,2019)。
在公共议题的设置层面,多种形态的媒介和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下公共生活的基础设施(潘忠党,2017),作为承载网络公共讨论的空间,平台理应具有一定公共性,即协助传播活动落实民主和理性的价值规范。但实际上,人们在社交平台创造并分享内容的同时也将自己对社会关系的控制权让渡给了平台 (Jenkins et al., 2016:154),公共生活的议题往往依照商业逻辑设定,争议性的娱乐议题被放大,社交平台成为传统媒体、粉丝、意见领袖、商家各方的“吃瓜广场”和“批评广场”。而在对公众议题的关注层面,为了实现打击对手的目的,除了与自身相关的娱乐话题,粉丝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关注政治议题,并通过订阅官方媒体账号,扩展了解政治话题的途径。
在公共舆论层面,对于饭圈外部的人而言,针对明星和粉丝群体的举报以社交平台为依托,不可避免地会外溢到原本应该用于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平台、商家等对极端粉丝的“选择性注意”使理智的粉丝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进一步凸显了饭圈的“非理性”和“争吵”的“群体特征”。事实上,作为基数极大的群体,粉丝群体中参与争吵与举报的仅是极少数,但当“举报”成为粉丝群体打击其他对立群体的舆论工具,当个体行为演变成带有群体标签的“战争”,则会导致整个粉丝群体再次被污名化。很多访谈对象都表示这种“再污名化”导致自己“社会性死亡”:不敢显示自己的粉丝身份,不敢公开追星。
在公共参与层面,虽然粉丝加强了对政治议题的关注,但这种关注的目的不是为了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就共同议题展开交往,进而通过信息的交流和意见的交锋影响公共政策(潘忠党,2017)。本应作为反映民意、维护权利渠道的网络举报成为部分人获利的工具,侵占了人们通过公共参与而创造出来的政治文化。通过将对手“非法化”、“妖魔化”(扬-维尔纳·米勒,2020),粉丝举报成为一种消极的公共参与,呈现出一定的民粹色彩,不利于多元社会的发展。
七、余论:作为另类参与的举报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无意对具体的粉丝举报行为做价值判断,因此没有对举报素材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关注这种特殊的粉丝实践也并不意味着要忽略粉丝群体内部的异质性,而是希望通过分析此类行为背后的动因与詹金斯等提出的作为参与文化的粉丝研究展开理论对话,从而在深化和发展参与文化理论。
首先,参与文化先入为主的正面意涵有待商榷。不同群体之间的争吵、斗争、举报作为带有一定负面情感的参与,也是粉丝生活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因此不应当把参与文化局限在积极的预设中。其次,参与文化的洞见之一是看到了粉丝群体作为社会公民的政治属性,认为他们能够以“公民的想象力”与他人产生共情,帮助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通过新的社会参与模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从而改变社会(Jenkins et al., 2016:152-155)。这种想象显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粉丝实践,在跨群体的日常交流中,他们更普遍性地从情感、道德的角度出发进行情绪式的“撒播”,其最终目的也并非为了相互理解和形成友爱互助的沟通氛围,往往单纯是为了“争口气”。第三,相关研究忽略了领导权(hegemony)赢取“动态平衡”的能力。詹金斯认为,传统政治机构习惯用官方语言和政治术语,把政治建构为一门专门知识,从而把它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实际上,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并非同质不变,而是会不断进行修订和改编(Gramsci, 1973)。通过对话语载体和话语内容的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巧妙改变了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原先的对抗关系,让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粉丝互相争斗与举报的过程中一次次得以重申与强调,在维护统治的同时塑造着对统治的认同。最后,现有关于参与文化的讨论中,对商业文化和媒介技术的关注显然不够,在当下的文化模式中,粉丝虽有主动参与的特征,但需要同时遵循平台技术逻辑、商业竞争逻辑和政治正确逻辑来行动。这些个体既是粉丝,也是网络议题的讨论者与行动者、商业竞争中的博弈者,以及政治的关注者。在强国家、强技术和强市场的渗透下,饭圈这个原本仅仅与个人好恶有关的文化圈层越来越难以逃脱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
尽管詹金斯等人关于参与文化的讨论存在一定不足,笔者仍然同意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期望——参与文化应当作为一种动态的定义,既包括对参与文化现实的描述,也包括对参与文化未来的期待。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一个典型、一种我们正共同努力实现的社会结构、一种对更好的文化构型的设想(Jenkins et al., 2016:22),一种“应然”的期待,能够通过个人道德和集体道德实现。
本文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从政治、经济、媒介三个外部因素出发,忽略了对粉丝情感和心理动机的探讨;其次,研究的经验材料只来自微博,随着粉丝举报的日常化,举报行为也慢慢向知乎、b站等其他平台扩散,举报在不同平台是否有不同的动员和组织方式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最后,粉丝在一轮举报完成后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会删除部分举报文本,我们并没有实时性地对相关事件做详尽的观察,难免缺少时间线上的梳理和归纳。后续研究可以针对以上问题进一步观察总结,从而提高相关粉丝研究的丰富性。■
注释:
①黑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粉丝,而是基于利益对特定明星或作品进行抹黑的群体。
②小粉红:源于晋江文学城论坛,因该网站采用粉色配色且女性用户比例较高而被称为“晋江忧国少女团”,并逐渐衍生为“小粉红”。新浪微博兴起后“小粉红”所指代的群体被扩大化,因为不同的动员和思考模式也存在“晋江小粉红”和“微博小粉红”等划分方式。在“帝吧出征”、表情包大战、萨德事件后,“小粉红”逐渐成为90后中爱国主义网民的代名词。
③应援:指通过购买专辑、支持票房、捐钱捐物等方式为自家偶像加油打气、接应援助。
④爆吧:起源于网络聊天室,指出于一定目的不断重复发送无实质内容的辱骂贴、水贴、垃圾贴,扰乱贴吧秩序。
⑤具体讨论可参考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58977160。
⑥指微博搜索某一词条或公众人物后显示的页面。
参考文献:
陈晨(2017)。“Anti粉”:解析互联网时代的另类粉丝文化。《青年探索》,(2),20-29。
崔迪(2019)。从Fandom1.0到2.0:粉丝实践的文化变迁。全媒派。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jaMnDTdUMe1CZGy6y6MsIg。
崔凯(2020)。破圈:粉丝群体爱国主义网络行动的扩散历程——基于对新浪微博“饭圈女孩出征”的探讨。《国际新闻界》,(12),26-49。
付晓光,宋子夜(2017)。情绪传播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极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142-151。
高承实,荣星,陈越(2011)。微博舆情监测指标体系研究。《情报杂志》,(9),66-70。
郭小安,杨绍婷(2016)。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米姆式传播与共意动员。《国际新闻界》,(11),54-74。
洪培琳(2018)。冲突视角下的粉丝文化现象分析——浅谈粉丝微博骂战频发症候。《现代营销(下旬刊)》,(1),200。
胡百精(2016)。互联网、公共危机与社会认同。《山东社会科学》,(4),5-12。
胡岑岑(2020)。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中国青年研究》,(2),112-118+57。
胡泳(2011)。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青年记者》,(34),30-32。
黄典林(2020)。从边界危机到霸权重构:科恩与霍尔的道德恐慌与媒体研究范式转换。《新闻与传播研究》,(6),5-20。
李慧(2018)。《微博发布报告显示:粉丝数超过2万的头部作者已达70万人》。光明新闻网。检索于https://life.gmw.cn/2018-12/21/content_32217159.html。
刘海龙(2017)。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7-36。
刘海龙(2020)。《宣传 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吕鹏,张原(2019)。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中国青年研究》,(5),64-7。
麦克卢汉(2019)。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孟威(2020)。“饭圈”文化的成长与省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9),52-59+97。
潘忠党(2017)。导言:媒介化时代的公共传播和传播的公共性。《新闻与传播研究》,(10),29-31。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11),33-53。
王艺璇(2019)。建构与赋权:网络粉丝社群的文化再生产——基于鹿晗网络粉丝社群的实证研究。《学术界》,(11),151-158。
威廉斯(2011)。《文化与社会:1780~1950》。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吴靖,卢南峰(2019)。政治成熟的可能性:以“工业党”和“小粉红”的话语行动为例。《东方学刊》,(2),2-14。
熊光清(2014)。中国的网络监督与腐败治理——基于公民参与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2),42-46。
扬-维尔纳·米勒(2020)。《什么是民粹主义》。江苏:译林出版社。
杨国斌(2013)。《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玲(2020)。撕:网络圈层冲突中的语言操演、认同建构与性别鸿沟。《文化研究》,(1),37-53。
艺恩数据(2021)。2020年中国偶像发展报告。检索于https://www.endata.com.cn/Market/reportDetail.html?bid=5741aa27-4a35-49b0-8d4b-be535dab433f。
尹一伊(2020)。粉丝研究流变:主体性、理论问题与研究路径。《全球传媒学刊》,(1),53-67。
俞婷,丁俊萍(2019)。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构路径思考。《学习与实践》,(11),23-28。
张婧(2019)。新媒体时代下“粉丝”过度参与式追星引发的弊端及影响。《戏剧之家》,(12),204-205+208。
郑欣(2007)。当平民遭遇“皇后”:“粉丝”及其偶像崇拜行为研究——以后选秀时代的“玉米”粉丝为例。《青年研究》,(3),15-20。
朱丽丽,韩怡辰(2017)。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6),72-76。
BroughM. M. , & Shresthova, S. (2012). Fandom meets activism: Rethinking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 10.
Cohen, S. (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Fiske, J. (1989). Reading the popular. Routledge.
GarberE. , & PaleoL. (1983). Uranian worlds: A reader’s guide to alternative sexuality i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Hall Reference Books.
GrayJ. (2003). New audiencesnew textualities: Anti-fans and non-f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6(1)64-81.
GrayJ. (2005). Antifandom and the moral text: Television without pity and textual dislik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8(7)840-858.
GrayJ. , Sandvoss, C. , & Harrington, C. L. (2007).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mediated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HoP. , & EdmondsR. (2007).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Routledge.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Routledge.
Jenkins, H. (2006a).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H. (2006b). Fans, bloggers, and gamers: Exploring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H. , & ItoM. , Boyd, D. (2016).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a networked era: A conversation on youthlearning, commerce, and politics. John Wiley & Sons.
JensenJ. (1992). Fandom as pathology.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9-29.
JungS. , & Shim, D. (2014). Social distribution: K-pop fan practices in Indonesia and the ‘Gangnam Style’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7(5)485-501.
Kim Mi-gyeom. (2012). 90?? HOT vs ?? ??? ‘??+?????’. newsen. http://sns. newsen. com/news_view. php?uid=2012082223482306102012-08-23.
Price, L. , & Robinson, L. (2017). ‘Being in a knowledge spac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cult media f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43(5)649-664.
ShimD. B. , & NohK. W. (2012). YouTube and Girls’ Generation Fandom.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 Contents Association12(1)125-137.
ThompsonJ. B. (2005). The new visi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2(6)31-51. https://doi. org/10. 1177/0263276405059413.
ThompsonK. (1998). Moral panics. Psychology Press.
Tulloch, J. , & JenkinsH. (1995). Science fiction audiences: Watching doctor who and star trek. Routledge.
Young, J. (1971). The drugtakers: The social meaning of drug use. MacGibbon and Kee.
Zhang, Q. , & NegusK. (2020). East Asian pop music idol prod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ata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3(4)493-511.
Zhang, W. (2016). The Internet and new social formation in China: Fandom publics in the making. Routledge.
Zhang, W. , & MaoC. (2013).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1)45-61.
秦璇、陈曦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韦路教授和“百人计划”研究员黄广生曾对本文提供意见和指导,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