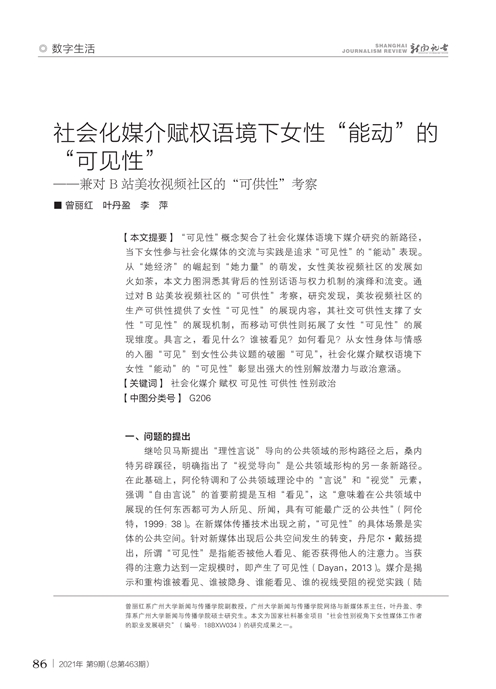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
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
■曾丽红 叶丹盈 李萍
【本文提要】“可见性”概念契合了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媒介研究的新路径,当下女性参与社会化媒体的交流与实践是追求“可见性”的“能动”表现。从“她经济”的崛起到“她力量”的萌发,女性美妆视频社区的发展如火如荼,本文力图洞悉其背后的性别话语与权力机制的演绎和流变。通过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研究发现,美妆视频社区的生产可供性提供了女性“可见性”的展现内容,其社交可供性支撑了女性“可见性”的展现机制,而移动可供性则拓展了女性“可见性”的展现维度。具言之,看见什么?谁被看见?如何看见?从女性身体与情感的入圈“可见”到女性公共议题的破圈“可见”,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彰显出强大的性别解放潜力与政治意涵。
【关键词】社会化媒介 赋权 可见性 可供性 性别政治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继哈贝马斯提出“理性言说”导向的公共领域的形构路径之后,桑内特另辟蹊径,明确指出了“视觉导向”是公共领域形构的另一条新路径。在此基础上,阿伦特调和了公共领域理论中的“言说”和“视觉”元素,强调“自由言说”的首要前提是互相“看见”,这“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阿伦特,1999:38)。在新媒体传播技术出现之前,“可见性”的具体场景是实体的公共空间。针对新媒体出现后公共空间发生的转变,丹尼尔·戴扬提出,所谓“可见性”是指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的注意力。当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即产生了可见性(Dayan, 2013)。媒介是揭示和重构谁被看见、谁被隐身、谁能看见、谁的视线受阻的视觉实践(陆晔,赖楚谣,2020)。作为赋予事件、个人、群体、辩论、争端、描述等可见性的机构,媒介是通过“展现”来赋予他人可见性的(Dayan, 2013)。然而,可见性并不是以一种线性的、直接的方式与识别联系在一起的,其有一个最低限度,即“公平的可见度”,低于这个限度,就会被社会排斥了(Brighenti, 2007)。媒介化社会中的女性如何被“看见”,即女性的媒体再现(representation),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经久不衰的中心话题(冯剑侠,2020)。然而有学者研究指出,当下女性形象的媒介再现过于强调女性是男性主导媒介产业中的被动受害者,对女性的描述起因于(result from)映射(reflect)和复制(reproduce)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而“逆向再现(counter-representation)”的性别话语如何被生产,应成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重要任务(Fotopoulou, 2016:11)。
社会化媒体是建立在Web2.0思想与技术基础上的网络应用,它促成了用户生产内容的生产与交换,体现出强烈的社交倾向和用户主导特征。赋权(empowerment)的概念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歧视研究,天然具有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意识(黄月琴,黄宪成,2021)。赋权常常和参与、权力、控制、自我实现和影响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范斌,2004),由于权力的关系转向,赋权理论从“为弱者的传播”转变为“弱者的传播”,弱者的内部性、关系性和能动性得到重视和强调(黄月琴,2015)。数字技术的出现与普及给普通用户尤其是社会弱者进行“赋权”,赋权并不是简单地从外部输入权力和资源,而是一种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这意味着,弱者从作为受动对象和权力客体的地位,转换为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能动者(黄月琴,2015)。当下女性的数字交流实践可视为技术赋权语境下女性追求“可见性”的一种“能动”表现。在这里,“能动”指涉的是一种主体性实践,它强调主观意志的自由支配性。“互联网媒体、手机、便携式相机以及它们提供的多种组合已经成为重新部署可见性的工具,这种形式允许公众以自己的方式获取知名度以及定义他人知名度,成为知名度的组织者”(Dayan, 2013)。譬如在新冠疫情中,武汉市民李丽娜的“敲锣救母”事件折射出自我曝光的可见性追求(刘鹏,2020)。可见性的获得将用户重新塑造为传播主体,“重返公共领域”,通过被“看见”,“构成了公共生活的意义,也是人类获得存在感、确认自身以及这个世界的方式与源泉”(孙玮,李梦颖,2014)。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生态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了“可供性”的概念,他认为“可供性”源自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对象的客观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构成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Gibson, 1979),在传播研究中其被应用于探讨媒介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Hutchby, 2014)。“可供性”探讨人与技术环境之间的积极交互关系,故而为当下的新媒体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循此理论逻辑,潘忠党将新媒体的可供性界定为三个层面: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内容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潘忠党,刘于思,2017)。立基于此,本文采纳“可见性”这一概念作为衡量女性在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技术可供性)能动展现的价值尺度。诚然,女性的“可见性”离不开媒介提供的“可供性”资源。在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本文将着力探讨以下问题:女性的“可见性”将通过何种“可供性”条件“能动”地展现出来?社会化媒介平台的技术资源如何遭遇女性“能动”的策略性使用?具言之,看见什么?谁被看见?如何看见?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将如何勾连性别权力结构的流变以及性别政治话语的浮现?
二、研究方法
B站(Bilibili.com)是依托社交互动模式发展起来的网络视频社区,其主要视频类型从当初的动漫和御宅族游戏向如今的美妆、电影、娱乐、学习等多元分区转变。B站月活用户超过1.72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时尚潮流文化社区。本研究选择B站美妆视频社区作为展现女性“能动”的“可见性”的实证考察对象,主要是因为其对女性而言具备强大的平台“可供性”,这种“可供性”资源极大地赋权了女性在数字空间的能动性即“弱者的传播”:其一,B站美妆视频社区以聚集的女性用户为主,她们因美妆视频而结缘,因数字实践而群聚,是一个适合于做女性研究的绝佳样本;其二,B站美妆视频体量庞大,内容丰富,涵盖美妆教程以及彩妆、护肤相关产品测评和分享等,其内容生产呈现出高度的UGC倾向,凸显出丰富的生产可供性;其三,B站基于Web2.0技术架构,用户的社交性和互动性很强,是研究社会化媒介平台技术赋权的恰当场所,提供了多样的社交可供性;其四,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发展,“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新媒体用户的新生活方式。社会化媒体的移动场景拓展了美妆视频社区女性用户的“可见性”范围与领域,这种新的可见性突破了物理时空阈限,具备鲜明的移动可供性特征。此外,B站美妆视频社区每日自动生成热门榜单,有利于研究者对数据的抓取、遴选和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潜入B站美妆视频社区观察用户日常交流实践的媒介社交生态,抓取美妆博主与用户以及用户之间的互动评论进行分析。通过PYTHON爬虫软件,研究者抓取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5月25日每日上午10时以前美妆区热门榜前三名的美妆视频和前两百名的热门评论每天3篇,一共抓取样本459篇。在这段时间内,B站运营团队主推美妆视频,主题活动较多,热点事件频繁。在话语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参考了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实践分析方法中的重要维度,即对一个完整的语言使用互动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力图挖掘出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美妆社区女性“能动”的“可见性”机制与性别话语实践表征。此外,研究者还采取了“滚雪球”的方式追踪访谈了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女性用户。这些访谈对象均具有一年以上的美妆视频观看经验,且涵盖不同的职业和学历背景。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通过不断的深入提问和反复追寻,引导访谈对象从多种角度呈现美妆观看经历和内在体验,从而保证个体经验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呈现,最终访谈话语将结合评论话语与弹幕文本共同展开分析。
三.看见什么?生产可供性提供女性“可见性”的展现内容
诚然,任何的媒介都是通过展现来赋予他人可见性的。在信息生产可供性层面,B站作为社会化媒介平台提供了一套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和可关联的话语生产模式与数字实践系统。平台是计算和架构,但也可以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理解为政治舞台或表现行为的基础设施。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来,平台是转义者而不是中介者:它不仅仅促进,同时也塑造了社会行为的表现(范·迪克,2021:32)。而话语具有建构性的力量,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的论证性言语,话语的形成、散播、转换、合并等过程势必搅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曹晋,徐婧,黄傲寒,2015)。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女性用户通过编辑、审阅和复制,采纳伸缩性和关联性等话语实践,能动地展现出身体和情感这两个维度的性别话语,并以数字书写的自主传播方式聚焦女性的主体性欲望,从而让美妆视频社区成为一个社会性别意义的协商中心和权力场域。
(一)可伸缩话语能动地展现女性身体
传统的大众传播将传播仅仅视为一种精神交往,却忽略了身体这一特殊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刘海龙,2019)。巴特勒认为,身体是承载一切身份的重要场所,而自我也在身体之上书写(王玉珏,2018:15)。美妆视频社区的女性用户通过独特的身体经验进行数字交流与实践,在群体氛围中不断地进行性别审视和自我确认,最终内化为稳定的主体性诉求,藉此以抵抗男权凝视下的客体他者化属性。在此过程中,女性身体意向背后象征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探索也得以显现,由此而带来的积极正面评价能够帮助女性建构更好的自我身份认同。
1.共享女性身体的美妆经验
女性的身体是个人的,社会的,也是文化的。女性通过讲述自己的身体、欲望和疼痛,由此来实现社会化媒介“可供性”资源的技术赋权过程。在这里,“赋权”是一个动态的、跨层次的体系概念,是社会互动的实践过程,需要嵌入日常的互动场景来得以实现(Rogers & Singhal, 2003)。在B站这样的文化社区,话语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交流,更是一种身份标签和社交货币。美妆视频社区以“姐妹”、“集美们”(姐妹谐音)、“小姐姐”、“小伙伴”等带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称谓来互相称呼,并挪用“大家”和“我们”这种天然具有代入感的第一人称主语,如“大家都在变得更好啊!女孩子为了变美努力的感觉好棒啊”(2020-2-7,3),诸如此类的话语让美妆社区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性别排斥的女性媒介。在这种话语空间中,女性可以不受遮蔽地明确表达个体的身体经验,譬如在开放的性别氛围下女性可以自由地谈论较为私密的如脱毛、医美整容、术后恢复等问题,有助于打破女性身体话题的被遮蔽状态。“手臂上的毛毛超级多,又黑又干,蜜蜡或者脱毛膏脱过后还是很快长出来了,绝望了”(2020-2-25,1)。传统的性别秩序习惯打压女性的审美意识,将女性追求身体美与虚荣肤浅划上等号,而当下美妆社区却能通过数字实践为女性出谋划策,将女性的身体审美追求正当化。“很多术后修复的问题都是特别具体的,我会跟姐妹私信聊天,大家也都很真诚给你意见。比如最近美容仪器风特别大,然后牌子型号功用特别多,我就跟一个姐妹私信讨论了挺久,互相分享使用感受,最后决定了买哪一款”。①去中心化的交互平台为女性谈论身体经验提供了一个安全场所,女性用丰富的话语表达和内容创意呈现出被遮蔽的青春体验与身体故事。
2.重构女性身体的审美标准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身体美不仅成为一种交换工具,而且不断地为男权社会的欲望及认知代言(何涛,2015)。被规训的女性化妆往往服务于男性,特别是其配偶或对其具有权力关系的男性的审美需求,具有“女为悦己者容”的价值导向(郝大海,朱月婷,2016)。B站美妆视频社区改变了单向度的男权话语体制,让更多女性身体的另类审美标准得以呈现。女性积极参与表达对身体美的理解,并在审美层面上创建了新的话语通道和建制标准。有女性用户大胆表达了对传统“白瘦幼”、“斩男色”等过时男性审美标准的抵制,创造了女性定义的新标准,如“姨妈色、吃土色直男不懂的”(2020-3-4,1),重建美妆只为取悦自己的价值理念,“化妆不是为了吸引别人,只是为了漂亮自己看了也开心”(2020-1-27,2);“我为什么要管你喜不喜欢,我自己喜欢不就行了吗?我化妆是给自己和姐妹看得,直男根本不懂我妆容的细节”。②女性的身体美不再是男权凝视下的物化欲望,而是众多姐妹的共享之物。反对以标准模板管理女性的身材,关爱女性产后恢复的身材焦虑。譬如“要我生养,还要我面容发光身材不走样。真的,活着够累了,接受自己的身体开心就好”(2020-3-21,3)。波伏娃认为女性身体应是女人获得自由的情境和媒介,而不是一种被定义和限制的本质。女性通过对自己身体的自由支配,叛离社会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气质,并将这一背离举措与自我、性别、身份想象相勾连。“你有权力支配你自己的身体……当我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用来取悦自己而不是迎合他人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男人味’还是‘女人味’的标签都无所谓了”。③通过社会化媒介平台的协商互动,女性用群体经验和话语修辞改造或重新书写了女性身体美的定义与标准。女性通过身体展演创造出自我定义的审美身体,通过携带这些“可见性”表征和“能动性”元素从而进入公共领域。
(二)可关联话语能动地展现女性情感
女性的自我主体性通常涉及两个向度,纵向上的自我是主我与客我的关系,是“自我意识深度感和内向感”;横向上的自我是“主我”与非我的关系,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王成兵,2004:16)。从主体性生成的角度来看,纵向上的自我是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探索,而横向上的自我则是女性与他人的关系,体现为女性的主体性得到他人乃至社会认同的过程。B站美妆社区为女性搭建了一个开放的数字话语平台,女性可以从中汲取她人给予的情感资源与力量,并将这些资源内化为主体的身份认同进而实现主体的蜕变与升华。
1.纵向自我的心灵互鉴
B站美妆视频社区以制造美丽为核心议题,锻造了独特的性别话语空间并链接共享了一套内部流通的数字符码系统。如“转发”是社会化媒体的一种主要传播形式,也是型构社会传播链条的关键技术机制,是社会议题、信息、意见和舆论扩散所仰赖的重要手段(黄月琴,黄宪成,2021)。在这个开放的信息集散平台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话语和经验,女性通过信息的转发扩散与连接交换实现心灵成长。如“种草一个隔离”、“杨树林212和阿玛尼405鬼打墙,已拔草”和“给集美安利TF20的平替”(2020-1-8,2)。用“种草”、“拔草”、“安利”等词汇迅速地进行知识共享,并形塑主体之间的身份认同。如“我加入了一个二手闲置美妆群……总有万能的网友帮你解决问题。姐妹之间聊什么都可以。很多小姐姐发自己的妆面大家都会夸好好看,大家都抱着很善意的心态”。④“大概像最近浪姐里面流行的那句话,女性是可以帮助女性的”。⑤诚然,一个展现女性生活多维图景和滋养女性身心健康的数字实践社区能够让女性得到心理满足感,社会化媒介平台的交互性与“可见性”,让女性在信息共享和情感交换的“弱关系”连接中抵达心灵互鉴与精神皈依。
2.横向自我的情感支持
当下美妆视频成为女性的潜在教育资源,博主们在传递美妆技术的同时,还会向追随者传递更深刻的性别解放意涵(Choi & Behm-Morawitz, 2017)。“社交平台也是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可能通过数字空间的自主选择进行自我表达的替代性场所”(陆晔,赖楚谣,2020)。美妆社区这一性别乌托邦成为了情感交换的安全场所和关系型传播实践场域,在这个平台上,女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男性中心视角的忽略、骚扰和嘲笑,可以大胆地分享自己的困惑、脆弱和无助。如“烂脸+胖+腿粗……青春期到了就开始长痘,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有的长辈一见到我就说哎你的脸怎么这样了,我妈妈也就这件事骂过我很多次,就越来越自卑(2020-12-25,3)。其他用户则给予了充分的情感支持,“前期经历和你很像,现在感觉一切都在慢慢变好吧……”和“不哭不哭会越来越幸福的宝贝!”当女性看见与自己有相似经历者时往往会激发情感能量,那些曾经遭受过霸凌的弱势女性之间的情感支持网络也会编织得更加绵密,即构成所谓的“强关系”连接。“我初中也遭遇过霸凌,虽然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看到评论里有人因为胖被嘲笑而难过,忍不住安慰她告诉她都会过去的。希望能让善意跨越5G飞到眼前,毕竟这个世界还是好人更多”。⑥传统的性别秩序涵化培养了女性对自我身体和情欲的耻感,抑制了女性的主体诉求和展现欲望。B站美妆视频社区着眼于女性个体的成长经历,聚焦容貌焦虑、身材管理、术后修复等一系列女性独特的社会经验,在数字实践平台凝结形成了短暂的性别共同体。她们相互看见、彼此承认、肯定彼此的女性魅力和力量,重新定义女性价值,进而有效地抵制了男权社会的话语规训和符号暴力。
四、谁被看见?社交可供性支撑女性“可见性”的展现机制
电子媒体创造的“可见性”能够顺利抵达“去空间化”的观照:在远处的其他人可以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变得可见,即可以在他们说话的时刻被听到,在他们行动的时刻被看到(Thompson, 2005)。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数字虚拟空间使得身处不同时空的个体变得“清晰可见”,其社区内部的技术链接还可以拓展“彼此可见”的视觉范围。从话语权力位置来看,B站女性用户主要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可见性”的勾连:一方面美妆博主与用户之间属于纵向话语权力结构下的“可见”,用户自下而上的社区实践被博主看到,博主主动收编强化用户的群体归属感;另一方面用户之间的“可见”属于横向平行话语权力之间的“互见”,用户的交流实践都是基于相同话语权力阶层的意见交换和观点表达。总之,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话语权力下的“可见”,实际上都是将数字媒体创造的“可见性”推及女性群体层面。用户的数字交流实践是社区得以形成与修护的重要载体与手段,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点赞、评论和转发的形式也是追求可见性的标记(Duffy & Hund, 2019)。具而言之,B站的数字交流实践在社交可供性层面,衍生出一系列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等可供性指标。
(一)用户赋权博主以“可见性”
1.一键三连机制。“一键三连”指的是B站弹幕推出的支持Up主的一种方式,指长按点赞键的同时对娱乐作品进行点赞、投币、收藏(闽南网,2019)。伴随着美妆博主及其视频影响力的增加,用户的观点也会随之被放大。用户们通常通过一键三连的方式支持博主,这些内容经过用户推荐,会获得更高的热度,进而促使博主快速出圈。换言之,用户选择与自身价值观相一致的美妆博主意见领袖,通过数字实践方式助力其发声最终实现博主的破圈可见。故而博主在美妆社区的地位以及博主的视频内容及灵感有赖于这些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粉丝用户的支持,可以说是这些用户赋予了博主在美妆社区中的“可见性”排序。
2.仪式互动实践机制。参与网络社区的成员因为共同的爱好和价值观产生了情感纽带,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联系是短暂的,因此,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博主与用户还需要借助仪式性的互动举措来巩固她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网络社区也是一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只不过在网络社区中划分等级的标准不再是以个体成员的社会身份、地位或名望等社会资本为主,而是以文字表达技巧、专业知识以及上线时间、频率等文化资本为主(宫承波,齐立稳,2008)。如果某用户拥有某美妆博主的粉丝勋章,则表示该用户与博主之间的互动连接程度较高,粉丝勋章的级别越高,则表示该粉丝对博主的喜爱度与贡献度也越高。当用户加入到博主的应援团和粉丝团中,便可践行仪式性的互动实践活动,譬如通过签到来强化粉丝的社区成员仪式感与归属感,仪式性的互动实践还可有效推进社群内部的规范化执行。粉丝的劳动贡献大小、掌握资源信息的多少、阐释能力与传播技巧等形成等级分化,最终决定了美妆博主“被看见”的机会与频率。相应地,应援团与粉丝团的数量与质量也将决定博主在圈内或出圈“被看见”的程度。
(二)用户赋权自身以“可见性”
1.课代表机制。用户通过自己在网络社区的文本叙事等数字虚拟实践引发博主与其他用户的关注,从而让自己被看见。在B站美妆视频社区中,用户最主要的虚拟实践行为就是信息性交流,通过信息性交流,用户可以凸显自身的“可见性”,直至“被看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课代表机制。“课代表”一般会针对视频中美妆博主所使用的化妆品、护肤品、化妆技巧与服饰品牌进行总结,然后把相关信息放在评论区,供其他用户或者粉丝能够轻松获取。“课代表”的信息往往占据评论区前排的位置,如在美妆博主@二门_发布的一则“一起换头/不用p图也是靓女的春天日常妆”美妆视频的评论区中,一位用户主动承担起“课代表”的职责,她在评论区发表文字:“课代表来了!ysl all hours粉底液#b10(划重点吃糖长痘!懒的姐妹可以用湿巾把海绵蛋打湿2.歌剧魅影遮瑕膏(二门抠门小技巧:用卷发棒加热一下哈哈哈哈)在泪沟处盖住用扁的刷子在边缘晕开把不顺眼的痘印全遮住遮住遮住!”于是“课代表”得到了美妆博主本人的点赞与评论“棒棒”(2020-04-17,1),众多粉丝也将其评论顶为热评,并在该条评论区中留言表示支持。“课代表”通过认真总结美妆信息,从而让自己被博主与其他用户“看见”,进而强化了自己在美妆视频社区中的地位。
2.弹幕互动实践机制。B站的流量主要是通过Up主的个人视频所形成的私域流量,评论区和弹幕区成为用户最主要的被可见场所。在观看网站的视频时,弹幕会随着视频滚动播放,这种“即时交流”的错觉会带给用户“共同观看”的感觉。在美妆博主@程十安an(2020-01-06,3)发布的视频“拯救肿单眼/肿内双!肿泡眼超级自然放大术”中,视频内容主要是博主针对模特的肿单眼皮进行改造。面对模特的肿单眼皮,该视频用户的弹幕纷纷表示“你拍我干啥?”、“这不就是我的同款眼睛吗?”由此可见,女性对于单眼皮美妆的操作难度感同身受,她们借助弹幕这一文化实践形式让自己的观点适时出现,同时被其他用户看到进而与之在情感上产生勾连达成共鸣,进而使得B站美妆视频社区升华为一个聚焦共同情感经验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被看见的过程中,(女性)个体通过对话、传播而获得信念,抑或是借由媒介进行自我言说产生自我效能与彼此的认同感(Rogers & Singhal, 2003;丁未,2011)。
五、如何看见?移动可供性拓展女性“可见性”的展现维度
社交媒体的潜在解放作用是给弱势群体提供发声的渠道和公共空间、带来参与体验和认同感,以及建立守望相助的社群,从而进行内生性赋权(黄月琴,黄宪成,2021)。社会化媒体的移动可供性涵括可携带性、可获取性、可定位性等多项指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发展,“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当代新媒体用户的新生活方式。“受众不再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使用媒介,而是呈现出一种连续不断的新媒介使用状态”(周葆华,2020)。当下媒介技术日趋透明化与隐形化,已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领域的普通实践(孙玮,2020)。在社会化媒介的可供性配置下,女性在流动的数字实践社区通过“反叛身体”和“姐妹情谊”的互文叙事来寻求适合自己的传播话题与交流范式,从而“能动”地构建出女性主体的“可见性”。
(一)展现流动空间的“反叛身体”
B站美妆社区的类型结构决定了视频的规范程式和叙事脉络是建立在身体展演基础之上的,无论用户还是博主都致力于维护一个特定的、理想的身体形象。在美妆视频社区,我们看到的都是女性“能动”呈现的身体状态,一方面女性通过主动性化身体来俘获男权凝视,另一方面女性又主动改写身体审美标准以抵御男权凝视,这种矛盾的镜像表征映衬出女性自我放逐的反叛意愿。显然,重塑流动空间的审美身体和姐妹情谊是见证女性主体性觉醒和成长的过程。
社会化媒体构成了公共传播的舞台,在那里规范得以形成,而规则受到质疑。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提出的那样,规范构成了基础法律法规的社会和文化黏合剂(范·迪克,2021:20)。吉尔强调的“强制性别个体”(compulsory sexual agency)如今变成了必需,它再次把女性的性别个体变成一套技术规训:即主体化依然是一种基于自我审视和自我规训意义的性别化(斯泰纳,2021)。然而,伴随着“她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社会价值的提升,女性敢于从自身立场出发,以一种挑衅的、不可回避的姿态,大胆宣扬自身的主体欲望。“我打扮成什么样实际上就是想变成什么样,身体即表达”。⑦社交平台上的身体表演带有强烈的社交属性,一些女性用户刻意呈现暴露面积较大,妆容艳丽等夸张的欧美浓妆风格。她们通过性感的妆容反抗监管女性身体、规范女性审美标准的社会樊笼,并用这种身体越轨的行为来挑战传统观念中男权意识对女性身体的枷锁和规约。当下男权对女性身体的监管正在逐渐弱化,性别道德的约束力也正在式微。社会化媒体空间的数字能动性进一步给女性的身体松绑,女性通过多媒介符码主动“戏仿”客体化的她者形象,进而对男权社会景观化的技术规训进行了批判和颠覆,并且将性感的身体由荡妇羞耻改写为女性魅力的新典范。
此外,女性还通过主动降低身体的可观赏性来实现身体反叛,找回女性身体的归属权。正如学者所言:“流行文本中所产生的模棱两可的意义对应了主导意识形态内部的断裂带,而流行观众正试图在商品化流行文本的缝隙和边缘建立自己的文化”(詹金斯,2016:33)。女性正试图从主流文化的性别图式中挣脱出来,通过美妆实践建立自我界定的女性气质。在这种媒介实践的流行文化消费中,女性可以只选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或是有快感的文本内容来加以呈现。而这种斗争和协商正如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群体竞争象征权力——亦即对象征价值的诠释权”(王金玲,2013:127)。概言之,“我不需要为他人的目光而活”。⑧一直以来,男权体制迷恋于对女性身体的象征意义进行争夺,但是在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通过媒介性别的“逆向再现”,有意建立起具有对抗性和区隔度的身体审美标准,以改变不对称的男女位置关系,意即通过主导身体的审美逻辑来抵抗男权体制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再生产。
(二)展现互联场域的“姐妹情谊”
传播学者齐齐·帕帕卡瑞斯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引入了一个模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界限的空间概念,并声称这种不确定为身份的形成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范·迪克,2021:17)。当下姐妹情谊一直是当代女性运动中重要的团结力量,其强调女性在社会以及家庭中次要地位的相似性,这一概念在反对男权体制中具有号召力。姐妹情谊通常理解为是一种对其他女性的依恋、忠诚、滋养与支持的感觉,这种感觉生发于共同的受压迫的经历(Dill, 1983)。姐妹情谊跨越种族、阶级与性别的视角,尤其是当女性被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层特权等分割时,能够“唤醒共同被压迫(common oppression)的感觉”(Hooks, 1986)。因此,姐妹情谊概念颇具政治色彩,正如当下女性在公共领域团结为女性发声,谋求女性群体的政治权力等。然而,“当前本土数字空间中的‘姐妹情谊’更多是一种情感性而非政治性的话语/行动召唤,即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女性互助与团结:‘我们感受到另一个女性的需要和她们的痛苦,并感到这跟自己休戚相关’”(冯剑侠,2020)。换言之,流动数字社区的女性会因为共同的性别身份或者相同的人生经历产生共情,并且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在困境之中挣扎的姐妹,进而在数字互联场域寻求到女性所特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其实就是想找个树洞倾诉一下自己的故事。很多留学经历都感同身受,好多姐妹分享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包括好玩的地方啊,哪里有化妆品折扣啊,就觉得很温暖。尤其是在天天说英语的环境里,有时候就想听一下中文,看一下中文,自己用中文组织一下语言跟人说说话就很好了”。⑨B站美妆视频社区女性用户之间的互帮互助构成了数字空间的姐妹情谊,这种情谊突破了物理时空边界的阈限。对于她们而言,女性向(以女性为主要生产对象)的美妆视频社区是一个在线安全空间,可以实现女性公共议题的探讨,提升女性在数字空间的话语主导权。概言之,陷入容貌、身体和情感焦虑的女性在美妆视频社区中,通过相互扶持与彼此温暖来连接流动空间的姐妹情谊,一声声“集美”、“姐妹”作为一种流动的符号化中介,将互联场域的姐妹情谊和亲密关系生态群簇具象化与祛蔽化。
六、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
每个人都拥有可见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Dayan, 2013)。本文通过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从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层面发掘出女性数字社区“看见什么”、“谁被看见”、“如何看见”等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的“可见性”机制,进一步拓展了“可见性”概念在女性媒介实践过程中的内涵与外延空间。正如巴特勒所言,我们需要通过他者来发现自身,社会化媒体能够帮助女性自我发声并且超越现实中个体的连接进而从更广阔的范围内凝聚女性力量,有助于引领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媒介“可见性”性别体系,因而也拓展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可见性”范围与强度。诚如学者所说的,“社交媒体极大地拓展了公共空间的内涵,让‘当今的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由各种形态的中介的可视性(mediated visibility)所形成’”(潘忠党,於红梅,2015)。“在互联网时代,赋予‘可见性’的主体不再仅限于大众媒介,而是扩展到了社会个体”(姜红,开薪悦,2017)。诚然,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的“可见性”从个体出发对公共领域做出了新的阐释和理解,“媒介的公共领域不仅仅是社会持续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提供展现和表演的可见性空间。甚至,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可见性可等同于公共性”(Thompson, 1995)。
赋权是指弱势群体通过自身参与或外部推动,激发自身潜能,令其在更大程度上掌握社会资源和自身命运,从而改变自身无权或弱权的社会现状(丁未,2009)。而民众的自我书写行为可视为底层作为传播主体所践行的一种自主传播实践,凸显其公共意义(Dixon & Linz, 2000; Rajaram, 2002; Flores, 2003; Xing, 2012; Brophy, Cohen & de Peuter, 2015),这是一种以“参与式赋权”与“互动赋权”为主导的“主动赋能”或“内生性赋权”模式。从根本上讲,可见性是以媒介为媒介,并受媒介本身的影响(Bucher, 2012)。在社会化媒介语境中,可见性拓展了以人为媒介的传播机制,并给予女性更多可见背后的能动权力。因为“增加可见性是获得更多机会、公平和权力的关键”(斯泰纳,2021)。除了女性社区的私域交流之外,“她经济”的持续走高也推动了女性话题的高能见度与可见性,美妆性别话语由圈层内部的相互可见逐渐融为出圈破壁的社会公共讨论。“这两年微博热搜话题特别多,像是今天很火的BM风就引起全民对瘦的讨论,以小红书和INS为主鼓吹女性力量”。⑩美妆圈的女性公共议题正在脱离阈限的趣缘传播路径,向其他圈层和平台病毒式扩散,进而形成了卡斯特所谓“流动空间”的溢出效应。社会化媒介平台的数字实践推动意见领袖博主强势出圈,凭借“她力量”携带女性议题登上热搜,将被遮蔽的女性话题带入公共领域,争夺社会注意力,成为舆论“可见”的传播主体,进而为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领域的平等发声提供机遇。而女性在社会化媒介平台的自我书写和自主传播实践过程中,有可能孕育和发展主体性并成为潜在的政治行动者。这说明,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的女性自我书写与自主传播实践仍然有可能穿越数字媒介的中介化机制,携带积极的性别政治意涵。
巴特勒始终关注那些被排斥的生命如何实现社会文化的可见性问题,诚如其所问,“那些被规范的暴力所驱逐的生命,应该如何得到承认,以避免社会与文化意义的死亡呢?”(王玉珏,2015)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女性用户通过社会化媒介的“可供性”资源进行数字交流与话语实践,最终建立属于自己的性别权力话语体系。也诚如阿伦特所坚持的,“公共空间中所有参与者的出现是必要的,看见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他人,并使自己被他人看见正是公共生活的意义”(阿伦特,1999:44)。社会化媒介的“可供性”展现的“可见性”具备跨越地理、社会和心理层面的意义,能够让我们看到女性的不同生存境遇与生活状态,有助于推进女性的性别政治与身份认同。概言之,社会化媒介的“可见性”机制通过数字空间的圈层传播来定义、组织和给予,最终抵达社会文化层面的制度认可,进而实现性别正义。在变动不居的数字空间中,女性将自我展演、自我定义的碎片化主体反身性地融合于一个统一的状态,这是女性实现“可见性”的重要条件。在丰富的技术可供性与数字能动性背后,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体性更多自由灵动的游弋空间,这个空间赋予了女性更多“她力量”的崛起以及性别解放的潜能。诚然,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资源提供了女性“逆向再现”的能动条件,打破了媒介即社会文化延续脉络的常规“可见性”机制。女性(身体/情感/议题)唯有被“看见”,方能被展现并被言说,进而才有机会进入公共领域摆脱长期以来被主流媒介“符号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乃至主体无法言说的困窘姿态。■
注释:
①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3月15日,在广州大学城对在读研究生YZ的访谈记录整理。
②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3月18日,在线对金融公司文员WSY的访谈记录整理。
③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3月20日,在线对新媒体运营者YQ的访谈记录整理。
④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3月25日,在广州大学城对在读研究生YZ的访谈记录整理。
⑤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4月2日,在广州大学城对在读大学生ZYC的访谈记录整理。
⑥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4月15日,在线对医美行业从业者LZM的访谈记录整理。
⑦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4月18日,在广州大学城对在读研究生LL的访谈记录整理。
⑧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4月22日,在广州大学城对在读研究生LY的访谈记录整理。
⑨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5月25日,在线对留学生MLQ的访谈记录整理。
⑩资料来自于对2020年5月28日,在广州大学城对在读大学生CJ的访谈记录整理。
参考文献:
曹晋,徐婧,黄傲寒(2015)。新媒体、新修辞与转型中国的性别政治、阶级关系:以“绿茶婊”为例。《新闻大学》,(2),50-59。
丁未(2009)。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10),76-81。
丁未(2011)。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开放时代》,(1),124-145。
范斌(2004)。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12),73-78。
冯剑侠(2020)。#看见女性劳动者#:新冠疫情中的女性自媒体与话语行动主义。《新闻记者》,(10),32-44。
宫承波,齐立稳(2008)。试析网络社区中的角色扮演。《新闻界》,(2),164-166。
汉娜·阿伦特(1999)。《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郝大海,朱月婷(2016)。顺应与抗争:当代女大学生化妆意义研究。《青年研究》,(6),69-78。
何塞·范·迪克(2021)。《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涛(2015)。身体政治与性别权力解构——女大学生整形美容的身体社会学审视。《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1),75-77。
亨利·詹金斯(2016)。《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月琴(2015)。“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新闻记者》,(7),28-35。
黄月琴,黄宪成(2021)。“转发”行为的扩散与新媒体赋权——基于微博自闭症议题的社会网络分析。《新闻记者》,(5):36-47。
姜红,开薪悦(2017)。“可见性”赋权——舆论是如何“可见”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3):146-153。
琳达·斯泰纳(2021年3月10日)。学术|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的崛起。微信公众号“传媒文化评论”。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v28wsEMGNZsp9cMSTSailA。
刘海龙(2019)。中国传播学70年:知识、技术与学术网络。《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06-114。
刘鹏(2020)。“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国际新闻界》,(9),62-84。
陆晔,赖楚谣(2020)。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以抖音为个案。《国际新闻界》,(6),23-39。
闽南网(2019年6月10日)。B站一键三连是什么意思什么梗支持up主就来个一键三连。检索于http://www.mnw.cn/keji/internet/2167591.html。
潘忠党,刘于思(2017)。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1),2-19。
潘忠党,於红梅(2015)。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3),140-157。
孙玮(2020)。媒介化生存:文明转型与新型人类的诞生。《探索与争鸣》,(6),15-17。
孙玮,李梦颖(2014)。“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37-44。
王成兵(2004)。《当代认同危机的人类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金玲(2013)。《性别话语与社会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玉珏(2015)。重思可能性——朱迪斯·巴特勒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4-39。
王玉珏(2018)。《主体的生成和反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葆华(2020)。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新闻大学》,(3),84-106。
Brighenti, A. (2007). Visibility: A categor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urrent sociology55(3)323-342.
BrophyE. , CohenN. S. , & de Peuter, G. (2015). Practices of Autonomous Communicatio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315.
BucherT. (2012). Want to be on the top? Algorithmic power and the threat of invisibility on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14(7)1164-1180.
ChoiGrace Y. , and Elizabeth Behm-Morawitz. (2017). Giving a new makeover to STEAM: Establishing YouTube beauty gurus as digital literacy educators through messages and effects on viewe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 7380-91.
Dayan, D. (2013). 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 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7Feature137-153.
DillB. T. (1983). Race, classand gender: Prospects for an all-inclusive sisterhood. Feminist Studies9(1)131-150.
Dixon, T. L. , & Linz, D. (2000). Overrepresentation and under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Latinos as lawbreakers o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0(2)131-154.
Duffy, B. E. , & Hund, E. (2019). Gendered visibility on social media: Navigating Instagram’s authenticity bi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320.
FloresL. A. (2003). Constructing rhetorical borders: Peonsillegal aliens, and competing narratives of immigra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4)362-387.
FotopoulouA. (2016). Feminist activism and digital networks: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vulnerability. London, UK: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GibsonJ. J. (1979)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ooks, B. (1986). Sisterhood: Political solidarity between women. Feminist Review, 23(1)125-138.
Hutchby, I. (2014). 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 and participation frameworks in mediated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7286-89.
Rajaram, P. K. (2002). Humanitarianism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efugee.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15(3)247-264.
RogersE. M. & Singhal A. (2003).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7(1)67-85.
Thompson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J. B. (2005). The new visi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22(6)31-51.
XingG. (2012). Online activism and counter-public spheres: A case study of migrant labour resistance. Javnost-The Public, 19(2)63-82.
曾丽红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叶丹盈、李萍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发展研究”(编号:18BXW034)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