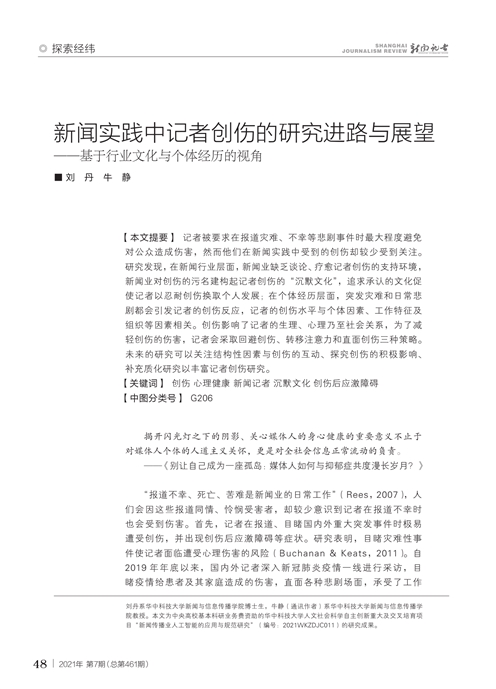新闻实践中记者创伤的研究进路与展望
——基于行业文化与个体经历的视角
■刘丹 牛静
【本文提要】记者被要求在报道灾难、不幸等悲剧事件时最大程度避免对公众造成伤害,然而他们在新闻实践中受到的创伤却较少受到关注。研究发现,在新闻行业层面,新闻业缺乏谈论、疗愈记者创伤的支持环境,新闻业对创伤的污名建构起记者创伤的“沉默文化”,追求承认的文化促使记者以忍耐创伤换取个人发展;在个体经历层面,突发灾难和日常悲剧都会引发记者的创伤反应,记者的创伤水平与个体因素、工作特征及组织等因素相关。创伤影响了记者的生理、心理乃至社会关系,为了减轻创伤的伤害,记者会采取回避创伤、转移注意力和直面创伤三种策略。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结构性因素与创伤的互动、探究创伤的积极影响、补充质化研究以丰富记者创伤研究。
【关键词】创伤 心理健康 新闻记者 沉默文化 创伤后应激障碍
【中图分类号】G206
揭开闪光灯之下的阴影、关心媒体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对媒体人个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是对全社会信息正常流动的负责。
——《别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媒体人如何与抑郁症共度漫长岁月?》
“报道不幸、死亡、苦难是新闻业的日常工作”(Rees, 2007),人们会因这些报道同情、怜悯受害者,却较少意识到记者在报道不幸时也会受到伤害。首先,记者在报道、目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时极易遭受创伤,并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研究表明,目睹灾难性事件使记者面临遭受心理伤害的风险(Buchanan & Keats, 2011)。自2019年年底以来,国内外记者深入新冠肺炎疫情一线进行采访,目睹疫情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的伤害,直面各种悲剧场面,承受了工作带来的心理创伤。研究者调查了大型知名新闻机构中参与疫情报道的73名记者(答复率为63%),发现约70%的记者有心理障碍,11%的记者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Selva & Feinstein, 2020)。记者在报道战争、灾难等悲剧事件后也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困扰(Feinstein & Nicolson, 2005; McMahon, 2001)。其次,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报道、目睹普通人遭遇地震、交通事故、暴力虐待时,也会受到创伤(路鹏程,卢家银,2014;Seely,2019)。另外,记者不仅会因目睹灾难现场遭受创伤,还会因在报道过程中感受到他人所承受的痛苦或悲伤而遭受创伤(Beam & Spratt, 2009)。这些发现表明,记者在新闻实践中受到心理创伤的情况属于常态。
虽然记者在工作中遭遇创伤的情况并不罕见,但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一方面与心理创伤本身的隐蔽性有关。心理创伤指向一些令人感到震惊或恐怖的事件,且这些事件威胁生命安全、或实际上已经涉及死亡,使人难以预防或制止由此造成的心理伤害(Reyes et al., 2008:ⅹ)。记者的心理创伤关乎个人的内心感受,天然地带有隐形的属性。与有形的、身体上的创伤相比,心理上的创伤更加不可见。另一方面,虽然记者在采访时会因移情作用感受到当事人的痛苦,但新闻机构缺乏与创伤报道有关的培训和资源(Seely, 2019),使得记者难以从工作机构获得专业的心理咨询。记者实际上处在一个缺乏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的职场环境。
一个良好的新闻业离不开健康的记者(Feinstein et al., 2014)。换言之,新闻行业与记者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新闻业的良性发展、新闻生产的顺利进行与记者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因此探讨记者创伤至少应从新闻行业和记者个体两个层面展开。具体来说,新闻行业对记者创伤持何种态度、赋予怎样的意义,这种意义如何影响记者?对记者个体而言,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创伤,创伤反应与哪些因素相关,他们又是如何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理解创伤、应对创伤?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首先从新闻业层面探讨职业规范和文化对记者创伤的意义塑造,剖析新闻行业对记者创伤的立场;其次从记者个体层面梳理记者遭遇创伤的经历、反应、影响因素、结果与应对策略;最后本文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尝试提出记者创伤研究的未来研究方向。
一、被行业静音的创伤:“沉默文化”与“承认文化”的合力之果
记者在工作中遭受创伤没有受到重视,并不是新闻机构对记者创伤不知情,而是记者创伤被新闻业的规范与文化重塑了意义,这在客观上压制了关于记者创伤的讨论。新闻业存在着对记者创伤保持沉默的文化和激励记者争取承认的文化,这些行业文化构建起记者创伤在新闻职业中的意义,成为记者一边忍耐创伤、一边投身新闻报道活动的规训力量。
(一)“沉默文化”:新闻业对记者创伤的污名和压制
“沉默文化”指的是新闻行业中存在对记者创伤保持沉默的现象。“沉默文化”的形成首先与新闻行业缺乏公开言说创伤、应对记者创伤的制度环境有关。和具备专业、成熟的创伤培训体系的医疗、消防、警察行业相比,新闻业针对记者创伤的应对培训是缺乏的。新闻编辑室缺乏对记者报道创伤性事件的培训(Seely, 2019),客观上导致了公开讨论记者创伤的话语空间和制度文化的缺失,反映出记者创伤在新闻行业中处于一种无声状态,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记者在前往现场报道时往往没有心理准备。Beam和Spratt(2009)对400位美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约20%的记者对与暴力或创伤事件的受害者打交道感到“准备充分”,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记者认为自己“准备不足”或“根本没有准备”。李双龙、於红梅(2009)调查了249名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现场报道的记者,只有6.4%的受访者表示单位组织过心理调适训练,有30.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赶赴灾区之前毫无心理准备。
新闻业创伤应对培训的缺乏初步构建起言说记者创伤的静音环境,而新闻业文化中对记者创伤反应的偏见和污名,以及受此影响的记者则进一步强化了“沉默文化”。新闻业文化将记者采访创伤性事件而出现的情绪困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视为记者不够专业、软弱的表现(Feinstein et al., 2002;Keats & Buchanan, 2013)。由此,创伤反应被新闻业文化重塑为记者缺乏个人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负面意义。而这一意义也改变了记者对创伤反应的认知。正如Hassim和Wagner(2013)所言,“文化的影响塑造了人们认为正常或异常以及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东西”。记者受到创伤反应被污名的新闻业文化的影响,难以正常看待自己的创伤反应,甚至会将新闻业对创伤反应的污名内化。有记者认为,记者报道悲剧产生不良反应的迹象会被同行和编辑视为其无法应付与工作相关问题的弱点(Berrington & Jemphrey, 2003)。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记者更倾向于隐藏、压制创伤,而不愿讨论创伤。如在一项对加拿大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创伤研究中,有记者认为哭泣是软弱的标志,必须控制眼泪;有些记者不愿意将自己报道创伤性事件的经历告诉管理者、同事,在一些情况下也不愿意告诉家人和朋友(Keats & Buchanan, 2013)。于是认同出现创伤反应是个人软弱标志的记者,他们自身也成为强化新闻业“沉默文化”的一股力量。
新闻业对记者创伤保持沉默,显然没有尽到减轻新闻工作对记者造成的伤害、为记者提供持续支持的关怀义务(Duty of Care)(Dubberley et al., 2015)。相反,新闻业通过强调新闻职业的专业化要求,构建创伤反应的负面意义,使记者潜移默化地受到“沉默文化”的影响,结果是促成记者学会压制自己的创伤反应、忽略他们所经历的创伤带来的影响,甚至阻碍他们寻求专业的帮助。许多战地记者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和酗酒没有受到治疗,在研究者看来,这种现象表明在一些新闻机构的领导和记者中存在沉默文化(Feinstein et al., 2002)。
(二)以创伤交换事业:“承认文化”对记者创伤的调节
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遭遇创伤,还能够继续投身新闻报道,除了受到“沉默文化”的规训外,还在于新闻业形成了记者凭借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努力获得新闻业同行、公众承认的“承认文化”,这种文化调节了记者对创伤的感受。“承认文化”调节记者创伤主要通过外部承认转化为内在激励,以及外部承认驱动这两种机制来实现。
外部承认转化为内在激励的调节机制,是指报道创伤性事件使媒体、记者获得外界的承认,这一外部承认又给记者带来与自身工作有关的内在激励。外部承认代表外界对新闻机构和记者的认可和职业地位的尊重,表明新闻机构收获了良好的名声和公众的关注。新闻机构维系公众承认的有效途径是持续发布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因此记者需要继续投身到创伤性事件的报道中。换言之,新闻机构为获得、维系外部承认,倾向于给记者分配报道创伤性事件的任务。在绩效考核制度之下,记者完成更多的报道任务有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最终,新闻机构的外部承认与作为记者内在激励的个人发展形成了紧密联系,促使记者主动投身到创伤性事件的报道中。例如,一些记者拥有发展事业的野心,相信通过报道战争可以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从而促进职业发展(Feinstein et al., 200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记者愿意接受报道战争、冲突的任务指派,而不愿透露自己的恐惧和不安,选择默默承受报道战争带来的痛苦。许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的战地记者没有接受相应的治疗(Feinstein et al., 2002)。在外部承认转化为内在激励的调节机制中,职业发展作为一种内在激励吸引着记者从事创伤性事件的报道,同时职业发展也作为一种补偿调节了记者遭受创伤的应对行为。
外部承认的另一种形式——荣誉,也通过带来记者职业地位提升这一内部激励,使记者的注意力从个人创伤转移到追求外部承认上,从而起到调节记者创伤的作用。赢得新闻行业的奖励、荣誉是记者获得承认的标志之一,而在获得奖励和荣誉的新闻作品中,不乏关于战争、冲突等暴力事件的报道(Keats & Buchanan, 2013),这使记者认识到报道战争或冲突等创伤性事件可以获得荣誉。有研究者发现,摄影记者在国际报道中拍摄人类苦难、冲突和恐怖主义,这类描绘暴力行为的照片在年度国际图片奖和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照片中占65%以上(Greenwood & Smith, 2007)。这表明报道冲突、承受创伤增加了记者获得行业承认的可能性。记者在获得外部承认的情况下,职业能力受到认可,这又会给记者带来职业发展的内部激励。例如,摄影记者通过报道国际战争、冲突等创伤性事件获得奖项,这些奖项对提升他们的职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增加在海外工作的机会,他们也渴望实现在海外工作的目标(Keats & Buchanan, 2013)。简言之,报道创伤性事件给记者带来荣誉,荣誉又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这种转化使记者降低了对个人创伤的关注度,转而追求更高的职业目标。
外部承认驱动的调节机制,指的是记者为了获得外界的承认而容忍创伤,进行创伤性事件的报道。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是记者为获得公众的承认,愿意冒着遭受创伤的风险报道战争、冲突事件。记者之间存在着争取公众承认的“竞争”,这种争取公众承认的意识体现在他们关心不同类型的记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排序,也反映在他们勇于进入危险的环境中采集新闻信息。例如,在记者看来,驻外记者往往被公众视为“名人”,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本地记者,作为驻外记者得到承认是决定记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Keats & Buchanan, 2013)。虽然驻外记者报道战争、冲突意味着遭遇创伤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更高,但他们的工作更受公众好评。认识到这一点的记者为获得公众的承认,他们甘愿冒险进行采访或拍摄,(Keats & Buchanan, 2013)。在外部承认驱动的调节机制中,获取公众承认既是记者报道创伤性事件的一个动力,也是记者承受创伤后希冀实现的目标。通过这样一种调节机制,凸显出创伤的交换价值,促成了记者对承认的追求和对创伤的忍耐。
新闻业的“沉默文化”和“承认文化”一同定义了什么报道是被肯定的、什么样的记者是被赞扬的、什么样的新闻事业是成功的,无形中为记者树立了职业发展道路上有待实现的目标。记者一方面受到“沉默文化”的规训,压制自己的创伤反应,另一方面受到“承认文化”的鼓动,投身到创伤性事件报道中,以承受创伤换取外部承认和职业发展。在两种文化的合力之下,创伤成为新闻行业和记者内心的隐秘角落。
二、难以回避的个体经历:记者创伤的症状与影响因素
新闻业的“沉默文化”和“承认文化”促使有关记者创伤的表达被静音,但并不意味着记者因工作遭受创伤的经历可以被消除。对记者个体而言,遭受创伤仍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那么,什么样的报道经历会给记者带来创伤,记者会出现怎样的创伤反应,这些反应又与哪些因素有关?从个体层面探讨记者创伤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
(一)从罕见灾难到日常悲剧:多元场景下的记者创伤反应
记者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报道一些重大灾难性新闻,如战争、地震、海啸等。这些事故往往会造成较多的人员伤亡,现场的场面对记者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记者在报道这些罕见灾难后会出现何种反应和症状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简称PTSD)的症状。战地记者、报道重大自然灾害的记者更容易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出现应激的生理反应。Feinstein等(2002)对多次报道过战争的140多名战地记者和107名从未报道过战争的记者进行调查,发现战地记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得分显著,高于从未报道过战争的记者。报道地震的记者中也会有人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出现地震现场的创伤经历反复且不受控制地浮现在记者的记忆和睡梦中,高度紧张、心跳加快、呼吸困难、恐惧、焦虑、失眠、痛苦等反应(路鹏程,卢家银,2014;李双龙,於红梅,2009)。
遭受创伤的记者除了会出现生理上的应激症状之外,还会保留视觉、嗅觉等感觉上的记忆,并因这些记忆被唤醒而感到痛苦。如记者在主动回忆报道海啸的经历时会想起当地被海啸破坏的场景、感到震惊或极度痛苦的受害者、尸体、受到创伤的儿童,记者还会想起闻到的强烈的腐烂气味(Weidman et al., 2008)。当记者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与创伤性事件现场相似的元素时,他们的创伤记忆也会被激活,并对个人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有摄影记者因看到金枪鱼寿司的颜色而联想起尸体皮肤的颜色,导致不能食用该食物(Keats & Buchanan, 2013)。这些研究发现反映了记者创伤反应的隐蔽性。
多数记者创伤研究关注国际上的战地记者和报道重大灾难新闻的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地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没有遭遇创伤。实际上,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国内、本地记者这一群体在日常新闻工作中遇到的创伤性事件和反应。有研究发现,令记者感到痛苦的创伤事件包括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绑架、凶杀、自杀、与工作有关的事件、交通事故、法院逮捕、家庭问题、儿童伤亡和疾病等,报道这类事件的记者也会出现做噩梦、烦躁、焦虑等反应(Keats & Buchanan, 2013)。Pyevich等(2003)对美国的报纸记者调查发现,记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过多地暴露于创伤事件(如火灾、性侵犯等)有关。记者间接接触创伤事件同样会受到创伤。如记者目睹社交媒体用户拍摄的未经打码的暴力、血腥等视觉内容而产生心理不适(Feinstein et al., 2014)。这些研究发现反映出记者在日常工作的场景中遭遇的创伤并不少。
(二)记者出现创伤症状的影响因素:个体因素、工作特征与组织环境
如果说调查、描述记者的创伤反应是在进行事实层面的确认,那么寻找与记者创伤症状相关的因素则是在摸索记者出现创伤症状的规律。个体因素、工作特征、组织和社会环境对记者创伤症状的影响得到研究的证实。
个体因素中,记者的性别、婚恋状况、受教育程度、创伤经历、从业时间与罹患创伤症状有关。研究发现女性记者更容易因报道创伤事件而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路鹏程,卢家银,2014),单身记者报道创伤事件时有更高程度的抑郁(McMahon, 2001)。记者的受教育程度负向预测PTSD的入侵、回避症状,即受教育程度越低,记者的创伤症状越严重(Feinstein, 2013)。先前有过创伤经历的记者也更容易在报道创伤事件时出现创伤反应(Breslau et al., 1999)。记者从业时间与罹患PTSD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方面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越长,罹患心理创伤症状的可能性越高(Simpson & Boggs, 1999),但另一方面,较长的从业时间会给记者带来更多的应对创伤的经验。年长而富有经验的记者应对灾区危险环境和调适心理平衡的能力更强,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年轻、缺乏经验的记者(Sin et al., 2005)。
工作特征方面,记者接触创伤事件的频率、方式,创伤事件本身的危险程度与出现创伤症状有关。记者报道创伤事件的频率越高、强度越大,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越严重(Newman et al., 2003; Seely, 2019)。在报道战争这类极度危险的事件时,记者也会承受更为严重的心理痛苦(Feinstein & Nicolson, 2005)。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浏览社交媒体用户上传的内容成为记者寻找新闻线索的新途径,这使得记者接触创伤性事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同于亲临灾难现场而受到创伤,记者还会因观看社交媒体用户上传的、未经打码的暴力图像而受到创伤。记者反复接触创伤性图像可能会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焦虑和沮丧;接触暴力图像的频率而不是持续时间会令使用用户生成内容的记者在情感上更加痛苦(Feinstein et al., 2014)。
此外,记者工作的地理位置特征也与创伤症状有关。一则,记者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工作,遭受创伤的程度不同,距离新闻现场越近的记者越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创伤症状。在新闻现场工作的记者、摄像师,他们的PTSD症状得分显著高于不在现场工作的新闻从业者(如播音员)(Hatanaka et al., 2010),反映出在不同地点工作的新闻从业者的创伤程度有显著差异。二则,记者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工作,遭受创伤的类型不同。这一差异在前往战区报道战争的记者和在本地生活、报道本地冲突的记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Feinstein(2013)比较了在墨西哥本地生活、报道当地贩毒集团的记者和报道战地新闻的记者,发现只有本地记者的家人受到贩毒集团的威胁,报道战地新闻的记者的家人没有遭到这样的威胁,且家庭成员受到威胁是本地记者罹患PTSD和抑郁症的预测因素。在本地生活、工作的记者在报道创伤性事件时,认识创伤事件当事人的可能性增加,这也有可能给记者带来不同的创伤反应。有研究发现22.4%的记者(N=851)在工作中至少遇到一次认识受害者或犯罪者的情况(Pyevich et al., 2003)。如果记者认识新闻报道中涉及的对象,他们的创伤体验和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MacDonald et al., 2017)。
组织与社会支持方面,记者在职场的负面经历与出现创伤症状有关。记者在职场遭遇欺凌与出现心理、身体健康问题和创伤后应激症状呈正相关(Nielsen & Einarsen, 2012)。关于组织和社会支持对记者创伤症状的影响,已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记者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影响,如在报道海啸的记者中,那些认为上级和同事对自己认可程度低的记者有更多的创伤后症状(Weidman et al., 2008);社会支持的减少增加了摄影记者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Newman et al., 2003)。而有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记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没有显著影响(Hatanaka et al., 2010)。
三、创伤之果:记者遭遇创伤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当记者在工作中不断遭遇创伤而新闻行业对此保持沉默时,创伤就成为记者个人去承担、消化和应对的“职业之痛”。创伤对记者个人的心理、生理、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影响,也对新闻生产有所影响。为了减轻目睹、报道灾难等创伤性事件带来的影响,记者主要采取回避创伤、转移注意力和直面创伤三种应对策略。
(一)心理、生理、社会与新闻生产:创伤对记者的多重影响
Keats和Buchanan(2013)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目睹创伤对记者的心理、情感、认知、身体、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具体来说,心理影响包括记者会出现创伤事件的图像不受控制地在脑海里闪回、做噩梦、焦虑等侵入症状;设法避免碰触创伤记忆的回避症状;以及对危险过度警觉的唤醒症状。情感影响包括记者变得易怒、焦虑和抑郁,情绪更加敏感。认知影响包括记者会控制情绪、反思创伤事件及职业行为等。身体影响包括记者出现昏厥、高血压、心脏病、轻度中风、颈部受损等问题。家庭关系影响包括记者为避免家人担心而对创伤经历闭口不谈,反而导致与家人关系的疏远。除此之外,记者遭受创伤后,对其融入社会和社会交往也有影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地记者谈到,他们从战场回来无法适应文明社会的生活、不愿与朋友交往(Feinstein et al., 2002)。
记者因新闻实践遭受创伤,创伤反过来也影响了新闻生产。鉴于新闻编辑室很少教授记者如何报道创伤性事件,记者一方面会遵循专业、客观的新闻规范,在事实面前保持中立,和信源保持身体上和情感上的距离;另一方面记者会通过在工作中观察其他记者来学习报道的规则,程式化地报道创伤性事件(Barnes, 2016)。
(二)回避、转移与直面:记者应对创伤的三种策略
为了减轻目睹、报道创伤性事件带来的伤害,记者较常采取的策略是回避创伤。记者回避创伤的第一类方式是回避先前的报道经历所带来的创伤,如避免与他人讨论创伤,不向别人敞开心扉;避免想起受到创伤的场景,以免唤醒创伤记忆再次受到创伤;采取物质滥用(substance misuse)的应对手段来麻痹自己;逃避情绪困扰,如吸烟、酗酒、吸食大麻等(Buchanan & Keats, 2011)。记者回避创伤的第二类方式是回避未来可能使其遭遇创伤的报道任务或行为,如拒绝报道创伤性事件的任务指派,向主管谎称自己不能承担某个报道任务;不去看报纸上关于车祸或其他创伤性事件的报道,避免情绪失控(Buchanan & Keats, 2011)。记者通过采取回避策略,避免唤起创伤记忆和痛苦情绪,以此规避二次受创的风险,将自己和创伤隔绝。
转移策略主要指的是记者通过从事其他活动,分散自己对创伤的注意力。比如记者会通过跑步、健身、攀岩等体育锻炼避免思考创伤,或者通过听音乐、自驾旅行暂时切断与工作的联系,缓解压力;或者提醒自己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更高的职业目标,将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思考如何报道创伤性事件而不是聚焦于自己的创伤,以此控制自己;或者报道不涉及死亡等创伤性事件的、轻松一些的新闻;还有记者使用黑色幽默来摆脱创伤性事件带来的恐惧,避免自己过于关注创伤性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Buchanan & Keats, 2011; Seely, 2019)。
直面创伤即是记者不回避、不否认创伤反应的存在,通过向内、向外两种方式缓解创伤。记者直面创伤的一类方式是通过写日记、哭泣、或写作来发泄内心的痛苦(Seely, 2019)。另一类方式是向外寻求社会支持,包括向他人倾诉、寻求家庭成员和新闻机构外的朋友的支持,但记者向新闻机构寻求创伤相关问题的帮助不那么积极(李双龙,於红梅,2009;Greenberg et al., 2009)。面对报道灾难事件带来的情感伤害,一些记者更愿意向专业人员咨询而不是新闻机构,他们担心自己向新闻机构咨询创伤问题会被贴上标签,将来可能不会被安排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Muller, 2010)。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机构的社会支持没有效果。有研究发现媒体组织提供的社会化支持能降低报道地震的记者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还能激发记者进行新闻活动的积极因素(路鹏程,卢家银,2014)。
四、讨论与展望
新闻活动的可持续性有赖于记者良好的健康状况,然而记者向公众报道战争、冲突、危机等新闻实践常常给自己带来情感风险和创伤体验(Kotisová, 2017),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承受心理创伤。研究记者创伤的意义,不仅仅是关怀记者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告别孤独的自愈者的角色,而且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正视以往较少关注的新闻职业活动对记者的心理、情感影响这一话题。系统、深入地研究记者创伤,不应止步于从心理学视角关注记者创伤的症状和影响因素,还要审视新闻业乃至社会中的各方力量关于记者创伤的塑造与话语,反思创伤在更深层次上给记者和新闻业带来的改变,弥补心理学取向的创伤研究对情境、文化、结构等要素关注的不足。这无不表明持续研究记者创伤是必要的,而要回答上述问题,有赖于未来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推进。
(一)探究其他结构性因素与记者创伤的互动
如前文所述,有研究者开始关注新闻业文化对记者创伤的影响,探究文化这一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记者关于创伤的态度和行为,并提出了“沉默文化”的概念。然而,文化是复杂且多元的,新闻行业中由性别、职级等带来的刻板印象,以及新闻职业共享的准则、价值观等文化与创伤的关系值得探索;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对记者解读创伤、应对创伤起何种作用,中国新闻行业中的特色文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此之外,探究记者创伤还应考虑记者和新闻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场域,考察这些结构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与记者创伤之间的互动。由此,记者创伤研究得以超越研究创伤本身,挖掘职业、政治、经济、社会等背后的力量对创伤赋予的意义、这些意义如何对记者产生影响,以及经历创伤后的记者如何参与新闻生产,又如何重新构建起对创伤、自我和新闻职业的理解。
(二)关注记者创伤的建设性力量
以往对记者创伤的研究遵循了传统心理学研究心理疾病的范式,通过发现导致创伤的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干预,以减轻创伤的影响。这种将创伤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消极认知模式忽略了创伤作为一种潜在的建设性力量对记者乃至新闻业的积极作用。20世纪末以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自身的积极力量受到关注(任俊,2012:3)。在此背景下,“创伤后成长”在近年来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这为记者创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创伤后成长”关注经历创伤的幸存者发生的积极改变(Tedeschi & Calhoun, 2004)。研究者发现不同职业群体如口译员、救灾人员等都经历了创伤后成长(Splevins et al., 2010;Linley & Joseph, 2006)。如心理治疗师和创伤幸存者一起工作,在同情、洞察力、宽容、同理心、敏感度方面有所改变(Arnold et al., 2005)。Tedeschi和Calhoun(1995:30-41)总结了个人在经历创伤后发生积极改变的三个领域:其一,自我认知的改变,如成功应对创伤带来的困境使人更自信、更独立,感受到自我的价值和成长,但极端的创伤也会让人意识到自己是脆弱的;其二,与他人关系的改变,如经历丧亲之痛会更懂得改善与家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加深与他人的关系;其三,生活哲学的变化,如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对未来规划的改变,学会欣赏生活。这些发现传递出一个信息——个人在苦难中也会有收获(Joseph & Linley, 2005)。
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以丰富记者创伤的探讨角度,不再一味将创伤视为“苦难”,把记者定位为被动承受创伤、寻求疗愈的个体,而是去发现记者自身应对创伤的积极力量和品质,挖掘创伤给记者的自我认知、新闻生产、人际关系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变化,关注记者经历创伤之后的成长。当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记者创伤,并不是否定传统心理学范式下记者创伤研究的成果,而是从另一个面向重新认识创伤。
(三)突破以临床标准测量、问卷调查主导的路径依赖
在记者创伤的研究中,研究者测量记者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的工具主要是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如是否经历、亲眼目睹创伤事件,反复出现与创伤事件相关的梦境,努力回避与创伤性事件有关的痛苦记忆等(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271-272)。这样以医学诊断的标准测量记者创伤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直接采用美国精神病协会的诊断标准忽视了症状表现的文化差异。最新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提到:“PTSD症状或症状群的临床表现可能因文化而异,特别是在回避和麻木症状、痛苦的梦境和躯体症状(如头晕、气短、热感)方面”(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278)。在不同文化中,记者经历的创伤事件类型、对创伤严重程度的认知与容忍等都有所不同,因此对创伤症状的测量应兼顾文化差异。
其次,以临床诊断标准测量记者创伤,忽视了那些出现相关症状但没有达到诊断标准的记者。对创伤的界定关乎什么样的个体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如果将创伤视为疾病,那么只有达到诊断标准的个体才会被关注。但创伤暴露并不一定导致PTSD(Shah et al., 2020)。在现实中,有不少记者同样在接触社会的善恶,报道悲剧、暴力等事件,虽然症状没有达到所谓的疾病标准,但我们很难否认他们没有被笼罩在焦虑、抑郁的情绪之中。对这样的群体而言,创伤不再是“没有身体疾病或身体虚弱”的狭义的身体健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上不舒适的体验。如果将创伤视为“舒适或秩序被剥夺”(dis-ease或dis-order)的体验(彼得·莱文,2017:29),那么频繁暴露在与工作有关的创伤性事件中,且出现了心理不适的体验,但症状没有严重到可以归为精神障碍的这类记者群体就得以进入研究者的视线(Pyevich et al., 2003)。未来的研究应突破过于依赖临床诊断标准的思维,关注那些在日常工作中同样遭受创伤、创伤反应未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记者群体。
最后,记者创伤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在呈现记者创伤的个体差异、变化等方面存在不足。研究者在进行问卷调查时,记者可能不会如实填写问卷;问卷调查能收集记者在某一时间节点及之前遭遇创伤的经历,属于对“过去时”的调查,被调查对象难免会遗忘创伤经历中的细节,从而影响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运用田野调查、访谈等方法,观察、记录记者在报道灾难、悲剧等事件过程中的实时反应和行为,并追踪记者在创伤认知、创伤反应方面的纵向变化,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呈现研究对象的内部差异性和记者创伤的动态变化。■
参考文献:
彼得·莱文(2017)。《心理创伤疗愈之道:倾听你身体的信号》(庄晓丹,常邵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双龙,於红梅(2009)。新闻记者在特大地震灾害中的心理调适及其效果研究。《新闻大学》,(2),79-82+124。
路鹏程,卢家银(2014)。地震灾区记者的心理创伤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6),36-39+62。
全媒派(2020)。别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媒体人如何与抑郁症共度漫长岁月?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200219/20200219A04LHB00.html。
任俊(2012)。《积极心理学》。北京:开明出版社。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ArlingtonV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rnoldD.CalhounL.G.Tedeschi, R.& Cann, A. (2005). 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5(2)239-263.
BarnesL. (2016). Journalism and Everyday Trauma: A Grounded Theory of the Impact from Death-knocks and Court Reporting.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amR. A. & Spratt, M. (2009). Managing Vulnerability: Job satisfaction, morale and journalists’ reactions to violence and trauma. Journalism Practice, 3(4)421-438.
BerringtonE. & Jemphrey, A. (2003). Pressures on the press: Reflections on reporting tragedy. Journalism, 4(2)225-248.
Breslau, N.Chilcoat, H. D.KesslerR. C.& DavisG. C. (1999). Previous Exposure to Trauma and PTSD Effects of Subsequent Trauma: Results from the Detroit Area Survey of Traum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6(6)902-907.
BuchananM. & KeatsP. (2011). Coping with traumatic stress in journalism: A critical ethnographic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2127-135.
Dubberley, S.GriffinE.& BalH. B. (2015). Making Secondary Trauma A Primary Issue: A Study of Eyewitness Media and Vicarious Trauma on the Digital Frontline. Retrieved from http: //eyewitnessmediahub. com/research/vicarious-trauma.
Feinstein, A.AudetB.& WaknineE. (2014). Witnessing images of extreme violence: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the newsroom.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Open, 5(8)1-7.
Feinstein, A. (2013). Mexican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ts Covering War: A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Aggression, Conflict and Peace Research, 5(2)77-85.
Feinstein, A. & Nicolson, D. (2005). Embedded Journalists in the Iraq War: Are they at greater psychological risk?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8(2)129-132.
Feinstein, A.Owen, J.& BlairN. (2002). A hazardous profession: Warjournalistsand psychopat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9(9)1570-1575.
Greenberg, N.GouldM.Langston, V.& Brayne, M. (2009). Journalists’ and media professionals’ attitudes to PTSD and help-seeking: A descriptive study.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18(6)543-548.
Greenwood, K. & SmithC. Z. (2007). How the world looks to us: International news in award-winning photographs from the Picture of the Year, 1943-2003. Journalism Practice, 1(1)82-101.
HassimJ. & Wagner. C. (2013).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psychopatholog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1)4-10.
HatanakaM.Matsui, Y.Ando, K.InoueK.& ItamuraH. (2010). Traumatic stress in Japanese broadcast journalist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3(1)173-177.
JosephS. & Linley, P. A. (2005). Positive adjustment to threatening events: an organismic valuing theory of growth through adversit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3)262-280.
Keats, P. A. & Buchanan, M. J. (2009). Addressing the effects of assignment stress injury: Canadian journalists’ and photojournalists’ recommendations. Journalism Practice, 3(2)162-177.
Keats, P. A. & Buchanan, M. J. (2013). Covering Trauma in Canadian Journalism: Exploring the Challenges. Traumatology, 19(3)210-222.
KotisováJ. (2017). Cynicism ex machina: The emotionality of reporting the ‘refugee crisis’ and Paris terrorist attacks in Czech Televis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2(3)242-256.
LinleyP. A. & Joseph, S. (2006).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disaster work: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Loss & Trauma, 11(3)229-245.
MacDonald, J. B.HodginsG.& Saliba, A. J. (2017). Trauma Exposure in Journalist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 //www. fusion-journal. com/issue/011-dangerous-journalism/trauma-exposure-in-journalists-a-systematic-literature-review/.
McMahon, C. (2001). Covering disaster: a pilot study into secondary trauma for print media journalists reporting on disast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16(2)52-56.
MullerD. (2010). Ethics and trauma: lessons from media coverage of Black Saturday. Australian Journal of Rural Health, 18(1)5-10.
NewmanE.SimpsonR.& HandschuhD. (2003). Trauma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Photojournalists.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0(1)4-13.
Nielsen, M. B. & Einarsen, S. (2012). Outcomes of exposure to workplace bully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Work & Stress, 26(4)309-332.
Pyevich, C. M.Newman, E.& Daleiden, E. (2003).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gnitive SchemasJob-Related Traumatic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Journalist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4)325-328.
ReesG. (2007). Weathering the trauma storms.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18(2)65-70.
Reyes, G.ElhaiJ. D. & Ford, J. D. (2008). The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Seely, N. (2019). Journalists and mental health: The psychological toll of covering everyday trauma.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40(2)239-259.
Selva, M. & FeinsteinA. (2020). COVID-19 is hurting journalists’ mental health. News outlets should help them now. Retrieved from https: //reutersinstitute. politics. ox. ac. uk/risj-review/covid-19-hurting-journalists-mental-health-news-outlets-should-help-them-now.
ShahS.Jaan, F.Ginossar, T.McGrailJ. P.& UllahR. (2020). Trauma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regional journalists in Pakistan. Journalism. DOI: 10. 1177/1464884920965783.
Simpson, R. & BoggsJ. (1999).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raumatic stress among newspaper journalist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1)1-26.
Sin, S.Huak, C.& Chan, A. (2005). A Pilot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Tsunami on a Group of Asian Media Work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ency Mental Health, 7(4)299-306.
SplevinsK. A.CohenK.Joseph, S.Murray, C.& Bowley, J. (2010). 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interpreter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12)1705-1716.
TedeschiR. G. & CalhounL. G. (2004).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15(1)1-18.
TedeschiR. G. & CalhounL. G. (1995).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Weidman, A.Fehm, L.& FydrichT. (2008). Covering the Tsunami Disaster: Subsequent post-traumatic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social factors. Stress and Health, 24(2)129-135.
刘丹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牛静(通讯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的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创新重大及交叉培育项目“新闻传播业人工智能的应用与规范研究”(编号:2021WKZDJC01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