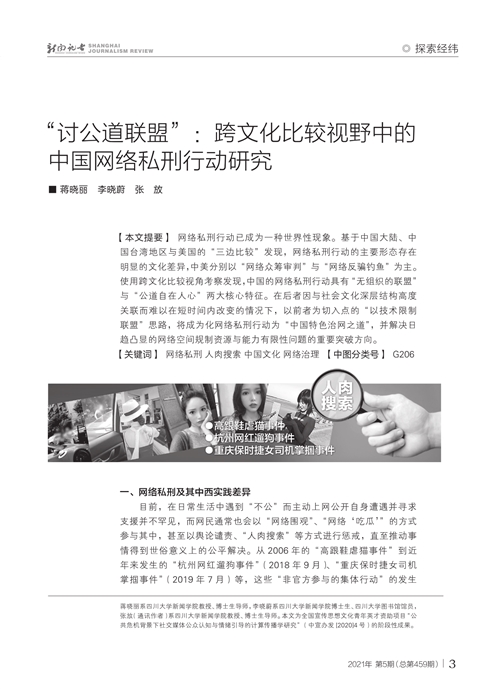“讨公道联盟”:跨文化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网络私刑行动研究
■蒋晓丽 李晓蔚 张放
【本文提要】网络私刑行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基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的“三边比较”发现,网络私刑行动的主要形态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中美分别以“网络众筹审判”与“网络反骗钓鱼”为主。使用跨文化比较视角考察发现,中国的网络私刑行动具有“无组织的联盟”与“公道自在人心”两大核心特征。在后者因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高度关联而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情况下,以前者为切入点的“以技术限制联盟”思路,将成为化网络私刑行动为“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并解决日趋凸显的网络空间规制资源与能力有限性问题的重要突破方向。
【关键词】网络私刑 人肉搜索 中国文化 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网络私刑及其中西实践差异
目前,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公”而主动上网公开自身遭遇并寻求支援并不罕见,而网民通常也会以“网络围观”、“网络‘吃瓜’”的方式参与其中,甚至以舆论谴责、“人肉搜索”等方式进行惩戒,直至推动事情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公平解决。从2006年的“高跟鞋虐猫事件”到近年来发生的“杭州网红遛狗事件”(2018年9月)、“重庆保时捷女司机掌掴事件”(2019年7月)等,这些“非官方参与的集体行动”的发生越来越频繁,甚至出现了“上访不如上网”等高度经验性总结的俗语,人们越来越习惯利用网络舆论、网络技术等数字手段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和管理。这种行动在国外研究中被称为“网络私刑(digital vigilantism/online vigilantism/cyber vigilantism/Internet vigilantism)”,并界定为“网民未经国家授权以数字方式促进执法的行动”(Neubaumet al.,2018)。认为其虽然符合传统私刑的六要素(Smallridge, Wagner & Crowl, 2016)且同样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负面后果(Kossef, 2016),但却不仅仅是传统私刑的简单“数字化”,而是出现了质变(Reichl, 2019)。然而,尽管在我国长久以来已有大量相关案例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Cheong & Gong, 2010),但其更多地只在新闻报道(例如:腾讯网,2012;搜狐新闻,2018;共产党员网,2018)或网络评论中被提及,学界则常常将其与“网络暴力”、“网络舆论监督”等相混淆,并未将其作为正式概念纳入学术研究,更遑论对其整体机制展开深入讨论。
笔者认为,网络私刑之“私”的内涵应为“官与私”之“私”而非“公与私”之私,即网络私刑行动是非官方的,是与自上而下的刑罚相对应的民间惩罚。因此网络私刑是指网民在互联网上面对社会越轨行为或潜在的社会偏差行为时,自发地通过非官方手段对越轨者进行阻止或惩罚,以达到维护网络社区规范、重申社会伦理、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行动。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暴力”、“网络欺凌”是“网络私刑”的常见手段和表现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私刑都一定带有羞辱谩骂、人身攻击等暴力倾向,还可以是相对温和和仪式性的,因此才会有“只转不评”、“笑而不语”、“我只吃瓜不说话”、“围观打卡”等这类并不具有实际施暴倾向但可以起到惩罚效果的私刑行动。而网络私刑与网络舆论监督的区分可以从惩罚对象的性质上加以考量:对于行政主体或公权身份的监督属于“舆论监督”范畴;对于个人行为的惩罚属于“网络私刑”范畴。
尽管存在争议,网络私刑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常态”。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西方网络私刑在形态上似乎存在明显差异。有学者根据惩罚手段的不同将网络私刑行动分为反骗“钓鱼”(scam baiting)、众筹审判(crowdsourcing for justice/crowdsourced justice)和黑客行动(hactivism)三种主要类型(Zingerle, 2015;Smallridge,Wagner & Crowl, 2016)。西方对本土网络私刑行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反骗“钓鱼”,即假装成容易上当的受害者骗取骗子的信任,然后一步步收集其身份证件、银行账户、电话号码等信息并公开曝光,甚至实施进一步的惩罚(如举报、戏弄甚至示众羞辱等)(Zingerle, 2015)。其主要类型除了最为常见的反网络经济诈骗钓鱼,还有反网恋诈骗钓鱼(Sorell, 2019;Sorell & Whitty, 2019)、反网络儿童色情钓鱼(Sorell, 2019)等。西方学者认为它“以一种小型而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了私刑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反抗网络犯罪的类型”(Tuovinen & Roning,2007)。而众筹审判的典型形态之一即通常所说的“人肉搜索”(e.g., Chang & Leung, 2015;Chang & Poon, 2017; Chia, 2018),是指“在线参与者通过集体搜索的过程获取有关越轨个人的人口和地理信息,通常是为了揭露、羞辱和惩罚他们,以恢复法律正义或公共道德”(Cheong & Gong, 2010)。张耀中(Lennon Yao-Chung Chang)等在《大中华区网络众包(人肉搜索)简介》中引用的一份2010年报告就指出,人肉搜索在中国普遍流行:在2001年至2007年记录的35起人肉搜索的案件中,有31起发生在中国;2010年1月至5月记录的87起网络私刑事件中,85起发生在中国(Chang & Leung, 2015)。斯莫尔里奇等(Smallridge, Wagner & Crowl, 2016)在总结了被媒体称为网络私刑行动的大量案例后,认为“人肉搜索”就是中国网民的“众筹审判行为”(crowdsourced acts of vigilantism)。除了学界的关注,西方媒体报道也将“人肉搜索”视为中国特有的网络私刑行动类型,例如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人肉搜索’对于这个数字化时代而言,就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李建,若英,2013);美国《纽约时报》、《福布斯》杂志和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则专门为中国的“人肉搜索”现象创造了一个短语“Chinese style Internet man hunt(中国特色网络围捕)”(李惠婷,孙春在,林珊如,2010)。有学者直接将其命名为发生在“东方文化”传统国家网络社区中的“数字东方主义”(Mayer, 2020)。
这样的中西网络私刑实践差异,使得部分学者将关注焦点集中于文化与网络私刑行动之间的勾连,例如周荫强(Patrick Y. Chau)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以集体主义为本质的亚洲文化在重新解释和利用外部影响方面优于基于希腊罗马传统的个人主义文化”(Chau, 2008);戴维·赫罗德(David Kurt Herold)则指出,由集体主义价值分享、合作与社会责任等情感驱动的在线民族主义往往会导向网络私刑行动甚至群体极化,反过来又对线下社会的政治产生影响(Herold, 2009);马可·斯科里克(Marko M. Skoric)等也提出“文化与国籍也可能影响一个人对揭发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看法。例如,像日韩这样的集体主义的亚洲国家会更积极地看待揭发行为,认为其有助于集体利益”(Skoric et al., 2010)。但是很显然,仅用集体主义来解释过于笼统。
因此,笔者拟使用实证方法对中国网络私刑行动进行比较文化视角的考察,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独特文化因素以对中西实践差异做出解释。
二、中西网络私刑实践的“三边比较”
传统的基于两个目标对象的比较,若观察到差异则很难确定其是否可归因于语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因素或多层面影响,故祝建华等(Zhu et al., 1997)提出了“三边比较”方法。其具体做法是:以美国为对象同时以其他两个区域作为参照,而后两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中之一应与美国有相似的政治制度,但与美国有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这一参与比较区域应该与另一参与比较区域具有相同的文化”。根据这一标准,祝建华等选择了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等三个区域进行三边对比研究。本文借鉴这一方法,以中国大陆地区为对象并参照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进行“三边比较”,拟验证以下理论假设:中国文化情境中网络私刑以“网络众筹审判”形态为主,而西方文化情境中网络私刑以“网络反骗钓鱼”形态为主。
理论假设中的关键概念为网络私刑形态呈现,将其操作化为事件发生频度与社会认同度两个变量,分别使用三个区域的社交媒体相关案例数量及态度倾向性呈现来予以测量,数据搜集时间跨度设置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五年。其中,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发文来源于微博,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社交媒体发文来源于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相关内容检索词如(表1 表1见本期第5页)所示。
以下分别呈现统计分析结果。
中国大陆:“网络众筹审判”案例数量远超“网络反骗钓鱼”,前者约为后者的20倍,且整体态度倾向以认同与中立为主,不认同者仅占约四分之一(26.78%)。网民们认为越轨者无论是否负有法律责任,都应当受到舆论谴责。例如有微博用户公开表示,性骚扰罪犯在受到法律惩罚之外,“在社交范围内受到公开批评和孤立也是应当的”(猪蹄蹄小朋友,2018);而在某些法律无法管辖的领域,“公开曝光、舆论谴责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风的节奏吹,2019)。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中“网络反骗钓鱼”相关案例数量则仅为“网络众筹审判”的二十分之一,相差两个数量级。尽管拥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其主要被认同为一种娱乐大众的方式而非惩罚行骗者的手段,其私刑属性较弱。例如有微博用户分享了自己在线“调戏骗子”的视频并让“大家听着玩吧”(cv旁师傅,2016)。还有微博用户分享与茶叶诈骗者的聊天对话,笑称“无聊到开始以调戏骗子为乐了”(青衫居士李探花,2017)。甚至一些公安政务微博也将调戏骗子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分享一些和骗子聊天的技巧,笑笑,然后好好睡觉,晚安”(金盾广安,2017)(表2 表2见本期第6页)。
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情况类似,台湾地区“网络众筹审判”案例数量远超“网络反骗钓鱼”,前者约为后者的24倍,且对前者持认同与中立态度者近九成(87.79%)。其网络私刑行动主要以“求惩罚”为目的,例如有Facebook台湾用户发现自己照片被盗图,因此公开求助网友对盗图者进行舆论惩罚:“真的很可恶!拜托大家了!用舆论压力让他受到惩罚吧!”(熊熊BearGenie, 2018)由于“反骗钓鱼”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交媒体上的案例出现太少,其态度倾向性分布无意义,故不予考察(表3 表3见本期第6页)。
美国:“网络反骗钓鱼”案例数量4倍于“网络众筹审判”,同时前者的认同度高达84.06%且不认同者为零;而对后者的认同度仅有4.76%。与中国大陆地区不同,在美国,“网络反骗钓鱼”主要被认同为一种“惩罚”行动,私刑属性非常明显。例如有推特网友(Hunter, 2019)发帖称:“我终于加入reddit(论坛)的网络钓鱼群了。是时候浪费骗子的时间、逮捕他们或关掉他们的信号塔了。我无法告诉你我对此有多兴奋。”脸书网友@Kendall Sharpe称,“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召唤这些蠢货们,浪费他们盗窃的时间,让他们不能从任何真正的受害者那里偷东西”(Sharpe, 2019)(表4 表4见本期第6页)。
三边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网络私刑形态呈现高度相似,且显著区别于美国。从事件发生频率看,“网络众筹审判”在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均占据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而美国则以“网络反骗钓鱼”为主;从社会认同度看,中国大陆地区也与中国台湾地区较为相似,而与美国存在明显差异。综上,文化因素极有可能是三个地区之间网络私刑形态呈现差异的重要原因,其机制值得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三、“无组织的联盟”:中国网络私刑的外在表现
在中国,以“网络众筹审判”为代表的网络私刑行动首先突出地在组织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可称为“无组织的联盟”的特征,而这一组织特征也决定了相应的“网络众筹审判”惩罚手段。
西方偏好的网络私刑行动通常高度组织化,例如国际著名黑客行动组织“匿名者”(Anonymous),或网络反骗钓鱼组织“网骗消灭者”(419Eater)。这类组织有明确的主题和目标,并在相应的网络社区中有针对性地对成员进行长期动员;但在组织内部,行动者通常是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分头行动,成员之间的群体性协作程度并不高,行动偏向“原子化”。而中国以“众筹审判”为代表的网络私刑行动外在表现则更“无组织化”,大部分网络私刑行动者是临时集结而成的,参与者并不属于某个确定的组织;但这并不妨碍同一个事件中的参与者之间形成高度协作的“联盟”。在“人肉搜索”行动中,有人发布事件现场照片,有人分享事件地理位置,有人上传现场监控画面,有人公布涉事者履历……通过碎片化的个人行为高效“拼凑”成完整行动。在网络民族主义“众筹审判”事件中呈现出分工明确、整体协同的群体行动,例如在“帝吧FB出征”行动中,参与者根据自身意愿加入“前线部队”的不同分工中,包括情报工作(收集“台独”言论和图片)、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帖招人)、武器装备工作(制作反“台独”图片和言论)、对外交流工作(外语翻译)、战场清理工作(负责社交媒体点赞或举报)等(刘海龙,2017b)。这种集体情报系统和跨平台的信息共享实践,通常会在短时间内引发网民集体参与的浪潮,形成广泛而积极的“无组织的联盟”。有研究认为,中国“人肉搜索”行动这种创造性和协作性源于中国历史上具有信息共享特征的文化实践(Cheong & Gong, 2010)。集体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价值共享,合作和社会责任”的需求,并在Web2.0技术中得到了很好的满足(Chau, Herold, 2008, 2009)。身处集体主义的个人基于儒家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一套家庭和社区导向的责任观的影响,会受到更大的善、道德与和谐观念的约束(Cho & Kim, 2013);而坚定认同这类价值观的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止不良行为,参与网络私刑行动就是个人对社会群体的贡献(Skoric et al., 2010)。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互联网用户热衷于“众筹审判”的原因。
这种群体分工的协作形式继而影响到了惩罚手段。西方有一句俗语是“唯有上帝可以审判我(Only God can judge me)”,西方人对于为恶、犯罪都是一种自觉的省察,而个人言行的动机无需向众人展示或解释,同时也无权评判他人的私事。这种价值观显然削弱了“众筹审判”的实施空间。在被称为“美版天涯”的美国Reddit论坛上,与网络私刑行动最相关的板块“RBI(Reddit调查局)”首先从版规上明确了论坛不能被用作“众筹审判”的武器:“第一,任何犯罪事件都需要由警方处理,未经审判不予讨论;第二,禁止透露个人信息;第三,RBI不是私人部队!也不会帮助追捕冒犯您的人。”论坛成员之间具有广泛共识,针对私人报复性、惩罚性的意图会被敏感地识别并遭到拒绝,报复性的“众筹审判”被认为是“错的”,报告警察、遵循法律途径被认为是“对的”。而对生活在关系性社会中的传统中国人来说,和谐是中国人最大限度获得人生幸福感和满意度的保障,俗语有言“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而儒家在正面宣扬“无讼”的益处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时,还制造了“以讼为害”的反面舆论,如“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沈德咏,2012:163),因此“与人争讼”、“对簿公堂”是在社会生活中要尽量避免的行为。这一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直到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诉讼率不高的社会”(徐昕,2015:170-171)。正是这种“息讼”或“无讼”的社会风气导致的“厌讼文化”,也从另一方面必然要求和极大刺激了私刑实践的发展。在中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或许是比法律制裁更可怕的震慑,因此在社交网络中揭开越轨者的匿名面具、将个人恶行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会导致其“社会性死亡”。而这一文化体验来自中国社会文化中暗含的“耻感文化(shaming cultures)”。翟学伟(2017:197)曾指出,“耻感文化是海内外学者对我们东方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概括,它可以同西方罪感文化相对照,其特征是这种文化中的人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这样一些外在的社会标准所规范和制约”。这一研究结论在当下中国的网络社会中也依然富有解释力。例如2017年马里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毕业演讲时称美国空气“新鲜而甜美”、“格外的奢侈”,让在家乡出门就要戴口罩的她“感到自由”(刘美武,2017)。这些谬误偏颇的演讲伤害了中国民众的集体情感,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演讲者很快遭受到了网络众筹审判,随后迫于压力该留学生发文致歉。类似的案例还有“厦大洁洁良事件”(刘雪松,2018)等,人们集结起来的原因是为了惩罚这些道德上有问题的越轨者,通过让他们感到“丢脸”和“羞耻”进而自我反省和规训,并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申社会规范。已有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Skoric et al., 2010)表明,坚定地认同儒家思想或亚洲价值观的人更有可能被网络羞辱威胁吓退,网络上的曝光和辱骂等手段对他们更有效,因为“耻感文化”是“儒家社会的显著情感”,回避耻感是“压倒一切的关切”。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罪”往往是一种法律条文的认定;而“耻”则不同,当越轨者不能“罪有应得”时,羞辱要比告发更有威慑力,因此在中国网络私刑行动中,公开个人信息和在线羞辱就是最常用且有效的手段和技巧。笔者考察中国“人肉搜索”发源地之一天涯论坛的“天涯杂谈”板块后发现,其版规主要强调禁止发布色情内容和人身攻击、广告等,既未提及有关个人信息应当保密,也未提及涉及违法犯罪的事务只能由警方处置。2021年1月16日笔者以“人肉搜索”为标题在天涯论坛中进行搜索,共搜索到1.252万篇帖子,其中绝大部分直接曝光了个人姓名、电话、住址甚至照片等个人信息,诸如“人肉搜索这个无良的老师”、“爱情受伤,金钱受骗!请大家人肉搜索”、“深圳诈骗犯,骗取别人一年工资,顶起来,人肉搜索他!”等等,都是对发起网络众筹审判私刑的直接呼吁。
四、“公道自在人心”:中国网络私刑的内在逻辑
中国网络私刑在外在形式上表现出与西方不同的“无组织的联盟”的同时,还与后者存在惩罚对象和行动边界的差异,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公道自在人心”。
何为“公道”?《说文·八部》中提到“公,平分也”;《说文·辵部》中指出“道,所行道也”,引申指“道义”。“公道”就是指“公平,合理”。因此,“讨公道”的根本含义就是要求自己或他人被公平合理地对待。“公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遭遇不合理对待时,人们常常引用“公道自在人心”来劝慰不利的一方,对其遭遇表示理解和同情;同时,对占上风的一方用“想要公道,打个颠倒”的俗语来劝诫其公平待人。韩起祥(1997)还指出“它(公道)贯穿于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对于建立和维护封建法制的统一性,保护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稳定,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可见“公道”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唐代诗人杜牧在《送隐者一绝》里就赞扬道:“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倘若在立法、守法、执法中发生徇私枉法的情况,那显然也是“不公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不公待遇时,依据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被称为“讨公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司法上已有定夺时,依靠主观体验来反抗不符合“公平”预期的判决也可以被称为“讨公道”。显然,这种作为“公道”判定依据的主观体验并无明确的标准,势必造成“讨公道”准则的模糊性,从而使得其在具体实施中更多地依赖公众内心的道德准则——此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这就首先导致了中国的网络私刑实践在惩罚对象上更多地指向法律不能规制的道德失范行为而非西方网络私刑指向的违法犯罪行为。约翰斯顿·莱斯(Johnston Les)提出了私刑主义中有“犯罪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区别,认为前者偏向于关注阻止或惩戒犯罪行为的发生,而后者偏向于关注维护社区、种族或宗派的秩序和价值观;虽然传统的私刑研究案件大都属于前者,但后者这种对价值观的冒犯也应当被纳入考察(Les, 1996)。正如莱斯所言,西方长久以来对私刑主义的研究主要关注犯罪行为的惩戒问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彼得·塞德伯格(Peter C. Sederberg)就指出“通常私刑行动者的愤怒是针对那些对人身和财产犯下被现行法律秩序明确定为犯罪行为的人”(Sederberg, 1978)。而到了网络空间,不少西方学者同样认为“对法律界定的(感知的)犯罪行为作出反应”是构成私刑主义的要件(Silva, 2018)。因此,西方网络私刑行动的类型主要是针对网络经济诈骗、儿童色情问题的“网络反骗钓鱼”,亦或是针对恐怖组织的“黑客行动”,其指向对象均系犯罪行为,而对于个人言行道德失范的反应却并不积极。相反,在中国语境下网络私刑行动却多针对道德失范行为,从而体现出莱斯所说的社会控制取向。中国人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关涉伦理道德事件时常常会认为,法律并不能及时起到伸张正义以至安抚民心的作用,转而觉得公众自会作出恰当的评价(即所谓“是非自有公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其标尺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即所谓“人心自有一杆秤”)。道德共同意识在以儒家传统为背景的文化中的核心位置明确且清晰,熟悉这套伦理的成员都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根据自身经验为生活中的纠纷“评事理”、“摆公道”。正因如此,马克斯·韦伯(2003:109)才说在中国“公道”比“法律形式”更重要。譬如在“留日女大学生江歌被害案”中,比起已经伏法的行凶者,民众对“见死不救”、“恩将仇报”且无“法”可治的刘鑫更加不满,因而自发实施了长期的舆论谴责;而网民的行动目的“无非是刘鑫真诚地悔过,真诚地道歉,拿出行动来的表现,而不是一直巧舌如簧地为自己辩解”(绕口令真拗口,2018)。这正是网民在法律无法对刘鑫“失德”行为进行惩罚的情况下试图为受害者及其家人“讨公道”。因此,中国网络私刑行动主要针对道德失范行为,作为一种额外的社会控制机制发挥了补充惩罚、维护道德的作用。
其次,“公道自在人心”的内在逻辑还反映在行动边界的标准上。有学者指出“中西方对待‘人肉搜索’事件的不同选择,是信奉自由个体主义的共同体与网民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刘晗,2011)。西方学者不断宣扬“隐私”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项利益,甚至认为在使人类得以生存的各种价值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中,隐私处于核心地位(惠特曼,杨帆,2006)。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同程度的自我暴露成为个人在文明共同体中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刘易斯,2016:69)。网络私刑行动更加突出了隐私和公共空间的矛盾,西方学者指责它是“一种私人形式的暴力,从一开始就标志着对目标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Trottier, 2017)。因此,西方在实践中选择了冗长而缓慢的“网络反骗钓鱼”而非“人肉搜索”,前者在起到阻断犯罪、惩罚罪犯作用的同时,既实施了有效惩罚,又巧妙地避免将自己置于触犯他人隐私的风险之中。在儒家文化中,“公私”的边界始终模糊并且强烈依赖情境。翟学伟(2016: 153)对东西方的隐私观念有一段深刻的分析:“西方人的隐私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既然每个人都有隐私,那么每个人都没有权利打听别人的隐私……但在中国文化中,虽然人们事实上也有隐私,却没有隐私的观念。”在这一理念下,对于那些针对违章乱停、婚外情、虐待老幼等越轨行为进行人肉搜索的网民而言,保护个人隐私的逻辑是说不通的,所有的信息搜索、汇总、发布的自发行为都是以服务于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为目的的,因此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刘晗,2011)。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基于公益需求的“人肉搜索”个人资料视为合法,而超出公共利益范围的则可能被判定违法。具体来说,其规定有关脸书(Facebook)、博客等张贴他人照片的行为必须限制在社交活动或家庭生活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至于在互联网上进行人肉搜索,并无太大争议,合法与否主要看个案是否符合公众利益”(韩福东,何淑贤,2010)。此外,这种“公—私”的情境性还表现在,人们认为一个人在私人领域的言行应当与其在公共领域的言行一致。正所谓“君子慎独”、“君子不欺暗室”、“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即使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应当谨言慎行,因为个人言行在公共和私下场合都具有同等的道德意义,应该受到同样程度的道德审查。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人们甚至会将“是否经得起人肉搜索”作为考验干部选任的准则(张培元,2009);而公民个人也会有类似想法:“如果我们在网络和现实中言行一致,我们就经得起检验,经得起人肉搜索”(许炯君,沈之蓥,2010)。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当个人隐私因网络私刑而遭到侵犯时,受害者一方面会因为厌讼思想、耻感文化而感到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因“道德不完美”的自我审查而选择沉默,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十大人肉搜索事件仅两起追责”(程媛媛,2015)的情况。相比于西方选择的“网络反骗钓鱼”,中国利用“网络众筹审判”惩戒公德或私德失范之人在网络社会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也获得了更为实际的效果。
五、“讨公道联盟”:中国网络私刑行动的实质及其转型方向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网络私刑行动的实质可概括为“讨公道联盟”。这至少凸显出其两个核心构成要件,一为“讨公道”,二为“联盟”。两者都受中国文化特质的影响,其中前者是中国网络私刑行动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心理基础,与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高度关联。这一发现或能为中国网络私刑行动向网络空间民间协同治理手段的转型提供些许启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不完全依赖官僚(张维迎,邓峰,2003)而以宗族、保甲、乡约等乡村基层组织为根基,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这些独特的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经验利用地缘、血缘关系构建起“监管关系”,将个人置于灵活有效的监督、管理、干预、劝导等微观权力之下,并渗透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尤其能使无法入刑而有违公道的行为得到惩戒。时至今日,日趋凸显的网络空间规制资源与能力局限使得发展网络空间的民间协同治理手段也具有了必要性,而网络私刑行动正是重要备选之一。莱斯(Les, 1996)曾明确了私刑行动的“自治公民(autonomous citizenship)”特征,即私刑主义是由自发参与社区事务以改善社区环境的“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在没有国家或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从事的自愿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自治行动。具体到中国,常常被忽视的一点是——私刑行动在破坏着秩序(法律)的同时也在维护着秩序(道德),而如何发挥其建设性作用限制其破坏性的一面,就成为将其转变为自治手段的关键。
本文的发现揭示出,在中国网络私刑行动的两大核心构成要件中,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高度关联的内在逻辑——“讨公道”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对于参与人数众多的中国网络私刑行动来说,对整个行动进行合理协调形成“联盟”尤为重要。在前互联网时代,组织协调这些“微小贡献”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变革,密集的超人际网络和信息高度共享的互联网为中国网络私刑行动提供了更加深厚的技术背景(Cheong & Gong, 2010)。例如,在互联网平台上,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节点用户的“微小贡献”可以通过标签(tag)技术等互联网自动聚类技术的形成,高效而自动地协调系统。这意味着,从技术维度限制“联盟”这一协作形式应是更具可操作性的突破方向——这或许就是本研究发现的应用价值所在。虽然限于篇幅,进一步的探索有待后续研究完成,但可以肯定,在经过互联网时代的重新表述之后,传统中国大规模、高效率、低成本的协同自治机制如果能够通过当下的网络私刑行动,继续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网络空间的治理,将成为推动网络空间公民参与、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重要资源。此外,必须承认中美隐私保护法律在数量和力度上的“寡众悬殊”(王敏,江作苏,2016)也可能对网络私刑行动的形态存在影响,这是本文未及之处,也是未来值得探讨的一点。■
参考文献:
安东尼·刘易斯(2016)。《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徐爽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陈好毅(2005)。浅谈中国的公道、人情和法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19-20。
cv旁师傅(2016年9月13日)。一次很不成功的调戏骗子经验。新浪微博。weibo.com/1667086511/E87MNqWHu?refer_flag=1001030103_&type=comment。
程媛媛(2015年5月7日)。十起人肉搜索案例仅两起追责。《新京报》,A15。
风的节奏吹(2019年5月30日)。没人能管,公开曝光、舆论谴责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新浪微博。weibo.com/1108242961/HwB7ry5gF。
共产党员网(2018)。人肉搜索是一种网络私刑。检索于http://tougao.12371.cn/gaojian.php?tid=1995717。
江湖视界(2018年5月15日)。帮忙“人肉搜索”这个暴力司机,以后别出来祸害姑娘了。新浪微博。weibo.com/2815128207/GgJ8hgAM7。
金盾广安(2017年11月28日)。调戏骗子的技巧来了,看看吧。新浪微博。weibo.com/2918589882/Fx8sN3CW4。
韩福东,何淑贤(2010年4月29日)。台湾修法:人肉搜索关乎公益即合法。检索于http://it.southcn.com/9/2010-04/29/content_11504895_2.htm。
韩起祥(1997)。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当代法学》,(6),30-34。
李惠婷,孙春在,林珊如(2010)。台湾人肉搜索文化之探讨,硕士学位论文。新竹:交通大学。
李建,若英(2013)。西方国家允许“人肉搜索”吗?。《红旗文稿》,(10),39-39。
兰陵笑笑生(1999)。《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二)。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香港:梦梅馆。
刘晗(2011)。隐私权、言论自由与中国网民文化:人肉搜索的规制困境。《中外法学》,(4),870-879。
刘锐(2008)。“人肉搜索”与舆论监督、网络暴力之辨。《新闻记者》,(9),87-89。
刘美武(2017年5月26日)。我们应该如何评论自己的国家?《中国国防报》,23。
刘海龙(2017b)。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4),27-36。
刘雪松(2018年4月23日)。撕开“洁洁良”们的丑恶嘴脸。《浙江日报》,5。
MusicZHEN(2018年5月17日)。伟大的微博请帮人肉搜索这个诈骗犯,我们的血汗钱啊。[新浪微博]. weibo.com/2815128207/Gh5LbsAMT。
马克思·韦伯(2003)。《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青衫居士李探花(2019年1月20日)。论茶叶骗子的聊天日常。新浪微博。weibo.com/3933780956/HcPZVE2Rl。
绕口令真拗口(2018)。如何看待刘鑫及背后团队以遭受网络暴力为由起诉江歌妈妈?检索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327269/answer/350787434?utm_source=wechat_session。
沈德咏(2012)。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对加强当代法院文化建设的意义与启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公安部法制局编,《公检法办案指南(第155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搜狐新闻(2018)。高铁“座霸”:法律缺位导致的一场“网络私刑”。检索于http://www.sohu.com/a/249668232_106321。
腾讯网(2012)。隐私权与网络“私刑”。检索于https://news.qq.com/a/20120701/000595.htm。
王敏,江作苏(2016)。大数据时代中美保护个人隐私的对比研究——基于双方隐私保护最新法规的比较分析。《新闻界》,(15),55-61。
许炯君,沈之蓥(2010年1月14日)。公布警察身份压力大不大?我们经得起人肉搜索。《杭州日报》,94。
[汉]许慎(1963)。《说文解字》卷2《八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陈昌治刻本。
徐昕(2015)。《论私力救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熊熊BearGenie(2018年9月28日)。真的很可恶!拜托大家了!用舆论压力让他受到惩罚吧!脸书。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947533185314625&id=408302015904424。
张维迎,邓峰(2003)。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3),99-112+207。
张培元(2009)。公开公正选官何惧“人肉搜索”。《政府法制》,(22),51-51。
詹姆士·Q.,杨帆(2006)。西方文明中的两种隐私文化:尊严vs自由。《私法》,(1),101-170。
翟学伟(2016)。《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2017)。附:耻感文化的狡黠之处——从一项问卷调查想到的。见翟学伟(编),《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第197页)。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知识经济》编辑部(2019)。“民族资产解冻”骗局。《知识经济》,(17),112。
朱昌俊(2018年8月23日)。惩治高铁上“霸座”,仅舆论谴责还不够。《南国早报》,A102。
猪蹄蹄小朋友(2018年5月27日)。性骚扰是一种“罪名”。新浪微博。weibo.com/1677574270/GiA0h4SIp。
AbaoCarmel V. (2018). Vigilantism: Crime or justic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appler.com/thought-leaders/205025-vigilantism-crime-or-justice.
Browning J. (2019May 26). This has to be one of the best ever scam baiting videos.[Tweet].twitter.com/JimBrowning11/status/1132377389210775552.
E. SilvaK. (2018). Vigilantism and cooperative criminal justice: is there a place for cybersecurity vigilantes in cybercrime fight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Computers & Technology, 32(1)21-36.
Chang, L. Y.& LeungA. K. (2015).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 crowdsourcing (human flesh search)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In R. G. SmithR. C. Cheung, L. Y. Lau(Eds.)Cybercrime Risks and Responses (pp. 240-252). Palgrave MacmillanLondon.
Chang, L. Y.& Poon, R. (2017). Internet vigilantism: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 cyber crowdsourcing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61(16)1912-1932.
ChauP. Y. (2008).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diffusionadoption, and infusion of Web 2.0.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16(1)i-iii.
ChenR.& Sharma, S. K. (2011). Human flesh search-facts and issu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Security, 7(1)50-71.
CheongP. H.& Gong, J. (2010). Cyber vigilantismtransmedia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4)471-487.
ChiaS. C. (2018). Crowd-sourcing justice: tracking a decade’s news coverage of cyber vigilantism throughout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045-2062.
ChiaS. C. (2020). Seeking justice on the web: How news media and social norms drive the practice of cyber vigilantis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8(6)655-672.
Cho, Y. H. & KimT. J. (2013). Asian civic value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three east Asian societies.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2(1)21-31.
HeroldD. K. (2009). Cultur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Web 2.0 in Asia. KnowledgeTechnology & Policy, 22(2)89-94.
Helsel H. (2019Nov 15). I’m finally part of a scam baiting group on reddit. [Tweet].twitter.com/Hunter_Helsel/status/1195058319523758081.
Kosseff, J. (2016). The hazards of cyber-vigilantism.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32(4)642-649.
Sharpe K. (2019Jul 26). We call up these prejudiced fools to waste their thieving time so that they can’t steal from any real victims. [Facebook]. facebook.com/kendall.sharpe1/posts/10157367835175350.
Les, J. (1996). What is vigilantism?.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2)220-236.
Li J. (2019May 15). The Chokehold of China’s Internet Vigilantes.The New York Timesp.25.
Mayer, M. (2020). China’s authoritarian Internet and digital orientalism. In D. Feldner(Ed.)Redesigning Organizations (pp.177-192).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ham: Springer.
Murdoch, I. (2019). Lateral violence and online bashing takes lives. Retriaval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497368090550952&id=100008333559927.
Neubaum, G.Rosner, L.GansterT.HambachK.& Kramer, N. C. (2018). United in the name of justice: How conformity processes in social media may influence online vigilantism.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7(2)185.
ReichlF. (2019). From vigilantism to digilantism?. In B. Akhgar, P. S. Bayerl, G. Leventakis(Eds.)Social Media Strategy in Policing (pp. 117-138).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ham: Springer.
SkoricM. M.Chua, J. P. E.Liew, M. A.Wong, K. H.& YeoP. J. (2010). Online shaming in the Asian context: Community empowerment or civic vigilantism?. Surveillance & Society8(2)181-199.
SmallridgeJ.Wagner, P.& CrowlJ. N. (2016). Understanding cyber-vigilant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Theoretical & Philosophical Criminology8(1)57-70.
SorellT. (2019). Scambaiting on the Spectrum of Digilantism.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38(3)153-175.
SorellT. & Whitty, M. (2019). Online romance scams and victimhood. Security Journal32(1)342-361.
Sederberg, P. C. (1978). The phenomenology of vigilant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1(3-4)287-305.
TrottierD. (2017). Digital vigilantism as weaponisation of visibility. Philosophy & Technology, 30(1)55-72.
TuovinenL. & Roning, J. (2007). Baits and beatings: vigilante justice in virtual communities. In Proceedings of CEPE 2007.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puter Ethics: Philosophical Enquiry (Vol. 397405). in: Proceedings of CEPE 2007.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puter Ethics: Philosophical Enquiry397-405.
ZingerleA. (2015August). ScambaitersHuman Flesh Search Engine, Perverted justiceand Internet Haganah: Villains, Avengers, or Saviors on the Internet?. In ISEA Conference.
Zheng, YWu, G. (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ublic space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38(5)507-536.
Zhu, J. H. Weaver, D.Lo, V. H.Chen, C.& Wu, W. (1997).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influences on media role percep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China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4(1)84-96.
蒋晓丽系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蔚系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张放(通讯作者)系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公共危机背景下社交媒体公众认知与情绪引导的计算传播学研究”(中宣办发[2020]4号)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