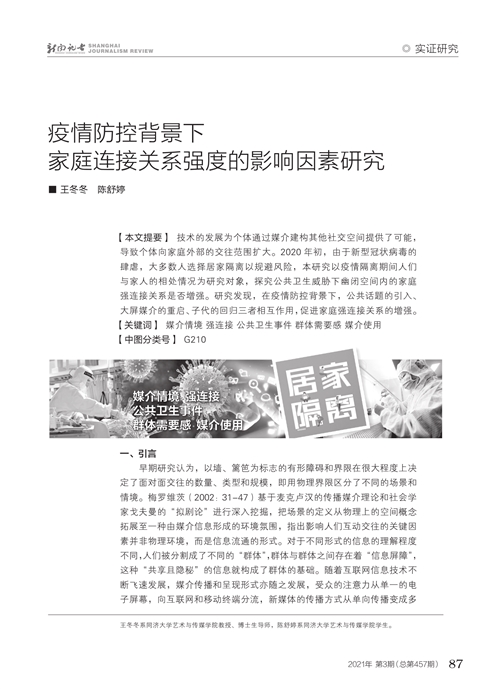疫情防控背景下家庭连接关系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王冬冬 陈舒婷
【本文提要】技术的发展为个体通过媒介建构其他社交空间提供了可能,导致个体向家庭外部的交往范围扩大。2020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大多数人选择居家隔离以规避风险,本研究以疫情隔离期间人们与家人的相处情况为研究对象,探究公共卫生威胁下幽闭空间内的家庭强连接关系是否增强。研究发现,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话题的引入、大屏媒介的重启、子代的回归三者相互作用,促进家庭强连接关系的增强。
【关键词】媒介情境 强连接 公共卫生事件 群体需要感 媒介使用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早期研究认为,以墙、篱笆为标志的有形障碍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面对面交往的数量、类型和规模,即用物理界限区分了不同的场景和情境。梅罗维茨(2002:31-47)基于麦克卢汉的传播媒介理论和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进行深入挖掘,把场景的定义从物理上的空间概念拓展至一种由媒介信息形成的环境氛围,指出影响人们互动交往的关键因素并非物理环境,而是信息流通的形式。对于不同形式的信息的理解程度不同,人们被分割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存在着“信息屏障”,这种“共享且隐秘”的信息就构成了群体的基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飞速发展,媒介传播和呈现形式亦随之发展,受众的注意力从单一的电子屏幕,向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分流,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从单向传播变成多向传播。用户获取信息、自我表达和人际互动的方式等都随之改变,个体可以同时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出现不同情境相互重叠的现象,社会角色产生混淆。个体交往意愿发生改变,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屏障”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群体和其中的个体行为都发生改变,即“谁与谁分享信息”影响“谁与谁构成群体”。
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以血缘、地缘关系联结的家庭是个体交往的主要空间。社会的主要功能都集中在家庭之中,封闭的家庭环境使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性强,很少对外交往,排外、排他性强(王冬冬,李芊芊,2016)。存在着只在家庭内部流通,不与外人分享的信息。家庭扮演着戈夫曼(1989)所说的“后台”,使得成员更好地适应在“前台”的表演。但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人类的活动空间慢慢延展,人们的社交圈辐射面也随之拓展(周大勇,孙红昶,2018)。一方面,随着子代的成长,进入社会,其所活动的实体空间也越来越大。人本分析学家弗洛姆认为儿童在幼年时期完全依赖父母,有着非常稳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同父母的联系日益减少,个人责任日益增大(叶浩生,1994)。即人在成长过程中,社交活动的基础从家庭变成了个人。当与他人联系的可能性增大后,以血缘为联结的关系在社交中的比重便下降。
另一方面,网络结构具有德勒兹(1988)所说的“块茎”系统的特点,每个个体形成一个节点,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受地缘、血缘或业缘的限制,形成“个人—个人”的由弱连接发起的社交关系。移动互联端的社交媒体具身,使人们选择交往空间的介入成本得以填平,从而将由成员间日常关系的亲疏、价值观念的异同等造成了空间中的个体的接触选择性意向的作用放大。当家庭成员共处于同一实体空间时,人们更倾向通过移动端和PC端的电子媒介去虚拟空间中获取与本人思想相一致的内容,使物理性的家庭空间中共生着延伸于其外的其他社交空间,减弱了原有家庭成员间的沟通频次。加之家庭成员的共同经验变少,兴趣共识分化,导致家庭成员间的强连接关系受到挑战,甚至使原本属于“后台”的家庭“前台化”。事实上,人的肉身栖居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二维分离,导致了每个个体的主体性会更加凸显,人们基于需求生成性地建构自己的交往空间,在当代技术、经济条件支撑下,被信息流牵引的个体在实体空间的行动也变得更加自由,这也与信息的流动形成了互构。也就是说,媒介具身之后的个体逐渐摆脱了家庭、社会关系的束缚,从实体空间解放出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对社会发展及个人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活力取决于每个家庭的和谐状况。对于个体而言,家庭是其情感的港湾,也是个人再生产的主要场域,尤其是遇到外在威胁性压力出现,家庭是不良心情缓解和压力释放的调节地带,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助于人们的心灵建设。面对网络社会的新型人际交往特征,探究实体空间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重起加强以血缘或婚姻为纽带的强连接关系的作用是有必要的。2020年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大多数人选择居家隔离以规避风险,本研究以疫情隔离期间人们与家人的相处情况为研究对象,探究公共卫生威胁下幽闭空间内的家庭强连接关系是否增强。
二、文献综述
(一)安全感与群体需要感
安全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他假定:当个体接受到的刺激超过了本身控制和释放的能量界限时,就会产生一种创伤感、危险感(叶浩生,1994:199)。伴随着这种创伤感、危险感出现的体验就是焦虑。马斯洛认为,人的心理安全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阿瑟,1996:765)。也就是说,“它是对可能出现的对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处置时的有力/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安莉娟,丛中,2003)。这种身体或心理的危险或风险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为身体上的病痛、学习工作中的压力、情感上的挫折等。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因恐惧所迫或生存之需而加入群体。“自然选择叫人屈从于群体的声音。不听从狼群的孤狼会被饿死。不对羊群及时做出反应的羊会被吃掉”(Trotter, 1917:30)。也就是说,社会群体是人们为了对付外在的压力、寻求安全感和相互支持、通过合作相互补充而形成联结的共同体(章志光,2001:46)。而维持该共同体的是杰曼·格里尔所说的“共享且隐秘的行为”(Greer, 1972:23),这种行为将“狼群”与“羊群”分隔开来。当个体加入群体后,由于共同的经历,个体与其他成员形成情感上的联结,从而对群体产生依赖与信赖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被称为群体感或群体归属感。这种认同一般建立在群体成员互相信任、互惠合作的基础上。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也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甚至参加集体行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会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 1978:63)。在家庭内部,由于一直以来共享隐秘话题,并互相信任、互相照顾,互相满足生存生活或情感上的需求,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群体连接,成员之间相互关心、依赖。
在近年来的实验研究中也发现,安全感量表得分与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得分呈显著负相关(安芹,陈浩,2015)。个体社交回避与苦恼水平越高,体验到的孤独感越强烈,越容易导致安全感降低(张雪凤,高峰强等,2018)。即当个体倾向于进行社会交往时,就可以通过改善人际关系和构建社会支持系统,从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客体关系理论认为外部客体对建立内部心理有重要影响,是心理发展的基本材料(Clair, 2002)。当个体加入群体时,群体中的亲人、朋友等客体承担了容器功能,个体从客体身上获得了爱与亲密的力量,从而能够重建安全感(谭锦花,2019)。公共疫情的突然爆发使人们感受到对外界不确定与不可控,对风险的感知使不安全感增强,个体会受恐惧等因素推动去寻求集体慰藉。
H1:在公共疫情压力下,个体与家庭外部的信息交往频率增强。
H2:在公共疫情压力下,个体在家庭内部的交往程度增强。
(二)实体交往空间与虚拟交往空间
社会学关于空间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客观环境论到社会关系论的转变过程。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研究从基础的物理或自然空间转向社会空间,并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Lefebvre, 1991)。后来的哈维(2003:254)、卡斯特(2001:505)也强调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空间。基于社会学与传播学相关研究,空间可以被分为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实体空间是指“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的有形实体的广延状态与伸张状态”(王逊,1991),虚拟空间则是指人与人或人与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状态,既可以建立在实体空间之上,也可以以自身为基础,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联系(李彬,关琮严,2012)。而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交可以摆脱地缘关系的限制,即虚拟空间可以与实体空间脱离,对物理空间的依赖性降低。即使在居家隔离时期,依然可以通过线上虚拟空间产生外界交往。
传统观念认为,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是直接传递到一般受众的,而“传播流”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发出的信息,要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最终“流”向受众。其中包括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信息流”,和作为效果或影响的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影响流”即对某一事件的各种意见、态度、看法等,通常与“信息流”相生相伴,在社会热点事件发生时,其作用更加明显。个体的社会交往空间中,“传播流”同时存在于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在虚拟空间的弱连接关系中,专家、大V等“意见领袖”发表自身看法,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而在实体空间中,主要体现在个体与身边人在某一问题上交流信息与观点的互相影响。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选择居家隔离,将实体空间限制在住所范围内,实体空间中可以形成“传播流”的被限制在了家庭之中,而家庭外的其他人则基本移至线上虚拟空间。虚拟空间中的“传播流”不止存在于公共媒体中,也存在于私密性更强的私聊或群聊中。
另外,实体空间内的口头传播是最快的。从手机等私人媒介获得的信息以最快传播方式(口头交流)传播给家人。口头传播在营销方面的研究较多,根据传播学定义(Rogers,1983),口头传播营销是由生产者、销售者以外的个人,不经过第三方处理加工,传递相关信息,从而使被推荐人获得信息、改变态度、甚至影响购买行为的一种双向互动的传播行为。当传播的主体是家人、朋友等,可信度会更高。口头传播能够促使人们做出判断后立即采取行动,这表明了口头传播反馈的即时性。在本研究的议题下,对于疫情相关信息的口头传播所获得的反馈是个体的防护行为或是对事件的共同探讨。当人们的实体空间范围被限制在住所时,口头传播则被限制在家庭内部。个体与家人可以就手机等私人媒介中的传播内容进行交流讨论。
H3:在公共疫情压力下,个体实体空间活动范围收缩。
H4:在公共疫情压力下,个体在实体空间行为受限后会转向虚拟交往空间与外界联系。
H5:通过关注与疫情相关的公共话题,有助于推动家庭交往程度。
(三)媒介使用与家庭关系
由媒介情境论可知,技术发展催生的移动媒体产生了新的媒介情境,行动者们为适应新情境,行为方式也相应改变。在互联网进入家庭之前,人们倾向于在一起看电视。看电视这种公共家庭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家庭的一种仪式(张晨阳,2016),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涂尔干,1912:413-436)。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发生了改变。一项民族志研究发现,当小孩在看电视,妻子在照顾孩子,而丈夫无事可做时,拥有移动视频设备的丈夫会选择陪在家人身边,默默地看移动视频。即在家中,当有多人共处一个物理空间时,通过独自观看移动视频,使用者倾向于创造一种在场却不共享话题的空间“共存感”(O’Hara & Mitchell, 2007)。因此,家人只需相互在对方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不必有共同的活动。而这种媒介使用创造的新的空间也直接打破了传统媒体努力营造的共同收视、共同议题的收视体验,使得人们在同一时间收看的内容更加多元(雷蔚真,王天娇,2009)。这种视线内的“共存感”,成为多屏时代下家庭互动行为的新型模式(何志武,吴瑶,2015)。
智能电视大屏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如今5G时代正在到来,在更多领域为智能电视大屏提供海量内容。根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达到28.6%,在全媒体的竞争中,电视依然占据一席之地。电视作为主流的大屏媒体,有区别于手机、平板等新媒体的独特优势。根据《2019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在有线数字电视缴费用户逐年下降的背景下,高清有线电视用户同比增长9.16%,有线电视智能终端同比增长26.59%,这表明用户追求更加高品质的声音与画质,开启大屏联网时代,家庭内部电视的高清大屏带来的视听体验是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且在居家隔离时期,家庭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使用电视,因此大屏媒介被开启的可能性更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沉浸在私人媒体,导致家庭内部成员虽然处于同一实体空间,但通过手机等具身媒介在家庭内部建立更深度的私人空间。而大屏幕的回归使得家庭成员运用同一个媒介获取相同信息,成员被重新联结在一起,重塑了家庭关系。
H6:实体空间受限的疫情压力环境下,大屏媒介逐渐回归。
H7:大屏媒介的回归推动家庭群体感的加强。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与测量
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和所设计的具体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将家庭关系分为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两大类别,主要从实体空间、媒介使用(虚拟空间)、与外界交流频率、话题、大屏媒介使用、家庭交往程度、家庭群体感几方面进行预先分类(见表1),预设相关问题。
媒介使用包括媒介类别、使用时长、使用频次,以及无疫情的对应时间段内时长和频次的比较;外界交往频率主要包括线上私聊与群聊的频率以及对疫情相关信息的分享;话题分为线上所关注的话题、私聊与群聊讨论的话题和线下与家人讨论的话题;大屏媒介主要以家庭内部电视的使用情况为主;家庭交往程度从互动内容、交流内容、互动时长三个角度评判,同时与过去无疫情的对应时间段内情况比较;家庭群体感分为代际亲密度和婚姻亲密度。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借助线上社交媒体平台,于2020年2月底至3月初发放问卷,此时因疫情而居家隔离已满一个月。由于疫情来临时恰逢春节假日,大部分家庭中子代回归,代际间的交往增强。子代一般由社会活跃度和媒介接触率较高的青年群体组成,一般情况下成年后的子代开始与父母分开居住(主要是平时求学或务工),19岁的青年群体属于最年轻的一批结束异地生活后返家的年轻人。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调查对象集中于19岁至39岁。此外,作为代际关系的对照样本,本研究亦调查了40至59岁年龄层段。另外,鉴于调查的普遍性,离婚、丧偶等特殊状况已筛查剔除。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214份,其中有效问卷1212份,有效回收率为99.84%。有效样本量超过题项数量的10倍(i=47),表明该问卷所得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采用SPSS 25.0。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由上述表格可知,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平均每天的外出时长不超过1小时,外出地点仅限于小区内部或超市、菜场等购置必需品的场所,即疫情期间,个体外出意愿不强,皆处于居家幽闭环境,实体活动空间趋于收缩。此外,超过半数的人表示看到的负面信息增多,并常常担心自己或身边人感染病毒,也为国家现状感到担忧,由此可见疫情期间,人们普遍处于压力环境之下。
四、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交往程度
在家庭交往程度方面,将家庭交往时长中选择“2小时以下”记为1,“2-4小时”为2,“5-8小时”为3,“8小时以上”为4,如表3所示。可得其均值为1.94,整体交往时长不高。但其中60.6%的受调查者表示和家人互动的时长较过去无疫情对应时间段更高,可见家庭交往程度在时长方面呈正向发展。
表4显示了疫情期间家庭互动内容:一起做家务的人数从58.9%上涨至67.2%,一起看电视的人数60.4%增长至66.3%,打牌等娱乐活动的人数比例也从29.4%上涨至36%;与此同时,零互动的人数下降了0.7个百分点。在家庭交谈内容比较方面,表5显示:讨论社会热点话题的人明显增多,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内容,讨论人数高达91.1%;零交流的人数降低了0.8个百分点。
(二)媒介使用
在媒介使用方面,同样将媒介使用时长中选择“2小时以下”记为1,“2-4小时”为2,“5-8小时”为3,“8小时以上”为4,如表6所示。可得其均值为3.11,整体使用时长超过5小时。且73.6%的受调查者表示使用媒介产品的时长较过去无疫情对应时间段更高,可知在疫情环境下,个体沉浸于虚拟空间的时长增加。此外,期间有42.57%受调查者表示私聊频率更高,54.29%表示群聊活跃度更高。即疫情期间实体交往空间受限,个体倾向于利用媒介与外界产生联系。
另外,在所有受调查者中,有1030位会分享疫情相关信息,分享率高达84.98%。而在这1030人中,如表8所示:高达94.56%会分享给家人,86.8%会分享给朋友,71.84%会分享给同学或同事。可以看出,个体从外界获得的信息会通过转发流入内部圈子,其中以家庭内部最为明显。
在研究话题方面的问题时,将线上私聊、群聊的话题与家庭内部的交流话题对比得出表9。可以看出,高达91.09%的受调查者会与家人讨论与疫情相关的社会话题,明显高于线上与外人谈论的频率;与疫情无关的公共话题的提及率也达到了54.13%,私聊与群聊的频率皆未超过半数。可见公共话题在家庭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
而在媒介种类方面,如表10所示,电视使用率仅次于手机和电脑,排在第三位,使用频率达到75.9%,明显高于其他种类。同时,从前文表4可知,与家人一起看电视的人数从无疫情对应时间的60.4%上升至疫情期间的66.3%。这表明,在疫情条件下,以电视为代表的大屏媒介逐渐回归生活。
(三)家庭群体感
1.代际亲密度
在研究疫情防控背景下的代际关系时,样本数量共1212份,其中对于问题“与亲代/子代关系更亲密”的回答,选择“有一点符合我”的人数最多,占46.79%;选择“完全符合我”和“不太符合我”的人数相近,分别占26.52%和23.56%;选择“完全不符合我”的仅占3.13%(见图1)。
在研究大屏使用和代际亲密度的相关性时,将使用的媒介种类中选择“电视”的样本记为1,未选择记为0;与家人互动内容中,选择与家人一起“看电视”的样本记为1,未选择则记为0;代际之间是否亲密的问题,将“完全符合”记为4,“完全不符合”记为1。得出表11:是否代际亲密度与是否使用电视(r=.097,p<.05)及是否与家人一同看电视(r=.093,p<.05)呈正相关。即子代与亲代间的家庭群体感提升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屏媒介的重启息息相关。
2.婚姻亲密度
在1212份样本中,已婚群体共436人。未婚群体中与父母居住者超过95%,未婚群体家庭关系中的父母关系亦构成对疫情防控背景下婚姻关系的参考。对于“与伴侣关系更亲密”的问题,选择“完全符合我”的人数最多,占51.69%;排在第二位的是“有一点符合我”,为36.44%;选择“不太符合我”和“完全不符合我”的人数分别仅占10.17%和1.69%(见图2)。这表明大部分受调查者与伴侣的关系更亲密了。
通过对已婚样本的婚姻亲密度和代际亲密度的分析,可得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亲密度(r=.629,p<.01)也呈正相关,如表12所示。可推断子代回归家庭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正向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对回收问卷的统计和分析,以新冠疫情期间的居家个体交往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下,处于线下交往活动范围受限的相对封闭空间内的个体交往意愿和媒介使用的改变,由此分析家庭连接关系强度是否会被加强。
第一,出于对新冠疫情威胁的恐慌,人们居家禁足的过程中,在不断增加线上交往获得信息的同时,家庭内部的交流变得更加紧密,有压力的不确定环境促进了家庭内部沟通。新冠疫情作为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出突发性、群体性和危害健康的特征,既属于公共领域事件,也与私人领域息息相关,对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个体生活实践都会产生威胁和影响。在线交流表现为群内话题围绕疫情更集中,发布在相对弱连接的公众号、朋友圈中相关疫情信息经过个体过滤、分类,借助微信群和关系更亲密的好友私聊,沿着相互关系由强到弱扩散,并成为家庭成员和密友间的谈资;在实体空间的家庭内部表现为,在疫情给公众带来的压力下,生活在一起的各位家庭成员通过手机和pad等移动媒体获得相同或相似内容指向的媒介信息,增强了相互交往的机会和意愿。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同处于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更有条件进行面对面的线下交往,而交流中的场景、信息传播的手段更全息,信息表达的符号直接性更鲜明,所获得的反馈及时性更强,家庭内部的交流会更频繁。
第二,由于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大部分人选择居家隔离,实体空间的活动和交往被固定在住所的小范围内,个体与外界的联系减少,社交活动的频率和内容都大为减少。个体表现出利用媒介与外界发生联系、获取信息或获得娱乐的倾向,即通过拓宽虚拟空间来弥补实体空间活动受限产生的缺失。基于此,在媒介使用率增高的基础上,当群体内有超过一名成员对同一或同种媒介内容感兴趣时,人们倾向于选择电视或家庭投影等大屏媒介共同观看。而人们在对利益攸关或风险判断的信息求证中,还是会倾向于接触主流媒体或官方权威媒体,并进行即时讨论。所以,以电视为代表的大屏媒介也逐渐回归公众的日常休闲生活,大屏幕媒介也起到联系家庭成员的中介作用。表4中疫情发生前和发生中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三,新冠疫情期间,子代的户外社交受限,线上交往范围收缩之后,子代在家庭沟通中的介入对于夫妻间的沟通状况是有影响的。参与本研究数据调查的已婚样本共436份,在其他填写问卷的未婚人群中,有超过95%的人与父母一起居住。此次疫情爆发时间又包括了春节假期,这个时段许多代际关系中的子代回归原生家庭,与无疫情对应时间段比较,这次调查的时段中,子代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显著延长。当子代与亲代长期处于同一活动空间时,疫情话题和节庆话题作为催化,代际之间的交流和接触较过去有明显上升。同时,由于子代的介入,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增多,代际亲密度促进了婚姻关系亲密度的上升。
总体而言,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话题的引入、大屏媒介的重启、子代的回归三者相互作用,促进了家庭连接关系的增强。立足于本研究,可以对于5G、智能技术介入人们的日常社交之后线下的交流及诸如家庭关系等强连接关系的保持和增进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媒介融合时代下,传播网络中容易形成的公共热点话题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尤其是抖音、B站、西瓜视频等自媒体音视频平台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日常媒介接触的主要媒体,影像对于日常生活的直接表述使世俗生活题材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这无疑会填平既往代际交流的鸿沟,可以触发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从而将家庭关系从日渐疏离的状态中挽救回来。
第二,重视家居生活中大屏媒体(目前主要是电视媒体)在增强家庭成员沟通交流中的作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当前许多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各居一室,或者同处一室各具移动媒体,各自通过不同的客户端进行线上社交。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家关注的内容不同;二是新媒介载体的屏幕尺度不足以满足多人集体观看的需求。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居家禁足,家庭成员重新回到大屏媒介前应该是一个改变人们媒介接触习惯的机会。既然新冠疫情让人们重新检视生活方式,回归对家庭生活的重视,那么,它也可以让人们重启客厅中的大屏媒介,以此作为促进家庭成员交流的中介。这一次新冠疫情事件所形成的大屏回归媒介接触现象应该引起大屏媒介内容制作机构的重视,找到符合受众接受大屏媒介文本的动机,制作符合这一动机的优质节目,保证大屏媒介在媒介融合传播路径中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阿瑟.S.雷伯(1996)。《心理学词典》(李伯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莉娟,丛中(2003)。安全感研究述评。《中国行为医学科学》,(6),98-99。
安芹,陈浩(2015)。自我分化与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关系:安全感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3(5),791-794+798。
哈维·戴维(2003)。《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何志武,吴瑶(2015)。媒介情境论视角下新媒体对家庭互动的影响。《编辑之友》,(9),9-14。
克莱尔(2002)。《现代精神分析的圣经》(贾晓明,苏晓波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卡斯特·曼纽尔(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彬,关琮严(2012)。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国际新闻界》,34(5),38-42。
雷蔚真,王天娇(2009)。移动视频与空间流动化——简论收视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国际新闻界》,(8),86-90。
欧文·戈夫曼(1989)。《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2006)。《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谭锦花(2019)。民办高校辅导员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7(1),94-197。
王冬冬,李芊芊(2016)。节点化生活方式的婚姻家庭形式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1),10-15。
王逊(1991)。实体空间和关系空间。《怀化师专学报》,(6),44-49。
叶浩生(1994)。《现代西方心理学流派》。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晨阳(2016)。互联网对现代家庭关系的影响——基于媒介情境论的思考。《今传媒》,24(12),162-164。
张雪凤,高峰强,耿靖宇,王一媚,韩磊(2018)。社交回避与苦恼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孤独感、安全感和沉浸的多重中介效应。《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6(3),494-497。
章志光(2001)。《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周大勇,孙红昶(2018)。互联网“圈子”传播:分层互动与关系的弥合。《图书馆学研究》,(17),17-21。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8).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Greer, G. (1972).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Bantam.
LefebvreH. (199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Wiley-Blackwell.
O’Hara KMitchell, A. S. & Vorbau, A. (2007). Consuming video on mobile devi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RogersElla M.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oja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TajfelH. (1978).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W. (1917). 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王冬冬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舒婷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