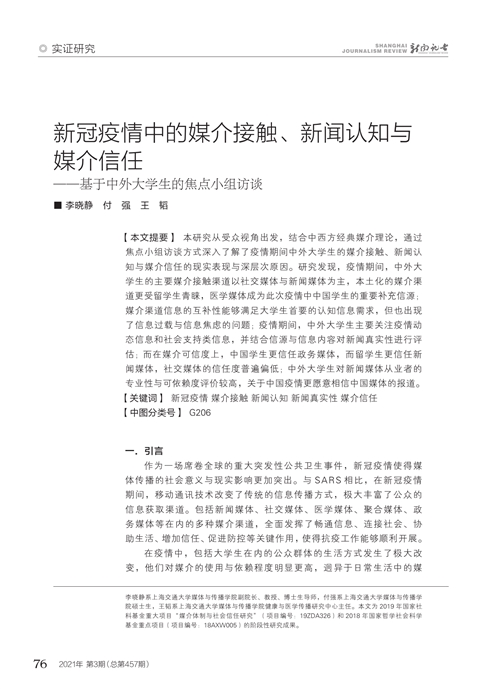新冠疫情中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
——基于中外大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
■李晓静 付强 王韬
【本文提要】本研究从受众视角出发,结合中西方经典媒介理论,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方式深入了解了疫情期间中外大学生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的现实表现与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中外大学生的主要媒介接触渠道以社交媒体与新闻媒体为主,本土化的媒介渠道更受留学生青睐,医学媒体成为此次疫情中中国学生的重要补充信源;媒介渠道信息的互补性能够满足大学生首要的认知信息需求,但也出现了信息过载与信息焦虑的问题;疫情期间,中外大学生主要关注疫情动态信息和社会支持类信息,并结合信源与信息内容对新闻真实性进行评估;而在媒介可信度上,中国学生更信任政务媒体,而留学生更信任新闻媒体,社交媒体的信任度普遍偏低;中外大学生对新闻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性与可依赖度评价较高,关于中国疫情更愿意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
【关键词】新冠疫情 媒介接触 新闻认知 新闻真实性 媒介信任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使得媒体传播的社会意义与现实影响更加突出。与SARS相比,在新冠疫情期间,移动通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极大丰富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包括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医学媒体、聚合媒体、政务媒体等在内的多种媒介渠道,全面发挥了畅通信息、连接社会、协助生活、增加信任、促进防控等关键作用,使得抗疫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在疫情中,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公众群体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他们对媒介的使用与依赖程度明显更高,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场景。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人数达9.89亿,其中20-29岁网民占比17.8%,在各年龄群体中排第三位(CNNIC, 2021)。虽然长期以来,有关媒介使用、新闻认知、媒介信任等问题的研究均备受学界重视,但多数研究是在正常社会生活中针对普通公众进行的探讨,而新冠疫情无疑为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特殊的天然条件。大学生作为媒介使用格外活跃、新闻认知相对丰富的群体,探究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媒介渠道选择、新闻态度以及媒介信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比中外大学生在疫情中媒介使用和媒介态度的异同,则对于把握当下及未来中国社会的高知群体,在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评判和因应媒体,提供了良好的参考价值。
综观已发表的相关研究,不少学者从本土样本调研切入舆情治理、应急宣传、应急情报监测等议题并展开探讨,并产出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本文拟结合中西方媒介理论,通过在线焦点小组访谈的研究设计,探究疫情期间中外大学生如何选择并使用各种媒介渠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使用,他们对疫情新闻关注的重心是什么,如何对新闻的真实性作出判断,他们对疫情期间各类媒介渠道的可信度评价如何,对疫情期间本国和外国媒介的信任程度如何。此外,本文还将对媒介接触、新闻认知如何影响媒介信任判断的问题展开考察。
二.理论背景
1.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使用与信息需求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伴随着短时间内的大规模人群致病、致残或丧生,面对紧急状况与巨大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通过获取各种信息,减少信息弱势,降低风险感知,并形成对疾病的主观认知与行为决策(Li & Liu, 2020)。作为公众获取疾病信息的重要来源,不同的媒介渠道提供疾病动态、防护措施、最新政策、行动建议等重要信息,帮助人们减少信息焦虑(Choi et al., 2017)。
媒介使用反映的是个体日常使用和接触媒体的情况,包括媒介使用类型,媒介接触的时长、频率,媒介使用偏好等(Wilczek, 2018)。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使用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通常而言,人们往往会增加对媒介的使用,如增加使用时长、增加关注度、扩大获知信息的体量,采用更多类型的媒体和渠道来获取信息(贾哲敏,孟天广,2020)。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人们接触的媒介类型丰富多样,囊括专业新闻媒体、公众社交媒体、聚合媒体、医学媒体和政务媒体等多种不同渠道(李晓静,2020)。不同的媒介类型丰富了公众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但其各自的定位与作用也存在着一定差异。比如,报纸等专业新闻媒体通常被认为能够较好地传播疾病信息,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与风险意识,而电视能够更好地提升低教育程度受众的信息理解水平与预防行为能力;在对公众预防性行为的影响程度上,研究证实社交媒体的影响程度最高,新闻媒体与聚合媒体次之,而政务媒体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低(Li & Liu, 2020)。
使用与满足理论表明,受众的媒介使用往往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个人在社会与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某种需求,期望通过媒介的接触与使用得到满足(Rubin & Alan, 1993)。随着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往往根据自身需求和偏好来配置个人化的媒介菜单,呈现出明显的媒介使用偏好(喻国明,杨颖兮,2020)。有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政务媒体如中央级权威媒体也是人们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是专业自媒体等市场化机构媒体则较为小众(楚亚杰等,2020)。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媒介使用的特殊性,本研究聚焦媒介活跃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以期了解这一特殊时期,中外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偏好与媒介需求,以及这种偏好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分析不同的媒介使用对其新闻认知与后续的媒介信任产生的影响。
2.新闻认知与新闻真实
在媒介与信息多元化的背景下,考察受众如何对新闻真实性作出判断,显得尤为重要。新闻真实性代表新闻媒介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必须真实、全面、准确,表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李良荣,2013:42)。作为新闻的生命与核心,新闻工作必须坚持以真实为起点,保证新闻报道方式、报道内容等方方面面的真实准确性。在疫情背景下,公众需要通过真实可靠的新闻信息获取对疫情现状的基本认知与判断,各种疫情防控信息更是不少公众获得自我防护知识、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资源。
从新闻生产的视角出发,新闻真实重点关注的是“报道真实”的特征及其实现路径(杨保军,2016),即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符合程度,强调“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二元对应关系。虽然从媒介建构的理论视角来看,新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行为,新闻活动把发生的事件转变为新闻事件,并从日常生活中选取材料加工成故事,构成了新闻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塔奇曼,2008:175)。但新闻生产的行为应是对现实本身的建构,在新闻真实性的要求上,强调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相互统一。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受众的主动权与选择权得到极大提升。研究发现,个人首先会基于自身对信源与信息的判断来评估新闻真实性,如果仍不能提供明确答案时,他们才会转向外部资源去验证新闻的真实性(Tandoc et al., 2018)。因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新闻受众对于新闻真实性评价的重要性,逐步完善新闻真实性的评价体系,在以往“报道真实”的基础上逐渐纳入受众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对于新闻内容而言,如果受众不相信,那么真实的新闻内容对于受众而言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了(杨保军,2017)。因此,除了事实真相,受众的新闻真实观也是实现新闻真实的关键所在。
然而,事实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过程,人对事实的认知也是一个过程,因而新闻真实通常被界定为一个过程(陈力丹,2007)。在媒介技术的变革下,受众对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解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此次疫情中,媒介渠道异常丰富,事实与谣言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新的“信息疫情”。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活跃受众,大学生们在疫情期间关注哪些新闻信息,又根据哪些因素来衡量媒介新闻的真实性,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3.媒介使用与媒介信任
媒介信任,也被称为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中西方大量学者都在该领域进行了持续、系统的研究。一般来说,媒介可信度指媒介机构、媒介内容和媒介渠道被公众所信赖的程度,通常用以评价公众对信源、信息和渠道可信度的感知程度(Metzger et al., 2015;Sundar, 1999;李晓静,2019:11)。
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影响媒介可信度评价的诸多因素,其中媒介使用是媒介信任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通常来说,媒介的使用频率越高,对该媒介的信任程度往往也越高(Zhang et al., 2019),但具体媒介的可信度因研究对象与研究议题表现出明显差异,弗拉纳金在新媒体情境下检验了维基百科与更专业的网络百科全书(即Citizendium和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的可信度。研究发现,尽管很多人将维基百科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和渠道,使用越来越普遍,但人们对它的信任度并不高,尤其是在与在线大英百科全书的对比实验中,人们强烈地依赖专家生成或审查的内容。同样地,博拉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拥有大量点赞的专家来源的收益框架信息被认为是最可信的信息(Borah & Xiao, 2018)。
着眼于本土环境,有学者在中国社交媒体情境下对比分析了社交媒体与web1.0媒体、传统媒体的可信度,研究同样发现,尽管社交媒体被使用得越来越普遍和频繁,但其可信度却在三者中最低,传统媒体仍然被认为最可信(Li & Zhang, 2018)。由于大学生群体的整体文化水平高于普通公众,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媒介的影响力格局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发生变化。不少实证研究已证实,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兼备多种媒体渠道与信息来源,日益成为大学生们认为可靠的信息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媒介的可信度评价已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宋欢迎,张旭阳,2016;周勇,钟布,2019)。由此可见,媒介可信度不仅包括受众的认知态度,随着个体的主观判断与评价而有所差别,也是一种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Metzger et al., 2015;李晓静,2019:41),应当基于特定环境与特定群体展开考察。
基于此,本研究期望通过针对中外大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一方面弥补传统媒介可信度研究侧重量化研究的局限,能更深入地揭示大学生们在疫情期间对于媒介渠道、媒体从业者以及不同国家媒体可信度的判断及原因;另一方面,能够为重大公共事件中的媒介可信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研究素材。
三.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1)媒介接触:中外大学生在疫情中如何选择并使用各种媒介渠道?他们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各类媒介提供的信息能否满足其需求?
(2)新闻认知:中外大学生对疫情新闻关注的重点有哪些?他们是如何对新闻的真实性作出判断的?
(3)媒介信任:中外大学生对疫情期间的不同媒体渠道、新闻从业者的可信度评价如何?对中国和外国媒体的信任程度如何?为什么这样评价?
2.研究方法
已有的疫情相关公众的信息行为与媒介表现的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如问卷调查)进行,优点在于能够快速了解公众在多方面的态度、行为并进行统计分析,但量化方法不适合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与解读。对一些需要深入、丰富地描述和解释的问题,采用质化研究方法更为合适。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深入探讨新冠疫情下中外大学生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情况,因此,本文设计了在线焦点小组访谈的研究方案。
研究者在华东地区某重点大学线上招募访谈对象,抽样标准为质化研究常用的分层目的性抽样,保证每个小组内至少有10-12名具有相同背景的参与者(陈向明,2000:220)。访谈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将被访者按照国别进行分层,然后再在国别基础上进行目的性抽样,以便了解每一个同质性较强的层次内部的具体情况,进而再进行具体比较和多维探讨。
经筛选,最终参与本研究焦点小组访谈的受访者共有33人。为了减少受访者之间经验和语言方面的差异,保证组内深入讨论,研究者将受访者按照国别分为中国和外国大学生两组。其中,中国大学生组19人(M年龄=20.79岁),外国大学生组14人(M年龄=21岁)。组间受访者国别差异显著,组内受访者较为同质,符合焦点小组访谈的基本要求。研究者根据研究主题事先准备了访谈提纲,内容包括受访者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媒介接触及排序、新闻价值与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对不同媒介及从业者的可信度判断等。受制于疫情因素,焦点小组访谈在线上Zoom会议室进行,主持人根据访谈提纲引导受访者进行自由深入的讨论,每组访谈时间均为1.5小时左右。焦点小组访谈样本的构成如(表1 表1见本期第80页)所示。
四.研究发现
(一)疫情中的媒介使用
1.媒介接触与使用:社交媒体成为首要选择
访谈发现,中国大学生在疫情期间常用的媒体渠道为社交媒体与主流新闻媒体。大部分受访者提到,会首先通过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快速及时地获取疫情最新信息,再通过有一定报道深度和专业性的中国新闻媒体(如澎湃、三联周刊、第一财经等)和西方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CNN等)来获取更全面的疫情相关资讯。除此之外,不少受访者还提到了丁香医生、微医等医学媒体,这些渠道凭借实时的疫情感染数据和防护、辟谣等专业知识,成为不少中国学生获取疫情相关资讯的重要途径。
与中国受访者类似的是,外国大学生的常用媒体渠道同样为社交媒体与新闻媒体。但不同于中国学生的多渠道并行使用,外国大学生更偏向使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来了解本国及全球的疫情信息。在新闻媒体的接触上,本土化特色更明显,如泰国的泰叻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等本国新闻媒体,都被外国学生较多提及,而对本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他们并不关注,医学媒体也未被提及。
总体而言,社交媒体是中外大学生受访者首选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疫情信息获取渠道。访谈发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媒介使用习惯,如受访者LEI提到,“微信和Facebook是我每天都要登录的软件”;受访者XFW也指出,“平时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习惯延伸到了疫情期间,使得我把微信排在所有媒介渠道前面”。二是社交媒体内容多元丰富,它以公共传播为主要特点,个人通过互动的形式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因此社交媒体平台几乎汇集了各类渠道的疫情信息,满足了个体的各种信息需求。三是社交媒体的人际传播属性。不同于其他媒体渠道,社交媒体能够同时满足个体的社交需求与信息需求,实现疫情期间人际沟通与信息传播的多重目标。比如,受访者CXL就表示:“微信提供了线上人际交流的渠道,使得我在疫情居家期间,也能够和朋友、同学讨论疫情信息,发表个人观点,同时满足了我获取信息、交流与表达自我的多种需求。”
可见,面对疫情期间丰富的媒介渠道选择,个体媒介接触会因媒介属性和自身的使用习惯等因素出现差异,但在社交媒体的接触上,中外大学生也存在着一定共性。
2.疫情信息的使用与满足:认知需求与信息过载
不同的媒介接触往往与受众的需求有关。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受众基于特定需求进行媒介接触活动,在媒介接触与使用中得到需求的满足。在面对疫情期间巨大的不确定性时,个体往往需要通过媒体来获取疾病信息,降低对环境感知的不确定性,并形成对于疫情的主观认知与行为方向。受众使用媒介的需求主要包括:认知需求、情感需求、个人整合需求、社会整合需求与疏解压力需求。基于此,本研究探析了疫情期间中外大学生的主要媒介需求。
访谈发现,33位受访者中,有30位受访者都将认知需求列为首位。面对疫情这个陌生且动态变化的话题,个体在隔离在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媒体信息了解疫情发展状况,满足自我认知的需要。受访者YXY就谈道:“新冠疫情对我而言是陌生的、非专业领域的事物,同时也是记忆中首次亲历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政府会采取何种政策,这些都是陌生的,需要通过获取知识、信息才能解决我的困惑。”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情况,受众的信息需求也是多样的,各类媒体渠道呈现的不同信息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信息互补作用,满足了受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从受访者反馈来看,各类媒体在疫情期间所提供的全面、多角度的疫情资讯,基本能够满足其认知需求。受访者ZIH就谈道:“因为新闻频道与发布会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我不是每一次都能准时观看,这时候社交媒体和政务媒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旦错过,我只需要打开手机上任何一个社交App,就能看到有哪些最新的疫情信息。如果我想要了解相关详细内容,报纸上的新闻内容也可以一览无遗,甚至比卫生部门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更加全面、详细。”
然而,媒介海量信息的同时涌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信息过载”问题。过度沉浸在与疫情有关的负面信息流中,也容易让受众陷入应激状态,并进一步加重焦虑情绪。这一点也得到了不少受访者的认同,如受访者BVR就谈道:“我严重认为分分秒秒不停地在关注信息,尤其是被新增和死亡人数的数据绑架是一件很恐怖且无意义的事,可以适当地获取一些相关信息,目前的信息有时候过度了,反而会影响生活,疫情的存在本身影响就够大了,没必要再另外给自己添加恐怖情绪。”
可见,受众基于认知需要,主动从不同媒介渠道获取信息,形成对疫情现状的主观认知与行为指导,差异化的信息内容满足了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信息过载与信息焦虑的问题。
(二)疫情中的新闻认知
1.新闻信息关注:动态信息与社会支持
信息需求是公众接触与使用媒介的重要原因,面对海量的疫情信息,受众往往会结合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么,受众具体关注哪些信息?结合访谈可发现,中外大学生对疫情中的信息关注聚焦在两个层面:
一是对疫情动态(包括疫情数据信息、动态新闻)的关注,如实时更新的疫情数据、世界各地疫情感染情况与防疫政策信息等。这类信息直接反映疫情的发展动态与趋势,能够帮助受众进行认知判断与行为决策。受访者LYY就谈道:“国内外疫情变化是我在疫情期间贯穿始终的关注点,因为我们需要关注时刻都在变化的情况,才能理解、分析、判断当前形势和未来走向。病毒是流动的、快速传播的,所以每一个区域的疫情都不应该被忽略。”
二是对社会支持类特殊信息(包括疫情防护措施与个体新闻报道等)的关注,如新冠病毒病理研究、日常防护类新闻,以及前线医护人员实况、志愿者故事等。这一类信息给予受众社会帮助,能够帮助受众进行心理调适,获取情感上的慰藉与支持。如受访者GY提到:“在疫情这样的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是低落的,包括我自己也时常会陷入不安、忧郁的情绪中。因此一些正能量的、积极的新闻报道可以塑造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希望。”
受访者PUN也补充道:“武汉日记中,普通人最质朴的记录不输很多专业媒体传递的爱与感动。无论是一线医护、建设者,还是志愿者,都在为国家奉献,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很令我很感动。”
可见,公众在疫情下的新闻信息关注既包括整体形势变化与趋势走向,也包括个体的防护措施与生存处境,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不同新闻信息的价值和意义。
2.新闻真实性判断:兼顾信源与信息内容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闻信息,尤其是在谣言丛生的处境下,公众又如何进行真实性判断?访谈发现,多数受访者认为,本国新闻媒体的真实性整体表现较好,能够客观报道事实,阻止谣言传播。不少媒体(如丁香医生推出的辟谣板块、马来西亚的打击假新闻网站SEBENAR.MY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谣言和假新闻的传播,保障公众获取真实的疫情信息。
受访者也存在一些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质疑。在中国学生中,质疑集中在疫情尚未大规模爆发的初期阶段。受访者认为,一些新闻报道存在对疫情实际感染人数谎报瞒报的情况,严重不符合真实性原则。在媒介渠道层面,多数受访者认为官方新闻媒体的真实性要高于社交媒体,但新闻媒体也存在不够客观、真实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外国受访者的叙述中。比如,韩国大学生受访者结合“朝鲜TV”指出了媒体报道的政治倾向问题,日本大学生受访者结合日本奥运会背景谈到的媒体不实报道等,均反映出不同媒体渠道在新闻真实性的表现上存在差异。
在新闻真实性的判断上,中外大学生都表示信源很重要。对于公众而言,在接触信息时首先会关注信息内容由谁生产,是否具有权威性与专业性,信源是判断新闻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受访者YXY谈道:“看防疫政策报道时,信源是否是政府发言人;或者深度报道中的采访,受访者的身份回答相关问题是否可信;又或者涉及专业性的医学问题,各执一词的专家们,哪些专家可信、有无政治立场干扰等都是我考虑的因素。”
此外,信息内容本身也是受访者考虑的重要因素。报道内容中的基本信息是否经得起核实,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是否合乎逻辑,以及是否与其他公开信息一致,也是受众判断新闻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受访者MDN指出:“对于医疗相关的信息,我持怀疑态度,会主动去找寻和搜索报道中公开的信息来源、相关专家、药物信息等,进行综合判断。”
受访者YEP也补充道:“疫情期间,重要的、突发性的、政策性新闻,都会在多家新闻媒体反复出现,如果一则普通新闻(非独家深度报道)在三十多家媒体中都没有找到相似的内容,说明这则新闻很可能有问题。”
可见,新闻真实性作为新闻信息的重要价值,受到公众的普遍重视。在新闻报道整体真实性较好的背景下,仍然存在着媒体报道良莠不齐的情况。受众会结合信源与信息内容对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评估判断。
(三)疫情中的媒介信任
过往研究已从信息来源、媒介从业者、媒介渠道、新闻内容等各角度开展了有关媒介信任的实证调研。本文主要从疫情期间的媒介渠道、媒介从业者与不同国家的媒介可信度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媒介渠道可信度:政务媒体和新闻媒体最可信
访谈发现,中国大学生最信任政务类媒体(8位受访者将政务媒体排在首位,4位受访者将政务媒体排在次位),凸显了中国受众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里对政府信息供给的高度认可。以国家卫健委为代表的政务媒体资质权威、专业性强,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有保障。受访者普遍表示,政务媒体代表的是“官方”,意味着更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政务媒体发布的信息。
外国大学生则更信任新闻媒体,尤其是在报纸仍使用较多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受访者主要认为,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媒体,新闻媒体有把关人的身份,报道内容有来源和依据,报道更专业和全面,所以可信度更高。
此外,访谈还发现,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社交媒体被受访者评为可信度最低(16名中国受访者与8名外国受访者均把社交媒体的可信度排在最末)。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准入门槛低,海量用户自发生产上传的内容和宽松的监管极易滋生虚假新闻。此外,社交媒体互动性强,信息传播与流通速度快,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容易导致虚假信息进行快速广泛的传播,这也极大降低了受众对其的信任程度。
2.媒体从业者可信度:一线记者高度可信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获取新闻信息是社会公众在灾难面前保持知情、消除恐惧、积极防护必需的途径,媒体从业者则是保障这份知情权的重要力量。访谈发现,中外大学生对于其所在国家的新闻从业者(尤其是一线记者)的可依赖性和专业性充分认可。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新闻从业者通过还原疫情潜伏至爆发过程、记录病患及医护人员经历、科普卫生防护知识等多种报道,满足了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帮助甚至指导人们及时应对公共卫生风险,表现出高度的新闻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效提升了民众对于媒体从业者的信任与依赖感。尤其是深入一线的新闻记者,往往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医院、医护和患者的真实情况,报道疫情最新信息。不少受访者均表示被“圈粉”并愿意主动购买其新闻产品。
同时,由于媒体机构的多样性与从业者的差异,受访者对于记者和编辑之间的可信度评价表现出明显的分化。深入一线的记者得到了受访者的认可与信赖,而作为新闻信息的二手加工者,部分新媒体编辑与自媒体从业者出于利益考量对报道框架进行修饰调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信息的真实性,扩大了谣言与假新闻的传播范围,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不少受访者对此表示质疑与否定。受访者XYL谈道:“我国的编辑所表现出的可信赖性与专业性并不如记者,尤其是当下新媒体在传播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部分新媒体编辑为提高新闻点击率与阅读量,会想方设法将新闻编辑得更具有话题性,吸引人眼球,常在标题中省略重要信息或前提条件,像‘双黄连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等,最终造成误导读者、引导错误风向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当好把关人。”
由此可见,媒体从业者作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和把关人,其可信度直接影响着受众对媒介内容与媒介渠道的信任度。
3.不同国家的媒介可信度:中国媒体的疫情报道更可信
由于不同媒介的特性不同,受众对于不同国家体制下的媒介可信度判断往往也会有所差异。访谈发现,多数中外大学生都接触过非本国的媒介渠道,并从中获取疫情信息。但对于本国疫情,受访者大多倾向于相信本国媒体的报道。
关于中国的疫情,中外大学生受访者都表示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在疫情期间,处于抗疫一线进行报道的多是中国媒体,如财新、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报等,在疫情初期派记者、编辑前往武汉,获取一手资料,因而相对于境外媒体工作者,中国的媒体从业者拥有更可靠的信源。此外,由于疫情初期的感染爆发地集中在中国,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加入了一些讽刺、批评、夸张甚至抹黑,不少受访者指出,这种带有偏见的报道立场让其无法信任。
受访者CSY就谈道:“无论是境外媒体还是中国媒体,彼此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客观、不含偏见,在采访对象的选择、采访话语的引用、新闻内容的编排上都会有意识地偏向己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境外媒体在疫情中表现的偏见更为明显。”
假新闻是智能传播时代全球媒体都面临的普遍问题。本次疫情期间,外国媒体同样也出现了谣言、虚假信息等类似现象。疫情期间,发布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甚至危险信息的德语网站数量大幅增长,互动量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德国联邦卫生部的100倍。不过中外媒体都开设了大量信息核实、辟谣平台,为遏制假新闻的传播扩散做出了很大努力,维护了媒体的良好形象与社会秩序,有效提升了媒介信任与社会信任。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使用与满足、新闻真实、媒介可信度等经典媒介理论,从受众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外大学生的在线焦点小组访谈,深入了解疫情期间中西方年轻人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的表现与原因,为研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体传播问题提供了一手研究素材与研究结论。本文的发现表明:
第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使用既特殊又多元:从媒介使用类型来看,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与新闻媒体在重大公卫事件中的作用值得重视,医学媒体异军突起,成为重要补充信源。内容的丰富性与平台的交互性使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媒介渠道,而新闻媒体的专业性和报道深度也在疫情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此外,医学媒体也凭借专业背景成为年轻人获知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重要补充信源。总的来说,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的媒介类型从不同角度满足着受众的信息需求,凸显了智能媒体时代“积极受众”主动选择信息、参与媒介内容生产的新特征。与此同时,大学生更加倾向于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反映出社交媒体潜在的广泛受众。这提示我们,未来的信息传播可更多地借助社交媒体平台来提升信息传播效果,提高疫情信息传播的可及性。
第二,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受众接触媒介的首要需求是获取信息的认知需要,但要谨防信息焦虑问题。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由于情况危急且不确定因素过多,居于信息弱势的受众需要通过信息获取来满足认知需求、缓解恐慌情绪,获得社会支持。此次疫情中,丰富的媒介渠道和差异化的内容实现了信息互补的效果,满足了受众在事件中及时获取信息、了解和应对环境变化的需要,充分说明了危机状态下信息及时传播的重要性。但是在封闭环境中接触海量信息,也带来了信息过载和情绪焦虑的问题,加剧了受众的心理压力,值得后续开展具体研究。
第三,动态信息和社会支持类信息(如数据新闻、卫健知识和人文关怀的报道),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年轻人最关注的信息,信源和信息的真实可靠是突发事件中新闻的生命。从社会认知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类行为又反作用于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本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大学生主要关注疫情数据信息、新闻动态、防护措施和个体新闻四类信息,前两者帮助受众进行认知判断与行为决策,后两者帮助受众获得社会支持,进行健康防护和心理调适。未来的突发事件中,媒体可重点关注上述几类信息的报道,更好地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受众获取信息与社会支持的双重需求。
第四,媒介可信度作为一种具体情境下的现象,随受众、环境、情境等具体条件变化而变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信任问题值得具体研究。本研究聚焦新冠疫情中大学生群体的媒介信任,为具体情境下的媒介信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结论。研究发现,疫情期间中外大学生的媒介信任呈现出明显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媒体的总体可信度较高,大学生更信任政务类媒体,而外国大学生更信赖专业新闻媒体。这两类媒体本质上都代表着专业性和权威性,反映出高学历群体更注重媒介资质的专业性。而社交媒体尽管被频繁使用,但其可信度评价则普遍偏低,凸显了公共危机时期人们对专业信息的高期待与高认可。
此外,中国媒体从业者,尤其是一线记者的专业性和可信赖性得到了高度认可,但部分自媒体编辑在疫情中编造谣言获取流量,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专业性尚需提升。中外大学生都信任中国媒体的报道,也凸显了中国官方媒体在公共危机状态下信息治理关键主体的角色,证实了中国媒体对外宣传的重要性,这对于纠正境外媒体充满偏见的报道、引导国内外受众正确认识突发危机具有重要价值。
需指明的是,本文囿于样本限制,聚焦于中外大学生群体,探究他们在特殊时期的媒介使用、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研究结果虽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素材,但并不具备外在效度,仅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前瞻性的探讨,期待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力丹,闫伊默(2007)。新闻真实与当前新闻失实的原因。《新闻传播》,(7),9-12。
CNNIC(2021)。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北京: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新冠疫情下中国公众的知与行——基于“全国公众科学认知与态度”调查的实证研究。《新闻记者》,(5),3-13+96。
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贾哲敏,孟天广(2020)。信息为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媒介使用、信息需求及媒介信任度。《电子政务》,(5),14-27。
李良荣(2013)。《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李晓静(2019)。《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媒介可信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李晓静(202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来源、媒介信任与防控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图书与情报》,(2),19-24。
宋欢迎,张旭阳(2016)。多媒体时代中国大学生媒介信任研究——基于全国103所高校的实证调查分析。《新闻记者》,(6),17-28。
杨保军(2016)。新闻真实需要回到“再现真实”。《新闻记者》,(9),4-9。
杨保军(2017)。论收受主体视野中的新闻真实。《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8),25-28。
喻国明,杨颖兮(2020)。接触、时段、场景:中国人媒介使用全景素描——基于“2019全国居民媒介使用与媒介观调查”的分析。《新闻记者》,(4),28-36。
周勇,钟布(2009)。数字时代的媒介信任——关于中国新闻工作者对网络信息与媒体新闻报道信任度的调查。《国际新闻界》,(7),81-85。
Borah, P. & Xiao, X. (2018). The importance of ‘likes’: the interplay of message framingsource, and social endorsement on credibility perceptions of health information on Facebook.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3(4)399-411.
ChoiD. H. , YooW. , NohG. Y. & Park, K. (2017).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risk perceptions during the mers outbreak in south kore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7)422-431.
FlanaginA. J. & MetzgerM. J. (2011). From encyclopdia britannica to wikipedia.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14(3)355-374.
LiX. & LiuQ. (2020). Social media useehealth literacy, disease knowledgeand preventive behavior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Chinese netizen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2(10)e19684.
LiX. & ZhangG. (2018).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Chinese social media: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30(1)79-101.
Metzger, M. , Flanagin, A. & Nekmat, E. (2015). Comparative optimism in online credibility evaluation among paren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59(3)509-529.
Rubin, & Alan, M. (1993). Audience activity and media us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0(1)98-105.
SundarS. S. (1999). Exploring receivers’ criteria for perception of print and online new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6(2)373-386.
TandocE. C.Ling, R.Westlund, O.DuffyA.GohD. & Zheng WeiL. (2018). Audiences’ acts of authentication in the age of fake new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Media & Society20(8)2745-2763.
Wilczek, B. (2018). Media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even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65(2)1-28.
Zhang, H.Du, J. & Wang, R. (2019). Media credibility: The impact of privately-owned websites on state-owned television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29(2)188-210.
李晓静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付强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王韬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健康与医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研究”(项目编号:19ZDA326)和201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8AX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