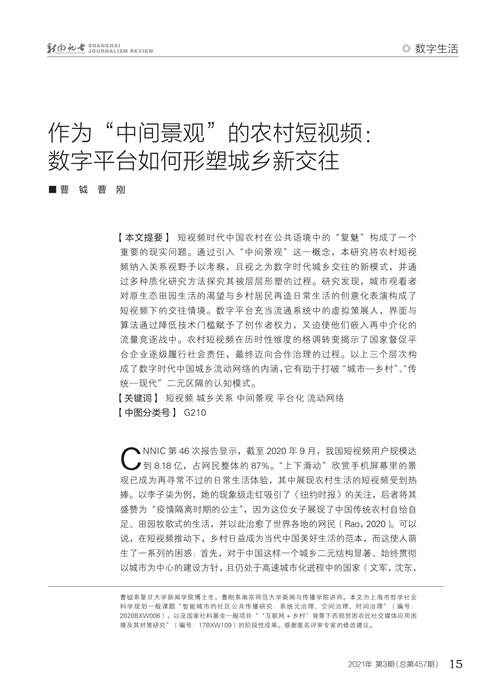作为“中间景观”的农村短视频:数字平台如何形塑城乡新交往
■曹钺 曹刚
【本文提要】短视频时代中国农村在公共语境中的“复魅”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通过引入“中间景观”这一概念,本研究将农村短视频纳入关系视野予以考察,且视之为数字时代城乡交往的新模式,并通过多种质化研究方法探究其被层层形塑的过程。研究发现,城市观看者对原生态田园生活的渴望与乡村居民再造日常生活的创意化表演构成了短视频下的交往情境。数字平台充当流通系统中的虚拟策展人,界面与算法通过降低技术门槛赋予了创作者权力,又迫使他们嵌入再中介化的流量竞逐战中。农村短视频在历时性维度的格调转变揭示了国家督促平台企业逐级履行社会责任,最终迈向合作治理的过程。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了数字时代中国城乡流动网络的内涵,它有助于打破“城市—乡村”、“传统—现代”二元区隔的认知模式。
【关键词】短视频 城乡关系 中间景观 平台化 流动网络
【中图分类号】G210
CNNIC第46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9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8.18亿,占网民整体的87%。“上下滑动”欣赏手机屏幕里的景观已成为再寻常不过的日常生活体验,其中展现农村生活的短视频受到热捧。以李子柒为例,她的现象级走红吸引了《纽约时报》的关注,后者将其盛赞为“疫情隔离时期的公主”,因为这位女子展现了中国传统农村自给自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并以此治愈了世界各地的网民(Rao, 2020)。可以说,在短视频推动下,乡村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美好生活的范本,而这使人萌生了一系列的困惑: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始终贯彻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方针,且仍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军,沈东,2015)而言,这多少有些奇怪;其次,如果我们联系几年前由“返乡书写”①引发的公共讨论,这种反转更令人惊讶,因为彼时人们所哀叹的正是中国农村无可挽回的衰败;最后,为什么在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日益现代化的农村中,短视频所勾勒的却更多是前现代的意象?
本文以为,回应上述问题首先需将研究对象置于城乡关系的视野中。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农村短视频展现了“城市用户围观农村创作者”的观看结构。②并且,这种观看涉及一系列舞台化的事件、空间、表演技术与配置,需要整个社会去组织,使之系统化(约翰·厄里,乔纳斯·拉森,2016:218)。段义孚的“中间景观”提供了一个在关系视野下审视农村短视频的概念透镜。在他看来,人类故事大部分可叙述为一种迁徙活动,即逃离原先的生存环境,而去追求更富饶的土地、更好的赚钱机会或是更优质的文化。而“中间景观”就是处于都市与自然两个端点之间、人为创造的人类栖息地之典范(段义孚,2005:29)。如果说传统的中间景观(如郊区、花园、主题公园)多为物理实体,那么短视频的涌现正使“迁徙”成为一种触手可及的新型感官体验。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数字化的中间景观揭示了怎样的城乡意象?它又是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形塑出来的?以上探索能为反思数字时代的中国城乡关系提供什么样的启发?
一、背景脉络:城乡意象的表征困境与新视角
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是一种产生于日常生活中,被社会集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它被同一组织内部的成员所共同拥有,并且成为群体成员之间沟通的基础(管健,2009)。按照传统唯物主义的理解,“乡村”与“城市”暗示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对立随着野蛮向文明、部落制向国家制、地方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0:56-57)。Williams(1975)的分析则更细致地揭示出“乡村”(country)与“城市”(city)被人为建构为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一方面,城市象征着现代的文明、发达、先进,而乡村则充斥着前现代的野蛮、愚昧、落后;另一方面,城市也被视为欲望、功利、冷漠的化身,而乡村因其淳朴、热情、善良的品质成为人们的慰藉之地。Williams认为,这种对文化情感与地理空间关系的自然化遮蔽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剥削的强化。而城乡二元对立的意象之所以根深蒂固,亦与古典社会学“传统—现代”的理想类型密不可分,它暗含了这样的预设:(1)现代与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一个人无法同时生存于两种结构中;(2)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阶段是线性的、必然的(项飙,2018:7)。
回归中国语境,城乡意象的对立还在于人们不自主地将“乡土性”构想为一种应对西方凝视的话语资源。这实际上是把《乡土中国》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某些属性扩大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本质特性,从而曲解了费孝通先生的原意,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乡土社会与城镇社会的有机联结,比如商品流通集散的城乡网络(陈映芳,2007)。如此的后果便是以“追思乡土性”来回应当代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问题,而无视城乡之间的沟通互动。以近年来火热的“乡愁书写”为例,其背后都预设了一个去历史化、纯粹本真的乡土社会。反映到学术研究上,人们又习惯性地将农民设想为沉默、失语的底层(张爱凤,2019),或去追问“农村出场”、“土味文化”是否本真,能否为自己代言等问题(顾明敏,2020)。
要想打破上述深陷于本质主义的表征困境,首先需重新理解“城市”。麦克卢汉(2000:132)曾谈道:“公路的改善把城市日益引向农村。当人们开始说‘驾车到乡下去兜兜风’时,公路就成了城市的替代物。”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已不再被构想为根据规模、人口密度、职业、环境等要素划分出的区域单元,而是由各种实体或虚拟的连接方式缔造而成的关系网络,它既是信息传递之网,也是社会交往与意义共享之网(孙玮,2013)。与之相对应的是,乡村也和城市一样,或密或疏地嵌入世界性网络之中。因此,当我们将城市、乡村视为共在于一个流动网络中的节点时,需要考察的问题就变成了——它们怎样因位置、传播技术的变化,调整节点间的关系形态,因而塑造不同的城乡意象(谢静,2016)?而在此过程中,什么样的交往模式正在生成,什么样的宰制结构又逐渐浮现?
二、分析框架:媒介情境论与平台化理论
个体对城乡意象的认知与评价需经由沟通成为社会表征。而此种沟通即为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人们需要界定情境,根据他人的回应调整自我认知,主动沟通以修正事件的意义,并在维持社会秩序、遵守共同准则的前提下,选择最恰当的行为表现出来(管健,2009)。这与Goffman(1986:2)所谈论的框架(frame)异曲同工,即追问我们对“社会事实为真”的感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梅洛维茨(2002:33)敏锐地觉察到了电子媒介在重塑社会场景方面的能力,并指出对人类交往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信息流动的模式。
短视频无疑展现了迥异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信息接触模式,民众需要通过手机界面在移动网络空间中维系远距离关系、学习社会化过程,并且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表演(performance)(约翰·厄里,乔纳斯·拉森,2016)。③根据Thompson(1995:83-98)对现代交往情境的划分,农村短视频属于“中介式准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的范畴。在此,一些个体为无限范围内潜在的接受者生产符号形式,而另一些人主要参与接受其他人生产的符号形式,生产者的人格特质是建立在“远距离可视性”基础上的,因而会获得一种明星人物般的“光晕”(aura)。那么具体如何分析新媒介环境下交往情境的特性?梅洛维茨(2002:66)抛出的三个问题可构成关键性的分析维度:(1)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削弱了社会场景与物质地点的传统关系;(2)媒介能允许人们后台、前台行为的最大差异;(3)媒介将不同类型的人分离、合并到不同或相同的信息世界的尝试。
不过,仅考虑日常生活交往这一端并不充分,因为框架背后往往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条件,这些庞大、坚固的机构不公平地分配着诸如权力、声望、社会资本之类的互动资源(Goffman, 1986:XV)。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应被视为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这是一种可编程的数字架构与生态系统,它以面向用户采集的数据为动力,由复杂、动态的算法机制驱动,旨在通过组织用户之间的互动塑造其日常生活实践(van Dijck et al., 2018:9)。平台通过数据化(datafic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选择性(selection)三种机制完成内部生态系统的构建。而“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则指涉数字基础设施搭建的过程,在其中连接性平台的运作及其技术逻辑愈发深刻地卷入到社会安排之中(van Dijck et al., 2018:19)。可以说,平台化注定是一个多元、动态、充满张力的过程,它由国家、平台公司、用户、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相互塑造,技术系统与行动者之间并非决定性的。
目前,欧洲的平台理论研究者已开始更系统地审视这些新现象,他们大致形成了由日常生活实践、数字基础设施、治理三重向度构成的分析框架(Nieborg & Poell., 2019;de Kloet et al., 2019)。参照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城乡居民围绕短视频的中介式准互动置于前端,平台界面与算法置于中端,国家治理措施置于后端,以此具体分析“中间景观”的形塑过程。
三、方法介绍:平台行走法
本文采用了Light、Burgess与Duguay(2018) 开发的“行走法”(walkthrough method)来探索短视频平台,这种方法鼓励研究者直接进入一个App的界面中,通过亲身实践检验其技术机制、文化指征,它能有效考察平台生态系统与日常生活实践的互嵌。行走法的核心在于通过放慢日常使用过程中的交互行为,观察与记录App的界面、功能及行动流,从而发掘交互的深层意涵。这是一种充满弹性的方法,足以将上述三重维度囊括其中。具体而言,它包括App外的材料收集与App内的界面漫游两大部分。前者涵盖了对于平台公司愿景(vision)、运行模式(operating model)和治理措施(governance)的调查,包括查询公开发言稿、科技行业报告、服务条款(term of service)、政府部门文件等资料。后者则要求研究者通过滑动屏幕、点击按钮、探索菜单、追踪关键用户等方式获取数据。田野日志、截屏、录音录像、访谈等方式均可生成数据集(Light, Burgess & Duguay, 2018)。
研究者从2019年8月注册账号进入抖音平台,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月的行走实践,包括观看乡村短视频、关注内容生产者、采集短视频文本、进行点赞和评论,参与直播互动,在线购买农产品等活动。我们还注册了两个第三方平台的账号以获取相关数据,并对8位农村短视频创作者进行了线上访谈。④一些具体的资料分析将在研究发现部分展开。
四、交往情境:围绕“美好生活”的展演与讨论
为了探究农村短视频的情境框架,研究者在平台行走中兼顾了话题标签、算法推荐机制以及第三方榜单数据,立意抽取了257个农村短视频进行扎根理论编码。编码过程试图回应梅洛维茨(2002:66)界定交往情境的三个问题,以发掘城乡居民围绕短视频互动所仰赖的框架。编码元素包括视频影像这一主文本,以及文案、评论互动等副文本,并得到表1 表1见本期第18页 。⑤总之,城乡居民的交往围绕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什么样的生活值得去过”而展开。
(一)时空体验:恒常农村对加速社会的反叛与迎合
短视频创造了非连续的时空体验,它标志着日常线性时空框架的中断。中介式准互动情境下的观众是时空旅行者,他们参与不同时空框架的谈判,并在不同时间、地点的中介体验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联系(Thompson, 1995:94)。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点开手机屏幕所进入的是一个恒常的乡村世界。不同于城市短视频倾向于打卡标志性的地理景观,在农村短视频中具体的地理位置总是模糊不清,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田间地头、古镇院落等意象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同样惯例化的还有村民的每日生活,“炊烟袅袅,夕阳西下”的景象几乎将我们拉回了传统农耕社会,这种稳定感正是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所稀缺的。而标志着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综合服务中心等则难寻踪迹。这种乡村田园诗往往被视为城市病的解药(Li, 2020),由此传统的世界被召唤出来抵抗“加速社会”对人的异化(曾一果,时静,2020)。这暗合了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叙事,事实上已有不少都市白领选择从一线城市返回老家农村,并用Vlog记录两种生活的差异。在此,农村作为对城市生活的反思而出场,它也被建构为现代人追寻主体性的家园。
而另一方面,这些景观往往是浪漫化的,它们借助精巧的摄影摄像技法展现出了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ity)色彩,拉开了与庸常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制造出梦幻般的观看体验。例如,创作者S会使用Gopro跟随拍摄以及无人机航拍,并且每个视频的后期处理和剪辑都要花费巨大的功夫,而这些是不被一般观看者所见的。即使是最普通的视频,比如对“采摘瓜果”、“农活劳作”等场景的抽帧处理,或是倍速处理饮食景象以表现狼吞虎咽的效果,它们都仰赖于后期剪辑。这些工作或由团队的专业摄影师完成,或是农村居民摸索、学习的成果。除此之外,农村短视频中嵌入的各种滤镜、背景音乐、字幕等中介化手段亦有助于调动观者的情绪,营造出电影化的观看体验。这实际上反映出农村短视频在制作上是反传统和高度现代化的,它迎合了长久浸润于加速主义媒介文化中的受众感官比率。就本研究选取的257个视频而言,其平均时长仅为28.6秒。农村短视频中“减速”与“加速”之间的张力就构成了观者的时空体验。
(二)后台前置:敞开的私人生活与粗粝的身体话语
短视频改变了社会行为“前台”、“后台”的关系。当手机作为一种拍摄媒介进入农村时,新的社会情境已然浮现。农村短视频实际上是一种“中介化日常生活”(mediated everyday activity),景观生产所采撷的正是行动者实际生活的一部分(Thompson, 1995:104),我们将其概括为“后台前置”的表演行为。从内容上看,创作者所展现的烹饪、吃饭、采摘瓜果等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生活,但其内在的“原生态”特质深受城市观众喜爱。事实上,如果创作者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反而会遭致留言中“演得太假”的质疑。从交往方式上,创作者不仅是带领观看者一睹乡村风光的导游,这些风光也指向其私人生活,在此他超越了功能性的社会角色,而通过维持一种“远距离的非互惠亲密关系”来扮演朋友与邻人。如果说传统农村对大众媒介的曝光始终持有恐惧心理,私人领域为人们撤出众目睽睽的围观提供了庇护之所;如今的短视频创作者则反过来热情地邀请观看者进入私人领域以此建构本真性的农村生活和本真性的自我。“在观看下表演”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新型社会化的过程。
厄里、拉森(2016:241)认为,被拍乃是一种社会情境;这种身体姿态是以表达为目的。我们注意到半数以上的农村短视频并无台词,只呈现了身体的话语。农村人的身体呈现出一种粗粝感,他们的日常行为、衣着,甚至表情都没有经过中产阶级礼仪的规训。而这种“放肆”反过来凸显了自由、潇洒的视觉体验,例如他们会在玉米地、溪水畔等任何地方唱歌跳舞;他们会表演“山顶上扔帽子”、“水下吃西瓜”等意想不到的技艺。视频镜头还经常将特写给到一些肢体动作,如布满茧的双手、健硕的臂膀、矫健轻盈的步伐。这些在日常劳作中所锤炼出来的身体特质,是久居写字楼、公交地铁、出租屋等闭塞空间中的城市身体可望而不可及的。段义孚的论述揭示了这种粗粝感对于城市观众的价值。在他看来,中产阶级优雅生活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泡沫,它虽然使人们远离了严酷的现实境遇,但也使“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心理潜入了生活各个领域,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束缚而非自由,于是他们渴望着重获以自然需求为条件、不存在多大幻想的“生命之重”(段义孚,2005:6,31)。而农村短视频所展现的农业劳作之艰辛,无疑使观看者重新体会到了这份切实的“生命之重”,它亦彰显了一种脚踏实地的美好生活叙事。
(三)调和认同:印象管理与道德叙事
短视频制造了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的环境,多样化、异质性的受众被折叠到同一空间中,这使表演者无法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以多种角色示人,而必须呈现一个可证实的、单一身份(Marwick & Boyd, 2010),并努力应对多种张力关系。从微观上,短视频创作者既要直面传统农村道德规范的规训,又要应对汹涌而来的陌生观众之凝视,并且寻求自我叙事的主体意识。从宏观上,他们也在努力调和城乡认同的叙事,凝聚关于“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中国农村传统的价值规范总是将陌生人置于正当社会关系的对立面,而在社交媒体上过于引人注目就会遭致人们的猜忌,以及对道德动机的质疑(McDonald, 2016:113)。农村女孩X就遭遇了这样的困扰,她在某则短视频的介绍中写道:“他们说我脸皮厚,到处卖脸,我认为在这个社会,比起钱,面子不值得一提,靠自己的努力不丢人,你们说呢?”该视频收获了一众关注者的支持和鼓励。微名人(micro-celebrity)的光环有时也会带来麻烦,例如陌生人大胆的求爱、隐私打探等行为会让X无所适从。不过,她渐渐学会了无视骚扰,而只对友善的留言予以回复。农村小伙M通过拍摄短视频创业,一开始也被周围的人指责“不务正业”,但随着他带领其他人一起致富,并受到官方的加冕,逐渐就成了村里的榜样人物。以上反映的正是勤劳致富话语对传统道德规训的调节,表演者通过将自己定义为“小微创业者”,从而与陌生人建立起“店家—顾客”的关系,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
农村短视频也在无形中构成了乡村较之于城市的“差异性优势”,其中既包括知识也包括情感的层面。例如,农村人对各种自然作物的讲解、家畜的养殖,以及农具的娴熟使用常常让观看者大开眼界。他们也经常与小动物相伴,与耄耋老者团聚在院子里,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家庭生活其乐融融的景象。对于许多长在农村,之后到大城市打拼的人来说,这种趣味盎然、无忧无虑的生活场景亦激发了童年记忆与乡愁。此外,阳光、健硕的男性与勤俭持家、心灵手巧的女性作为典型人物出场,也投射了道德意涵,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城市审美中的“小鲜肉”、“名媛风”等话语。
不过这种城乡认同仍可能随时卷入分歧的漩涡。例如,有主播直播了上游拦网抓鱼的过程,被大批观众指责“竭泽而渔”、“不注重生态平衡”,只得临时关停。而过分推崇农村生活的宜居性,反倒会带来“便利程度”、“医疗教育质量”、“财富机遇”等方面的质疑,有一位网友便谈道:“农村适合养老,在城市里才能赚到钱……有钱乡下是净土,没钱乡下尽是土。”这实际上反映出所谓的“逃向自然”(到农村去)依然是以“逃避自然”(城市化)为基础的,人们期望逃向的地方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这一迷人的概念(段义孚,2005:21)。
五、流通系统:作为策展中介的平台界面与算法
上述揭示城乡居民围绕“中间景观”而开展的一系列轻量级的社会互动,需要注意的是其背后还隐藏着复杂的技术基础设施,使这些交互痕迹数据不断被聚合、分析。Hogan(2010)指出,社交媒体空间中的人际交往并非仅是“表演”(performance),还包括“展览”(exhibition),最大的区别在于由虚拟策展人(curator)为特定的受众选取可供观看的数字档案,它借助过滤、排序和检索等机制调节了人们的交往体验。平台就充当了这样一种角色,它将社会活动编码、转化为计算架构,通过算法与格式化协议处理(元)数据,并以友好的界面加以呈现和解释(何塞·范·戴克,2018:25)。本部分将聚焦平台与用户的关系,期望从数据化、商品化、选择性三种机制入手探究界面与算法如何中介了数字时代的城乡交往。⑥
数据化(datafication)指涉了平台将以前从未量化的社会行为转化为数据的能力,它所捕获的正是使用者与界面的交互痕迹(van Dijck et al., 2018:33-35)。以抖音为例,其主页采用了单列下滑、自动播放的设计,用户可通过点击“关注”、“推荐”以及“同城”按钮进入视频观看。关注页是根据用户所关注的账户定制的内容流,但具体展览哪些账户的视频内容,与双方的互动黏性、被关注者的粉丝数均相关。推荐页是人们主要滑动的页面,其内容流由更复杂的算法掌控,它是对用户兴趣的建模,其中的参数包括视频点赞率、评论率、观看时长、同类型用户的喜好程度、观看历史、搜索历史、创作者粉丝黏性等等。农村短视频创作者并不了解算法机制,但每个视频的点赞数、评论数、转发数会量化人们对自身表演的社会评价。即使不为了盈利,它也赋予了生活被承认、被看见的意义。M就谈到,他一开始只是用来记录生活,当意外地发现某些视频能引发广泛关注时,心里有了前所未有的喜悦……于是便会想着法子拍出更好的视频。这也解释了许多创作者积极利用文案、台词引导观众发言,或直接在视频中请求点亮小红心、添加关注的目的。
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机制将在线与离线的物品、活动、情感、想法等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它在赋予用户权力的同时,也施加了剥削隐患(van Dijck et al., 2018:37)。农村居民的ICTs(信息与通信技术)资本普遍不高,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平台生态中实现自我价值,因为抖音平台提供了一套界面交互的支持系统,降低了技术使用的门槛。例如,人们可以进入“创作者服务中心”界面学习官方录制的教学课程,包括平台审核、推荐规则、内容创作、赚钱变现等系列内容。抖音还推出了提供一键生成式模板、使后期制作趋向“傻瓜化”的剪辑工具“剪映”。此外,平台购买了大量音乐版权并鼓励原创音乐人入驻,使短视频创作者可免费使用资源。最后,平台为扶持创作者变现设计了一系列按钮,如“商品橱窗”功能可使农民直接将农产品卖给消费者,在抖音内部完成电商闭环;“找我官方合作”按钮则可使广告商直接向创作者报价。以上连接元件(connectors)创造的友好环境招徕了大批内容生产者,使平台成为一个表演者与观众共在的流量剧场。然而,单枪匹马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抢占高额流量,本文访谈的8位农村网红中就有半数签约了MCN机构,它们充当了创作者、平台与广告主之间的中介,并将旗下艺人视为雇佣劳动力,不仅会收取5%-10%的抽成,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自由发展。2018年9月,抖音推出了更大的中介平台“星图”,广告主必须通过该平台与创作者协商广告投放事项,而创作者入驻“星图”则要满足10万粉丝、挂靠MCN机构两项条件。由此可见,不同于技术赋权宣称的“去中介化”,短视频生产者亦被卷入了层层“再中介化”的组织关系中,这是比“媒体—受众”结构更复杂的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s)(Nieborg & Poell, 2018),剥削与规训机制不可避免地嵌入其中。
平台的选择性(selection)机制取代了传统专业主义的把关,从而影响特定内容、服务和人员的在线可见性,其核心要素围绕平台规则(服务条款)、自动化技术(算法)与审核过程展开(van Dijck et al., 2018:41)。首先,平台公司以商业机密为由制造的算法“黑箱”暗示了分发推荐规则的不确定性。根据相关行业报告的调查,⑥抖音算法类似于一个信息流漏斗,上传的新视频在通过审核后会先投入200-300人的初始流量池,根据转发数、评论数、点赞量、完播率等反馈指标(粉丝数并非重点)决定是否推荐到更大的流量池。当逐级攀升至精品推荐池(人们常说的“上热门”)后,视频分发的人群标签会被弱化,成为无差别的大众传播。总之,它呈现出一种中心化、幂律分布的流量分发模式。创作者Q谈到,“每条短视频就好像是‘从零开始’,如果不精心设计就会掉队……如果把它当作一份职业的话会时刻充满危机感”。其次,抖音平台规范通过《社区自律公约》、《用户协议》、《隐私政策》三份条约发挥效力,它们规定了平台禁止发布和传播的内容、用户行为规范、未成年人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数据权限、违约惩罚等内容,这些条约会被内化到算法中。字节跳动的公开报告宣称,只要1%的内容出现问题就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工程师专门开发了低俗内容识别模型,并可人工调节算法权重打压广告、标题党,对低级别账号降权处理。⑥变动的审核算法也意味着创作者需时刻摸索“红线”,事实上因为偶然原因被下架视频已成为农村创作者面临的常态,例如夏天干农活时衣领过低会被判涉嫌色情,在水库游泳则会被视为危险行为。不过,他们也琢磨出一些对策来应对审核,例如用同音字、表情符号来规避抖音对于视频中不能出现“钱”字的规定。
总之,以上过程使农村短视频趋向于“偶然性的文化商品”(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人们需要不断根据用户反馈、平台规范、组织章程等变动的因素修订自己的表演(Nieborg & Poell, 2018)。对于久居于非数字的、稳定生活框架中的农村居民而言,这些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或许正如Crary(2013:100)所说,“人的物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个体不得不为更好地参与数字环境或适应数字化的速度来重新认识自我”。
六、平台治理:从“底层残酷物语”到“美丽桃花源”
上述三种机制的运作使平台公司深度卷入了城乡交往之中,平台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特征也愈发凸显。van Dijck等学者(2018:25-26)指出,平台中嵌入的价值、规范可能与既有社会结构中铭刻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因此公共价值问题会成为争论的核心。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将不仅充当执法者、监管者,并且作为公共价值的塑造者出场。此处涉及的正是平台治理问题,即如何优化多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健康、有序的集体活动创造条件(Gorwa, 2019)。就中国平台化的情况而言,国家的介入性作用已被视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关键因素,治理本身亦规范着不同行动者对于意义的协商(de Kloet et al., 2019)。本部分将透过农村短视频美学格调的转变来审视背后政企关系的优化过程,从而思考中国平台治理的意涵。佐证的资料来源于媒体报道、行业观察报告以及政策文件。
农村短视频兴起初期,平台公司“唯流量论”的市场圈占逻辑与国家监管的缺位互为表里。快手是最早下沉到农村做短视频社交的平台。根据相关资料的梳理,其用户流量在2014年春节后开始井喷。当一线城市务工者将App传播到老家后,春节返程的地理区隔再次切断了城乡联系,使快手在农村地区野蛮生长。⑦直到两年后,人们才因一篇题为《残酷底层无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自媒体文章见识到了这种光怪陆离的景象——快手里的农村充斥着生吃异物、花式自虐、早熟儿童、黑社会讨债等博眼球的表演。以喊麦红人MC天佑为例,其歌词中频繁出现的“兄弟”、“称霸”、“金钱”、“女人”等意象直指对丛林法则的推崇。这种价值取向既冲击了传统农村的道德秩序,也与现代文明的期许相悖。如作者所述,“快手展现的6.74亿被遗忘的农村人口,是与北上广深没有共鸣、交集的世界” ⑧,早期农村短视频的扩散建立在城乡鸿沟的基础上,这种“不可见性”使其免于卷入公共领域。与此同时,平台试图采用“技术中立”、“避风港原则”等话语策略规避企业社会责任。⑨另一方面,国家监管仍以单边的内容治理为主,将2007年出台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作为规制依据。当它面临大量低门槛、个体化、碎片化的UGC短视频内容时,难免捉襟见肘。监管的缺位亦使商业资本趋之若鹜,2017年快手得到3.5亿美元的投资,用户规模突破6亿,今日头条旗下的西瓜视频、抖音等应用也陆续创立并迅速抢占下沉市场。[10]随着短视频逐渐成长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公共领域,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和行为异化被进一步放大,诸如“传播涉毒歌曲”、“教唆粉丝谩骂”、“全村最小妈妈”、“黑社会讨债斗殴”等低俗内容[11]严重影响了国家对“道德互联网”(moral internet)的建构,并挑战了新技术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合法性(McDonald, 2016:144, 182),这引发了政府牵头的运动式治理。在2018年,国家网信办依法查处MC天佑等一批违规主播,约谈平台负责人,要求暂停算法推荐功能,下架问题产品,勒令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应用。[11]以上“组合拳”揭示了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政企发包制”特点,即政府将网络事务的具体治理权发包给非公有制企业,并附加高强度的负激励,同时自己保留监督权和奖惩权。这样既规避了产权安排的约束(平台为非公有制单位),也节省了直接管理平台的治理成本,当然它以政企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为前提(于洋,马婷婷,2018)。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接连发表社论占领舆论高地,将短视频乱象归咎于“平台公司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缺少总编辑和把关人的媒体成为纯粹的流量平台”,并转而倡导“用主流价值驯服、驾驭算法”。[12]上述运动式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以“元治理者”的身份推动企业形成合乎公意的“个体自治”(肖红军,李平,2019)。它虽然属于事后治理的范畴,但首先明确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要求,将农村短视频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纳入道德关照之中;其次在治理实践中总结了经验,为针对性规制的出台奠定了基础。2019年1月,《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与《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两大专项条例出台,明确了内容先审后播、优先推荐正面内容、积极引入主流媒体和党政军机关团体账户、建立总编辑内容管理负责制度和审核员队伍。[13]由此,短视频平台治理完成了从运动式向常态化的过渡。
如果说前述治理还落在外部监管、内部自治的层面,那么在第三阶段政企关系逐渐迈向合作共治,最突出的便是平台公司推出的扶助三农短视频补贴计划。[14]这不仅紧随2018年国家首创的“农民丰收节”,还在宏观层面响应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战略”。CNNIC第45次报告显示,超过500万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人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收入。用户实践亦是在平台的社会期许框架下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涌现出来的农村微名人不再展演“底层物语”,而是因其对美丽乡村的“记录”被主流媒体加冕为“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言人。[15]与此同时,国家政策的推动使“返乡创业”悄然取代“进城务工”话语,[16]而短视频行业相应地成为吸纳大量闲置劳动力的保障。我们可将上述话语实践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等聚集区环境差”、“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一线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推动相关产业外移”等表述相关联,可以窥见新农村建设仍然与城市发展的需求息息相关。总之,治理促使平台企业从遵守“底线要求”迈向“贡献优势”,通过发挥社会资源整合配置的功能带动金字塔底层(BOP)实现自我价值,解决社会问题(肖红军,李平,2019)。
综上所述,农村短视频从“底层残酷物语”到“美丽桃花源”的格调转变背后蕴含着政企关系导向的平台治理。具体而言,它是平台公司在国家逼促下认识到其社会责任,并履行不同层次责任的过程。随着平台嵌入整个社会的肌理,国家逐渐完成了从事后整治到设定规范,从政府治理到发包平台,从内容管控到全面治理的体系化建设。其结果是,平台放任自由环境下滋生出的“适者生存”江湖崇拜被国家规训下的“勤劳致富”价值观所取代,城乡割裂的表征意象由此转化为城乡融合。
七、结语:数字时代的中国城乡流动网络
短视频时代中国农村在公共语境中的“复魅”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通过引入“中间景观”这一关系性概念,本研究搭建了一个嵌套式的分析框架以阐释农村短视频被多元行动者形塑的过程(图1 图1见本期第24页)。它囊括了“城市观众—农村创作者”、“平台—用户”、“国家(政府)—平台”三组关系的复杂互动,并且每一层互动都呈现了信息流、资本流、符号流、商品流在结构中的运作,而建立在交往情境、流通系统、平台治理三个范畴之上的正是数字时代中国城乡的流动网络。具体而言,首先,城乡居民围绕着对当代“美好生活”的想象展开交往。农村创作者通过操演一系列视觉符码建构了原生态、浪漫化的乡村生活,使城市观看者获得了中介化的视觉消费体验。这种“后台前置”的表演亦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再造,它逐渐模糊了艺术、生活和幻想之间的界限。在此过程中,新农人需在本地居民、网络微名人之间调和身份认同,并努力弥合城乡裂痕。其次,这种交往体验是由平台界面和算法作为“虚拟策展者”来调节的。通过数据化、商品化、选择性三种机制,平台既降低了技术门槛,从而赋予每个农村居民成为创意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又迫使他们为竞逐流量而陷入多边市场的剥削关系与规制审查的风险当中。最后,农村短视频历时性的格调转变揭示出国家推动的、“刚柔并济”的平台治理策略。一方面,网信办将具体治理权发包给平台公司,并通过约谈、整改、下架、永久关停产品等惩戒手段监督平台与创作者;另一方面,官方媒体对符合国家意志的短视频创作者予以加冕,并联合平台发展战略、引导公众舆论,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渗透到整个社会中。以上也反映了中国平台化进程的技术政治色彩——虽然每个人接收到的是个性化订制的短视频信息流,但国家意志仍可以塑造“千人千面”之上、跨平台性的公共价值与美学风貌。
数字时代城乡流动网络突出的价值还在于深刻冲击了“城市—乡村”、“传统—现代”的二元区隔认知模式。某种意义上,它呼应了卡斯特(2001:505-506)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之意涵,即空间通过流动性的运作把同一时间并存的实践聚拢起来,流动支配了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由此挑战了传统的线性秩序。农村短视频所展演的田园生活无疑是传统、复古主义的,但人们所参与的交换网络、技术对主体的形塑,以及背后由国家推动的平台治理,都是高度现代化和组织化的。这两者并非“再现”与“本真”的关系,而是相互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所以,传统与现代的并行、城市与乡村的互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然是大势所趋。■
注释:
①“返乡书写”体的兴起以2010年梁鸿出版的《中国在梁庄》,2015年春节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以及2016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第一人称纪实作品为代表。它们都以知识分子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农村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一系列危机,比如留守儿童、养老困境、治理真空、医疗保障教育资源的缺失,以及人情淡漠等种种问题,并抒发了对曾经家乡的缅怀之情。
②以短视频龙头平台抖音为例,根据QuestMobile的报告(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new/58),其一、二、三线城市用户的比例超过七成。笔者亦借助“抖查查”“新榜”等第三方数据平台查询了农村网红粉丝的地理位置分布,发现大多数来自于城市,加上后续在平台行走实践过程中对留言用户个人信息的查看,基本上印证了这种观看结构的存在。
③此处的“表演”并非指涉“社会行为的真或假”,而是在剧场社会学语境下谈论的。其侧重描述的是人们在与陌生人互动的情境中扮演某些社会角色,从而期望达到特定的目的。
④本文选取了新抖(https://xd.newrank.cn)与抖查查(https://www.douchacha.com)两个第三方平台,它们通过与抖音API接口的协议获取了后台数据。在上面可以查到视频创作者的各项信息,包括分类排名、销售情况、粉丝画像、评论留言、所属MCN机构等内容。我们访谈的8位农村短视频生产者,男女各占50%,平均粉丝数95.3万,年龄25至38岁。为保护隐私,文中引述均以字母出现。
⑤需要说明的是:(1)扎根理论并非完全拒绝理论预设,有理论预设作为导引能使编码更容易聚焦。此外,本段落中并无意图在三个主轴编码之上提炼新的概念,而更多是为了勾勒交往情境的框架。(2)立意取样很大程度上期望选取更具代表性的农村短视频,为此我们特地考察了这257个视频的数据表现,均超过了70%的同类型视频。(3)为节约篇幅,表格中的开放式编码没有放入更低频数、无法归类的编码,特此说明。
⑥本部分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行走法搜集、对农村短视频创作者的访谈,以及两份外部材料:(1)方正证券2020年3月出品的《抖音vs快手深度复盘与前瞻》(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26331.html),这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尽的调查报告;(2)字节跳动公司目公开的算法原理解读(主要解释其算法架构,而非底层代码),可见:https://www.toutiao.com/a6511211182064402951/。
⑦可参见虎嗅网的互联网观察文章《底层生猛物语:被无视的快手和被遗忘的3亿庞麦郎》,检索于https://www.huxiu.com/article/162451.html。
⑧霍启明:《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2016年6月8日,检索于 https://xw.qq.com/news/20160609003283/NEW2016060900328301(此文当时在公共领域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阅读量超过10万,点赞达到9343,由于原文已删除,上面提供了转载后的网页)。
⑨2016年12月14日,张一鸣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表示“今日头条的内容是算法决定的,人工不予以干预”,以及“媒体是要有价值观的,它要教育人、输出主张,这个我们不提倡。因为我们不是媒体,更关注的是信息的多元性与吞吐量,并不想教育用户”。具体可见:http://tech.sina.com.cn/i/2016-12-14/doc-ifxypipt1331463.shtml。
⑩这些概括性表述的依据来源于艾瑞咨询2017年发布的《中国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检索于https://www.iresearch.com.cn/Detail/report?id=3118&isfree=0。
[11]以上内容均检索自中国网信网,可参考《国家网信办依法查处一批严重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和主播(http://www.cac.gov.cn/2018-02/13/c_1122415948.htm)、《网络直播需戴“紧箍”》(http://www.cac.gov.cn/2018-04/17/c_1122693562.htm)、《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视频网站主动自查 集中清理下线问题节目150余万条》(http://www.cac.gov.cn/2018-05/11/c_1122814550.htm)三则报道。
[12]可参见人民日报于2018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检索于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620/c40606-30067275.html。
[13]可参见澎湃新闻的报道《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发布:应持视听许可证,节目先审后播》,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31930。
[14]例如今日头条推出的“金稻穗计划”,承诺以5亿资金补贴优质的三农短视频创作者;快手推出的“福苗计划”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家乡特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实现可持续脱贫;以及抖音推出的“新农人计划”,承诺投入12亿流量资源扶持三农内容创作,并对国家级贫困县的创作者给予优先培训、流量加成等政策倾斜。
[15]可参见新华社对徐艳、周小龙夫妇的报道《乡村里的“网红”夫妇:与百万粉丝分享生活》(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4/28/c_1125917890.htm),以及CCTV《致敬新时代的新农人》专题对“巧妇9妹”甘有琴的报道(http://tv.cctv.com/2019/01/15/VIDElmrqpBeUHIhcNCZhcQkH190115.shtml)。
[16]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2019年12月20日发布,检索于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1/t20200108_352969.html。
参考文献:
陈映芳(2007)。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开放时代》,(6),95-104。
段义孚(2005)。《逃避主义》(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顾明敏(2020)。城乡接合部的文化表征:土味美学及土味文化再思考。《新闻爱好者》,(5),58-62。
管健(2009)。社会表征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对莫斯科维奇《社会表征:社会心理学探索》的解读。《社会学研究》,(4),228-242。
何塞·范·戴克(2018)。《互联文化:社交媒体批判史》(赵文丹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曼纽尔·卡斯特(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玮(2013)。传播:编织关系网络——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新闻大学》,(3),1-12。
文军,沈东(2015)。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探索与争鸣》,(7),71-77。
项飙(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肖红军,李平(2019)。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管理世界》,(4),120-144。
谢静(2016)。连接城乡:作为中介的城市传播。《南京社会科学》,(9),108-115。
于洋,马婷婷(2018)。政企发包:双重约束下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基于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研究。《公共管理学报》,(3),117-128。
约翰·厄里,乔纳斯·拉森(2016)。《游客的凝视》(第三版)(黄宛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约书亚·梅洛维茨(2002)。《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曾一果,时静(2020)。从“情感按摩”到“情感结构”:现代性焦虑下的田园想象——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22-130。
张爱凤(2019)。“底层发声”与新媒体的“农民叙事”——以“今日头条”三农短视频为考察对象。《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49-57。
Crary, J. (2013). 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de KloetJ.PoellT.Guohua, Z.& Yiu FaiC. (2019).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3)249-256.
Goffman, E. (1986).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Gorwa, R. (2019). What is platform governanc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6)854-871.
Hogan, B.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30(6)377-386.
LiH. (2020). From Disenchantment to Reenchantment: Rural Microcelebrities, Short Videoand the Spectacle-ization of the Rural Lifescap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4)3769–3787.
Light, B.BurgessJ.& Duguay, S. (2018). The walkthrough method: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 New Media & Society20(3)881-900.
Marwick, A. E.&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13(1)114-133.
McDonaldT. (2016). Social media in rur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Nieborg, D. B.& PoellT. (2018).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orizing the 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 New Media & Society20(11)4275-4292.
Rao, T. (2020). The Reclusive Food Celebrity Li Ziqi Is My Quarantine Queen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2/dining/li-ziqi-chinese-food.html
Thompson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 DijckJ.PoellT.&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R. (1975).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曹钺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曹刚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智能城市的社区公共传播研究:系统元治理、空间治理、时间治理”(编号:2020BXW006),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乡村’背景下西部贫困农民社交媒体应用困境及其对策研究”(编号:17BXW10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