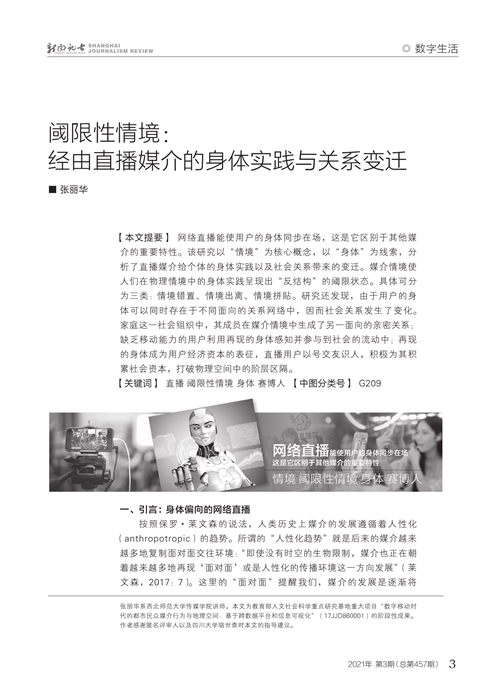阈限性情境:经由直播媒介的身体实践与关系变迁
■张丽华
【本文提要】网络直播能使用户的身体同步在场,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媒介的重要特性。该研究以“情境”为核心概念,以“身体”为线索,分析了直播媒介给个体的身体实践以及社会关系带来的变迁。媒介情境使人们在物理情境中的身体实践呈现出“反结构”的阈限状态。具体可分为三类:情境错置、情境出离、情境拼贴。研究还发现,由于用户的身体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面向的关系网络中,因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家庭这一社会组织中,其成员在媒介情境中生成了另一面向的亲密关系;缺乏移动能力的用户利用再现的身体感知并参与到社会的流动中;再现的身体成为用户经济资本的表征,直播用户以号交友识人,积极为其积累社会资本,打破物理空间中的阶层区隔。
【关键词】直播 阈限性情境 身体 赛博人
【中图分类号】G209
一、引言:身体偏向的网络直播
按照保罗·莱文森的说法,人类历史上媒介的发展遵循着人性化(anthropotropic)的趋势。所谓的“人性化趋势”就是后来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复制面对面交往环境:“即使没有时空的生物限制,媒介也正在朝着越来越多地再现‘面对面’或是人性化的传播环境这一方向发展”(莱文森,2017:7)。这里的“面对面”提醒我们,媒介的发展是逐渐将“身体”纳入交往场景的过程。在由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博客、网页、照片和视频共享网站以及约会网站等构成的更为可视化的互联网环境中,我们经历了离身(disembodied)又重新以化身、照片、视频的方式再度具身(reembodied)(Belk, 2013)。经由技术中介后的我们成为拥有两副身体的“赛博人”(孙玮,2018)——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海勒,2017:6)。
直播媒介独特的技术优势——同步性(张丽华,骆世查,2019),实现了身体的共同在场。在直播间里主播以影像在场的方式出现,其他用户则是以再现的身体在场。头像、等级、徽章、进场座驾,带有声画效果的礼物共同表征着用户们的身体,消费越多化身的形象和功能越完备。例如在观众席一栏,用户的“座次”排列是根据其等级和闪星情况决定的;由于电子书写转瞬即逝,加之直播间里原则上不限人数,所以用户容易被他人忽略,这时候,驾着座驾的、有徽章的用户在直播间里会更醒目;达到一定级别以上会享有专属的聊天特效和礼物,还可以将其他玩家“踢”出直播间,也就是说再现的身体“本身成为具备移动性(mobility)的空间实践主体”(周逵,2018)。身体的同步在场意味着“在没有地域邻近性的情况下,为同步进行的社会互动捕捉实体的布局(the material arrangement)”(霍华德,2019:85),即越来越多的身体元素进入交往场景中,通过几乎没有延时的互动感知双方的在场。这既不同于电话这种同步媒介的只闻其声,也不同于当下流行的短视频是一种延时性互动。在直播平台交往双方能够察觉到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彼此的姿态和情感。在同步性的媒介中,交往双方同时在场,可以产生有焦点的互动,能够形成情境(Rettie, 2009),这为笔者后文中以“情境”作为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身体:情境论中被忽视的维度
戈夫曼将情境视为基本的分析单元,通过阐述情境社会学来分析日常生活的表演和社会秩序的构成(Anne, 2003:231)。情境是“一种物理区域,在它里面的任何地方,两个或以上的个体彼此处于视觉与听觉的范围之内”(Goffman, 1981:84)。这里的“彼此”提示我们:只有处在某一场所中的个体能够被他人感知,并且也能够感知他人的存在,个体才是在场的,交往双方才算处于同一情境中。人们对情境的共同定义创造了社会现实的连贯性。如果参与者不再对“这里发生了什么”有着共同的定义,情境就会“崩溃,瓦解,化为乌有”(Goffman, 1974:302),即使互动者仍然是共同在场的,但情境所发挥的作用是中断的。
情境论中的个体是具身性的行动者,他们能够看、听、感知并对他人和环境做出反应,个体的服饰、神态、动作、声调等无不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身份状态,构成互动的基础。戈夫曼把微观公共秩序中的肉身看作是社会行动者呈现的“实践性”完成,他关注的是身体如何通过它的感觉和具体化的实践来发挥作用(Crossley, 1995)。作为行动要素的身体,“并非简单地被看作共同在场的情境中沟通的‘附属物’,而是沟通技能的支撑物,它能够转换成非身体化的信息类型”(Giddens, 1988:257),通过关注情境化的身体实践,戈夫曼将微观的个体行为与宏观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社会组织也就是处于彼此呈现之中的人们之间的组织性交往”(Goffman, 1967:148),对情境的界定以及每一种表演方式实际上表明社会结构的不同组织原则。有学者总结戈夫曼的情境论是“通过有知觉的人和身体化的社会实践确立新的社会分析模式,使实践的、身体化的行动与能动者的感知领域(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交织在一起”(王晴锋,2019)。当然,戈夫曼的情境是在无中介的面对面交往中生成的,他认为有中介的接触是社会接触的边缘模式或衍生模式,不能满足交往双方必要的观察,仅仅是种“类情境”(situation-like)(Goffman, 1979:46),因而,对于媒介介入互动情境会给原有的情境和交往带来何种改变,戈夫曼并未着墨太多。
然而,在征用情境这一概念时,学者们对在场的理解多是身体元素出现在某个地方,而忽略了戈夫曼强调的只有当交往双方能够彼此感知对方,才算共同在场,才能形成情境。在梅洛维茨的信息系统中,有形的地点不再是限制交往行为的必需因素(梅罗维茨,2002:34)。但是观众没办法和媒介人物即时互动,媒介人物也感知不到观众的存在。因而,大众媒介给观众提供的是一种无法参与其中的仅是“借来的”体验(Herzog, 1941);孙玮提出的“移动场景”这一概念,虽然提及身体可以穿梭在多重情境中(孙玮,2015),但忽略了交往双方对彼此存在的感知。也有不少文章考察电子媒介中介后用户的自我呈现时,用文本内容的呈现置换了情境论中交往双方的身体呈现。例如Marwick和boyd考察了推特将不同类型的用户压缩到单一的情境中后,人们在使用推特的时候怎样想象他们的受众,以及他们采取了怎样的印象管理策略引导观众(Marwick & boyd, 2011)。
值得一提的是,潘忠党和於红梅提出传播学研究可以借用人类学中“阈限性”这一概念,考察行动主体展开空间创造的过程。两位作者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阈限空间,他们认为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情境性的”阈限空间。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特定时刻使用媒介或其他数码技术对空间的征用和转换。通过对空间的征用人们得以脱离某种结构性的状态(角色、身份、活动等)(潘忠党,於红梅,2015)。但人们究竟是运用怎样的策略,用情境论的术语表达则是怎样的身体呈现,转化既定的情境以超越某种结构性状态的,两位作者并没有展开讨论。
本研究顺此而下,尝试提出“阈限性情境”这一术语,概括直播媒介介入既定的物理情境后,物理情境所承担的功能变得模糊不明的现象,具体分析拥有两重身体的赛博人,“置身”在多个情境中时,其身体实践和社会关系呈现出怎样的景观。阈限是从正常的社会状态中分离出来的一段时间和空间(特纳,2006,169)。“阈限”所指涉的模糊、之间、突破边界的“反结构”状态与笔者收集的经验材料形成了若干层面的贴合。首先,在直播媒介介入物理空间后,出现空间的交织融合和边界的相互渗透,即我们常说的混合空间(Silva, 2006);其次,因为直播媒介同步性的特征,被访者们能够同时穿梭在虚拟或真实的空间中,并且两个空间还有互动,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物理情境的感知和界定发生了变化。此外,阈限和情境都涉及空间的维度,这也是笔者将两者结合的理论依据。但是既有的研究多强调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阈限性,身体在阈限性的研究中是间接在场的,阈限主体自身的身体经验被忽略掉了。本研究以阈限修饰情境,是为了突出行动者的身体实践处于不同结构“之间”的状态,强调“身体”并不意味着对阈限时空维度的否定,而是视角的转换,即将身体视为能动性的基础和实践的主体(Tangenberg & Kemp, 2002)。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采取质化取向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传统的田野工作时长至少是一年的完整生产、生活周期。依此要求,笔者于2016年10月16日至2018年2月底,在直播网站六间房进行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田野作业。六间房近年来在网络直播行业中的排名并不突出,将其作为“田野”原因有二:一方面,六间房是我国创立最早的视频直播网站,通过其发展可以窥见整个行业的发展历程;其次,不同于快手、抖音等后起之秀只有手机端;也不同于YY、虎牙等需要下载PC客户端才能登陆,六间房网页版和手机客户端兼备,操作便捷。此外,笔者对44名直播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有3位是网络主播,均预先获得了他们的知情同意。除了个别访谈半小时结束外,其余访谈时间通常保持在一小时至三小时,并且针对不清楚的地方进行了二次甚至三次回访。在访谈方式上,受条件所限,笔者将面访和线上访谈相结合。笔者陆续在上海、北京、常州、武汉、兰州、合肥等地对11位用户进行了面访,其余用户则采用QQ或者微信语音的方式进行访谈。
本研究通过分析用户们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在情境中的实践,拟回答以下问题:1.当网络直播介入物理情境后,情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在媒介情境和物理情境交织的情形下,用户们的关系有何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在情境论中,情境和社会关系是同一问题的两个面向。情境即共同在场的行动者通过举止外表等信息交换,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双方展开互动的场所。不同情境中行动者需要遵循不同的表演框架,交往双方的关系就是在一定的表演框架中生成和维持的,不同的身体实践意味着和他人不同的社会关系。这里的身体实践是指身体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的感知、呈现、行为等。
四、阈限性情境:僭越结构的身体实践
笔者用阈限性情境这一术语概括直播媒介介入物理情境后的情形,这里的阈限是指人们脱离了既定的物理情境中的行为规则,利用直播媒介所营造的情境,改变了有形的建筑对于社会生活的功能性划分。身体是人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的阈限强调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居间状态,忽略了身体在这两个层面的实践。直播媒介能够使交往双方的身体同步在场,屏幕两端的用户能够感知彼此的存在,形成新的媒介情境。由于媒介人物涉入以门窗等有形建筑为区隔的社会组织,并且能够和远方的人发生实时的交流,这改变了用户们的情境感知和身体实践,他们对特定场所做出了不同于结构性设定的情境定义,并以新的定义框架展开活动,原有的物理情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变得模糊不明。笔者根据不同用户群体的身体感知和呈现,区分出了三类阈限性情境。
1.情境错置:私人生活的前置
不同于机构化的大众媒体,主播开设直播是个人化的行为。按照桑内特的说法,“‘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桑内特,2009:18)。很多用户选择在家中开设直播,“家”这一私人的生活后台便转化成他们实现自己主播这一角色的前台。不论有意无意,主播们的衣食起居都会呈现给观众,他们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不得不考虑到自己的主播身份。在家中开设直播,并不是生活后台的全然前置,而是经过刻意改造的日常生活。
英特尔曾在上海做了“在家工作”的调查,涉及直播对家里布置的改造(Gregg, 2019),主播们所处的物理空间风格颇为相似。床、落地式台灯、绿植、毛绒玩具、单人沙发等已经成为女主播们的标配;男主播则多在书房,他们坐在大靠背椅子上,身后一排木质的书柜。苗乔乔的直播场所就是她的卧室。透过摄像头,卧室里的陈设布置一目了然。她的床上放着一个大大的公仔熊,窗台摆放着三四盆多肉,桌子旁边还有一盏落地式台灯:“家族要求这么布置的。毛绒玩具是自己买的,台灯是家族配的,族长说增添点情调。”苗乔乔认为在卧室里开直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电脑放卧室里不是近吗,一开机就能播,一关机就能睡觉。放客厅那还不得干扰其他人。”镜头中的苗乔乔经常穿着睡衣,她解释道:“在家就应该穿睡衣啊,我一天直播快十个小时,穿着睡衣方便舒服啊。”有一次我和她逛街,苗乔乔特意挑选了几件居家工作都可以穿的睡衣:“要恰到好处地性感,又不能太暴露,直播也可以穿”(苗乔乔,兰州)。像大多数主播一样,苗乔乔将自己在平台中的直播间称为“家”,将直播间里的其他用户称为“家人们”,当有人刷出礼物时,苗乔乔除了口头表示谢意外,还会通过抛媚眼、撅嘴、比心、抱拳等肢体语言和对方拉近距离。
尽管每天直播将近十小时,但苗乔乔的爱人和孩子很少出现在镜头中。她上播时,爱人韩夜则在客厅里通过手机看她直播,孩子则由公婆照看。韩夜向笔者抱怨道:“天天晚上播到12点,12点完了又要和人家聊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早上又早早地醒来,把粉丝们哄得好得很!她就像着魔了,啥都不管,孩子连看一眼都不看。我妈就一个人看小孩儿,带做饭。有时候吃饭也不上桌,连吃饭都要播,你说这还像个家吗?哎!”(韩夜,兰州)
可见,人们对“家”这一情境的界定已不是单纯的生活区域,当家庭这一私人场所被主播征用,成为其实现身份转换的阈限空间后,主播们同时“身处”两个情境中,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生活—工作居间的状态。当家庭中某个成员成为主播后,他们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是一体的,由于直播平台同步性的特征使主播和化身在场的其他用户感知到彼此的在场,因而形成了内嵌于家庭情境中的直播情境。主播们把本应呈现给自己家人的表演——从随意的服饰装扮到亲昵的言行举止——刻意呈现给了千万匿名的用户,主播与这些用户将直播情境界定为“家”;同时,主播也是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置身于“家”这一情境中的,但直播镜头的存在改变了他们的行为礼仪。如苗乔乔为了使其主播的身份“顺滑”地生产出来,拉大了与同处一屋檐下的亲人们的身体间距,刻意地回避了其母亲、妻子、儿媳的角色,对于其他家庭成员而言,是一种弱化的情境性在场。
2.情境出离:群体生活的反抗
情境出离是指直播用户表现的身体暂时从物理情境中撤离,将沉默作为一种沟通和表达形式,而再现的身体却介入直播平台其他用户进行着往来。“家庭生活有时和独居是对比的,但事实上更大的对比是和一群同侪吃喝拉撒睡,而无法维持有意义的家务存在感”(高夫曼,2013:59)。“工人”、“学生”这类群体,虽然未受到如同全控机构那样严格的管控和凝视,但前台和后台的区隔消失,使他们生活在他人时刻在场的公共空间。为了创造出一方私人空间,这类被访者通常会在休闲时间拿起手机,“无声地从公共空间中切割出一隅,作为自己的私人领域,同时也重新界定在场与不在场的他者”(潘忠党,2014)。
飞宇哥是位工程监理。他们的工地常在市郊,和其他三位同事合住,桌柜在下,床在上,类似于大学寝室的格局。访谈时,他向笔者反复诉说工地生活的乏味单一:“你知道工地上的生活是多么单调吗?你说平时天天工作在一起,下班之后还是在一起,吃的都是一样的。你说,还有什么乐趣可言。”晚饭后,飞宇哥的常态是躺在床上拿着手机,戴上耳机进入了自己的“深后区”,有时候他甚至会刻意忽略同事们的邀请:“他们叫我打麻将,我连头都不抬一下(问:这样会不会不礼貌?)装作没听到嘛!知道吗,插上耳机就是一种姿态,告诉他们别来打扰我,时间长了他们也不叫了。”当我问到为什么选择看直播而不是其他方式逃离群体生活时,飞宇哥纠正了我的表述:“不是看直播,是‘玩’,知道吗,玩儿和看不一样,玩儿是你在里面,看你互动不了啊!”飞宇哥在直播间非常活跃。他喜欢送拖鞋这种礼物,因为送出后,屏幕上会有手扔拖鞋的特效,这时主播会配合特效捂着脸,高喊着“好疼”,有时候还会要求主播把他们的生活场景详细地展示给直播间的“兄弟们”:“直播是活的,玩儿游戏看电视是死的,明白吗?只要刷礼物,你让她干啥就干啥,不是太过分的都行!天天在一个圈子里腻了,玩儿这个你能进入不一样的圈子,懂吗?”(飞宇,南京)。
个体对在群居生活的体验是单一、透明的,他们的身体实践几乎24小时面向同一类观众。在四人宿舍这种小型空间中,更无法和对方保持身体距离。这时候,个体会以忽略对方的声音,回避他人的眼神等姿态呈现出肉身的沉默,物理情境中的他人为避免窘境的产生,通常会对他们的在场表现出漠视,从而配合其生产出情境出离的状态。手机和耳机不仅是与物理情境中的他人保持区隔的屏障,也是再现的身体进入直播平台的中介,他们与远方的他人同时在场,直播情境成为与工地生活并存的数字深后区。
3.情境拼贴:独居生活的补充
情境拼贴意味着将两个不同的空间纳入同一时间。不少独居的被访者为打发“孤独”、“寂寞”而流连于直播平台,直播媒介嵌入物理空间后,主播声音、形象的呈现,指名道姓地和某位玩家即时地互动,让玩家们生发出主播“在场”之感。主播的到来改变了独居者们“独自一人”情境感知,这是对他们独居生活的补充。
秦明的住处因为女主播晓君的到来变成了家。他曾是一家银行的高管,离异4年,儿子7岁由老家的父母带。秦明每天的行动轨迹大致如下:早上七点多起床,在家吃完早饭,开车去单位,午餐在单位附近解决,不加班的情况下,五六点下班,吃完晚饭后,秦明会打开电脑,登录进六间房,开始在晓君的直播间“挂机”。晓君开始直播往往是凌晨了,这个间隙,秦明会睡一觉,直到直播间的声音将他唤醒,凌晨五点,晓君结束直播,秦明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我养成习惯了,我也依赖她,就像到饭点,就该吃饭了那种感觉吧,习惯每天看到一个人,习惯每天跟这个人说话,生物钟都一致了。这一年多,她直播的时候,我都在。怎么办?晚上下班,先吃口饭,然后睡觉,把电脑挂在她直播间,声音开到最大,她一般都是两点多才直播,然后直播完五点多,我再睡觉”。由于表现的身体在直播间是不在场的,这能够让秦明以更为灵活轻松的姿态和主播交往:“如果是面对面我还得精心挑选合适的服装、地点、考虑很多外在的因素;如果是直播的话,我可以穿衣服也可以不穿衣服,我可以在床上、沙发上以各种舒适的姿态去面对。”再现的身体“在特定界面上的相互邻近”(谢静,2018),生发出了“在”之感。秦明喜欢送一种叫沙发的礼物,这在直播平台叫“踢沙发”,因为送出这种礼物后,会出来一个踢脚的礼物特效,并且从直播页面上看,沙发席就在主播身体的正下方,玩家的头像和发言都会以更醒目的方式呈现出来,“感觉那一脚踹出去特别爽,再说看着离她近啊,我的头像、发言都能显示出来”。“声音的空间性,使得听觉跟视觉相比更加牵涉身体”(季凌霄,2019),夜深人静时的相伴,秦明的感知仿佛经由“穿出”电脑屏幕的声音而延伸了,当主播叫秦明的名字时,他甚至有种主播就在身边的感觉:“她叫我名字的时候我都特别兴奋,哪怕是需要我刷礼物。(问:为什么会兴奋呢?)像是在家里她喊我帮忙一样,我手一伸就能保护她。”对比前面的“住处”,直播情境的介入明显让秦明身处的物理空间有了“家”的感觉:“房子是一个人住的,家是两个人的。”在后面的叙述中他梦呓般地用了一连串形容知觉的词:“曾经的相互取暖,相互依赖,相互抚慰,相依为命……不过后来证明,我认真了,她是演戏了,如此而已。”当然,晓君在网络里消失以后,秦明的“家”又变成了“空落落”的房子:“突然没了她的声音,过了这么久,我还是不适应”(秦明,苏州)。
当主播的声音、形象等身体元素介入独居者的居住空间后,意味着直播从身体感知方面对他们的居住场所进行了重构。和主播们的远程胶着生发出的亲密关系,使独居者们对所处的情境的界定从“住处”变成了“家”。虽然是有中介的互动,但身体的同步在场,使交往双方拥有协调一致的行为模式。当然这种交往方式和面对面交往并不完全相同,独居者是以再现的身体和主播进行交往的,这使他们放松了对肉身的反思性监控,不用严格遵从物理情境中的交往礼仪。
本节考察了媒介情境的出现对物理情境中人们的日常接触产生的影响。情境论强调共同在场情境下的日常接触构成和维持着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传统的面对面的日常接触涉及交往双方的动作、神态甚至身体距离等。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成为拥有两个身体的赛博人。他们的身体不但可以穿梭在不同的空间,“既在这里,又在那里”;而且由于直播媒介的同步性特征,用户们可以同时和空间不邻近的他人保持身体的在场,感知到彼此的存在,从而构筑出媒介情境。也就是说用户的身体可以同时出现在媒介情境和物理情境中。无论是情境错置、情境出离还是情境拼贴都表明直播媒介的介入使得成为赛博人的用户打破了物理情境中的交往秩序和结构局限,人们在物理情境中的身体实践呈现出“反结构”的阈限状态。
五、再现的身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以情境论考察社会关系强调关系是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遵循特定的表演脚本而生成和维系的。不同情境中的交往代表着不同性质的关系,给人们带来的体验和社会意义有所不同。在实体空间,由于个体只拥有一副身体,因此何时出现于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表演,与何人结成何种关系是一种线性的状态。以传统的阈限过程为例,阈限主体脱离原有的关系,但又还未进入新的社会地位,这种经历是“一时一地”的,角色和身份的不确定是暂时的。网络直播中交往双方的身体是同步在场的,个体能够同时身处两个甚至多个情境中,所以他们的身体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面向的关系网络中。甚至只要登录直播间,双方同时在场,用户之间的关系便获得了时间性的延续,因而我们从中出离或回归的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Neumann, 2012),用户能够在原有的关系网络和新的关系网络中进出,呈现出同时存在于两种关系网络之间阈限的状态。
1.相见不相识
当个体拥有不止一副身体时,即使物理情境中的熟人也会在赛博空间中遭遇相见不相识的境况。直播平台中,玩家的肉身是不出现的,只能依靠符号表征,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分离,用户能够同时“置身”于直播舞台和平日生活舞台,“于是我们就像是有了两个表演的前台”(Ling, 2008:169),将不同的身体表演呈现给不同的观众。
前文提到,在直播平台中,玩家消费得越多,再现的身体可以展示给他人的部分越为饱满和立体。见到老杨时,笔者很难将他和直播间里那位“玉树临风”的“藩王”联系在一起。老杨经营着一家修理电动车的铺子,每个月的收入约莫七八千元,他个子不高,干瘦,花白而蓬乱的头发,脸上一笑挤出道道皱纹,右眼因为早年打架还留下一道疤痕。在苗乔乔直播间里,老杨的头像因为每天高额度的消费闪烁着五颗星星熠熠生辉,平台还给他配备了入场时的豪华座驾,老杨很喜欢送一种价值200多人民币的叫“守护”的特效礼物来凸显自己身体的在场:“画面好看啊,上面出来一个人,玉树临风的”(老杨,阜阳)。
老杨经常和妻子一起看苗乔乔的直播,妻子的在场并不耽误他在六间房里和苗乔乔调情或者给其送礼物。老杨每一次进场,苗乔乔总会提高嗓门,来一句“欢迎我茗哥(注:老杨的昵称)回家!”边说不忘对着屏幕比一个爱心,老杨送出礼物后都会换来苗乔乔的一番夸赞:“感谢我茗哥爱你呦,威武霸气帅帅帅!”妻子是文盲,她并不知道活跃在直播间中的“茗哥”就是她老公:“她不懂,儿子也不懂,她又不知道我网名叫什么,她不知道上面哪个人是我。她不懂不识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更不知道老杨已经在苗乔乔的直播间里消费了20多万人民币:“知道的话事情就闹大了,早晚得知道,我妈盖房子,不是需要出钱嘛,一出钱不就完了吗”(老杨,阜阳)。
在直播情境中一人分饰两角儿的现象也非常常见。苗乔乔的粉丝榜第一名是一位叫“大叔”的“亲王”。苗乔乔直播间里其他几位常客也对这位大叔赞口不绝,可谁都没有见过他的样貌:“我和他很熟啊,但是我没见过他人。有的时候没钱了,要刷礼物,他帮我们充,你说有哪个人能帮你充值”(东子,温州)。“大叔人不错,看样子对她也没有歪心思……有时候也聊天,没视频过”(老杨,阜阳)。苗乔乔的直播间里还潜伏着她的丈夫韩夜,大叔的出现让他觉得直播间里来了“大土豪”,“财运好”:“现在已经成传说了,当时很火,一共来了三个月,一个月10万块钱的消费在六房已经是土豪了。”韩夜也没有意识到那位和他积极互动,被他“刺激消费”的“大叔”就是他的妻子。在他得知真相时,苗乔乔三个月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而且还败完了家里的十多万积蓄:“你说她一天累不累,她一个电脑开了两个号,一个是自己的号和大家聊天说话,一个是她这个号给她刷礼物。一个人充当两个角色,你说累不累?玩儿得特别好,谁都看不出来,在我眼皮子底下,我都没发现。花了多少钱你知道不?将近40万啊!”(韩夜,兰州)。
在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中,亲密关系发生着变化。一方面,用户能够以再现的身体进入直播间,和远方的他人同时在场;另一方面表现的身体和自己的爱人进行着家庭的生活。也就是说成为赛博人的用户,可以同时处于两重亲密关系的阈限状态中,即使和他们在同一情境中的至亲,也难以觉察出这些直播用户已然用化身编织出了另一面向的亲密关系。
2.固着的观光者
鲍曼用“观光者”和“流浪者”作为当代生活的隐喻。观光者的特征是“避免固定认同的出现”(鲍曼,2002:105),他们是高度移动性的,具有选择的自由。一部分被访者,囿于社会资本的限制,缺乏移动的能力,丧失了对家以外其他场所的感知和交往。他们或是留守在家庭照顾小孩的妇女,或是在村子附近做长工的男子,还有遭受着疾病折磨的残疾人。但赛博人不再以肉身所处的位置为中心感知远近,“就赛博空间或交流空间而言,地理上的距离消失了”(曹继东,2006)。经由再现的身体,他们得以进入不同的直播间,通达不同的场所,成为了赛博空间中的观光者。
对建民哥而言,物理世界似乎只是一个延续其肉体存在之所,他的大部分活动都“挪”到网上了。他身体行动不便,自己却不知病的名称:“天津市里的医院也看过了,他们也说不清楚,原因是我不是马上得的病。”长期患病使他的身体日趋肥胖,这更加局限了他的活动空间:“我150斤,1.67米。不运动,连呼吸都难受,只能小范围活动。”以前能走动的时候,若是天气暖和,建民还会出去溜达,随着病情的加重,他只能“宅”在家里,“平时就是上网,玩儿就是我的活儿!就在炕上”。访谈建民哥的时候,他刚在京东上买了适用电子界面的新“装备”——一副墨镜:“我眼睛看屏幕不行了,怕光。网上买个墨镜,夜里看直播也能用,黑天白天都能用。”虽然在物理情境中行动不便,但建民哥并不觉得孤独,再现的身体使他在各种媒介情境中穿梭自如。在六间房,建民哥是位“伯爵”,进璐璐姐直播间时,他驾驶着伯爵专属的轿车,在页面上“巡视”一圈,然后从车里走下,脱帽,这时候璐璐姐不忘提高嗓门来一声:“欢迎我三D(注:建民哥在六间房的昵称)!”说着不忘放出一段虚拟的欢呼声,而直播间里的熟人也纷纷发一个表情符或者一段文字,以示欢迎。建民哥说道:“感觉比面对面聊天、看电视都有意思。这上面你能接触到天南海北的人,一起聊天嗨皮,也能学到不少东西。”璐璐姐不直播的时候,建民哥喜欢刷快手,他是一对户外旅行主播的忠实粉丝:“这两口子是河北人,跟着他们去了不少地方:甘肃、陕西、青海、西藏……”,看快手上素人旅行的乐趣在于,建民哥可以跟随主播的视角参与他们的旅行过程,“这就是现场直播啊,又没有导演,也没有事先安排好,还能和房间粉丝们一起互动和鼓励他们,感觉自己也亲身游历了似的”。此外,快手同城对他而言就是对地方生活的体验,他关注了周边钓鱼的、工地工人、还有红白事演出的鼓乐班子:“不用出去跟就在现场一样!不想看了就走,换一个,自由!别看我不出门,天津发生了什么我都清楚!”(建民,天津)
诚然,现有的直播技术未必能给用户身临其境般的全息体验,但是却为那些以固着为生活方式的用户提供了随时走出界限而进入外界天地的可能性(齐美尓,1991:1-8)。他们通过再现的身体,游走在不同直播平台的直播间,摆脱了固着的情境和结构性的状态,参与到人际交流的维系和社会关系的再造中,感知整个社会的流动,并且成为流动社会的一员。
3.以号会友
直播平台中,再现的身体的成长是一个有目共睹的过程。头像、用户名、等级是化身最基本的配置,用户消费越多,他们的等级成长得越快,能够在直播间中呈现的部分越是丰满。一部分用户热衷于使再现的身体逐渐完备,这个过程被称为“养号”。他们会花重金买下“吉利”、“顺口”的ID编号,每天消费超过1000元人民币维持自己的等级熠熠生辉,达到最高级别还可以定制出场特效。再现的身体成为平台用户判断他人经济资本的重要依据,相比面对面交往中个人前台的呈现,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屏幕中的身体意象。
小李生活在河北的农村,他喜欢游走在各个直播间结交“大哥”,当有人刷出高额的礼物后,小李总是不忘发一个抱拳或者威武的表情,再恭维对方几句。他将直播平台中的等级和现实生活中的财富等同:“六间房刷礼物的是没钱的吗?人家全是大哥,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真正有自己的事业闯下来的。”和大哥们的称兄道弟,能够打破物理空间中的阶层区隔。小李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区分为同村的、外边的和网络上认识的。遇到困难,肯定同村的朋友首先能帮上忙,离家范围“十几里路外的”都属于外边的人,相比较还没有网络上认识的人更有作用:“如果说是网络上的朋友和同村的朋友,我肯定选同村的;如果我一个外边的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我肯定选网络上的朋友。不是我看不起农村人,我也是农村人,你现实中的朋友,他也是个打工的,只能是精神上帮助你,六房的朋友,他是个老板,他能当时就给我一个职位,现实中的朋友他要能给你的职位是N多年以后的”(小李,保定)。在小李看来,直播平台重组了他的社会网络,使他跨越了结构边界,增加了与自身圈层之外的人的交往和接触。
斌哥在合肥经营着一家传媒公司,在六间房他是“神”级别的玩家,这意味着他消费了100多万人民币。斌哥认为在直播平台消费上百万的玩家,肯定家底雄厚,反而身边人的底细未必清楚:“像身边的朋友,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你又没有消费给我看,我怎么知道啊;在六间房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你消费了这么多,一个玩家能够在六间房消费上百万,他身家一定不低于千万。”斌哥还和南京、黄石的两位玩家成了生意伙伴,一起注册了公司:“我们在六房都刷了几百万了,一人拿出一百万做一点事情,谁在乎啊……所以就是在六房看消费,见面看人品,大家在一起碰一碰找商机,就这么简单”(斌哥,合肥)。
对于一部分用户而言,化身比肉身更为可信,成为他们交友识人的依据。且不论以再现的身体判断他人的经济资本是否可靠,但至少为用户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即直播平台能够为他们的交往互动提供自身圈层之外的选择,并促成了新的关系,成为他们积累社会资本的新途径。
作为赛博人的用户以再现的身体进入同步的交流情境构筑了另一面向的关系网络。他们可以实时穿梭在不同的情境中。身体的流动打破了空间、机构和群体的局限,呈现出阈限的状态(Lzak, 2015)。以情境论的视角,用户是同时出现在由表现的身体在物理情境中编织的关系网络,以及由再现的身体在媒介情境中编制的关系网络中。由于再现的身体的样貌、外观和表现的身体是分离的,即使至亲也会出现相见不相识的情况,家庭这一最基础的社会组织中,其成员在媒介情境中生成了另一面向的亲密关系;缺乏流动能力的用户,以再现的身体突破自身圈层的束缚,感知并参与到社会的流动中;再现的身体成为用户经济资本的表征,直播用户以号交友识人,积极为其积累社会资本,打破物理空间中的阶层区隔。
六、结论与讨论
传统的情境论强调面对面的交往。“在场”在该理论中并非简单的身体出现在某个地点,而是身体化的信息交换,人们通过身体进行感知,同时也会感知到正在感知的他者。在大众媒介时代,媒介人物和观众是准社交关系(Horton & Wohl, 1956)。观众能在自身的物理情境中感知媒介人物的在场,但是媒介人物却感知不到某个具体观众的在场,观众无法和媒介人物产生同步互动,也没有化身进入媒介情境。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情境这一概念不适用于分析大众媒介所形成的交往情形。随着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以及有中介交流中“身体”的回归,我们有必要拓展情境的应用范畴。身体的同步在场,这是直播媒介区别于其他媒介的重要特性。一方面直播间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再现的身体和他人展开同步的交流,交往双方通过身体实践能实时地感知彼此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再现的身体并不是用户肉身的表征,这为他们同时在另一情境中开拓关系网络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直播媒介能够保证赛博人同时存在于两个情境中。如果没有双方身体的同步在场,无法生成情境,关系也不成立。这是当下流行的短视频甚至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的微信视频通话都无法比拟的。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社会行动者不断地被“连根拔起”,跨越预先设定的结构界限(鲍曼,2018:48-50)。笔者用“阈限性情境”概括直播情境介入物理情境之后用户身体实践的变化,也呼应了液态社会去稳定化和去地域化的景观。这里的阈限与人类学的用法类似,指涉的是对边界和结构的僭越,这一概念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得到阐发,常与杂合、间隙性、边缘化等表述结构与过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Neumann, 2012)。前文提到的移动场景在某种程度上触及电子媒介的出现使社会情境变得边界模糊且具有流动性的阈限现象。但以往的研究没有将行动者的身体实践这一情境论中的关键因素纳入考察的视野。阈限性情境则强调了这种反结构状态是处于情境中的主体身体实践的结果。也就是说成为赛博人的用户可以同时身处物理情境和直播情境中,并且同时在不同的情境中编织关系网络,导致原有物理情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变得模糊。情境错置是指主播们对“家”这一私人情境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家成为他们的工作情境,其他家庭成员为配合其工作,行为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玩直播是群居者对单一生活体验的反抗。这些用户们表现的身体以静默的方式从日常情境中出离,再现的身体进入直播间和远方的他人共同构筑出生活的深后区;直播情境的介入还改变了独居者的单身状态,主播以声音、影像以及指名道姓的互动等方式“置身”于用户的物理空间中,彼此形成亲密关系,直播情境和用户所处的物理环境拼接在一起,使他们对此类虚实结合的阈限性情境界定为“家”。
在情境论中,关系是在不同的表演框架中生成和维持的,不同的身体实践意味着和他人不同的社会关系。直播平台的用户一方面以表现的身体在物理情境中维持着既有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经由再现的身体编制出超越空间、地域、阶层的关系网络。因而用户的关系也同时处于两种结构“之间”的阈限状态。由于再现的身体的样貌、外观和表现的身体是分离的,即使至亲也会出现相见不相识的情况;缺乏流动能力的用户,以再现的身体突破既有圈层的束缚,感知并参与到社会的流动中;再现的身体还是用户经济资本的表征,直播平台能够为用户的交往互动提供自身圈层之外的选择,并促成新的关系,成为他们积累社会资本的新途径。
当下,媒介成为我们拥有“世界”的基础,中介了我们的经验。网络直播从最初个人化的活动,大有扩展到所有社会组织的趋势。全球疫情期间,当物理情境中的活动受到限制时,各机构以开设直播的方式确保其社会功能的延续。教学直播、电商直播、会议直播、政务直播等似乎使我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参与到自我的维持和社会的维持之中。但直播技术不只是提供交往的渠道,直播情境也不只是物理情境的再现,阈限性情境重构着我们的身体实践和关系结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停留点”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情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社会舞台中的位置以及我们是谁,也不再仅由物理情境决定,我们已不再“各安其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察特定情境中的交往应该是基于大量细致的观察。囿于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只是将直播平台作为田野,观察用户们在直播情境中的行为方式,笔者未能亲自参与观察到直播情境介入用户的日常生活后,用户们与周围人的互动情况。笔者只能通过长时间和被访者交往,在访谈时反复地询问,勾勒出他们日常生活的情况,其中难免粗疏,未来研究还需要在经验材料上加以补足。■
参考文献:
保罗·莱文森(2017)。《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曹继东(2006)。现象学与技术哲学——唐·伊德教授访谈录。《哲学动态》,(12),31-36。
厄文·高夫曼(2013)。《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者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群学翻译工作室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菲利普·N·霍华德(2019)。《卡斯特论媒介》(殷晓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奥尔格·齐美尓(1991)。《桥与门——齐美尓随笔集》(涯鸿,宇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季凌霄(2019)。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国际新闻界》,(3),24-41。
凯瑟琳·海勒(2017)。《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理查德·桑内特(2009)。《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潘忠党(2014)。“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析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53-162。
潘忠党,於红梅(2015)。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一个重新想象传播的维度。《开放时代》,(3),140-157+8-9。
齐格蒙·鲍曼(2002)。《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齐格蒙·鲍曼(2018)。《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玮(2015)。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12),5-18。
孙玮(2018)。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6),4-11。
维克多·特纳(2006)。《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建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晴锋(2019)。身体的展演、管理与互动秩序——论欧文·戈夫曼的身体观。《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5-42。
谢静(2018)。时空之流:移动新媒体的城市尺度。《探索与争鸣》,(10),128-135+144。
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周逵(2018)。沉浸式传播中的身体经验:以虚拟现实游戏的玩家研究为例。《国际新闻界》,(5),6-26。
张丽华,骆世查(2019)。同步性中的“存在感”:经由直播媒介的人际交往与日常生活。《新闻与传播评论》,(4),64-77。
BelkRussell W. (2013). Extended Self in a Digital World.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3)477-500.
de Souza e Silval, A. (2006).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and Culture9(3)261-278.
DonaldHorton. & RichardWohl.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Psychiatry-interpersonal & Biological Processes19(3)215-229.
Giddens, A. (1988). Goffman as a systematic social theorist //Drewp, Wootton A. Ed. Eeving Goffam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Ph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Anchor.
Goffman, E. (1979). Gender Advertisemen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erzogH. (1941). On borrowed experience: An Analysis of Listening to Daytime Sketche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ience, 9(1)65-95.
LingR. (2008). New tech, new ties: How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reshaping social cohesion. 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
IzakM. (2015). Situational liminality: Mis-managed consumer experience in liquid modernit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31(2)178-191.
Marwick, A. &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and Society13(1)114-133.
Melissa Gregg. (2019). Domestic enterprise in a data centric world. Geomedia conference.
NickCrossley. (1995). Body Techniques, Agency And Intercorporeality: On Goffman’s Relations in public. Sociology29(1)133-149.
Neumann, Iver B. (2012). Introduction to the Forum on Limina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8(2)473-479.?
RuthRettie. (2009). Mobile Phone Communicaion: Extending Goffman to Mediated Interaction Sociology43(3)421-438.
TangenbergK M. & Kemp, S. (2002). Embodied practice: Claiming the body’s experience, agency, and knowledge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47(1)9-18.
WarfieldAnne. (2003). Order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lligibility: Intersections between Goffman and Garfinkel by Way of Durkheim// Javier Trevifio. Ed. Goffman’s Legac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张丽华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民众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基于跨数据平台和信息可视化”(17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以及四川大学骆世查对本文的指导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