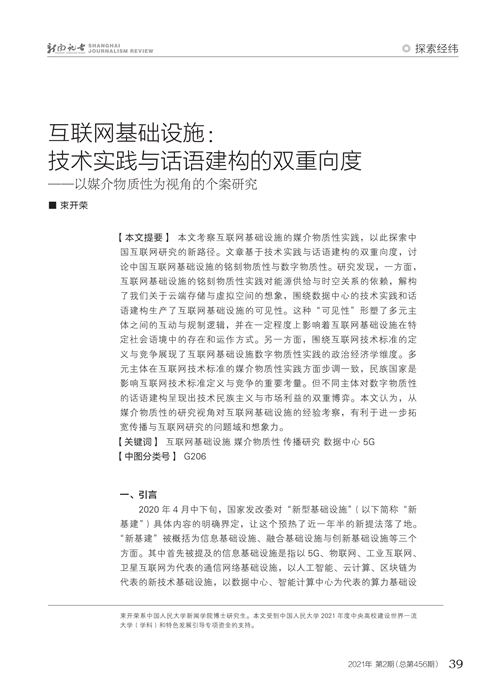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
——以媒介物质性为视角的个案研究
■束开荣
【本文提要】本文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实践,以此探索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新路径。文章基于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讨论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与数字物质性。研究发现,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实践对能源供给与时空关系的依赖,解构了我们关于云端存储与虚拟空间的想象,围绕数据中心的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生产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这种“可见性”形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规制逻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方式。另一方面,围绕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定义与竞争展现了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物质性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维度。多元主体在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媒介物质性实践方面步调一致,民族国家是影响互联网技术标准定义与竞争的重要考量。但不同主体对数字物质性的话语建构呈现出技术民族主义与市场利益的双重博弈。本文认为,从媒介物质性的研究视角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经验考察,有利于进一步拓宽传播与互联网研究的问题域和想象力。
【关键词】互联网基础设施 媒介物质性 传播研究 数据中心 5G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2020年4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以下简称“新基建”)具体内容的明确界定,让这个预热了近一年半的新提法落了地。“新基建”被概括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其中首先被提及的信息基础设施是指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国家发改委,2020年4月20日)。在此之前,从地方政府到国内投资界对“新基建”的讨论与实践已经徐徐展开。截至2020年3月5日,全国24个省市区陆续公布了新基建投资计划(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3月6日)。2020年上半年,阿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相继宣布未来数年内,将在云计算、人工智能、服务器、大数据中心、超算中心、5G网络等方面投入规模资金用于“新基建”的全面布局(中国青年报,2020年4月20日;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26日;新华网,2020年6月19日)。
显然,“新基建”涉及的多个细分领域都是以互联网为运作基础的社会技术体系。如今,这些社会技术体系已然或即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的基本构成,本文将它们统称为互联网基础设施(internet infrastructure)。那么,将数据中心、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应用视为基础设施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样理解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
首先,将互联网视为基础设施,意味着它们已经成为构建与组织社会的物质系统(material systems)。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电力、邮政、交通以及城市管道等其他基础设施一样,都是人类所构建并被广泛共享的物质资源,这些物质资源“是建成的网络,是能够使其他物质(货物、人或思想)得以流动的物质”(拉金,2013)。其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构成并形塑着人们的栖居环境,是实现公共利益和制度安排的重要方式(Anand, Gupta & Appel, 2018)。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一样,是表征现代性并形塑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质力量(Edwards, 2003)。不难发现,上述关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困惑和思考指涉互联网的物质性(materiality)。为此,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是如何被实践和表达的?这种实践和表达的方式所蕴含的话语逻辑和影响是什么?对这种物质性实践的学术考察之于当下的传播与互联网研究有何启发?
二、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视角与理论向度
在传播研究的视域中,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维度聚焦的是互联网及其广泛且深入的技术与制度安排对生活世界的物质构筑与维系,以及多元社会主体就这种物质构筑与维系所进行的传播实践、话语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在学理层面,本文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研究旨趣勾连起了当前传播研究的新兴视角——媒介物质性(media materiality)。
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对媒介物质性的相关讨论与研究逐渐兴起(戴宇辰,2020;章戈浩,张磊,2019;吕清远,2019;丁方舟,2019;第六届中外新闻思想史论坛——媒介的物质性、具身性与当代传播,2019年11月,重庆;物质性转向——媒体与文化分析学术研讨会,2019年3月,北京)。就中国互联网研究而言,媒介物质性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打破将互联网想象为承载非物质性(immateriality)数据与信息之虚拟空间的思维定势。一直以来,互联网的非物质性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Barbrook & Cameron, 1996),也作为一种迷思,作用于我们对它的言说和想象。超链接、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之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它的解放与自由潜力,同时伴随着挥之不去的神秘感(Boomen & Lammes et al., 2009)。
基于此,本文认为,传播研究对媒介物质性的聚焦以及国内就互联网基础设施而展开的广泛实践,是促使我们反思并开启互联网研究替代性(alternative)路径的重要契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媒介物质性强调的是媒介及其社会与文化影响的物质基底(material substrate)(Casemajor, 2015)。所谓的“物质基底”是指信息和数据得以生产、存储与流动所需的物质材料、技术结构、能源供给及其社会组织方式,这些物质基底使动和框限着人们对于互联网的理解和想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研究需要在充分凸显其物质基底的同时,避免陷入物质性的一元论或者决定论。因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社会运作与日常生活的组织和维系往往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具体化”(in-material of embodied)(Boomen & Lammes et al., 2009)过程。这种“物质性的具体化”意味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始终会与特定地域的社会语境遭遇并发生影响,而非作为一种技术客体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直接设定。也就是说,在一定时空环境下展开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物质性实践,总是会在特定的社会安排、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协商和调解,我们所能够使用和感受到的各种互联网应用及其影响力即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与社会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社会语境取向的媒介物质性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理论偏向,是近年来不少学者(Platin & De Seta, 2019; Plantin, Lagoze, Edwards & Sandvig, 2018; Parks & Starosielski, 2015; Holt & Vonderau, 2015; Bowker, Baker, Millerand & Ribes, 2010; Larkin, 2008)将互联网视为基础设施并考察其物质性实践的主流视角。其中,丽萨·帕克斯(Lisa Parks)与妮可·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在她们主编的论文集《信号交通:媒介基础设施的批判研究》(Signal Traffic: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前言中,主张从“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s)与“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s)两个理论维度,去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及其社会影响。她们所说的“物质形式”在于强调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公共或者私有化的社会实体(entity)所设计并制造的物质产品,它们的存在本身意味着能源消耗、资本流动以及地理环境等物质资源的聚集;而“话语建构”凸显的是互联网基础设施需要被纳入社会的话语生产、政策规制以及集体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来考察(Parks & Starosielski, 2015:5),这关系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嵌入社会并为人类所使用的方式。本文进一步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形式”拓展为层叠化(layered)的“技术实践”(technical practices);在此基础上,夯实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话语建构”与其物质性实践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作为考察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双重理论向度,能够被整合到媒介物质性的研究视角之下,并服务于后文对两个案例的经验分析。
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实践构成我们对互联网物质性的基本感知。它涉及三个部分,其一,网络基站、服务器、数据中心、互联网协议、互联网接入与输出的终端设备在地理环境中的分布和普及;其二,普通用户、程序工程师、互联网公司、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设计、制造与使用;其三,政策规制、行业标准、能源供给等维持互联网基础设施正常运作的社会机制。三个部分交错连接在一起,形成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实践网络。而且,这个网络具有明显的层叠化特征(Langlois, 2006;Brunton & Coleman, 2014)。这意味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实践网络在不同的社会主体那里处于不同的层级,且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见性”(visibility),但其在普通用户中保持着最大程度的“透明性”(transparency)(伊德,2012;Parks, 2015),它们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始终处于背景层次。直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出现故障(disrupted)时,人们才会感受到它们的巨大影响(Graham, 2010),并在政府的通告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看见和关注它们。互联网基础设施具有的“透明性”和“物质性”特征,以一种看起来矛盾的方式共存于人们的日常媒介使用与传播实践中。
另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话语建构是指互联网基础设施并非某种中立的或者自然化的技术系统,它们本身需要接入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同主体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言说和规制始终会被各种话语所建构、修改与维系。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话语建构”并不是社会建构主义范式意义上的,即它不是从主观意图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视角出发,而是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为前提,强调“客观现实并非纯粹是基于‘软性的’社会建构,而是与建构活动中所遭遇的‘硬性的’物紧密相关……传播的物质性分析意味着对物质性与社会性如何交织的分析”(戴宇辰,2020)。具体而言,互联网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互联网输入/输出终端、数据库、网络基站、海底电缆、大型服务器、超算中心等物质性的技术实践,还包括与这些物质性技术实践相关联的互联网公司、政府机构、技术组织、新闻媒体等不同社会主体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制度安排、知识型构、意义生产、利益竞争以及价值维系等方面所建构的各种话语(Parks & Starosielski, 2015:5-13)。可以说,媒介物质性实践过程中的话语建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们持续主导着我们关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想象与理解,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话语建构与其技术实践一道内嵌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并产生重要影响。
三、研究问题与个案选择
通过上文的概念分析与文献梳理,本文试图从媒介物质性的视角来切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研究,并据此提出如下问题:
1.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如何能够在经验资料的组织中获得恰当的分析?即在经验层面,中国语境中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媒介物质性是怎样被实践和表达的?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国内传播学界对媒介物质性的讨论主要还是以脉络梳理和理论思辨为主,以媒介物质性为研究视角的经验考察尚不多见。
2.互联网基础设施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两个向度上的媒介物质性是怎样被整合在一起的?即在中国语境下,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所蕴含的话语和实践逻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进一步检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双重向度对于经验分析的理论契合性。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本文选取两个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典型个案进行经验分析。一是贵州“数据中心”走廊。近年来,国内外的互联网巨头在贵州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心,大规模且集中的服务器设备影响着中国互联网数据的生产、存储以及流动。二是华为与高通围绕5G技术标准的定义与竞争,5G作为当下正在协商中的互联网协议标准,它的正式确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内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发展。笔者将在接下来的个案分析中将上述两个案例所代表的媒介物质性实践进行理论维度上的区分。
本文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实践以及相关负责人的公开言说,二是国内新闻媒体所生产的事实性资料与媒体话语,三是政府机构的政策文件以及新闻发布会所披露的事实性资料与评论。笔者在对这些经验资料进行地毯式阅读和甄别的基础上,注重对这三个方面的经验资料进行交叉验证与比较分析。
四、个案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与数字物质性
在开始个案分析之前,本文试图区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两种媒介物质性实践:铭刻物质性(inscribed materiality)和数字物质性(digital materiality)。马修·柯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在《机械装置:新媒介及其取证的想象》(Mechanisms: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中将电子媒介的物质性分为:取证的物质性(forensic materiality)和形式的物质性(formal materiality)(Kirschenbaum, 2008:59)。所谓的“取证”是类比法医学中的痕迹侦查,以此来指涉比特在硬盘上的铭刻(inscription)现象,它是互联网数据生产、存储与流动的物质性基础,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这种物质性,本文提倡采用“铭刻”来代替法医学意义上的“取证”。而柯申鲍姆所说的形式物质性是指能够被计算机识别的规则和模式,比如二进制代码0和1(Kirschenbaum, 2008:59-62)。相对于痕迹的铭刻,二进制代码显然更加抽象,它作为一种固定下来的“形式”被计算机识别。许煜在《论数码物的存在》(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形式化作为数据“物化”的方式,对于计算机运作与数字媒介发展的重要性。所谓的数据物化是指人类设计的能够被计算机识别的技术标准(譬如,HTTP、HTML、XHTML、5G等),而数码物(digital objects)就是这些技术标准所要组织和处理的对象(许煜,2019)。它们构成了媒介物质性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即数字物质性。
因此,对于互联网基础设施而言,其媒介物质性不仅意味着各种互联网接入设备、服务器、数据中心、网络基站等铭刻物质性,还包括其运作过程中所遵循的各种技术协议或标准等数字物质性。基于此,下文的案例分析就将分别涉及这两个维度的媒介物质性。
(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贵州“数据中心走廊”的能源与速度政治
从2014年开始,腾讯、百度以及苹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将数据中心规划或者建成在贵州省的山区地带。这些数据中心的集中分布形成一条长达30公里的数据中心走廊(黔中早报,2014年4月8日)。近年来,国内对贵州数据中心的关注主要局限在工程学、自然科学以及管理学的范畴内,亦有学者(Pan,2020)以社会科学的视域关注这些数据中心在中国西南的布局,并从国家—技术—地方的关系来考察技术所承诺的“连接性”与边缘地区作为数据存储中心的逻辑悖论。但是目前尚未发现传播或者媒介研究将其作为个案进行系统考察。本文认为,贵州“数据中心走廊”是理解和研究中国语境下互联网基础设施铭刻物质性的典型个案。
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提出“注重对现有数据中心及服务器资源的改造利用,建设绿色环保、低成本、高效率、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和区域性、行业性数据汇聚平台……开展区域试点,推进贵州等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区域大数据基础设施的整合和数据资源的汇聚应用”(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26号)。值得注意的是,贵州是公报中唯一被提及的省份和地域,而且节能环保是贵州成为综合试验区的重要考量。2018年5月31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其印发的《贵州省数据中心绿色化专项行动方案》中将新建数据中心能效值(PUE)低于1.4列为首要目标,已建数据中心能效值高于1.8的降低8%(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2018年6月1日)。PUE是评价数据中心能源效率的指标,PUE=数据中心总设备能耗/IT设备能耗,这个比值基准为2,越接近1表明能效水平越好(贵阳晚报,2018年6月10日)。上述从中央到地方对数据中心能效值的规定,关系到互联网基础设施日常运作的两大成本,一是电力,二是散热。而这两大成本都与自然环境和能源供应相关,这是互联网基础设施构建技术实践网络的物质性基础。
2013年,富士康率先把自己的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山区的隧道中,官方资料显示,这一数据中心“有效运用喀斯特地形,于山与山之间的垭口,以简易的方式建立类隧道式数据中心,不但加强了风力,且有效运用季风及烟囱效应排放热气,从而形成动态自然冷却技术为数据中心制冷”(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5月22日)。富士康绿色隧道数据中心负责人黄清白在接受央视纪录片《创新中国》采访时也谈到这一点,“风会特别强,对准了季风的方向,现在外面的温度有可能到达27度,但是隧道里面基本上是在20度以下。一般来说,全世界要做节能环保的数据中心通常是落在高纬度的地区。所以说,我们在低纬度地区建设一个完全没有空调的数据中心的确是一种挑战”。大型数据中心对贵州自然冷源的利用让这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外观上似乎保持着与自然环境一样的开放性,“没有紧闭的大门,没有厚厚的保温墙,听不到冷却塔的轰鸣,甚至见不到一台空调。服务器散发的热气,从顶端的排热孔自然排出,任何物理降温措施都不再有必要”(中央电视台,2018年1月27日)。在这之后,2018年4月28日和29日,被称为“山洞鹅厂”的腾讯贵安七星湖数据中心的施工现场首次呈现在公众面前,在“百米的小山间(所)开凿出的5条山洞是即将用于储存腾讯上百万台服务器的特殊仓库。贵阳凉爽的气候,结合山洞洞体和岩层物理特性,其气流组织特点,会将外部自然冷源源源不断地送入洞内,而不影响洞内设备稳定,给腾讯数据中心的绿色节能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腾讯科技,2018年4月29日)。
此外,数据中心在实体空间中的位置选择本身即凸显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实践对时空关系的依赖。也就是说,互联网数据的传输并非想象中的瞬时和虚拟,它们需要在密布于实体城市中的交换机和网络节点之间来回穿梭,数据在服务器中的响应速度(包括访问、上传、下载的速度)直接影响网民对云端存储的体验,而响应速度的首要影响因素就是空间距离。苹果iCloud在2018年2月28日将其云端数据委托给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上贵州”)负责运维,并为此投资10亿美元(新华社贵阳,2018年1月10日),这一迁移行动使得国内苹果iCloud用户不再需要通过位于国外的云端服务器来存储和访问自己的数据。2017年7月12日,在官方对外发布的《贵州省人民政府与苹果公司iCloud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双方即同意由“云上贵州”作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iCloud业务唯一牌照合作伙伴(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2017年7月13日)。出席该协议签署仪式的苹果公司副总裁丽萨·杰克逊在答记者问时谈到,“这一新的合作关系将通过减少延迟和提高可靠性改善中国iCloud用户的体验”(国新办,2017年7月12日)。苹果在2018年1月以弹窗形式给其中国用户手机发送的《有关iCloud(中国)的重要通知》中也提到,“此举将有助于我们继续提升iCloud服务的速度和可靠性”(腾讯网,2018年1月24日)。其实早在2014年8月,苹果就开始将其中国用户的部分数据存储在中国电信的服务器上,苹果对此的回应亦是“将数据中心建在用户尽可能近的地区,意味着iCloud存储的数据将拥有更快的运行速度”(腾讯科技,2014年8月16日)。相较此前,苹果用户的数据中心均位于美国,中国用户的数据生产与存储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城市节点以及海底电缆之间频繁穿梭,而且数据的跨国和跨洋旅行需要在数以万计的网络节点中“借路”。在此过程中,一次访问所造成的响应延迟甚至传输失败使得通常处于背景层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显现”在用户面前。
对苹果(中国)的用户数据交由国内数据中心运维这一技术实践的理解,值得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更加本地化的分析。成立于2014年11月的“云上贵州”数据中心具有国内互联网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贵州省大数据管理局注资的双重背景。当年4月,阿里巴巴派遣百名技术人员进入贵州,免费为“云上贵州”搭建系统(第一财经,2019年2月25日)。2018年11月,“云上贵州”完成股权变更,公司大股东从省经信委变为省国资委,国有股东持股比例100%(新京报,2018年11月16日)。由此可见,“云上贵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数据公司,这一点呼应了2017年6月1日颁布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中央网信办,2016年11月7日)。而且,在苹果发送给用户的《有关iCloud(中国)的重要通知》中,在解释数据转移有助于提升速度的同时提到“遵守中国法规”(腾讯网,2018年1月24日)。因此,国内有媒体将苹果此次的数据迁移解读为跨国企业的让步和妥协。2016年苹果总裁库克访华期间,曾到访贵阳,并与贵州省委完成首次会面,当时《网络安全法》征求意见稿出台不到两个月(第一财经,2019年2月25日)。此后,双方经历了两年的艰难谈判,其中苹果对是否将云上贵州作为其在国内的唯一合作伙伴犹豫不决,“云上贵州公司坚称,运营这么大的项目,如无排他性,将面临巨大风险。最终,经过反复磋商,苹果妥协了”(科技日报,2018年1月17日)。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能够获得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理解。贵州“数据中心走廊”这一个案在技术实践层面生产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云端”作为一种对虚拟空间的存储想象被拉回具体的物质性层面,比特在硬盘轨道上的铭刻、数十万台服务器对外界温度和散热效率的依赖,意味着互联网在海量数据的生产、存储以及流动过程中所需的能源支撑以及庞大的物质空间。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使得那些被非物质主义倾向一再强化的虚拟传播网络被“看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这种“可见性”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于,它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上形塑了互联网公司、国家机构、当地政府以及能源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规制逻辑。
首先,在技术实践层面,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集群所造成的巨大能耗,如前文所述,使得国家机构、当地政府得以通过环保标准的制定来介入和影响互联网公司布局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成本。而且,当地的国有能源公司能够通过电力保障与降低用电成本的方式参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技术实践。2015年10月10日,贵州电网公司为贵阳市贵安新区的大数据中心设立“贵安供电局”,相继投入近30亿元为国内外互联网巨头设立在此的数据中心搭建区域电网(贵阳日报,2020年6月11日)。这一区域电网的建设与存在本身即确认了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大规模布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此外,“云上贵州”作为贵州当地100%国有控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其服务器的供应商主要来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浪潮”公司(环球网,2015年6月30日),而作为服务器生产商的浪潮也在贵州当地成立“浪潮云上(贵州)”,它是与“云上贵州”合作成立的合资公司,主要服务于“云上贵州”的运维和安全保障(云上贵州,2020年1月15日)。可见,互联网数据在铭刻过程中的“可见性”要求这些数据在交换与共享的过程中具备高度的“安全性”,当地政府与本土服务器生产商之间的亲密合作就此达成。
其次,在话语建构层面,政策文件、互联网公司对其数据中心的自我陈述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框架不断强化互联网基础设施对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单维度话语。这种话语建构产生的影响在于,它令我们相信数据中心能够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些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可见性”就此“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中”(hiding in plain sight)(Holt & Vonderau, 2015)。而互联网数据在传输速度与响应时间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可见性”,建构了苹果iCloud中国用户数据向国内数据中心迁移的合法性,苹果公司亦通过“有利于提高iCloud的运行速度”等优化用户体验的话语来确认和强化这种“可见性”。“云上贵州”对苹果(中国)iCloud数据的接管,使得互联网数据的生产与交换能够被维持在管理者“可见的”视线范围之内。其中的地缘政治逻辑主要体现在主权国家基于“网络安全”和“属地管理”的话语及其法律实践来形塑和规制跨国互联网公司与本土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方式。
(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物质性:技术标准的定义、竞争及其政经之维
近年来,华为与高通围绕5G技术标准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竞争与博弈,是分析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物质性的典型个案。政府、媒体以及互联网公司等不同社会主体所参与的这一仍在持续之中的媒介物质性实践,凸显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学维度。
2017年2月22日,华为与高通在同一天宣布完成5G移动端到基站之间的连接测试,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移动通信标准(澎湃,2017年2月23日)。但是在澎湃新闻22日下午3点左右所发的另外一篇稿子里,开展5G互操作性测试的中国企业只有中兴和中国移动两家,华为不在其中(澎湃,2017年2月22日)。当天晚些时候,华为通过“中国5G推进组”对外发布消息称,“华为基于所构建的北京怀柔外场测试环境,率先开展了5G新空口(即移动端到基站之间的连接协议)技术的相关测试”(中国新闻社,2017年2月22日)。“中国5G推进组”的官网显示,该推进组于2013年2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联合推动成立,其主要成员包括华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北京邮电大学、大唐电信、中兴、欧珀以及维沃,推进组的组织架构中设立有5G承载工作组和5G试验工作组(IMT-2020-5G, 2013)。由此可见,我国对5G标准的试验和制定是由国内多家互联网公司、国有电信部门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技术实践。
华为选择与高通在同一天宣布5G外测成功的消息,意图显而易见。澎湃新闻发布的报道证明了这一点,“两年前,华为高调推出5G新空口技术F-OFDM与SCMA,若最终能成为5G新空口标准,则将掌握更大话语权。移动通讯的标准之争是各大企业利益的博弈,高通、华为等借助标准制定来争取更大话语权。其背后更深一层则影响到国家利益”(澎湃新闻,2017年2月23日)。相比之下,政府主管部门在谈及华为5G技术标准方面的重要进展时,往往将其置于多边协作的话语框架中来评价,“5G的发展,我想华为在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我)更想说的是,它是全球产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前期中国在5G领域和各国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开展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工信部,2019年5月21日)。
华为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倾向于在话语建构层面淡化两家互联网产品制造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2019年7月18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从市场规则的角度提到了华为与高通的竞争,并将这种“竞争”的范围解释为两者在进入国内而非国际5G市场时需要遵守的准入秩序,“5G独立组网全世界只有华为一家做好了,中国招标法规定,必须有三家公司做好了才能开始招标,所以,中国只有从明年才能开始独立组网的5G SA。我们在等待高通的进步”(任正非,2019年7月18日)。而在谈到5G标准的垄断问题时,任正非以技术标准的社会价值淡化了标准垄断的市场利益,“世界5G标准只有一个,如果出现两个标准,另一个标准的地方,你怎么能进得去呢?……世界标准只有一个,所有人都要互联互通,不互联互通的产品是没有价值的”(任正非,2020年3月24日)。他在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采访时,被问及华为与高通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任正非从自由市场的角度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这是企业自主权问题。没有5G有6G,没有6G有7G,未来道路很宽广”(任正非,2019年9月9日)。
此外,技术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技术实践伴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言说和建设,这是研究中国语境下媒介物质性实践的一个重要考量。首先,国内主流媒体会主动将华为应对竞争的方式隐喻为民族精神,“华为早在十几年前就有预判,并为如何极限生存作了长期艰苦和充分的准备。备用方案的启用,显示出其居安思危的战略远见、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以及坚忍不拔、攻坚克难的奋斗豪情……中国企业如此,中国和中华民族也是如此”(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5月19日)。而华为所遭遇的困难也被等同为中国社会的困难,“美方的断供会对华为业务产生一定影响,但那些影响是有限的,具体有限到什么范围取决于华为的未雨绸缪,也与华为的对策和中国社会与它共度时艰的动员程度有关”(环球时报,2019年5月20日)。其次,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国有电信部门也在积极寻求华为的5G技术标准在国内落地。2020年工信部印发《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其中提到将“支持基础电信企业以5G独立组网(SA)为目标,控制非独立组网(NSA)建设规模”(工信部,2020年3月24日)。而这里所说的“5G独立组网”目前只有华为掌握该技术标准(国务院新闻发布会,2019年9月20日)。而且,三大运营商在获得5G商业运营牌照不久之后就相继宣布从2020年1月1日起,NSA模式的手机将不再被允许入网,采用SA模式作为5G网络统一标准(快科技,2019年6月26日)。这意味着,搭载高通骁龙芯片(该芯片只支持NSA模式)(封面新闻,2019年6月27日)的手机将无法在2020年之后接入中国5G移动互联网,而华为手机搭载的巴龙芯片则同时支持NSA和SA两种组网模式(ZAKER科技,2019年6月9日)。
通过上述对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实践、新闻媒体报道框架以及政策文件的简单分析,不难发现,5G技术标准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物质性,它的定义和竞争不仅仅取决于互联网公司的技术实践,企业主体、新闻媒体以及政府机构围绕这一技术实践所进行的话语建构同样形塑着5G技术标准嵌入民族国家以及市场空间的方式。本文认为,这种定义和竞争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意味在于技术民族主义与市场利益的双重博弈。
一方面,就技术实践而言,互联网公司、政府机构、国有电信部门以及新闻媒体之间的步调相当一致。这种步调一致的逻辑和影响在于,围绕5G所开展的测试、定义与竞争中,民族国家是推进和参与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技术实践的重要变量,在中国语境下,由民族国家牵头的顶层设计主导着关键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发起和建设。作为市场主体的互联网公司和国有电信部门与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新闻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合作,将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注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实践。上文提到的由多元主体参与成立的“中国5G推进组”以及三大运营商把SA独立组网作为中国5G移动网络的市场准入资质即印证了这种技术实践的方式。简言之,华为与高通围绕5G技术标准的商业竞争,涉及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基本面,民族国家的入场并始终在场,在价值和利益导向方面影响着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实践。
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数字物质性在话语建构上的表现更为多元,互联网公司、政府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对华为与高通的5G竞争搭建了不同的表达框架。这说明了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处于不同场域位置的行动主体就互联网基础设施物质性实践进行话语生产与价值维系的复杂性。作为市场主体的华为始终将其与高通的竞争限制在自由市场和社会价值的框架内,对华为而言,与高通进行的5G竞争只关系到企业利益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价值,民族国家不曾进入其言说范围。而国内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华为与高通的5G竞争时,往往会将两者的技术实践纳入国家利益、民族情感以及话语权争夺的框架,企业自身的商业利益在其中被淡化处理,而基于地缘空间和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倾向则被凸显。相比之下,政府机构并不会在话语建构层面直接言及华为与高通之间的市场竞争,在政府机构的言说中,华为作为5G组网的龙头互联网企业主要服务于国内的新基建进程,并在对外开放的语境下强调其支持华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
五、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明确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双重向度以及媒介物质性的两个维度,并以此搭建分析框架,经由两个典型个案的经验研究,聚焦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与数字物质性。研究发现,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分别在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上呈现出不同样貌的媒介物质性实践,两者被整合在互联网公司、新闻媒体以及政府机构等多元社会主体针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实践与言说方式中。此外,本文认为,基于媒介物质性视角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考察,有利于进一步拓宽传播与互联网研究的问题域和想象力,由此带来的启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学理分析而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铭刻物质性和数字物质性,共同构建并发展着当下的媒介图景(media landscape),这个媒介图景包含着媒介研究的多个面向。从媒介物质性视角研究中国互联网,有利于跳脱传播研究,尤其是效果论通常把互联网视为内容生产与关系建构之虚拟空间的思维定式。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实践,为我们考察媒介技术、制度安排、民族国家及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条整合路径,这一整合路径所倡导的研究旨趣既体现了传播研究的主体性,也为传播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和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此外,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媒介物质性研究,也为传播研究中的经典议题,譬如,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知识与数字鸿沟、资本与媒介垄断、数字劳工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与较为丰富的经验资料。
另一方面,就历史书写而言,较长时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书写主要呈现为简单的数目字统计与管理,这些数目字主要是历年更新的国内互联网接入与普及状况。这样的历史书写缺少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如何嵌入自然环境与社会语境,并与不同社会主体围绕资本、技术、利益进行互动与博弈的分析和解释。媒介物质性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可以为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书写提供一条有待耕耘的学术路径。从技术实践与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切入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历史脉络,可以让那些描述中国互联网接入和普及状况的数目字真正落地,将典型个案置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语境,以铭刻物质性和数字物质性的两个维度来描述和分析互联网公司、新闻媒体、政府机构以及普通公民等多元社会主体介入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实践与言说,由此展现那些数目字背后所折射出的生动故事。■
参考文献:
布莱恩·拉金(2013)。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陈荣钢译)。《人类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42),327-343。
丁方舟(2019)。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新闻界》,(1),71-18。
第一财经(2019年2月25日)。打败三大运营商和互联网巨头,云上贵州如何拿下苹果iCloud大单。检索于https://www.yicai.com/news/100123754.html。
戴宇辰(2020)。“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3),54-67+127。
21世纪世界经济报道(2020年3月6日)。“新基建”融资调研。检索于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00306/504edc15217322ab37337da2ca35a49e.html。
封面新闻(2019年6月27日)。三大运营商发声:5G首班车,NSA+SA双模手机是最低门槛。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7500486716974170&wfr=spider&for=pc。
国务院公报(2015年第2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检索于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29345.htm。
国新办(2017年7月12日)。贵州举行苹果公司iCloud战略框架《协议》发布会。检索于http://www.scio.gov.cn/xwfbh/gssxwfbh/xwfbh/guizhou/Document/1558278/1558278.htm。
国新办(2019年9月20日)。国新办举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发布会。检索于http://www.scio.gov.cn/m/xwfbh/xwbfbh/wqfbh/39595/41794/index.htm。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2018年6月1日)。关于印发《贵州省数据中心绿色化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检索于http://dsj.guizhou.gov.cn/xwzx/tzgg/201806/t20180601_1079.html。
贵阳晚报(2018年6月10日)。贵州推进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全面提升节能环保水平。检索于https://wb.gywb.cn/epaper/gywb/html/2018-06/10/content_15028.htm。
贵阳日报(2020年6月11日)。贵安供电局:强电网优服务为5G“上岗”插上“电翅膀”。检索于https://epaper.gywb.cn/epaper/gyrb/html/2020-06/11/content_8974.htm#article。
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2016年5月22日)。贵安信投-富士康绿色隧道数据中心。检索于http://www.gaxq.gov.cn/ztzl_71/2016/lssjzlzccyzxsj/xmjs/201812/t20181217_1994986.html。
贵州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2017年7月1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苹果公司iCloud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检索于http://www.gaxq.gov.cn/xwdt/jrtt/201812/t20181211_1965110.html。
工信部(2019年5月21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检索于http://www.gov.cn/xinwen/2019zccfh/32/index.htm。
工信部(2020年3月24日)。工业与信息化部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检索于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7832353/content.html。
环球时报(2019年5月20日)。如果弱到一掐就死,华为安能引领5G。检索于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kCrV。
环球网(2015年6月30日)。浪潮服务器支撑“云上贵州”实现省级数据互通开放。检索于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9CaKrnJMz7l。
IMT-2020-5G(2013)。中国5G推进组主页简介:推进组介绍—组织架构。检索于http://www.imt-2020.org.cn/zh/category/65588?。
科技日报(2018年1月17日)。苹果云飘落贵州幕后。检索于https://tech.sina.com.cn/roll/2018-01-17/doc-ifyqqciz8337554.shtml。
快科技(2019年6月26日)。中国移动:2020年1月1日起不再允许NSA5G手机入网。检索于https://news.mydrivers.com/1/633/633354.htm。
吕清远(2019)。作为经验的传播:传播学研究物质性转向的逻辑进路与范式转换——在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念当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新闻界》,(8),70-79。
澎湃新闻(2017年2月23日)。高通华为争锋5G标准:同日宣布完成新空口规范下的5G连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4784。
澎湃新闻(2017年2月22日)。高通中兴中移动将开展5G互操作性测试,加速5G标准出台。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4329_1。
黔中早报(2014年4月8日)。贵阳打造“大数据”走廊 从长岭路延至白金大道。检索于http://www.gywb.cn/content/2014-04/08/content_580740.htm。
任正非(2019年7月18日)。意大利媒体圆桌纪要。检索于http://xinsheng.huawei.com/cn/ index.php?app=forum&mod=Detail&act=index&id=4373903&search_result=1。
任正非(2020年3月24日)。任正非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纪要。检索于http://xinsheng. huawei.com/cn/index.php?app=forum&mod=Detail&act=index&id=4710807&search_result=1。
任正非(2019年9月9日)。任正非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采访。检索于http://xinsheng.huawei.com/cn/index.php?app=forum&mod=Detail&act=index&id=4433165&p=1&pid=43614751#p43614751。
唐·伊德(2012)。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腾讯科技(2018年4月29日)。腾讯贵安七星数据中心“山洞鹅厂”正面曝光。检索于https://tech.qq.com/a/20180429/016845.htm。
腾讯网(2018年1月24日)。来自苹果向中国iPhone用户重要通知:iCloud服务器迁移,提升速度。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180124/20180124A0W3C6.html。
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26日)。新基建!腾讯宣布投入5000亿。检索于http: //mp.weixin.qq.com/s/NKxDZsqeEzujNYV_3xaFA。
国家发改委(2020年4月20日)。发改委举行4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检索于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fzggw/Document/1677563/1677563.htm。
许煜(2019)。论数码物的存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京报(2018年11月16日)。云上贵州完成股权划转 贵州省国资委为大股东。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7259270643827260&wfr=spider&for=pc。
新华社贵阳(2018年1月10日)。苹果中国iCloud服务将由云上贵州公司负责运营。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2018-01/10/c_129787810.htm。
新华网(2020年6月19日)。百度宣布加大新基建投入2030年百度智能云服务器超过500万台。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0-06/19/c_1126136633.htm。
云上贵州(2020年1月15日)。浪潮云上(贵州)技术有限公司。检索于https://www.gzdata.com.cn/c436/20200115/i7300.html。
章戈浩,张磊(2019)。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6),103-115。
中国青年报(2020年4月20日)。阿里云3年2000亿投资新基建。检索于http://news.cyol.com/app/2020-04/20/content_18577112.htm。
中央电视台(2018年1月27日)。创新中国(第6集)。检索于http://tv.cctv.com/2018/01/27/VIDEuY2PrKo6xu6eDYhVyBkE180127.shtml。
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5月19日)。华为绝地反击 中国居安思危。检索于http://news.cctv.com/2019/05/19/ARTInEoB6RMhgZjhwtKO1tW5190519.shtml。
中央网信办(2016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检索于http://www.cac.gov.cn/2016-11/07/c_1119867116.htm。
中国新闻社(2017年2月22日)。北京怀柔规划全球最大5G试验外场。检索于http://www.chinanews.com/it/2017/02-22/8157022.shtml。
ZARKER科技(2019年9月6日)。华为发布麒麟990 5G芯片,同时支持SA/NSA。检索于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d72209932ce402936000043。
Anand, N.GuptaA.& AppelH. (eds). (2018). The promise of infrastructu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wker. G.BakerK.MillerandF.& RibesD. (2010). Towar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tudies: Ways of Knowing in a Networked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ternet Research. J. Hunsinger et al. (eds).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BarbrookR.& CameronA. (1996).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6(1)44-72.
BoomenS. Lammes, A.LehmannJ.Raessens & MT Schaefer (eds) (2009). Digital Material Tracing New Media in Everyday Lif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Brunton, F. & ColemanG. (2014). Closer to the Metal. In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Materiality& Society. GillespieTarleton, P. J. Boczkowski, and K. A. Foot(eds). The MIT Press.
Casemajor, N. (2015). Digital materialisms: Frameworks for digital media studies.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10(1)4-17.
Edwards, P. N. (2003).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ty: ForceTim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 J. Misa.P. Brey.A. Feenberg. (eds). The MIT Press.
GrahamS. (2010). Disrupted cities: When infrastructure fails. Routledge.
HoltP.& Vonderau, P. (2015). “Where the Internet Lives” Data Centers as Cloud Infrastructure. In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 ParksL. & Starosielski, N. (ed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irschenbaumM. (2008). Mechanisms: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 The MIT Press.
LarkinB. (2008). Signal and Noise: Media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ngloisG. (2006). Networks and layers: Technocultural encodings of the World Wide Web.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0(4). 565-583.
Plantin, J. C.& de Seta, G. (2019). WeChat as infrastructure: the techno-nationalist shaping of Chinese digital platform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3)257-273.
Parks, L. & Starosielski, N. (2015).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arks, L. (2015). WaterEnergy, Access Materializing the Internet in Rural Zambia. In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 ParksL. & Starosielski, N. (ed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an, D. (2020). Storing Data on the Margins: Making 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in Southwest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Communication Seminar Series, 8 Apr 2020.
Plantin, J. C.Lagoze, C.EdwardsP. N.& Sandvig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20(1)293-310.
束开荣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