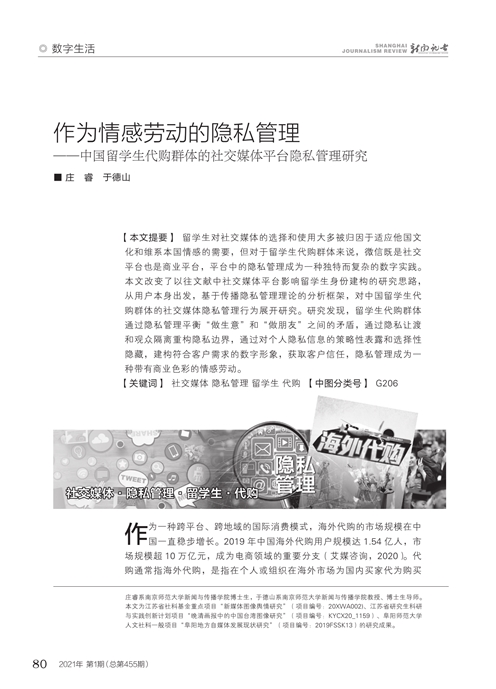微博微信使用对公民知识差距的影响差异研究
——政治兴趣和偶然接触的调节作用
■万旋傲 刘丛
【本文提要】随着社交媒体成为公民接触新闻和了解公共事务的替代方式,它对公民知识学习和知识差距的影响广受关注,但因不同社交媒体的平台差异、受众差异和传播逻辑差异,现有研究结果呈现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本文关注微博、微信对中国公民政治知识差距的影响,通过配额分层抽样调查获取1000个样本分析发现,微博的知识传播效果整体比微信更好,但微博使用扩大了高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微信使用缩小了高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扩大偶然接触新闻的机会,是抑制微博知识差距的一种有效机制。
【关键词】微博 微信 知识差距 政治兴趣 偶然接触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过去几年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传统媒体的受众正在不断减少,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来源快速兴起,逐渐被确立为公民接触新闻和了解公共事务的替代方式(Newman et al.,2017;Shehata & Stromback, 2018)。2020年,全世界约有36亿人在使用社交媒体,普及率高达49.0%,Facebook每月活跃用户数已超26亿(Clement, 2020)。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人(68%)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五分之一的人是社交媒体新闻的重度消费者(Matsa & Shearer,2018)。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已接近9.3亿,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市场。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公民的新闻环境,会扩大还是缩小公民的政治知识差距,成为政治传播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今天的公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机会接触新闻和公共事务信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能被认为是培养知识渊博的公民和缩小知识差距的理想选择,尤其是考虑到社交媒体中新闻的数量和广度都更有利于公民的知识学习(Barabas & Jerit,2009),即使对新闻不感兴趣的人也会因无意识地偶然接触新闻而或多或少地增进对公共事务的了解(Gilde Zúniga, Weeks & Ardèvol-Abreu, 2017;Shehata et al., 2015)。然而,伴随着一系列新兴的媒体现象和传播逻辑出现,这个问题逐渐趋于复杂化。著名互联网学者帕理泽(Pariser)在他的书中提出警示,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定制的个性化新闻流,使人们越来越生活在过滤泡中,限制了人们接收更多样的信息和更具挑战的观点,从而破坏了公民知识和话语体系(帕理泽,2011/2020);不少人质疑:充斥于社交媒体的“娱乐、肤浅、煽情、缺乏信息量、缺少调查、与时事政治和公共事务无关”的软新闻(Valenzuela,2013),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操纵和散播的假新闻,不仅不利于公民知识学习,还扩大了不同公民的知识学习机会的不平等现象(Davis, 2014;Lazer et al.,2018)。可见,社交媒体作为新兴的新闻传播媒介,它是否为公民提供了更良好的、更趋于平等的知识学习环境,学者们的预测并非一致乐观。
此外,社交媒体的具体指涉较广,从Facebo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LinkedIn、WhatsApp到各国的本土社交媒体,不同社交媒体的信息环境、媒体逻辑、传播特征都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这给社交媒体的知识效应评估带来了难度。许多社交媒体研究也因局限于整体的社交媒体分析,或者用一些特定的平台代指社交媒体,而忽视了平台差异(Nam & Stromer-Galley,2012;Swigger,2012;Yoo & Gil de Zúniga, 2014)。
流行于中国的社交媒体以中国本土私营企业创立的微信、微博为主,分别吸引了12.0亿和5.5亿的月活跃用户,在全球社交媒体中的热度分别排第5和第9位(Clement, 2020)。除了社交媒体的一些基本功能,如发送和接收文本和语音消息、发布和分享图片视频、共享位置和游戏等,两者也都在拓展创新型生产工具,试图融合传统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巩固社交用户群(微信,中国信通院,2020)。但从传播逻辑来看,微信和微博则是两种迥异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是主要依靠用户的社交关系和自主选择进行信息过滤的社交工具,微博则相对更依赖于算法推荐;微信是在即时通讯工具的基础上衍生的熟人社交,微博则是在名人明星、网红、媒体内容生态下建立的陌生人社交;尽管微信微博的信息供给都很丰富,但从用户内容选择的角度而言,微信是相对低选择的社交媒体,微博是相对高选择的社交媒体;微信用户的使用目的以“和朋友互动”、“分享生活内容”为主,微博用户的使用目的则以“及时了解新闻热点”、“关注及获取感兴趣的内容”为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a)。已有的社交媒体理论假说很难概括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交媒体的属性特征,更难以简单预测两者的知识效应。据此,我们试图关注微信、微博对中国公民的政治知识学习和知识差距的影响,以此观察不同媒体逻辑的社交媒体知识传播效应,充实社交媒体的平台差异化研究。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
(一)社交媒体与政治知识
政治知识是“存储在人们长期记忆中的事实政治信息的范围”(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10)。根据Delli Carpini和Keeter提出的经典OMA模型,公民的政治知识学习受到三个核心要素的影响:机会(opportunity)、动机(motivation)和能力(ability)。机会是信息的可得性,也可以称为信息环境,媒体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动机是人们对时事和公共事务信息的兴趣;能力指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技能来吸收和理解信息。其中,动机和能力均为相对稳定的个人特征,机会则是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媒体环境为个人带来完全不同的知识学习机会(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179;Luskin, 1990)。
关于政治信息环境,有一个潜在共识,即政治信息供给越多,人们接触政治信息并进行政治学习的可能性就越高(Van Aelst et al.,2017)。毫无疑问,政治新闻的绝对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增加,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对社交媒体的政治信息供给持悲观态度,并提出了几个鲜明的观点:第一,政治信息的绝对数量增长,并不意味着政治信息的相对数量也在增长,通常媒体信息总供给量的大幅增加,与体育信息、娱乐信息的增长更相关;第二,政治新闻的绝对数量更多,也不意味着人们在日常媒体使用中能看到的政治新闻也在增加;第三,人们对政治新闻的需求可能正在下降;第四,高质量的政治新闻数量可能正在下降;第五,政治新闻的多样性在减少(Van Aelst et al., 2017)。帕理泽的“过滤泡”理论也指出,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使我们周围充斥着已经熟悉、并且已经认可的想法,这实际上限制了我们所接触的内容,我们不仅看不到那些激发学习欲望和创新力的异质信息,也看不到泡沫之外的公共事务和一些真正重要的话题,最终我们的信息世界一再缩小(帕理泽,2011/2020:64-65)。同时,用户的偏好正在推动软新闻不断扩张,如今Facebook的Web链接(URLs)中已有87%为软新闻,13%为硬新闻,人们点击的内容中软新闻更增至93%,硬新闻仅剩7%,但硬新闻才是对知识有效的新闻类型,因此也没有理由相信社交媒体对人们的政治知识学习产生积极影响(Bakshy, Messing & Adamic, 2015;Lee & Kim,2017;Pariser, 2015)。
从实证研究结果上看,与批评者的担忧一致,多数研究证明社交媒体对政治知识没有影响或影响有限(Bode, 2016;Cacciatore et al., 2018;Dimitrova et al., 2014;Gil de Zúniga, Weeks & Ardèvol-Abreu, 2017;Shehata & Stromback, 2018;Wolfsfeld,Yarchi & Samuel-Azran, 2016)。如Cacciatore等人(2018)结合在线调查和皮尤调查数据的论证发现,公民在社交媒体中的新闻消费和新闻分享行为,均与公民的政治知识呈负相关关系;Shehata和Stromback(2018)针对瑞典的小组调查研究也表明,使用传统媒体和在线新闻网站对政治知识有积极效果,但使用社交媒体却没有效果,尽管社交媒体中充斥着传统媒体新闻,社交媒体仍然无法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公民政治知识积累的来源。
不过在针对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不同调查方案、不同测量方法的研究中,二者关系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一项比较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三种不同社交媒体对美国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差异的研究显示,博客和Facebook的使用与政治知识的联系比Twitter更强(Yoo & Gil de Zúniga, 2014);如果将政治知识区分为事实政治知识(能够正确识别信息)和结构政治知识(能够看到相关概念之间存在的联系),在线新闻的阅读量与事实政治知识的增长呈正相关,而共享在线新闻与结构政治知识的增长有关(Beam,Hutchens & Hmielowski,2016);还有学者利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公民的总统竞选知识的六轮面板调查数据,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有助于公民掌握与总统竞选相关的事实知识,并且社交媒体的作用高于其他任何新媒体(Gottfried et al., 2017)。可见,尽管目前批判性观点居多,但社交媒体与公民政治知识的关系为正向、负向还是无关系,结论仍然尚不确定,平台差异、测量问题的复杂性,使社交媒体的政治知识传播效应变得不稳定。据此,我们提出问题:
RQ1:微博和微信使用,对公民政治知识的影响如何?
(二)社交媒体与公民政治知识差距
在OMA模型的基础上,学者们也逐渐关注到机会、动机和能力三者之间不可忽视的交互作用,不同的媒介环境不仅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政治信息环境,也给不同动机和能力的人带来了不同的政治学习机会,其中一个重要关注点就在于,新闻和政治信息供应的变化如何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并影响人们对时事和公共事务的学习(Prior,2007)。在过去,人们的媒体选择较少,只能通过广播、报纸等媒体获取新闻,媒体使用导致的知识差距还不明显。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有线电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媒体信息越来越丰富,获取便利性越来越高,政治兴趣就成为影响新闻消费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新闻寻找者和新闻避免者的新闻消费出现严重分化,政治知识学习的机会不平等加剧(Bonfadelli, 2002;Ksiazek, Malthouse & Webster, 2010;Stromback, Djerf-Pierre & Shehata, 2013)。Beam和Kosicki(2014)针对算法推荐新闻平台的研究也指出,个性化的新闻平台为那些有政治兴趣、积极主动寻找新闻的人提供了一个更便利的新闻获取工具,因此使用这些个性化新闻平台可能导致不同兴趣水平的公民政治学习机会的不平等。
但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核心的辩论点,即社交媒体是否为公民(尤其是缺乏政治兴趣的公民)提供了偶然接触政治信息的机会,以及偶然接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的被动学习,影响公民间的政治知识差距。如果社交媒体的偶然接触与被动学习的效果存在,平常不主动寻找政治新闻的人,也获得了更多学习政治知识的机会,那么社交媒体必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削减信息不平等和缩小知识差距的环境(Bode, 2016;Gil de Zúniga, Weeks & Ardèvol-Abreu,2017;Shehata, 2013;Song, Gil de Zúniga & Boomgaarden, 2020)。偶然接触不是一个新概念,20世纪50年代的Downs(1957)就建立了学习的副产品模型,讨论过政治信息作为副产品偶然被获得的现象,他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人在缺乏学习动机的情况下,也可以因为环境向他们提供信息而增加知识。Krugman和Hartley(1970)意识到人们通过看电视偶然学习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这种学习方式“通常是毫不费力地、放松地对动画刺激做出反应,不会产生对学习内容的抵抗情绪”。软新闻研究也发展了偶然学习的概念,认为软新闻结合了娱乐与新闻内容,使那些只有娱乐兴趣没有政治兴趣的人,也可以至少得到一些政治问题的解释,获得了偶然学习政治的机会(Baum, 2003;Baum & Jamison, 2006)。
关于偶然接触的成熟论证,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社交媒体研究(Bode, 2016;Lee & Kim, 2017)。美国皮尤民意调查显示,目前,62%的Facebook新闻用户是偶然得到新闻,而不是因为他们积极尝试关注最近的社会动态(Gottfried & Shearer, 2016)。和电视一样,社交媒体总是给人们提供“动画刺激”和十分轻松的环境,那些政治信息都夹杂在宠物信息、婴儿信息的中间,很可能出现与早期电视类似的偶然学习效果——人们在愉快地使用社交媒体的同时,愉快地吸收了许多隐藏其中的政治信息(Bode, 2016)。社交媒体用户不仅可以看到传统新闻媒体的文章预览或链接,还可以看到其他用户分享的新闻内容或用户自己撰写的新闻评论,不管他们有没有点击新闻链接仔细阅读,他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和学习新闻信息(Fletcher & Nielsen, 2017;Klinger & Svensson, 2015;Messing & Westwood,2014)。有学者推测,社交媒体这种轻松地被动学习可能比主动学习产生更丰富和更多样的学习收益,因为用户更容易接受他们所接触的信息,降低了政治学习的障碍,从而增加了自己平时不太注意的政治知识(Bode, 2016)。然而,也有学者对偶然学习的效果提出质疑,一方面,鉴于学习通常需要对内容进行深入地认知处理(Eveland, Shah & Kwak, 2003),人们偶然接触社交媒体中的政治信息,如果缺乏处理信息的愿望,可以很容易地瞬间切换内容,从这个角度看,社交媒体的偶然学习效果可能不会理想,并不足以像电视一样出现被动学习(Shehata, 2013)。另一方面,偶然接触和被动学习促使人们进行媒体多任务处理,即快速、连续地同时或交替处理工作、学习、娱乐、社交互动等多项任务,这种模式在社交媒体中十分流行,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媒体多任务处理通常与人们的政治知识积累呈负相关(Ran et al., 2016)。此外,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偶然接触的新闻,培养了公民“消息灵通”的感知,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用主动寻找新闻,也能获得足够的信息,这种感知不仅不利于人们的知识学习,还可能削弱人们寻找新闻和主动学习的动机(Gil de Zúniga,Weeks & Ardèvol-Abreu, 2017;Müller, Schneiders & Schafer, 2016)。鉴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研究问题和研究模型(图1 图1见本期第72页):
RQ2:微博和微信使用,是否会扩大高政治兴趣和低政治兴趣者的政治知识差距?
RQ3:偶然接触新闻,是否会调节微博微信用户中不同政治兴趣水平者的知识差距?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搜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在线调查样本提供商Dynata招募的会员样本。为了确保最高的数据质量、完整性和代表性,我们按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b)发布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中互联网新闻用户的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学历)对样本库进行了配额分层抽样,使调查样本的配额与我国互联网新闻用户的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学历)基本匹配。为获取能代表某一群体的样本,配额抽样是应用较广的方法,许多学者发现其质量可与传统的随机数字拨号方法(RDD)相媲美(Ansolabehere & Schaffner, 2014;Beam, Hutchens & Hmielowski, 2016)。本次调查完成于2019年4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调查随机向22.6584万个会员发出了邀请,1.3898万人响应了该邀请,针对1.3898万名响应者进行配额分层抽样,共计3391个样本符合配额比例。向该3391个样本发送并回收问卷,获得有效样本共计1000份。
(二)测量因变量
政治知识:与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参照了Delli Carpini & Keeter(1996)的政治知识量表,考察受访者对一般事实政治知识(如政府职位、政治体系规则、政策问题等)和公共事务知识的了解,并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当前的重要话题对量表进行改编,与受访者所在国家一年内普遍关注和经常讨论的问题接壤(Lecheler & de Vreese, 2017;Yoo & Gil de Zúniga, 2014)。具体测量问题主要使用了崔迪、吴舫(2019)调查中国公民知识的部分问题,其余问题也改编自Delli Carpini和Keeter(1996)、Strabac和Aalberg(2011)和Yoo和Gil de Zúniga(2014)等研究中的同类型问题。其中,一般事实政治知识包括以下4道问题:“英国现任首相是谁?”(正确率43.4%);“什么是欧佩克?”(正确率41.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叫 号?”(正确率41.6%);现任我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谁?(正确率39.1%)。公共事务知识包括3个问题:“曾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的华为高管叫什么?”(正确率62.1%);“滴滴顺风车女乘客遇害事件发生地点是?”(正确率40.7%);“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的原因是?”(正确率83.2%)。每个问题均设置了五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为正确答案,三个干扰选项,以及一个“不知道或不确定”选项。要求受访者在不寻求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回答,且每题限时30秒填答(Clifford & Jennifer, 2016)。受访者每回答正确一个问题,计值1分,总分7分(Cronbach’s α=.67,M=3.52,SD=1.93)。
自变量
微博使用:受访者评估自己使用微博获取信息的频率,从“从不”到“每天”分别计值1-5分(M=3.53,SD=1.53)。
微信使用:受访者评估自己使用微信获取信息的频率,从“从不”到“每天”分别计值1-5分(M=4.58,SD=0.83)。
调节变量
政治兴趣:采用Gil de Zúniga,Weeks和Ardèvol-Abreu(2017)使用的测量问题,分别为“您对时事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感兴趣吗?”和“您对时事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关注程度如何?”,从低到高分别计值1-5分(Cronbach’s α=.88,M=3.27,SD=0.86)。
偶然接触新闻:参考以往文献的测量方法(Gil de Zúniga, Weeks & Ardèvol-Abreu,2017;Kim, Chen & Gil de Zúniga, 2013;Tewksbury, Weaver & Maddex, 2001),分别询问受访者“在使用微博、微信进行其他事情时,偶然遇到或者被动看到新闻的频率”,从“从不”到“非常频繁”分别计值1-5分(M=3.21,SD=1.40;M=3.69,SD=1.07)。
控制变量
Kenski和Stroud(2006)发现,政治知识因性别、年龄、教育、收入等人口学变量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将性别(女性48%)、年龄(M=31.5,SD=12.7)、教育水平(分为6类,M=3.78,Mdn=大专)、收入(分为4类,M=2.06,Mdn=2000-5000元)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我们也将报纸(M=2.43, SD=1.41)、电视(M=3.48,SD=1.35)、广播(M=2.47, SD=1.41)、浏览器/网页(M=4.31, SD=1.09)、新闻APP(M=4.17, SD=1.22)、视频APP(M=4.07,SD=1.14)等其他媒介的使用频率(从“从不”到“每天”分别计值1-5分)纳入了控制变量,以减少对微博、微信预测力的干扰。
四、研究结果
分层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表1 表1见本期第74页),性别(β=.12, p<.001)、年龄(β=.25, p<.001)、教育(β=.15, p<.001)和收入(β=.11, p<.01)都对政治知识有显著正向影响。报纸、电视、广播、浏览器/网页、新闻APP、视频APP等媒介中,电视使用对政治知识有显著负面影响(β=-.20, p<.001),广播使用对政治知识有显著正面影响(β=.09, p<.01)。控制人口学变量和其他类型媒介使用后,微博使用(β=.10, p<.01)和政治兴趣(β=.29, p<.001)对政治知识的主效应显著,微信使用对政治知识的主效应不显著(β=-.04, p>.05)。此结果回答了RQ1。控制人口学变量、其他媒介使用和主效应后,微博使用与政治兴趣的交互效应(β=.07, p<.05)、微信使用与政治兴趣的交互效应(β=-.09, p<.01)均显著,但不同的是,微博使用扩大了高政治兴趣者与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微信使用则缩小了高政治兴趣者与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在同样控制人口学因素和其他类型媒介使用的情况下,不同政治兴趣水平下微博微信使用与政治知识的关系不同(图2、图3 图2、图3见本期第74页)。当政治兴趣处于高水平(M+1SD)时,微博使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为正向影响(β=.18, t=3.68, p<.001);当政治兴趣处于低水平(M-1SD)时,微博使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不显著(β=.04, t=0.95, p>.05)。而微信的结果相反,对于高政治兴趣者(M+1SD)来说,微信使用对政治知识有显著负面影响(β=-.14,
t=-2.94, p<.001),对于低政治兴趣者(M-1SD)来说,微信使用对政治知识的影响不显著(β=.01, t=0.16, p>.05)。以上结果回答了RQ2。
RQ3纳入了第二个调节变量——偶然接触新闻,考察偶然接触新闻是否会影响政治兴趣对微博微信使用与政治知识关系的调节效应。我们使用了Hayes(2013)的PROCESS模型3验证该问题,检验了两个交互效应:(1)微博使用、政治兴趣和偶然接触影响政治知识的交互效应;(2)微信使用、政治兴趣和偶然接触影响政治知识的交互效应(协变量均为人口学变量和其他媒介使用)。结果显示,仅微博使用、政治兴趣和偶然接触三者的交互效应显著(B=-.10, t=-2.42, p<.05, CI=[-.19, -.02];△R2=.01, F=5.85, p<.05),微信使用、政治兴趣和偶然接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B=-.05, t=-1.51,
p>.05, CI=[-.11, .01];△R2=.00, F=2.28, p>.05)。微博使用过程中,政治兴趣低(M-1SD)、偶然接触高(M+1SD)时,微博使用对知识有显著正面预测作用(B=.25, t=2.23, p<.05),而政治兴趣高(M+1SD)、偶然接触高(M+1SD)时,微博使用对知识没有显著预测作用(B=-.01, t=-0.13, p>.05)。这表明,微博用户中,不同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受到了偶然接触新闻的调节,偶然接触新闻给了低政治兴趣者更多的学习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图4、图5 图4、图5见本期第75页)。
五、结论与讨论
为充实社交媒体的差异化研究,我们以中国的微博、微信为研究对象,关注两种不同媒介环境和传播逻辑的社交媒体使用对公民政治知识学习和知识差距有什么影响。正如预期,微博和微信展现出了极具差异的新闻媒介特质和知识传播效应。
首先,微博的知识传播效果整体比微信更好。依据Luskin(1990)和Delli Carpini与Keeter(1996)提出的机会、动机和能力框架来作解释:第一,在机会(或信息环境)方面,面对微信的强势竞争,虽然经常有唱衰微博的言论,但微博依旧保持着公共舆论中心的优势地位,是公民了解时事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主要平台(喻国明,朱烊枢,张曼琦,汪之岸,2019)。在打造个性化推荐内容之外,微博还推出了实时更新的“微博热搜”专栏,专栏下包含“热搜榜”、“要闻榜”、“同城榜”,榜单中的话题和新闻聚集了微博的主要流量,塑造了重要的公共话语和知识传播空间;当然,微信作为新闻媒介的功能也不容小觑,62.8%的网络新闻用户曾通过微信参与新闻评论,43.2%和29.2%的网络新闻用户曾通过朋友圈、微信公众号转发新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b),但是微信的封闭式熟人传播逻辑,使高新闻参与的作用没有凸显,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效应仍然有限。第二,在受众使用动机方面,60.7%的微博受众是为了“及时了解新闻热点”,58.0%的受众是为了“关注及获取感兴趣的内容”;而微信受众中,70.3%主要为了“和朋友互动,增进和朋友之间的感情”,50.7%为了“分享生活内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a)。尽管微信和微博的使用动机具有一定重合性,但以获取资讯为主要目的的微博相比于以社交互动为主要目的的微信,知识效应更为显著。第三,在受众能力方面,高教育水平有助于提升公民吸收和理解信息的能力(Yoo & Gil de Zúniga,2014)。微信的普及率高于微博,同时,受众教育水平整体低于微博。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受众在微信中占比约四成(39.7%),而在微博中仅占25.4%,更高的受众教育水平使微博更好地发挥了知识传播功能。
其次,微博使用扩大了高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而微信使用缩小了高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过多的微信使用反而不利于高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学习。微博、微信作为新闻媒介的特征差异更加明显:一是相对高选择和相对低选择的社交媒体新闻环境的差异。微博的新闻环境中,内容可选择性高于微信,给积极主动寻找新闻的人提供了更便利的学习机会,但也导致政治兴趣较低的公民更容易地“避免新闻”和“退出新闻”,消费他们喜欢的非政治内容,造成了不同兴趣水平的公民政治学习机会不平等(Gil de Zúniga, Weeks & Ardèvol-Abreu, 2017;Prior, 2007;Stromback, Djerf-Pierre & Shehata, 2013;Van Aelst et al., 2017);而在微信中,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量有限,人们几乎能浏览微信朋友圈共享的全部信息,属于相对低选择的社交媒体。微信的信息供给和微信用户的信息需求,都不是以政治和时事新闻传播为主,而是以娱乐、社交和生活信息为主,尽管其中也包含不少时事新闻传播。过多的微信使用,反而不利于高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学习,导致高低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呈缩小趋势。二是熟人社交与陌生人社交的差异。从Mark Granovetter的强关系和弱关系说可以看出,社交关系本身具有一定的功能意义,并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强关系交往具有较强的同化作用,形成趋同的集体注意力、习惯、认知和行为(Granovetter,1973)。基于熟人社交的微信使用过程中,社会交往动机本身成为人们关注特定信息的驱动力,也形塑着人们的共同兴趣和注意力,但基于陌生人社交的微博使用,仍然在持续强化个人偏好和个人兴趣的影响,这也是解释微信使用缩小知识差距而微博使用在扩大知识差距的原因之一。
第三,扩大偶然接触机会,是抑制微博知识差距的一种有效机制。与早期的电视类似,微博受众也有偶然接触新闻和被动学习知识的机会,他们即使政治兴趣较低,也能在偶然接触中缩小与高政治兴趣者的知识差距。该结果在一些针对Facebook和Twitter的研究中也有所发现(Bode, 2016;Fletcher & Nielsen, 2017;Gil de Zúniga, Weeks & Ardèvol-Abreu, 2017;Shehata, 2013),这提醒我们注意,微博等社交媒体是一个高控制的媒体还是低控制的媒体,与大多数研究者的预期不同。根据Bold(2016)的分析,在高控制的媒体环境下(如个性化网站),人们对自己接触的信息有高度控制权,更倾向于选择性地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并且有便利的新闻避免和退出机制,导致信息不平等和知识差距一再拉大;而低控制的媒体环境下(如早期的电视),人们常常无法控制他们即将接触什么信息,从而获得一些意料之外的信息和学习机会,偶然接触就是低控制媒体环境的现象之一。尽管微博等社交媒体给用户提供了可定制的信息环境,但我们仍要避免过高地估计微博媒体环境的控制性和可选择性,它更像是一个介于高控制和低控制、高选择和低选择媒体之间的复杂机制,在选择性接触和偶然接触之间摇摆和切换。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向低政治兴趣的微博用户增加新闻内容的推荐,同时加强“微博热搜”中的新闻质量、多样性、专业性建设,不失为值得尝试的克服知识差距的可行性方案。
可见,社交媒体作为公民接触新闻和了解公共事务的替代方式,它虽然受到了“个性化”、“过滤泡”、“技术霸权”、“假新闻”和“软新闻”等众多理论、假说的批判和否定(帕理泽,2011/2020;Baum, 2003;Beam & Kosicki, 2014;Lazer et al., 2018;Shehata & Stromback, 2018;Stroud, 2008;Sunstein, 2017),甚至常常被建构成异化的、充满陷阱的、给信息环境带来威胁的媒介,但是,社交媒体的新闻媒介特质和知识传播潜力仍然值得我们抱有期待。社交媒体平台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不容忽视,不同平台的信息供给和信息需求特征,才是知识收益的关键。如果社交媒体平台及用户都有较强的新闻动机,并能在信息环境建设和信息需求上达成默契,那么它仍然是一个培养知识渊博的公民的有效工具。相反,高度的社交化、娱乐化和群体同化,也会成为社交媒体知识效应的阻力。
更重要的是,一个有趣的理论意义值得关注——越来越多的偶然接触证据,试图倡议研究者们将社交媒体视为一个“偶然接触媒介”,而不是一个“选择性接触媒介”、“个性化媒介”或“高选择媒介”。偶然接触打破了社交媒体因个性化、高选择等特征导致知识差距扩大的必然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缩小知识差距的机制,也为社交媒体知识差距的理论解释作了重要补充(Bode, 2016)。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一是微博微信使用与政治兴趣的交互效应,微博使用、政治兴趣和偶然接触三者的交互效应虽然显著,但其额外解释的差异量均偏低,因此该结果的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该结果的解释也应谨慎对待。二是我们验证了微博微信的知识传播效果差异,但是对差异的讨论均属于事后分析或据证推论,未来有待从探索因果关系的角度设计研究,破解两种社交媒体知识传播效果的差异成因。三是西方社交媒体的知识效果研究常常因测量方法、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出现结果的不稳定性,该问题还需要更多可靠的、优化的研究设计进行多维验证,增强结果的信服度。■
参考文献:
崔迪,吴舫(2019)。算法推送新闻的知识效果。《新闻记者》,(2),30-36。
微信,中国信通院(2020)。2019-2020微信就业影响力报告。检索于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005/t20200514_281774.htm。
伊莱·帕理泽(2011/2020)。《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方师师、杨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喻国明,朱烊枢,张曼琦,汪之岸(2019)。网络交往中的弱关系研究:控制模式与路径效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9),141-14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a)。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检索于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712/P020180103485975797840.pdf。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b)。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检索于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mtbg/201701/P020170112309068736023.pdf。
AnsolabehereS.& SchaffnerB. F. (2014). Does survey mode still matter? Findings from a 2010 multi-mode comparison. Political Analysis, 22(3)285-303.
BakshyE.MessingS.& Adamic, L. A. (2015). 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 Science3481130-1132.
Barabas, J.& JeritJ. (2009). 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s of media coverage on policy-specific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53 (1)73-89.
BaumM. (2003). Soft news goes to wa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edia ag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umA. M.& JamisonA. S. (2006). The Oprah effect: How soft news helps inattentive citizens vote consistentl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8(4)946-959.
BeamA. M.Hutchens, M.J. & Hmielowski, J. D. (2016). Clicking vs. sha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news behavior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9215-220.
BeamA. M.& KosickiG. (2014). Personalized news portals: Filtering systems and increased news exposur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1(1)59-77.
BodeL. (2016). Political news in the news feed: Learning politics from social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19(1)24-48.
BonfadelliH. (2002). 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 gap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1)65-84.
CacciatoreM. A.YeoS. K.ScheufeleD. A.XenosM. A.Brossard, D.& Corley, E. A. (2018). Is facebook making us dumber? Exploring social media use as a predictor of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5(2)404-424.
Clement, J. (2020August 21). Global social networks ranked by number of users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014/global-social-networks-ranked-by-number-of-users/
CliffordS.& Jennifer, J. (2016). Cheating on political knowledge questions in online survey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80(4)858-887.
Davis, A. (2014). The impact of market forces, new technologies, and political PR on UK journalism. In R. Kuhn, & R. K. Nielsen (Eds.)Political journalism in transition: Western Europ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I.B. Tauris. 111-128.
Delli CarpiniM. X.& Keeter, S.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VitoM. A. (2017). From editors to algorithms, Digital Journalism, 5(6)753-773.
Dimitrova, D.V.ShehataA.StrombackJ.& Nord, L.W. (2014). The effects of digital media o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 campaign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95-118.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Eveland, W. P.Jr.Shah, D. V.& Kwak, N. (2003). Assessing causality in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A panel study of motivations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during campaign 2000.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4)359-386.
FletcherR.& NielsenR. K. (2017). Are news audiences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oss-platform news audience fragmentation and dupl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7(4)476-498.
Gil de ZúnigaH.WeeksB.& Ardèvol-Abreu, A. (2017). Effects of the news-finds-me perception in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use implications for news see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2(3)105-123.
Gottfried, J. A.HardyB. W.HolbertR. L.Winneg, K. M.& Jamieson, K. H. (2017). The changing nature of political debate consumption: Social mediamultitasking, and knowl- edge acquisi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34172-199.
Gottfried, J.& ShearerJ. (2016May 5).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6)1360-1380.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KenskiK.& Stroud, N. J. (2006).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50173-192.
Kim, Y.Chen, H. T.& Gil de Zuniga, H. (2013). Stumbling upon news on the Internet: Effects of incidental news exposure and relative entertainment use on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2607-2614.
Klinger, U.& Svensson, J. (2015).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media logic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17(8)1241-1257.
Krugman, H. E.& HartleyE. L. (1970). Passive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4(2)184-190.
Ksiazek, T. B.MalthouseE. C.& WebsterJ. G. (2010). News-seekers and avoiders: Exploring patterns of total news consumption across media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civic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54551-568.
Lazer, D. M. J.et al.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359(6380)1094-1096.
LechelerS.& de Vreese, C. H.(2017). News mediaknowledgeand political interest: Evidence of a dual rol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7(4)545-564.
Lee, J. K.& KimE. (2017). Incidental exposure to news: Predictors in the social media setting and effects on information gain onlin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51008-1015.
LuskinR. C. (1990). Explain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2(4)331-361.
Matsa, K.& ShearerE. (2018September 10).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m.org/2018/09/10/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8/
Messing, S.& Westwood, S. J. (2014). Selective exposure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trump partisan source affiliation when selecting news onlin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8)1042-1063.
MüllerP.Schneiders, P.& SchaferS. (2016). Appetizer or main dish? Explaining the use of Facebook news posts as a substitute for other news sourc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5431-441.
Nam, T.& Stromer-GalleyJ. (2012). The democratic divide in the 2008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9(2)133-149.
NewmanN.Fletcher, R.Kalogeropoulos, A.Levy, D. A. L.& NielsenR. K. (2017).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7.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Pariser, E. (2015May 7). Did Facebook’s big study kill my filter bubble thesis? Wire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ired.com/2015/05/did-facebooks-big-study-kill-my-filter- bubble-thesis/
Prior, M. (2007). Post-broadcast democracy: How media choice increases inequality in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polarizes elec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n, W.et al. (2016). Media multitasking during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A relationship with factual and subjective political knowledg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6352-359.
Shehata, A. (2013). Active or passive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Political information opportunities and knowledge gaps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Journal of ElectionsPublic Opinionand Parties23(2)200-222.
Shehata, A.& StrombackJ. (2018). Learning political news from social media: Network media logic and current affairs news learning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ehata, A.HopmannD.Nord, L.& Hoijer, J. (2015). Television channel content profiles and differential knowledge growth: A test of the inadvertent learning hypothesis using panel dat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32(3)377-395.
SongH.Gil de Zúniga H.& Boomgarden, H. G. (2020). Social media news use and political cynicism: Differential pathways through “News Finds Me” percep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3(1)47-70.
Strabac, Z.& AalbergT. (2011). Measuring political knowledge in telephone and web surveys: A cross- national compariso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9(2)175-192.
Stromback, J.Djerf-PierreM.& ShehataA. (2013).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news media consumption: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5(4)414-435.
StroudN. J. (2018).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 Political Behaviour30(3)341-366.
Sunstein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wigger, N. (2012). The online citizen: Is social media changing citizens’ beliefs about democratic values? Political Behavior, 35589-603.
Tewksbury, D.Weaver, A. J.& Maddex, B. D. (2001). Accidentally informed: Incidental news exposure on the World Wide Web.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8(3)533-554.
ValenzuelaS. (2013). Unpack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rotest behavior: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opinion expression, and activism.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57(7)920.
Van AelstP.et al. (2017).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41(1)3-27.
Wolfsfeld, G.Yarchi, M. & Samuel-Azran, T. (2016). Political information repertoir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New media & society18(9)2096-2115.
Yoo, S. W.& Gil de ZúnigaH. (2014). Connecting blog, twitter and facebook use with gaps in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7(4)33-48.
万旋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丛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十分宝贵的修正建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一带一路’国际舆情的生成演变机制及引导策略”(项目编号:16YJC860017),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国际涉沪舆情的传播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6EXW002),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资助基金“突发事件中政府网络话语传播的受众反向认知研究”(项目编号:20YF144740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