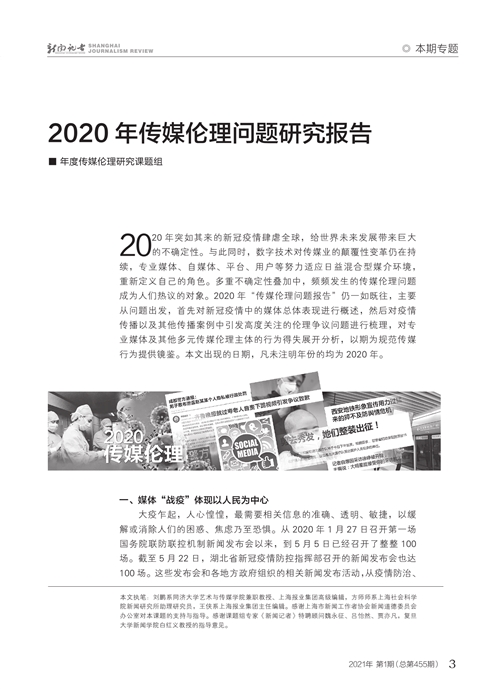2020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给世界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对传媒业的颠覆性变革仍在持续,专业媒体、自媒体、平台、用户等努力适应日益混合型媒介环境,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多重不确定性叠加中,频频发生的传媒伦理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2020年“传媒伦理问题报告”仍一如既往,主要从问题出发,首先对新冠疫情中的媒体总体表现进行概述,然后对疫情传播以及其他传播案例中引发高度关注的伦理争议问题进行梳理,对专业媒体及其他多元传媒伦理主体的行为得失展开分析,以期为规范传媒行为提供镜鉴。本文出现的日期,凡未注明年份的均为2020年。
一、媒体“战疫”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大疫乍起,人心惶惶,最需要相关信息的准确、透明、敏捷,以缓解或消除人们的困惑、焦虑乃至恐惧。从2020年1月27日召开第一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以来,到5月5日已经召开了整整100场。截至5月22日,湖北省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也达100场。这些发布会和各地方政府组织的相关新闻发布活动,从疫情防治、物资保障、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报告疫情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成为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政府权威信息的重要窗口。信息发布的及时透明,传播渠道的多元畅通,新闻报道的丰富深入,对于提高公众的防控意识、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起到关键作用。
疫情相关报道中,主流媒体成为凝聚民心的主力军。特别是在武汉“封城”之际,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常驻当地的中央媒体派出机构早已闻风而动,全国445名新闻工作者主动请缨,奔赴武汉,与当地媒体及并肩作战,第一时间多角度、全方位报道疫情救治防控情况。新京报、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第一财经、财新、澎湃新闻、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中国经营报、北京青年报、界面等一大批专业媒体也在疫情初起时就派出记者赶赴湖北,并以高质量的深度报道展示了专业媒体的业务水平和专业价值。3月27日,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副总理在与抗疫一线媒体记者座谈时说,媒体记者不畏艰险、深入“红区”,在医院、方舱、重症病房等地舍生忘死记录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用情用心讲述抗疫感人事迹,客观真实反映广大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职业操守和无私无畏、忘我拼搏的崇高精神,你们是抗疫战士,是抗疫英雄,为湖北武汉疫情防控凝聚起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一线士气。①
9月8日上午10时,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来自新闻战线的54人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7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3个集体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3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者履行以人民为中心职责的最高褒扬。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2020)的两次调查显示(两轮调查时间分别为:2020年1月24日-1月25日和2020年1月25日-1月29日),从农历大年初一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部署疫情防控以来,社会各界全力投入疫情防控的态势使得民众信心大增,对以中央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各种渠道信息的信任度明显上升。调查显示,“政府部门发布的疫情整体判断”的可靠性从76%增加到85.6%,上涨了9.6%;“中央媒体,如央视、新华社、人民网”的可靠性从89.5%增加到93.3%,上涨了3.8%;“地方新闻媒体”的可靠性从75.6%增加到84.2%,上涨了8.6%。这是来自民众的对党的媒体履行以人民为中心职责的高度肯定。
多项调查表明,无论平时还是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已经是微信、QQ、抖音等社交媒体(喻国明,杨颖兮,2020;楚亚杰,陆晔,沈菲,2020)。从健康传播角度,社交媒体是用户获取公共卫生信息最直接、便利的途径,同时也是公众即时发布健康状况、疾病问题和疾病治疗信息最重要的渠道,另外也可能为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提供预警(陈娟,郭雨丽,2020)。活跃在社交媒体的新闻行动者,早已不仅是专业媒体,各种政务新媒体、机构用户、自媒体作者,乃至普通用户、算法技术等,都已成为新闻生产传播的重要主体。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分布协作式生产(Bruns,2018),与专业媒体一起为人们建构了外部世界的新闻图景。对疫情期间新浪微博的研究表明,疫情相关的讨论中普通公众的舆论声量最大,大大高于网络意见领袖和活跃分子,更远远高于新闻媒体和政务机构微博(汪翩翩等,2020)。本次新冠疫情期间,普通人书写自己的疫情经历、分享自己的观察思考的现象更加突出,形成“全世界都在说”的用户新闻景观(刘鹏,2020)。
总体来看,2020年度中国媒体抗疫行动,无愧时代要求。但另一方面,在疫情及其他方面的信息传播的具体操作中,也不无草率、疏失,甚至引发混乱的情况。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2020)认为,新冠疫情健康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部分健康传播中出现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部分健康传播的内容存在不准确、不科学或刻意夸大的情况;部分健康传播的内容可读性较差、晦涩难懂;个别健康传播的内容在传播前未做好风险评估工作;部分健康传播的公众可及性较差。这些问题的产生,既与传媒环境大变革的挑战相关,也有各种传播主体行为失范的原因。
二、2020年度传媒伦理争议问题典型案例
1.“信息疫情”妨碍疫情防控
【事件】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社交媒体上散布着大量真假不一的疫情相关信息,公众很难区分哪些是来源可靠的和有效的防疫指南。12月7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在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发布了“2020年度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榜”,并选出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国内粮食短缺、“吃大蒜、喝白酒”等可防治新冠肺炎等十大辟谣内容。②
对于伴随新冠疫情爆发而来的虚假信息过载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大规模信息疫情”(massive infodemic)。③信息疫情(infodemic)一词由信息(information)和流行病(epidemic)组合而成,意味着线上和线下的信息过剩,包括蓄意传播错误信息以破坏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推进团体或个人的替代议程,让人们在需要时反而难以找到有价值的信息。④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疫情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仅2020年1月至3月间,全球就有至少800人因各种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假消息而丧命,5800多人被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不实信息迷惑而不得不送医治疗。⑤
【点评】信息疫情妨碍了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2020年2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谈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信息疫情时指出:大量谣言和错误信息阻碍了应对行动。假新闻比病毒传播得更快、更容易,但同样危险。⑥世卫组织等机构还指出,信息疫情可能会有害身心健康,加剧污名化,威胁来之不易的卫生成就,导致公共卫生措施执行不力;此外,虚假信息正在使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公开辩论趋于极化,放大仇恨言论,加剧冲突、暴力和侵犯人权的风险,威胁推进民主、人权和社会凝聚力的长期前景。⑦
信息疫情首先源于人们对未知疫病的恐慌、焦虑,因此,历史上每次传染病的爆发都会同时伴随着“信息疫情”的爆发。⑧而新冠疫情是社交媒体时代首次全球疫病大流行,传媒生态变革,特别是社交媒体分布式传播的技术特征,无疑也放大了信息疫情规模及其危害。数据生产、传播与再使用的高度分布式特点,导致道德责任的“分散”乃至消解,给责任分配和追责造成困难(闫宏秀,2020)。
防控信息疫情,当然需要社交媒体用户提高媒介素养,有效辨识虚假和不良信息。但面对这样全球规模的信息疫情,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组织到各国政府再到各大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积极行动,有效合作。对此,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⑨呼吁各会员国以及各相关主体共同为打击错误和虚假信息行动起来。包括联合国系统应该利用自身专长处理数字领域的错误和虚假信息,努力防止有害网络活动损害卫生应对措施,缓解疫情持续造成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向公众提供基于科学数据的准确信息,倾听社区意见,提高民众抵御错误和虚假信息的媒介素养能力;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包括传播错误和虚假信息的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能够设计和制定有效战略和工具应对信息疫情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民间社会领袖和有影响力的人,与联合国系统、会员国彼此协作,进一步加强行动,以传播准确信息,防止错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除此之外,网络社会中的最基础节点——每一位普通用户也须担负起自己的传播责任,不但要学会更负责地“说”,也需要学会认真“倾听”和以开放心态“对话”。
2.“双黄连、板蓝根可治新冠”成闹剧
【事件】1月31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发布消息:“记者31日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人们对“特效药”的迫切需求迅速被这一消息点燃,民众掀起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热潮,线上一度脱销,多地线下药房也排起了长队。甚至有人因外出购买双黄连感染新冠病毒。⑩
2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微博:“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特别提醒: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
当晚,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发布声明称,“向媒体提供的《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结论是基于实验室体外研究的结果。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我所提供的稿件中也提到目前正在开展临床研究”。[11]不过,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了上海药物所相关人士,在问到“那么消息出来,大家都去抢购双黄连,您觉得有必要吗?”时,对方没有回应。
2月3日,在武汉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张伯礼院士指出,双黄连对新型冠状病毒不具针对性,不主张将双黄连作为预防用药。
无独有偶。时隔8个多月后的10月16日,“复方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的消息又冲上了微博热搜。一则题为《钟南山:白云山复方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不会乱讲》的视频被广泛传播,视频显示,10月13日,在白云山板蓝根澳门转化研讨会上钟南山说:“复方板蓝根的试用,对新冠病毒有效”,“我们说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不会乱讲的,有效就是有效。”
虽然这次人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忽悠,不少网友和媒体发出质疑之声,但上市公司“白云山”的股价当天仍强势涨停,板蓝根也再次大卖。
随后有媒体质疑白云山价格波动涉嫌股价操纵。10月19日白云山发出澄清公告,表示这是体外筛选的实验结果,尚存不确定性。10月23日,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在几天前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合作协议(论坛)中曾讲过一句话,复方板蓝根,而非板蓝根在实验室有抗新冠病毒作用,这离体内有效还很远,白云山药厂作为‘内行人’应很了解,但(其中)有人断章取义,将我这句话扩大,甚至说是板蓝根,这是一种歪曲”。[12]证监会也表示将密切关注相关公司及相关事项,若发现违法违规,将依法严肃查处。
【点评】大疫当前,科学家、媒体人、相关企业都希望尽快拿出特效药,拯救生命,缓解危机。这种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无论科学研究还是新闻报道或者商业运营,都要遵循各自的规律和伦理,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把科学传播变成伪科学的闹剧。
科学传播首先是科学界的责任。在“双黄连案例”中,上海药物所的信息发布是有明显缺憾的,体外研究有效和临床实验有疗效中间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而且绝大部分在细胞上有用的药在临床上是失败的。[13]正如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2020)所提倡的,“在健康传播中,应当采用循证医学的思维,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健康传播工作者的专业知识,考虑大众的需求和健康素养,将三者结合,从而为大众创作出科学易读的优质健康传播作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公众急切获取有关疫情的最新信息,而健康传播一旦缺少了科学性原则,传播内容不准确、不严谨、不科学,就会造成谣言的滋生,放大公众的恐慌情绪,造成社会不稳定”。
对媒体来说,研发单位公布的只是阶段性成果,对它的正确解读有赖于严格的语境和条件。而媒体报道不是科研报告,其工作常规即是对“异常个案”、“亮点中的亮点”的追逐(甘斯,2009:114),因此往往将科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进行弱化处理,将研究成果的某一方面强化放大而忽视其限制性条件,再加上公众在焦虑、恐惧和不确定情绪中理性辨别力的降低,从而产生了“抢购双黄连”闹剧。这其实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科学研究的严谨性与媒体报道的大众性、通俗性之间张力的体现。
而“板蓝根”案例则有所不同,相关视频是对钟南山院士发言的断章取义,有意炮制虚假新闻。在其背后,视频制作和上传者有何商业利益?发布视频的媒体是否履行了把关责任?这些,都应给关注此事的民众有个交代。
3.“温情报道”滥情煽情适得其反
【事件】2月15日,甘肃省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启程。甘肃日报社主办的“每日甘肃网”微博发布了一则题为《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的视频报道,来自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的14名女护理人员全部被剃光头,她们在理发时流下眼泪,理发师还将剪下来的长发在她们面前“展示”。
这则报道引发网友们的质疑:“集体剃光头,是强制决定,还是自愿行为?医护人员流泪,是不满剃头,还是出征时的情感释放?”,“让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成光头是当地在博眼球、搞宣传”。[14]针对批评,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回应称,援鄂医护人员剃光头是为了防止感染,方便清洗,也是当事人的自愿行为。甘肃省妇联宣传部领导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报道由于拍摄方式、表达方式不恰当,确实引起了非常多的质疑,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报道中被剃光头的护理人员落泪有较复杂的因素,不能单纯解读为“因为剪头发而哭”,还包括即将赶往一线,与亲人离别等因素。
另一事件与之类似。2月19日,长江日报发表题为《病危时颤巍巍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的新闻,报道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47岁的肖贤友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捐献遗体的事迹。但是网友们在配图中发现,肖贤友遗书中还有一行字:“我老婆呢?”网友为此感动,称赞他“平凡而伟大”,同时也对长江日报刻意的选择性报道提出质疑。
疫情报道中被广大网友诟病的还有“87岁老人为抗疫捐出20 万,她的家却让人泪目……”、“杭州退休环卫工捐出10万元后,银行卡余额只剩13.78 元”等“倾家荡产式”捐赠报道,以及“援鄂女护士放下植物人丈夫毅然奔赴一线”、“流产十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医务工作者怀孕九个月,依然奋战在一线”等不近人情的抗疫英雄宣传。
【点评】中国记协网对此发表评论,提醒疫情报道要避免将“温情报道”变成煽情报道,“过分渲染、刻意煽情,就会适得其反”。[15]灾难事件发生后,以煽情报道宣扬人间大爱、无私奉献精神,已经成为一些媒体惯用的套路。学者黄月琴(2016)将其称为“社交网络时代媒体炮制的心灵鸡汤”——这种媒体所熟悉和惯常运用的话语运作技术,将新闻和情感混合搅拌,共生互补,建构着国民的现实感和道德秩序,并源源不断地生产集体意识、家国情怀与民族荣誉感。但需要注意的是,仪式激起情感,而不是催生思想和资讯。这样的报道套路一方面是掩盖信息贫乏,同时也会消解大众媒体的公共性和专业性。
针对女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报道,胡锡进在微博中指出,这个视频招致大量负面舆情,就是因为脱离了人们的平常心和世俗认知,过犹不及。“对于伤痕味太浓的奉献和格式化的有编排痕迹的各种拔高,年轻人的感受越来越复杂,乃至排斥”。他提醒说,各地在展示正能量和英雄主义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尊重网络上这种越来越强的心理,从而避免事与愿违,煽情遭到嘲讽,陷入难堪。[16]胡锡进提到的代际差异问题,反映了随着时代变化伦理观念的变迁。多年来我们大力宣传、着力塑造的英雄形象,是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通过精神的自我超越所升华,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谢保杰,2015:37)。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当然仍受到推崇,但是对于普通个体来说,往往难以亲近和效仿,更能打动他们的是普通人的道德观,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社会奉献。而部分煽情报道正是忽视了这一方面,就如东方网对女医护人员集体剃光头的报道所批评的那样:她们不是宣传的工具,她们也有尊严,也需要被尊重和保护。女医护的牺牲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不要再试图用她们的身体来做浓墨重彩的“宣传”,她们不应该被这样道德绑架。[17]新冠肺炎病危者弥留之际决定将遗体捐献国家,不忘自己的妻子,完全符合人情人性,令人感动,我们的报道不应忽视人情,更不能把人情与社会奉献对立起来,似乎体现了人情就会有损奉献精神似的。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受到网友的批评,媒体及相关部门也吸取了教训,之后的报道如《急诊科护士长被“强制休假”,东莞这家医院的霸道做法很暖心!》、《战“疫”紧急,十堰男子却收到了“强制休假令”》、《连续上班35天没休息 结果等来一纸休假书》等,既宣传了一线战疫人员的奉献精神,也蕴含了浓浓的人文关怀。
4.患者个人信息频遭泄露
【事件】12月7日,成都新冠肺炎感染者赵小姐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曝光,其中不但有她的姓名、身份证号、具体住址,还包括她前一晚每个时段的行程轨迹。网友们由此对赵小姐的私人生活展开各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评论,有人对她进行人肉搜索,还有人打电话、发短信对她羞辱谩骂。
次日,赵小姐发布道歉声明,其中表示,“我只是一个确诊患者,发现确诊后第一时间配合防疫部门做了流调工作,把自己的行踪如实地上报给防疫部门,以免疫情扩散”。“隔离期间,我看到网络上有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很多是对我和我家人的诽谤和谩骂,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攻击我,我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12月9日,成都警方通报,王某因散布泄露赵小姐个人隐私被处以行政处罚。
疫情期间,患者或相关人员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事件多次发生。比如,2月,山西临汾一男子擅自将微信内部工作群中严禁转发的“35名密切接触者名单”转发至其小区业主微信群中,名单内容涉及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公民个人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同月,云南省文山州5名医务人员因偷拍、散布新冠状感染患者的姓名、家庭详细地址和病程信息等,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处罚。7月,大连王某某擅自将微信内部工作群中严禁转发的涉疫情公民隐私信息转发至两个自己的亲戚朋友微信群中,并引发网民大量转发,大连警方对其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同月,重庆沙坪坝区一冷冻仓库部分进口冻虾外包装核酸检测呈阳性,某微信公号发布《重庆已购进口白虾顾客名单》,其中包括一万多名购买进口白虾的人员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等详细个人信息。顾客赵某起诉该公众号运营公司并胜诉,该公司被判决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1元。
也有专业媒体在报道中不慎泄露患者隐私。如7月2日,北京石景山一名女子被确诊,某卫视在报道其流调过程时,镜头中出现了文字清晰可辨的流调工作记录页面。
【点评】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民法典》,并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中规定了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2条)。“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第1034条)。2016年《网络安全法》已经对个人信息作出定义,《民法典》则增添了最后三项。泄露患者个人信息的往往是防疫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的本意或许只是想提醒自己的亲友,而没有考虑今天的社交媒体已经模糊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界限,手指动动却已触犯了法律,追悔莫及。
除了需要追究患者隐私泄露的源头责任,相关媒体平台也应担负其责任,及时屏蔽有关信息,阻断其泛滥传播链条。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社会情绪高度紧张,包括患者、疑似患者及密切接触者在内的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对疫情防控与社会情绪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江海洋,2020),因此在有关管理部门和疫情防控相关机构、组织履行职务时,需要公民隐私权的适度克减,在个人信息提供等方面予以积极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可以毫无原则地被公开披露,更不能藉疫情防控过度侵犯个人信息权益。比如有的城市计划将健康码追踪程序常态化,导入个人医疗等敏感数据,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同时这样的评分还会同工作单位、地理位置、社区治理等联系起来,针对不同场景进行排名和对比。这一计划被认为滥用疫情期间搜集的个人信息,会导致结构性的社会歧视。[18]医学界更是提醒,传染病患者不但身体和心理上受到影响,即便重回社会也往往受到歧视,应被视为弱势群体。疫情防控中所公开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个人信息,在疫情结束后应尽快消除其影响(关健,2020)。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有必要阶段性地将前期曾经公布的患者、疑似患者及密接者的个人信息从网络上删除,这也可以说是维护公民的“被遗忘权”吧。
5.疫情期间报道频现常识性差错
【事件】密集的疫情报道中,不少媒体忙中出错,闹了笑话。
比如,2月15日,华商报头条号“华商汉中”刊发的“抗疫大事记”集纳了多位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故事,其中《孩子出生不到20天,他却主动申请投入抗疫一线……》提到,刚起床不久的两个孩子稚气地问,“妈妈干嘛去了?”出生20天的孩子开口说话显然有违常理。第二天华商报致歉,表示编辑在整合几篇抗疫报道过程中因工作仓促出错,将其中两个事件混淆。再如,2月28日,辽宁卫视《第1时间》节目中,在播报沈阳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时,显示的日期为“2月29日、2月30日、2月31日”。还有3月2日湖北卫视在新闻节目中将一位援鄂医务人员信息标注为“江苏省合肥市”。7月13日北京头条客户端报道疫情期间血液供应情况时,将全市4.1万人无偿献血“5.1万单位”误写成“5.1万吨”。
【点评】总体来看这些都是常识性错误,严加审核可以及时发现并避免。低级错误频发,可能与疫情期间信息量大、媒体工作高度紧张有关。不过,俗话说“办报无小事”,范敬宜当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期间,每天坚持写值班手记,曾多次提醒记者编辑要注意文字的准确性,因为虽然是小的失误,但是经过编辑、主编、审稿、检查均未发现,出现在版面上,读者会笑话我们太没文化,成为笑柄,影响报纸的威信(范敬宜,1997:472)。准确,一向是新闻业的基本守则,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实际上没有哪家媒体能保证不出任何差错。有了差错,及时更正,是有效补救之道,也是体现媒体责任意识的操作惯例。从上世纪70年代起,纽约时报就固定刊登“更正”栏目,1993年修订了刊出程序,不仅要求“立即刊登”,而且只需编辑主任或代理主任同意即可刊出(李子坚,1999:128)。也许认为这点小错不值一提,或者觉得认错有失面子,很多差错我们没有看到更正的信息。
6.营销号恶意炒作带节奏
【事件】1月10日,微信公众号“青年大院”发布了《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以1987年中国政府应对大兴安岭火灾作为对比,批评澳大利亚政府救灾不力。文章获得大量点击,并被多家媒体、公众号转载。
文章很快引发批评:新京报评论认为,“这篇爆款文章‘把灾难当凯歌’,不仅是对生命和自然的亵渎,也是对历史事实、对常识的无知和扭曲”。[19]方可成发表文章《对不起,33年前的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凯歌》,引述中国青年报对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不仅有对救灾人员的肯定,更有对灾难的反思,对管理部门的批评,“不要再把悲歌唱成赞歌”是这组已成新闻史经典报道确立的核心理念。文章追踪“青年大院”的前身发现,其曾因发布编造煽情内容的《那个17岁的上海少年决定跳桥自杀》被封,公号虽然改头换面,但以流量为导向,炒作煽情的路数没变。[20]还有网友查询发现,“青年大院”运营商“浮光跃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同时操作着数个公众号,分别以不同的价值观导向煽动受众情绪,被称为“对冲式写作”,“全方位收割流量”。[21]2月28日,青年大院被微信平台处以“阶梯处罚”;12月18日,“青年大院”公众号被屏蔽所有内容,停止使用。
营销号编造新闻恶意炒作的典型案例还有疫情期间发生的“华商太难了”事件。3月初,数百篇标题极为相似的“疫情之下的某国: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的自媒体文章在网络刷屏。这些文章的情节如出一辙,仅仅更换了主角的姓名、从事的生意和所在国家。因炮制虚假文章,相关公众号管理人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2]【点评】“青年大院”引发争议后,“咪蒙”迅速公开表态撇清与自己的关系,但其运营套路显然一脉相承,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0)。这些自媒体营销号套用了传统的“煽情路线”,并进一步扩大和滥用虚构与“合理想象”的成分,通过组织化、集团化的造假方式,全方位收割流量,进行恶意营销。
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旨在通过产生强烈的震惊、愤怒或兴奋感的方式呈现事实或故事”。在大众化新闻业,“煽情”也是一种编辑策略:通过选择新闻故事中的事件和主题,通过措辞来激发读者情绪,获取最大的发行数量和广告收入。
自媒体时代,营销号最大的目标就是进行无差别的流量收割,将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同每个个体可能会关注的兴趣点联系起来,“最大化”地利用多种信息资源来攫取利益(Thompson, 1999)。在对用户取向、使用惯习掌握不够充分的条件下,通过左右开弓、快速更新的方式,再配合平台的智能推荐、流量分配,煽情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内容顶流。而这样的“套路”也因为可以被复制而导致煽情报道大肆流行。
煽情报道非常容易助长对事件的误解和偏见,还可能会操纵事实真相。而在恶意营销号传播的煽情内容中,“非虚构”与“合理想象”的边界被挑战。有的营销号会自认为“我们写的东西都是有依据的,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我们这是合理想象,我们是文学作品,不是新闻”,“这是创意写作”等等。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比如《古罗马日报》这样写在公共留言板上为了教育下层阶级而进行的“热情的新闻写作”(Stephens, 2007),也有19世纪60年代促进了期刊销量的英国“感觉小说”(Gabriele, 2009),但是这些内容无论是流传范围还是出发点,都和今天的营销号煽情内容不可同日而语。“青年大院”之类的推送,不仅将其思想操控、情绪鼓动风格表现得一览无余,还不断消解主流价值观,歪曲架空历史。这样的内容将严肃问题泛娱乐化、媚俗化、低智化,并且价值倾向严重偏差,会带来社会整体性的历史虚无感。
“青年大院”的母公司旗下有多个公号,正话反说、反话正说都是流量。而像炮制了“华商太难了”这样的网络科技公司则是将这种“复制性传播”进行了彻底的组织化和集团化。这种“话多没营养”内容的风靡,是网络时代助长“集体性倦怠”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指出,通过组织化、集团式地“漫灌”各种低质、无聊、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内容,社会将渐渐处于一种“认知麻木”状态:用户知道这些内容“可能”是假的,也知道没什么意思,但是因为数量太多,经常见到,也无法躲避,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形成信息倦怠;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会麻木和政治冷漠(Marwick & Lewis, 2017)。而一旦在社会上建立起这样的信息氛围,那么即便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新闻,也再难引发关注,受众对于内容的疏离将从底层消解社会信任和凝聚力。
7.“高管性侵养女案”报道平衡问题惹争议
【事件】4月9日,南风窗发表《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一文,讲述了48岁的烟台某跨国企业高管、某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独董、业内知名海归法务专家鲍某某以收养为名,从“养女”韩某某[23]14岁时就对其持续多年性侵的故事。报道称,鲍某某为了实施性侵,一直试图控制韩的精神和人身自由,韩某某重度抑郁多次尝试自杀。2019年4月韩某某向烟台警方报案,却被敷衍塞责,最后只得到一纸《撤案决定书》。
不过,南风窗的报道并未采访另一方当事人鲍某某,以及受理案件的当地派出所、检察院或提供检查的医院等第三方。文中存在多处主观性表述,如“由韩某某报案,掀开了这张父亲的‘画皮’”、“韩某某的抵抗情绪,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包围、瓦解”。且文中对“性侵”的过程、两人相处的细节等做了大量甚至涉嫌色情的描述,如“巨痛,从下体一直冲到肚子里来,她流血了”。
耸人听闻的故事掀起轩然大波,舆论对鲍某某骂声一片,同时也质疑烟台警方的处理方式。随后,相关公司表示解除与鲍的劳动关系,山东警方宣布重新立案调查。
4月12日,财新网发布苑苏文采写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一文。针对南风窗的报道主要采用韩某某一方的说法,“疑云”一文则主要根据鲍某某“通过中间人做出的书面回应”,以及曾经援助韩的志愿者和办案人员的视角,并与南风窗报道对照叙事,重构了女孩与鲍某某相处的故事。报道的编者按点明:“女孩在多地多次报警称未成年时遭跨国国企高管性侵,警方均未立案,高管则称双方是恋爱关系。这更像是一个自小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
财新报道从鲍某某视角展现的“疑云”并未带来舆论的反转,反而引起大量批评甚至谩骂,被指责采用单方面信源,“吃人血馒头”。作者苑苏文在朋友圈转发自己报道时的评论被截图流传,她本人也遭到人肉搜索。
4月13日财新发布致歉声明:“财新网4月12日刊发报道《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疑云》,引起舆论较大争议,我们认真核查,报道确有采访不够充分、行文存在偏颇之处,已在当日撤回报道。……有未经慎查明辨的仓促报道,我们诚挚致歉,并将做出修正和追踪报道。”
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某涉嫌性侵韩某某案调查情况:韩某某为改善生活条件,在网上看到鲍某某发布的“收养”信息后,主动与鲍某某联系,两人以“收养”名义开始交往并发展为两性关系。“经深入调查,未发现鲍某某违背韩某某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韩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证据。韩某某与鲍某某见面时已年满十八周岁,不属于法律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韩某某“多次报案、撤案,对外寻求帮助,均与其和鲍某某产生矛盾或两人关系出现问题相关,一旦两人关系恢复或和好,韩某某即否认报警或者要求公安机关撤案……未发现被鲍某某控制人身和通讯自由的情况”。
【点评】高管、性侵、未成年少女,这些关键词意味着它必将是一个引发轰动的事件,专业媒体在采写报道时应更加谨慎,特别注意报道的客观全面。在本案例中,南风窗和财新网的报道不但引发网络舆情,也引起专业争议,其中较多的是针对财新报道的批评。比如认为财新的报道提供了来自鲍某某的大量材料,但是在面对这些材料的时候,财新展现出的质疑不够。对于双方叙述中不一致的地方在交叉验证方面做得很不够(方可成,2020)。还有学者指出,财新的报道更大的问题出在整体的阐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上。尤其是新闻导语中那句极具暗示性的洛丽塔式话语(缺爱少女求爱的故事),设定了整个报道的总基调和定义边界,导致后续的素材无论如何呈现都会被限定在这个预设的框架之中。换言之,即便记者能够呈现出来自更多信源的不同陈述,文章导语所设定的这个解释框架也导致文章整体的倾向性是不可避免的(黄典林,2020)。尽管财新的报道明显具有为南风窗倾向性报道纠偏的意味,但在批评者看来,对于“打响第一枪”的媒体来说,在报道平衡方面存在缺憾也是可以理解的(方可成,2020)。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2020)对比了南风窗和财新两篇报道,发现南风窗报道中提到的35条事实性信息中,有4条出自韩母口述,6条出自韩口述,有多达16条没有交代消息源(其中有9条疑似出自韩口述),所有关键信息均出自或疑似出自韩口述。而财新报道的34条事实性信息中,有7条出自鲍某的书面说明,7条出自聊天记录,10条出自曾援助过韩某某的志愿者,仅有1条未交代消息源。同时,财新的报道还引用了大量南风窗报道中的女方说法予以平衡。
从平衡报道的规范性上,柴会群的梳理显示了两篇报道的高下。那么,为什么更体现专业性的财新报道反而受到更猛烈的批评?财新匆匆撤稿道歉是否被舆论绑架?这个现象背后彰显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具有轰动效应的议题引发汹涌而起的极化舆论面前,如何坚守专业媒体寻求事实真相的立场?有时确实很难,然而又是必须努力去做的。
8.无中生有的“南方洪灾专业媒体失声”反映深层问题
【事件】自6月2日入汛以来,我国江南、华南和西南地区发生多轮强降雨过程,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这是继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汛情:主汛期全国有751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长江、黄河、淮河、珠江、太湖等大江大河大湖共发生18次编号洪水,长江、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其中长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等等。
相关舆情研究报告发现,从6月5日到15日,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上,以“南方汛情”为主题的舆论开始发酵,呈现出“小幅发酵—突然爆发—平稳回落” [24]的形态。村庄被淹、房屋倒塌、城市道路以船为车、千年古桥毁于一旦的图片、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但同时,有不少网友质疑主流媒体对南方水灾没有突出的报道。6月11日,某公众号在《悄然消失的南方暴雨洪灾……》一文中写道:南方发洪水了吗?看朋友圈,一张张城市被洪水围困、高速公路被冲毁、汽车被困在“孤岛”的图片,触目惊心。但是看国内正规、权威的媒体机构所推送的新闻,又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洪水,举国上下风平浪静。……有网友撰文愤怒地发问:中国的媒体人都死绝了吗?本轮波及南方多个省的暴雨洪灾,为什么就没有国内的新闻媒体关注?为什么没有记者去报道?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南方暴雨灾区群众的遭遇?[25]7月1日,公众号“野火青年”发表《1122万同胞受灾,媒体为何集体失声?》的推文,指责媒体对南方洪涝灾害全面失声,“时至今日,留给我们的只剩好人好事,戏谑调侃”。“全面真空的环境,让我感到一丝害怕”。[26]其实检索相关媒体,无论是央媒还是地方主要媒体,对汛情都有浓墨重彩的报道。《人民日报》从6 月10日起在要闻版开设“防汛救灾 全力以赴”专栏,每天刊出3至4篇稿件;白岩松在7月11日播出的新闻周刊节目中说,2020年央视对汛情的报道是10年来最多的;庄永志对新闻联播7月2日到9月2日长江流域长达63天的应急响应期间与汛情有关所有报道进行统计发现,防汛救灾报道共有消息86.5条(含25则快讯,每则快讯计为0.5条)、总时长10732秒(约178分),平均每天一条多、2.8分钟。[27]财新、凤凰网、中国青年报相关领导在媒体访谈中也都认为专业媒体关于南方水灾的报道并不少,其中还有不少精品佳作。[28]针对“浮光跃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野火青年”恶意带偏舆论的行为,新京报发表评论称,“稍微留心下就知道,说媒体‘集体失声’只是一种视障。说得更确切些,不是媒体开启了静音模式,是媒体报道被‘野火青年’给消音了”。[29]白岩松批评说,这种为了流量、利益带节奏的自媒体,是舆论中的洪水,危害很大,应当露头就打。[30]【点评】此次对南方特大洪涝灾害的媒介呈现中,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出现了典型的“媒介间感知差距”(Gil de Zúniga,Weeks & Ardèvol-Abreu, 2017)。经典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强调媒介的中介化效应,比如拟态环境、知识沟、信息茧房、过滤泡等概念和假说,都涉及不同群体在特定媒介接触条件下对于外部环境感知的“差别”,但此次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清晰地呈现出社交媒体时代通过不同媒介形态感知信息的“差异性”:
首先,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与公众关注点不相匹配。“议程设置”一直是传统媒体的核心功能之一,“不能影响受众怎么想,但可以影响受众想什么”一直是其传播能力的体现。但对此次南方特大洪涝灾害的媒介呈现中,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至少在上半场表现尚有欠缺。而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则集中体现了广大用户和公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这也是此次事件中最应该被反思的要点。
第二,全面客观呈现无法弥补“时间差”带来的信息量不足。多家媒体机构反思此次特大洪涝灾害的报道时都提到,专业媒体依然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比如不会刻意逢迎用户兴趣,对信息的呈现力图客观全面,对不同消息来源会仔细甄别,要在多个不同参与主体间进行协调,以及进入现场需要时间和条件等。这些本身都没有问题,但这样一种“工作常规”遭遇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时,会因为“加速社会”中的“时间差”导致“信息量不足”。大量用户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内容生产和消费,这样的界面互动以一种传播的“光电速度”(保罗·维利里奥,2018:26-27)消灭了现实社会中传统媒体“人+交通工具+传播工具”的“生物+机械速度”。由于存在无法弥合的时间差,后者报道信息量不足、信息延迟等无法满足“加速社会”的传播要求。
第三,作为竞争性话语的社交媒体倒逼传统媒体的报道节奏。当前的传播生态呈现出从庙堂到街巷,从引导到迎合,从实时到适时的特点。社交媒体传播的下沉、渗透水平大大超过传统媒体;相比传统媒体所习惯的“舆论引导”方式,智能媒体通过算法整合用户画像、社交关系、全局热度所给出的智能推荐更加受到用户的青睐;而通过算法改变的信息流,并不特意关注信息呈现的“时间顺序”和实时性(real time),而是更加关注适时性(right-time),即在合适的时间向用户呈现适合的内容(Bucher, 2020)。这样的传播特征使传统媒体既无法感知自己的用户兴趣,也缺乏必要的工具和能力去整合用户。社交、智能媒体不再是传统媒体业务的衍生品和附属品,而是成为竞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逼迫传统媒体去跟随社交媒体热点。
第四,新媒体呈现的信息颗粒度相比传统媒体大大细化。在此次特大洪涝灾害的报道中,虽然主流和专业媒体反复强调自身的业务水平,比如维护知情权、强调个体体验等,但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报道却大多来自技术创新和社交网络,如无人机对洪涝灾害现场进行的全景航拍、损失了9000万元茶叶的茶农、安徽高考时考生穿着泳裤进考场等,这些既宏大又细微的内容,结合了事件的整体性和个体的独特体验,相比传统媒体上准确但冰冷的数字、带有门槛的术语、缺乏情感共鸣的套话,更加能够打动人心,也能够取得更具“穿透性”的效果。
第五,社会信任与媒介信任作为底层逻辑始终影响媒介传播效果。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通过后台数据发现,六七月份国内新闻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中印冲突、中美关系博弈、新冠疫情转折等重大国际国内事件。[31]而对于洪涝灾害,相对而言重要程度在一开始并没有被提得很高。这个结论也得到了财新、中青报等多家媒体的证实。但这样安排在特定的语境下也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对于一些临场感、现场感、个体感很强的新闻事件,社交媒体传播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如果将这种“比较优势”理解为是“被压制后的宣泄出口”,那么海量的用户生产将不是专业媒体工作的有力补充,而是变成了“打脸”的证据。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的生产协作,是同盟但可以不雷同,可以存在不同的维度、面向和层次,但这种协作是为了生产出更为充分的信息量,增加信息覆盖的颗粒度,而不是恶性竞争,彼此怀疑。而这需要不同媒体间形成良好的生态位,社会群体间相互信任,共同关注重大问题的发生和化解。
9.“做寿老人下跪视频”引发双重反思
【事件】8月29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致29人不幸遇难。事发时一位80岁老人正在办寿宴,他的老伴和多位亲友遇难。8月30日17:20,齐鲁晚报微博发布“襄汾饭店过寿老人下跪道歉:很内疚”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争议。
8月31日,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发布《这家山东媒体犯了众怒》,批评齐鲁晚报“单独截出老人下跪画面,做成短视频在各大平台发布”。“如此‘吸睛’的操作,自然获取流量无数,不过同时,此举也犯了众怒,网友们群起痛斥齐鲁晚报,各种骂声一片”。文章还透露,正是因为“齐鲁晚报记者口无遮拦,在采访李大爷时贸然发问:‘你老伴和你亲戚因为给你过生日去世了,你现在心情怎么样?’”才“诱导老人下跪”。文章对此评论说,“媒体是社会的守夜人,其关注和监督的对象,主要是权力而非无权者。在临汾坍塌事故的报道中,有些媒体把镜头一味对着受害的老人,这本身就是一种错位。这还不算,居然还敢吃人血馒头,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消费受害老人的痛苦,把他作为牺牲品”。
当天齐鲁晚报发表声明,表示对老人下跪视频引发的网友批评“高度重视,诚恳接受,特此致歉”,并宣布启动全面调查。
9月1日齐鲁晚报发布调查结果: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不存在违背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几名记者一起进入老人家中,看到两名消防应急人员和一位女士正在安慰老人。记者进屋后,并没有进行提问采访,而是一起安慰老人。当老人情绪激动,哭着要下跪时,本报记者连忙和消防应急人员一起上前搀扶,并连连说:“不怪你,不怪你”。同行三家媒体拍摄的现场视频,从不同角度还原了现场。整个过程持续一分多钟,没有记者提问,更没有记者提出“亲属遇难,您什么心情”之类的问题。记者一边安慰老人,一边说让老人休息。
9月2日“鱼眼观察”微信公众号中致歉,承认相关内容是在微博、知乎等渠道看到网友转发的信息,并没有核实,就写进文章里去了。
【点评】对于媒体是否应该发布老人下跪的短视频,相关讨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老人自愿接受采访,真情流露,藉此可以在更大范围表达歉意,郁结于心的痛苦也会稍微得到释放,因此不必过分指责媒体;反对方则认为这段视频有误导性,被着重描述的“下跪”、“内疚”会勾连出老人和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老人也是受害者。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台湾2007年修订的“公共电视节目制播准则”有一条要求,具有参考价值:尊重悲伤为私人的时刻,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不过度侵扰悲剧或灾难受害者,不强迫访问哀痛中的人。访问时应避免询问空泛冷血的问题(例如“你有什么感觉”),而应询问具体实际的问题(例如“你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等)。如果同时采访的其他媒体问了不得体的问题,尽量在报道中删除(陈力丹等,2012:323)。
“鱼眼观察”的作者也是一位媒体人,他在致歉中自省:“之前在做编辑工作时,对于事实性的信息,是极为敏感的,如果发现存在疑点,往往穷尽办法,也找到信息源头所在。但是做公众号以来,脑子里的这根弦逐渐有些放松了。看了老人自责的视频,加之网友们的讨论,脑子被情绪冲昏,加上为了追求发稿的速度,不加甄别,就想当然地选择采信,并引用在文章里。在喧嚣的新闻事件面前,没有保持足够的客观和冷静,为了抢时效和速度而不顾其他。”相信这是他诚意的反思,其中的问题,在自媒体写作盛行的今天也具有普遍性。社交媒体让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体写作规避了机构媒体完整、规范的把关制度,笔下可以更加潇洒恣肆,张扬个性,但也容易无所顾忌,失真失范;个体力量有限,同时却要不断更新,势必无法深入调查,难免道听途说,拼凑注水;不少自媒体作者不乏公共意识人文情怀,但在网络世界没有流量就没有可见度,有时候很难克服流量诱惑,不免耸动夸大以吸引眼球。当前,自媒体内容生产已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来源,这些结构性矛盾如何克服,仍有待深入的探索。
伦理讨论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在善与恶、合乎道德的正义行为与非正义行为之间做出理性的抉择(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2006:3)。经过这次事件,相信媒体在报道“悲伤”、“痛苦”的时候会更加谨慎;自媒体作者在一抒怀抱的时候也可以三思而后行吧。
10.西安地铁导演“正能量新闻”引发负面舆情
【事件】9月18日,微博“西安地铁”以“遇见最美西安”、“西安身边事”的标签,图文并茂地发布了一则暖心小故事:地铁工作人员发现一位女乘客踮着脚走路,一问之下才知道她被新鞋磨破了脚。工作人员立即拿来医药箱,为女乘客简单处理伤口,并送上创可贴备用。
但是,疑似受助女乘客发在朋友圈的澄清很快在社交媒体流传开来:女乘客主动找到地铁“爱心服务站”要创可贴,而不是工作人员主动发现的。整个过程“经过三个工作人员的来回工作交接,最后一个男工作人员让我稍等待,他去工作间取。在我等待了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带着他的相机,及他的领导,领导手里提着药箱来了。领导又对我进行了询问,缓缓蹲下,打开药箱,拿出创可贴。我反复说了,我只需要一个,然后给到我手中由两个变为四个,直到确定照片拍合适稳妥,才把创可贴交到我手中”。
令人啼笑皆非的“真相”引发网友质疑和媒体报道。次日,微博“西安地铁”发布“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说明,承认工作人员在未征得当事乘客同意的情况下拍照,微博运维人员在未征得当事乘客同意的情况下编发该微博信息,承认工作中存在“不细、不严等形式主义问题”。
【点评】这是一件小事,但所反映的问题却颇有典型性。2019年一项针对湖北省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调查表明,36%的被调查对象“比较同意新闻就是宣传”,“绝对不同意”的只占9%(廖声武,刘倩,2020)。对于新闻与宣传之间的界限认识不清,是造成类似荒唐事件的关键。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很多机构也开设了自己的微博、微信号,一方面发布相关服务信息,一方面对自身形象进行正面宣传。正面宣传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编个小故事或者表演戏剧等,而一旦采用了新闻报道的形式,就必须遵循真实性标准。西安地铁反复强调“未征得当事乘客同意”,貌似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场群众演员不太配合的演出,而在乘客看来,“西安地铁”微博作为“公众媒体”“做了不实的报道”。
类似为了传播“正能量”摆布新闻、制造新闻的事件还有不少。比如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一张成龙、熊召政、冯远征等明星委员坐在一起讨论《民法典》的照片在社交媒体流传,几位明星有坐有站,虽然表情生动,但他们的视线显然没有落到摊在桌上的《民法典》上。如果说这只是几位明星在会议期间的合影留念,但与其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张,就刊登在5月27日的中国艺术报上,俨然具有了新闻的身份。中国摄影报的评论也谈到这种屡见不鲜的现象:“每当重要会议结束后,一定会收到不少学习会议精神题材的照片,其中最多的是几个人坐的坐站的站、高高低低地看报纸的场景。这种有一定时效性的围看报纸的新闻照,好像是一些人绕不过去的表现手法(王冬斌,2020)。
其实,为了宣传不惜摆布、组织新闻的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新闻界有所讨论(晋永权,2009),但直到今天仍然“绕不过去”,而且随着新闻行动者的多元化又有泛滥之势,这里面,既有新闻观念的问题,也关涉着党风、政风问题。
11.公关对新闻业隐秘操纵之冰山一角
【事件】8月21日,一组微信群聊天截图在社交媒体热传:在“北京保利媒体群”中,保利地产一名高管要求群里的媒体人在朋友圈转发其宣传稿,“没转发的移出本群”。很多记者愤而退群。此事引发热议,次日该高管致歉,称“昨晚在群里的发言和表述确系我本人唐突,严重失当,给各位朋友们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也破坏了与媒体之间本应相互依存、互相成就的良好关系”。
9月18日,新京报一名记者以“蜉蝣”网名在豆瓣发表长文《为了哄大明星开心,报社主编把我开除了》,叙述了自己8月份采访某徐姓艺人,徐某团队曾多次修改采访提纲,成稿后又几乎逐句修改,甚至在截稿后再次提出修改要求,不允许提某电影的名字。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报社,没想到部门领导并没有保护记者的独家采访信息,反而直接按艺人团队意见修改后发稿。因为“他能接受你的采访,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徐某以前帮过报社的大忙”。
“蜉蝣”连续发帖,在网络上沸沸扬扬,但是新京报方面始终未做公开回应。我们撰写本报告时发现,“蜉蝣”在豆瓣的原帖已经删除。
【点评】这两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内幕详情都不够清晰,但足以透露出公关与媒体复杂关系的冰山一角。
长期以来,媒体与企业公关就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公关需要利用独立媒体的表象发布其信息,来维持其可信的表皮(威廉·迪南,戴维·米勒,2014:271);而如果没有这些存有利益关系的消息来源的话,没有任何记者可以只靠突发新闻填满所在媒体的新闻洞(甘斯,2009:153)。
国际新闻业的研究证实,愈来愈多的新闻记者将新闻收集工作交给公关人员去完成,即使是最大的报纸,也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资讯来自于公关稿件(press releases)。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媒体中也很普遍。这意味着,公共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道内容,甚至成为社会真实的首要界定者(primary definers)(陈先红,2012)。丹尼斯和梅里尔(2019)分别扮演正方和反方,阐述了“公共关系操纵着新闻”与“公共关系提供一种必要的新闻服务”这两种难以遽下断语的对立观点。但即便把公共关系看作新闻服务,也要以公关提供新闻线索—媒体独立采编报道为前提,而决非公关给媒体审稿改稿,甚至要求媒体原封不动转发宣传稿。在媒体艰难转型的当下,企业公关对媒体的隐秘操控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上述案例中对媒体人颐指气使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媒体伦理教材中,对公关与新闻的关系都十分重视,大多有专门的章节加以探讨;而国内几种知名新闻院系的教材中,对这一话题大都付诸阙如,这既是学术研究上一个亟需弥补的方面,也是媒体伦理责任上亟须给受众一个交代的环节。
三、讨论与结语
本课题选取的2020年传媒伦理事件虽然只是个案,但已能管窥随着传播环境的大变革,传媒伦理出现的新趋势、新问题。
1.新的媒介环境产生新变化
延森将媒介融合理解为经过数字技术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传播形态的网络化整合。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新编码和再媒介化,跨越不同的物质载体与感官形态(延森,2018:61)。查德维克(Andrew Chadwick ,2017)将这种多元行动者以及组织边界模糊的新传播生态称为混合型媒介系统(the hybrid media system)。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普通用户对新闻传播的参与,使新闻从一种专业活动变成社会化活动(刘鹏,2019)。大量伦理争议,正是由于这种混杂状态下发生的。以“信息疫情”现象为例,传统媒体时代科学传播主要是建基于科学共识的信息在科学家共同体、政府决策机构、专业媒体中单向流动,经过重重把关之后才到达受众。而社交媒体时代疫情信息就像新冠病毒,在社会网络中以更变化多端的路径和更快的速度更广泛地传播。学者对来自推特等国际主要社交媒体关于新冠肺炎的传播大数据进行分析,将信息传播同流行病传播模型匹配起来发现,被标记为“可靠来源”和“可疑来源”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模式几乎没有显著差异。这项研究证明信息的传播是由特定社交媒体强加的交互模式或参与主题的用户组的特定互动模式所驱动的,社交媒体平台确实存在一定的谣言放大机制(Cinelli et al., 2020)。对此,梵·迪克等提出以社交媒体为中心的网络化离心力互动模式(见下图)。其实,不仅仅是科学信息,其他领域的公共讨论中信息交流模式同样呈现巨变,难免出现种种扭曲错乱以及不适症状。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将事实、观点、情感等混搭在一起(hybridity),事实当中又混杂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可能发生的事实、希望发生的事实等等(Papacharissi,2015)。即便是专业媒体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时也会与传统媒体版本呈现新闻框架的不同(刘慧雯,2020),新的传播生态,无疑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公共讨论的话语面貌。
孙玮认为,“信息疫情”作为一个概念浮现,至少说明在当下“信息处置成为全球应对重大公共事件至关重要的议题。信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信息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价值,是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信息也展现出惊人的破坏性力量。当前处置信息的方式遭遇挑战,人类社会现有的信息系统失灵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而普遍”(上观新闻,2020)。若干传媒伦理案例正展现了这种新传媒生态下的破坏力。
对于新的混合型传播生态,当然要重视大量错误信息甚至阴谋论等破坏性传播产生的可能,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渠道,而且社交媒体具有“公众声音放大器”的效果,提供了一种平衡力量,“来平衡人们感受到的体验与官方机构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对它们的缺乏信任”。因此,无论科学界还是专业媒体、政策制定者,都需要重视这场传播革命,邀请公民等非专家一起,来为后新冠社会寻找制订新的战略(van Dijck & Alinead, 2020)。
2.围绕新闻业边界的挑战与竞争
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新闻学使用规范标准和道德原则来进行边界的区分:区分自己职业中的“好”和“坏”成员;区分内部人士和外部人士(Singer, 2015)。但在新的传播生态下,新闻业正在“解体”,以至于不再有一个稳定的实体可以贴上新闻业的标签。谁算新闻工作者,什么算新闻工作,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新闻行为,什么是越轨行为,都出现游移模糊的情况(Carlson, 2015)。多起伦理争议都是专业媒体之外的行动者的参与而引发的。比如西安地铁事件中“犯错误的”是“微博运维人员”;中国艺术报刊出的明星摆拍,摄影者是参会的政协委员——由于疫情防控影响,记者无法进入现场,于是采取了邀请两会代表委员当记者的创新措施,虽然很能体现媒体融合的特色,但暴露的问题也颇有媒体融合的特点。外部行动者一旦闯入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带入他们原来的伦理规范。比如李文亮在微信群中发布“非典”的消息,实行的是朋友间要共享重要生活信息互相帮助的伦理标准(刘鹏,2020);传播疫情患者隐私的不少是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或许有炫耀自己掌握独家信息的心态,同时也不乏提醒亲友注意防范的善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泽利泽将新闻工作者视为一个阐释性社群,他们通过各种专业讨论共享职业价值、建构职业认知、确立职业权威、设立职业边界,同时也组成职业共同体(Zelizer,2017)。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诸多议题上中国的机构媒体工作者尚无法形成共识,在疫情期间围绕廖君获奖等争论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新闻实践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未来还会有更多对新闻业边界的挑战和竞争会以传媒伦理争议事件的面目出现。
3.新价值观与旧宣传模式的冲突
本次疫情报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体现了平民性:苦难不再被分成等级,普通人的不幸也被有尊严地记录着;医护人员、志愿者,甚至外卖员、快递小哥成为被大家记住的抗疫英雄,他们的行动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正常生活,是那么依赖于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忠于职守,依赖于他们的善良、同情和特殊时期的自我奉献(林猛,2020)。报道的变化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李泽厚(2016:41)认为,现代社会以前,个人经常是从属于群体的,个体以群体生存、延续作为生活的目标原则,而现代社会以降,自启蒙主义突出了理性和个人,个人成为轴心并以之建立,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对个体权利意识的尊重,是现代性观念的特征。就像一位年轻的博主“阿部部”的“热帖”所说的:我特别喜欢那个“一线抗疫战士要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马上安排”的新闻,我也特别喜欢“抗疫战士穿着好的防护服带着自豪展示给家人看”的新闻,特别喜欢“山东抗疫人员到了一线,马上就给他们蒸上了馒头”的新闻。……我们不想看到一线抗疫人员流汗还流泪,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付出了很多了;我不想看到他们牺牲所有,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更想看到的是他们的每一滴眼泪都被珍惜,每一点心愿都能被听见,我希望他们能够在疫情结束放下担子的时候能好好地休息一下。不要让他们不敢说累,不敢说苦,不敢说痛。[32]这种想法已成为我们社会新的主流价值观,如果媒体在宣传报道中违背这种价值观,难免受到大众的指责。
新闻宣传上的惯性和惰性,是造成伦理争议事件的重要原因,往往让正面宣传反而起到负面效果。比如3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提出,“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地摊经济”随即成为热议话题。但是一些媒体迅速推出“大排档业主:每天收入三万元”、“90后女子摆地摊日卖4千,520奖励自己一辆奥迪”、“地摊经济火了!济南老板日入4万”等报道,也引发不少质疑。这些新闻标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摊经济”的成效,比如那位大排档业主3万元的收入是在允许出店经营的前提下挣到的,而且也不是“每天”挣3万;而那位摆地摊的90后女子其实是买了一辆“二手”奥迪。这些一窝蜂、夸大拔高性质的报道,其实就是多年前新闻界批评的主题先行、带着观点找材料的做法。
另外,民族主义、民粹思想、女权运动等各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冲突不断涌现,也对媒体如何把握好时度效,处理好伦理争议问题提出挑战。■
注释:
①新华社(2020)。《中央指导组与抗疫一线媒体记者座谈: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检索于https://share.gmw.cn/politics/2020-03/27/content_33692749.htm。
②齐鲁网(2020)。《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榜发布,“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等谣言在列》。检索于 https://new.qq.com/omn/20201207/20201207A06KQO00.html。
③WHO(2020)。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situation report。检索于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30778。
④WHO(2020)。《管理COVID-19信息疫情:促进健康行为,减轻错误和虚假信息的危害》。检索于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3-09-2020-managing-the-covid-19-infodemic-promoting-healthy-behaviours-and-mitigating-the-harm-from-misinformation-and-disinformation。
⑤中国新闻网(2020)。《喝甲醇能治新冠?调查称约800人因新冠病毒假消息身亡》。检索于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20/0814/c1007-31822405.html。
⑥WHO(2020)。《世卫组织总干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⑦WHO(2020)。《管理COVID-19信息疫情:促进健康行为,减轻错误和虚假信息的危害》。检索于https://www.who.int/zh/news/item/23-09-2020-managing-the-covid-19-infodemic-promoting-healthy-behaviours-and-mitigating-the-harm-from-misinformation-and-disinformation。
⑧《世界卫生组织:病毒之外,“信息疫情”同样会危害健康》。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370984798_282570.?spm=smpc.content.huyou.5.1589029925460ZEmD9Eb。
⑨WHA(2020)。《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应对 COVID-19 疫情》。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3/A73_R1-ch.pdf。
⑩北京日报(2020)。《迷之操作!河南一女子外出购买双黄连11天后确诊》。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607222470176154&wfr=spider&for=pc。
[11]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2020)。《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声明》。检索于http://www.cas.cn/tz/202002/t20200201_4733194.shtml。
[12]第一财经(2020)。《白云山板蓝根对新冠病毒有效?钟南山:有人断章取义》。检索于https://www.yicai.com/video/100810607.html。
[13]邸利会(2020)。《双黄连“治疗”新冠病毒?当事院士试图澄清,专家表示不可思议》。检索于https://new.qq.com/omn/20200201/20200201A0D8E200.html。
[14]人民日报(2020)。《“剃头”驰援?细致贴心的保障才是真关爱》。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8869596538956580&wfr=spider&for=pc。
[15]中国记协网(2020)。《战“疫”报道如何增强专业性实效性?请听专家建议》。检索于http://www.zgjx.cn/2020-02/19/c_138799270.htm。
[16]传媒内参(2020)。《用“给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做宣传,合适吗》。检索于http://k.sina.com.cn/article_5617179120_v14ecf59f001900q0zs.html?from=ent&subch=oent。
[17]东方网(2020)。《东方快评丨女医护集体剃光头,这样的宣传妥吗》。检索于http://pinglun.eastday.com/p/20200218/u1ai20357349.html。
[18]《渐变色健康码离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还有多远》。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398263993_223323。
[19]新京报(2020)。《灾难就是灾难,别把它变成“打鸡血素材”》。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13/doc-iihnzahk3812029.shtml。
[20]方可成(2020)。《对不起,33年前的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凯歌》。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460073790341260。
[21]三言财经(2020)。《“青年大院”被处罚无法搜索,对冲式写作被指全方位收割流量》。检索于https://36kr.com/p/1725176053761。
[22]北京日报(2020)。《不是“华商太难了”,是营销号“失控了”》。检索于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20-03-19/doc-iimxyqwa1778897.shtml。
[23]为保护隐私,各媒体报道中对当事女孩用了不同化名,方便起见,本文统一采用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中的名称表述。
[24]蚁坊软件(2020)。《南方汛情舆情专题研究分析》。检索于https://www.eefung.com/hot-report/20200618164100。
[25]《悄然消失的南方暴雨洪灾》。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NzQ2OTcyMA==&mid=2247485212&idx=1&sn=2ad4d5b59995b3b7a1dcacfa6accdcbd。
[26]《1122万同胞受灾,媒体为何集体失声》。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y1nfVcMdhe6kGGxSk4wTkg?url=https%3A%2F%2Fmp.weixin.qq.com%2Fs%2Fy1nfVcMdhe6kGGxSk4wTkg&share_menu=1&sinainternalbrowser=topnav&mid=4522181810223727&luicode=10000011&lfid=231522type%3D1%26t%3D10%26q%3D%23%E6%B4%AA%E7%81%BE%23&featurecode=newtitle&u=https%3A%2F%2Fmp.weixin.qq.com%2Fs%2Fy1nfVcMdhe6kGGxSk4wTkg。
[27]庄永志(2020)。《新闻联播》2020防汛救灾报道简析。《青年记者》(12上)。
[28]南都观察(2020)。《关于洪水的报道少了吗?为什么有人说“媒体失声”》。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410152620_481285。
[29]新京报。《“野火青年”们,别假装关心洪灾受灾同胞了》。检索于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20/07/04/745196.html。
[30]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自媒体称“媒体只见疫情不见汛情”,白岩松驳斥:这类操作才是舆论中的洪水》。检索于http://m.news.cctv.com/2020/07/13/ARTIdKw1WTG7Fos0AMLSSfCh200713.shtml。
[31]南都观察(2020)。《关于洪水的报道少了吗?为什么有人说“媒体失声”》。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410152620_481285。
[32]传媒内参(2020)。《用“给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做宣传,合适吗》。检索于http://k.sina.com.cn/article_5617179120_v14ecf59f001900q0zs.html?from=ent&subch=oent。
参考文献:
保罗·维利里奥(2018)。《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柴会群(2020)。“弱者”的谎言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溃败——评《南风窗》与《财新》对鲍某涉嫌性侵案的报道。微信公众号“红嘴乌鸦”2020年5月9日。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g-aIkalL7DUiETMzaX-Omw。
陈力丹等(2012)。《中国新闻职业规范蓝本》。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陈娟,郭雨丽(2020)。社交媒体与疫情:对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测、沟通与干预。《新闻记者》,(4),60-68。
陈先红,陈欧阳(2012)。公关如何影响新闻报道:2001-2010 年中国大陆报纸消息来源卷入度分析。《现代传播》,(12),36-41。
范敬宜(1997)。《总编辑手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方可成(2020)。《“高管性侵养女”案中的媒体表现》。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2020年4月14日。检索于http://newslab.info/2020/04/bao-yuming-sexual-assault/。
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2006)。《媒介伦理学》(李青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健(2020)。从伦理和法理角度谈突发公共卫生疫情防控实践及研究中的个体权益。《中国医学伦理学》,网络首发2020-03-27。
赫伯特·甘斯(2009)。《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黄典林(2020)。财新的鲍案“报道”为何不可接受?微信公众号“典林同学”2020年4月13日。检索于https://mp.weixin.qq.com/s/cUR-XOdMY9rCplmXC-iejA。
黄月琴(2016)。“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9),114-118。
江海洋(2020)。论疫情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学报》,(4),183-194。
晋永权(2009)。《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北京:金城出版社。
廖声武,刘倩(2020)。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现状与思考——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新闻记者》,(10),73-79。
李泽厚(2016)。《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青岛:青岛出版社。
李子坚(1999)。《纽约时报的风格》。长春:长春出版社。
刘鹏(2019)。用户新闻学: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学开启的另一扇门。《新闻与传播研究》,(2),5-18。
刘鹏(2020)。全世界都在说:新冠疫情中的用户新闻生产研究。《国际新闻界》,(9),62-84。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0)。2020年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新闻记者》,(1),3-21。
上观新闻(2020)。复旦大学教授孙玮:当信息也成为疫情,我们如何寻找真相。检索于https://xw.qq.com/cmsid/20200620A0IWNB00? f=newdc。
汪翩翩等(2020)。融合与分化:疫情之下微博多元主体舆论演化的时序分析。《新闻大学》(10):16-36。
王冬斌(2020年9月4日)。老生常谈说摆拍。《中国摄影报》(1)。
威廉·迪南,戴维·米勒(2014)。新闻,公共关系和制造舆论。卡琳-沃尔·乔根森,托马斯·哈尼奇编《当代新闻学核心》(张小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谢保杰(2015)。《主体、想象与表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闫宏秀(2020)。疫情下的伦理与人文之思②|“信息疫情”的数据伦理学应对。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378940。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2020)。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健康传播伦理共识。《中国医学伦理学》,(4),507-510。
BrunceA. (2018). Gatewatching and News Cura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Carlson, M. (2015).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CarlsonM.& LewisS.C. (ed.)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New York:Routledge.
ChadwickA. (2017).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nelli, M. et al. (2020). The COVID-19 social media infodemic.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0-73510-5.
GabrieleA. (2009). Reading Popular Culture in Victorian Print: Belgravia and Sensation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Gil de ZúnigaH.WeeksB. & Ardèvol-Abreu, A. (2017). Effects of the news-finds-me perception in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use implications for news seeking and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2(3)105-123.
José van Dijck & Donya Alinead(2020). Social Media and Trust in Scientific Expertise: Debat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Netherlands. https://doi.org/10.1177/2056305120981057.
PapacharissiZ. (2015) towards New Journalism(s)Journalism Studies16:127-40.
SingerJ.B. (2015). Out of bounds: Professional norms as boundary markersIn CarlsonM. & LewisS.C.(ed.)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New York:Routledge.
StephensM. (2007). A History of News (3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wick, A. & LewisR. (2017). Media manipul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line. New York: Data & Society Research Institute.
ThompsonJ. (1999).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In Mackay & O’Sullivan(eds.). The Media Reader: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Zelizer, B. (2017). 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本文执笔:刘鹏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方师师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侠系上海报业集团主任编辑。感谢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对本课题的支持与指导。感谢课题组专家《新闻记者》特聘顾问魏永征、吕怡然、贾亦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白红义教授的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