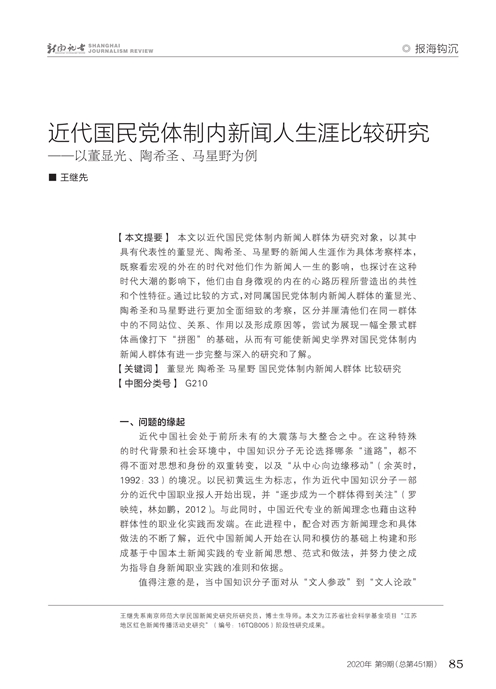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生涯比较研究
——以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为例
■王继先
【本文提要】本文以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的新闻人生涯作为具体考察样本,既察看宏观的外在的时代对他们作为新闻人一生的影响,也探讨在这种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他们由自身微观的内在的心路历程所营造出的共性和个性特征。通过比较的方式,对同属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的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考察,区分并厘清他们在同一群体中的不同站位、关系、作用以及形成原因等,尝试为展现一幅全景式群体画像打下“拼图”的基础,从而有可能使新闻史学界对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有进一步完整与深入的研究和了解。
【关键词】董显光 陶希圣 马星野 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缘起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大震荡与大整合之中。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不得不面对思想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以及“从中心向边缘移动”(余英时,1992:33)的境况。以民初黄远生为标志,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部分的近代中国职业报人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一个群体得到关注”(罗映纯,林如鹏,2012)。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专业的新闻理念也藉由这种群体性的职业化实践而发端。在此进程中,配合对西方新闻理念和具体做法的不断了解,近代中国新闻人开始在认同和模仿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基于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的专业新闻思想、范式和做法,并努力使之成为指导自身新闻职业实践的准则和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从“文人参政”到“文人论政”的转变而迫切需要一个平台延续自我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时候,新闻事业恰好成为首选。①从一开始,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就被当时新闻人所具有的“文人论政”或“文人参政”的情结所浸染,并成为他们实现“文人报国”价值追求的工具和手段。在救亡图存和国家现代化目标统揽下,为实现自身理想,近代中国新闻人对现实中的各种“主义”及其实现“路径”做出了不同理解、倾向和选择;而这既为他们提供了特定的发展空间和不同的发展资源,也促成他们在新闻工作中展现出不同的个体风格。这一点,对于矢志投身体制内的新闻人而言,尤为明显。同时,对于同一条“道路”上“走法”的不同理解、倾向和选择,既导致了他们共性的形成,也推动了他们个性的发展。本文选择同为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重要代表的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一认知。
正因如此,本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将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这三位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放在同一“舞台”上进行考察,通过分析他们在时代大环境中如何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来处理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形成不同的“舞台站位”等,以期尽可能地展现出这个群体的不同侧面,并进而为更加细密的全景式考察打下“拼图”的基础。在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这三位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身上,这种彼此之间的共性,尤其是个性,也就是“站位”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在群体全景中的个性(或是说差异性和多样性)又是如何展现的?等等。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和旨归。②
二、比较的可行性分析与研究文本的选择
我们认为,要厘清和解答以上若干问题,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是一条合适的途径;而鉴于目前本文所研究的文本,基本以回忆性著述或自述(档案)为主,因此对研究文本做一定的梳理、考证和鉴别,也应是本研究的基础和开端。
(一)比较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都是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的代表。他们三人选择的“道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各自的新闻人生涯中所处的体制内“大环境”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③
第二,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三人都曾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的重要岗位上任职,都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地位,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尤其是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都作出过贡献。④尽管他们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尽管旁人对他们的新闻人身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或部分划归“新闻人”这一群体。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交集,我们才能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个社会条件和同一种体制内的新闻事业圈中以比较的方式探讨三位新闻人的异同。
第三,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三人曾长期共事,都属于“侍从在侧”而从未有实质的“异议在外”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实际上,他们与蒋介石、蒋经国(以下简称“两蒋”)一直处于一种“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所说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asymmetry of power relation)的关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两种选择:顺从,从而留在体制内获得“资源”;反抗,从而成为“敌人”被剥夺“资源”(林淇瀁,2008:333)。显然此三人都选择了前者——这是一种共性;同时,更关键的是,他们各自的新闻人生涯由于家世、所受教育、实践经历、个人理想等的不同,而在新闻事业的认知感悟、做事方法乃至做人态度、处世之道上都有很大不同,继而人生奋斗的结果也各有不同——这是一种差异。或者说,此三人分别代表了那一时期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中的三种不同的“角色”,且差异鲜明。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上述三个理由,我们认为将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作为人物对比研究的样本,是有效而可行的。而通过上述比较研究,发现、分析和总结比较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差异性或多样性,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进行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全景式考察。
(二)研究文本的选择
作为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圈的代表人物,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的经历阅历之丰富,思想变化之复杂是无法在简短篇幅内并述的,因此只能择其要点而言之。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此三人亲笔撰写的三部自传体文本(即《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八十自序》、《马星野自述》)为分析的蓝本,同时参照其他资料,提炼出他们在各自新闻人生涯中的特点,发现其中规律。
《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由董显光本人以英文撰写,成文时间不早于1959年。⑤1973年,曾虚白以近80岁高龄将其翻译为中文并公开发表。这部自传共24章,以时间为序,以记述事实为主,记载了董显光自1887年出生至1959年底这70余年的人生,其中包括大量的新闻事业生涯内容,且颇多感悟与体会。笔者参考的是1981年《新生报》出版部在台北再版的文本。
《八十自序》成文于1978年,亦即陶希圣80岁时亲笔撰写的一部类似“生平简记”的著作。该文共分24个部分(含余论一段),同样以时间为序,逐一列述其80年人生历程中的诸多重大事件,其中对于家世、求学、从教、治学、从政的经历及心得等均有涉及,是目前研究陶希圣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之一。⑥文本所涉及的有关新闻事业生涯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十至十二、十六、十八至二十一、二十三及余论等十个部分中。笔者参考的是1979年食货出版社在台北出版的《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中刊载的文本。
《马星野自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952年4月12日,记述的是马星野43岁之前的人生经历;第二部分写于1954年6月29日,记述的是其1952年5月12日至1954年6月29日这两年又一个半月的经历。在1952年撰写的部分中,马星野以时间为序,分“家世”、“学历经历”、“服务时之功过”、“生活状况”、“最钦佩之长官师友及工作同志”、“思想与信仰”、“自我批评”、“今后之抱负与志愿”等八个部分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1954年撰写的部分中,马星野从“工作情况”、“生活状况”、“实践训词心得”、“研究心得”、“对于实践风气之观念”、“今后之志愿”等六个部分对两年多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综述。⑦这部自述不仅比较全面地记载了马星野这段40多年的人生经历,主要是新闻人生涯,还记载了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量感悟、反思和展望;更重要的是,因这部著述没有公开发表,故其中的内容和感想可能更加贴近马星野本人当时面对的现实环境以及相应的真实心态。笔者参考的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马星野档案》中的手稿文本。
三、相同的时代与道路,不同的感悟与站位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尽管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都是在同一个时代,同样走在国民党体制内道路上的新闻人,但由于他们身处的政治生态、自身对新闻人概念的认知,以及家世、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等不同,因此他们在同一条道路、同一个群体中显然有着不同的感悟、选择与站位。
(一)身处的政治生态不同,形成了与国民党体制核心“距离”的不同⑧
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作为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都曾在近代国民党新闻宣传“中枢”盘桓,因而就他们身处的政治生态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1.他们同是国民党党员,而入党动因却各有不同。
1925年,时为上海大学教授的陶希圣加入国民党,时年26岁;1927年,马星野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政校前身)以学生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年18岁;1934年,董显光于上海《大陆报》时期加入国民党,时年47岁。
尽管三人成为国民党党员对他们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人生涯都起到了“开启大门”的作用,但他们各自入党的动因却有所区别:董显光为国民党服务最早,加入国民党却最晚。1913年,时年26岁的董显光回到国内就开始为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工作,但他当时却没有加入组织——他只是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为其工作而已。他一直是个基督徒(董显光,1959?/1981:70)。直到1934年以后,他在国民党对外宣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并由此和蒋介石关系日益紧密,这才在蒋亲自“提示”下正式入党(董显光,1959?/1981:126)。因此,他加入国民党可说是当时国民党对他有迫切需求所致。
陶希圣参加国民党最早,介入国民党体制内的工作也最早。他在加入国民党之前的学生和学者生涯都是沿着“经世致用”的路径,围绕“文人参政”的目标推进的。当他的政治主张同当时国民党的要求相契合后,他的表现被国民党看中也就顺理成章了。⑨然而由此直到“悬崖勒马”⑩前,他一直未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局势及国民党内部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直到1942年他返回大后方,并立志追随蒋介石后,才终于稳定下来。[11]因此,他加入国民党可以说是一个个人主观愿望和国民党客观需求相互配合的结果。
马星野加入国民党时年龄最小。年龄最小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主观上,他当时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已经对国民党及其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而是进“党校”读书的必然要求;二是在客观上,他受国民党影响最深。“余自……进中央党务学校,同时入党,始系统研究主义。……而使余真正之主义信仰日坚。……余一生之思想,于此短时间内铸成定型”(马星野,1952)。因此,他加入国民党除了满足求学的实际需求外,也还多了一层藉此从政的愿景。
正因接触国民党及其主义的环境、原因和动机等不同,他们三人所受的影响也就各有不同:对于董显光而言,影响应该是最小的,因此他在回忆录中更强调他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效果,以及自己的感慨;对于陶希圣而言,影响应该是最为理性的,因此他在回忆著述中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多是采取一种“学术”的态度,非常理性地说明其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和作用;对于马星野而言,影响应该是最为感性和深刻的,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对于国民党的“主义”采取了一种近乎“信仰”的态度,是必须坚持贯彻的“最高标准”和“行动指南”。
2.他们与蒋介石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密切的“程度”不一。
董显光与蒋介石同龄,且曾是蒋的老师(董显光,1959?/1981:98)。[12]然而他与国民党的联系,却起自孙中山(董显光,1959?/1981:61)。从为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工作开始,他在主观上就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受体制的约束(董显光,1959?/1981:67)。即使与蒋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之后,他也试图保持着这种状态。就董个人而言,他对蒋怀有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出于爱国和对蒋个人的尊重,而不是崇拜(董显光,1959?/1981:97-100)。这从他接受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的“劝说”,决定担负外电检查工作的过程可见一斑。而端纳的这次“劝说”显然是受命于蒋介石夫妇。[13]在进入国民党体制后,董显光依然希望继续保持相对的“独立”状态,不论是在国民党的宣传部门,亦或国民政府新闻机构,他始终在做着似乎只有他才能胜任的对外宣传工作,不愿与他人他事有太多瓜葛(董显光,1959?/1981:125)。蒋对于董的专业水平和“独立”的个性是了解的,因此这就形成了蒋既充分信赖董为他的对外宣传服务,又不把董真正放在国民党“中枢”地位上的局面。董与蒋的关系中,时代因素至关重要:当特殊的时代需要董的专业服务时,他就被看作是“一个专为政府排难解纷的人”(董显光,1959?/1981:122-123),他与蒋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一些;当世易时移,董的“独立”个性和意愿,又会使得他与蒋若即若离。这在董的后半生不得不脱离他所心爱的新闻事业而转入其他领域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董显光之于蒋介石,更像是一个“伙伴”。
陶希圣的思想和行动以1942年为界不停摆动:之前,他最初的“社会政治思想路线,左亦不至共产主义,右亦不至国家主义”(陶希圣,1964/2009:93),随后其成为汪精卫团体的骨干,继又弃汪投蒋;之后,他“出乎意料”地得到蒋的重用,担任蒋的“侍从室第五组”组长,因感蒋之知遇之恩,以至于“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陶希圣,1978/1979:25)。这种“自毁其名”(陶希圣,1978/1979:47)的做法多少有一点中国传统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李杨,范泓,2008:83-84)。抗战时期,陶希圣在《中央日报》做总主笔,负责社论,“那时候《中央日报》社论有关国际问题都由自己多写一点,因为抗战时期中央日报的社论代表蒋委员长、代表国民政府”(陶希圣,1987/1988:48)。甚至他的夫人陶万冰如(时间不详/2009:369)在回忆中也认为陶希圣是替蒋做事的。因此我们认为,陶希圣与蒋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蒋的报恩之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蒋的感激与由之而来的忠诚;而他这种中国传统文人深厚的“滴水涌泉”的性格和价值观是蒋能够信任、把握和重用他的重要原因。[14]因此,陶希圣之于蒋介石,在1942年以前,是国民党内的“政敌”;1942年后,则是一种类似于“近侍”的角色。
相较于董显光和陶希圣,马星野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单纯——他从18岁开始即受教、受业、受制于“蒋家”,从未与国民党和“蒋家”有过实质的“脱幅”;从权力的对称性上来讲,三人中,他与“两蒋”在资源占有上是最不对等的——对比董显光和陶希圣,蒋对马星野的影响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相反,马对于蒋的影响却是最小的;马星野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生涯中的个人处境是随着蒋对他的信任和认可的变化而变化的。自始至终,马星野在国民党体制内的资源获得,既依靠“两蒋”的认可和信任,也有赖于他对蒋怀有的一种近似崇拜的“服从”。马克斯·韦伯(1926/2016:57)认为,“在现实中,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因此,马对于蒋的这种“服从”态度并未随着威权统治的强化和其自身发展的挫折而有所减弱,相反,还在不断加强——这一点我们从马星野去台之后的著述中长期大量“语录式”引用蒋的言论作为自己新闻观点的立论基础这一事实中可以清楚看到。[15]马之于蒋而言,是一个多了一层师生亲近关系的“干将”。因此,与董、陶相比,马的被动性是最为明显的: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生涯中,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没有大声说“不”的机会和资本;他所能做的,只是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包括工作状态和心理状态,时刻警醒自己摆正“我的理想”与“蒋的要求”之间的位置,从而找到一种“自我”与“体制”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则是以他压缩自身的主动性的发挥空间为代价的。
综上所述,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三人都应是国民党体制内蒋介石的“嫡系”,也都是蒋身边相对信任和重用的幕僚。他们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自身处的现实,最直观地反映了威权统治下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不得不直面并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生涯中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和价值追求。“一如林丽云的研究所指,威权体制可用‘保护主——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来形容,即社会中行动者双方之间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保护主’具有较高地位、较大的权力来分配‘侍从’所需的资源;而‘侍从’地位较低,须透过对‘保护主’的效忠与服从换取所需资源”(林淇瀁,2008:333)。
但是,由于他们每一个人和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对于蒋的作用,都是不同的,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中的不同定位。如果将他们三人比作当年“政校毕业生”的话,那么作为“伙伴”的董显光,当然可以顺利“毕业”;作为“干将”和“爱徒”的马星野,不仅可以顺利“毕业”,而且可以作为优秀的“前二十名”进入“中枢”;作为“近侍”的陶希圣,更可以列为最优秀的“前十名”进入“中枢的核心”。
(二)对“新闻人”理念的认知不同,形成了新闻人态度与风格的不同
作为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的代表,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圈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同的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态度,塑造了三人迥然各异的新闻人风格和特征。
董显光既是一个受过美式专业训练的职业记者,也是一个较为成功的报业经营者和管理者。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式新闻教育及其后的新闻业务实践使他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工作方法深受较为纯粹的西方新闻理念影响。因此,即便是在1935年投身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圈后,他仍希冀借助较为特殊的“国际宣传”来保持他在新闻工作中的“专业的独立性”,他的“舞台站位”更偏向于新闻专业的一侧。尽管在客观上,为了继续在国民党体制内从事新闻工作,董显光仍然必须要保持“平衡”,但他并没有刻意对此加以营造。也就是说,尽管董显光是一名国民党员和一位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人,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做一个专业的新闻人更好。比如,对于新闻检查,他本着专业精神,以专业的方式去改善这个制度,以自己认为比较恰当的尺度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新闻言论自由,并坚信只有这样,才能够“给中国培养国际好感”(董显光,1959?/1981:113)。因此,董显光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中所扮演的似乎是一位更接近于具有专业精神的职业新闻人的角色。
陶希圣的新闻人生涯就是一个单纯的国民党体制内宣传人或是政论家。从业务范围上讲,陶希圣与董显光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董负责“对外”,即以外国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等为主要对象,以国际舆论舞台为主阵地,以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为主要内容,在体制中的掣肘相对较少;陶负责“对内”,即以中国民众为主要对象,以《中央日报》为主阵地,以国民党及蒋的言论(政论)、主张等为主要内容,与体制的关系密切。陶希圣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新闻专业教育,因此在他的新闻实践中很少有西方新闻专业的概念。他在南京《中央日报》时期最大的矛盾并不是来自个人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如董显光),也不是来自个人内心在“专业”与“党意”之间徘徊与平衡的艰难痛楚(如马星野),而是单纯来自“中央”与“日报”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中央后日报”还是“先日报后中央”的矛盾。换句话说,陶希圣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生涯其实更像是一个国民党体制内的职业政论家的生涯。只不过他这个政论家,主要是通过《中央日报》这个媒体平台阐发他的言论,抑或是说通过他的言论反映和传达蒋介石的主张和要求。[16]同时,他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生涯实质上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从政生涯——他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人办报”到“文人论政”,最终实现“文人参政”的思想和行动路线(陶希圣,1978/1979:47)。马克斯·韦伯(1926/2016:80)曾指出:“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新闻工作依然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于陶希圣而言,这点是最为明显的。
马星野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生涯是三人中最为复杂和艰难的。与董显光相比,他们两人都受过密苏里的新闻教育,都具有西方专业的新闻理念,然而马星野的新闻人生涯几乎都是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的核心部门,受到国民党新闻政策的高度制约;同时他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涉及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从工作的性质、范围和内容上讲,都要比董更为复杂。因此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独立性”或是“自主性”要远远小于董,在坚持专业的新闻理念和做法方面也要比董更加小心翼翼。与陶希圣相比,情况转向了另一端。他们两人在《中央日报》共事的时间很长,尽管马并未坚持贯彻“先日报后中央”的做法,而是力图保持“中央与日报并重”,但这仍然与陶所坚持的“先中央后日报”的理念产生冲突。因此,在陶、马共事中,马的这种刻意的“平衡”往往让陶感到其有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倾向”,这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蒋及国民党统治核心对马的共同看法。马星野晚年曾感慨:“大家还批评我注意力不够,党性不够强,认为我是自由派……”(马之骕,1986:37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尽管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都身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圈中,但他们三人似乎站在了一个“舞台”的三个不同位置:董显光和陶希圣分列两端,而马星野似乎努力在这两点间徘徊:他既不像董显光那样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从而可以相对自由地遂行自己的专业主张,也不像陶希圣那样单纯地以“喉舌”的标准来把握自己工作的尺度。他不得不做的是自觉地保持着与陶一样的“方向感”和热情,而他的理想却是希望能够像董一样做一个合乎专业标准的“好记者”,也就是他在纪念董显光的文章中所说的“说老实话爱自由的新闻记者本色,珍惜新闻记者的人格”(马星野,1957/1972:26)。而这种“意欲兼顾”,使得马星野必须不断地平衡和调适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这也正是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中由马星野所代表的一类人的重要特征。
(三)家世、教育背景与人生经历的不同,形成了个人风格和处世方式的不同
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身上都有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传统儒家文人气质和精神追求,也都不得不面对有可能被边缘化的现实。尽管他们没有机会通过科举入仕,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固有的文人士大夫情结使得他们的报国理想与热情丝毫没有减少,且依旧满怀着强烈的参与“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韦伯,1926/2016:73)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陶希圣(1987/1988:50)所言:“我自告奋勇到中央日报是基于一种对报社言论的热忱,也想以此来报国。”——这也是他们身上共同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由来。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都是体制内的“文官”,这同样也是他们维系自身赖以生存的体制(机构)的职责和荣誉所在。
文官的荣誉所在,是他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地加以执行。……没有这种最高意义上的道德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机构就会分崩离析(韦伯,1926/2016:76)。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人始终会认为“参政”是报国的最佳途径;而当他们依然满怀着报国的理想,却没有科举入仕这条路可走时,他们就只能另辟蹊径。而选择进入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圈作为报国阵地,就使得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三个相似点:一是“传统文人”;二是“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三是“国民党体制内的职业政治家”。而这种选择的本质,就是要通过体制内的新闻事业(报业)这条道路来“参政”,进而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然而,尽管都怀有一颗“热情的心”,尽管都走上了“报人报国”的道路,但是一个人性格及其处世方式的形成,却深受家世的影响,也有赖于教育的熏染,还与其人生经历和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董显光出身于纯粹的农民家庭,年幼时家道艰难。尽管这个家庭既无“读圣贤书”的传统,更无入仕的经历,却有着浓厚的西方基督教背景。[17]从他的父母是基督徒,自己自幼成为基督徒,到娶妻亦是基督徒,可见他的一生都笼罩在基督教的氛围之中,这是其一;其二,除了那短暂的并不令他开心的私塾经历以外(董显光,1959?/1981:28),董显光从小学到中学再到美国巴克学院、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接受着美式教育的熏陶,美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对于董显光的影响潜移默化;其三,尽管他身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环境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价值观和处世哲学的影响,然而在他身上,这种影响并没有西方的价值观与处世哲学以及新闻专业精神来得更强烈一些。这造成了他虽身处中国社会,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正因如此,当他在国民党体制内的工作艰难之时,便一再强调自己受美国教育,“赋性率直,不解迂回”,而与“国人传统保持含蓄态度”格格不入(董显光,1959?/1981:122)。
陶希圣出身于传统文人官宦之家,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志在经世之学,虽然早年上过一年半的英文馆和外国语专科学校(陶希圣,1964/2009:27),在大学时也学过英文、日文(陶希圣,1964/2009:35、51),却从未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陶希圣,1978/1979:3-4)。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书生而论政,论政而犹是书生”(陶希圣,1978/1979:45)。[18]从青年时期参加各种学生活动,到主编《政治与民意》,成为《独立评论》的骨干,再到武汉、南京、上海的任职任教经历,以至于后来毅然投身政治漩涡,虽几经波折,仍可清楚看到他这种文人论政并意图参政的强烈愿望。[19]但是书生毕竟是书生,“书生论政”犹可,而一旦“参政”,也会陷入“不知政”的尴尬,“难免不辨阡陌,误入歧途,自招其祸”(李杨,范泓,2008:83-84)。只是后来他“悬崖勒马”,加之自身努力,从而能在蒋的知遇之下转身国民党中枢。因此,他对西方的价值观没有明显的认同,也就是说,在陶希圣的身上,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观与处世哲学要表现得更加强烈。
马星野出身于家道小康的农民家庭(马之骕,1986:481),有着儒家的读书传统,却无人入仕(马星野,1952)。这种家世的影响,使得马星野身上既有着一种中国传统儒家文人报国的情怀和价值追求,也少了一点与政治“亲密接触”的经验;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得马星野对于西方有比较直接的了解,尤其对西方新闻专业理念的认识相对较为深入。然而他在美国的时间并不长,说他对西方有多么深刻和全面的了解,也不尽然。因此,与董显光和陶希圣相比,他兼具董、陶两人的特点,却又没有董、陶两人那么明显的倾向。在他身上,以下三点融为一体:一是中国传统儒家文人的价值追求根植于精神最深处,无法磨灭;二是西方专业新闻精神为他一生所从事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工作提供了合适的理念和方法,是为理想;三是体制内的资源为他能够实现上述两个追求提供了重要舞台,不可放弃。因此,从性格上来讲,马星野始终秉持着儒家中庸态度,鲜有过激言行,处世温良恭谦、春风和气;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地、主动地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努力调整自我,力求在动态中保持理想与现实的平衡。而这种看似最为“稳妥”的平衡,却一直在让他付出代价:他在国民党体制内也就只能进入“忠诚可靠的二十人圈”,却注定进不了“最忠诚可靠的十人圈”——这也就是以马星野为代表的一类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在努力坚持协调理想与现实矛盾之时必然“得到”和“失去”的东西。
四、同一群体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形成
冯·卡勒(1920/2016:148)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他的世界观组成了他的思想,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是否应当发生,便取决于此。”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都面对着一个“中”与“西”相互碰撞与融合的问题。因此,没有直接受过西方新闻专业精神熏陶的新闻人,也依然会在自己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多多少少受到一点“泊来”的影响,比如陶希圣;受西方价值观深刻影响的新闻人,也同样会受到环绕自身的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比如董显光;但是对于同时深受西方新闻专业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新闻人而言,他身上所表现出的两者碰撞与糅合的特征就更加明显,比如马星野。这种碰撞与糅合的结果,在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所代表的三类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身上形成了三种显著不同的倾向:董受西方基督教伦理与价值精神的浸染深刻,因此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言行更加倾向于“西”;陶受中国传统经世之学影响颇为深刻,因此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言行更加倾向于“中”;马则兼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新闻专业理念的深刻影响,因此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言行就更加倾向于“中、西”之间的妥协与熔融。
既然倾向无可避免,那么无论是哪种倾向,只要具有这种倾向的主体认为其并无不妥,那么他就不会有寻求“平衡”的困难和痛苦,或者说不会那么困难和痛苦。董显光和陶希圣就属于这种类型。在新闻人生涯中,他们的理想与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当确定了自己的理想之后,他们是直奔着这个目标而去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太会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矛盾的过多影响,即使有影响,他们的处理方式也会是比较简单的“合则留,不合则分”。比如抗战时期,董显光要做一个“体制内职业新闻人”,而他所从事的国际宣传工作与自己的专业理想一致,他就留了下来;抗战结束后,现实的环境不再需要他这样做,那他也就可以离开了(董显光,1959?/1981:224);再比如,1942年以后,陶希圣要做一个“体制内言论家”,这非常符合当时的需要,因此从进入《中央日报》的那一天起,他的理想与体制的现实需求就是匹配的,他也就长期留在了国民党体制内宣传事业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两人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生涯都没有马星野那么复杂和艰难。马星野则采用了鲜明的“中体西用”与“矛盾协调”的中庸方式在国民党体制内新闻圈中安身立命。在现实中,国民党体制要求他像陶希圣那样做;在理想中,他自己却更加认同董显光。因而他只能始终“执着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楚崧秋,1992:55)。事实上,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只能由他自己完成;而导致“不平衡”的因素,却可能来自他所身处环境的方方面面,且不受他的控制。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董显光、陶希圣、马星野都选择了走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道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条“道路”上,国民党具象为蒋介石——他们都认同、服从和追随着蒋。尽管如此,他们在这条路上的“走法”却不尽相同,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对彼此的看法有所不同——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他们对彼此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认同与否。从这点上看,董显光和马星野显然走得更近一点。[20]董显光(1959?/1981:282)在回忆录中对马星野评价颇高:
很幸运地我得了一位很得力的助手,马星野。他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做着中央日报的社长。……后来马星野因故离中央日报,我亦请辞,未蒙核可,不得不继任旧职,然已失去努力兴趣。
同时,马星野(1952)在《自述》中对董显光更是敬佩有加:
董显光先生与余在师友之间,彼为密苏里大学早期毕业生,极得美国新闻界之推重。……彼之可敬处,为诚恳,为虔诚,对人不欺诈,自奉很刻苦,只知有公,不知有私,助人以求快乐,不以夺取名利为心。故新闻界公奉彼为完人。余又何幸得与共事也。
陶希圣(1981:21)对董显光的评价同样很高:
我们这一代有董显光先生以诚信为立言行事的宗旨,又身居新闻界而为其领导,在其生时受尊重,在其逝世之后被怀念,是事理所当然。
然而,董显光和马星野对陶希圣的新闻生涯却鲜有评价。同样在陶希圣的回忆性著述中,我们也只能看到极少的有关马星野的叙述,而这些叙述也大多为事务性的记录,没有多少深入的评价。[21]但就私人关系而言,陶希圣和马星野似乎并无太大龃龉,比如,马星野要求南京《中央日报》的那群“年轻人”要尊重陶希圣,他自己对陶希圣的尊重也是毋庸置疑的;而陶希圣作为老同事也在马星野竞选“国大代表”时不仅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他,而且还在事先“为星野致电东区各地报社友人请其助彼选票”(陶晋生,2014:85-86)。
五、结语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尽管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三人同属于一个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根据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表现出的差异性或多样性,而将他们细分定位为三种不同的类型,[22]即更偏于西方思维与行为方式,更注重新闻专业与“记者”职业感受的董显光;更偏于中国传统思维与行为方式,更注重体制的要求和“职业政论家”感受的陶希圣;更偏于中西兼顾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更注重所谓“两全其美”感受的马星野。
然而,无论如何,站在近代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圈子不同位置的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都做了同样一件事,即都在以自己的言行表现调和并修正自身所面临的必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从而内在自认和外在证明他们的选择和做法都是“正确”的,抑或至少不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斯·韦伯(1926/2016:116)所言: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而以董显光在回忆录中的自谦之言作为本文的最后一段话,应该是合适的:“我的一生并不是推动时代主流的动力。……因此,我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辅助的”(董显光,1959?/1981:25)。而陶希圣和马星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释:
①在这个平台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文人办报——报人办报——报人报国”这样一个过程。这里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文人”和“报人”不同。这种“不同”不在于“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而在于是否接受了专业新闻理念和方法,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很好地在新闻实践中加以运用;二是“参政”和“议政”不同。对于“文人”而言,实现“报国”理想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参政”,但在“参政”不得之时,他们往往会尝试采用迂回式的“议政”来填补遗憾。这一方式对正经历由“文人”转变为“报人”的中国近代新闻人而言,一样有效。
②有学者以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为中心,对这一类“国民党新闻管理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具有“共性”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由于对研究对象选择的相对一致性,尚未能对“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特征深入描述,从而在展现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全貌的研究中缺少了某些必要的“拼图”版块。
③跨“道路”的对比似乎并不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近代新闻人的个体特性及内部的共性特征。就中国近代新闻史人物研究而言,选择不同“道路”的新闻人,因其选择所能带给他们的支持和约束不同,从而使他们在新闻人生涯中所获得的资源和面对的环境迥然不同。因此,跨“道路”的对比实质上是将研究对象放在了不对等的条件和不一致的背景中比较,从而失去一定的可比性。
④他们三人都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工作;三人都从事过政校(政大)的新闻教育;都曾在《中央日报》服务,尤其在《中央日报》企业化改革后,董为董事长、马为社长、陶为总主笔,在此期间,董与马共事5年,陶与马共事7年。除此之外,马星野与陶希圣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四组”主任,执掌国民党去台初期的文宣中枢;董显光与马星野同为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都属于“密苏里新闻帮”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张威,2012:29-30),并分别于1957年和1984年先后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杰出新闻事业终生服务最高荣誉奖章”。
⑤在自传中,董显光提到了“莎丽在1959年底返台”,莎丽即董显光夫人赵荫芗。而董显光在该书《自序》中提到,这部自传是在妻子的要求和鼓励下写成的。笔者推断,这部自传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1959年底(董显光,1959?/1981:332)。
⑥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研究陶希圣生平的资料主要有四部,即《潮流与点滴》(陶希圣,1964/2009)、《八十自序》(陶希圣,1978/1979)、《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陶希圣,1986-1987/1994)和《陶希圣日记(1947-1956)》(陶晋生编,2014)。而选择《八十自序》为主要参考是因为:(1)1964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将陶希圣离开大陆后在台湾陆续发表的回忆文章以《潮流与点滴》为名结集出版。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以原名出版该书。然而《八十自序》与之相比,成文更晚,思考更加成熟,且是一气呵成,并非系列文章的结集,因此尽管内容远没有《潮流与点滴》丰富,但却显得更加精炼和系统。(2)《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是陈存恭等于1986-1987年间对陶希圣所作访问纪录的文稿整理,1994年出版。但这部访问纪录有两个遗憾:一是其内容从1931年开始,到1950年代初结束,时间跨度仅为20年左右,并不足以反映陶希圣作为新闻人的丰富经历;二是陶希圣于1988年去世,因此该书出版前可能未经其本人亲自校正确认。(3)《陶希圣日记(1947-1956)》所载内容时间跨度仅为10年,所载内容大部分极其简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取以陶希圣亲撰之《八十自序》作为主要参考资料,而辅以《潮流与点滴》和《陶希圣日记(1947-1956)》,并个别参考《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的方式来开展研究是比较稳妥和恰当的。
⑦马星野并未有亲自撰写并正式出版的自传或自述。根据马星野档案的记载,他有三部手稿是以自传或自述体例撰写:一是《自述》(马星野,1952;马星野,1954);二是《生平简记》(马星野,时间不详);三是《国民党干部个人档案登记表》中所附“自传”(马星野,1973)。其中《生平简记》为马星野自撰的“年表式”的简历,且1949年后的部分没有涉及;《国民党干部个人档案登记表》中所附“自传”尽管成文时间最晚,但只是登记表的附录,非常简单。因此,相较之下,只有《自述》是能够比较全面反映马星野人生经历的自传体文稿。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自述仅仅截止到1954年,而对其后30余年没有涉及。
⑧作为研究对象的董显光、陶希圣和马星野都是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事业圈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与国民党核心的距离和关系是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延续和动态变化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暂未能将这种复杂和动态的变化过程、原因和影响等加以详尽系统地阐述。不过,这也为后续的专题研究和深入探讨打开了学术空间。
⑨1925年,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提出“三个自决”(即“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主张,于是“接到环龙路中国国民党党部的信,认为《独立评论》的三个自决是与三民主义相契合。由此而与中国国民党有了直接的接触”(陶希圣,1964/2009:92)。
⑩此处的“悬崖勒马”指的是1940年1月的“高(宗武)陶(希圣)事件”。
[11]实际上,蒋介石对陶希圣应该是一直关注着的。比如,早在1939年8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汪、陈诸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之时,唯独陶希圣“榜上无名”。陶希圣后来说,这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在通过上述名单时,蒋提议把他的名字给剔除了(陶希圣,1964/2009:167)。
[12]根据董显光自传记载,1906年前后,董在奉化龙津书院任教员,教英文和算术。蒋介石在1929年前后,与董谈话时得知董这段经历后,“高兴地说到:‘那你就是我的先生了’”(董显光,1959?/1981:98)。
[13]董显光当时要求端纳说明他在“劝说信”中所说的“为了爱国”是什么意思,端纳解释为:“中日关系日转恶劣,中国需要国际间正确的了解比任何时期更为迫切。蒋委员长夫妇经常接到外国记者申诉电稿受过多检查的抗议。……实使中国在国际宣传上陷于重大不利。”董显光表示认同端纳的看法,并认为“这是亟待补救的缺失”,于是同意接受任命(董显光,1959?/1981:112-113)。
[14]实际上,陶希圣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在1947年4月30日的日记中,他郑重地记下了当他向蒋提出辞去《中央日报》差事时,“主席并提及‘老兄’。不许辞中央日报事。”可见陶希圣对蒋的这样一句话的在意和自豪(陶晋生编,2014:41)。
[15]马星野著述中的这种现象并非突然出现,比如在其早期的《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马星野,1939)等文中就有所体现,然而此时这种现象并未突出和鲜明。然而,从《“总裁”所期望于党报的是什么?》(马星野,1956)首次全面运用“语录式”的表达方式强调蒋介石新闻观点的指导地位后,他著述中的这种现象就开始变得密集起来,到他所作名为《由“总统”训示看三民主义新闻政策》(马星野,1975)的演讲而达到顶峰。而这种现象的强化显然与这一时期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是同步的。
[16]对于到南京《中央日报》任总主笔,陶希圣认为既不是《中央日报》社长的聘约,也不是国民党“中宣部”的命令,而是其以侍从室第五组组长身份,由蒋介石指示,陈布雷转达,与时任社长胡建中等一同到社的(陶希圣,1978/1979:27)。而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必须将蒋主席的决策表现出来”,因此只能由他“自己来做”(陶希圣,1987/1988:50)。
[17]中国近代本土教民的形成,尤其是社会底层农民成为教民的原因,大抵都有一种“投靠”的意味,亦即在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摆脱压迫之时,希冀通过加入教会而获取庇护和帮助,这反过来也给了他们坚持信仰的力量。董显光的家庭亦是如此,他的父母都是长老宗教会的信徒。在自传中,董显光曾坦言,在他幼年受到乡邻欺辱后,母亲立刻要求父亲从上海赶回家,“要他借助宁波教会的协助,控诉那些欺负我的孩子,给我伸冤”(董显光,1959?/1981:28)。
[18]2008年,陶恒生为《潮流与点滴》一书所作序言即以此为标题(陶恒生,2008/2009:1-18)。
[19]1927年1月至12月,陶希圣在武汉先后担任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校政治教官”、“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兼特务连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秘书”、“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党军日报社长”等职务,兼任“武汉大学教授”。1928年春至12月,陶希圣到南京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处第一科科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政治部训育科科长”、“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第一科主任”等职。1928年12月,陶希圣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37年后,陶希圣先后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大本营第六部”、“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艺文研究会”等工作,并在抗战爆发之初即成为“低调俱乐部”成员(陶希圣,1978/1979:13-21);1938年他随汪精卫出走,1939年任汪的宣传部长,1940年1月21日与高宗武在香港揭露日汪密约;1942年由香港辗转抵达重庆(陶希圣,1986-1987/1994:2-3)。
[20]从籍贯上来讲,他们两人也同是浙江人。
[21]关于这一点,在我们所考察的文本样本中体现的较为明显;而在《陶希圣日记》中,有关于马星野和董显光的记载也大多从工作角度,言之极简。
[22]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划分,实际上是朝着细化研究迈进的尝试。尽管比较笼统,还不能够非常精确地表达复杂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中的诸多细节,但却为我们今后开展类似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楚崧秋(1992)。执着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吉人(主编),《马星野先生纪念集》(第55-59页)。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
董显光(1959?/1981)。《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曾虚白译)。台北:《新生报》出版部。
冯·卡勒(1920/2016)。科学职业。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第143-154页)。北京:三联书店。
林淇瀁(2008)。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机器的合与分。李金铨(主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310-35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杨,范泓(2008)。《重说陶希圣》。台北: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映纯,林如鹏(2012)。公共交往与民国职业报人群体的形成。《新闻与传播研究》,(5),102-108。
马克斯·韦伯(1926/2016)。《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
马星野(1952)。自述(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1-01-00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马星野(1954)。自述(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1-01-00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马星野(时间不详)。生平简记(上)(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1-01-002。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马星野(1973)。国民党干部个人档案登记表(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1-01-003。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马星野(1939)。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建设。《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59-168。
马星野(1956)。“总裁”所期望于党报的是什么?。《马星野档案》099-01-02-02-073。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马星野(1975)。从“总统”训示看三民主义新闻政策(手稿)。《马星野档案》099-01-02-01-005。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
马星野(1957/1972)。董显光与美苏里新闻学院。载董显光先生追思录编辑委员会(编),《董显光先生追思录》(第23-26页)。台北:董显光先生追思录编辑委员会。
马之骕(1986)。《新闻界三老兵:曾虚白、成舍我、马星野奋斗历程》。台北:经世书局。
陶恒生(2008/2009)。序。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陶万冰如(时间不详/2009)。逃难与思归。载陶希圣,《潮流与点滴》(第277-37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陶希圣(1964/2009)。《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陶希圣(1978/1979)。八十自序。食货月刊编辑委员会论文作者史学及法学家二十三位(主编),《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第1-47页)。台北:食货出版社。
陶希圣(1986-1987/1994)。《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苏启明、刘妮玲访问,陈存恭、尹文泉总整理)。台北:“史政编译局”。
陶希圣(1987/1988)。难忘的回忆。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第48-51页)。台北:《“中央”日报》社。
陶希圣(1981)。评介。载董显光,《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曾虚白译)(第21页)。台北:《新生报》出版部。
陶晋生编(2014)。《陶希圣日记(1947-195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明亮,秦汉(2015)。从记者到“新闻官”:国民党新闻管理者的职业抉择和职业悲剧。《国际新闻界》,(10),127-148。
余英时(1992)。《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
张威(2012)。《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继先系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地区红色新闻传播活动史研究”(编号:16TQB00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