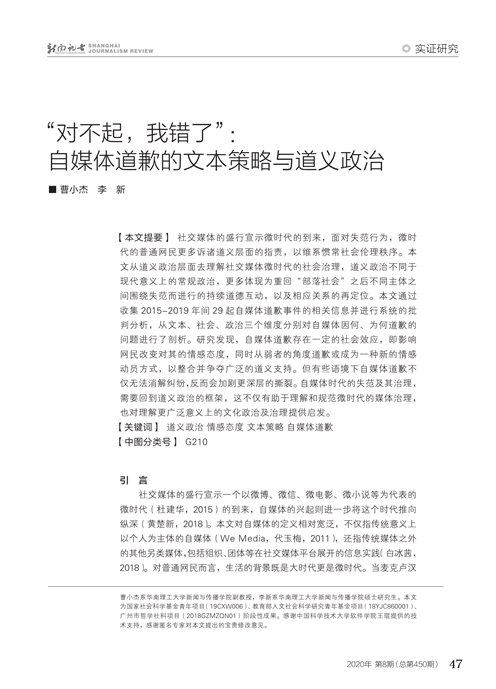“对不起,我错了”:自媒体道歉的文本策略与道义政治
■ 曹小杰 李新
【本文提要】社交媒体的盛行宣示微时代的到来,面对失范行为,微时代的普通网民更多诉诸道义层面的指责,以维系惯常社会伦理秩序。本文从道义政治层面去理解社交媒体微时代的社会治理,道义政治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常规政治,更多体现为重回“部落社会”之后不同主体之间围绕失范而进行的持续道德互动,以及相应关系的再定位。本文通过收集2015-2019年间29起自媒体道歉事件的相关信息并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析,从文本、社会、政治三个维度分别对自媒体因何、为何道歉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自媒体道歉存在一定的社会效应,即影响网民改变对其的情感态度,同时从弱者的角度道歉或成为一种新的情感动员方式,以整合并争夺广泛的道义支持。但有些语境下自媒体道歉不仅无法消解纠纷,反而会加剧更深层的撕裂。自媒体时代的失范及其治理,需要回到道义政治的框架,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规范微时代的媒体治理,也对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及治理提供启发。
【关键词】道义政治 情感态度 文本策略 自媒体道歉
【中图分类号】G210
引言
社交媒体的盛行宣示一个以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等为代表的微时代(杜建华,2015)的到来,自媒体的兴起则进一步将这个时代推向纵深(黄楚新,2018)。本文对自媒体的定义相对宽泛,不仅指传统意义上以个人为主体的自媒体(We Media,代玉梅,2011),还指传统媒体之外的其他另类媒体,包括组织、团体等在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的信息实践(白冰茜,2018)。对普通网民而言,生活的背景既是大时代更是微时代。当麦克卢汉宣称我们重回“部落社会”的时候,那些被抛弃的部落社会的文化、政治也在以某种新的方式回归,其中就包括纠纷应对的道歉政治。上至一国总统或总理的口误(如新西兰总理抗击新冠肺炎的不当言论)、一个城市领导人的不当言论(如布拉格市长贺瑞普屡次涉台涉藏言行不当),中至一个公司或企业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如杜嘉班纳辱华广告),小至网络亚文化群体的相互争斗(如肖战事件),道歉成为标准的申诉要求和过程特征。道歉既是对受害人的道义补偿,也是面子理论的复归。网络上的口水官司争的可能不全是经济赔偿,也是某种认同的政治:通过对社交时代关系失范的伦理学修补,来实践某种动态的身份建构和圈层认同。
一般来说,道歉是对不适当或有损害言行及其后果进行纠正的社交礼节行为。尽管道歉的种类划分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根据道歉者的语气程度,可以划分为弱道歉和强道歉,如“对不起,这周我们又拖更了”就是社交礼仪性质的弱道歉,而“我对我过往的不当言论,表示深切的懊悔和歉意……我将关闭个人微博等社交媒体账号”则是一种强道歉(如邱晨事件中的道歉)。从道歉者的真诚程度来看,还可以划分为“真道歉”和“伪道歉”,“真道歉”是指道歉者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过失所带来的损害后果,不仅表示出懊悔、遗憾等情绪而且会采取实际的补救措施,而“伪道歉”则是形式上的道歉,其实质意图是间接性指责或推脱责任等。当然正如下文所示,有些“伪道歉”也需要置于更大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来理解。
事实证明,社交微时代的道歉正在变得日益流行,各种自媒体在失范时调用的道歉策略往往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当事人的诉求、网民的态度乃至更为宏观的社会政治气候。如何理解道歉策略的运用,不仅需要话语和文本层面的分析,也需要历时性和语境化的分析。本文将对2015-2019年间的主要自媒体道歉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和批判分析,包括分析其语用特征、道歉时机和客观效果等维度。在具体分析之前先对道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一、作为话语、权力和道义的道歉
自柏拉图时代开始,对道歉话语的研究一直都是语言学、修辞学等关注的热点,包括道歉的内涵与外延(Austin, 1962)、表现与策略(Fraser, 1981),以及道歉的本质与维度,如责任归属、原因解释、补偿措施、耐心承诺等(Blum-Kulka & Olshtain, 1984)。从“谁在道歉”这种类型学来说,道歉的主体可以分为个体、专业或商业组织、宗教组织、精神领袖、政府、国家领导人等(Cunningham,1999)。从道歉与惩罚的关系来看,道歉可能是一种仪式(Bennett, 2008),涉及空话、修辞以及似是而非的表述。随着研究的深入,诸多有关道歉的问题得以澄清,比如跨文化语境下道歉的差异(Suszczyńska, 1999;祁福鼎等,2019)、道歉的契机和心理分析(拉扎尔,2018:114-143)、道歉的宽恕效果(张田,傅宏,2019)等。
而媒介研究对道歉的关注则往往置于媒介伦理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对新闻媒体而言,如何平衡公域和私域的关系是个微妙而恒久的问题,一面是舆论监督、公共利益、公众知情权,另一面则是名誉权、隐私权等,道歉话语最多的起因就在于对公私域的处置失当。在这种语境下,要求道歉的理由通常包括内容失实、评论不当、暴露隐私、故意毁损名誉等,拒绝道歉的理由往往是保障舆论监督、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知情权或已尽审查义务等(王利明,杨立新,2010:453)。媒介道歉往往适用对等原则,即在同等版面或时段、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潘祥辉,2015)。
从社会政治学视角来看,尽管道歉属法律范畴,但它远比恢复名誉、金钱赔偿甚至刑罚等其他惩罚来得轻。当然道歉具有相似的作用,即纠正行为并使之符合社会普遍认同的伦常秩序。这里也就涉及权力问题。针对自媒体“类新闻媒体”的功能,虽然在失范处理中不能以新闻侵权来进行司法裁决,但运用法人名誉权要求自媒体赔礼道歉是合理的(王锦东,展江,2017)。在今天自媒体盛行的微时代,当错误不至于大到诉诸法律而侵害却真实发生时,回到传统法则、诉诸道歉政治的道义审查成为非常重要的方式。但道歉行为的出现和操作,既可能涉及文本政治的玩弄(潘祥辉,2015),形成某种姿态性的撤退;也可能涉及社交媒体平台的操控(Poell et al., 2014),以平衡上级行政指令和商业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自媒体的运作者中不乏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精英,不仅擅长网络信息技术,也熟悉网民心理特征,并且非常灵活地游离于宏观政治的边缘,在微时代极大地被技术所赋权。自媒体账号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粉丝群体,日益成为议题设置和引导的组织化权力,普通网民不得不诉诸更广义的群体/部落力量才能抵御这种新兴权力的压迫。不是说网民不能诉诸法律或者正式的渠道,而是正式的渠道成本更高,且显得大材小用,使用起来也容易力不从心。移动互联网技术既能赋权普通人,更能赋权自媒体实现流量变现(Wei, 2013)。有些自媒体为博取公众关注,对信息内容不加核实和深入理解就断章取义、夸大其词,触碰法律红线的事件因此时有发生(单士兵,2019),引起学术圈对自媒体规范的关注(牛静,2019)。自媒体通常不隶属任何机构,缺乏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监督,出现失范行为时,只有当受害者主动提出才可能做出回应。从实证的角度来说,我们无法知晓自媒体拒不纠错的案例数量,但想必这种状况是存在的。在自媒体和受害者之间存在某种或显或隐的权力关系,受害者通常诉诸网络舆论压力、法律诉讼等方式下才能形成对自媒体的某种制约。
道义政治和面子理论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理论路径。社交媒体时代也就是翟学伟(2004)的“情理社会”时代,强调人情面子和同情心。对面子和人情的强调,并不等于对法规、制度和理性社会的否定,但如果忽略这一点,将无法很好地理解今天社交媒体盛行的微时代。当麦克卢汉宣称信息技术将我们重新拉回某种“部落社会”的时候,意味着传统社会理论的同时回归。就像道义伦理是基层政治的必备属性,“去道义化”将会带来基层治理的危机(魏程琳等,2014),在自媒体盛行的微时代,回归道义也就是回到普通人的生存伦理和日常政治(黄振辉,王金红,2010)。道义政治强调对政治合法性的思考要兼及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礼制文化原则、行为秩序等层面(吴根友,2007)。从运作层面来说,它至少包括三个维度:首先涉及常规政治在运作过程中如何回应道义诉求的问题;其次包括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的道义准则或秩序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可能,并籍此反思常规政治权力及其运作的合法性;第三,对理解微观社会中各种泛政治化权力的互动关系也具有解释空间。上述第三个维度(当然下文对谭秦东、崔永元等案例的分析也会延伸至第二个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本文对道歉进行分析的道义政治学框架,涉及自媒体、当事人、社会公众甚至相关部门等多元主体,在冲突和失范过程中如何运用道义法则来进行类政治协商的问题。在这种协商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文本策略、情感动员、社会反应等并不全然是简单的社会事件,同样也是政治事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交媒体时代微观政治、文化政治围绕道义运作的可能。
综上所述,一方面目前关于道歉的概念、本质、策略等问题得到了较多关注;另一方面以自媒体涌现为表征的微时代出现了更多的冲突和失范现象,并不适用经典的规制法则。如何理解道义法则在网络部落社会中的回归,亟需更深刻的理论剖析。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普通网民与自媒体在失范事件中的互动上,围绕“自媒体道歉是否有用”这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不仅分析文本层面的语用特征和修辞逻辑,也观察社会层面的道歉时机和效果,政治层面的微观权力运作,从而反过来也将对微时代的道义政治作出更深刻的理解。
二、样本收集与分析思路
鉴于2015年之前有关自媒体失范事件被知悉的较少,普通网民与自媒体的互动非常有限,不适合用来分析本文的主题。而近几年随着自媒体快速发展,自媒体道歉的事件明显增多,且更容易收集到完整的语料。因此本文所采样本时间范围为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
我们利用Python3.7,以“自媒体+道歉”为关键词,对国内最大搜索引擎百度进行网页语料的爬取,获得了上千条事件相关数据。通过样本去重、清洗得到包含有29则受到高关注度的自媒体道歉事件的样本语料库。过去几年,自媒体道歉案例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2015年2则,2016年1则,2017年4则,2018年7则,2019年15则(见表1)。
对这29则道歉案例的分析将从文本、社会和政治三大层面来展开,具体分析维度参见表2。在分析时不同的典型案例将侧重不同的层面。本研究中案例数量仅有29个,虽在代表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对本文所关注理论问题的解释,即对道歉的触发动机、影响维度、作用效果,以及与道义政治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文本层面重点梳理29个案例中的20篇公开道歉信,依据责任归属、原因解释、补偿措施、郑重承诺、表达遗憾、请求宽恕等6个维度展开分析。
社会层面的分析则主要围绕样本中的5个自媒体账号相关道歉的微博评论数据进行道歉策略与社会效果的关系分析。微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社交资讯平台之一,对社会热点呈现快、网友参与度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而可作为本研究分析的直接样本来源。在剔除评论数据过少、缺乏记录的事件后,最终得到5个自媒体账号:“办公室小野”、“暴走漫画”、“二更食堂”、“咪蒙”、“汽车博主王兮兮”。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评论抓取。使用Python3.7在微博进行爬取,共获得4865条评论数据集。
第二步,人工打分。从4865条评论中抽取1200条评论,进行人工打分(1-10分,分值越高则态度越正面)、数据清洗(即把不可信的数据进行人工剔除,包括纯卡通、纯表情、纯图片等数据,以及“@某人”等无明显意义的数据),确定可靠数据集。
第三步,机器学习。用第二步得到的数据集进行机器学习的训练,采用的模型是自然语言处理(NLP)中的LSTM模型,即建立一个网络结构后先对文本进行预处理,然后放入一个浅层的LSTM网络,辅之以SoftMax网络对评论态度做预测。期间涉及不断改进的过程,如人工打分时,尽可能包括1-10分的全部数段,同时避免过多出现某个数值的情况,以便机器能更为准确地学习。
第四步,数据预测。用经过学习的机器对剩余的3665条评论进行态度分值预测。
第五步,可视化展示及验证。用Python工具中的Matplotlib库进行直方图绘图,发现直方图符合大样本条件下的高斯分布,反过来验证第二步打分的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对鸿茅药酒案中的道歉、崔永元道歉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对其所蕴含的道歉政治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和理解。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对不起”的统计学:自媒体因何及如何道歉
关于自媒体道歉的基本特征将从道歉的主客体、失当言行的具体内容、道歉的致因和道歉的主要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道歉的主客体来看,个人作为道歉主体的比例(59%)高于机构或团队作为道歉主体的比例(41%),被道歉客体中的个人或公众占比(52%)同样高于机构或团队占比(48%)。个人在主客体中的占比都比较高。这在一定意义上佐证了自媒体失范行为与个人是密切相关的。微时代的行动者主要牵涉个人微观层面。
从失范言行的具体内容来看,虚假和失实内容占比最高(59%),其他失范言行包括审查失误、消费死者、盲目模仿、讽刺英烈、职业歧视、私挪善款等。自媒体运营者尽管不乏ICT精英人士,如“咪蒙”、“呦呦鹿鸣”、“六神磊磊”、“丁香医生”等运营者都是领域内的精英,但同时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甚或资质非常低浅者。总体上行业门槛低,运营者在专业素质、知识储备、业务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欠缺,且缺乏被普遍认可的行业标准和成熟的行业规范(张洪忠等,2016),一不小心就会侵害当事人的情感、形象或合法权益。如果把关不严或者刻意吸引眼球,就容易导致消费死者、讽刺英烈、职业歧视等失范现象的出现。绝大多数自媒体账号在现有机制下没有新闻采访资质,只能转载或改编具有新闻采访资质媒体的内容,这个客观的管理语境也不能被忽略。
从道歉的致因来看,绝大部分自媒体道歉都是因为受到了法律诉讼与舆论压力(占比57%),其次是因为信息被官方辟谣或相关机关的介入调查(占比11%),而认识错误后自发道歉的非常少见(占比7%)。这说明法律和舆论压力是道义法则产生效果的主要致因。尽管很多问题并不至于最终争论双方要对簿公堂,但法规和制度作为一种隐形的力量,给微时代的社会互动画上一层理性的底色,在此基础上,道义和人情的某种规范力量才得到更好的体现。
从道歉的方式来看,选择使用书面或视频进行公开道歉的占比最高(58%)。公开道歉意味着道歉者承认言行存在过失,而且也往往与其他道歉方式连在一起使用。其他道歉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删除文章(16%)、经济赔偿(9%)、停更或注销账号(7%)、开除或劝退涉事人(2%)、主动辞职(2%)等。尽管选择任何方式的道歉并不等于伤害的彻底清除。比如删除文章并不等于删除了互联网记忆(吴飞,2014)。截屏或其他便捷的保存方式意味着伤害痕迹可能会在互联网上存续很久。
(二)道歉的文本策略
在道歉策略中,责任归属和原因解释形成对问题的认识与澄清,补偿措施和郑重承诺强调对失范行为的纠正和未来承诺(Blum-Kulka & Olshtain, 1984),而表达遗憾和请求宽恕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和后悔(Kádár et al., 2018)。对大部分自媒体来说,道歉更多地从表达遗憾、责任归属、原因解释和郑重承诺等道义层面入手,较少使用补偿措施策略。
笔者所收集的20封自媒体道歉信中,表达遗憾使用频次最高,达20次,如“我们犯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错误”、“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和悔恨”、“对此我很后悔”、“对造成的相关影响本人深表歉意”等。其次是责任归属(18次),如“李明非常愧疚和自责”、“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等。继而是原因解释(16次)、郑重承诺(11次)。补偿措施(7次)和请求宽恕(5次)较少见。尤其是补偿措施,涉及删除文章、关停账号、停更、免去当事人职务等,涉及的往往是比较大的个人自媒体或机构自媒体账户,大部分自媒体道歉在补偿措施方面是模糊处理的。
从道歉用语来看,29则案例的20封公开道歉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道歉词语统计如下:主题上,“道歉”、“致歉”和“歉意”共29次;影响上,“名誉”、“商誉”和“声誉”共15次;原因上,“诋毁”、“捏造”、“虚构”和“侵害”共13次;担责上,“责任”、“错误”和“反省”共11次;态度上,“诚挚”、“痛苦”、“原谅”共10次。道歉文本的核心依然是“致歉”,为“捏造”事实、损害个人或组织形象而寻求“原谅”,同时表明承认“错误”,深刻“反省”,并愿承担“责任”。
为了更好理解道歉的文本策略,我们选择“办公室小野”针对易拉罐爆米花悲剧的道歉视频和“咪蒙”针对《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文字道歉进行对比分析(见表3)。“办公室小野”使用了六种策略,“咪蒙”用到了四种策略。
在表达遗憾和责任归属方面。两个自媒体均是面向“大家”表示道歉,并未针对具体的当事人,而是针对抽象的社会公众。相较“咪蒙”直接承认责任,“办公室小野”拒绝承认悲剧是因她的视频而起。但她明显意识到如果否认意外与己无关,一定会“被众口说成甩锅推卸责任”,因此在道歉的最开始便承诺“愿意为小雨的后续治疗和哲哲的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随后也表示“如果有相关方对我提起诉讼,我将完全尊重法律,全面配合法律机关的调查和裁决”。这种文本策略既澄清了自己的责任(拒绝被视作“杀人犯”),同时也表达不会完全“置身事外”的态度。相应地,在郑重承诺、补偿措施两方面,“办公室小野”也都显得更为真诚。这也是为什么“咪蒙”道歉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当文字商人没错,但不能尽熬有毒鸡汤”)、公众(“到底是真诚忏悔,还是公关需要”)等持续对其进行质疑的原因,但“办公室小野”道歉之后几乎很少人怀疑她的真诚。
(三)道歉是否有用:来自舆论的视角
道歉对当事人(或直接关联人)无疑具有重要的心理安抚作用,但更为重要的也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开的社会宣示,意味着在冲突中道歉者承认“我错了”。但从舆论反馈的视角,道歉是否真的有用呢?基于“办公室小野”、“暴走漫画”、“二更食堂”、“咪蒙”、“汽车博主王兮兮”等5个自媒体道歉后的微博网民情感态度比较(见图1),发现微博舆论予以积极反馈的只有“办公室小野”的道歉,其他4个自媒体道歉后依旧是负面评价高于正面评价(“咪蒙”是中间高两端低,针对“咪蒙”的中立态度高达43.77%,其他4个自媒体都是两端高中间低)。
以唯一得到更多积极评价的“办公室小野”的道歉为例,前述有关她与“咪蒙”道歉的不同文本策略似乎早预示了不同的结果。从道歉内容和策略来看,“办公室小野”道歉的篇幅要远长于“咪蒙”的(前者1980字,后者171字),态度也更加诚恳,使用的道歉策略更多,更为重要的是采用高成本的补偿措施,如全面整改并无限期停更、全平台永久下架账号中一切存在安全隐患的视频、为受害人家庭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等。道歉成本越高,证明道歉者对事件的重视程度越高,态度上越真诚、越有责任担当,也就越容易获得公众的包容和认可。相对“咪蒙”道歉受到的指责,比如“大概意思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还敢”、“‘咪蒙’的毒鸡汤真的要关停了,特别是误导了很多的女性”,针对“办公室小野”的道歉,网民留言整体更为积极正面,比如“相信小野和你的团队也一样,会走过来的会更好的”、“看到最后你都哽咽了,真的很心疼,我们一直都在身后支持你,加油”。
对“办公室小野”来说,道歉是有用的(如图1所示,道歉后网民情感峰值右移趋好,整体上偏正面,正面比重达到57.97%,中立态度占比13.70%)。她在此后重返短视频创作领域,至今非常活跃。但“咪蒙”等其他自媒体的道歉是否就毫无意义?此问题转换成实证问题,即道歉前后公众对道歉者的舆论态度是否存在改变?我们对微博上“咪蒙”道歉前后的网民回帖态度进行了分析,共抓取道歉前近800条、道歉后逾1000条的评论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见图2),发现不管是道歉前还是道歉后,网民对“咪蒙”《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所引发的争议的情感态度均偏负面。但道歉以后,负面评价总体上得到大幅弱化(从53.02%降至28.26%),正面评价得到较大提升(由13.32%升至27.96%),而且中立者比重增加一成多(由33.67%提至43.77%)。由此可见,道歉未必会改变舆论的情感态度,使负面态度扭转为正面态度,但却可以较为显著地降低负面态度的负面程度。关于道歉的上述社会效应问题,在“暴走漫画”、“二更食堂”、“汽车博主王兮兮”等其他3个自媒体账号的道歉案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四)从情感动员到道义政治
尽管道歉诉求的依据不是权力而是道义本身:一旦违背道义原则,不论强弱都需要道歉。但在具体的道歉案例中,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在社交媒体时代,权力既指传统意义上的政经权力,也指技术平台日益壮大所带来的平台权力。
在鸿茅药酒案例中,谭秦东虽在自媒体上使用“毒药”有错在先,但鸿茅药酒的“跨省抓医生”直接瓦解了其后续行为的道义性(魏英杰,2018)。随着更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鸿茅药酒历年的违法广告也被梳理出来(春雨医生,2018)。公众情绪被动员起来,谭的道歉在回应具体错误的同时,也整合了社会情绪和情感,激活了某种更深刻的不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当2019年中国中药协会授予鸿茅药业和鸿茅药业副总裁鲍东奇“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奖”荣誉称号时,不仅引发媒体质疑(崔桂忠,2019),也引起了新一轮的舆论风波。同样地,在崔永元道歉案例中,道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舆论的道义性与司法监督、权力监督的微妙关系被这种姿态所遮掩,但舆论道义并不等于真正的公平、正义,而可能只是公众特定情绪的表达,比如部分网民关于崔永元手写的是“声明”而不是“道歉”的解读,意味着道歉可能成了一种仪式(Bennett, 2008)。
同时也存在平台权力的问题。以新浪财经为例,在转发自媒体文章《为什么说林志玲结婚是一次失败的IPO》之后,因言论不当而向林志玲道歉,但其道歉在新浪微博上收到的负面评论远高于正面评论。比如“渣浪是不是该封自己的号呀”、“你知道你们养的那些营销自媒体有多恶臭吗”等大量嘲讽话语出现在该道歉的回帖中。新浪微博平台的用户将平日累积的对该平台审查等方面的不满情绪,通过林志玲案例得到宣泄。类似地,当腾讯视频就推送“山东全省人死亡”事件发道歉声明后,网民的情感倾向也是以负面居多。腾讯和新浪属于当前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众多的社会情绪动员过程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也不乏僵尸粉泛滥和平台治理不透明等问题,因此当这些平台出现明显的道德失范行为时,舆论将基于道义立场而倾向于放大这种错误和累积的不满。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道歉往往受到政经结构和平台权力的双重影响。但社交媒体时代,相比网络举报以及特定自媒体账号的停更或关停(比如“新闻实验室”),要求自媒体道歉仍是留有余地的治理办法,意味着多元观点的表达是可能的——只是出现错误、出现失范时,需要认错。不过我们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道歉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情感动员方式,通过舆论整合来争夺广泛的道义支持。在特定语境中,道歉可能不仅无法消解纠纷,反而会激发或彰显更深层的社会撕裂。
四、结论与讨论
以圈层文化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微时代下,自媒体的野蛮生长给互联网治理带来了难题。当自媒体失范行为不可避免地出现时,诉诸法律未必是最合适的方式,而道歉作为道义法则、道义政治语境下的冲突应对办法,在“重新部落化”的今天变得流行。普通网民不仅通过诉诸道歉来实现对自媒体群体的可能的道义约束,也通过诉诸道歉来形成对解决更广泛社会政治问题的舆论压力。道歉因此成为一种消极进攻策略(passive-aggressive strategy)。
本文通过收集2015-2019年间29起自媒体道歉事件并进行系统的批判分析,从文本层面的语用特征和修辞逻辑、社会层面的道歉时机和效果、政治层面的平台运作和权力运作等维度,对自媒体因何、为何道歉等问题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自媒体道歉存在一定的社会效应,即影响网民改进对其的情感态度,同时从弱者的角度道歉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情感动员方式,以整合并争夺广泛的道义支持。但在某些语境里,道歉可能不仅不会消解纠纷,反而激发出更深层社会的撕裂。本文因此认为,自媒体时代的失范及其治理,需要回到道义政治的框架,这对理解和规范微时代的媒体治理乃至理解和规范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及治理将有所启发。
在本文结束之前,有必要对前述道义政治略作进一步的补充。在詹姆斯·斯科特对马来西亚农民的研究中,装糊涂、假装顺从、装傻卖呆、诽谤等均被视作弱者的武器,是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表现方式(Scott, 1990: 183-201))。道义在本质上是弱者的伦理原则,道义伦理实际上给底层政治涂上了一层光芒,因为一旦脱离道义,底层行动对社会政治的积极意义将不值一提,“去道义化”也会给底层社会、底层治理带来巨大的危机。就此而论,道义政治与底层政治存在一定的相通性,回到道义也就是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伦理。籍由集结为群体、舆论的可能,弱者所代表的道义力量就可能反过来左右强者的行为,从而将社会秩序约束在可接受的范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歉也逐渐成为社交媒体时代道义政治的表现方式。当然在常规政治的意义上,需要警惕道歉作为仪式、作为政治姿态对道义本身的损害,因为正如巴蒂斯泰拉(Battistella, 2014:157)所发现的,如果仅仅停留在话语或者修辞层面,道歉可能制造更多的不利境地而不是解决方案。
同时值得说明的是,自媒体道歉与传统媒体道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共性方面,真诚及时的道歉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媒体回应失误、塑造形象和提高公信力(甘丽华,2016;刘佩,2004),在权力阶序语境下向权势部门、权势人群、更具强博弈能力的资本主体、舆论主体道歉的情况更常见(潘祥辉,2015)。但也存在差异,如我国传统媒体在某些时候的表达并不完全是面向公众的,代表的也并不完全是媒介自身的立场,道歉需要综合各方利益的考虑才可能作出,不完全是媒介专业伦理范畴的问题(潘祥辉,2015)。自媒体道歉所面临的额外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也并非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国内传统媒体在刊发虚假新闻引发舆论争议后进行主动、及时道歉的并不多(张振亭,张会娜,2014),而自媒体迫于舆论压力往往会更多地选择道歉的原因。自媒体道歉很少围绕文字错误更正进行,而更多涉及事实错误和引发纠纷的情况。并且因为对流量和市场的重视,避重就轻进行策略性道歉的空间和可能性相对来说远小于传统媒体。
本文通过自媒体道歉这一经验现象来对社交媒体时代的道义政治进行探讨。尽管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只是以2015-2019年为时间段进行抽样,时间上的跨度不是很大,而且收集到的29起自媒体道歉文本中有完整道歉文本的只有20起,样本未必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媒体道歉文本策略的整理,以及对围绕文本策略、情感动员所展开的道义政治行动的理解。当然,在话语和文本分析中,如何更好地、更充分地考虑历时性和语境化的因素,尤其当我们聚焦自媒体、朋友圈时,传统媒体以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角色可能会被不自觉地边缘化,自媒体似乎成为社交媒体时代所有问题起因、发展和解决的自足场域。这种浪漫化的取向是本文希望避免但却没有真正避免的。在本文写作结束时,又出现许多新的与道歉有关的案例,比如“回形针”的道歉、肖战道歉等。我们可以发现自媒体的治理依旧无法逃离传统的政经结构和新兴的平台权力框架,但同时也可能与圈层亚文化存在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艾伦·拉扎尔(2018)。《道歉的力量》(林凯雄,叶织茵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白冰茜(2018)。自媒体的发展研究。《新媒体研究》,(6),109-110。
春雨医生(2018)。打不倒的鸿茅药酒:上千次违法广告竟被一笔勾销。检索于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5345987586196318&wfr=spider&for=pc。
崔桂忠(2019年12月27日)。鸿茅获奖,辜负了社会责任。《大连日报》,第11版。
代玉梅(2011)。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5),4-11。
杜建华(2015)。“微”时代:表现、特征及传统媒体的着力点——以纸媒体为例。《新闻大学》,(2),60-67。
甘丽华(2016)。新媒体时代美国媒体的核查与更正机制。《中国记者》,(1),24-26。
黄楚新(2018)。当前我国新媒体发展状况、问题及对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9),79-87。
黄振辉,王金红(2010)。捍卫底线正义:农民工维权抗争行动的道义政治学解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1-26。
刘佩(2004)。网络时代的新闻更正制度——从搜狐“有奖网络纠错”活动谈起。《当代传播》,(1),51-53。
牛静(2019)。缘起与路径:自媒体用户信息传播伦理规范的拟定。《青年记者》,(24),23-24。
潘祥辉(2015)。“我们错了”:中国式媒介更正与致歉的政治社会学考察。《传播与社会学刊》,(33),49-83。
祁福鼎,肖婷婷,Dániel Kádár(2019)。到底是声明还是道歉——日语公开道歉的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3),56-66。
单士兵(2019)。自媒体的核心价值与理性发展。《青年记者》,(18),16-17。
王锦东,展江(2017)。赔礼道歉能抚慰“伤心”的企业法人吗?——由阿里巴巴等诉自媒体人葛甲案的判决谈起。《新闻界》,(7),17-23。
王利明,杨立新(2010)。《人格权与新闻侵权》。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魏程琳,徐嘉鸿,王会(2014)。富人治村:探索中国基层政治的变迁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8-15。
魏英杰(2018年4月20日)。跨省抓医生,鸿茅药酒底气何在。《钱江晚报》,第A0024版。
吴飞(2014)。名词定义试拟: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新闻与传播研究》,(7),13-16。
吴根友(2007)。道义论——简论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对治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证。《孔子研究》,(2),15-23。
翟学伟(2004)。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5),48-57。
张洪忠,梁爽,张诗雨(2016)。自媒体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新闻与写作》,(5),28-31。
张田,傅宏(2019)。“对不起”有用吗:道歉对群际宽恕的影响。《心理与行为研究》,(1),119-125。
张振亭,张会娜(2014)。困境与突破:关于我国媒体更正的现状、问题及思考。《编辑之友》,(9),86-89。
Austin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ttistella, E. L. (2014). Sorry about that: The language of public a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C. (2008). The apology ritual: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punis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um-Kulka, S. & E. Olshtain. (1984). Requests and apologies: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atterns. Applied Linguistics5(3)196-213.
CunninghamM. (1999). Saying sorry: The politics of apology. The Political Quarterly70(3): 285-293.
FraserB. (1981). On apologizing. In F. Coulmas (ed.). Conversational Routine: Explorations in Standardized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and Prepatterned Speech. Th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Kádár, D.P. Ning & Y. Ran. (2018). Public ritual apolog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DiscourseContext & Media(26)21-31.
Poell, T.J. de Kloet & G. Zeng. (2014). Will the real Weibo please stand up? Chinese online contention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18.
Scott, J.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uszczyńska, M. (1999). Apologizing in EnglishPolish and Hungarian: Different languagesdifferent strategi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053-1065.
Wei, R. (2013). Mobile media: Coming of age with a big splash.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50-56.
曹小杰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新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XW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60001)、广州市哲学社科项目(2018GZMZQN01)阶段性成果。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王琨提供的技术支持,感谢匿名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