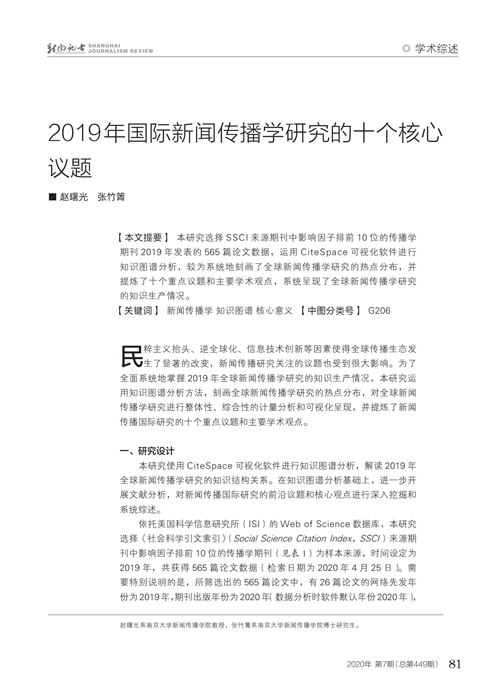2019年国际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核心议题
■赵曙光 张竹箐
【本文提要】本研究选择SSCI来源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前10位的传播学期刊2019年发表的565篇论文数据,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较为系统地刻画了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分布,并提炼了十个重点议题和主要学术观点,系统呈现了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情况。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知识图谱 核心意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信息技术创新等因素使得全球传播生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新闻传播研究关注的议题也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情况,本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刻画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分布,对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呈现,并提炼了新闻传播国际研究的十个重点议题和主要学术观点。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解读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关系。在知识图谱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文献分析,对新闻传播国际研究的前沿议题和核心观点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综述。
依托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本研究选择《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来源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前10位的传播学期刊(见表1)为样本来源,时间设定为2019年,共获得565篇论文数据(检索日期为2020年4月25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筛选出的565篇论文中,有26篇论文的网络先发年份为2019年,期刊出版年份为2020年(数据分析时软件默认年份2020年),鉴于此26篇论文在2019年已发表于网络,也纳入了本次研究的范围。
二、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分布
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数量最多的国家为美国(259篇);其次是英国(66篇);德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位列三、四、五名,发表数量分别为46、36和33篇,中国排名第六(24篇)。从中心度来看,前6个国家中,美国中心度最高为0.62,说明美国与其他国家(地区)合作研究最为密切,并且处于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英国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中心度为0.37;西班牙和比利时共居第三,中心度均为0.15。中国处于第十位,中心度为0.06,这说明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虽然中国的发表数量较多,但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相对较少。
整体上,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分布较为分散,研究热点较为多元,但是,社交媒体研究的热度最高。结合(表2 表2见本期第82页)分析可知,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发表的高频词为“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出现次数高达129次;“media(媒体)”出现频次排名第二,共出现69次;“communication”(传播)出现频次排第三,共出现63次。“facebook”(脸书)、“internet”(互联网)和“online”(在线)出现频次分别为52、48和46次,排在第三、四、五位。“news”(新闻)、“impact”(影响)中心度排名位列第一和第二,分别高达0.13和0.11;“attitude”(态度)、“youth”(青年)出现频次虽然不高,但中心度位列第三、第四,分别为0.1和0.09;“exposure”(曝光)、“digital inequality”(数字不平等)和“politics”(政治)共居第五,中心度为0.08;并列第六的关键词为“internet”(互联网)、“technology”(科技)、“gender”(性别)和“network”(网络),中心度为0.07;“privacy”(隐私)和“labor”(劳动)紧随其后,中心度为0.06。结合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可以看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仍是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基于社交媒介的政治传播、公共传播、新闻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较多,同时,互联网研究、青年研究、新闻学研究、媒介效应、数字鸿沟、性别研究、通信技术、数字劳动等也是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点。
三、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核心议题
(一)社交媒体与政治传播模式的变化
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传播革命彻底改变了当今的政治传播模式。拉尔森(Larsson, 2019)认为,在国家政治选举中,社交媒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党派和政治家都积极主动地使用社交媒体对选民进行信息释放和政治劝服。克莱宁尼惠斯等(Kleinnijenhuis, et al., 2019)的研究证实,尽管大众媒体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作为信息源的主导地位已被推翻,公众政治观念和偏好的变化受大众新闻媒体和社交新闻媒体的综合影响。斯特劳特(Stroud, 2019)的研究表明,公众接触政治信息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超半数的美国人会从社交媒体获得政治信息。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政治新闻的偏好存在差异,政治策略新闻产生更多的点击率,而政治议题新闻获得较多的评论和反馈。山本正弘等(Yamamoto et al., 2019)的研究证实,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在线搜索和在线讨论两个因素在上述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议程设置是政治传播领域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最初是对传统媒体与政治传播之间关系的研究。最近,议程设置理论扩展到了更多的媒体渠道和更广泛的传播领域。菲泽尔(Feezell, 2019)等学者研究发现,通过社交媒体偶然接触政治信息可能不会导致人们政治知识的增加,但它可能会改变人们对政治世界的认识和参与政治事件的意愿。同样,克莱因伯格(Kleinberg, 2019)认为,当代美国年轻人偏好使用互联网访问政治信息,因此,互联网上的政治知识替代了人们记忆中存储的传统政治知识,互联网对人们理解政治事件和参与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加勒特等(Garrett et al., 2019)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在当代新闻环境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公众有更多机会寻找或发布感兴趣的政治新闻。因此,社交媒体新闻对人们的政治学习和政治理解具有推动作用。上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的政治信息仍会对公众产生议程设置效应。
在当代民主国家,政治动员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社交媒体成为青年公民表达和探索政治自我的重要空间。因此,社交媒体时代的青年公民政治参与研究成为热门议题。欧姆(Ohme, 2019)的研究证实,青年公民使用社交媒体接触新闻的比例高于中老年人,社交媒体通过影响青年公民意识从而增加了青年公民们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莱恩等(Lane et al., 2019)学者研究了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青年公民的政治参与情况,结果发现,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即时性和地缘性增加了青年之间政治交流的数量和质量,社交媒体成为年轻人进行政治表达的自由场所。贾拉米洛-登特(Jaramillo-Dent, 2019)和莱特拉特(Literat, 2019)等学者发现,备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媒体,例如Instagram和TikTok,已成为年轻人接收和发布政治信息的主要社交媒介,其用户的政治代表性很可能会渗透并影响政治选举。更多研究结果共同表明,Instagram、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西方政客们对青年选民进行政治操纵和政治劝服的沃土。
社交媒体拓宽了社会运动的影响范围,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重要社会问题的参与度。因此,社会运动的数字化被认为是进一步民主化的过程,学术界对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巴里汀等(Barisione et al., 2019)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上发出的公民声音将传统的舆论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化政治力量,他们称之为“数字舆论运动”。数字舆论运动表达了沉默的多数人的态度以及在社会运动领域中所隐含的思想,即集体行动需要积极的少数群体进行非数字动员。研究证实,当数字舆论发挥作用时,它会在公共政治话语中体现出合法力量,并在决策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陈思敏(Chen, 2019)认为,社交媒体能够快速地将社会运动信息传播给在线支持者,它降低了社会运动的成本和复杂性,允许普通公民在没有传统社会运动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自由、灵活与便捷地组织和建立社会运动。亨特(Hunt, 2019)认为,社会运动已能够独立于传统媒体而引起关注。首先,社交媒体为公众在民主国家和专制政体中发出更多的声音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更具参与性的政治;其次,社会运动的构成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数字化沟通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第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微小的社会运动可以迅速扩大规模,即时将信息传递至可能被影响的其他人。罗林格(Rohlinger, 2019)认为,社交媒体可以帮助社会运动者和社会运动团体在更大的媒体系统中传播他们的思想。特别在当今的数字时代,社会运动应该考虑使用机器人或自动化应用程序来影响集体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其次,社会运动需要考虑网络暴力者在运动轨迹中的作用,暴力分子的恶意行为旨在破坏在线互动和对话;最后,社会运动还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意见领袖的话语力量可以将以前非政治性的在线论坛政治化,并动员人们采取行动。罗曼(Rohman, 2019)在肯定了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推动意义后,将研究重点落在了社会运动后期社交媒体的作用和意义上。他研究发现,社会运动后期,社会运动者们仍然使用社交平台保持联系,准备扩大已经进行的活动并分享新的不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社交媒体能够发展和维持社会运动者们共同的意识形态,使社会运动得以持续或循环进行。
(二)网络虚假新闻侵蚀事实和真相的传播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引发了人们关于网络虚假新闻的广泛关注,尽管网络虚假新闻不是一个新现象,但它已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并被战略性地用于实现政治目标,从备受争议的网络现象演化成政治传播领域的重点议题。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后现代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真相与假象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人们与真相和事实失去联系。奥格尼亚诺娃(Ognyanova, 2019)认为,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业务,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数据生成了大量的算法新闻,公众对新闻的看法通常与谣言、故事和假消息挂钩。公众的信任度下降被视为新闻合法性受到严重侵蚀的征兆或新闻业制度性衰落的迹象。维尔科娃(Velkova, 2019)认为,算法作为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固有部分,其在构建日常网络交流、组织和推送媒体信息或在公共管理领域行使决策权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算法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社会的风险和控制危机。布雷萧等(Bradshaw et al., 2019)的研究发现,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带有特朗普标签的机器人账号在Twitter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大量推送自动生成的虚假新闻,Twitter用户分享的虚假新闻与专业制作的新闻比例为1∶1。社交媒体用户几乎无法确定网络传播的新闻是由人类还是由机器人生产,虚假新闻可以在社交网络快速传播并且欺骗用户。帕吉特(Padgett, 2019)认为,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到来使媒体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加剧了党派冲突和政治两极化,使得党派新闻重新出现。这些新闻媒体扩大了意识形态最极端的政治言论,并加剧了新闻中现有的政治偏见。随着美国党派两极化的加剧,大规模的虚假信息遍布互联网,公民对媒体机构的信任度大幅下降。汉弗莱特(Humprecht, 2019)研究发现,使用媒体时间较少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年轻人更可能相信在线虚假新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社交网络作为新闻的主要来源,在线虚假新闻传播将成为民主国家政治传播的主要挑战。与西方政坛相反的是,博尔索(Bolsover, 2019)对网络上的中国政治新闻和信息进行研究后发现,在Twitter和微博上,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新闻基本不存在自动生成的虚假信息,这表明中国政府没有将算法和虚假新闻作为其政治宣传的一部分,更没有使用自动化手段影响公众舆论。
随着社交媒体上虚假新闻乱象的日益加剧,公众辨识虚假新闻和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学术界对于提高公众新闻素养的呼声愈发高涨。瓦拉和塔利(Vraga & Tully, 2019)的研究表明,新闻素养较高的人会选择可靠的媒体渠道寻求新闻而不是社交媒体,因此提高公众的新闻素养可以提高公众辨识虚假新闻的能力,其中批判性思维和怀疑主义在虚假新闻的分辨中发挥了作用。不幸的是,该研究意味着新闻素养较高的人没有向社交媒体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信息,这可能导致偏好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愈发缺少新闻素养,从而长期禁锢于虚假新闻构建的信息茧房中。沈翠华等(Shen et al., 2019)认为,随着用于创建和编辑数字图像的工具越来越普遍以及易于使用,虚假图像在社交媒体新闻中广泛传播,并在世界范围内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威胁。他们的研究证实,辨识虚假图片的关键不在于图像内容,而是受公众的教育背景、媒介经验和数字媒体素养的影响。因此,公众的技能和经验极大地影响了其对虚假图像的判断,为降低社交媒体新闻中虚假图像的危害,最好的策略是对教育进行投资,以提高公众的数字媒体素养。除此之外,为了从源头阻止虚假信息的产生,艾克和多诺万(Acker & Donovan, 2019)从技术视角研究认为,元数据作为治理虚假信息现象的切入点,能够迫使互联网平台开放并建立更透明的问责制流程。因此,亟待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跨部门联盟组织,以回应公众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审核的呼吁,并对互联网平台的虚假信息等其他不当行为进行监督。
(三)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20世纪,人们大多是通过媒体组织的渠道来了解公共事务,例如广播、报纸、电视以及网站。进入21世纪,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等平台搜寻网络新闻。从以直接发现为主的媒体环境到以分布式发现为特征的媒体环境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的主导地位和特权地位被极大削弱,全球新闻传播学界围绕新闻业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开展了系列研究。卡洛格罗普洛斯等(Kalogeropoulos et al., 2019)认为,新闻机构的品牌对于用户搜寻新闻的方式、评价新闻的质量,以及与新闻机构建立可持续的业务至关重要。与新闻用户的态度一致并与其竞争对手的产品实现差异化是新闻机构品牌设计的重要标准。因此,分布式发现的新闻环境中,提高新闻机构的品牌知名度,可能会对新闻业的经济增长做出长期贡献。费茨杰拉德(Fitzgerald, 2019)认为,互联网出版的压力和逻辑已经渗透到了新闻业,这些转变带来的压力和约束是新闻业与过去划定界限的推动力量。三个新“新闻价值”: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对于数字化的新闻业的逻辑有重要意义。艾尔德里奇(Eldridge, 2019)认为,数字平台为自由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发布新闻的平台,来自自由新闻媒体发布的评论和报道可以促进而不是分散新闻核心。自由媒体工作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功突破了传统媒体圈定的新闻边界,其作为传统新闻业的补充促使新闻报道更加透明与客观。
随着互联网和无线移动技术的发展,新闻业开始失去对其发行渠道、受众和资源的控制权,面临着21世纪初报业所经历的困境。为了应对这波挑战,新闻从业人员做出了多种努力以维持新闻业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鲍尔斯(Powers, 2019)等学者以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为视角调查发现,新闻从业人员的立场对数字环境与技术转型的反应具有重要意义。在新闻机构中处于较低地位的人,倾向于忍受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相比之下,处于中级职位的人更有可能将这些挑战作为机遇进行投资。而那些职位较高的人,则完全无视这些挑战。加西亚-珀多莫(García-Perdomo, 2019)通过对电视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关于技术的两种想法渗透到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信仰中,并影响他们在新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实践。第一个信念是,使用数字技术降低电视频道的时间和资金投入,以确保其新闻从单纯的电视环境过渡到多平台的数字环境;第二个信念是,传统媒体即将消亡,为此电视新闻媒体正尝试创建小型视频单元,作为未来制作网络和社交媒体新闻的过渡形态。莫利纽克斯等(Molyneux et al., 2019)认为,当代新闻行业的紧迫性、焦虑感和不稳定性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不断扩大,在这种环境中,许多新闻从业人员被迫对个人职业和身份进行重新评估。自我推广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已成为许多新闻从业者的日常需求。研究证实,新闻从业者的个人品牌越突出,其在新闻业的声望和资源就越好,品牌塑造是数字化环境下新闻从业者提高职业成就的方式之一。
(四)网络暴力与网络犯罪的升级循环
网络生活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存方式,与之伴随的是网络暴力与犯罪行为也在网络空间飞速发展,网络安全和治理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格雷厄姆(Graham, 2019)认为,网络暴力作为一种互联网实践,自其诞生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网络暴行者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贯性,这些目标群体大多是妇女、儿童、同性恋等社会弱势群体。库克等(Cook et al., 2019)学者以网络游戏中的暴力语言为案例研究发现,网络暴行者的语言特征呈现消极性和攻击性的特点,且出现的主动性和重复性较高。这意味着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网络暴行者倾向于主动攻击别人并持续加强暴力行为。研究进一步表明,网络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会转变为加害者,最终以“暴力行动的升级循环”告终,这便是网络暴力在互联网能够快速蔓延的原因之一。齐格勒等(Ziegele et al., 2019)对新闻网站中的不文明评论感到担忧,他们认为,评论中的不文明行为对读者和新闻媒体产生负面影响,破坏了公民在互联网的建设性交流。鉴于不文明评论带来的紧迫社会挑战,政府和媒体平台应该进行必要的监管,维护和构建良好的互联网交流氛围。
互联网的使用已从被动信息访问转变为主动信息共享并与他人互动。随着用户逐渐在互联网上提供个人信息,这已经改变了互联网使用的私有性和匿名性程度。此外,网络安全威胁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使用户更难识别访问互联网和共享个人信息时涉及的风险。盖恩斯伯里等(Gainsbury et al., 2019)认为,与现实生活相比,人们在网络生活中受到的行为规范约束较小,人们更有可能在互联网上披露个人信息或偏离常规的社会规范。因此,网络环境使人们更容易被网络信息误导,从而导致恶意行为或危险情况的发生,这增加了人们成为网络犯罪受害者的风险。研究还提出了一种基于经验的网络受害分类,共有四类:骚扰、盗窃身份、诈骗和欺凌。这项研究表明,继续制定政策和实践以保护互联网用户免受负面网络影响显然很有必要。人肉搜索行为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网络犯罪问题,包括侵犯隐私、冤枉无辜以及网络私刑。斯特拉·嘉(Chia, 2019)研究发现,从2006年到2015年间,人肉搜索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获得了大量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报道倾向于强调人肉搜索的自愿性质,并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公民行为,可以有效地加强社会规范和法律。相比之下这种做法的不良属性,例如侵犯个人隐私或迫害目标人群,受到的媒体关注相对较少。该研究认为,人肉搜索行为属于公民运动,其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民主的新闻媒体对此持开放态度。
(五)公众隐私安全与网络治理
在西方话语体系下,隐私被视为自由的重要条件和民主的基本价值,隐私是个人自治和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常常在用户完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披露个人信息,人们的网络隐私安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对网络隐私的监管成为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挑战。霍恩(Horne, 2019)等的研究证实,新的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会影响隐私规范和信任。互联网用户为了使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可以牺牲自己的隐私作为交换,即使用户中有人出现隐私问题,他们对技术提供者的信任也不会受到影响。因此,使用侵犯隐私的新信息技术的人越多,隐私规范的作用就越弱。同样,冈纽克斯(Gangneux, 2019)的研究证实,年轻人对于社交媒体上的隐私监视现象已习以为常,并将其作为社交媒体互动的一部分。库什等(Keusch et al., 2019)学者认为,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的被动数据收集加剧了用户个人隐私泄露问题,他们调查研究后发现,超半数智能手机用户并不愿意与应用程序供应商共享个人数据,包括个人通讯录、地理位置、浏览记录和应用程序使用情况等。多伯等(Dobber et al., 2019)学者的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以解释人们对隐私的担忧,这表明隐私问题不仅限于社会的特定人群,而是整个社会的现象。研究进一步表明,青年人群和中老年人群的“经验差距”使得数字原生代人群更有能力应对其隐私方面的威胁。韩国学者黄和盛等(Hwang et al., 2019)的研究发现,疲劳因素(社交互动负载、不良关系)和诱导因素(同伴压力和替代吸引力)对社交网站用户的切换意图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当用户感到现有社交网站使用造成身心负担而且更有吸引力的社交网站出现时,他们切换新社交网站使用的愿望就会增加。研究还证实,隐私因素不会对社交网站的切换意图产生重大影响,社交网站用户为了人际交往愿意牺牲个人隐私,因此未来的社交网站研究应更加关注用户的隐私问题。
通过网络治理的概念可以认识到,治理不仅是由国家进行的,而且还由多种行动者通过多种机制合法地进行。虽然网络治理一词通常用于人口治理的语境下,但它也可以用于自我治理。班纳曼(Bannerman, 2019)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新颖的自我治理形式和可视化的自我监控功能,但他对网络自我治理的兴起和更普遍的网络治理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在网络时代,必须重新考虑隐私在自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隐私在自我网络治理中的四个功能:个人自治、情感释放、自我评估和人际交往对隐私政策和法律具有重要意义。隐私法必须存在于更广泛的政策生态系统中,旨在重新配置和选择我们所参与的网络来实现自我治理。范迪克和雅克布斯(Van Dijck & Jacobs, 2019)认为,电子身份证(eID)已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战略性基础设施。电子身份证是证明个人身份的数字解决方案,它不仅可以用作身份验证和登录数字机构的工具,还可以对电子文档进行数字签名授权。潘格拉齐奥和塞尔温(Pangrazio & Selwyn, 2019)认为,提高个人数据素养是隐私保护的重要做法之一,并提出了个人数据素养框架,包括数据识别、数据理解、数据批判、数据使用和数据策略五个重要领域。利纳巴里等(Linabary et al., 2019)以权力关系中的隐私为视角,研究认为隐私嵌套在多个相交的权力关系中,享有控制权的个人或组织拥有能力授予和侵犯隐私。因此,学者在解决网络隐私问题时,必须与社会和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打交道,例如在性别、性取向、阶级、种族和宗教信仰中的弱势群体。研究进一步表明,侵犯弱势群体的隐私会增加他们受到数据监视和歧视的风险。
(六)社交媒体空间的数字女权运动
距离2017年全球“Me Too”运动的发起已有两年,女权主义者呼吁的“女性平权”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其与社交媒体相结合形成的数字女权运动成为全球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门德斯等(Mendes et al., 2019)学者指出,数字空间是女性主义行动的“沃土”,尤其是博客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为数字女权行动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数字化运动不仅可以打击性暴力行为,而且可以使受害者发声并为她们提供替代的司法援助。普鲁赫涅夫斯卡(Pruchniewska, 2019)指出,尽管多年来女权主义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面对这些歧视经历,各个行业中的女性正在创建女性专用的私人Facebook团体,以提供专业支持、网络机会和职业发展。研究表明,这种针对职业女性的私人Facebook团体成为倡导女权意识、提升女权主义的数字化第四次浪潮的一部分。利纳巴里等(Linabary et al., 2019)指出,“标签女权主义”的出现就是数字女权运动的一个例子。主题标签已成为数字女权运动的工具和空间。标签女权运动通过使用话题标签来分享个人不平等经历,并邀请经常沉默或被忽略的个人分享经验,从而共同构建反话语以及批评话语来解决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
艾尔什克(Elsheikh, 2019)和索森(Thorsen, 2019)通过网络女权运动的案例,考察了埃及和沙特的女权主义运动。研究发现,当代女性已经能够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活动,这种方式便是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数字女权运动。社交媒体本身无意发起反公共的社会运动,但它的匿名性为女权主义者团结更多女性进行社会变革的愿望提供了空间。女权运动者在一个类似于微型公共领域的友谊网络中讨论女权问题时,不仅能够挑战社会规范,且不会激怒国家或安全机构,避免成为政治两极化环境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在线女权运动模式为全球建立更强大的女权主义公共领域开辟了一条变革的道路。
女性化广告被定义为旨在挑战女性刻板印象和女性社会污名的广告。温德尔斯等(Windels et al., 2019)学者的研究探讨了曾获奖的女性化广告后发现,女性赋权广告有时会采用后女权主义话语,其特征是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话语的纠缠,女权主义理念既被宣扬又被否定。后女权主义表明女性已经实现了平等,因此不再需要女权主义。在女性化广告语境中,广告商试图将女权主义话语附在商品上,本质是将女权主义推向直接购买的目的,女权主义理想沦为品牌或产品定位的噱头。
在互联网上,女性容易成为被骚扰者,而男性通常成为犯罪者。与其他形式的数字仇恨(例如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一样,网络厌女症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吉恩等(Ging et al., 2019)学者发现,Web2.0促进了一个特别“有毒”的数字男性权利主义运动团体,统称为“Manosphere”的亚文化社群。这个社群以其强大的反女权主义和极端的厌女症协同作用而闻名。Manosphere社群的网络影响力日益壮大,这对青少年对性别平等或性关系的看法有着潜在的负面影响。近期,“男人走自己的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简称MGTOW)作为一个分裂主义的Manosphere社群之一,在助长网络性骚扰方面受到抨击。琼斯等(Jones et al.,2019)学者研究发现,MGTOW团体对女性的骚扰根植于其深深的反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中,从而产生厌恶女性和暴力行为,其根本目的是在互联网空间中构造男性气质的新霸权。MGTOW团体的不文明在线行为和针对女性的劣等侵犯具有危险性。
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LGBT)社群及其行动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互联网的人际交往逐渐从匿名模式转移到开放的、基于多种多样个人资料和身份的社会交往模式。但是,所谓的基于匿名性的社会交往在互联网上还没有完全消失,这种匿名性为不符合社会主流文化的群体,特别是LGBT群体的兴趣和身份表达提供了空间。菲利斯等(Ferris et al., 2019)学者发现,很少有专门针对LGBT群体的交友应用程序,LGBT群体只能转向流行的异性恋约会应用程序来结识约会对象。但是,异性恋约会应用程序会为LGBT群体带来麻烦,因为他们需要在多个重叠的受众群体中努力凸显自己的身份,从而找到符合自己性取向的约会对象。特里格斯等(Triggs et al., 2019)学者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交平台要求的用户信息很少,但由于LGBT群体的社会边缘性,为了保证其在互联网的完全匿名状态,LGBT用户仍需间歇性采用“社交情境崩解”(context collapse)策略,以避免或阻止不受欢迎的浏览和评论。达恩斯和伯吉斯(Dhaenens & Burgess, 2019)的研究表明,流行音乐文化是LGBT群体表达舒适、愉悦、归属和认可的重要资源。尽管在数字时代音乐消费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音乐的社会和文化重要性并未减弱。以LGBT为主题的数字音乐策展通过三种富有成效的方式与LGBTQ文化互动,分别为保存LGBT音乐文化、寻求LGBT盟友和建构LGBT身份政治。
(七)数字鸿沟的影响与弥合
数字鸿沟并非一个新概念,但是,目前约有一半的世界人口仍未上网(Park, 2019),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创新以及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活方面的深度应用,更加凸显了数字鸿沟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到弱势群体面临数字化浪潮时的挑战。
学习如何正确地参与数字生活是儿童成长过程最重要的一项技能。梅斯等(Meeus et al., 2019)学者指出,儿童在成长时期对媒体的认知与使用,其家庭和教育环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谢尔德等(Scheerder et al., 2019)的研究证实,家庭教育背景是数字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互联网表现出批判性的看法,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对互联网兴趣不大。这种差异在互联网驯化过程早期阶段出现,并在随后的阶段中加剧,从而导致数字不平等现象。斯塔基等(Starkey et al., 2019)学者认为,儿童不是信息的被动消费者,他们与成年人一样渴望参与数字生活。儿童参与数字生活的方式和程度与缩小未来的数字鸿沟息息相关,最小化未来的数字鸿沟意味着所有年轻人都将学习如何参与数字环境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格德哈特等(Goedhart et al., 2019)学者的研究证实,在家庭结构中,母亲在支持子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母亲的数字素养对未来社会数字鸿沟的缩小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卡茨等(Katz et al., 2019)学者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学历和英语能力有限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包括父母和儿童),可以从互联网的使用中获得更多收益。因此,通过为弱势家庭提供互联网补贴的计划是解决数字不平等的重要基础。
虽然互联网被认为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针对残疾人群体互联网使用的研究还处于边缘地带,近年来,残疾人群体的数字生活研究逐渐受到关注。阿尔弗里德森等(Alfredsson et al., 2019)通过调查法研究了智障青少年的数字参与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超过60%的智障参与者拥有设备来访问互联网,但设备属性对智障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构成了挑战,随着自适应硬件和软件设备的不断升级,应该为不同程度的智障人士设计更适合他们访问互联网的设备。彼特曼(Bitman, 2019)认为,尽管智能手机的使用丰富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残疾人群体可能无法“激活”其所有的社会和技术功能。智能手机在设计过程中便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因此,智能手机特定的使用模式会加深数字鸿沟现象。帕切科(Pacheco et al.,2019)等研究发现,有视力障碍的残疾学生可以在一系列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掌握必需的技能和知识,并获得自我决策的能力。信息通信技术促进了视障年轻人的社会化,对缩小社会数字鸿沟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尼姆罗德(Nimrod, 2019)、潘宏辉(Pan et al., 2019)、韦尔斯(Welser et al., 2019)等学者研究了老年人和农村青年的媒体使用情况后认为,将老年、农村等社会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世界,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并消除其参与者的物质性和技术性障碍,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代际数字鸿沟等数字不公平现象的关键。
(八)人际关系与自我身份表达的再界定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工具,例如Facebook、Skype、Viber以及WhatsApp等,重新定义了通信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拓宽了人们的社交体验;甚至创新了人们构造身份的方式,从而产生了“更灵活的人类”。雷奎纳(Requena,2019)等研究证实,现代数字通信工具不应被视为面对面交流的替代品,数字网络使我们能够维持并加强以前仅限于面对面互动的人际关系,是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取代。作为社会生活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即时通信工具通过加强个人现有的人际关系并增加与他人交流的机会来促进社会交往,从而导致网络社会中用户角色、层次结构和权力形式的变化。同样,坎贝尔(Campbell, 2019)认为,智能手机的出现给移动通信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通过提供社交媒体、移动游戏、位置导航和一系列其他功能,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多功能性扩展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使单纯的人际交往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智能手机被描绘为社交生活领域中的附加连接层,移动通信工具通过为媒体用户之间提供不受限制的访问,从而加强了人们社交网络之间的连接强度。
随着社交网站上人际互动的流行,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印象形成不仅限于面对面互动,还扩展到了数字环境,人们可以通过其个人网页或网络活动推断他人的个性。因此,社交媒体对于互联网用户的身份表达以及自我认知起着重要作用。个人资料编辑在数字文化中已变得司空见惯,许多数字平台包括网络银行、游戏网站、交友程序以及社交网站等,通常要求互联网用户创建个人资料。舒尔茨(Szulc, 2019)认为,社交网站要求用户进行资料编辑的实践与用户个人身份的表现和构建密切相关。用户进行个人资料编辑的行为是一系列构建数字身份的表演性过程,数字身份和离线身份表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用户自我认识的形成。斯蒂芬妮·唐等(Tong et al., 2019)认为,人们在网络交友时,其撰写的个人资料是向他人介绍自己并发现潜在好友的主要方式。研究发现,人们在交友时的自我陈述行为往往具有战略性。人们倾向于选择性地展示出最“理想的”自我,同时将一个“真实的”自我隐藏。尽管在任何交流环境中真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的这种张力始终呈现,但网上交友环境使这种张力尤为突出。斯蒂芬妮等(Stefanone et al., 2019)对自拍进行研究发现,互联网用户通过美化自拍照来展示出个人最具竞争力的视觉特征,与拍照相比,美化图片的过程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该研究表明,美化照片是一种战略性和竞争性的自我展示方法,社交媒体用户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维持或增强其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展示。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网站上的图片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交活动,分享图片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日常交流行为。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例如Facebook、Instagram和Snapchat都鼓励人们以数字形式与亲友或他人分享生活。图片在社会上的用途已经多样化并嵌入移动通讯技术和人际交往实践中。赖斯(Reiss, 2019)认为, 图片已成为互联网用户自我披露和自我表达的主要工具,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个人发布或分享的图片可以作为其教育和经历的重要信号。社交媒体上大量基于图片的活动加剧了其用户对身体图像的关注,包括身体不满和自我客体化等问题。科恩等(Cohen et al., 2019)认为,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通常归因于社交比较的结果,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对自我评价的追求促使个人寻求与自己相似而不是相异的人进行比较,从而导致对自己身体和外观的不满意。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上关于身体正面内容的帖子可以提高女性用户的积极情绪、身体满意度和身体欣赏能力。帝格曼和安德伯格(Tiggemann & Anderberg, 2019)的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查看真实的、未美化的照片对于减少用户身体不满意具有正向作用。因此,这些研究鼓励社交媒体用户上传更加真实的照片供他人查看,以降低或消除观看理想图像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社交媒体用户对自己身体的接受、喜爱和尊重。
(九)算法与人工智能的伦理建构
大数据和算法改变了组织的决策方式,社会越来越依赖算法与人工智能做出决策,伦理的问题因此变得日益突出。麦肯锡(Mackenzie, 2019)认为,随着算法被嵌入组织内部,其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且越来越不透明。创建算法的人可以在“数据价值链”的每一阶段做出任意决定,但是这些主观性却无法被看见。算法可以反映出其创建者的偏见,可以强化既定的思维方式并可能带有某些政治倾向。霍夫曼(Hoffmann, 2019)指出,偏见和公平是新兴的数据正义领域的中心主题,大数据和算法决策应用于特定类型的问题时,其具有的隐瞒和放大现有威胁的能力,有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冈瓦达兰(Gangadharan, 2019)等证实,以技术为媒介的歧视与其他形式的歧视一起存在,这些歧视导致以社会差异为特征的个人和群体的系统性边缘化。数字技术的不透明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要求公共及私营组织在开发、实施和使用算法时更加透明。肯珀(Kemper, 2019)等学者指出,算法的透明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其面对的受众,不考虑受众的关键性和公正性,算法的透明性便无从谈起。评估算法的透明性时,应该通过算法与受众建立的实际效果来考察而不是预期效果。将算法问责制视为人与机器的一种社会技术组合,对于提高数字技术的透明度最为有效。阿拉道等(Aradau et al., 2019)学者认为,将数字技术赋予人道主义观念是推动数字技术更加透明的关键。算法编写和大数据处理等行为的背后终究归属于人类实践。人类在数字化生产时将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既关注技术的科学性又考虑伦理性,这对技术透明和社会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埃罗非耶娃(Erofeeva, 2019)指出,工程师将人类的能力委派给机器以实现人工智能,人不再是话语实践和主观行动的唯一来源,人工智能技术将人的控制权转移到人与技术的混合控制权上。技术转折标志着人类社会未来面临的严峻挑战。格雷(Gray, 2019)以“数据见证”概念作为出发点认为,人类可能正在从基于记忆的社会决策转变为基于数据的社会决策。人类依靠外部工具来解决问题,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人类大脑的类似扩展以及做出社会决策的工具。包括可穿戴技术和增强现实在内的尖端技术向社会的传播,很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模糊人类认知与计算机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系统在人类社会的许多领域都有重要作用,关于人工智能的道德行为与影响逐渐受到关注。尚克等(Shank et al., 2019)的研究证实,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观念可能将道德过失从人类身上夺走,从而更多地将道德过失归因于机器本身。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被用作人类失败的道德替罪羊。而与人工智能交互的技术人员的过失则被忽视。因此,了解人工智能的行为、道德和感性含义不仅是了解技术的关键,对于更广泛地了解人类和社会也很重要。
普斯卡(Puskar, 2019)通过回顾手指计数的历史及其与计算技术的相关性认为,人类的手指早已塑造成为数字手指,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也早已融入手指中。从更早、更简单的技术追踪到数字技术的出现,普斯卡认为,人类的手指也曾经是“新媒体”,从罗马算盘到触摸屏,技术以非常特定且一致的方式对身体进行数字处理。他强调,人体的数字化既不是人类的基础也不是人类的否定,它只是人类的一种特别配置。数个世纪以来,数字化如此牢固地存在于人体中,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计算机不仅是人类控制下的功利性工具,而且是当今世界的人性化引擎,它们定义了对人类的意义。
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模拟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法,迄今为止各种难以解决的计算问题,例如图像识别、语言处理和大数据识别等,现在都可以依靠深度学习自动解决。穆尔霍夫(Mühlhoff, 2019)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是一种新型的联网技术,该技术通过将人类作为认知主体来实现智能设备的学习。因此,深度学习的“突破”不仅需要开发高性能并行计算机,还需从根本上改变人机交互的典型问题。深度学习的成功所依赖的稀缺资源既不是算法也不是计算机,而是其数据的可用性,而数据的最终来源依靠人类的参与。人类资源的重要性导致了基于现有社会经济鸿沟的新形式的剥削和隐性劳动的出现。
(十)创意产业的分布式生产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更灵活、更弹性化的分布式生产。斯科勒(Scolere,2019a)认为劳动条件已经转向后福特主义模式,即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的生产模式。越来越多的劳工开始依赖兼职、临时工作、第二份工作和咨询项目来构成投资组合职业。斯科勒(Scolere, 2019b)强调,“灵感工作”是数字灵感经济中的一个要素,作为这些数字平台的一部分,灵感成为专业设计师之间交换的一种货币形式。这些设计师在浏览和管理数字灵感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同时创建出新作品,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工作形式。
2011年,直播平台Twitch.tv的出现受到了游戏玩家和新兴专业游戏玩家的欢迎,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向休闲娱乐方面的转变正在加速。布里瓜里洛认为,游戏直播的新自由主义标志着身份和情感的去政治化,可以解决女性游戏玩家、有色人种游戏玩家和酷儿游戏玩家在直播平台上遭受的身体和情感虐待。简而言之,最有利可图的策略是刻画公平竞争的直播环境,即使笼罩在剥削性的不稳定的经济体系中,任何人,无论身份如何,都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和自营工作来成为直播者。直播已经被定义为一种媒体现象,通过它,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主播,将自己及活动展示给大量的在线观众。此外,诸如时尚博客、旅游博客、美食主播、购物直播等富有创造力和自由的职业,成为当今收入丰富但不稳定的职业选择。约翰逊(Johnson, 2019a)的研究发现,对于在直播中获得经济成功的人来说,直播正迅速发展为他们的职业化道路。成本低、效率高的直播行业的增长使网络主播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全球知名度,成功的创意工作者正在成为数字“文化工作”的鲜明特征。
与传统的直接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业不同,共享经济公司以中间商的身份进行运作,将拥有商品或资产的人与愿意付费共享商品或服务的人联系起来。共享经济公司的广告倾向于将其服务构建为技术进步的杰出产品,甚至是实现更大的个人自由的途径,但福克斯(Fuchs, 2019)警告说,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商品化抽象逻辑扩展到信息和通信领域的危险。杜林格(Duerringer, 2019)的分析表明,应将共享经济公司视为新自由主义对公众攻击的预兆。共享经济公司利用私有领域的语言来包装业务,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边界上行走,成功地进行了长期的套利交易,从而确保了出售商品或服务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又支付了很少的社会成本。这样的企业只要成功说服公众将商品共享视为好心人之间的私人交易,便可以低买高卖,从而将差额收入囊中。这些新兴的共享经济公司并没有发放免费的午餐,他们只是在赚取公众的利益。拉森(Larson, 2019)的研究表明,在共享经济条件下,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增强的特定社会策略也可以提高员工的弹性,并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创造力和经济回报的平衡。艺强灿(Chan, 2019)指出,共享经济公司的员工与传统员工的区别在于,前者越来越关注数字化劳动中的大数据工作安排和算法式劳动力管理。共享经济公司和创业者可以从技术和新形式的工作中获得巨大收益,而这些技术和新形式的工作使那些实际执行工作或使用技术的劳工们变得更加不稳定或不安全。代尔凡蒂(Delfanti, 2019)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公司旨在通过算法统治员工以满足其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实际上,将员工整合到算法系统中并不能消除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随着劳动过程技术性的增长而不断扩张。算法系统促进了资本对其数据的较新需求,他们负责数据的收集和抓取,然后使用这些数据来控制劳动过程。■
参考文献:
Acker, A. & DonovanJ. (2019). Data craft: a theory/methods packagefor critical internet stud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1)1590-1609.
AlfredssonA.K.Anette, K. & Helena, H. (2019). Digital participation?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8398.
AradauC.E.Blanke, T. & Greenway, G.R. (2019). Acts of digital parasitism: Hackinghumanitarian apps andplatformisation. New Media and Society21(11-12)2548-2565.
Bannerman, S. (2019). Relational privacy and the networkedgovernance of the self.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187-2202.
Barisione, M.MichailidouA. & AiroldiM. (2019). Understandinga digital movement of opinion: the case of #RefugeesWelcom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8)1145-1164.
BitmanN.& John, N.A. (2019).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martphone Users: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Penetration of Ableist Communication Norm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4(2)56-72.
BolsoverG. & Howard, P. (2019). Chinese computationalpropaganda: automation, algorithms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politics on Twitter and Weibo.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063-2080.
BradshawS.Howard, P.N.Kollanyi,B. & et al. (2019). Sourcing and Automation of Political News and Information over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6-2018. Political Communication37(2)173-193.
CampbellS.W. (2019). From Frontier to Field: Old and New Theoretical Directions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Studies.Communication Theory, 29(1)46-65.
ChanN.K. (2019).“Becoming an expert in driving for Uber”: Uber driver/bloggers’ performance of expertise and self- presentation on YouTube. New Media & Society21(9)2048-2067.
ChenS. M. (2019). Women’s March Minnesota on Facebook: Effects of social connection on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2694.
ChiaS.C. (2019). Crowd-sourcing justice: tracking a decade’newscoverage of cyber vigilantism throughout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045-2062.
Cohen, R.Fardouly, J.Newton-JohnT. (2019). BoPo on Instagram: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viewing body positive content on young women’s mood and body image. New Media & Society21(7)1546-1564.
CookC.Conijn, R.SchaafsmaJ. & et al. (2019). For Whom the Gamer Trolls: A Study of Trolling Interactions in the Online Gaming Contex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4(6)293-318.
Delfanti (2019). Machinic dispossession and augmented despotism: Digital work in an Amazon warehouse.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91613.
DobberT.Trilling, D.HelbergerN. & et al. (2019). Spiraling downward: The reciprocal relation between attitude toward political behavioral targeting and privacy concerns. New Media & Society21(6)1212-1231.
DhaenensF. & BurgessJ. (2019).“Press play for pride”: The cultural logics of LGBTQ-themed playlists on Spotify. New Media & Society21(6)1192-1211.
DuerringerC.M. (2019). Rhetorical Arbitrage: The Rhetoric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ommunication Theory, 29(4)383-400.
EldridgeS.A. (2019). “Thank god for Deadspin”: Interlopersmetajournalistic commentary, and fake news through the lens of “journalistic realization”. New Media & Society21(4)856-878.
ElsheikhD. & Lilleker, D. G. (2019). Egypt’s feminist counterpublic: The re-invigoration of the post-revolution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90576.
ErofeevaM. (2019). On multiple agencies: when do things matter?.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5)590-604.
Feezell, J.T. & OrtizB. (2019). “I saw it on Facebook”: an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learning through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97340.
FerrisL. & Duguay, S. (2019). Tinder’s lesbian digital imaginary: Investigating (im) permeable boundaries of sexual identity on a popular dating app. New Media & Society22(3)489-506.
FitzgeraldA.A. (2019). “Mapping” Media Spaces: Smoothness, Striationand the Expropriation of Desire in American Journalism from Postindustrial to Datafied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9(4)401-420.
Fuchs, C. (2019).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9(2)129-150.
Gainsbury, S.M.Browne, M. & Rockloff, M. (2019). Identifying risky Internet use: Associating negative online experience with specific online behaviours. New Media & Society21(6)1232-1252.
Gangadharan, S.P. & Niklas, J. (2019). Decentering technologyin discourse on discriminat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7)882-899.
GangneuxJ. (2019). “It is an attitude”: the normalisation of socialscreening via profile checking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68460.
Garcia-Perdomo, V. (2019). Technical frames, flexibilityandonline pressures in TV newsroom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57163.
Garrett, R.K.Long, J.A. & JeongM.S. (2019). From Partisan Media to Misperceptio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as Mediato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9(5)490-512.
GingD.Lynn, T. & Rosati, P. (2019). Neologising misogyny: Urban Dictionary’s folksonomies of sexual abuse. New Media & Society22(5)838-856.
GoedhartN.S.BroerseJ.E.KattouwR.& et al. (2019). “Just having a computer doesn’t make sense”: The digital div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thers with a low socio-economic position. New Media & Society21(11-12)2347-2365.
GrahamE. (2019). Boundary mainten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rolling. New Media & Society21(9)2029-2047.
GrayJ. (2019). Data witnessing: attending to injustice with data in Amnesty International’s Decoders project.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7)971-991.
Hwang, G.S.Shim, J.W. & Park, S.B. (2019). Why we migratein the virtual world: factors affecting switching intentions in SN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127-2137.
HoffmannA.L. (2019). Where fairness fails: data, algorithms, and thelimits of antidiscrimination discours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7)900-915.
Horne, C. & Przepiorka, W. (2019). Technology use and normchange in online privac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vignette stud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84542.
Humprecht, E. (2019). Where“fake news”flourishes: a comparison acrossfour Western democrac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3)1973-1988.
HuntK. & Gruszczynski, M. (2019). The influence of new and traditionalmedia coverage on public atten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Dakota Access Pipelineprotest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 8X.2019.1670228.
Jaramillo-DentD. & Perez-Rodriguez, A. (2019). MigrantCaravan: The border wal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therness on Instagram.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94241.
Johnson, M.R. & Woodcock, J. (2019).“It’s like the gold rush”: the livesand careers of professional video game streamers on Twitch.tv.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3)336-351.
Jones, C.TrottV. & Wright, S. (2019). Sluts and soyboys: MGTOW and the production of misogynistic online harassment.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7141.
KalogeropoulosA.Fletcher, R. & NielsenR. (2019). News brand attribution in distributed environments: Do people know where they get their news?. New Media & Society21(3)583-601.
KatzV.S.MoranM.B. & OgnyanovaK. (2019). Contextualizing connectivity: how internet connection type and parental factors influence technology use among lower-income childre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2(3)313-335.
KemperJ. & KolkmanD. (2019). Transparent to whom? No algorithmicaccountability without a critical audienc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081-2096.
KeuschF.Struminskaya, B.Antoun, C. & et al. (2019).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assive Mobile Data Colle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83(s1)210-235.
Kleinberg, M.S & LauR.R. (2019).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Knowledge for Effective Citizenship.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83(2)338-362.
KleinnijenhuisJ.Van Hoof, A.M.J. & Van AtteveldtW.(2019).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on Political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9(6)650-673.
LaneD. S.DasV. & Hiaeshutter-RiceD. (2019). Civiclaboratories: youth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anonymousephemeralgeo-bounded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171-2186.
LarsonC. (2019). Open networks, open books: gender,precarity and solidarity in digital publishing.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21922.
Larsson, A.O.(2019). Right-wingers on the rise online: Insights from the 2018 Swedish elections.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7700.
LinabaryJ.R.Corple, D.J. & CookyC. (2019). Feminist activism in digital space: Postfeminist contradictions in #WhyIStayed.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4635.
LinabaryJ.R. & Corple, D.J. (2019). Privacy for whom? a feministintervention in online research practic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0)1447-1463.
Literat, I . & Kligler-Vilenchik, N. (2019). Youth collective political ex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affordances and memetic dimensions for voicing political views.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37571.
Mackenzie, A. (2019). From API to AI: platforms and their opacit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3)1989-2006.
Meeus, A.EggermontS. & Beullens, K. (2019). Article Navigation Constantly Connected: The Role of Parental Mediation Styles and Self-Regulation in Pre- and Early Adolescents’ Problematic Mobile Device Us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5(2)119-147.
MendesK.Keller, J. & Ringrose, J. (2019). Digitized narratives of sexual violence: Making sexual violence felt and known through digital disclosures. New Media & Society21(6)1290-1310.
MolyneuxL.LewisS.C. & Holton, A.E. (2019). Media work, identity, and the motivations that shape branding practices among journalist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New Media & Society21(4)836-855.
MühlhoffR. (2019). Human-aid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how to run large computations in human brains? Toward a media sociology of machine learning.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5334.
NimrodG. (2019). Selective motion: media displacement amongolder Internet user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9)1269-1280.
Ognyanova, K. (2019). The Social Context of Media Trust: A Network Influence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9(5)539-562.
OhmeJ. (2019). Updating citizenship? The effects of digital media use oncitizenship 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3)1903-1928.
Pacheco, E.Lips, M. & YoongP. (2019). ICT-enabled self-determination, disability and young peopl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8)1112-1127.
Padgett, J.DunawayJ.L. & Darr, J.P. (2019). As Seen on TV? How Gatekeeping Makes the U.S. House Seem More Extrem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9(6)696-719.
Pan, H.H.Donder, L.D.Dury, S. & et al. (2019).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Belgium’s Flanders region: exploring the roles of both new and old media usage.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3)1956-1972.
Pangrazio, L.Selwyn, N. (2019).“Personal data literacies”: A critical literacies approach to enhancing understandings of personal digital data. New Media & Society21(2)419-437.
ParkS. & HumphryJ. (2019). Exclusion by design: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digital and data exclus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7)934-953.
PowersM. & Vera-ZambranoS. (2019). Endure, Invest, Ignore: How French and American Journalists React to 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9(3)320-343.
PruchniewskaU. (2019). “A group that’s just women for women”: Feminist affordances of private Facebook groups for professionals. New Media & Society21(6)1362-1379.
PuskarJ. (2019). Counting on the body: Techniques of embodied digitality. New Media & Society21(10)2242-2260.
Reiss, M.V. & TsvetkovaM. (2019). Perceiving education from Facebook profile pictures. New Media & Society22(3)550- 570.
Requena, F. & AyusoL. (2019). Individualism or complementarity? The effect of digital personal networks on face-to-face personal network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4)2097-2111.
Rohlinger, D.A. (2019). Symposium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movements: ships passing in the night.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5)724-738.
RohmanA. (2019). Persistent connection and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use in post-peace movement AmbonIndonesia.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31973.
Scheerder, A.J.Van DeursenA.J.A.M. & Van Dijk, J.A.G.M. (2019). Internet use in the home: Digital inequality from a domestication perspective. New Media & Society21(10)2099-2118.
Scolere, L. (2019a). Brand yourself, design your future: Portfolio-building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New Media & Society21(9)1891-1909.
Scolere, L. (2019b). Digital inspirational economy: the dialectics of design,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 10.1080/1369118X.2019.1684543.
Shank, D.B.DeSantiA. & Maninger, T. (2019). When a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ersus human agents faulted for wrongdoing? Moral attributions afterindividual and joint decision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5)648-663.
ShenC.H.KasraM.PanW.J. & et al. (2019). Fake images: The effects of source, intermediary, and digital media literacy on contextual assessment of image credibility online. New Media & Society21(2)438-463.
Starkey, L.EppelE.A. & SylvesterA. (2019). How do 10-year-old New Zealanders participate in a digital world?.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2(13)1929-1944.
Stefanone, M.A.YueZ.Y. & Toh, Z. (2019). A 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 to traditional media content and social media use: Selfie-related behavior as competitive strategy. New Media & Society21(2)317-335.
StroudN. J. & Muddiman A. (2019).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With Strategy- and Issue-Framed Political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9(5)443-466.
Szulc, L. (2019). Profiles, Identities, Data: Making Abundant and Anchored Selves in a Platform Society. Communication Theory, 29(3)257-276.
Thorsen, E. & Sreedharan, C. (2019). EndMaleGuardianship: Women’s rights, 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21(5)1121-1140.
Tiggemann, M. & AnderbergI. (2019). 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The effect of “Instagram vs reality” images on women’s social comparison and body image.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8720.
TriggsA.H.M?llerK. & Neumayer, C. (2019). Context collapse and anonymity among queer Reddit users.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90353.
TongS.T.Corriero, E.F.Wibowo, K.A. & et al. (2019). Self-presentation and impressions of personality through text-based online dating profiles: A lens model analysis. New Media & Society22(5)875-895.
Van DijckJ. & Jacobs, B. (2019). Electronic identity services as sociotechnical and political-economic constructs. New Media & Society22(5)896-914.
Velkova, J. & Kaun, A. (2019). Algorithmic resistance: mediapractic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air.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57162.
Vraga, E.K. & TullyM. (2019). News literacy, social media behaviorsand skepticism toward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9.1637445.
WelserH.T.Khan, M.L. & DickardM. (2019). Digitalremedi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can help offset rural digital inequality.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2(5)717-723.
Windels, K.Champlin, S.SheltonS. & et al. (2019). Selling Feminism: How Female Empowerment Campaigns Employ Postfeminist Discourses. Journal of Advertising49(1)18-33.
YamamotoM.NahS. & YoungS. (2019). Social media prosumption an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xamination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New Media & Society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19886295.
Ziegele, M.Naab, T.K. & Jost, P. (2019). Lonely together? Identif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corrective action against uncivil comments. New Media & Society22(5)731-751.
赵曙光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竹箐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