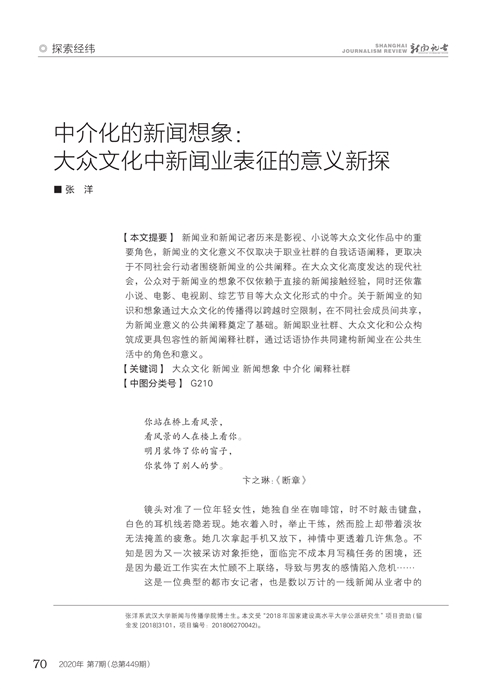中介化的新闻想象: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意义新探
■张洋
【本文提要】新闻业和新闻记者历来是影视、小说等大众文化作品中的重要角色,新闻业的文化意义不仅取决于职业社群的自我话语阐释,更取决于不同社会行动者围绕新闻业的公共阐释。在大众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对于新闻业的想象不仅依赖于直接的新闻接触经验,同时还依靠小说、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大众文化形式的中介。关于新闻业的知识和想象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在不同社会成员间共享,为新闻业意义的公共阐释奠定了基础。新闻职业社群、大众文化和公众构筑成更具包容性的新闻阐释社群,通过话语协作共同建构新闻业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和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 新闻业 新闻想象 中介化 阐释社群
【中图分类号】G21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镜头对准了一位年轻女性,她独自坐在咖啡馆,时不时敲击键盘,白色的耳机线若隐若现。她衣着入时,举止干练,然而脸上却带着淡妆无法掩盖的疲惫。她几次拿起手机又放下,神情中更透着几许焦急。不知是因为又一次被采访对象拒绝,面临完不成本月写稿任务的困境,还是因为最近工作实在太忙顾不上联络,导致与男友的感情陷入危机……
这是一位典型的都市女记者,也是数以万计的一线新闻从业者中的普通一员。然而她此刻并非正在进行电视新闻的连线直播,而是出现在一部以记者为主角的电视连续剧中。她的工作状态和感情生活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牵动着屏幕前观众的心弦。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以记者为主角的电影和电视剧出现在观众面前。一部再现了《波士顿环球报》如何针对宗教势力进行调查的电影《聚焦》,一举斩获201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三年后,汤姆·汉克斯与梅丽尔·斯特里普联袂出演的《华盛顿邮报》再度为新闻业的荣光加冕。美剧《新闻编辑室》更是风靡全球,剧中曲折刺激的新闻采编场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令无数心怀理想的青年萌生了投身新闻业的信念。
那么新闻研究者应当如何看待和反思这些以新闻业为主题、以记者为主角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如何参与新闻业的意义阐释和权威建构?大众文化中的新闻业形象如何影响公众对于新闻业的想象?本文尝试在理论层面澄明大众文化对于新闻业的意义,并将大众文化表征置于新闻业文化研究的脉络之中,与该领域的诸种经典分析范畴和理论框架进行对话。
一、理解大众文化中的新闻业表征:既有研究的发现与遮蔽
早期描绘新闻业的大众文化传播载体是小说,自19世纪后半叶至今,仅美国一地就出版了1000多本关于新闻工作者的小说(Brennen, 1993)。关于记者的小说通常体现为三种叙事模式:刚走出校园的新手记者在一系列挫折中接受职业训练;充满正义感的记者孤身调查,揭露黑幕,为自己赢得名声或爱情;小镇报纸在风俗淳朴的社区中有条不紊地工作(Good, 1986)。
20世纪以来,随着视觉媒体叙事蓬勃兴起,电影成为描绘新闻业的主要流行艺术形式。根据Ness(1997)的统计,20世纪有超过2000部关于新闻业的电影。电影的影响范围比小说和戏剧更加广泛,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商业电影是当代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主要来源(McNair, 2009:13)。因此,国际学界关于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相关研究,最初关注电影中的记者和新闻业形象,其后又逐渐辐射至小说、戏剧、电视节目等众多类型的流行文本。
此类研究大抵可归结为三类研究导向:第一类是大众文化中记者形象的类型学盘点,主要关注大众文化对某一特殊类型记者的表征,某一时期文本中的记者形象建构。就第一类而言,研究者曾先后对不同时期电影中的记者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提炼出一系列记者形象的原型,其中正面原型包括调查者、看门狗、见证者、女英雄、艺术家、犯罪克星、十字军,负面原型包括散布丑闻者、啜泣女孩、剥削者、恶棍、冷血动物、国王制造者、忏悔的罪人、杜撰者、诈骗者(Barris, 1976;Ghiglione, 2005;Ness, 1997;Langman, 2009, Saltzman, 2005)。众多五花八门的记者形象又可归为两种相互竞争的神话原型:游走于善恶之间、代表个人主义和自由的野生记者;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改良观念的严肃记者(Ehrlich, 2010:9)。
第二类研究关注战地记者、摄影记者以及女性和少数族裔记者等特殊群体如何被大众文本呈现,例如女性记者如何在大众文化中被烙上“啜泣的女孩”的性别刻板印象(Saltzman,2003),或是女性记者的性别气质如何被大众文化所规训(Lutes, 2006)。
第三类研究是对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历史考察,例如当代电影中的记者形象可以在早期电影中找到何种源头(Saltzman, 2002),记者及其工作状态从何时起成为浪漫喜剧的常见主题等(McNair, 2009)。此类研究又通常选取《公民凯恩》、《倒扣的王牌》、《总统班底》、《电视台风云》等不同年代的代表影片进行文本细读(Ehrlich, 2010)。
以上三种研究导向,究其本质而言均属于电影史或文学史研究的特殊分支,将表征新闻业的作品视为一种特殊的文艺类型,而与新闻理论、新闻实务、新闻史或是媒介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和问题意识相对脱节,难以形成有效的理论对话。此外有学者曾将关于新闻业的电影作为新闻伦理教学的案例库加以考察(Good, 2007),但此种路径仅仅将电影作为静止的客体和还原的镜像,未能充分阐发电影等大众文化形式对于新闻业的能动塑造。因此导致了上述研究成果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互相参照,而在新闻学、传播学总体研究领域中的引用率和影响力均较为有限。
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理论意义始终未曾得到充分的解读,部分源于大众文化研究中新闻学想象力的缺乏,部分则是因为新闻研究者对大众文化表征的长久忽视。这一理论盲点限制了我们对于新闻业文化权威塑造机制的反思,未能将新闻业与更广阔的文化生产场域联系起来。要突破这一盲点的限制,我们首先需要回到新闻业文化权威研究的理论起点,即由芭比·泽利泽(Zelizer, 1993)提出的“新闻阐释社群”概念。
二、被误读的“阐释社群”:从职业阐释到公共阐释
泽利泽(Zelizer, 1993)不满于将新闻视为职业的单一视角遮蔽了记者之间的非正式互动以及话语和叙事的作用,将当时人文研究中方兴未艾的“阐释社群”理念引入新闻研究的视野,指出新闻业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阐释社群,新闻从业者通过共同的论述和对重要公共事件的集体解释而联系在一起。由此出发,研究者应当关注那些新闻史上例如水门事件、麦卡锡事件等“热点时刻”,记者如何建构自己的专业话语以维持社群的想象。泽利泽(Zelizer, 2005)进而将“新闻业的文化”(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作为一种替代性视角,弥补职业、产业、机构和手艺等既有视角的
局限。
自泽利泽之后,从“阐释社群”的框架中流衍出“范式修复”、“记忆建构”、“新闻权威”等多元理论脉络。这些视角的共性是将新闻业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关注阐释新闻业意义的话语与元话语。此种研究路径被舒德森(Schudson, 1989)概括为文化取向,是新闻研究的三大传统之一。文化取向的新闻学者关注记者如何运用话语塑造新闻理念和专业权威,如何创造在主体间共享的文化价值,旨在阐释新闻实践中的意义建构(陈楚洁,2018)。在文化棱镜的观照下,国内外学者深入阐释了媒体纪念话语、媒体献词、新闻行业刊物、新闻奖颁奖辞、记者讣闻、离职告白等文本,包罗了新闻业界与学界、历史与现实、兴盛与危机的诸般面向。这些研究共同关注新闻从业者围绕与新闻业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各类公共议题的论述,即“新闻职业话语”(白红义,2018)。
在其宏文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中,泽利泽概述了各类关于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学术论述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其中起源最早、最具影响,同时也与泽利泽的理论之间具有最明确的起承关系的当属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文学研究中提出的阐释社群理论。然而被学界长期忽视的是,泽利泽回避了费什对于阐释社群的关键界定,由此而导致了对阐释社群理论的
误读。
斯坦利·费什是英美文学批评界“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y)的领袖学者,他批评传统的文学研究一味关注文本的形式结构,假定文本的生产者可以决定文本的意义,却忽视了受众在意义解读中的能动性。他提出不同读者面对同一作品会产生不同的意义阐释,正是读者的阐释为文本赋予意义,而非反之。这种强调读者自主性的阐释学观点面临着一种现实挑战,即许多读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解释是非常接近的,而且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一部作品的解释也相对稳定。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费什认为早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心中便已存在着某种阐释策略,这种阐释策略在不同读者之间共享,持有相似阐释策略的读者便构成了阐释社群。正是因为阐释社群的存在,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才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不同读者才能围绕文学作品的意义进行有规律的、秩序化的辩论。但阐释社群的稳定性也只是暂时的,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消长变化。(Fish, 2004:217-221)
泽利泽在三个层面上继承了费什的阐释社群思想:
1.意义阐释的社会性。不同于医疗、法律、心理咨询等传统职业(profession),新闻业本身缺乏坚实的职业技术壁垒,新闻职业正当性的建构依赖于社群成员的认同,而不是职业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天然特质。
2.意义阐释的规约性。阐释社群假定同一社群成员的眼光和行事必须与社群的目标相一致,早在新闻社群成员阐释行业事件之前,他们心中便已预先存有某种共享的阐释策略,规约着新闻从业者对事件意义的解读。
3.阐释社群的排他性。每个社群都存在边界,不同社群的阐释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社群的身份认同依赖于边界的维系。
然而在根本性的问题意识上,泽利泽走向了费什的反面。费什强调文学作品读者的重要性,强调意义是开放的,是由读者和作者共同生产的。而泽利泽则始终将目光投注于新闻职业群体的自我阐释,即新闻从业者群体对职业意义的建构,却没有将新闻作品的受众作为阐释的主体。因此泽利泽的阐释社群只是形式上的复数,其实质仍是由众多同质化的个体而构成的,聚焦记者如何通过话语修辞为自己的职业赋予意义。这恰恰是费什所批判的以文本生产者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费什力图解构文本的权威性,开放意义阐释的边界,从根本上否定文本形式和文本生产者对读者解读的任何决定作用,而泽利泽则力图为脆弱的新闻职业重建边界,将阐释新闻业意义的话语权力封闭在新闻职业社群中。
费什的阐释社群理论在文学理论界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批评,在于他完全取消了文学批评的正当性,将文学作品的意义解读归结为行业规范和体制性权力(赵毅衡,2015)。但这一在文学批评层面上的缺点恰好构成了对新闻行业的解释力。不同于文学作品复杂的文本形式和悠久的审美批评传统,新闻行业本身便与公共生活紧密相连,其意义历来附着于历史语境中的行业规范和体制性权力。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和新闻作品的评价标准相比文学作品,更加依赖于公众的认可与否,更少取决于文本本身和文本生产者的内在尺度。
如果按照“阐释社群”的原意来理解,那么新闻业的意义和重要性恰恰不在于记者如何自我言说,甚至不在于记者如何行事,而在于公众对新闻业意义的阐释。不同国家、族群、阶层、性别和教育程度的受众,对于新闻持有不同的想象,对日常新闻实践和新闻业的“热点事件”进行不同的意义阐释。共享着同类意义阐释策略的受众,便组成了范畴更广的新闻阐释社群。
新闻职业话语主要在职业社群内部流通,维系着社群的共享信念和凝聚力,但对社群以外社会成员的影响有限。与新闻业无关的男女老少,通常不会对记者的慷慨独白或是媒体人之间的相互评价给予太多关注。相反,在门户网站、媒体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区,以及在广泛的社交媒体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都在围绕新闻事件展开讨论,同时也在审视和点评记者的专业表现。记者的选题是否有公共价值,采访信源是否平衡,报道是否存在明显倾向,乃至于文字措辞是否妥帖,都被无数双眼睛紧密关注着。这些评论“旨在界定好新闻和坏新闻、好记者和坏记者以及应采取的措施”(Haas, 2006)。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到新闻生产中来,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唯一阐释主体(陆晔,周睿鸣,2016)。
尤为重要的是,从新闻业的规范理论来看,公众对媒体的信任被视为新闻业维持活力的“血液”,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是现代新闻业正当性的重要来源(Brants, 2013)。新闻业的权威地位,依赖于公众承认其制度化的知识控制。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话语阐释的权力空前地开放与分散。记者在“高度现代主义”(Hallin, 1992)时期养成的专业自信和自视甚高的形象,在后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被彻底动摇(Bogaerts, 2013)。仅关注新闻职业内部话语的阐释社群研究,在规范性和经验性的双重层面都面临着挑战。
因此,卡尔森批评泽利泽过于关注新闻业自身的话语,忽视了新闻业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他提出新闻的生产和消费都嵌入在公众关于新闻业的信念中(Carlson,2017:91),新闻权威并非被某种单一的力量所决定,而是与新闻业有关的特定行动者相互作用达成的理解,不仅依赖新闻业内部的专业主义、新闻形式和记者的自我叙述,同时还依赖于新闻业与四种外部因素的关系建构:公众舆论、信息源、技术和批评者。在部分国家,还包括新闻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记者与公众的关系是首要的(Carlson, 2017:185)。新闻业内外的行动者通过“元新闻话语”相互竞争,协商新闻实践的可接受边界(丁方舟,2019)。
根据卡尔森的界定,文化权威至少应当包含三个要素:创造知识的行动者,知识的话语建构,知识得以被创造和流通的关系(Carlson,2017:183)。但他本人所提出的关系模型在扩展了创造新闻知识的行动主体的同时,对最后一个要素的解释相对单薄,即人们关于新闻业的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和流通的?是哪些具体的作用机制促使人们内化了关于新闻业的种种规范性叙事?例如中国民众谈起记者时往往持有“为民请命”的角色期待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浪漫化想象,而美国民众则会首先联想起“看门狗”或是“扒粪者”的经典意象,人们进而根据这些预先熟悉的话语或形象来阐释当下新闻实践的意义。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为何会共享某种阐释新闻业意义的策略?不同类型的新闻阐释策略为何会在社会中呈现出具有一定秩序的分布?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对新闻想象的创造和流通机制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三、作为想象中介的大众文化
相比于权威视角强调建构新闻业的正当性,“新闻想象”(journalistic imagination)的概念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解框架。Ryfe将“新闻想象”界定为人们对于新闻业将要(would)、可以(could)和应当(should)如何行事的设想。Ryfe犀利地指出,记者只有在新闻想象的范畴之内行事才具有意义,不仅要内在于记者本人的新闻想象,同时还要符合公众的新闻想象,不然将无人资助其新闻实践,其新闻产品也无法获得正当性。他将新闻业的核心想象归结为三种:讲述真相、建构社群和促进协商辩论(Ryfe, 2016:106-107)。
公众围绕新闻业的想象,既是对新闻实践和新闻事件进行意义阐释的结果,同时也是意义阐释的前提。人们在讨论某起事件中记者的表现之前便已预先存在相应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既是规范性的,引导着人们思考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记者应当如何行事,新闻业应当扮演何种专业角色;同时也是经验性的,让人们得以理解记者在实践中可能面临怎样的困难,以至于无法很好地履行其角色。基于这种知识储备,关注新闻事件的人们才会富有逻辑地讨论记者的实践表现,以及这些表现是否合乎公众对于新闻业的期待,由此对新闻业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进行协商。持有不同知识储备的公众对新闻业也抱有不同的想象,以此为前提生成不同的意义阐释模式,构筑起多样的阐释社群。一种违反想象、不可想象或是超越想象的新闻实践行为,在任何语境下都很难获得社会正当性。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终其一生也不会踏入新闻编辑室的大门观摩新闻生产,甚至不会同新闻从业者直接打交道,他们唯有通过阅读新闻文本和关于新闻业的种种话语,才能了解新闻业的知识工作(Coddington, 2019:193),并使得关于新闻业的想象被正当化(Carlson, 2017:93)。个体获得新闻想象的过程,实则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新闻的直接阅读和收看,固然是新闻想象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被阅读或收看的新闻文本只是新闻生产的最终产品,并不能揭示隐含在新闻生产中的各类知识及其正当性依据。人际交往中关于社会经验的口耳相传,同样也是人们想象新闻业的重要源泉,但我们更需追问这种知识的最初起源来自何处,为何能够跨越时空界限而在社会成员之间有秩序地共享。
新闻想象的更加制度化的来源渠道,在于各类披露新闻生产“黑箱”的大众文本,包括但不限于记者的传记和回忆录、通识教科书中关于新闻业的论述、弥散在社交媒体空间中的围绕新闻业的讨论等,以及小说、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流行文化对新闻业的表征。如此种种,可以归结为一种想象创造和扩散的基本形式:中介化(mediation)。
“中介化”和与之伴生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此前已有众多学者辨析其概念,梳理其源流,本文在此不做详细展开。一言以蔽之,中介化是一种理论视角,将人类的交往与互动视为通过某种介质的中介而得以展开的过程,人们的交往形态被中介的性质所塑造。现代传媒兴起以来,迅速成为人们跨越时空交往的重要中介,深刻地塑造了象征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生产、传输与接收的方式,以及人们体验在时空背景上远离他们的行动与事件的方式,甚至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汤普森,2005:16)。媒体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中心的角色,媒体权力成为定义象征形式的普遍来源(Silverstone, 2005),媒体的传播过程直接介入意义生产之中(Couldry, 2008)。各种媒体按照不同规则生产和传播的文本、叙事和话语结构,提供了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公共意义和话语资源(潘忠党,2014)。
新闻学者对于中介化概念从不陌生,因为新闻正是人们认知现实和了解世界的重要中介,但却也因此容易忽视人们对于新闻业的认知和想象同样依赖于其他大众文化形式的中介。传统的新闻业建基于理性主义范式之上,认为新闻业应当提供客观信息和理性讨论,而与情感和娱乐划清界限(Pantti, 2010)。这隐含了一种启蒙式的假设,即认为公众应当按照经典民主理论来构想新闻业,那些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夸大或扭曲了记者的形象,令公众目眩神驰,干扰他们对于新闻业的理性思考。然而理性主导的公共话语范式近年来日益受到“情感转向”思潮的挑战。McGuigan(2005)提出,文学、影视等大众文化构成了以审美和情感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文化公共领域”,与正襟危坐讨论问题的政治公共领域相互补充。相比于教科书中对新闻业规范职能的道德说教,大众文化将种种理性思考和抽象论述转译成人格化和具象化的形式加以呈现,召唤起公众对于新闻业的共情式理解。人们对于新闻业所持有的信任、依赖、激赏、厌倦、怨恨、漠然等种种复杂态度,并非全然出于对新闻角色功能和职业理念的理性思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众文化所塑造(Stone, 1990)。
新闻业与法律业都是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职业团体,新闻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也共享着职业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路径和理论资源。法律与文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法律与电影研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子领域,关注文艺作品中体现的法律现象和对法律的想象(Manderson, Durham, Carodine et al., 2011),以及这些作品可以与法律互为补充的道德教化功能(努斯鲍姆,2009)。法律文化研究的奠基学者Friedman(1975)对法律文化做出关键性的理论区分,指出律师、法官、法学家等从业者对于法律实践的态度构成了内部(internal)法律文化,公众对法律的想象则构成外部(external)法律文化。Greenfield(2001:4-11)进一步提出,大众文化是外部法律文化建构的重要场所。
我们可以做出类似的区分,将内部新闻文化定义为新闻从业者社群内部共享的信念和态度以及表征这些信念和态度的象征体系,而外部新闻文化则是社会公众和其他专业社群对于新闻业的态度和想象,既包括公众对于新闻业的信任程度、接触水平、消费习惯等,同时也包括其他社会行动者对新闻实践的表征和评价。如果说内部新闻文化是泽利泽所说的“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那么外部新闻文化则可以表述为“the culture about journalism”,即关于新闻业的文化。外部新闻文化构成了新闻业赖以存续的文化背景,或如Alexander(2016)和Ostertag(2016)所说,构成了新闻实践的“文化结构”(cultural structure of journalism),塑造着记者的日常实践、职业道德和价值判断,并为新闻实践提供了道德语境。
但对新闻文化的内外二分还不足以揭示“中介化”机制在创造和传播公共新闻想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主张对外部新闻文化进一步区分,提出阐释新闻意义的三元主体:新闻职业社群、大众文化以及公众。如下图所示:
上述三元主体之中,新闻职业社群是新闻实践的主体和规范性新闻理想的承担者,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职业意义的话语建构是全部新闻意义阐释活动的基础,也是自泽利泽以来的文化取向新闻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公众对于新闻业的认知与想象是新闻实践正当性的重要来源,其意义在社交媒体时代日益显现,新闻从业者只有在公众对于新闻业的规范性想象之内行事,才能维系自身的职业文化权威。卡尔森(Carlson,2017)提出的新闻权威关系模型将公众纳入理论范畴,视之为阐释新闻业意义的能动主体,但未能充分解释公众认知和想象新闻业的机制。Alexander(2016)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存在着关于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同时规范着新闻从业者的实践和公众对新闻业的期待,但他并未清晰地说明该文化结构由何种因素构成、被何种因素塑造。
本文引入大众文化对新闻业的表征维度,作为联结新闻职业社群和公众的纽带。新闻业和新闻记者经常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有些大众文化产品直接以表现和反思新闻业为主题,另一些作品则以记者为主体串联起戏剧化的叙事(McNair, 2009:232)。电影、电视、小说等虚构作品不受客观、真实等新闻规范性原则的束缚,而是更注重故事的反思性和审美意义(Ness, 1997:15)。相比于新闻从业者本人生产的职业话语,大众文化关于新闻业的表征较为浅表,但更具戏剧性,受众群体更加广阔(Korte, 2015:17-19),因此在涵育公众新闻想象中的作用也更加显著。大众文化的表征一方面塑造着关于新闻业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又镶嵌在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根据深层意识形态的需求而不断生产某种特定类型的新闻业表征。
三种意义阐释的主体既遵循不同的场域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彼此紧密交织,相互作用。大众文化表征是在新闻职业文化基础之上的阐发与映照,无法脱离由新闻业本身确立的实践常规和道德规范,但也会结合自身的场域逻辑对新闻职业话语进行改造,使之契合通俗叙事所需的表现张力。大众文化生产者对新闻业的表征提供了另类的文化表达空间,使得不同社会团体可以在其中协商对于新闻价值观的判断(Ness, 1997:17)。这种协商空间有意无意间挑战了新闻职业社群对职业意义解释权的垄断,有时会激起新闻业的回应,要求大众文化描绘更加真实和正面的新闻业形象(Enhrich, 2010:3;张洋, 2019)。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对记者的表征会反作用于新闻场域,记者对于描绘自身职业的虚构作品非常关注,并且会参照虚构作品中的道德叙事来反思自身的职业实践(Korte, 2015:16, 31)。
大众文化生产者关于新闻业的表征为公众提供了认知新闻业所需的知识来源和参照语境,但大众文化产品并不能精准地框定公众对新闻业意义的解读,受众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文本中的价值观进行协商(张洋,2019),最终形成关于新闻业的公共阐释。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从业者与公众的交流变得更加直接、即时和日常化,公众认知与想象新闻业的渠道也变得更加多元、开放。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将新闻职业社群、大众文化与公众作为新闻业意义阐释的三元主体,旨在将中介化的新闻想象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填补新闻阐释社群和新闻权威研究的理论盲点,而非提出一种封闭性的理论框架,将其他社会行动者排除在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公共教育、人际传播等多种勾连公众与新闻职业社群的认知机制,围绕新闻业的意义展开协商,并随着不同的时空环境而流动变化。多元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构筑成更具包容性的新闻阐释社群,通过话语协作共同建构新闻业在公共生活中的职业边界、文化权威和道德想象。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广泛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理论演绎将大众文化表征纳入新闻研究的理论视野,旨在引入一种新的视角来反思新闻文化的建构。通过对阐释社群的理论溯源,本文指出新闻业的文化意义并不仅仅取决于职业社群的阐释,更取决于围绕新闻业的公共阐释。在大众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众对于新闻业的想象不仅依赖于自身直接的新闻接触经验,同时越来越多地依靠小说、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大众文化形式的中介,关于新闻业的知识和想象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得以跨越时空限制,在不同社会成员间形成秩序化的共享,筑成了公共阐释的基础。
因此,研究者需要对大众文化中的新闻业形象进行更具理论想象力的考察,批判性地考察这些表征构成了怎样的规范性话语,试图为新闻业赋予怎样的理想职能,又如何对新闻业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进行褒贬,而这些话语是否有助于人们反思新闻业与民主政治或社群整合的关系。同时更要引入受众分析的视角,通过影评、书评、留言、讨论等多种类型的衍生话语,考察受众在阅读或观看通俗文本后究竟对新闻业产生了怎样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否会生成关于新闻业的新型想象,这种外部的想象是否会注入新闻业的职业文化之中,为新闻业的变革提供道德驱力。
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追问,大众文化所表征的新闻业与记者形象,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言说间产生何种张力,这种张力如何影响着公众对于新闻业意义的阐释?从跨媒介叙事的角度来看,小说、戏剧、影视、综艺等不同中介形式,其文本逻辑和社会逻辑如何影响着新闻业形象的表征,进而生成不同类型的新闻想象?大众文化的形式和技术在数字化时代迅速革新,又会如何影响着新闻业的公共表征?而新闻想象中介化的过程,又是如何被地方性的社会文化结构所塑造,表达地方性的情感体验的?
在好莱坞占据全球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考察大众文化中新闻学表征的研究都局限于美国经验,比较研究的视角显得尤为稀缺和可贵。曾有法律文化学者对比法国与美国电视剧中的律师形象,发现法国电视剧中此类题材数量较少,对正义的集体表征也不同于美国(Villez, 2009)。英国学者Lansdale(2016)则研究了20世纪英国作家撰写的150多篇关于新闻业的文学作品,发现英国作家比美国同行对记者的描述更加负面,多将记者描绘成狂人、凶手和脆弱的人。那么在新闻实践情境迥异的非西方国家,大众文化又对记者寄予了怎样的想象,这些想象背后体现的新闻价值观和记者角色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的延伸,亦或是挑战这种垄断性观念的正当性?
相比于刻画新闻业的电影、小说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现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总体上没有将新闻业作为重要的表现主题。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新闻业起步较晚,在实践中受到的限制因素较多,在公共生活中相对不够活跃,因此较少受到大众文化的青睐;其次则是中国大众文化生产领域本身的单薄。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新闻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以新闻业为主题或以记者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大量涌现。据统计,2000-2015年之间有40余部中国影视作品以记者为主角(周琪,2016)。近两年的热门国产电影如《红海行动》、《送我上青云》等重点刻画了女性记者的成长经历,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则将新闻伦理作为主要的表达主题。在文学领域仅以笔者目力所及,2000年后至少有数十部长篇小说以记者为主角,刻画新闻业的生存样态。
关于记者和新闻业的表征在中国大众文化中正在迅速浮现,记者作为责任与欲望的主体开始勇敢发声,又与现代性的都市想象如影随形。这些对记者和新闻业的表征同时也在不断介入人们对于新闻业的认知与想象,刻写下当代中国新闻业的传神写照。大众文化中的记者表征为快速变迁的新闻业提供了一帧帧剪影,而将这些剪影拼接起来,便成为记录新闻业演变轨迹的长镜头。通过对不同时代大众文化中的新闻业表征进行谱系学的考察,可以从中勾勒出人们对于记者的想象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些变迁又如何折射出社会变迁和新闻业本身的变迁,从而为当代新闻史研究另辟一条蹊径。
最后,数字革命的浪潮使全球新闻业都深陷危机,新闻专业权威在自媒体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专业新闻机构面临财务和信誉的双重危机而步履蹒跚。在“新闻业是否/何时会消失”的致命诘问下,少数记者对于新闻理想的呼吁越发显得曲高和寡。杰弗里·亚历山大(2015)认为,不应仅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理解新闻业危机,更应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或维系了新闻业的文化承诺。作为新闻业文化承诺的重要建构者,大众文化如何对新闻业的危机时刻作出回应?如何建构新闻业危机的叙事?如何表征危机下的新闻从业者?这些表征能否重新激活人们对于专业新闻业的期待和想象?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研究者或许能从中发现反思新闻业危机的别样法门。■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8)。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8),25-48。
陈楚洁(2018)。意义、新闻权威与文化结构——新闻业研究的文化-社会路径。《新闻记者》,(8),48-63。
丁方舟(2019)。元新闻话语与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卡尔森《元新闻话语与新闻业的意义:定义管理、边界工作与正当化》译评。《新闻记者》,(8),74-81。
杰弗里·亚历山大(2015)。重思新闻业危机:文化的力量——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的文化社会学反思(周红丰,吴晓平译)。《新闻记者》,(3),4-12。
陆晔,周睿鸣(2016)。“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7),24-46。
玛莎·努斯鲍姆(2010)。《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忠党(2014)。“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58-167。
约翰·B·汤普森(2005)。《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张洋(2019)。神话叙事,协商解读与新闻权威的多元建构:基于电影《华盛顿邮报》(The Post)的分析。《新闻记者》,(7),85-96。
赵毅衡(2015)。意义标准:探索社群与解释社群。《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琪(2016)。新时期国产影视作品中的记者形象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
Brennen, B. (1993). Newsworkers in Fiction: Raymond Williams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7(1)95-107.
Alexander, J. C.Breese, E. B.& Luengo, M. (Eds.). (2016).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isA. (1976). Stop the presses! The newspaperman in American films. AS Barnes; London: T. Yoseloff.
BogaertsJ.& Carpentier, N. (2013).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to journalism: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a trustworthy identity. In Rethinking Journalism (pp. 72-84). Routledge.
BrantsK. (2013). Trustcynicism, and responsiveness: the uneasy situation of journalism in democracy. In Rethinking Journalism (pp. 27-39). Routledge.
Carlson, M. (2017).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at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ddingtonM. (2019). Aggregating the news: Secondhand knowledge and the erosion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10(3)373-391.
Ehrlich, M. C. (2010). Journalism in the Mov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Ehrlich, M. C.& Saltzman, J. (2015). Heroes and scoundrels: The image of the journalist in popular cul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ishS. (2004).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In Rivkin, J.& Ryan, M. (Eds.).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John Wiley & Sons.
FriedmanL. M. (1975).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Ghiglione, L.& Saltzman, J. (2005). Fact or Fiction: Hollywood looks at the News. Image of the Journalist in Popular Culture.
GoodH. (1986). The image of war correspondents in Anglo-American ficti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GoodH. (2007). Journalism ethics goes to the movi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GreenfieldS. (2001). Film & the Law. Routledge-Cavendish.
HaasT.& SteinerL. (2006). Public journalism: a reply to critics. Journalism, 7(2)238-254.
HallinD. C. (1992). The passing of the “high modernism” of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3)14-25.
Korte, B. (2015). Represented Reporters: Images of War Correspondents in Memoirs and Fiction. transcript Verlag.
Langman, L. (2009). The media in the movies: A catalog of american journalism films1900-1996. McFarland.
LonsdaleS. (2016). The journalist in British fiction and film: Guarding the guardians from 1900 to the present. Bloomsbury Publishing.
Lutes, J. M. (2006). Front Page Girls: Women Journalists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Fiction1880-193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nderson, D.Durham, A. L.Carodine, M. D. et al. (2011). Imagining legality: Where law meets popular cultur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McGuiganJ. (2005).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8(4)427-443.
McNairB. (2009). Journalists in fil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NessR. (1997). From headline hunter to superman: a journalism filmography. Scarecrow Press.
OstertagS. (2016). Expressions of right and wrong: The emergence of a cultural structure of journalism.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264-281.
PanttiM. (2010). The value of emotion: An examination of television journalists’ notions on emotion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5(2)168-181.
RyfeD. M. (2016).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John Wiley & Sons.
SaltzmanJ. (2002). Frank Capra and the Image of Journalists in American Film” From the beginning[he] had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newspapers”. USA TODAY-NEW YORK-13154-57.
SaltzmanJ. (2003). Sob sisters: the image of the female journalist in popular culture. The Image of the Journalist in Popular Culture (IJPC). Recuperado de: http://www. ijpc. org/page/sobsmaster. htm.
SaltzmanJ. (2005). Analyzing the images of the journalist in popular culture: A unique method of studying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its journalists and the news media.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chudsonM. (1989).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culture & society11(3)263-282.
Silverstone, R. (2005). The sociology of med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ogy188-207.
Stone, G.& LeeJ. (1990). Portrayal of journalists on prime time televi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67(4)697-707.
VillezB. (2009). Television and the legal system. Routledge.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0(3)219-237.
Zelizer, B. (2005). “The Culture of Journalism”.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 (4th ed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Bloomsbury Academic)2005198-214.
张洋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受“201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留金发[2018]3101,项目编号:20180627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