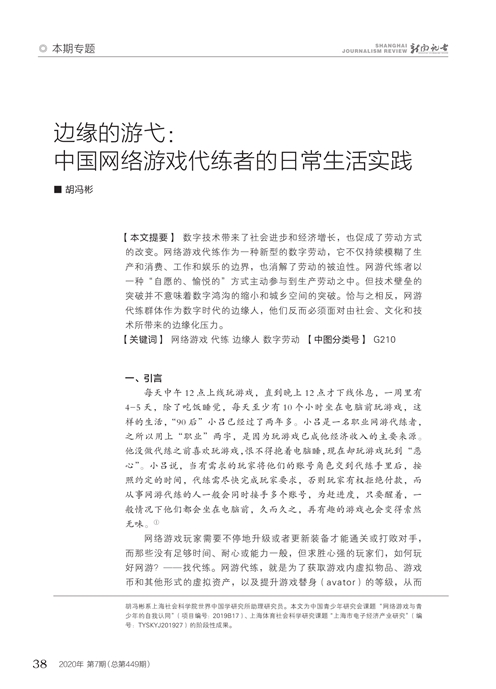边缘的游弋:中国网络游戏代练者的日常生活实践
■胡冯彬
【本文提要】数字技术带来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也促成了劳动方式的改变。网络游戏代练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劳动,它不仅持续模糊了生产和消费、工作和娱乐的边界,也消解了劳动的被迫性。网游代练者以一种“自愿的、愉悦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生产劳动之中。但技术壁垒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缩小和城乡空间的突破。恰与之相反,网游代练群体作为数字时代的边缘人,他们反而必须面对由社会、文化和技术所带来的边缘化压力。
【关键词】网络游戏 代练 边缘人 数字劳动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每天中午12点上线玩游戏,直到晚上12点才下线休息,一周里有4-5天,除了吃饭睡觉,每天至少有10个小时坐在电脑前玩游戏,这样的生活,“90后”小吕已经过了两年多。小吕是一名职业网游代练者,之所以用上“职业”两字,是因为玩游戏已成他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他没做代练之前喜欢玩游戏,恨不得抱着电脑睡,现在却玩游戏玩到“恶心”。小吕说,当有需求的玩家将他们的账号角色交到代练手里后,按照约定的时间,代练需尽快完成玩家要求,否则玩家有权拒绝付款,而从事网游代练的人一般会同时接手多个账号,为赶进度,只要醒着,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坐在电脑前,久而久之,再有趣的游戏也会变得索然无味。①
网络游戏玩家需要不停地升级或者更新装备才能通关或打败对手,而那些没有足够时间、耐心或能力一般,但求胜心强的玩家们,如何玩好网游?——找代练。网游代练,就是为了获取游戏内虚拟物品、游戏币和其他形式的虚拟资产,以及提升游戏替身(avator)的等级,从而进行的有目的性的代玩游戏行为。网游代练在21世纪初期伴随着网络游戏,尤其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的风靡而出现。网游代练者则是代替玩家完成上述游戏任务的操作者,他们需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玩家指定的任务才能获取酬金,与玩家构成了一种雇佣关系。在网游代练发展的早期,像小吕这样的个体代练者总是在家中或网吧从事网游代练。迅速发展的互联网络技术及计算机性能,推动了网络游戏内容或画面的升级,网络游戏内虚拟物品不菲的价值以及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等虚拟经济的兴起,推动了网游代练的全球化和产业化快速发展。散兵游勇式的个体代练者已无法满足代练行业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产业化的网游代练工作室。当前网游代练工作室犹如网吧,提供场所、设备等以供代练员有组织、有规模地代练。根据代练人数规模,代练工作室大致可分为个人工作坊、三至五人的小型工作室、一二十人的中型工作室,以及五六十人及以上的大型工作室和外挂工作室。
网络游戏代练既不是中国独有,也并非产生于中国(Dibbell, 2006:15),但是中国游戏代练产业“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下的游戏产业和游戏者间的互动”,依靠“以玩家为核心的业务和服务填补了游戏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空隙,出现了一个模糊了消费与生产、合法与非法界限的灰色地带”(Zhang & Fung, 2014:39)。近年来,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国家对游戏产业的大力支持,以及廉价的人力劳动成本等,这些都促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就形成了规模庞大、面向全球的代练产业链,一举成为全球网络游戏代练的中心。
那么,作为代练产业链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网游代练者,他们是怎样的群体?与其他数字劳动者有何区别?处于灰色地带的他们要面对怎样的生存压力?
二、研究方法
鉴于中国网络游戏发展、代练分布及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本文选择了上海、青岛、郑州、金华和昆山五座城市作为样本来源城市。它们代表着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同时也是游戏代练较为活跃的地域。代练者主要活跃在各类游戏网站、论坛及社交媒体,因此本研究通过58同城网、微信、淘宝、5173网、智联招聘、代练通等渠道,寻找到各具特色的游戏代练工作室,在5座城市共访谈了20家代练工作室,总计61名代练群体成员(表1 表1见本期第39页)。本文的研究对象——代练群体——由工作室组织者和代练者构成。②近年来手机游戏因游戏操作的便捷及无须场地要求等原因,玩家群体迅速增多,逐步抢占了原本网络游戏的市场占有率及玩家时间,对网游代练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往低成本运营的小型代练工作室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当前的网游代练多是以规模更大的大中型工作室为主。
本研究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为主,辅以焦点小组的方式。在当地进行多天的接触观察时,访谈虽因代练者们极度忙碌而断断续续,因此无法一次性完成,但每个受访者的访谈时间都保证在1.5小时左右。当受访者兴致较高或条件允许时,4-5名代练者即以小组形式展开话题的交流。
三、研究发现
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游戏代练者都来自农村或乡镇,他们主要由20-29岁之间的青年构成(偶有未成年者),这一年龄层的人数约占整个群体的八成,其学历多是初中或高中。这与“我国网民以中等教育水平的群体为主。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38.1%和23.8%。20-29岁网民规模占比最高,达网民整体的24.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19)的中国网民现状吻合。
代练者年龄普遍较小,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数字原住民,即与数字技术共同成长的第一代。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建成融合、泛在、安全、绿色的宽带网络环境,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即便在农村,他们也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电脑、手机以及各种电子设备所包围。数字技术是他们生活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而他们的父辈,多数正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一批外出务工者。虽然代练者们选择了一条看似跟父辈类似的“外出务工”的道路,但是“数字原住民的出生、成长和社会化都是在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完成的。数字时代传播方式的革新改变了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闫岩,2015:5-6)。他们与父辈的价值观大相径庭,代练者们没有父辈对于城市世界的那番憧憬和追求,也没有依靠奋斗来改变人生的梦想。
(一)边缘冲突:代练者多为农村数字原住民
网游代练被视为一种可剥削的劳动行为,使游戏者受雇为“愉快的”游戏劳工,为游戏商产出价值(Kücklich, 2005)。游戏劳工是数字时代数字劳动的一种典型体现,他们沉迷游戏的同时,又免费为游戏商吸引用户,改善甚至创造了游戏内容。网游代练被认为不仅是一种娱乐行为,而且是以生产为直接目的的雇佣劳动,只不过这样的劳动关系及行为被数字平台所掩盖。更有学者认为网游代练是后现代的“帝国”式管理,它体现了游戏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转移,欧美资本家对游戏世界的利益封锁被突破,一直占据利益支配地位的欧美发达国家面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挑战(Dyer-Witheford & de Peuter, 2009:327-330)。
而代练者的身份及特征证实了“自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特别是乡村的劳动力被卷入工业生产的领域,同时也是机器不断替代劳动者的过程”(吕新雨,2019:序言)。产业的升级换代,也意味着劳动在不断转型。依靠数字媒介的新一代工人面临着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即由数字劳动所衍生的诸如非正规的就业、弹性工作时间、计件工资形态、社会保障体系缺陷等新的社会化现象。
多数网游代练者处于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的边界,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数字劳动所带来的新问题,而且还有类似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笔下“边缘人”(Marginal Man)的困境。农村对于他们似乎有点“陌生”,城市又那么“遥远”。当年帕克研究美国城市移民时,发现美国的外来移民既未完全融合到新的社会或文化中,又远离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原有的或者新的社会中,他们都成为了边缘人(Park, 1928:888,893)。帕克的边缘人研究源于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而所谓的“陌生人”,“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是潜在的流浪者”,“陌生人是群体本身的一个要素……它的内在的和作为环节的地位同时包含着一种外在和对立……进行叛逆的和引起疏离作用的因素在这里构成相互结合在一起和发挥作用的统一体的一种形式”(齐美尔,2002:341-342)。
无论“陌生人”还是“边缘人”,他们与当地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上的二重性:物理空间的接近,社会空间的疏远。他们身处当地人的群体之中,物理上的接近却无法改变他们不能融入当地人的事实。代练者如同他们的父辈,仍是城市的过客,无常和游离构成了他们游弋于边缘的特征。且更重要的是,身为数字原住民的他们,不得不面对“传播技术过渡时代的必然特征——代际冲突、文化振荡、观念更迭”(闫岩,2015:7)。这些冲突加速了代练者在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的边缘化。
跟数字移民的父辈不同的是,身处农村的“90后”数字原住民依靠互联网络观看外在世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意图是以技术下乡打破城乡的部分壁垒,以期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消除信息壁垒、化解二元结构等诸多矛盾。但是技术发展的两重性在促进农村信息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加大了原有的鸿沟。年轻一代既是受益者,也易成为受害者。新媒介技术让他们具有父辈所没有的硬件设备和技术信息环境来认知与接触外在世界,但这也导致他们更易遭受技术二重性所伴随的沉迷、困扰、失控,以及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疏远等后果。
“我没有做过农活,也不会做。想回家么,不想”。③
“家里好无聊,都没有事做。在家也是跟朋友在网吧玩游戏”。④
“在哪都一样。我都没有出去(玩)过。这里(上海)跟河南没有什么区别吧。反正我每天白天都是在打(游戏),都没出去玩过”。⑤
帕克当年在研究移民群体时,发现他们像文化混血人,生活在两种不同人群之间,这些移民既不愿和过去及传统决裂,又无法被新的环境所接受。于是他们不得不站在两种文化和社会的边缘,成为“边缘人”。脱离过去的群体由于无法渗入或交融于不同文化中,这就使得他们不能融入新的环境。由此可见,这些年轻的农村数字原住民经历着类似于移民群体“边缘人”的心理矛盾。
(二)技术下乡:数字鸿沟的消弭与扩大
代练者,作为网游代练产业链最为核心的一环,他们的能力以及态度决定着代练工作室的口碑甚至成败。在外人眼中,网游代练者应具备不亚于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的操作水平。实则不然,代练者不仅没有职业玩家的能力和技巧,反倒多是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游戏少年。
做这个行业吧,很大一拨人,都是知识层次很低的年轻人,主要是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这些小伙子,他们无所事事。像这样的人,初中高中没有毕业,说难听点,逻辑思维能力、辨识能力不是很强,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应该鼓励。他只能出卖劳动力,很累很苦的情况下,能通过自己的时间做出来,跟在工厂做出来没有什么区别。⑥
“年龄小”、“喜欢打游戏”、“学历低”、“没有责任心”,这是工作室组织者眼中代练者最常见的形象。那么代练者为什么会选择网游代练这一“与众不同”的灰色行业呢?
影响新媒介技术在青少年群体中间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技术成本、家庭财力,以及家长对技术的认知和控制(闫岩,2015:70)。当新技术完成了观念层面的劝服、成本壁垒的突破或技术的普及,它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扩散就会迅速实现。“宽带中国”、“宽带村通”等农村信息基础建设工程突破了成本的壁垒,也迅速普及了网络技术。
中国自2010年推出《关于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的意见》,强调优先采用光纤宽带方式加速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光纤到村。2013年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进一步推进战略引导和系统部署,加大光纤到户、宽带进农村。以推进“宽带中国”、“无线城市”、“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宽带村通”等工程建设为契机,农村加快基础通信设施、光纤宽带网和移动通信网、广电有线网络建设,构建有线无线相结合、覆盖城乡的信息网络体系,得益于此,农村地区网民规模一直是我国网民规模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最先受益于新兴传播技术的通常是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的年轻人群体。
一旦具备了硬件设施,并且习得了使用新媒体的技能,技术世界中的动机、行为、能力等便呈现出脱离了地域和地区限制的新图景。虽然它们在青少年群体中依旧会有分层和分化,但相比城市,乡村地区的青少年因无过多的课外活动——如补习班、特长班等——反而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频繁使用新媒体。不过,新媒介技术工具性和知识性的价值需要经由一定的指引挖掘,否则他们虽然有更多的时间使用新媒体,但却只是应用于网络娱乐和社交。这也反映出青少年对新媒体工具的使用还是停留在消费性和休闲性的层面(闫岩,2015:255,139)。这种情况与农村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中所描述的网络使用图景一致,“游戏类应用在农村地区增速持续稳定,网络的完善、硬件设施的提升大大增加了农村网民网上娱乐的频率,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保持平稳增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29)。
(你现在应该正在读初三,为什么就出来做代练了?)“反正我在县里读书,也天天逃课在网吧玩游戏。现在玩游戏还能赚钱。我是书读不出来”。被问及第一次去网吧玩游戏的经历,17岁的小陈淡定地回忆道:“好久啦。小学吧,刚有网吧的时候,就跟同学一起去了。一下子就玩上了。” ⑦
“玩网游好早了吧,都快十多年了。在我小学的时候,去网吧玩的。上瘾了,逃课翻墙。家里人也不在,自己没日没夜地在网吧玩”。⑧
多数代练者坦言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是源于中小学期间去网吧。例如,代练员顾严甚至“自从跟着同学去过网吧两次,上手玩游戏之后,初中最后一年,差不多就是在网吧度过的”。⑨代练者最初使用网络时,因缺乏有效的引导,其用途主要是看电影和打游戏,又因年龄小、自控力不足以及父辈外出务工的原因,使得他们更容易沉迷于网络和网络游戏。喜欢玩游戏、不愿意吃苦、学习成绩较差、不习惯被管束的他们,高中毕业后面临的选择并不多,加之代练没有门槛,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代练当作了就业的最优选项。
(三)数字劳动:多重边界的消失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的升级换代也意味着劳动不断转型。全球信息供应链在产业升级换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也在不断网络化,数字劳动在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数字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性活动,它使得生产与消费一体化,又令社交与组成它的社会关系全都具备生产性,因而出现了一种自主的生产性协同,并使得身处其中的“工人”在生产中成为积极的与交流的主体,将个人与主体性融入价值生产的过程之中(邓剑,2017:183)。“工人”通常是怀着愉快的心情,自愿地进行数字劳动,因此提升了产业的经济和利用价值。网游代练者自诩这份工作既能玩又能赚钱,恰恰佐证了网游代练的本质正是数字劳动,通过游戏机制、代练产业链将代练者变成了“积极的与交流的主体”,在生产玩家乐趣或体验的同时,也在为游戏商创造价值。
“做过(其他工作),(代练)算是轻松吧。又可以玩游戏又可以赚钱”。(代练有什么让你不满意或厌烦的部分?)“嘿嘿,没有呀”。⑩
(代练怎么样?)“还可以。我觉得我很喜欢”。(代练哪部分让你满意喜欢?)“就是游戏体验度,能玩能工作”。[11]学界将网游代练这类数字劳动称为“玩工”(playbour),它消解了在空间上暂时出现的工作与游戏的区别,催生了“创造价值的娱乐互动、多产的消费行为和负担劳动力的游戏”(Fuchs, 2014:270)。“玩工”带来经济价值和经济利润,然而受益者并非“劳动者”。
网游代练这一数字劳动形式,彻底打破了“工作”和“娱乐”、“生产”和“消费”、“服务交付”和“服务使用”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将劳动者的被迫劳动转变成一种自愿、愉快的状态。信息和通信技术在这种模糊化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工作不要求太多的专业技能,劳动过程重复,代练者无需也无法学到有用的技能。“其实代练挺好做的,只要他们会玩游戏,就能做了”。[12]网游代练行业中有趣的现象是,相比年长的代练组织者,代练者年轻,学历更低,但却从事过很多其他工种——譬如工厂流水线工人、KTV保安、超市售货员、停车场保安等。在交流中,他们不约而同都认为代练是最为愉悦、最自由舒适,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工作。这种认同正是来自于工作和娱乐两者边界的模糊。由于他们喜欢玩游戏,甚至沉迷游戏,“边玩边赚钱”就成为他们认同代练的最大理由。“玩”大于“劳动”,“消费”遮蔽了“生产”,“自愿”胜出“被迫”,他们是“怀着愉快的心情,自愿地参与”其中(Tiziana,Terranova, 2000:39)。
“不累啊,挺开心的。这里工作环境也蛮好的”。[13]“就是跟朋友们一起玩啊,还有就是自己还能玩游戏”。[14]“比较起来,这个工作是最轻松的。每天十几个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15]“最喜欢代练呀。代练可以玩啊。关键是我们都是对游戏比较喜欢的”。[16]“可以打游戏还可以赚钱。即便我不做这个工作,也是在打这个游戏。这样一举两得,多好啊”。[17]代练工作因游戏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经常以延长工作时间甚至通宵的方式来按时完成任务。连续十几甚至二十小时的工作强度,他们都只是觉得累,但却不痛苦,更不会因此离职。在过去数百年间,雇主和工人争夺的核心问题一直是时间。双方就工作日、工作周的长度和节假日问题展开大规模的长期斗争,围绕着工作速度爆发着没完没了的矛盾冲突(乌苏拉·胡斯,2011:122)。这类矛盾冲突在代练组织者和代练员间却很少见。组织者不会像传统工厂那样扣压身份证或薪资,以防工人们离开。这是因为,代练者找工作的着眼点并非报酬,而是代练哪款游戏。代练也不似其他工作那样会签署合规的合约。工作室不拖欠工资,代练者领到薪水之后便不辞而别,待身无分文了又再次出现。这种自由散漫的做法,往往让组织者感到头疼和无奈。
“现在我是不会再开高工资的。上次有个一个月做得好,赚了一万六,拿到钱人就走了,说去玩几天,就再也没见到他。**太没责任感了。一点都没有工作的概念”。[18]游戏市场全球化和代练任务的特殊性使得代练者基本保持着每天至少工作十几小时,每月只休息两天的工作强度。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地面对一款游戏,爱好变成了工作,再有趣的游戏也会渐渐无味起来,但是代练者似乎不以为然。在他们眼中,父辈所从事的传统体力工作劳动时间少,但“无聊”、“累”、“没劲”,更易让他们有疲惫感。相比之下,代练就是累并快乐着。
“原来的那(工厂)太累了,做了一个月就不行了”。(每天打十几小时,一个月没休息,不累?)“嗯,肯定有点累的,能接受的那种”。[19]“做过其他工作啊,一般一两个月,最长的三个月。还是最喜欢这个(代练)。轻松啊。我喜欢”。[20]“那个(保安工作)太无聊了,还是这里好。有空调,也不累,每天可以坐着”。[21]代练者对工作的认知不同于父辈,也没有父辈用工作来改变命运的迫切感。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代际间工作形态的差异——工作和娱乐、生产和消费的边界变得模糊。边界消融对应了马克思所形容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转化为“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过程。数字劳动体现了资本如何将个人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等裹挟入工作之中,它模糊了多重边界,也促使代练者不得不游弋于这些边界之间。
(四)污名化:代练群体内的边缘化
边缘人存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环境或社会之中,但凡社会文化的界线被跨越的地方,就会产生边缘状态。游戏者,在我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常是被污名化的对象,常常对应着“无所事事”、“无良少年”等刻板印象。
“我大学时带我弟弟去网吧,一老头,七八十岁了突然冒出一句,‘两个不学好的’。我很莫名,我就是去趟网吧,我咋就不学好了,就是这样一种莫名的感觉”。[22]——上海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陈对于十年前的那一幕始终无法忘怀。他认为社会对于游戏的看法、态度虽有所好转,但仍是片面否定,他认为不应污名化游戏行业以及从事者。但当他谈及所雇佣的代练者时,却不由自主地表达了类似的负面态度:“我觉得这个群体(代练者)存在隐患,很可能包含着社会问题。如果有一天,工作室不能做了,这些人怎么办?会不会成为社会的炸弹?我开始不管他(求职者)适合不适合做代练,会让他住两天,然后让他出去找工作或怎样。后来我改变了,因为我丢了很多东西,就开始排斥了。这样的人他们最终会去哪呢,还是某个工作室?但是他们心理有问题,感觉早晚会出问题。” [23]“要不他们这些人怎么办,社会也不会接纳他们的”。[24]“这些代练真的是没有责任,给他们一个月1万多,这算是非常非常高的报酬,即便在外企,对于他们这些没有学历的来说,也很不错。他们倒好,说出去玩,就拿着钱出去玩了。什么也不管了。他们这样去社会上做其他工作怎么办。没有责任心”。[25]——老唐对不辞而别的员工耿耿于怀,在访谈中多次提及此事。因游戏的污名化而深受社会偏见歧视的网游代练组织者,却将这种污名化施加于同一行业的代练者。
长时间的代练工作以及场地的固定化,使得代练者被进一步原子化,自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区隔荡然无存。通常工作室会负责代练员的住宿,并解决一日三餐。一般而言,代练者居住环境犹如学生寝室,四至八人一间上下铺。个别工作室因房间略大,便安置了更多的上下铺以节约成本。空间边界的消失,导致传统的组织和交流的手段不复存在。代练者被隔离在工作室这样的单一环境中,难以融入社会或非工作环境,也没有父辈或老乡会来捍卫利益、争取权益。个体的原子化使得组织者集中化的管理更为有效,网络技术和游戏系统的完善,以及上线时间、任务完成量等数据的使用,使得代练者被时刻监控着。他们的无序、不可信任的状态加深了来自外部的污名和群体内部等级式的污名化以及被组织者的监控,代练者因此始终处于边缘群体中更为边缘的位置。
四、结语
20世纪初,因城市化进程而来的人口物理空间迁移,导致了“边缘人”的出现。边缘人因空间实体的变化,处于一种不同群体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夹缝之中,受到双重规范的约束而处于游弋状态。数字技术带来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也促成劳动方式的改变。技术的本意往往是向善,但是技术壁垒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缩小,也未必能打破既有的阶层和城乡空间的限制。因技术而起的数字劳动消解了传统劳动的生产和消费、工作和娱乐、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边界,模糊了劳动的强迫性。同样因为技术,作为数字时代“边缘人”的代练员群体承受着因社会、文化和技术所带来的种种边缘化的压力。■
注释:
①http://games.ifeng.com/a/20160408/41591844_0.shtml.
②工作室组织者即老板,由他们出资负责管理,多数也身兼代练者的身份。代练者是游戏代练工作室最核心的群体,也是游戏代练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本文访谈对象中,因网游代练工作时间长以及强度大,所访谈到的组织者和代练者皆为男性,受访工作室有个别女性,皆为工作室游戏平台的客服,因语言能力及学历较好,多负责工作室的运营及对外接洽。游戏代练行业除了游戏代练工作室之外,还有部分大学生兼职代练。他们代练的形式更为随意,根据各自上课时间安排,以及月花销决定是否接活和任务的多少。鉴于大学生代练的非固定化、随机性,这些分散的大学生代练员不在本文研究对象之列。
③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王,25岁,高中毕业,2016年9月15日。
④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马,21岁,高中毕业,2015年8月31日。
⑤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张,26岁,高中毕业,2015年6月15日。
⑥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王,2015年6月4日。
⑦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陈,17岁,初中在读,2015年8月31日。
⑧郑州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向,22岁,高中毕业,2015年7月9日。
⑨郑州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顾,28岁,高中毕业,2015年7月23日。
⑩青岛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左,22岁,高中毕业,2014年7月13日。
[11]郑州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开,26岁,高中毕业,2015年7月23日。
[12]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王,37岁,本科毕业,2016年7月16日。
[13]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山,20岁,高中毕业,2015年8月30日。
[14]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罗,21岁,高中毕业,2015年8月30日。
[15]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台,25岁,大专毕业,2015年5月30日。
[16]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刘,21岁,初中毕业,2016年8月11日。
[17]郑州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郑,19岁,高中毕业,2015年7月23日。
[18]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唐,34岁,本科毕业,2014年8月30日。
[19]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小刘,21岁,初中毕业,2016年2月16日。
[20]金山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老刘,39岁,高中毕业,2014年8月30日。
[21]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代练者老唐,34岁,本科毕业,2015年8月30日。
[22]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陈,33岁,本科毕业,2015年6月4日。
[23]上海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陈,33岁,本科毕业,2015年6月4日。
[24]青岛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庄,28岁,大专毕业,2014年7月14日。
[25]昆山游戏代练工作室组织者老唐,34岁,本科毕业,2017年1月26日。
参考文献:
邓剑(2017)。游戏劳动及其主体询唤:以《王者荣耀》为线索。《中语中文学》,(12):180。
蒋述卓(2005)。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文艺争鸣》,(3),33。
齐美尔(2002)。《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
潘毅(2011)。《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
乌苏拉·胡斯(2011)。《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闫岩(2015)。《数字原住民的聚合与分化:湖北青少年新媒体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杨建娟,吴飞(2012)。理解“生活在别处”的“边际人”——兼谈帕克的底层关怀意识。《新闻界》,(10),15-16。
吕新雨(2019)。《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2015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29。检索于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ncbg/201608/P020170907348967498375.pdf。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检索于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908/P020190830356787490958.pdf。
Christian Fuchs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NY: Routledge.
Lin Zhang & Anthony YH Fung (2014). Working as playing? Consumer laborguild and the secondary industry of online gaming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16(1)39.
Julian Kücklich (2005).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 Fibreculture Journal5. 搜索于http://five.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25-precarious-playbour-modders-and-the-digital-games-industry/.
Nick Dyer-Witheford &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bert E. Park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33(6)886-889.
Tiziana, Terranova (2000)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 63(18:2)39.
胡冯彬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课题“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的自我认同”(项目编号:2019B17)、上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上海市电子经济产业研究”(编号:TYSKYJ2019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