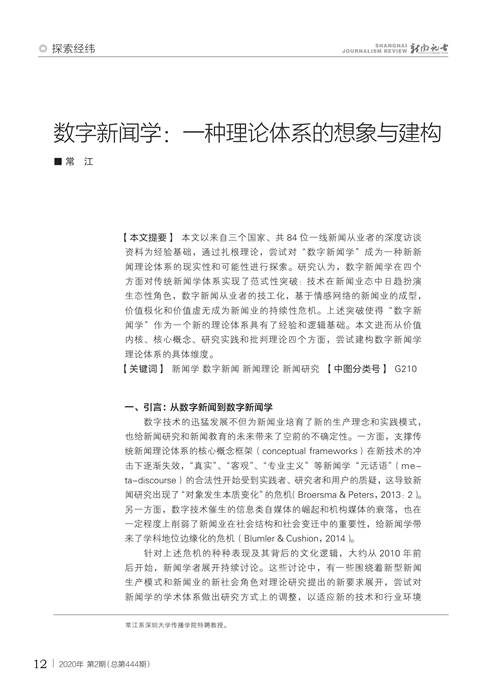数字新闻学:一种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
■常江
【本文提要】本文以来自三个国家、共84位一线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资料为经验基础,通过扎根理论,尝试对“数字新闻学”成为一种新新闻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进行探索。研究认为,数字新闻学在四个方面对传统新闻学体系实现了范式性突破:技术在新闻业态中日趋扮演生态性角色,数字新闻从业者的技工化,基于情感网络的新闻业的成型,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成为新闻业的持续性危机。上述突破使得“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具有了经验和逻辑基础。本文进而从价值内核、核心概念、研究实践和批判理论四个方面,尝试建构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具体维度。
【关键词】新闻学 数字新闻 新闻理论 新闻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从数字新闻到数字新闻学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为新闻业培育了新的生产理念和实践模式,也给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的未来带来了空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支撑传统新闻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s)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逐渐失效,“真实”、“客观”、“专业主义”等新闻学“元话语”(meta-discourse)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实践者、研究者和用户的质疑,这导致新闻研究出现了“对象发生本质变化”的危机(Broersma & Peters, 2013:2)。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催生的信息类自媒体的崛起和机构媒体的衰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闻业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给新闻学带来了学科地位边缘化的危机(Blumler & Cushion, 2014)。
针对上述危机的种种表现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大约从2010年前后开始,新闻学者展开持续讨论。这些讨论中,有一些围绕着新型新闻生产模式和新闻业的新社会角色对理论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展开,尝试对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做出研究方式上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技术和行业环境(Domingo et al.,2015;Lewis & Westlund,2015;Primo & Zago, 2015);有些则从新闻学学术发展的宏大脉络出发,认为数字技术给新闻研究的理论体系带来的影响超越简单的符号或工具层面,需要对新闻学进行“重新概念化”(Anderson, 2010),甚至尝试去界定新闻理论自规范(normative)、经验主义(empirical)、社会学(sociological)和全球比较(global-comparative)等主导范式之后出现的新范式(Steensen & Ahva, 2015)。数字新闻理论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在2015年专门出版了题为“数字时代的新闻学理论”(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特刊,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进行了归纳与聚合。
尽管上述两种数字新闻研究的理论化路径在性质上存在类似“改良”和“革命”的差异,但这无碍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数字化浪潮及其急速放大的技术驱动力在新闻生产和新闻业形态中的显著性,客观上令业已近半个世纪没有实质发展的新闻理论研究焕发了新的青春。在新闻学领域,或许从未如此密集地“诞生”新概念: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Anderson, 2016)、网络化新闻(networked journalism)(Russel, 2011)、环绕新闻(ambient journalism)(Hermida, 2010)……这些尝试为新闻学建立新概念框架的努力固然有相当一部分止步于对新的学科话语体系的“表达”,却也以一种近乎头脑风暴的方式,“迫使”新闻研究者从对新闻实践热点现象的追逐,转向对新闻学自身的理论范式和学科体系的反思。
受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新闻实践和新闻行业始终是易变的,但“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则必须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语境”的稳定性。在教育学家Gary Thomas(2007)看来,自洽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通常需要具备如下三个属性:(1)主要用于发现事实而非达成目标(后者通常属于“实践”);(2)通常由知识体系(body of knowledge)和阐释模型(explanatory models)构成;(3)以中性的方式协调不同价值体系的关系。这一针对理论体系而非具体理论本身的认知框架可以作为我们后续思考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假如我们认可数字技术环境下新闻研究路径的上述转变是范式性的,并呼唤一个新的学科体系的诞生,亦即,我们假设“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有可能指涉一个有别于那种基于特定类型社会机构共通专业实践的、奉客观主义为圭臬的传统新闻理论体系,那么,这种“新新闻学”包含哪些关于“新闻”和“新闻业”的新的事实?它的知识体系和阐释模型如何体现?它又是否具有协调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只有完全(或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数字新闻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二、研究设计:扎根理论
本文尝试采用具有扎根理论色彩的质化研究方法,通过对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新闻从业者的一手职业经验的解读,“自下而上”地归纳“数字新闻/数字新闻业”在日常新闻实践中的意义指涉,并据此判断建立在上述意指实践基础上、作为学科体系的“数字新闻学”的理论潜能和构成维度。
在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之间,针对不同的研究议题,本文作者对英国、美国、瑞士三个国家共84位一线新闻从业者进行了半结构或无结构的深度访谈。这些从业者分别来自17家新闻机构,其中既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BBC)、瑞士法语广播电视公司(RTS)等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老牌新闻机构,也包括ProPublica、Slate、美国在线等有代表性的数字新闻机构(表1 表1见本期第14页)。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一部分访谈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Skype以远程视频的方式完成的,还有一部分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书面采访。绝大部分访谈以英语完成,小部分访谈是通过法语的电子邮件通讯完成的。之所以选择在上述欧美国家展开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新闻业均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全球数字新闻生态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也因其传统的商营传媒体制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充分的空间去理解数字技术相对独立发挥作用的方式。
这些专项研究旨在帮助我们理解身处新闻业数字化变迁前沿地带的行动者对数字技术加诸新闻生产实践和新闻行业结构的影响的认知,以及(基于不同媒介的)新闻机构从业者的专业理念和生产模式与数字技术可供性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得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些一线从业者对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行业进行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这为我们“想象”一种体系化的数字新闻学理论提供了经验依据。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它跟新闻行业实践之间的紧密的话语互构关系(Zelizer,2004),这就使得从从业者的行业认知经验出发去展开新闻理论体系探析工作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路径和规范完成的,其基本逻辑就是“聆听他者的日常声音,解释其在地的创造力”(Burgess, 2006:201)。
实际上,新闻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难以调和的“不兼容性”。在Zelizer(2006)看来,这是由于传统新闻学根深蒂固的客观主义基础(她用God-terms来形容),亦即新闻学对事实(facts)、真相(truth)和现实(reality)等概念的合法性的不言自明的认同,在本质上是与文化研究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强调以及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理论化路径相矛盾的。但以Hartley(2008)为代表的一些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则认为,新闻学鲜明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文化研究有共通之处,文化研究路径下的新闻研究对新闻的消费过程和社会影响的强调可以强化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正当性——他进而提出“作为人权的新闻学”(journalism as a human right)这一理念。但本文认为,或许正是因为新闻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的上述张力,文化研究的路径对于我们尝试“跳出”传统新闻学体系的框架去想象一种(可能是全新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努力才有着独特的方法论价值:它对主体性的强调和鲜明的建构主义色彩可令我们获知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尝试突破旧式专业主义约束的能动性,它(与新闻学所共享的)坚定的民主价值追求则令我们在对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中始终立足于新闻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特价值。
具体而言,本文作者遵照扎根理论研究资料登录和分析的一般程序,通过对这些访谈资料的重新整理和三级编码(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最终提炼出六个主范畴概念:生态(ecology/ecological)、内容生产(content production)、责任(responsibility)、情感(affect/affective)、价值(value)、重建(reestablish/rebuild)。这六个概念又可进一步依照意义的接近性而形成四个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结合具体的访谈资料,笔者尝试对其相关话语做出文化主位意义上的解读,并据此理解作为理论体系的“数字新闻学”的合法性和构成问题。
三、研究发现
(一)数字技术的生态性角色
经扎根理论获得的第一个主范畴概念是“生态”。从访谈资料来看,当下的新闻从业者较为普遍地认为数字技术在新闻生产实践和新闻业的结构转型中扮演的角色是生态性的(ecological),而非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Anderson(2016)、Primo & Zago(2015)以及Kammer(2013)等学者的判断。
所谓数字技术的生态性角色,意指数字化进程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新闻和新闻业的外部形态,更有其内在运转的逻辑和机理。这在有些情况下意味着某些在传统新闻学体系中不言自明的命题,在数字新闻学体系下部分地或全部地失去了合法性。例如,对瑞士五家新闻机构13位可视化(visualization)编辑的深度访谈显示,这些在新闻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新的新闻工作岗位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与传统的编辑记者十分不同:一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新闻真实未必是一种“本质的”属性,而更多是一个操作性的概念,这体现出了数据科学的逻辑与人文主义、客观主义的传统新闻理念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传统新闻真实观的信仰,数字技术相关岗位的从业者对新闻失实的态度也较为宽容,且普遍认可新闻真实可以在“过程”中实现。此外,在访谈中也发现数字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专业主义”等概念的理解,也与传统新闻学体系有较大的不同。
不过,数字技术扮演生态性角色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将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影响视为一种单方面的“入侵”或“改造”,因为原来的新闻业所依存的媒介(技术)形态会依自身的“传统”与新的技术话语进行各种类型的协商,令这种生态性变化以较为平稳的方式实现。例如,研究发现,报纸、电视、广播和第一代网站的新闻从业者在接纳新技术的态度和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电视新闻编辑室的生态变化过程总体上较为稳定,这是因为在历史中获取了“强势”地位的媒介(如电视)往往比相对弱势的媒介(如广播和报纸)更有能力对各种类型的新技术的逻辑进行整合,以保持传统的延续(Evans et al., 2017)。本文作者对英国爱丁堡和瑞士日内瓦两家英文区域性报纸从业者的访谈则显示,数字技术对报纸新闻的专业生态的改变几乎是颠覆性的:原有的那种带有鲜明的社区服务意识和精英主义色彩的报纸新闻专业文化,正在不断转型为一种原子化、程式化的新兴文化,日趋具有价值中立、去个性化和民粹主义色彩。
需要强调的是,理解数字技术在新闻生产和新闻业转型中的生态性角色,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的思维方式去对数字技术进行理论化。传统新闻从业者基于不同媒介平台的技术-文化属性形成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心理具有强大的惯性和生命力。将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等传统新闻样式依新的技术逻辑统合为可被一体化解释的“数字新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新闻生产主体的技工化
经扎根理论所获得的第二组主范畴概念是“内容生产”和“责任”,这显然是与新闻生产主体(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与自我认同密切相关的。从对相关访谈资料的分析可知: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人文属性明显削弱,科学属性则显著强化,“自由”在新闻职业内涵的构成中渐渐隐退,对一种共享的“责任”的追求正在形成新的新闻职业身份。
上述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来自传统媒体从业者和数字媒体从业者(尽管两者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晰)的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传统媒体的媒介属性的确会依自身的特征对数字技术的生态性影响进行适应、消解乃至改造,致令供职于不同媒介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的数字化转型呈现为不尽相同的形态。例如,作为“弱势”媒介的电台广播,反而在过往半个多世纪边缘地位中形成了一种“强媒介属性”文化,这意味着广播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结构中,“广播”(媒介)的成色远远高于“新闻”(行业)的成色,因此其成员的职业身份认同的数字化转型就十分顺畅。相比之下,电视新闻从业者由于长期供职于“电视”这一强势媒体,数字技术的影响在其日常职业身份认同中便呈现出一种相对审慎的状态,“数字”的话语也更难实现对“新闻”话语的改造,因此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传统职业身份认同在所有媒介形态中最为稳定。但无论体现为何种方式和态势,在访谈中都可明确发现“新闻从业者”作为一个职业化群体的自我认知模式的变化:“新闻”的话语或渐进、或迅速地被吸纳进“数字”的话语,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接受“内容生产者”这一技工化(当然,也更中性化)的身份标签,并日趋习惯于以实用(如传播效果)而非价值(如新闻专业性)维度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工作。
上述发现,其实与一些欧美学者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化”和“去职业化”的话语冲突的考察有相近之处(Comer & Compton,2015;Revers, 2014;Witschge & Nygren,2009)。这些研究尽管从不同维度归纳了新闻媒介的数字化对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所产生的影响,却几乎未有触及这种认同行为在文化逻辑层面发生的变化。本文认为,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传统新闻职业认同以“客观/专业主义”和“自由/自主性”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渐被一种以“责任/公共服务使命”和“克制/道德标准”为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所取代。这是由于,随着新闻职业自身在数字化的过程中逐渐强化媒介(科学)属性、弱化新闻(人文)属性,原本附加在传统新闻学体系上的种种不言自明的道德要求就不可避免被稀释,因此对社会责任和更高伦理标准的追求这一行为本身,就成为数字新闻从业者将自己的职业身份与其他职业身份区分开来的重要依据——数字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身份的认同,在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重申(ethical reaffirmation)的过程。这一点,无论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老牌精英媒体的从业者,还是ProPublica、Slate这样的新兴数字媒体从业者中,都有广泛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用“技工化”这样的表述,并不包含对这种新的职业身份模式的贬低。这种新的身份,一方面要求新闻行业建立比以往更具标准化和可操作性的从业规范,另一方面也巩固了新闻作为公共文化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要求。正如Tait(2011)所指出的:新闻业对当下事务的守望将日益被视为一种道德责任,新闻用户正是通过新闻从业者的这种身份认知来摆脱传统新闻体系下的“窥视者”定位、获得参与新闻过程的主体性的。
(三)基于情感网络的新闻业
经扎根理论获得的第三组主范畴概念以“情感”为核心。通过对相关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数字新闻业的信息/知识传播过程,是建立在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情感网络(affective networks)之上的。这也就意味着,在对数字新闻的传播和接受过程进行理解时,我们要超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思维框架,将人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以及这种劳动的激进化(radicalization)功能纳入考量。
上述结论的得出固然首要基于对原始质化资料的扎根理论分析,但也受到了近年来传播学领域对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s)等新型信息网络研究的启发。比如,Papacharissi(2015)对热点事件的社交媒体传播过程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数字新闻用户普遍具有一种“为其语义学本能(semantic nature)建立能动性”的行为模式,这种能动性往往成为普通新闻用户的叙事驱动力,令其与外部世界发生关联;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信息平台的可供性则使这一能动性的实现成为可能(135-136)。这一观点使我们得以超越传统的(工具)理性框架,从(情感)本能的角度去理解数字新闻传播的网络:数字化的新闻传播模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生物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因素?
访谈资料在多个维度上印证了新闻传播的情感网络在数字环境下的存在和影响。例如,在针对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等五家新闻机构新闻编辑的访谈中发现,新闻机构对算法的使用,以及围绕着聚合(aggregation)机制形成的编辑室文化,越来越注重新闻生产过程对流行情感的把握。这种把握并不一定体现为“迎合”或“操纵”,而是要求新闻从业者日益将人的情感需求有机融入自己的日常生产实践。而针对瑞士本地两家数字化转型相当成功的广播电台(瑞士世界电台和日内瓦城市电台)的研究也表明,相当数量的传统媒体从业者是通过与自己想象中的数字新闻用户建立一种共同情感网络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转型的。在很多受访者看来,未来合格的新闻从业者应当拥有积极(positive)、敏感(sensitive)、共情(empathetic)等品质,这些“自我期望”显然都是情感维度上的,体现了正在经历数字化浪潮的新闻从业者对新的信息网络的准确认识。
新闻业的情感网络的本质,是以某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去组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此处的情感(affect)并非理性(reason)的对立面,而是有别于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能动性。比如,在新闻选择中,越来越多的从业者认为应当立足于大多数人所关切的社会问题寻找选题,而不是一味遵照固化的新闻价值标准——新闻从业者应当和用户共同决定新闻的形态。再如,也有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开始系统性、批判性地思考新闻的叙事(narrative)问题,他们比以前更重视“讲故事”这一行为本身所附加的情感能量,并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新闻文体在信息传达中的效能问题。
新闻业的信息网络的上述“情感转向”实际上也是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生态性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基于其自身的可供性,数字技术实际上为新闻业“制造”了一种新的“行动者-网络”(Primo & Zago, 2015)。在这样的生态转型中,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用户之间的情感关联变得比以往更强,新闻的叙事和语言甚至比新闻事实本身更好地在这一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建立其情感的纽带。同时,这一情感网络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新闻学体系对“客观-主观”“感性-理性”这样过于简单的二分法的强调(Papacharissi,2014;Wahl-Jorgensen,2012)。
(四)数字新闻业的价值危机
经扎根理论获得的第四组主范畴概念是“价值”和“重建”。与之相关的原始访谈资料主要集中在受访者对数字时代新闻业的行业危机的理解和应对策略上。对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新行业生态下,新闻业的持续性危机正在由“不存在的纯粹客观性”(Schudson,2001)转变为技术乌托邦主义导致的价值极化(the polarization of values)或价值虚无,因此数字新闻业应当持续不断对新闻业的民主和公共性价值进行重申、重建。
数字技术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主性和公共性新闻文化的衰落,这在很多受访者看来是整个行业过于迷信技术力量、缺乏反思、疏于伦理体系建设的后果。一方面,技术的狂飙突进带来了整个行业对效能的崇拜,致令新闻生产日益受短期效益目标的驱动,不再追求长远、宏观的总体社会价值,这导致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在社会变迁版图中的琐碎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掌控者(主要为跨国高科技公司)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通过资本的(如收购、兼并新闻机构)或文化的(如制造各种科技“神话”)手段去引导信息生产与流通领域的技术崇拜倾向,这又进一步压缩了公共性理念在新闻业的合法性空间。结果就是,“新闻的非民主化”(de-democratizing the news)成为全球性潮流(Fenton, 2012),“新闻机构不再将自身的公信力视为最高追求,也从未真正利用技术给生产各环节带来的透明性……这导致了新闻业(对公共性议题)的冷漠”(Domingo & Heikkila, 2012:285)。
围绕着“价值重建”这一话语,访谈资料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比如,来自美国在线和Slate两个新闻网站的受访者普遍认为,社交媒体的崛起实际上破坏了第一代门户网站通过超链接系统营造的信息民主氛围,且鼓励新闻用户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去理解和阐发新闻的意义,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无法就重大公共事件形成共识;而在互联网平台对流量(以及背后的商业利润)的追逐中,具有非逻辑性色彩的个体经验又很容易体现出情绪化特征,导致话语的“暴政”。再如,笔者在瑞士一家地方新闻网站展开的田野研究也显示,新闻机构对聚合服务的引入使得“路径锚定”在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传统新闻编辑体系的把关机制,这也就意味着能否迅速满足用户最直接的需求成为关乎数字新闻机构存亡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被证明具有更好“数字流通性”的新闻被大批量生产和重复推送,从而导致传统新闻行业生态下读者和新闻之间的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被破坏殆尽,数字新闻业沦为“内容农场”甚至“数字血汗工厂”(Bakker,2012)。
总体而言,在笔者所访谈的80余位新闻从业者中,绝大多数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新闻业的“不言自明”的价值追求的认同。尽管有学者指出,即使在“前数字”时代,“怀旧”(nostalgia)也始终都是新闻从业者在面对行业变动时所采取的最主要的集体情感策略(Frith & Peter, 2007),但这一策略在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生态下所具有的生命力,仍令人感慨传统新闻学体系在塑造价值认同上的成功。如果说“数字新闻学”是作为“传统新闻学”的承续者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前者对后者的继承性或许主要就体现在其对“理想型价值体系”的持续追求。两种新闻学赖以存在的价值体系或许有不尽相同的内涵,但它们共同反对承认价值极化或价值虚无在这个学科体系中的合法性。找寻或重建明确的价值目标,决定了我们对数字新闻学体系的想象或建构始终不能放弃对新闻学的规范性(normative)理论基因的坚守。
四、结论与讨论:数字新闻学体系想象
本文以在英国、美国、瑞士三国新闻机构展开的深度访谈所获资料为经验基础,通过扎根理论,尝试对“数字新闻学”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进行理论化。研究认为,数字新闻学在四个方面对传统新闻学体系实现了继承性突破:技术在新闻业态中日趋扮演生态性角色,数字新闻从业者的技工化,基于情感网络的新闻业的成型,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成为新闻业的持续性危机。这表明,数字新闻业无论在形态构成还是逻辑内核上,均与传统新闻业存在“范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拥有明确的现实依据。
为了对关于这一理论体系的上述想象的合理性进行验证,我们不妨回到引言部分依Thomas的社会科学理论评析框架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数字新闻学是否包含着关于新闻和新闻业的新的事实?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经扎根理论,我们看到了数字生态下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和新闻信息网络的构成均与“前数字”时代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是关于研究对象(新闻和新闻业)的新的事实,也是我们进行整个学科的重新理论化的认知基础。第二,数字新闻学是否同时提供了关于新闻(业)的知识体系和阐释模型?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新闻生产机制、新闻业相关的人与机构关系的构成,以及宏观意义上的新闻的社会价值指涉所呈现出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本身就构成了数字新闻学的知识体系,而它所阐发的分析框架就是:从媒介生态的角度去理解技术与新闻和新闻行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新闻的分析也需走向一种“技术-文化”共生论。第三,数字新闻学有否协调新闻业内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通过扎根理论来回答的问题,因为它要界定的是一种仍在剧烈变动的状态。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假若我们认可新闻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独特性部分地体现在它毫不含糊的民主性和公共性价值旨归,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要通过规范理论建构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数字新闻学”具备成为一种新的新闻研究范式和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条件。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我们对于这个正在逐渐成形,并有着可期未来的“新新闻学”体系的建构,应当从如下四个维度展开。
(1)价值内核:数字新闻学应当具有鲜明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色彩,它在价值层面应当坚持并发扬大众新闻业自19世纪上半叶诞生以来自始至终致力追求的民主及公共性价值。研究者和从业者应当对这种价值在数字生态下所面临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反思,并致力于通过完善学术建制(如改革新闻学院课程体系)的方式,为这一规范性价值内核赋予完整的、合乎逻辑的话语形式。
(2)核心概念:既然数字技术对于新闻和新闻业的影响是生态性的,那么数字新闻学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在新的学科体系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概念(如技术可供性、媒介化、行动者-网络、情感公众等)应当占据核心地位;而我们对于新闻的叙事、形态、传播路径、接受方式的理论化,也应当建立在上述核心概念体系的基础上。
(3)研究实践:数字新闻学的具体研究实践须有别于传统新闻学对新闻文体、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的社会责任等议题的优先化(prioritization),而应当立足于“数字新闻生态”这一新的“问题域”,探讨跨媒体新闻叙事的机制、新闻内容及文化的媒介化、新闻产消主体和新闻机构之间的信息/情感网络,以及新闻自身作为媒介化力量影响社会进程的方式。实际上,这些新的研究议题都指向以“作为媒介的新闻”这一生态性思路,取代“作为文本的新闻”、“作为机构的新闻”、“作为社会信息生产部门的新闻”等工具性思路,来引领未来的新闻学研究。
(4)批判理论:承认数字技术的生态性影响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拥抱这种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偏向。既然技术乌托邦主义是数字新闻业即将面临的持续性价值危机的根源,那么数字新闻学作为理论体系的批判性面向,也应当持续关注民主和公共性的价值元素在新闻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流失现象及其成因,同时在各种类型的研究实践中坚持对于新闻信息环境下的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倾向的批判性考察。
当然,本文只是一项文化研究路径下、基于欧美行业经验的探索性研究。本文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需要来自更加多元的社会语境的经验资料的支持,也呼唤不同视角下的理论化路径的共同参与。一个学科体系的确立既需要该学科的相关行动者(既包括研究者也包括实践者)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认同,也需要我们在不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化工作中进行大胆的想象和缜密的建构。这项工作不但关乎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社会进步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也关乎新闻业这一古老而新锐的行业究竟该如何在变动之中履行其对历史做出的最初的承诺。■
参考文献:
AndersonC. W. (2010). Journalistic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local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7 (3)289-309.
AndersonC. W. (2016). News ecosystems. In Witschge, T.Anderson, C. W.DomingoD. & HermidaA.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pp. 410-423). London: Sage.
BakkerP. (2012) Aggregationcontent farms and Huffinization: The rise of low-pay and no-pay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6 (5-6)627-637.
Blumler, J. G. & CushionS. (2014). Normative perspectives on journalism studies: Stock-taking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ism, 15 (3)259-272.
BroersmaM. J. & PeterC. (2013). Rethinking journalism: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public good. In Peters, C. & Broersma, M. J. (Eds.). Rethinking Journalism: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Transformed News Landscape (pp. 1-12). Oxon: Routledge.
Burgess, J. (2006). Hearing ordinary voices: Cultural studiesvernacular creativity and digital storytelling.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20 (2)201-214.
Comor, E. & ComptonJ. (2015). Journalistic labor and technological fetishis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3 (2)74-87.
Domingo, D. & Heikkila, H. (2012). Media accountability practices in online news media. In SiaperaE. & Veglis, A. (Eds.).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 (pp. 272-289).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Domingo, D.MasipP. & Meijer, I. C. (2015). Tracing digital news work: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the dynamics of news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use. Digital Journalism, 3(1)53-67.
Evans, E. et al. (2017). Building digital estates: Multiscreen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ephemeral televi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Televis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levision Studies12(2)191-205.
FentonN. (2012). De-democratizing the news? News media and the structural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In SiaperaE. & Veglis, A. (Eds.).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 (pp. 119-134).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Frith, S. & PeterS. (2007). Becoming a journalist: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journalism culture. Journalism, 8 (2)137-164.
Hartley, J. (2008). Journalism as a human right: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In Loffelholz, M. & Weaver, D. (Eds.).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Findings, Future (pp. 39-51).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ing.
Hermida, A. (2010). Twittering the news: 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4 (3)297-308.
KammerA. (2013). The mediatization of journalism. MediaKultur: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 (54)141-158.
Lewis, S. C. & Westlund, O. (2015). Actors, actantsaudiencesand activities in cross-media news work: A matrix and a research agenda. Digital Journalism, 3 (1)19-37.
PapacharissiZ. (2014). Toward new journalism(s): Affective news, hybridityand liminal spaces. Journalism Studies16 (1)pp. 27-40.
PapacharissiZ. (2015).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Techn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imo, A. & Zago, G. (2015). Who and what do journalism?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Digital Journalism, 3 (1)38-52.
ReversM. (2014).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s performance and boundary work: Source relations at the State House. Journalism, 15 (1)37-52.
Russell, A. (2011). Networked: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News Transition. CambridgeMA: Polity Press.
SchudsonM. (2001).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 (2)149-170.
SteensenS. & Ahva, L. (2015).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 An exploration and introduction. Digital Journalism, 3 (1)1-18.
TaitS. (2011). Bearing witnessjournalism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MediaCulture & Society33 (8)1220-1235.
ThomasG. (2007). Education and Theory: Strangers in Paradigms.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Wahl-Jorgenson, K. (2013). Subjectivity and story-telling in journalism: Examining expressions of affect, judgement and appreciation in Pulitzer Prize-winning stories. Journalism Studies14 (3)pp. 305-320.
WitschgeT. & Nygren, G. (2009). Journalistic work: A profession under pressure?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6 (1)37-59.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Zelizer, B. (2006). When factstruthand reality are God‐terms: On journalism's uneasy place in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1 (1)100-119.
常江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