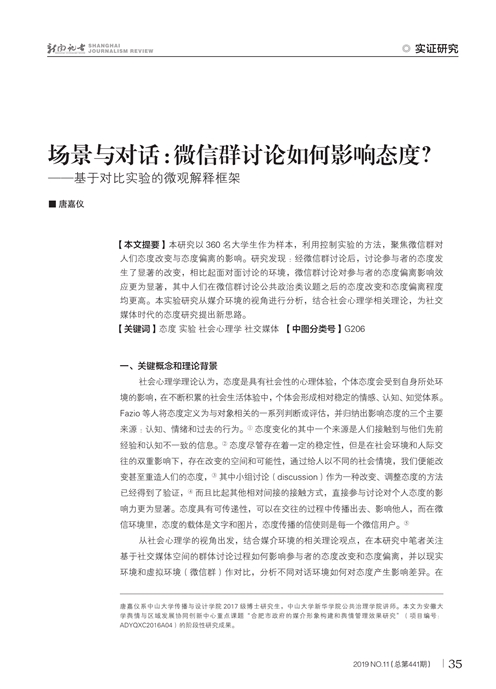场景与对话:微信群讨论如何影响态度?
——基于对比实验的微观解释框架
■唐嘉仪
【本文提要】本研究以360名大学生作为样本,利用控制实验的方法,聚焦微信群对人们态度改变与态度偏离的影响。研究发现:经微信群讨论后,讨论参与者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相比起面对面讨论的环境,微信群讨论对参与者的态度偏离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其中人们在微信群讨论公共政治类议题之后的态度改变和态度偏离程度均更高。本实验研究从媒介环境的视角进行分析,结合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态度研究提出新思路。
【关键词】态度 实验 社会心理学 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关键概念和理论背景
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态度是具有社会性的心理体验,个体态度会受到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在不断积累的社会生活体验中,个体会形成相对稳定的情感、认知、知觉体系。Fazio等人将态度定义为与对象相关的一系列判断或评估,并归纳出影响态度的三个主要来源:认知、情绪和过去的行为。①态度变化的其中一个来源是人们接触到与他们先前经验和认知不一致的信息。②态度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在社会环境和人际交往的双重影响下,存在改变的空间和可能性,通过给人以不同的社会情境,我们便能改变甚至重造人们的态度,③其中小组讨论(discussion)作为一种改变、调整态度的方法已经得到了验证,④而且比起其他相对间接的接触方式,直接参与讨论对个人态度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态度具有可传递性,可以在交往的过程中传播出去、影响他人,而在微信环境里,态度的载体是文字和图片,态度传播的信使则是每一个微信用户。⑤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媒介环境的相关理论观点,在本研究中笔者关注基于社交媒体空间的群体讨论过程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态度改变和态度偏离,并以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微信群)作对比,分析不同对话环境如何对态度产生影响差异。在一些情况下,态度改变源于人们从其他群体成员那里听到的观点或立场,由此可见从对话和讨论对态度改变的影响角度看,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是群体讨论和意见分享行为可以促成态度改变的重要原因。有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存在两个层面上的互动,共同形塑了互动参与者的态度改变:一是群体内有着不同态度的成员之间的互动,二是社会范围内有着不同规范的群体之间的互动。⑥但是,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并非所有态度改变都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影响,⑦发生对话和讨论的小组组成结构、群体规模、成员地位等,都会影响讨论过程中的具体人际互动情况,并改变态度改变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对话和讨论的发生场景特征影响了讨论本身对态度所能产生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在社交媒体时代,以微信群为代表的虚拟空间已经成为社会个体微观叙事表达和社会聚集的重要场所,⑧新的传播空间和技术拓展加深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在塑造人际交往模式和行为方面有了全新的表现。
基于文献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关注“态度改变”的文献主要来自说服研究、传播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领域,新闻传播领域有关“态度”的研究重点聚焦在媒介接触与使用对个人态度产生的影响,且更多的研究以描述性的、定性分析的方法讨论媒介对个人态度产生的影响,较少从具体态度改变程度着眼展开探讨。此外,由于态度的改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在群体环境中,对话和讨论对参与者的影响不仅反映在态度改变的具体程度上,还反映在个人与整体态度的差异程度上。“态度改变”反映的是态度的变化幅度,但是当我们把态度改变的方向纳入考虑范围时,单纯考虑态度改变的情况还不足以全面分析不同对话环境下的讨论分别如何对讨论参与者的态度产生影响。举例来说,假设我们将不同的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大致分为三种态度区间——极端积极、极端消极和温和中立,假设在一定范围内社会人群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整体落在“温和中立”的范围里,而个人在小组对话前后可能从“温和中立”的区间小范围挪动向“极端积极”或“极端消极”的区间里,那么单从态度改变的程度(数值)来看,个人的态度改变幅度并不高,但是从态度改变的方向来看,个人的态度可能因为小组对话的发生而产生了和整体态度差异变大的偏离现象。
因此,在本研究中,除了“态度改变”这一关键概念,笔者还使用了“态度偏离”的概念反映个人或小组态度与样本整体态度的差异情况,以进一步探讨微信群和面对面讨论分别如何影响讨论参与者的态度表现。其中“态度改变”指的是相比起讨论前,个人或小组态度在数值上的具体变化情况,而“态度偏离”指的则是在讨论后,个人或小组态度和整体态度的偏离程度。每个实验对象在前后测中的平均得分为该实验对象的“个人态度”数值,“群体(小组)态度”即实验中每个构造组包含的态度均值,“整体态度”为总体样本的态度参考值,不同数值的具体计算方法,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说明。
笔者从社会心理学和媒介环境的视角出发进行文献梳理,结合已有研究和新媒体技术发展实际情况看,归纳出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所构建的对话和讨论环境可能对用户的态度改变与偏离产生影响的四点基础:第一,作为一种互动和社交环境,微信塑造出一种社会心理互动的新模态。微信为人们形成聚合型的小群体提供了极佳的平台,也成为现代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把自己归类为群体的需要。在微信上,人们会组成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如家庭群、爱好群、同事群等,每个群都有一定的边界和门槛,一个微信群实际上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内群体。随着人们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实生活中以群体形式出现的讨论情况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以微信群为代表的网络讨论群体。进入Web2.0时代以来,网络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类似于公共领域的社交媒体环境,使得以公共议题为纽带、以观点和态度为分界的公众心理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⑨不同的微信群成为人们围绕不同议题和目的而组建的网络讨论小组,在不断的信息分享和讨论中自身或群内其他成员的态度和意见被形塑和改变。
第二,根据选择性机制理论,受众并非不加选择地接触所有信息,而是倾向于接触与自己原有的立场和观点更加接近甚至一致的媒介信息内容,社交媒体则为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接触机制提供了更多便利。微信为自媒体提供了内容生产、分发和传播的渠道和平台,通过“订阅”公众号并“接收推送”,用户每天可以接收到的信息更为丰富,而且通过将公众号文章分享到微信群、微信好友和朋友圈等信息分享行为,每个人可以被动接收到的信息量更大。虽然尚未有研究证实在社交媒体接触的信息量大小与态度改变之间的关系,但已有学者发现其他媒体(如电视、广播)上可选择信息的增加与态度改变的加剧存在关联性。
第三,社交媒体是一个意识形态差异信息共生的环境,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出现使公众日常接触的信息更加多元化。但是在这种信息多元的环境下,由于微信群中成员之间大多存在着某种现实关系,群成员之间相互分享的信息具有某种特定的偏好,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意见和态度传播的“马太效应”,即同意者越同意,反对者越反对。⑩小众化、分众化、定制化信息传播在微信中更加常见,受此影响,不仅可能促成用户态度的改变,甚至可能导致态度极化的出现。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仅是接触和阅读社交媒体上不同的信息,就有可能造成人们在意见观点方面的两极化表现,[11]从而加大参与者之间的态度差异情况,形成态度偏离现象。
第四,弥散性、碎片化的交流模式是社交媒体对话环境的一大特点,对话环境的特定塑造着身处其中的个体心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所构建的虚拟空间具有信息碎片化的特点,[12]在微信群中,讨论参与者的行为接近于一种“广场表达”,每个人都可以随时表达,因此话语表达往往是离散的、弥漫的。[13] “社交媒体作为一项技术,其致命弱点在于无法保证沟通与互动的真实性”。[14]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通过大量的小片段式的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而非深思熟虑地通过议论的方式表明态度。因此,社会化媒体上的舆论是一种破碎的共识,表现为在事件的事实层面上容易产生意见的碎片化,而在一般评价层面和情感层面上则容易产生意见的一边倒。[15]在碎片式的信息和观点传播过程中,人们的想法和态度很容易受到片面的影响而走向极端,从而加剧态度偏离。
麦克卢汉和英尼斯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也是一种环境。当下,我们身处的环境除了由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传统大众媒介等构成以外,基于网络技术形成的“赛博空间”已经成为形塑人们想法和行为的重要环境。媒介环境理论认为,每一种媒介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扮演着人类环境的角色。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由场域构成的。如果我们把微信空间看做一个特定的“场域”,那么在这一空间里主体之间的结构特点、互动关系等,都会影响着场内个体的思想和行动方式。在微信空间里,用户不仅可以相互交流,实现信息的传递,表达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判断,更重要的是可以相互影响,甚至改变彼此之间的态度。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说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包含了隐性态度的变化和显性行为的改变两类,本次研究只聚焦隐性层面的态度改变如何受微信群讨论的影响,对显性行为的情况则不作讨论。
二、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正如霍夫兰等人所说的,“传播是一个过程,即个人(传播者)通过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性的) 来改变他人(受众)的行为过程”,[16]而在很多情况下,一次传播就足以引起个人的态度变化。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目前关于态度改变的原因分析研究中,学者们较多从个体本身(如认知程度、意识形态及先验观点、学习能力等)、传播过程(如传播者的可信度、讨论成员互动情况、群体结构等)、传播信息特点(如恐惧诉求、议题内容)等角度切入,较少结合媒介环境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本研究借助媒介环境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重点讨论对三类不同议题,在微信群和面对面的讨论环境下,参与对话的个体态度的改变和偏离情况。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RQ1:在微信群中参与群体对话前后是否会造成群体态度和个人态度的改变?
社会心理学理论提出,态度变化的一个来源是人们接触到与他们先验态度不一致的新信息。[17]在小组讨论期间,让参与者积极讨论给定的一些议题,与没有参加讨论的实验者相比,讨论参与者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那些积极讨论小组的态度也会发生更大的变化。[18]而重复的表达方式在群体对话和讨论中会造成明显的态度改变效应,[19]当一个人反复表达或接收某种相似的观点时,他们对这种观点的认可和信任程度也可能得到强化。桑斯坦提出,小组成员如果一开始就有某种意见偏向,在商议后人们会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0]同时,人际关系情况影响着处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意见,尤其是当群体内的成员不断重复和提及某种观点时,个人态度更容易向极端方向发展。[21]综上所述,围绕研究问题1,笔者提出的研究假设为:
H1a:参与微信群对话前后,小组态度会发生显著差异。
H1b:参与微信群对话前后,个人态度会发生显著差异。
RQ2:基于社交媒体环境(微信群)还是基于真实环境 (面对面)的对话更容易带来态度改变?
有研究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时候,来自于社会角色的强大压力常常要求我们违心表达与我们私下信念不一致的看法,[22]社交媒体带来的匿名性导致禁忌的消解,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反规范行为倾向很容易被激发,[23]从而产生相对非理性的言论和行为;匿名传播形式也使人们更愿意提供自己的看法以及寻找“新奇”的证据来佐证这些观点。[24]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使用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沉默螺旋”现象,比如“舆论一边倒”。[25]同时,网络为相对平等的对话开展创造了条件,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在对话中相互碰撞,[26]更重要的是,在社交媒体平台,情绪化、碎片化、偏激化的话题被认为更易于传播,[27]近似狂欢式的网络互动和传播也会激发人们在观点生成和表达方面的偏激甚至无意识状态。
基于此,围绕研究问题2,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a:微信群对话后,群体(小组)态度的改变程度高于面对面环境下所造成的群体(小组)态度改变程度。
H2b:微信群对话后,个人态度的改变程度高于面对面环境下所造成的个人态度改变程度。
RQ3:与面对面讨论环境相比,微信群环境下个人/小组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情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在没有任何新环境刺激的情况下,反复接触一个态度对象会导致态度呈两极分化的方向改变,[28]从而导致不同阵营观点之间差异进一步扩大。传播心理学中关于人际讨论可能会带来态度的影响因素可以大致被追溯为三个方面——在问题上利用对方的立场引发社会比较;学习其他人的需求,促使讨论和关注的主题一致化;学习对方的论点导致认知上的改变。[29]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会随着多元价值观的出现而被解构与重构,社会价值的评判趋向也会从一元到多元发展。[30]而比起现实的对话环境,相对匿名和自由的社交媒体环境为人们发表和接收某种固定观点提供了便利性,受此影响人们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判断和看法也会出现更大的分歧,偏离中心态度的极端化意见容易出现。
综上所述,笔者预测在社交媒体情境下,对话对态度偏离带来的影响效应将会进一步加强,围绕研究问题3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a:在微信群环境下,对话后小组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程度显著高于面对面环境下的情况。
H3b:在微信群环境下,对话后个人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程度显著高于面对面环境下的情况。
RQ4:对不同议题(社会民生、公共政治、娱乐消遣)而言,微信群对话和面对面对话对讨论参与者态度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
态度指向事物本身的性质也会影响态度改变的幅度。在一些议题里人们的先验态度比较谨慎,那么在这个条件下他们态度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就会相对降低。[31]人们某种态度的形成和改变情况和他们所关注的具体议题密切相关。[32]对不同的话题,意见和舆论的分布也会有所不同,关于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话题,人们的态度和观点分布可能相对中立,但是关于重要话题的看法往往是极端的,[33]群体对这些“重要”话题的讨论则更有可能产生一些偏激和激进的看法。[34]有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网络公共舆论结构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即网民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议题上都出现了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态度分化,“左者恒左,右者恒右”,[35]其中政治类议题的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态度分化的效应最为明显。相比起现实环境,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多元地讨论公共议题空间,从而衍生出更加偏激的观点和态度。
基于研究问题4,笔者提出的假设是:
H4a:在微信群环境下,相比起社会民生和娱乐消遣的议题,讨论后个人对公共政治议题的态度改变程度和态度偏离程度均更显著。
H4b:在微信群环境下,相比起社会民生和娱乐消遣的议题,讨论后个人对公共政治议题的态度改变程度和态度偏离程度均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实验法,以直接评估态度变化的方法对态度的改变情况进行测量。[36]所有实验对象需对同一份问卷进行前后测共两次测试。实验开展时间为2018年6月5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通过自愿参与的原则获得实验样本,实验样本为广东省两所高校的在读大学生,样本中男女比例约为2:3,其中非党员约占74.2%,学历水平涵盖本科(74.4%)、硕士研究生(21.1%)和博士研究生(4.7%),生源地为华南地区的样本约占42.5%,样本中将近38%的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以上,学科背景为理工科和文史类的学生样本合占约68.6%。
实验包含三个部分:前测、实验(焦点小组讨论)、后测。每一个焦点小组的讨论时间为1.5到2小时。焦点小组分为两种类型:面对面焦点小组在周六或周日开展,讨论地点为两所学校内的咖啡馆;微信群焦点小组则在周六周日全天或周一到周五晚上8:30-11:00于线上开展。具体实验操作过程如下:
首先,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进行编号。通过方便抽样和配额抽样的方法,本研究的实验样本共获取360人,编号为1-360;实验对象被随机分为3大组,每个大组120人,分别为“公共政治组”、“社会民生组”和“娱乐消遣组”。以“社会民生组”中的120名实验对象为例,在前测中,每个实验对象均需要填写一份问卷,对该议题下的10个表述进行“打分”,以表达自己的态度,10分为“最同意”,1分为“最不同意”,5分为“未决定或无意见”。每个实验对象在该议题下的前测得分赋值范围为[10-100],平均得分赋值范围为[1-10]。三组实验对象分别填写三类问卷,其中“社会民生组”的前后测题目围绕物价消费、教育与就业、食品安全、医疗与卫生等问题展开;“公共政治组”前后测题目问卷涵盖政府治理、公共安全、反腐倡廉等领域;“娱乐消遣组”前后测题目则从流量明星、影视剧与流行文化、手机与自拍等方面展开。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120名实验对象按照随机分配的方式再分为两个组,每组60人,分别接受不同的实验刺激,一种是微信群讨论,一种是面对面小组讨论。在每一组60名实验对象中,研究员再将其按照随机的方式分配到10个焦点小组中,每个焦点小组包括6名实验对象。其他两类议题分组方式同上,故此次研究共包含焦点小组60个,每类议题包含焦点小组20个。每一个焦点小组除了6名实验对象,还有1名主持人(由研究人员担任),主持人只作为协调者和提问者,不介入实验对象的讨论中。三个讨论组的讨论主题以态度测试问卷中的10个问题(每组问题不同)为主,同时就讨论参与者提出的其他相关议题进行延伸性讨论。讨论过程主要聚焦参与者对相关议题的认知、态度以及形成某种态度的原因,并且围绕某些特别观点展开追问和进一步讨论,对具体态度则不做任何价值评价。
在焦点小组结束后,研究员组织所有实验对象当场填答问卷(后测),[37]后测问卷与前测问卷相同,赋值和得分情况如前测。之后由研究员计算并提取相对应的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分析实验刺激对实验对象在态度改变和偏离方面有何具体的影响。
对全部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发现,前测总体样本中值为5.70(Mean=5.67,SD=2.41)。由于前测样本数据基本呈正态分布,但后测样本数据呈偏态分布(见图1),因此在前后测中,整体态度的参考值均选取了前测中值而非均值。个人态度的改变情况用Y1和Y2表示,分别指向个人样本经过对话后,态度改变的具体数值以及个人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情况:
Y1(个人态度的改变程度)=后测A-前测BY2(个人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程度)=(|后测A-前测中值X1|)-(|前测B-前测中值X1|)
小组态度的改变程度用Y3和Y4表示,分别指向小组样本经过对话后,小组态度改变的具体数值以及小组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情况:
Y3(小组态度的改变程度)=后测C-前测DY4(小组态度与整体态度的偏离程度)=(|后测C-前测中值X1|)-(|前测D-前测中值X1|)
本次研究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3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按照格拉布斯(Grubbs)检验法的要求对前后测样本进行检验,并未发现异常值(outlier)。研究假设的验证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Mann-Whitney秩和检验以及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的方式进行处理,以确定实验的影响效果,即态度改变和态度偏离的情况(Knippenberg,Vries&Knippenberg,1990)。
四、假设验证与研究发现
(一)整体分析:实验样本的人口统计分析和实验结果描述
经SPSS检验,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三个态度测试问卷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1(社会民生组)、0.855(公共政治组)、0.916(娱乐消遣组); KMO统计量分别为0.896(社会民生组)、0.863(公共政治组)、0.911(娱乐消遣组),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显示了研究所具有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根据个人态度的前测与后测数据绘制出个人态度分布图(图1 图1见本期第41页)。虚线处为整体态度参考值
(前测中值),在前测中,个人态度在中值及附近的人数较多,在两极的人数较少;但是经过群体讨论和对话后,个人态度向两极移动的人数较多,个人态度呈现出三极化的偏态分布,极端积极、温和中立和极端消极的人数都较多,且分布较为平均。从个人态度分布的变化情况来看,群体讨论对参与者态度改变有一定的影响,这一结果与上个世纪中叶学者的研究发现相吻合。[38]针对研究问题1,如表1、表2和图2、图3(均见本期第41页)所示,经配对样本t检验,微信小组对话后意见评分高于对话前,均值由5.63上升到6.01;而经过Wilcoxon秩和检验,微信组个人对话后意见评分则低于对话前,均值由5.62移动为6.02,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5),研究假设1a和1b均验证通过。
针对研究问题2,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秩和检验,不同讨论方式下小组态度评分改变和个人态度评分改变情况均未见显著性差异(p>.05),研究假设2a和2b验证不通过。
针对研究问题3,经过独立样本t检验,不同讨论方式对小组态度偏离程度未见显著性差异(p>.05),研究假设3c验证不通过。如表3和图4(均见本期第42页)所示,经过Mann-Whitney秩和检验,对不同的个体样本来说,讨论后微信群样本的态度偏离均值为1.04,面对面组样本的态度偏离均值为0.80,根据前文说明的态度偏离程度计算方法,微信组态度偏离程度高于面对面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5),假设3b验证通过。
针对研究问题4,如表4和图5(均见本期第42页)所示,经过 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在微信群讨论环境下,不同讨论话题态度改变程度及态度偏离程度不完全相同(p<.05),公共政治组的态度改变均值为0.86,社会民生组的态度改变均值为0.48,娱乐消遣组的态度改变均值为-0.13,娱乐消遣组态度改变程度低于公共政治组(p<.05)。公共政治组的态度偏离均值为1.50,社会民生组的态度偏离均值为0.92,娱乐消遣组的态度偏离均值为0.69,社会民生及娱乐消遣组态度偏离程度低于公共政治组(p<.05),研究假设4a基本验证通过。
而在面对面对照组中,如表5和图6(均见本期第43页)所示,经过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面对面讨论组不同讨论话题间态度改变程度未见显著性差异(p>.05),态度偏离程度不完全相同(p<.05)。公共政治组的态度偏离均值为1.11,社会民生组的态度偏离均值为0.90,娱乐消遣的态度偏离均值为0.38,娱乐消遣组态度偏离程度低于公共政治组(p<.05),研究假设4b部分验证通过。
(二)研究发现:假设检验与现象阐释
1.假设1检验:微信群讨论对态度改变的影响程度
经统计检验,从整体上看在微信群场景下,小组态度分值显著高于对话前,个体对话后态度分值则显著低于对话前,微信群讨论对实验样本的态度改变有显著的影响。首先,社交媒体对网民赋予了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形成新的互动模式。在微信群讨论场景下,社会互动的过程相对复杂,[39]观察实验过程可以发现,不同于面对面对话方式,微信群中的对话有高度“碎片化”特点,人们在表达观点时通常不会一次性把自己想法说完,而是以几个句子甚至短句、短语、表情包的方式进行意见表达,使得交谈多方信息接收也呈现了碎片的特点,进一步导致公众产生态度改变。数字时代书写沟通行为可能存在某种非同步性时间特质,如果接收者不知晓有人向他发送信息,那么这时线上交流就是非同步的。[40]例如在实验观察中可以发现,在很多面对面实验小组中,均会出现明显的“意见领袖”引导讨论现象,即某一两个参与者会特别积极甚至强势地表达自己意见,尤其是当讨论小组是由熟人网络组成时,意见领袖影响力更大;相比之下,在微信群中,意见领袖尽管依然存在,但是相对而言他们对讨论的主导影响力较弱,几乎所有人在微信群环境下都有发声机会,哪怕只是发送一些表情包或者调侃类“段子”,因此讨论覆盖了更多参与者观点和看法。
其次,在社交媒体中,网络社群会呈现“分类”与“集合”状态。微信群使得具有某种相似观点的个人之间可以形成较为紧密的网络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信息窄化,其结果就是群间的区隔和疏离,使得充分的社会辩论未必能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展开。[41]正如桑斯坦所说,网络的出现让人们更容易听到与自己想法一致的言论,却也让自己更孤立,听不到相反意见,这对社会和民主的发展都是潜在危险。[42]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当有强烈先验信念的人遇到混杂或不确定证据时,他们可能会重新解释这些证据,从而导致他们的信念持续下去,甚至变得更加极端。通过观察微信群讨论过程可以发现,与面对面讨论形态不同的是,在微信讨论过程中,实验对象不仅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还经常会在讨论过程中分享一些与讨论议题相关的文章链接,当他们分享的文章是一些具有庞大阅读量的“爆款文”时,其他讨论参与者的意见则很容易被这些文章的观点所左右,改变自己的态度。比如在“娱乐民生组”讨论到关于“王菊”和“杨超越”走红现象时,不少参与者分享了公众号上一些带有明显主观情绪的文章到群里,试图用文章里的观点说服其他参与者,佐证自己的看法。
最后,多元化、多极化的传播在微信群讨论中成为常态。用户在微信上可以根据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和偏好关注不同的公众号,并且接收到不同的文章,互联网用户每天都在与个性化的信息系统进行交互,从而更轻易地获取和发布信息,使得不同阵营的观点和态度都可以获得传播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虚拟空间存在着大量虚假和失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激发网民某种极端情绪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加大了人们态度改变的可能性。综上,研究假设1验证成立。
2.假设2检验:不同讨论情境下的小组讨论分别如何影响态度改变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不同讨论方式小组态度改变程度和个人态度改变程度均未见显著性差异。从三类议题的整体讨论情况来看,经过微信群讨论之后小组的意见与经过面对面讨论的小组相比,未呈现显著的态度改变差异,研究假设2不成立。值得说明的是,实验环境的构造会影响实验的结果和内部效度,在本文的讨论部分笔者将分析本次实验过程可能对实验结果造成误差的一些操作因素。
3.假设3检验:不同环境下的小组讨论对态度偏离情况的影响对比
从统计检验结果看,不同讨论方式对小组态度偏离程度未见显著性差异,但是对个体样本来说,微信组态度偏离程度显著高于面对面组。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研究中,由于对小组态度改变的分析基于小组成员态度均值变化情况,小组意见得分可能会被群体成员相互之间的意见得分中和,因此在分析实验小组态度偏离是否会因讨论环境造成显著性差异时,结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结合对实验过程的观察,笔者认为可能造成微信组个体样本态度偏离程度高于面对面组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对话发生的时间维度看,面对面对话是同步的,直接影响彼此间的语言互动,但这一点在线上交流中正在改变。在微信群的对话场景下,参与者之间的讨论呈现出更“混乱”和“复杂”的状态,人们之间的讨论并不一定是直接的、一对一的、有指定对话对象的,尤其是在讨论气氛热烈的情况下,信息生成并不是依次出现而是同时发出的,导致其他讨论参与者对信息接收和处理难度加大,因而容易曲解对方的意涵。例如在实验过程中,就多次出现在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时,由于微信群对话的开放性,多人同时发表自己观点,当某一位参与者回复“我不同意”时,很难让其他人马上理解这种意见是针对哪一条观点,造成主体间对话和沟通的难度加大。
其二,群体心理学发现,与持有与自己相似意见的人接触和交流后,态度会发生显著的改变,在群体内部,对原有意见的支持程度会加强,而在不同意见群体之间,态度的差异程度则会更大。以微信群为代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出现使得志同道合的团体更容易地开展沟通和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如果一些讨论参与者在最初就对某一问题持有较为极端的态度和看法,那么在讨论之后他们更可能通过选择性记忆的机制记住那些与他们先验观点一致的信息,并通过将在微信群讨论中所接收到的信息转发到其他微信对话或朋友圈,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使既有的想法和态度不断巩固。
其三,在微信的讨论环境下,讨论参与者处于相对自由和隐匿的状态,对观点的表达也更随意甚至极端,不同于面对面环境下受传统规范的限制,观察实验过程可以发现,尤其是在讨论公共政治议题的过程中,参与者在微信群中的发言更为“激烈”,相对去中心化的讨论方式使得人们更可能坚持甚至强化自己原有的某种观点和看法,从而偏离了整体态度。基于此,研究假设3部分成立。
4.假设4检验:不同讨论情境下对三类议题的讨论分别如何影响态度改变
统计结果显示,在微信群讨论中,实验样本对公共政治议题形成的态度改变程度以及态度偏离程度均高于另外两个议题;而在面对面的讨论环境里,这种针对不同议题而形成的态度改变程度差异并不显著,但是态度偏离程度则呈现显著性差异,“娱乐消遣组”态度偏离程度低于“公共政治组”。社会心理学认为,态度改变不单纯是一种个体态度和观点的反映,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体对群体和社会规范的一种抗争性情绪表现。[43]根据英尼斯的说法,新传播技术的出现会推动和促进知识的传播,并激发普通大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受到长期以来国内舆论和媒体环境特点的限制和影响,公众在公开场合讨论公共政治类议题的成本较高,由此容易积累一种“堵塞”和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微信群这种虚拟的、不需要真实“在场”的对话环境出现,导致人们将长期以来在现实群体生活中的抗争情绪和意愿集中进行表达,容易出现极端的言论和观点。通过观察实验过程可以发现,围绕社会民生和娱乐消遣两类议题的讨论呈现出差异较小的观点和态度分歧问题,讨论参与者表现出更为一致的意见,折射出当前社会和民生领域向一元价值观方向发展。例如在“杨超越现象”以及“王凤雅事件”两个事件的讨论中,参与者的观点几乎呈现完全“一面倒”,也就是说,对话过后参与者的态度可能进一步强化,但是参与者之间的态度差异程度较小。
此外,值得说明的是,个人的态度形成和改变尽管受到媒介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更多时候“个人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社会和心理发展的一种反应”,[44]因此在本研究中,实验对象对公共问题态度的改变并不完全由社交媒体环境所造成,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出现一些公众不满意之处,加之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政府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危机事件影响了公众对公共政治问题的判断和认知,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上更容易形成了某些相对极端的观点。由此,研究假设4部分验证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媒介环境学将媒介视作一种环境,集中关注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梅罗维茨认为,媒介是导管、语言和环境,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由特定类型的“感性信息”所组成,这种媒介环境通常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我们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塑造着我们的体验。[45]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效果作为新的环境,就像水对于一条鱼是不可感知的,它对大多数人是下意识的”。[46]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提出,单纯的思考就可以引发态度的改变,而且这一过程极为简单。[47]微信群作为一种新的媒介环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谈和对话方式,同时也为对话发生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在网络环境下,人们的交往受到较少时空约束,互联网的存在消除了物质世界里存在的多重障碍,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话参与者在这种环境下的情感体验强度,改变了态度形成的模式和特征。
通过对已有文献和相关研究梳理可以发现,当前对“态度”问题的探讨以单一学科所开展的研究为主,结合社会心理学和媒介环境视角的实验研究介入不足。本研究试图通过量化实验的方法,聚焦社交媒体环境与真实环境下的讨论与对话分别如何影响态度改变和态度偏离,结合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就相关问题进行回应,为态度研究提供了一种符合当下中国传播语境和互动现实的思路和路径。本研究发现,在微信群讨论场景下,讨论参与者的态度会与讨论前发生显著差异,经过讨论后的个人态度偏离程度比面对面环境下的偏离程度更高;具体到在公共政治、社会民生和娱乐消遣三类议题讨论中,在微信群讨论娱乐消遣问题的态度改变程度显著低于公共政治话题,讨论社会民生及娱乐消遣话题的态度偏离程度均显著低于公共政治话题。
需要指明的是,由于研究方法的特点和实验操作受到的限制,在本实验设计中存在一些可能会对实验结果和研究发现造成一定误差和影响的问题: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选取主要考虑抽样方便性,因此可能会存在由实验样本本身构成特点所带来的实验误差(如地域、专业背景等),未来关于微信群对话如何影响态度改变、态度偏离等相关研究应考虑扩大样本范围,以提高实验样本代表性和科学性。
其次,正如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的“参与改变理论”,个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主动参与型,另一种是被动接受型,主动参与活动者比被动接受者更容易改变其态度和行为。[48]本研究中,部分研究假设的检验以6人为一组进行了以小组为单位的数据分析,由于分组的随机性,不同小组中包含的实验对象不仅在人口学结构上存在差异,而且可能存在对话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差异,不同小组成员的先验观点也可能具有异质性或同质性较强的特点,因此以小组为单位对态度改变、态度偏离等情况进行检验分析,不可避免会受到随机分组情况的影响,从而影响实验效度。
第三,本研究在构造实验小组时,考虑到实际操作的难度和时间以及讨论的深度,采用了随机分组的方法构造以6人为一组的实验小组,[49]实验组规模对实验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每个实验组中的讨论参与者在此之前可能是互不认识的陌生人(或部分熟人部分陌生人),但在真实场景下的微信群或面对面讨论环境都更多地由熟人网络构成,讨论的开放程度要比实验环境要高,实验环境的构造特点可能对实验效果带来一定的偏差;而且在真实的场景下,微信群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亲属群、同事群、兴趣群等,不同微信群具有不同目标和结构特点,不同性质的微信群讨论对参与者态度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最后,考虑到本实验前后测间隔时间较短,如果在没有接受实验刺激的情况下进行后测,则有可能造成因实验间隔时间太短而造成的重复实验带来的误差;[50]此外,所有实验对象分别只接受了一次实验刺激,没有纳入无实验刺激、重复讨论以及实验过后态度改变的长期情况等问题的讨论,对基于实验结果以及相关分析存在一定的影响,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需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技术作为一项自变量,对身处其中的人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和互动情况或多或少产生着某种影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关系的嵌入方式是复杂的,因此将社交媒体视作一种独特的技术和传播场景,聚焦这种对话环境对个体态度的影响并非意味着技术可以决定社会,也不等同于媒介中心主义,而是意味着技术作为一种环境,可以使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更加具体可见。社会发展现状、整体舆论环境、公众心理与情绪等本身对态度改变的发生有着同样深刻影响,尽管微信群构造的讨论环境不能被视作引发人们态度改变的根本或唯一原因,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对话和讨论场景为态度研究带来了新的语义和背景。随着未来研究的开展和延伸,对社交媒体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探究可以进一步挖掘个体态度、社会关系结构、历史背景脉络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获取更多关于对话和态度的理解和发现。■
①Zanna, M. P.& Rempel, J. K.“Attitudes: A new look at an old concep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Knowled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p.315-334.
②Festinger, L.& CarlsmithJ. M.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59,No. 58pp. 203-210.
③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第22页,张旅平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④Zanna, M. P.& Rempel, J. K.“Attitudes: A new look at an old concep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Knowled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p.315-334.
⑤赵文晶、申利净:《社交媒体用户迁移背景下微博、微信的态度传播生态研究》,《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10期
⑥Paicheler G. “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s”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Vol.9No. 1pp. 85-96.
⑦Brauer MJudd C MGliner M D. “The effects of repeated expressions 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during group discuss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5Vol. 68No.6pp. 1014-1029.
⑧郑满宁:《公共事件在微信社群的传播场域与话语空间研究》,《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
⑨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⑩余秀才:《微信传播的马太效应、木桶效应与涓滴效应》,《编辑之友》2015年第12期
[11]Abril EP,“Subduing Attitude Polarization? How Partisan News may not Affect Attitude Polarization for Online Publics”,Politics and Life Science2018,Vol. 37No. 1pp.68-77.
[12]巴志超、李纲、王晓、李显鑫:《微信群内部的会话网络结构及关键节点测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7年第20期
[13]郑满宁:《公共事件在微信社群的传播场域与话语空间研究》,《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
[14]骆正林,曹钺:“《被扭曲的交流”: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现象的三重批判》,《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4期
[15]杨洸:《社会化媒体舆论的极化和共识——以“广州区伯嫖娼”之新浪微博数据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2期
[16][美]C .I霍夫兰、I. L 贾尼斯、H.H. 凯利:《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第10页,张建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7]Festinger, L.& CarlsmithJ. M.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1959,No. 58pp. 203-210.
[18]Janis, I. L.& King, B. T,The influence of role playing on opinion change”,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54,No. 49pp. 211–218.
[19]Brauer MJudd C MGliner M D. “he effects of repeated expressions 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during group discuss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5Vol. 68No.6pp.1014-1029.
[20][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第43页,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
[21]Brauer MJudd C MGliner M D. “he effects of repeated expressions on attitude polarization during group discuss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5Vol. 68No.6pp.1014-1029.
[22][美]C .I霍夫兰、I. L 贾尼斯、H.H. 凯利:《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第174页,张建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3]Spears R. ,Lea M. & Lee S.,“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0,Vol. 29,No. 2, pp. 121-134.
[24]Sia C. L. ,Tan B. C. Y. & Wei K. K.,“Group Polarization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Cues,Social Presence,and Anonymit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2,Vol. 13,No. 1, pp. 70-90.
[25]周凯、刘伟、凌惠:《社交媒体、“沉默螺旋”效应与青年人的政治参与——基于25位香港大学生的访谈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播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26]叶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理论建设》2005年第5期
[27]赵路平、于泓洋、叶超:《特朗普怎样使用推特——对特朗普推文的大数据分析》,《新闻记者》2017年第7期
[28]参见BrickmanP.Redfield, J.Harrison, A. A.& Crandall, R. “Drive and predisposition as factors in the attitudinal effects of mere exposur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2, No. 8pp. 31-44.
[29]BrandstatterH.& Klein-ModdenborgV. “A modified proportional change model of attitude change by group discussion”,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79,Vol.9No.4pp. 363-380.
[30]郑杭生、郭星华:《当代中国价值评判体系的转型》,《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
[31]CookT. D.& Perrin, B. F. “The effects of suspiciousness of deception and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deception on task performance in an attitude change experiment”,Journal of Personality2010, Vol. 39No. 2pp. 204-224.
[32]乐媛、杨伯溆:《网络极化现象研究——基于四个中文BBS论坛的内容分析》,《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
[33]参见Liu James H & Latane Bibb, "Extremitization of Attitudes: Does Thought- and Discussion-Induced Polarization Cumulate? ," Basic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8Vol. 20No. 2pp. 103-110.
[34]Wallach M. A. & Kogan N.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Discussion,and Consensus in Group Risk Ta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65, Vol1No.1pp.1-19.
[35]马得勇、张志原:《公共舆论的同质化及其心理根源——基于网民调查的实证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6]Miller A GMchoskey J WBane C Met al. “The attitude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Role of response measureattitude extremity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reported attitude change”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3Vol. 64No. 4pp. 561-574.
[37]考虑到实验前后测相隔时间较短,如安排“无讨论”后立刻进行后测,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重复测试带来的实验误差,因此并未设置“无讨论”的对照组。
[38]参见Timmons, W. M.“Can the product superiority of discussors be attributed to averaging or majority influenc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42No.15pp. 23- 32.
[39]夏倩芳、原永涛:《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6期
[40][加]马塞尔·达内斯:《占领世界的表情包——一种风靡全球的新型社交方式》第16页,王沫涵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1]韩娜:《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影响的研究——基于批判的视角》,《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42][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第47页,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
[43]Paicheler G. “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s”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Vol.9No. 1pp. 85-96.
[44][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第77页,张旅平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45]刘燕:《媒介与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澳门内地移民为个案》第112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6]李西建、金惠敏主编:《美学麦克卢汉:媒介研究新维度论集》第149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47]参见Tesser. AMartin, L.& Mendolia, M."The impact of thought on attitude extremity and attitude-behavior consistency". In R.E. Petty & J.A. Krosnick (Eds.).Attitude strength: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MahwahNJ: Erlbaum.1995pp.73-92.
[48]牛耀红:《操控、赋权、话语空间:理社交媒体广告的三个维度——以微信信息流广告为例》,《编辑之友》2017年第10期
[49]参见Schkade DSunstein C RHastie R. "When Deliberation Produces Extremism" Critical Review, 2010Vol.22No.2pp. 227-252.
[50]参见Yardi Sarita, Danah Boyd. “Dynamic Debates: 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Over Time on Twitter."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 2010Vol. 30No.5pp.316-327.
唐嘉仪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公共治理学院讲师。本文为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重点课题“合肥市政府的媒介形象构建和舆情管理效果研究”(项目编号:ADYQXC2016A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