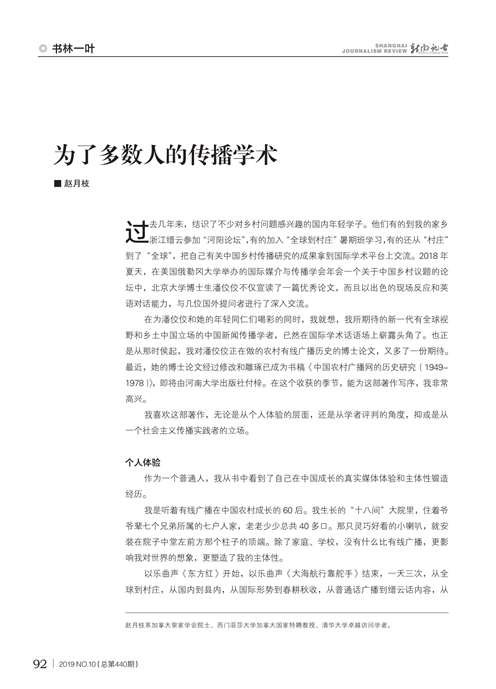为了多数人的传播学术
■赵月枝
过去几年来,结识了不少对乡村问题感兴趣的国内年轻学子。他们有的到我的家乡浙江缙云参加“河阳论坛”,有的加入“全球到村庄”暑期班学习,有的还从“村庄”到了“全球”,把自己有关中国乡村传播研究的成果拿到国际学术平台上交流。2018年夏天,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举办的国际媒介与传播学会年会一个关于中国乡村议题的论坛中,北京大学博士生潘佼佼不仅宣读了一篇优秀论文,而且以出色的现场反应和英语对话能力,与几位国外提问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为潘佼佼和她的年轻同仁们喝彩的同时,我就想,我所期待的新一代有全球视野和乡土中国立场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已然在国际学术话语场上崭露头角了。也正是从那时侯起,我对潘佼佼正在做的农村有线广播历史的博士论文,又多了一份期待。最近,她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和雕琢已成为书稿《中国农村广播网的历史研究(1949-1978)》,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付梓。在这个收获的季节,能为这部著作写序,我非常高兴。
我喜欢这部著作,无论是从个人体验的层面,还是从学者评判的角度,抑或是从一个社会主义传播实践者的立场。
个人体验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从书中看到了自己在中国成长的真实媒体体验和主体性锻造经历。
我是听着有线广播在中国农村成长的60后。我生长的“十八间”大院里,住着爷爷辈七个兄弟所属的七户人家,老老少少总共40多口。那只灵巧好看的小喇叭,就安装在院子中堂左前方那个柱子的顶端。除了家庭、学校,没有什么比有线广播,更影响我对世界的想象,更塑造了我的主体性。
以乐曲声《东方红》开始,以乐曲声《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一天三次,从全球到村庄,从国内到县内,从国际形势到春耕秋收,从普通话广播到缙云话内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普通话广播剧到时任缙云县文化馆馆长丁金焕同志的缙云话故事,从世界上一个个国家的名称到本县一个个村庄的名字,有线广播比课本更丰富和生动地给了我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语文、农业和日常生产生活知识的滋养。
虽然我只去过自家周围的村庄和本县有亲戚的几个村庄,虽然我直到15岁那年秋天去上大学才第一次走出县城,但广播新闻中那些地名,早已构成了我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想象共同体”。那种与首都北京“共时”、与全国各地“共时”的主体感觉,是有线广播,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赋予的。
我自己很少特意去听广播,而广播的特点也正在于它的伴随性,在于它“嵌入”了农村的日常生活。不过,在我的脑子里,也铭刻着我隔壁姑父端着饭碗,靠在中堂那个柱子上,专注入神地听广播的画面。姑父是个文盲,从一个几十里外的山村入赘到我隔壁的三叔公家。他出生的那个山村戏曲文化兴盛。我隐约记得,姑父专注听的节目,主要是文艺节目。
而我自己,对有线广播最深刻、最清晰的记忆,则停留在1980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清晨。那天,我在镇里溪边一座借宿的房子的阳台上背历史,准备高考。我背我的教科书上的历史,广播播它的国内国外新闻,它是我日常生活的背景声音。然而,我还是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一条有关于津巴布韦独立的新闻所吸引了。新闻中那旗帜鲜明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立场,播音员那激昂的声音和为津巴布韦人民的独立而欢呼的语调,深深地感染了我。它让我激动,让我奋进,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第三世界共同体的一员,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希望。
一条国际新闻,就这样为我续写了历史教科书上的民族解放和第三世界叙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世界的想象,就被这样的“无孔不入”的声音宣传所塑造和强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我成长为一个本书中所说的“身在农村、胸怀世界”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体。
我的体验也许是特殊的,但是,听有线广播的经历却是大多数人的。毕竟,直到1980年,中国农村人口还占80%以上。从我这样的学生到我姑父这样的文盲,有线广播影响了中国的大多数人,构建了几代人的主体性。
本书是一个有新意、有价值、有启发的历史研究,20世纪50到70年代,对于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并不遥远。对许多比我年长的人来说,农村有线广播是新的建设经验、新的生命实践、新的审美体验与新的社会情感;对我这样的有线广播“原住民”来说,有线广播是自己曾经呼吸的“媒体空气”。
在今天这个学术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远离普通百姓日常体验的年代,这部有关一个历史时期80%以上人口的“新媒体”体验的书,让我激动,引我共鸣。作为那80%中的一员,我在这部书的宏大叙事中,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的影子,知道了这个对我的主体性产生了这么大影响的公共传播体系,是如何在曲折、动乱和调整中,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它使我从一个农村有线广播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变成了一个对农村有线广播来龙去脉及其对于农民意义的“知情者”。
我无法代表所有听过有线广播的中国农民对此书做出评价。但是,作为中国有线广播网曾经的听众的一员,作为一个曾经被这个网络中的话语所“询唤”的主体,我不但乐于看到这样的让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的学术研究,而且乐于看到这个研究中所表达出来的对农民的尊重,以及对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孜孜以求之心的认同。
学者视角
作为一位传播学者,我喜欢本书的多维度、立体化学术视角,赞赏它在广播历史研究中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历史深度。在这部历史书中,我看到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辩证认知、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对结构性力量的重视、批判性政策研究对政策话语和政策过程的全面和动态检视,以及文化研究视角对主体性与日常生活体验的关照。在这些视角的有机交叉中,作者通过深思熟虑的谋篇布局,写出了一部既有“全球到村庄”的多层次分析,又能展现历史局限性和主观能动性双重互动的中国农村有线广播从起步到发展繁荣的历史。
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本科毕业生,我对世界广播史和中国广播史都不陌生。作为传播学者,我也知道,从欧洲的本雅明、布莱希特到加拿大的麦克卢汉、伊尼斯,从美国的主流传播与发展学者到美国的批判传播学者,有关广播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与此同时,从埃及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人之声”电台到玻利维亚矿工电台,广播在发展中国家的解放性实践,也在世界传播史上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在世界广播传播历史上都是极为独特的。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专著能像此书这样,把中国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生史”和意义,写得如此既恢宏又接地气,既有“制度世界”的深入分析,又有“生活世界”的工笔描摹,既有“全球60年代”的世界历史背景的勾勒,又有具体到县域、村庄甚至个体层面的叙述。最为重要的是,这部书既见物又见人,既见结构又见主体。
中国农村有线广播从发展到式微的20世纪中后期短短几十年,恰逢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大转变,也浓缩着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繁乱的历史线索、缤纷的社会时事奔涌其间,真诚、美好、狂热、破坏等不同的起起伏伏,均为历史书写者“拨开迷雾”增添了几分难度,也让人不由为年轻的、完全生长于当今时代的学者捏一把汗,怕其力有未逮,难以驾驭。然而,本书以并不算长的篇幅,通过对理论资源、历史资源和典型案例的有机调用,为读者勾勒了一幅在时间维度上跌宕起伏,在空间维度中错落有致的中国农村有线广播网发展历史画卷。
除了把中国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放在技术生成史的视野下和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框架之中,这部书的最大亮点之一,在于作者在第二章《大国治理的文化技术:历史形成与近代转型》中,把现代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展及其意义放在了中国几千年“大国治理”框架之下及其信息结构的衍变过程之中加以审视。在这一宏大的历史性叙事中,作者不是就媒介论媒介,而是自始至终贯穿了传播技术发展和社会解放的视角。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书面传播到民间口语文化,从主要迎合有消费能力的城市有闲阶层的无线电广播到农村有线广播网,在历史中作为一个整体处于无声状态的农民,通过有线广播网,被纳入到对于现代化国家、未来社会的想象之中。
虽然农村有线广播根植于基层,一般以县域为单位来组织,但是,它不是一个双向的传播模式,这点毫无疑问。实际上,从一开始,自上而下全国性宣传网络的建设和“让农民知晓”,就是有线广播网最主要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这一目标的分析,既包含了需要动员农民进行国家建设和把农民纳入到全国大一统的信息网络之中的角度,也体现了农民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主体,对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充满热望的视角。无论是从历史真实角度,还是从挑战那些对“皇权不下县”的“美好过去”颇有怀恋的历史虚无主义意识出发,作者对“让农民也能听上广播”这一目标的确立与实现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其意义的不遗余力阐发,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作者也力图显示“群众路线”在中国新闻历史上的双向性。从延安时代共产党培养和鼓励农民通讯员,到土改和解放初期的农民“诉苦”实践,再到1970年代的“土记者”和乡村通讯网建设,如何让农民“既能听到党的声音,又能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问题意识,一直贯穿于全书。
如果说,“印刷资本主义”描述了西方现代传播的本质,“底层人能说话吗”提出了后殖民现代传播的关键问题,那么,“有线广播社会主义”和“解放了的农民如何表达”可否成为由这一段历史所开启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的相关命题?
未来指向
作为一名志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改造世界的实践者,我认同本书所重构的中国农村有线广播历史所昭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体系的未来。
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本人在农村有线广播影响下成长的体验并不能代表所有农村人的体验,本书对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历史叙事,并不是唯一的“正确”叙事。毕竟,在冷战意识形态中,在一个把“流动的藏私”等同于个人自由甚至个体的“自主”的市场自由主义框架中,没有比无孔不入的有线广播和中国“大喇叭”,更能象征性地被当作负面理解的共产党“宣传”和对“自主”的信息空间的侵蚀了。因此,有同仁指出本书是否有浪漫化历史之嫌,也就不奇怪了。
也许,这种疑问的背后,是对当下大行其道的后现代历史观的本能警惕。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写作者会从想象出发“建构”历史,继而背离历史自身的逻辑,将历史浪漫化、神秘化或者黑暗化。以这种历史观出发,过去容易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情绪宣泄。不过,本书作者显然不但思考过这一问题,而且作了充分的方法论准备。正如书中所言,“历史学家的想象应该与证据呈现出一致性,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这是历史写作者的治学要求,也是治史得其合法性的根基:尊重人类留存的痕迹,敬畏人类的奋斗与创造,达成“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从而中介过去与现在。
从一定层面,“浪漫”的确洋溢在本书之中。然而,依我的理解,这不是对历史进行浪漫化的想象与建构,而是勾勒出了中国农村广播网建设中的两个维度: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从无到有之间,不仅横亘着物质条件方面的结构性阻力,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技术政治路线、立场,甚至部门利益间的纷争。农村广播网是复杂的现代技术系统中的一部分,它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受制于现实,也受制于人们的想象力。但是人类的社会意图与社会期待,往往会激发突破结构、重塑结构的能动力量。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不乏浪漫主义理想的挥洒,而这正是这个世纪留给今天的最伟大历史遗产。毕竟,这曾经是一个“庶民的胜利”的时代。用历史逻辑去理解集体行动与个体情感,探知出人的活动轨迹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人民本位”思想在克服物质与技术条件方面的局限,才能理解何以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大众媒介能够产生。当然,在某些框架中,“人民本位”和“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就是虚无缥缈的,因而也是“浪漫”的。
历史并不平滑如镜,它有不同横断面的立体棱镜,折射出不同的生命经验与灵魂面目。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的新闻传播部分,时常在“放卫星”、“假大空”、“大字报”、“大批判”等叙事中显得满目荒唐。通过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聚焦到几千年历史中占全国80%以上的人口如何第一次被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现代信息体系,这本书显然是意欲继续挖掘“前三十年”传播历史的丰富性、全面性以及复杂性,呈现曾经的历史主体在这个国度镌刻下的印记,展现一个公共的、普惠的文化基础设施如何诞生,如何编织入了亿万农村男女老少的人生经纬之中。将这个过程和在此过程中从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主张到村中老农的体验打捞出来,既可以使这段历史免于被遗忘,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国家与乡村之间正在经历数字化重构的传播体系与中国农民的情感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当然,于当下回望过去,在距离感中寻求方向感,需更加审慎与深思熟虑。但也唯有对历史总体性和多重性的不断探索,才能在不同话语的对照中,真正体认“人民本位”的立场,进而将之用于构建一个“人民知晓”和“人民表达”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实践。实际上,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就明确提出,本书是为如何构建县级融媒体这一“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写的。书中总结的信息治理的中国制度与中国经验,对理解中国传播史有特殊的价值,社会主义信息政治实践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也为当下新时代社会主义基层媒介网络的继续建设提供了借鉴。
结语:多数人的传播网络
出版过程中,作者曾希望有一个比现在这个原博士论文副标题更有诗意的书名。但是,我们建议她保留现有书名。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学者邓英淘那本叫做《多数人的现代化》的书。从有线广播曾经是实现这一“多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多数人的传播网络”的角度,也许可以给这部书起一个《多数人的传播网络》这样的别名?
不过,现在这个书名也很好。它既概括了本书的内容,又朴实无华,各类读者一看就明白。同时,因为它突出了历史研究的视角,让人感觉内涵丰富,而中国农村广播1978年之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它在正在构建中的县级融媒体中的角色,也颇值得研究。对于此书,我只是爱之深,才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从封面到它的名字,不免多想了一些!■
赵月枝系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卓越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