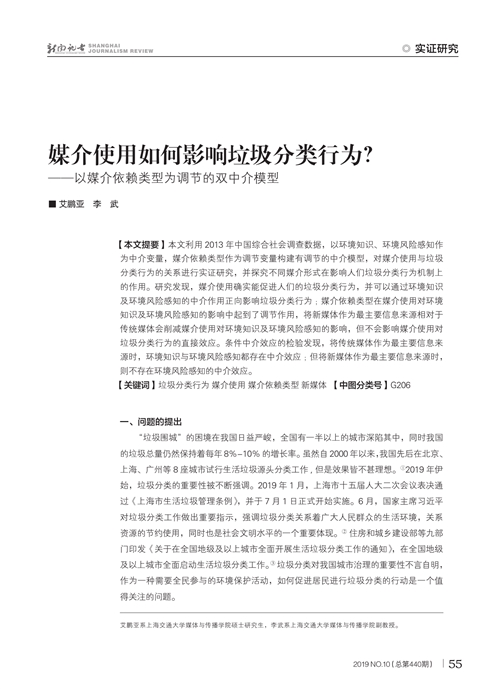媒介使用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
——以媒介依赖类型为调节的双中介模型
■艾鹏亚 李武
【本文提要】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环境知识、环境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媒介依赖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媒介使用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探究不同媒介形式在影响人们垃圾分类行为机制上的作用。研究发现,媒介使用确实能促进人们的垃圾分类行为,并可以通过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垃圾分类行为;媒介依赖类型在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将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相对于传统媒体会削减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但不会影响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效应。条件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将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时,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都存在中介效应;但将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时,则不存在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垃圾分类行为 媒介使用 媒介依赖类型 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垃圾围城”的困境在我国日益严峻,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城市深陷其中,同时我国的垃圾总量仍然保持着每年8%-10%的增长率。虽然自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座城市试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但是效果皆不甚理想。①2019年伊始,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2019年1月,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于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垃圾分类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关系资源的节约使用,同时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③垃圾分类对我国城市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作为一种需要全民参与的环境保护活动,如何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行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媒介使用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传播学长久以来关注的内容。媒介使用不仅仅对人们的暴力行为④、攻击行为⑤、冒险行为⑥等有所影响,也可以影响到人们的亲社会行为。⑦那么,媒介使用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垃圾分类行为呢?若确实存在影响,媒介使用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人们的垃圾分类行为呢?当人们选择的最主要信息来源不同的时候,其内在机理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并期待通过探索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为垃圾分类的推广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媒介使用与亲环境行为
亲环境行为指人们使得自身的活动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甚至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行为,⑧学者常常按照影响将亲环境行为分为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公领域亲环境行为包括公众领域的各类亲环境行为,如加入环保组织、参加环保活动等;而私领域亲环境行为则包括如环保购买行为、垃圾分类行为等各类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⑨动机、情境、习惯等因素都可以影响人们的亲环境行为。⑩
张萍和晋英杰认为大众传媒传播环境知识,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有助于信息公开,强化民众与环保的关系,因此媒介使用能够促进人们的亲环境行为。[11]目前一些聚焦于媒介使用对人们亲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也普遍验证了这一点:如Huang基于台湾的调查数据发现,个体的媒介使用对三类亲环境行为均有直接正向的显著影响;[12]Lee通过对6010名香港青少年的调查数据发现,接触媒体上的环境信息能够影响香港青少年的绿色购买行为。[13]垃圾分类行为作为亲环境行为的一种,可以推测媒介使用同样可以促进这一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有正向直接的影响。
(二)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
媒介使用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一定是完全直接的,可能经由对人们认知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传递信息是媒介的一个主要功能,人们可以从媒介中学习,而知识增长也是媒介使用的一个重要结果(无论人们是否是有意识地获取知识),在科学传播领域,诸多研究也发现了媒介使用能够增加人们的主观或客观的知识,如气候变化的知识。已有研究发现环境知识(如人们对环境问题及产生原因的认识、如何进行亲环境行为的知识)对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有所影响,[14]因此环境知识可能在媒介使用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如石志恒等对甘肃省农民亲环境行为的研究。[15]基于媒介建构论,媒介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16]McCallum 等人发现大众传播是公众环境风险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17] Wakefield 等通过内容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也验证了这一点。[18]媒体对于环境问题的描述、对环境事件的报道等塑造着人们对于身边环境风险的认识,已有实证研究发现对新闻信息的关注可以影响人们对环境风险的感知。[19]而当人们感知到身边环境风险的时候,可能倾向于调整自身的行为以有利于环境:一项在欧洲五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风险感知对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有着正向显著的影响。[20]因此,环境风险感知可能在媒介使用对人们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周全等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种中介作用的存在,并且其研究表明媒介使用越多,对于环境风险的感知越强烈,进而公众更可能进行亲环境行为。[21]综上所述,媒介使用除了可能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还有可能通过对环境知识以及环境风险感知的正向影响,进而间接地促进垃圾分类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环境知识在媒介使用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环境风险感知在媒介使用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媒介依赖类型的调节效应
已有许多学者开始探讨不同媒介形式使用对亲环境行为影响的差异:Ho等人通过对新加坡成年人的调查发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使用在预测人们两种不同的亲环境行为上存在差异,传统媒体使用可以正向显著地预测私领域亲环境行为(绿色购买),但是新媒体使用的预测作用却不显著;对于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环保公民参与),结果却相反;[22]金恒江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对人们的环保议题讨论和环保社会参与的影响上皆强于新媒介使用;[23]卢春天通过对西北地区4省8县(区)农村地区调查表明,媒介的使用可以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并且传统媒体使用对西北地区农村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影响更大。[24]因此,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使用在影响人们的亲环境行为上确实存在差异,可以认为在垃圾分类行为上也同样如此。
但是由于人们日常使用媒介时,并不会只用新媒体或传统媒体。使用新媒体频率较高的个体很有可能使用传统媒体频率也高于一般人群,因此直接将媒介使用区分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作为自变量探讨媒介使用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恐怕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对媒介形式的不同之处进行深入的探讨。对调节效应的讨论可以发现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规律,并可以对实践应用给予对应的启示。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将媒介依赖类型(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作为调节变量,以期比较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介类型不同时,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和其作用机理会存在哪些不同。
人们在使用传统媒体时很难对信息进行筛选,但是使用新媒体时(如互联网、手机)对信息的选择能力更强,因此更有可能选择那些自身感兴趣的内容。Ostma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媒介使用对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有着正向显著的影响,他基于媒介政治社会化的视角,认为除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外,媒介在人们的社会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促进青少年公众参与的重要因素,“青少年可以借助媒介使用知晓哪些因素对可持续发展存在威胁(就好像他们了解政治和社会一样),进而改变他们的日常行为以应对这些威胁”。[25]从这一视角来看,亲环境行为属于公共事务参与的一种。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他对于新媒体可能减弱人们参与公众事务的担忧,他认为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公民的角色可能会有所冲突,网络时代传播体系的个人化变得更为普遍,数字化生存的消费者对于信息的过滤和筛选的掌控增强,人们可能因此减弱公共领域的讨论。[26]在网络迅速普及的背景下,相对于互联网、手机这样的新媒体,大众媒体促进公共讨论的社会角色则可能被凸显出来,为公众提供未经个人筛选的话题和观点,促成经验共享和共同的社会关注。[27]因此,相对于传统媒体,互联网、手机之类的新媒体在影响人们亲环境行为的效果上可能弱于传统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信息依赖而言,人们对新媒体的信息依赖更可能“个人化”,从而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关心,通过媒体获取环境知识以及感知环境风险的可能性更低。也就是说,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个体的媒体依赖类型为新媒体时,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将减弱。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媒体依赖类型在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新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时,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媒介使用的影响将减弱;
H2b:媒体依赖类型在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新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时,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媒介使用的影响将减弱;
H2c:媒体依赖类型在媒介使用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新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时,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媒介使用的影响将减弱。
三、数据分析
(一)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项目。CGSS2013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1438个。在模型检验时,经软件自动过滤缺失值后,最终剩余样本9880个。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为公众的垃圾分类行为,问卷中对应问项“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 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中具体行为的第一条:垃圾分类投放。对应的选项为:1=从不,2=偶尔,3=经常(-3=拒绝回答,-2=不知道,-1=不适用均被编码为缺失值)。
媒介使用在问卷中对应问项为“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媒介的分类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共6项,对应的选项为: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3=拒绝回答,-2=不知道,-1=不适用均被编码为缺失值)。数值编码不变,数值越大表明媒介使用越频繁。将所有媒介的使用频率求均值作为媒体使用变量的测量。
对媒介依赖类型的测量为“在以上媒体中,哪个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调查对象可以选择:1=报纸,2=杂志, 3=广播,4=电视, 5=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6=手机定制消息,本文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归为传统媒体,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与手机定制消息归为新媒体。具体而言,若填写记录为1至4,则将“媒介依赖类型”编码为0(即主要依赖传统媒体获取信息);若填写记录为5或6,则将“媒介依赖类型”编码为1(即主要依赖新媒体获取信息)。若在“过去一年,您对媒体的使用情况是”一题中对所有的媒体使用频率选择均为“从不”,则该题不适用,将其编码为缺失值。对该变量的描述统计显示,以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占比78.9%,而以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占比21.1%
CGSS2013问卷中包含对受访者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评估。问卷采用10道判断题对受访者的环境知识水平进行测量,具体包括:(1)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2)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3)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4)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5)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6)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7)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空气质量好;(8)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其中单数项的表述是错误的,而双数项的表述是正确的。受访者依据自身知识水平对这些表述进行判断,选项包括:正确、错误、不知道。本研究根据表述的实际正误重新编码,将实际判断正确编码为1,而将实际判断错误或不知道编码为0。对各项进行加总,作为环境知识变量的测量。
对环境风险感知的测量对应的问题是“以下各类环境问题在您所在地区您是否知道?”,具体包括12个选项:(1)空气污染;(2)水污染;(3)噪音污染;(4)工业垃圾污染;(5)生活垃圾污染;(6)绿地不足;(7)森林植被破坏;(8)耕地质量退化;(9)淡水资源短缺;(10)食品污染;(11)荒漠化;(12)野生动植物减少。受访者选择:1=知道,2=不知道,本研究将不知道重新编码为0(-3=拒绝回答,-2=不知道,-1=不适用均被编码为缺失值),将这12个问项全部加总作为受访者的环境风险感知的测量。
(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本研究利用方杰等人推荐的中介效应检验的新方法——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8]在具体检验工具和操作方法方面,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PCOCESS插件。[29]选择模型8,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是否为城镇居民、地域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条件下,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在媒介使用及垃圾分类行为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检验媒介依赖类型在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如表2所示,回归分析表明,媒介使用可以正向显著影响人们的环境知识(β=0.741,p<0.001,CI=[0.6460.836])及环境风险感知(β=1.074,p<0.001,CI=[0.9331.214]),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也有直接的正向显著影响(β=0.110,p<0.001,CI=[0.0820.139]),环境知识(β=0.028 ,p<0.001,CI=[0.0220.034])及环境风险(β=0.009 ,p<0.001,CI=[0.0050.013])对垃圾分类行为同样有正向影响,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同时,媒介使用与媒介依赖类型的交互项能显著影响环境知识(β=-0.3874,p<0.001,CI=[-0.576-0.199])及环境风险感知(β=-0.963,p<0.001,CI=[-1.242-0.684]),但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β=0.023,p=0.413,CI=[-0.0320.078])。媒介依赖类型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均为负向。将媒体使用按照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分为低频率媒体使用与高频率媒体使用,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画出调节作用示意图(图2 图2见本期第60页)。
由于本研究中,媒介依赖类型(调节变量)通过影响环境知识(中介变量)与环境风险感知(中介变量),调节媒介使用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分析媒介依赖类型的调节作用,建立95%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不同媒介依赖类型(新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和传统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的条件下,媒体使用通过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显著性。2000次Bootstrap抽样的检验结果如(表3 表3见本期第60页)所示。
结果表明,在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无论是环境知识还是环境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媒体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即在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时,媒介使用可以通过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着正向的影响。但在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情况下,环境知识作为中介变量,媒体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而环境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媒体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包含0,即在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时,媒体使用可以通过环境知识的中介作用对垃圾分类行为有所影响,但无法通过环境风险感知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及媒介依赖类型的调节效应,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假设H1、H2a、H2b及假设H3b、H3c,但假设H3a没有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媒介使用除了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着直接效应之外,还能通过提高人们的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对人们的垃圾分类行为产生作用。并且人们的媒介依赖类型在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将新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会削减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但是在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效应方面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负向调节作用的验证在表面上看支持了本文在文献综述中所做出的推测,即传统媒体在促进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上要强于“个人定制化”更明显的新媒体,若确实如是,那么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依赖传统媒体为最主要信息来源者的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均当强于新媒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那些将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的环境知识均高于将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人,而对环境风险感知而言,仅当媒体使用频率较高时,以传统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才强于新媒体。在控制了各类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回归模型显示,媒介依赖类型变量的系数仍然为正值。因此依赖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削弱了媒介使用对环境知识及环境风险感知的作用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定制化信息”,也就是说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与桑斯坦的担忧相反。
这种负向调节作用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信息对人们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人们使用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时,其接触信息较少,媒介使用对人们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感知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但是当人们将新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时,信息过载的情况较容易发生,这时候媒介传递信息的功能及媒介效果开始减弱,然而总体而言,新媒体对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的信息传递作用和媒介效果仍然强于传统媒体;当媒介使用频率较高时,将传统媒体作为最主要信息来源的人的环境风险感知会强于新媒体,这有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相对于新媒体而言,对于环境风险有更多的强调,但在环境知识的传递上相对于新媒体这种富媒介缺乏优势。有学者指出,数字时代是一个内容丰裕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受众越来越根据自定义的“保留曲目”、经验法则和各种推荐机制来消费内容,“推送”媒体的特征被强化。[30]信息过载并不意味着信息的传播受到阻碍,新媒体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并且在如今,新媒体还可以通过社交、娱乐等方式向人们传递信息。
基于此,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对新媒体的作用持完全悲观态度,而同样应该通过新媒体向受众传递环境相关信息,以增进人们的环境知识,强化人们的风险感知,进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
此外,条件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当人们的最主要信息来源为传统媒体时,环境知识都存在中介效应;当人们的最主要信息来源为传统媒体时,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仍然存在,但当人们的最主要信息来源为新媒体时,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不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呈现环境相关内容存在差异,传统媒体在建构人们对环境风险的认识的同时,可能更多地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但是新媒体的内容更为碎片化,人们只能从中获知“风险”,却由于新媒体的内容引导不足而难以想到“我能做什么”。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注意新媒体上环境新闻等相关内容的表述,比如在告知公众环境风险的同时,加强对人们个人责任的宣传,以使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综上所述,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上起到了强化促进效果,除了直接效应之外,媒体使用还可以通过增加人们的环境知识和对环境风险的认识实现对人们垃圾分类行为的积极影响,并且媒介依赖类型不同,其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因此相关部门应当重视媒介在促进人们垃圾分类行为上的作用,并且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机制的不同之处。
虽然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及实践价值,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使用二手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在选择变量时有一定限制,例如媒介使用可能通过其他变量(如环境关心、环境意识、价值观等)的中介作用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但由于这些变量在CGSS2013数据中没有测量,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其次,由于科技的进步,从2013年至今媒介生态已经有了许多发展变化,而现有数据难以支持我们进行更多的探索和验证,这也是使用截面数据必然带来的缺憾,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自行设计问卷开展调查,更深入地探究媒介使用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对媒介形式产生的作用不同的个中原因进行更具体的讨论。■
①徐林、凌卯亮、卢昱杰:《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
②新华网:《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03/c_1124577181.htm,2019年6月3日
③人民网:《我国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606/c1001-31124586.html,2019年6月6日
④Anderson C ABerkowitz LDonnerstein Eet al. The influence of media violence on youth[J].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0034(3): 81-110.
⑤Bushman B JHuesmann L R.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violent media on aggression in children and adults[J].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06160(4): 348-352.
⑥Klein J DBrown J DDykers Cet al. Adolescents’ risky behavior and mass media use[J]. Pediatrics, 199392(1): 24-31.
⑦Prot SGentile D AAnderson C Aet al. Long-term relations among prosocial-media useempathyand prosocial behavior[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425(2): 358-368.
⑧王建明、吴龙昌:《亲环境行为研究中情感的类别、维度及其作用机理》,《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12期
⑨Stern P C. Towards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J]. 2000.
⑩Steg LVlek C. Encourag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929(3): 309-317.
[11]张萍、晋英杰:《大众媒介对我国城乡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2]Huang H. Media useenvironmental beliefsself-efficacy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69(6): 2206-2212.
[13]Lee K. The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of Hong Kong young consumers: The role of peer influencelocal environmental involvementand concret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201023(1): 21-44.
[14]Kollmuss AAgyeman J.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28(3): 239-260.
[15]石志恒、晋荣荣、慕宏杰、秦来寿:《基于媒介教育功能视角下农民亲环境行为研究——环境知识、价值观的中介效应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0期
[16]江根源:《媒介建构观:区别于媒介工具观的传播认识论》,《当代传播》2012年第3期
[17]McCallum D BHammond S LCovello V T. Communicating about environmental risks: how the public uses and perceives information sources[J].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199118(3): 349-361.
[18]Wakefield S E LElliott S J. Constructing the news: The role of local newspapers in 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355(2): 216-226.
[19]Zhao XLeiserowitz A AMaibach E Wet al. Attention to science/environment news positively predicts and attention to political news negatively predicts global warming risk perceptions and policy support[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61(4): 713-731.
[20]Lévy-Leboyer CBonnes MChase Jet al.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J]. European Psychologist, 19961(2): 123-129.
[21]周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与中国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22]Ho S SLiao YRosenthal S. Apply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media dependency theory: Predictors of publi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Singapore[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20159(1): 77-99.
[23]金恒江、余来辉、张国良:《媒介使用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24]卢春天、朱晓文:《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及行为适应——基于西北地区4省8县(区)的实证数据分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5]Ostman J. The influence of media use on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A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pproach[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20148(1): 92-109.
[26][美]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的民主问题》黄维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毛晓秋:《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自由国家还是自由市场》,《网络法律评论》第8卷,2007年
[28]方杰、张敏强、邱皓政.:《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回顾与展望》,《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1期
[29]Hayes A F. PROCESS: A versatile computational tool for observed variable mediation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modeling[J]. 2012.
[30]刘燕南:《数字时代的受众分析——〈注意力市场〉的解读与思考》,《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3期
艾鹏亚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武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