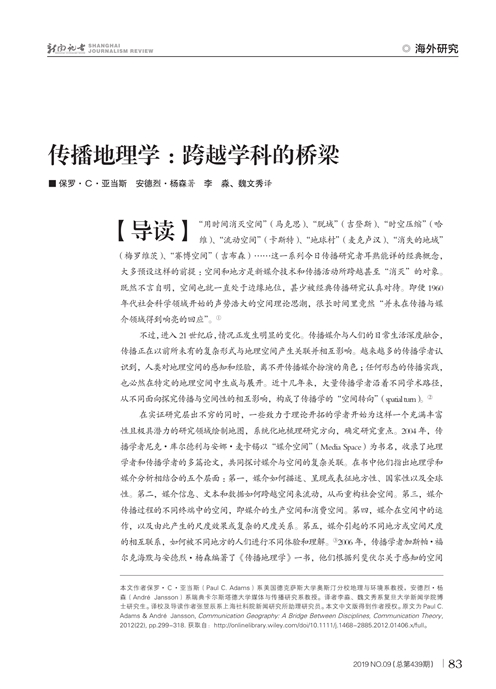传播地理学:跨越学科的桥梁
■保罗·C·亚当斯 安德烈·杨森著 李淼、魏文秀译
【导读】
“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脱域”(吉登斯)、“时空压缩”(哈维)、“流动空间”(卡斯特)、“地球村”(麦克卢汉)、“消失的地域”(梅罗维茨)、“赛博空间”(吉布森)……这一系列今日传播研究者耳熟能详的经典概念,大多预设这样的前提:空间和地方是新媒介技术和传播活动所跨越甚至“消灭”的对象。既然不言自明,空间也就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甚少被经典传播研究认真对待。即便196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的声势浩大的空间理论思潮,很长时间里竟然“并未在传播与媒介领域得到响亮的回应”。①
不过,进入21世纪后,情况正发生明显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传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式与地理空间产生关联并相互影响。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认识到,人类对地理空间的感知和经验,离不开传播媒介扮演的角色;任何形态的传播实践,也必然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生成与展开。近十几年来,大量传播学者沿着不同学术路径,从不同面向探究传播与空间性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传播学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②
在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的同时,一些致力于理论开拓的学者开始为这样一个充满丰富性且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绘制地图,系统化地梳理研究方向,确定研究重点。2004年,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利与安娜·麦卡锡以“媒介空间”(Media Space)为书名,收录了地理学者和传播学者的多篇论文,共同探讨媒介与空间的复杂关联。在书中他们指出地理学和媒介分析相结合的五个层面:第一,媒介如何描述、呈现或表征地方性、国家性以及全球性。第二,媒介信息、文本和数据如何跨越空间来流动,从而重构社会空间。第三,媒介传播过程的不同终端中的空间,即媒介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第四,媒介在空间中的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尺度效果或复杂的尺度关系。第五,媒介引起的不同地方或空间尺度的相互联系,如何被不同地方的人们进行不同体验和理解。③2006年,传播学者加斯帕·福尔克海默与安德烈·杨森编著了《传播地理学》一书,他们根据列斐伏尔关于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勾勒出把传播媒介研究与地理学研究结合的三种方式,并指出传播地理学作为跨学科领域已经形成。④
传播地理学的形成绝对不是传播学的一厢情愿。早在传播学空间转向之前,地理学早已积极接受和吸纳来自传播学科的知识。1998年,《人文地理学进展》刊登了传播学者肯·希利斯的文章,鼓励地理学者关注“地理学中不可见的传播”。此后,在线地理学期刊Aether创刊,发表了不少重要地理学者的论文;“国际地理联合会”(IGU)设立了“全球信息社会的地理学”(Geography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小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成立了“媒介与传播地理学”(Media and Communication Geography)专业研究团队。如今,几乎所有地理学主流英文期刊都可以见到涉及传播与媒介议题的论文。2009年,曾师从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并深受麦克卢汉影响的地理学家保罗·C·亚当斯更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批判的导论》(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指出地理学中的“传播转向”(communicational turn)。他将空间与地方的区分作为一个轴,以编码/表征与空间组织的区分为另一个轴,构造出传播地理学的四大子领域:空间中的媒介、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媒介中的空间。2011年,亚当斯发表A Taxonomy for Communication Geography,在吸收拉图尔等人理论的基础上,对之前的四大路径进行了补充,即使用混杂性、转译、行动者网络等概念来超越地方与空间、内容与情境的二元对立的第五条路径。
从前述背景看,本期《新闻记者》发表的这篇译文,某种程度上也是传播地理学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说在这篇文章里对四大主题的分析延续着亚当斯的思路,那么对一系列媒介技术变化趋势的分析则明显更多来自于杨森的贡献。两位作者率先垂范,鼓励不同学科学者打破学科藩篱,共同面对中介化/媒介化的移动性、技术融合、交互性、新型交互界面以及监控的自动化等新趋势,并积极介入再现、纹理、结构和关联等议题的研究之中。对于试图了解传播地理学的研究者而言,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深入浅出的知识地图。
近年来,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紧密合作,正在让传播地理学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2017与2018年保罗·C·亚当斯在《人文地理进展》期刊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 Metaphysics of encounter 和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I: Arcs of Communication同样值得一读。在这两篇论文里,亚当斯指出了传播地理学的新范式——“遭遇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encounter),该范式采用流动(flow)与生成(becoming)视角,将传播视为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遭遇(encounters),围绕着表演、能动性、物质性、非物质性、网络、政治、情感等议题,探究作为遭遇的传播对参与者的影响。他还借鉴了景观研究和地理人文(geohumanities)的研究成果,以乔治·雷维尔的“声音之弧”(arc of sound)概念为基础,发展出“传播之弧”(arc of communication)的概念。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前沿领域,传播地理学绝不仅仅是学科间策略性的联盟,它已经并还将继续为更新传播学和地理学现有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张昱辰)
①孙玮:《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四辑)导言》,《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FalkheimerJ. & JanssonA. (2006).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Goteborg: Nordicom.
③Couldry, N.&McCarthyA. (2004).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④FalkheimerJ. & JanssonA. (2006).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Goteborg: Nordicom.
【本文提要】我们呼吁对地理学和媒介/传播研究范式进行彻底重构,从而在两个学科的核心关注点之间搭建桥梁。这一尝试构成了对若干当代历史变迁的回应:中介化/媒介化(mediated/mediatized)的移动性、技术融合、交互性、新型交互界面以及监控的自动化。对诸如再现、纹理、结构和关联等议题的长期关注为搭建跨学科桥梁奠定了基础。将这些议题整合起来将产生一个半自治领域,这个领域将通过地理学者和媒介理论学者的合作得以展现。
【关键词】中介化/媒介化的移动性 技术融合 交互性 新型交互界面 监控的自动化
【中图分类号】G231
学科常常占据着一定的领域,而跨学科活动则构成了位于、围绕和僭越这些学科边界所展开的秘密运动。常见的跨学科情形是两个学科共享同一边界,在此经由多年的广泛互动、借用及交换创造了一个被正式确认的接触带,例如天体物理学、生物化学和心理生理学等。在另一些情况下,跨学科邂逅来自对未知的探索: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同时潜入同一个未知的领地,在这个彼此陌生的地带发生接触。20世纪中期,控制论(cybernetic theory)引发了来自工程学、生物学、博弈论与逻辑学的探索者在边界上的交锋。第三种类型的跨学科产生于这样的时刻:一个学科内部的发展推动学者们探究其他学科“占有”的话题,于是一个学科“侵入”另一学科的“势力范围”。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便是如此,它让数学与以往为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及人文地理学者探究和主导的社会组织议题之间产生关联。最终,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各自“心脏地带”之间搭起桥梁,连接彼此核心的认识论与本体论议题。这种跨学科研究会发生在两个并不相邻甚至相距甚远的学科之间。
本文旨在在地理学和传播学的核心议题之间搭起如此这般的桥梁。这两个学科并非“邻居”,它们既没有相近的学科主题,也没有共享的方法论基础。即便如此,媒介研究文献中出现了探索传播理论 “空间转向”的《传播地理学》(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①一书,而地理学文献中出现了强调地理学的文化或“传播”(communicational)转向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②这些作品不仅探究了两个学科都日益感兴趣的空间——传播关系话题,同时也说明两个学科的研究范式需要更为根本性的重构。正如福克海默和杨森所言,媒介和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将带来空间模糊性(尤其从全球化角度看)的技术与文化的过程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③与此同时,地理学掌握着诸多理解空间复杂性的理论关键,在今天媒介化的世界中,这种复杂性表现出令人惊奇的碎片化、多重化和分层化特征。
到目前为止,这些跨学科“转向”只是含蓄地涉及了“传播地理学”的研究议程。地理学者首要关注的是传播在不同尺度上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实施与合法化中所扮演的角色,④抑或关注在新传播技术背景下,距离、空间、可达(及)性和移动性等地理学基础概念可能包含的意义。⑤关于赛博空间和计算机编码的地理学研究已经部分地集合了这些兴趣点。⑥
传播学者从三个广阔的领域为“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首先,已经存在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学视角的媒介研究领域,关注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探索中介化传播中的仪式性、述行性(performative)、经验性与共享性元素,⑦近年来则常聚焦于跨国关系研究。⑧其次,传播学中研究空间(特别是城市)的物质的与再现的生产之分支——明确地扩大了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边界。⑨第三,还有研究立足更宏观的视角,探究媒介作为地缘政治、象征性权力与支配机器的角色,尤其是在全球尺度上以及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媒介如何扮演此角色。⑩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偏向传播的地理学者通常在国家、资本等大尺度上理解权力;而传播理论学者在更大程度上会在本地化和再现的路径上构想权力,[11]对社会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联更为敏感,而且揭示出权力与多重地理尺度发生微妙关系的潜能。[12]这并非说地理学家未能意识到微观尺度的理论,如米歇尔·福柯、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德·赛图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但地理学家们首先将这些理论家的作品改编以适应再现和表现的集体活动,以阻碍和干扰主导性/支配性群体之传播。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仍然是空间和地方。[13] “地方”这一概念保留了深植于本地环境和话语的特性之上的主体性经验,而“空间”则意味着身体、商品、资本、信息与传播可能发生的和实际发生的运动。
在以上的学术成果之后,我们希望构筑桥梁,将传播理论中核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议题与来自地理学的广阔视野相连接(反之亦然)。传播地理学的潜力不仅在于其提供了“作为空间生产的传播”这一过程性的观点,还在于其坚持用复杂的视角观照空间和空间过程,认为它们既由一般性的传播活动和特定的中介化实践所生产,同时也生产出后者。[14]虽然一些学者——最著名的当属大卫·莫利——已在进行类似研究,但我们认为概念性体系仍显欠缺,同时后续研究不能只是开疆拓土,还应对已经开拓的领域、其构成元素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展开分析。
我们聚焦于“传播地理学”这一新兴的子领域,试图在两个学科之间建立桥梁,但并不排除它们与其他相关学科及领域的关联,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等。然而,尽管这些学科为传播地理学研究议程提供了重要主题与洞见(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强调其中的一些),但它们超出了这里元理论分析的范畴。我们也相信,在传播学和地理学核心之间搭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桥梁,或许可以调和文化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边界之争。[15]这些边界之争时常或明显或隐晦地关乎尺度(scale)问题:即应将焦点放在宏观的、远处的问题之上,还是放在微观的、近处的问题之上。传播地理学的思想恰恰能够为辨明这种争论提供启示。地理学者们已经指出——例如在有关性别和权力的问题上——尺度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建构而非给定的东西。[16]由此,与其争论电视究竟是再现着世界还是改变着客厅,不如认识到这两个过程都十分重要,并且紧密关联,将会更加富有成效。[17]为厘清传播地理学的研究议程,我们将总结传播与地理研究最近共同关注的新趋势,然后探讨构成传播地理学分支领域的更持久性的议题。
一、新趋势
近年来一些新现象的出现使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也使媒介理论学者开始讨论地理问题,这正说明迫切需要在地理学与传播/媒介理论学科间搭建桥梁。虽然传播与空间过程的交叠特征与相互依赖,以及学界对此关系的关注并非新鲜之事,[18]但是,当下地理学的传播转向与传播学的地理转向(“转向”一词本身具有高度空间性的隐喻)缘起于明显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些转变与网络化数字媒介的新兴状态密切相关,这些状态包括中介化/媒介化(mediated/mediatized)的移动性、技术融合、交互性、新型交互界面以及监控的自动化。本文将依次对它们进行介绍。
1.中介化/媒介化的移动性(Mediated/mediatized mobility)
中介化/媒介化移动性指的是被一系列技术和相关的实践所增强和改变的运动。中介化与媒介化的区别十分复杂且存在争议。[19]在此这两者都极其重要,并且必须被视为是相互依存的。简单来说,中介化是指通过空间移动或传递特定内容的过程,媒介化描述的是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20]在这个过程中总体的空间实践(特别是移动性)变得越来越依赖不断扩展的中介化技术和体系。这些中介化技术和体系包括高度便携式音乐系统(如iPod)、无线上网技术、支持定位与导航的GPS系统,以及这些技术的不断整合/融合。每一种技术承载着不同功能,但都使得中介化与媒介化过程相继展开。处于支配地位的媒介化元过程,甚至可以被视为移动性与中介化的复杂缠绕。例如便携式音乐系统就提供了一种脱离周围环境的感觉模式,使得人们可以在移动过程中沉浸于源自另一时空的刺激流中。无线上网技术使人们在空间活动中保持随时可及,由此支持两种同时发生又分离的同世界的互动模式——感官的互动以及身体的互动。GPS技术提供了关于一个人的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的信息,不仅将人置于地图之上,还使得数字“地图”成为关于人之身体真实和潜在位置信息的接入口。
这些正在进行的变化同时意味着移动性的媒介化与媒介实践的移动化,这也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另一(可能是跨学科的)“转向”,即社会学的“移动性转向”(mobilities turn)形成共鸣。[21]移动性转向已在媒介与传播学[22]和地理学[23]中被概念化。显然,跨学科的传播地理学需要参与这一所谓的新移动性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的批判性对话。该范式强调身体、物品、观念与资本的流动,并同时提出流动的阻塞、排除和中断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等问题。媒介地理学与新移动性范式的交叉显而易见,在其中媒介成了:为不同的“流”设定时间节点和节奏的手段;构成异质性组合的元素;区域化和去区域化进程的驱动力量;启动和维系“流”的社会关系背后的支撑。[24]2.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技术融合意味着媒介间边界的消融,它让文本脱离了特定中介化语境,将它们转化为由多种媒介构成的网络中的节点。不同媒介之间的转译越来越频繁。我们越来越无法确定:电影、电视节目与电子游戏,究竟谁是谁的衍生品?一部小说究竟是独立的创作,还是仅仅作为电影与电视改编的前奏?一幅图像究竟是具有原始格式,还是由定制成不同格式的无限多的相关演绎所构成的?正如詹金斯所认为,融合不仅是技术变迁,还“改变了既有的技术、产业、市场、体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整个媒介产业与媒介实践,尤其是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生产和消费。[25]融合过程致使传播文本和语境与过去相比更为不稳定,两者的关联更为松散,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更加模糊。文本不必依赖媒介而存在,它可以成为自身的载体。Web 2.0时代的公众参与和“混搭”创造极大推动了技术融合,也为特定种类的创新提供了空间。[26]这种创新使作者成为问题,构成了对媒介与传播研究的挑战;同时也使创作或写作成为问题,构成了对地理学的挑战。
3.交互性(Interactivity)
交互性是一个复杂且颇具争议性的概念。[27]现在,交互性逐渐以动态文本关系取代了固定、预先设定的文本。在媒介与文化研究中,“用户生产力”、参与和阐释议题已经被讨论了数十年,特别是在流行文化中。[28]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本处于持续建构中,交互性逻辑激发了一连串新的空间条件。这一动力进一步将作者身份从特定时刻剥离,作者在社会空间中的多重性位置取代了原先的中心位置。新型交互媒介包括:玩家分散在不同空间的多人游戏,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交网络,“快闪”(及其他在线形式的政治动员),个性化娱乐产品与博客的小范围传播。许多网络报纸在新闻下方设有评论区,有些设置成树形结构,允许用户对已有评论再评论。[29]这些形式使来自各大洲的参与者可展开持续的讨论。[30]媒介越来越依据交互类型,而非根据文本传输系统和相关文本的集合来定义。
4.交互界面(Interfaces)
交互界面一端连接人类心理、知觉与运动系统,另一端连接代码、软件与硬件。键盘虽然陈旧过时、设计笨拙,但是它仍是一种重要的人机界面,不过它正在逐渐被更自然的界面所补充和改进。例如鼠标是通过在水平面上的几何学移动操纵在屏幕中的移动,而不是反复敲击随机指定的按键。当然,所有界面必然是人造的,但有些界面已十分接近人际互动时以及人在物理环境操控中的运动、知觉与表达方式。机器-人类界面和人类-机器界面都在进化,同时机器之间、人际之间的联动装置也在进化。鉴于界面是介于特定地点与传播基础设施之间的中间领域,界面的进化反过来又催生了“空间”与“地方”的新构造与交集。类似地,声音识别系统与文本-语音合成器成为技术系统与人之间新型语音界面的补充。
一些界面更接近身体,而另一些更接近机器。符合前者的例子是人工耳蜗,人工耳蜗通过麦克风捕捉声音并将其转化为电子信号,然后通过耳蜗将信号传到一套最多达24个电极的系统之中来重塑聋人的听觉功能。符合后者的例子是菜单驱动的引导式电话,将电话使用者联通到提前录好的回复或接线员处。前一种情况是,在身体中嵌入机器以协助沟通;后一种情况是机器作为一种廉价的、半功能性的人际沟通替代品来使用。介于这种接触界面和远程界面之间的是免提导航和控制系统,多用于军事和民用设备中,这一类通讯的发展近来成为社会学范式媒介研究的考察对象。然而,当我们学习以新方式讲话与倾听时,当软件越来越能够适应用户特性时,“近端”和“远端”界面的分界模糊了。我们越来越发现自身正在适应那些具有自我回应性和调节性的设备,如迅猛发展的“智能手机”,以致学习成为分布在传播系统中人类与非人类元素之间的任务。
5.监控的自动化(Automated surveillance)
传统社会的集体生活虽也涉及社会监控,但新形式的中介化监控极大地重构了日常生活——尤其在城市中。技术越来越多地用视觉化与数字化的方式记录城市空间中的踪迹,这些记录可以由计算机收集、核对、质询和随机访问,并被用于广告、营销、治安维护和政治劝服。应当注意到,监控的自动化与前文所述的交互性和技术融合的普及密切相关。用户生产数据或称capta [31]通过数字网络的多次转译在不同媒介之间流通,催生出有关隐私、时间与空间等社会实践的新权力系统。[32]这样,伴随着与数字传播密切关联的一系列新空间结构的诞生,监控呈现出全新样态。哈格蒂和埃里克森等学者[33]沿着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论述,用“装配”(assemblage)的概念阐述这种短暂结构形式,批判性理论学者则使用诸如“数字围场”(digital enclosure)[34]这样的空间隐喻来强调交互式监控如何催生社会隔离和商业剥削。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特别是Facebook)通过各种移动化监控手段(特别是上文提及的GPS系统)影响社会生活的纹理。例如,在一项网络定位服务的使用(现停止服务的Dodgeball公司)研究中,汉弗莱斯发现,在不同地点的惯例“打卡”强化了用户的自我监控,尤其是用户在社交圈中持续地信息曝光。[35]总而言之,在地理空间中曾十分清晰的公私分界逐步由虚拟空间中的密码和代码所取代,这一变化切实影响着人们的生活。[36]
二、持续性因素
上述种种新的情况向学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互动和共享跨过模糊的边界,形成新网络、拓扑结构和层结构的新方式,使得传播学经典的“传递模型(transmission model)”的线性以及“仪式模型(ritual model)”的社会语境都变得问题重重。 可是如果我们从诸如再现(representations)、纹理(textures)、结构(structures)和关联(connections)等更为持久的学科交叉点出发来思考,有关上述问题的思路就变得清晰起来。它们好像传播地理学宽阔的劈理(cleavage),[37]在劈理面上复杂的新媒体问题及其中模糊的地理学意涵都可清晰地显示出来(表1 表1见本期第89页)。这四个交叉点与“空间/地方”这一组相区别的概念有着根本性的关联,因而触及了地理学思想的核心。[38]再现和纹理与地方有关,结构和关联则占据并创造空间。这四个主题也与媒介/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程相关,而这个研究议程目前涉及两个非常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媒介内容及其使用,另一个是产业和政策驱动的过程。本文中提出的四象限模型帮助我们识别出各学科鲜有探索的领域,最终填补研究的空白。这并不是说这四部分将被视作并指定为相互独立或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相反,上文概述的发展不仅指明这些领域中的动态已经发生改变,而且让领域之间的分界变得问题重重。在一个象限中充当容器的东西,在另一个象限中变成了内容。尽管我们似乎不能视“容器/内容”为一种“错误的二元性(false duality)”,[39]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二元性中的元素会伴随着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框架更换位置。
1.再现(representations)
地方再现研究在传播学和地理学研究中都很常见,其研究焦点在于验证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是从传播活动中了解某个地方。这种情况对路途遥远或者难以到达的地方(如南极洲)特别明显,因为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语言再现或视觉再现间接地了解这些地方。对充满神话和象征意味的空间这种现象特别明显,例如欧洲视角之下的美国[41]或者月球。[42]在殖民时代,遥远地方的地方形象被调动起来以支持剥削和压迫;而直至今日,与此类似的“殖民地”想象仍继续塑造着跨国和跨地区的权力关系。[43]即便是关于自己的居住地点,一个人所知道的“此时此地”也仅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直接经验,而另一部分则依赖于中介化的在地存有方式(being-in-place)而获得——例如本地报纸、当地生产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张贴在墙上的海报,以及无数有关本地现状与事务的面对面的交谈。地理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他们不仅要意识到地方的物质性与象征性,还要了解仅仅凭借媒介呈现的模式化形象无法捕捉到地方的象征性意涵。每一个特殊地方的再现都具有偶然性和独特性,这不仅与权力有复杂的关联,[44]也与地方本身特性的关联同样复杂。
关于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再现的影响,最重要的趋势是交互性、便携性和可转译性的同步增进。日益完善的技术手段与地方形象的流动性互相调和。从电视屏幕的革新历程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趋势的发展,电视屏幕革新的一个方向是从黑白屏幕升级到彩色屏幕、大屏幕、高清屏幕,再到3D屏幕,另一个方向则是适用于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小尺寸、高清屏幕。图像逼真度的不断提升激活了现实主义的幻觉,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真实”仍处于争议之中。与漫画或者游戏等特定媒介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形象可以很容易地移植到诸如电影、电视、小说或者消费品等其他的媒介形式中。也就是说,通过多重转译“地方”在图书、电影、电脑游戏和T恤衫之间循环与流通。当地方形象在不同消费场合被消费或与身体相关联时,自我就被纳入这样的循环之中,并且和基于地理位置的自我身份表演居于同样的地位。地方总是通过参与建构起来的,但如今这种参与变得分层化,而且与媒介参与交织于一处,并且正如几十年前让·鲍德里亚的“超真实(hyperreality)”(1983)概念所预言的,虚拟和真实的边界已崩塌。
网站、旅游博客、专业化大众媒体,以及用于符号记录和流通的个人技术(特别是配有相机、导航和网络接口的智能手机),一起改变了游客对地方的感知、占用和再生产。[45]与此同时,像谷歌地图、Panoramio图片分享网站、Picasa网络相册等可公开访问的地图和数据库已成为大量附加了地理标记的图像资料库,这让它们可以链接到用户生产的评论和会话中。旅游、迁徙和流动总是依赖于先前的和现在的对地方的再现,但是新技术大大增加了这种再现的数量,并将其越来越多地与旅游交织在一起。即便在一个人的身体穿行于物理的、物质的空间中时,他依旧也徜徉于数量繁多的地方再现之中。
与此同时,在媒介再现记录和主题的影响之下,地方被重塑。[46]1970年代由地理学家爱德华·瑞尔夫提出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47]现象被继续扩大。地方的品牌推广活动不仅仅服务于旅游经济,而且试图把地方打造成吸引新商业和居民的磁石。[48]控制城市空间的斗争是通过符号经济进行的:地方看上去是独特的时候,它们也就更有发展价值,这种独特性又会利用文化多元性,但是文化工业推销的多元性(在所有意义上)会被发展所消费。那些一开始标榜着“多元”的地方自然可以继续凭借其多元性在服务业中获利,但是无中介的地方意义因此也会变得更加脆弱。[49]并非所有关于地方扩展的中介化都呈现如此暗淡的景致。通过融入参与性的城市规划,电影和录像成为培育社区会话的新方式。[50]与本地相关的设计和规划可依赖于新媒体与旧媒体的混合,例如讲故事。[51]即使是在全球市场的生产领域,地方也不仅仅意味着位置:“伦敦剧院、纳什维尔音乐、丹麦家具或者卡尔塔吉龙的陶器都不仅是一般的剧院、影片、音乐、家具和陶器,它们用自身的方式真诚表达着过往的荣光。” [52]总之,由于媒介的进化,地方再现不但变得更擅长愚弄感官、在媒介之间迁移,并随着观察者/使用者的身体一起运动,而且这种趋势持续地以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方式重构人与人之间、人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
2.纹理(textures)
最新的观察结果表明,如果说地方“附着”于媒介是对的,那么反之说媒介附着于地方也是对的。接下来要做的是辨识媒介充当地方关键要素的方式。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把地方视为由边界(例如建筑外墙、环绕公园的街道)所包围的区域,而应当将其看作一种特别的“纹理”。纹理这个词提醒我们地方是由传播编织而成的。地方以纹理的方式而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片领地或容积),因为地方承载着生活——平凡的日子、非凡的事件、日常的交集等,总之是构成与认知生活之交织混合编织特征的有意义的交流。这种构造过程被体验为一种可能性的领域:地方与让某些传播方式兼容的实践得以可能,也让与另外一些传播方式不太兼容的实践不再可能。不同地方的传播-关系有着系统性的差异,并与它们嵌入的更广泛的结构(如某种符号、制度规则及资源)产生关联,这就好像不同的纺织品有着不同的织法和颜色,呈现出来的整体纹理也不同。因此,我们建议研究者不能仅仅将地方看作传播的容器,还应当看到地方几乎就是用相互交叉的一段段传播线索编织起来的。
如果我们对媒介的理解超越了单一的技术层面,那么地方本身也是一种媒介,因为地方聚集、容纳、删除并再收集那些集体记忆。[53]正如通金斯所说,“即便现在人们脑海中所想象的公共领域是一种中介化联结(通过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在地集会仍然是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54]杨森提出“纹理分析”(textural analysis)的概念,用以分析地方中的传播模式是如何制定和协商的。[55]亚当斯、赫尔舍(和蒂尔)也将“地方纹理”视作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56]对传播理论而言,如此言说的世界不仅暗示了其空间转向,也暗指了其物质转向,目标是将传播视为本质上贴近现实的(grounded)、具身的(embodied) 、情境化(situated)的视角。[57]语言、视觉、听觉、触觉、姿态,甚至嗅觉和味觉,都是传播的方式,而在许多地方,都会出现支持某些传播方式而贬抑另一些传播方式的情况。例如,现代客厅里的电视机和立体音响使这里成为家庭聚会的场所。通常在一起看电视的是一家人,而在一起吃饭的却不一定是。[58]充斥着现代百货商店的不是气味,而是形形色色的、用来吸引潜在购买者的产品标签、文字和图片,选中的商品被放到连接着包含价格和最新仓储信息的远程数据库的机器那里扫描,接下来刷借记卡或者贷记卡购买——这都是机器和机器之间的通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的帮助,消费者甚至可以看到包装内部的产品或者通过对外文翻译获得产品信息。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新媒体如何作为一种“扩大装置”,日益与我们“真实的”日常地方相互交织不可分割。这些空间的、时间的连接将地方展示为一系列正在发生和持续变化的传播实践,这些传播实践连接着形形色色、不断变化的大批人类和非人类“发送者”和“接收者”。这一切都指向正在发生的(再)纹理化过程,而媒介和传播对于其生成和导向是必不可少的。
新媒体界面如今也被应用在城市生活中,地方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已经开始能够回应居住者们的指令。汽车内部就是一种地方,当然是一种小型的移动地方,在其中无声电脑界面让其可以对人类乘坐者的需求作出回应。似乎还没有对“可作回应的家”(responsive homes)的类似需求,但一旦人们开始习惯于对自己的汽车发号施令,“环绕智能”与“遍在软件”可能会统治人类未来的居所。[59]地方,特别是居所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持私密性。但是由于传播技术的渗透,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地方的私密性功能被削弱。[60]电视的扩散重新界定了私人空间,因为电视把公共议题带入了私密场所。[61]监控摄像头把公共空间变得透明了,普通市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适应自己的行为暴露在监控之下。如果这种变化预示着不论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个人隐私都有所损失,它所带来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移动化媒体(例如手机)的好处之一是它能够发出求助信号,这增加了不同环境的安全性和可控性(或者至少增加了安全感和控制感)。通过将更精确的定位信息与远程数据库相连,智能手机或其他“位置性媒介(locative media)”扩大了自我监控的功能。通过提供空间信息及非空间信息,这类设备便利了人们穿越地方以及往来于地方之间。“物理空间实际上变成了信息的界面,而信息变成了物理空间的界面”。[62]同时,当人们穿过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或相对而言的公共与私人空间)时,移动化媒介还提供了与基于家庭的数据之间持续的、潜在的连接。因此,移动不再与“进入”和“离开”有着同样的关联,媒介化以一种彻底的、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传播和地方成倍扩大了。总之,纹理的连接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其经由媒介化的演进给隐私、移动性、个人权力和安全性问题带来相当多的影响。
3.结构(structures)
地理学界已有的研究关注固定的通讯基础设施。每一种基础设施系统的“足迹”都可以在地理空间被绘制,无论是通讯卫星[63]、光纤[64]、图书出版商,还是其他媒介。关于不同地方的相对重要性或核心功能,媒介基础设施地图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东西。这些空间模式被描述为链接和节点、渗透的密度,以及限制接入的边界,所有这些共同将相对的互动空间置于绝对的地图空间之内。在这里,传播被理解为频道或渠道,或更微妙地被理解为半固定的流动模式。这一观点补充了那些强调纹理、再现和关联的研究。由远程通讯市场构建起来的不均匀流动模式是全球传播地理的基本要素之一。文化产品就生产地和生产内容而言高度本地化和专业化,但是我们无法简单地绘制一张创意原产地的地图,因为“创造性的领域是由一系列活跃的要素组成的,因而创意的所有权是多重且复杂的”。[65]一旦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使传播流得以可能的空间结构,就会遇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其基础设施的发展更迅速、更剧烈。不均衡发展存在于所有尺度:在发达国家和所谓的“南半球”之间,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一个国家的发达省份和落后省份之间,在世界性城市和特大城市之间,在高科技增长中心和衰落的工业地带之间,甚至在每一座城市中富裕和贫穷的地区之间。这是一个循环,当权力和财富资源被调动起来,各种尺度上传播设施的集中化也随之而来,这些集中化反过来又带来了某种以更快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具有活力的政治和文化为特征的优势。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富裕的地方越来越富,有人脉的人脉越来越广,相对的,其他的地方或人则处于停滞的状态。[66]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呈现出美国中心模式:规模经济和自由市场政策更有利于美国的媒体公司而非其他国家的媒体公司,[67]也有利于好莱坞而非美国的其他地方。[68]尽管恶性循环使得传播资源的有产者和无产者被固化,但一些地区已经能够通过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来实现跨越发展。手机在非洲的爆炸式扩散就是一个例子。[69]地理学家对媒介兴趣的增加,以及传播学者对空间关系的新兴趣,这两方面共同显示出传播空间结构最重要的转变仍然是中介化/媒介化的移动性的激增。专有名称反映了传播设施某种特定的空间结构:“手机”(cell phone)这个术语在美国的使用令人想到手机信号的捕获和传递是通过安装在“蜂巢”(cells)里的天线或天线塔实现的,“蜂巢”被数百种频率的电波信号覆盖,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就可以互相通信。所以,城市被分成一个个肉眼看不到的六边形单元格,好像蜂巢一般。硬件和软件共同构成的复杂混合体让人们通过不同的蜂巢时通话可以持续,通过天线对话得以自动传递。充满悖论的是,空间的蜂窝化分割反而带来了流动和移动性。
中介化/媒介化的移动性还包括手持设备的优化,进而涵盖促进移动性的各种特性。当GPS数据和远端地理数据库相结合,纹理和结构产生交集,使人们可以搜索附近的餐馆、公交站台,甚至订购巴士票或其他便利通行的文件。不同媒介融合形成了一个混杂的空间结构:有移动电话,有GPS卫星,有互联网,还有远程数据库。人们在家中、公司或者旅途中访问Twitter、Facebook 等在线社区证明了其他混杂空间的存在。在拥有网络资本(network capital)[70]、可以自由地移动并连接的人与缺乏这些资本和能力的人之间,我们还可以识别出新的媒介化权力的几何结构(mediatized power geometries)、物质不平等(material inequalities)以及象征性区别(symbolic distinctions)。
4.关联(connections)
“虚拟”一词的爆炸式使用与互联网的产生相伴随。诸如“虚拟空间”、“虚拟地方”、“虚拟环境”的短语表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有一些全新的特点。从那时起,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渐渐为人所熟悉,甚至习以为常,“虚拟”的魅力也消散了。[71]归于平静后回过头来,人们开始对虚拟的基本假设进行更具批判性、分析性和历史性的思考。最根本性的判断是:一种空间是由中介化传播所创造,为中介化传播而生,并与中介化传播相连接。我们可以在经典作品中找到关于此的最初洞见。巴什拉的“空间诗学(poetics of space)” [72]、列斐伏尔的有关生活空间(lived space)和再现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的概念,[73]把我们引向了空间结构虚构和想象又十分平凡的维度,以及既坚实具体又转瞬即逝的维度。但是,由节点和链接构成的“虚拟空间”并不是纯粹想象的;它们的内部动态是由链接和节点之间的特殊排列所维持的拓扑关系塑造的。[74]伴随着学界对虚拟性兴趣的增长,研究者开始关注中介化的关联是以何种方式、如何形成特定的网络拓扑结构,进而支撑着特定类型的虚拟空间的。这是我们所设想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第四个主要领域,它仍然是一个甚少被探索的领域,因此开展重要的概念创新和经验研究恰逢其时。
尽管关于虚拟性已经有一些更具开拓性的探究,[75]地理学家们还是时常提醒读者传播者是在地的(in-place),还总结出地理上集中化和不均衡的持续模式。[76]这些回应多少有点拐弯抹角,因为很少有媒介/传播学者认为地方差异性真的会因新技术而消失。学者对虚拟的著述揭示了我们熟悉的地理关系之外的新型替代性空间的创建,也普遍不再坚持用虚拟空间超越地理空间。[77]即使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也不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远程分享观点和认同并不需要依赖缓慢的、剥离了感官的书写文字媒介。鉴于此,“空间”显然可被视作机会与期待结构,以及结构化的连接系统。通过互联网和“私有的数字空间”(例如,用作支持跨国交易的装备防火墙的连接),新媒体支持着新的拓扑空间层,它构于地理空间之上,或与地理空间平行。[78]在这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进程同时展开。[79]更为复杂的是,它一方面加速了经济权力向一小撮跨国投资者集中的过程,一方面又为争取政治权力去中心化的民众运动提供了新机遇。[80]早期互联网研究人员对“虚拟”的迷恋无疑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尽管如此,空间的机会结构受到了这一隐喻有效的激发,隐喻思维无疑是有某种益处的。因此,“虚拟地方”这一天才的表达概括了由网络化计算创造出的新机会结构的想法,我们很快就对这个新结构习以为常了。如果我们拆解“虚拟”这个词语,就会发现其中的言外之意:不需要在空间上邻近就可以发生的人际交往、不需要符号和标志就可以进行的再现、远程的即时互动、将数据转译成三维模型的潜能。所有这些观念都指向了多重的新型数字空间的发展,这些空间补充了旧欧几里得空间并与之互动。马丁·道奇和罗伯·基钦对某些此类空间进行了有趣的勘察和分析。[81]凯恩·希利斯的研究显示,占领网络空间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仪式。[82]因此,网络革命[83]早期出现的“虚拟”狂热错误的程度并没有像地理学家通常所断言的那么严重。它反映了新媒体的本质的互动特性以及此种互动性对人类主体性所产生的影响,还反映了从地理学所谓的“量化革命”得出的更微妙的见解——空间是任何组织化了的关系系统。如果关于“虚拟”的学术探索是不完整的、非历史性的,那么我们需要重返这一议题进而填补漏洞,而非绕路而行。
三、前景和展望
本文所述的想法确实可能是由地理学者与媒介理论学者分别提出并且各自进行的。但是,通过地理学者和媒介学者的合作,更大的协同优势将在一个半自治的领域里形成。[84]跨学科合作必定要付出代价,因为需要额外的时间与精力来整合并不相邻的两个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跨学科合作不仅要求双方扩大学科的边界,本质上还需要通过追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跃迁,在一个学科中心和另一个学科中心之间搭建桥梁,并在各自的学科中心之间建构通道,为概念建构与重构提供可能。这将需要对地理学进行一些根本性重估,以便充分识别从“空间”与“地方”角度看我们称之为“纹理”与“关联”的现象,以及地方形象与基础设施地理学的更新近的联系。就媒介与传播理论而言,则需要进一步解构和重构既有的分析类别(如文本和语境)以及空间嵌入过程(如分发和联网),进而将地理学上对空间和地方的充分理解视为传播动力学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现有工作对此起到关键性作用,但这一领域最好的研究必然同时熟稔媒介理论与地理学,大卫·莫利的著作便是最有力的证明。[85]从本体论上说,地理学者常常脚踏实地,维护物质世界的首要性。传播学者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由象征符号构成。然而离开了物质性的空间与地方,象征符号的传播多少存在问题。即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学者也比大多数地理学家更清醒地意识到传播的非物质性。地理学家们所受的精细训练主要集中在地图、投影图、边界、流动性、农业、工业、劳动力、住房等诸如此类的物质性议题上。与此同时,媒介与传播研究也有声音呼吁发展“唯物主义的、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86]通过与交通和移动性研究,以及和其他探讨信息社会不可避免的物质基础的研究领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观念将不断扩大“传播”概念的意涵。
布雷特·克里斯托普斯的观点十分正确,大部分基于“媒介地理学”的学术成果仍“受制于地方和全球、地方与空间、经济和文化、生产和分配/消费等的二元对立的观念”。[87]与其偏执一端,或者继续发展彼此分离脱节的路径,我们主张必须建立这样的目标,即以更加连贯的方式把二元论的两端带到一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采纳了一系列方法,我们还将相应地采用混合的方法,辅之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灵活性。例如,为了同时研究手机信号发射器的基础设施以及手机使用方式侵入私人空间的方式,可能有必要将空间分析与民族志方法相结合。克里斯托弗斯所批评的“二元论”确实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进行的纯化所导致的后果,而这是以牺牲更全面、更综合的视野为代价的。
媒介和传播研究的思路不可以避免地与地理学的思路存在差异,因为它们有不同的目标、研究对象以及出发点,但是在跨学科桥梁的两端,两个领域的问题是相似或相同的,合作带来的回报也是巨大的。尽管挑战十分严峻,但本文尝试起码为搭建一座亟需的跨学科桥梁提供一个脚手架。■
①FalkheimerJ.& JanssonA. (Eds.). (2006).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G¨oteborg, Sweden: Nordicom/G¨oteborg University.
②Adams, P. C. (2009).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③FalkheimerJ.& JanssonA. (Eds.). (2006).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p.9. Goteborg: Nordicom.
④BarnesT.& Duncan, J. (Eds.). (1992).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BurgessJ.& Gold, J. (Eds.). (1985). Geographythe media & popular culture. London, England: Croom Helm.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and the urban regional process. Oxford, England and CambridgeMA: Blackwell. ScottA. J. (2010). 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creative field of the cit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Human Geography92(2)115–130.
⑤Brunn, S.& Leinbach, T. (Eds.). (1991). Collapsing space and time: Geographic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London, England and Boston, MA: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JanelleD. G.& HodgeD. C. (Eds.). (2000). Informationplaceand cyberspace: Issues in accessibility. Berlin, Germany and New York, NY: Springer.
⑥Crang, M.Crang. P.&May, J. (Eds.). (1999). Virtual geographies: Bodies, space and relations.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DodgeM.& KitchinR. (2001). Mapping cyberspace.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KitchinR.& Dodge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MA: MIT Press. Zook, M. A. (2005). The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Venture capitaldot-comsand local knowledge. Malden, MA: Blackwell.
⑦Couldry, N.& McCarthy, A. (Eds.). (2004). 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Meyrowitz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England: Comedia. Thompson, J. B. (2011).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28(4)49–70.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England: Fontana.
⑧Andersson, M. (2008). The matter of media in transnational everyday life. In I. Rydin & U. Sj¨oberg (Eds.)Mediated crossroad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G¨oteborg, Sweden: Nordicom. ChristensenM.JanssonA.& ChristensenC. (Eds.). (2011). Online territories: Globalizationmediated practice and social spac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Georgiou, M. (2006). Diaspora, identity and the media: Diasporic transnationalism and mediated spatialities. CresskillNJ: Hampton Press. Hepp, A. (2009). Localities of diasporic communicative spaces: Material aspects of translocal mediated networking. Communication Review, 12(4)327–348. Moores, S.& Metykova, M. (2010). ‘I didn’t realize how attached I am’: On the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s of trans-European migrant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3(2)171–189. Morley, 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⑨BlumA. (2003). The imaginative structure of the city. Montreal, Quebec and Kingston, 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BoutrosA.& StrawW. (Eds.). (2010). Circulation and the city: Essays on urban culture. Montreal, Quebec: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JanssonA. (2005). Re-encoding the spectacle: Urban fatefulness and mediated stigmatization in the ‘City of Tomorrow’. Urban Studies42(10)1671–1691. JanssonA.& Lagerkvist, A. (Eds.). (2009). Strange spaces: Explorations into mediated obscurity. FarnhamEngland: Ashgate. McQuireS. (2008). The media city: Media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London, England: Sage.
⑩Couldry, N. (2003). Media rituals: A critical approach.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MattelartA. (2000). Networking the world 1794–20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arksL. (2005). Cultures in orbit: Satellites and the televisual. Durham, NC: Duke UP. Roosvall, A.& Salovaara-MoringI. (Eds.). (2010). Communicating the nation: National topographies of global media landscapes. GooteborgSweden: Nordicom.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2nd ed.).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Verso.
[11]Hall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England: Hutchinson.
[12]Morley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13]Tuan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4]Christensen, M.JanssonA.& ChristensenC. (Eds.). (2011). Online territories: Globalizationmediated practice and social spac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15]Morley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England: Comedia. Morley, 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Morley, D. (2007). Media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New York, NY and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16]Marston, S. A.JonesJ. P. III&WoodwardK. (2005). Human geography without scal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30: 416–432. Staeheli, L. (1994). Empowering political struggle: Spaces and scales of resistance. Political Geography13387–391.
[17]Couldry, N.& McCarthy, A. (Eds.). (2004). 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Massey, D. (1994). Spaceplace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8]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Ontari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lph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England: Pion.
[19]LundbyK. (2009). Mediatization: Conceptchangesconsequence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20]Krotz, F.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3(3)256–260.
[21]Sheller, M.& Urry, J.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8207–226.
[22]CroftsWiley, S. B.& Packer, J. (2010).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after the mobilities turn. Communication Review, 13(4)263–268.
[23]Cresswell, T. (2010). Towards a politics of mobi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817–31.
[24]Sheller, M.& Urry, J.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38207–226.
[25]Deuze, M. (2007). Media work. CambridgeEngland: Polity Press.
[26]Kitchin, R.& Dodge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pp. 111-134.MA: MIT Press.
[27]Abe, K. (2009). The myth of media interactivity: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in Japa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26(2–3)73–88. Andrejevic, M. (2007).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 Communication Review, 10(4)295–317.
[28]Fiske, J. (1989/2010). Reading the popular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Sandvoss, C. (2011). Fans online: Affective media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convergence. In M. ChristensenA. Jansson& C. Christensen (Eds.)Online territories: Globalizationmediated practice and social spac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29]Deuze, M. (2007). Media work. CambridgeEngland: Polity Press.
[30]Adams, P. C. (2007). Atlantic reverberations: French representations of a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dershotEngland and Burlington, pp. 167-205. VT: Ashgate.
[31]译者注:capta是“captured-data”的缩略形式,指出于一定目的通过具体数字设备与途径获取数据。
[32]Kitchin, R.& Dodge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MA: MIT Press.
[33]HaggertyK. D.& EricsonR. V. (2000). 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51605–622.
[34]AndrejevicM. (2007).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 Communication Review, 10(4)295–317.
[35]Humphreys, L. (2011).Who’s watching whom? A study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surveilla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1(4)575–595.
[36]Curry, M. (1998). Digital places: Living with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PicklesJ. (Ed.). (1995). Ground truth: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Thompson, J. B. (2011).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28(4)49–70.
[37]译者注:劈理(Cleavage)为地理学名词,指变形岩石中能使岩石沿一定方向劈开成无数薄片的面状构造,用于确定物质的运动方向。
[38]Adams, P. C. (2009).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AdamsP. C. (2011). A taxonomy for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35(1)37–57.
[39]de Souza e SilvaA.& SutkoD. M. (2011). Theorizing locative technologies through philosophi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2123–42.p.36. Hayles, N. K. (2000). The condition of virtuality. In P. Lunenfeld (Ed.)The digital dialectic: New essays on newmedia (pp. 68–95). CambridgeMA: MIT Press.
[40]Adams, P. C. (2009).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AdamsP. C. (2011). A taxonomy for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35(1)37–57.
[41]LagerkvistA. (2006). Terra (in)cognita: Mediated America as thirdspace experience. In Falkheimer, J. & A. Jansson (Eds.)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G¨oteborg, Sweden: Nordicom.
[42]Sloan, J. (2009). Modern moon rising: Imagining aerospace in early picture postcards. In A. Jansson & A. Lagerkvist (Eds.)Strange spaces: Explorations into mediated obscurity. FarnhamEngland: Ashgate.
[43]Gregory, D. (2004). The colonial present. Oxford,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Blackwell.
[44]Hall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England: Hutchinson.
[45]Jansson, A. (2007). A sense of tourism: New media and the dialectic of encapsulation/decapsulation. Tourist Studies7(1)5–24.
[46]Reijnders, S. (2010). Places of the imagination: An ethnography of the TV detective tour. Cultural Geographies17(1)37–52.
[47]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England: Pion.
[48]FalkheimerJ. (2006). When place images collide. In J. Falkheimer & A. Jansson (Eds.)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pp. 125–138). GooteborgSweden: Nordicom.
[49]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p. 286.MA: Blackwell.
[50]SandercockL. (2010). Multimedia explorations in urban policy and plann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next frontier. Dordrecht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51]SandercockL. (2003). Cosmopolis II: Mongrel cities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Continuum.
[52]Scott, A. J. (2010). 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creative field of the cit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Human Geography92(2)115–130.p. 124.
[53]AdenR. C.HanM. W.Norander, S.PfahlM. E.PollockT. P.Jr.& YoungS. L. (2009). Re-collection: A proposal for refining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its places. Communication Theory, 19311–336.
[54]Tonkiss, F. (2005). Space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 social relations and urban forms. Cambridgep. 68. England: Polity Press.
[55]Jansson, A. (2006). Textural analysis: Materialising media space. In J. Falkheimer, & A. Jansson (Eds.)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pp. 87–103). GooteborgSweden: Nordicom.
[56]Adams, P. C.HoelscherS.& Till, K. E. (Eds.). (2001). Textures of place: Exploring humanist geograph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57]Jansson, A. (2006). Textural analysis: Materialising media space. In J. Falkheimer, & A. Jansson (Eds.)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pp. 87–103). GooteborgSweden: Nordicom. Morley, D. (2009). For a materialist 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10(1)114–116.
[58]Morley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59]Kitchin, R.& Dodge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p. 221. CambridgeMA: MIT Press.
[60]ThompsonJ. B. (2011).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28(4)49–70.
[61]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2]de Souza e SilvaA.& SutkoD. M. (2011). Theorizing locative technologies through philosophi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2123–42.p. 31.
[63]Parks, L. (2005). Cultures in orbit: Satellites and the televisual. Durham, NC: Duke UP.
[64]TownsendA. M. (2001).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network cities, 1969–1999.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839–58.
[65]Scott, A. J. (2010). 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creative field of the cit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Human Geography92(2)115–130.
[66]Castells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MA: Blackwell. Harvey, D. (2001).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Englan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2006). Territoryauthority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7]ChristophersB. (2009). Envisioning media power: On capital and geographies of televis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Lexington Books.
[68]Storper, M.& Christopherson, S. (1987).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The case of the U.S.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77(1)104–117.
[69]Comer, J. C.& WikleT. A. (2008).Worldwide diffusion of the cellular telephone1995–2005.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0(2)252–269.
[70]UrryJ. (2007). Mobilities. CambridgeEngland: Polity Press.
[71]Mosco, V. (2006).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MA: MIT Press.
[72]Bachelard, G. (1994).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73]Lefebvre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Blackwell.
[74]Adams, P. C. (1998). Network topologies and virtual pla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88(1)88–106.
[75]HillisK. (1999). Digital sensations: Spaceidentity, and embodiment in virtual real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hieldsR. (2002). The virtual. New York, NY: Routledge.
[76]Castells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and the urban regional process. Oxford, England and CambridgeMA: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MA: Blackwell. CrangM.Crang. P.&May, J. (Eds.). (1999). Virtual geographies: Bodies, space and relations.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Graham, S.& Marvin, S. (1996).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city: Electronic spaces, urban places.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Graham, S.& Marvin, S.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Sassen, S. (2006). Territoryauthority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7]Couldry, N.& McCarthy, A. (Eds.). (2004). Media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Morley, 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78]SassenS. (2006). Territoryauthority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9]SchubertT. W. (2009). A new conception of spatial presence: Once againwith feel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19161–187.
[80]SassenS. (2006). Territoryauthority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1]Dodge, M.& KitchinR. (2001). Mapping cyberspace. London,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KitchinR.& DodgeM. (2011). Code/Space: 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CambridgeMA: MIT Press.
[82]HillisK. (2009). Online a lot of the tim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83]ZookM. A. (2005). The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Venture capitaldot-comsand local knowledge. Malden, MA: Blackwell.
[84]Jansson, A.& Falkheimer, J. (2006). Towards a ge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In J. Falkheimer & A. Jansson (Eds.)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pp. 9–25). GooteborgSweden: Nordicom.
[85]Morley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Morley, D. (2007). Media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New York, NY and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Morley, D. (2009). For a materialist 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10(1)114–116.
[86]MorleyD. (2009). For a materialist 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10(1)114–116.
[87]ChristophersB. (2007). Media geography’s dualities. Cultural Geographies14156–161.
本文作者保罗·C·亚当斯(Paul C. Adams)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地理与环境系教授,安德烈·杨森(André Jansson)系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系教授。译者李淼、魏文秀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译校及导读作者张昱辰系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中文版得到作者授权。原文为Paul C. Adams & André JanssonCommunication Geography: A Bridge Between DisciplinesCommunication Theory, 2012(22)pp.299-318. 获取自: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8-2885.2012.01406.x/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