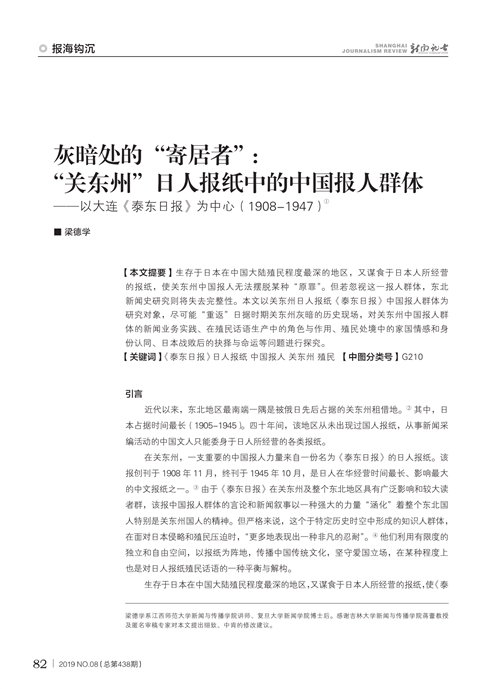灰暗处的“寄居者”:“关东州”日人报纸中的中国报人群体
——以大连《泰东日报》为中心(1908-1947)①
■梁德学
【本文提要】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使关东州中国报人无法摆脱某种“原罪”。但若忽视这一报人群体,东北新闻史研究则将失去完整性。本文以关东州日人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尽可能“重返”日据时期关东州灰暗的历史现场,对关东州中国报人群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殖民话语生产中的角色与作用、殖民处境中的家国情感和身份认同、日本战败后的抉择与命运等问题进行探究。
【关键词】《泰东日报》 日人报纸 中国报人 关东州 殖民
【中图分类号】G210
引言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②其中,日本占据时间最长(1905-1945)。四十年间,该地区从未出现过国人报纸,从事新闻采编活动的中国文人只能委身于日人所经营的各类报纸。
在关东州,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该报创刊于1908年11月,终刊于1945年10月,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③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言论和新闻叙事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特别是关东州国人的精神。但严格来说,这个于特定历史时空中形成的知识人群体,在面对日本侵略和殖民压迫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忍耐”。④他们利用有限度的独立和自由空间,以报纸为阵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平衡与解构。
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使《泰东日报》中的中国报人无法摆脱某种“原罪”。但若忽视这一日人报纸中的中国报人群体,东北新闻史研究则将失去完整性。由于关东州日人报纸中的中国报人在战后的历史记忆中被有意或无意隐去,当年有哪些中国文人活跃于《泰东日报》,除少数人外,此前尚难确知。此外,一些忍辱为稻粱谋的中国报人,往往不愿意在白纸黑字中留下自己的名姓。此一点,与现有近现代报人研究殊为不同:现有相关研究中,即便没有丰富的资料文献,但至少不必从零开始“发掘”。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史料为120卷《泰东日报》缩微胶片,报人“发掘”工作主要依赖于对这些缩微胶片的逐版爬梳。对同期出版的《满洲日日新闻》、《盛京时报》、《满洲报》等报刊,解放后东三省及下辖各市县出版的地方志和文史资料,报人创作的文学作品等,也一并进行了梳理和考订。研究过程中,有幸得到仍健在的原《泰东日报》报人、报人后代、早期大连市新闻记者协会负责人、大连地方史志主要编纂者等提供的史料,包括报人作品单行本、家族回忆录、诗词手稿、报人照片等。对上述诸位先生的口述访谈,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对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这个几乎未被历史记录的特殊知识人群体,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该群体如何形成与演变,基于何种历史背景?作为报人,他们的新闻业务实践和对职业身份的认知如何?他们在殖民话语建构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供职于侵略者经营的文化机构,他们的家国情感是否受到“异化”,又经历过怎样的认同挣扎?“宗主国”战败后,他们面对“汉奸罪”惩罚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其人生抉择及最终命运又如何?本文尽可能重返日据时期关东州灰暗的历史现场,对上述问题进行描述和解答。
一、中国报人群体的形成与演变
《泰东日报》自始至终是一份日人经营和掌控的报纸。本质上,社内的中国报人仅是日人社主的雇佣文人,具有“寄居”和“依附”的身份特征。在日本殖民者权力操控下,加之关东州日华杂居及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特殊环境,《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形成与演变具有较鲜明的殖民地色彩,同时又与近现代中日关系动荡演进的历史背景紧密关联。
《泰东日报》创刊的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关东州未曾有中文报纸问世,“风气初开,难得办报之人”。⑥初代社长金子雪斋虽有编辑日文《辽东新报》中文版的经验,但毕竟所主持的是一份中文大报,亟需中国文人襄理编务。在此情况下,清光绪乙丑恩科举人李在旃受邀“督理编辑事”,却不居名位,不支薪水。⑦秀才曲模亭及尚难查证准确姓名的“海外闲人”、“甦生”等人也曾在报纸创刊之初从事采编工作。
与中岛真雄等日人在华经营中文报纸时主要倚重日人不同,⑧金子雪斋经营《泰东日报》的显著特征,是大量聘请中国文人并在较大程度上赋予其自由采编权限。⑨1913年,在天津办报触怒袁世凯而避难至关东州的安徽籍同盟会会员傅立鱼,受金子雪斋邀请主持《泰东日报》笔政。入职后,傅立鱼对报社人事加以整理,通过乡缘、学缘、党缘等关系吸引或延聘了一批主要来自关内的爱国进步人士,如张复生(山东)、安怀音(安徽)、沈紫暾(安徽)、沈止民(广东)、汪小村(浙江)、毕乾一(关东州)、刘憪躬(奉天)等。傅立鱼对上述人的培养锻炼,使《泰东日报》在言论、新闻、副刊等方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中国报人体系。据傅立鱼自述,对自己提拔任用中国人的行为,金子雪斋“丝毫不加干涉”。⑩
1925年金子雪斋殁后,《泰东日报》爱国报人群体逐渐星散。更为重要的是,在失去金子雪斋的政治“庇护”及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报人生存处境明显恶化。不仅新闻与言论常遭掣肘,人身安全亦得不到保证,名记者王兰被日本浪人殴伤即是例证。约在1928年5月,关东州本土报人代表性人物、时任编辑长毕乾一离社,[11]据称是因为言论开罪于日人。[12]同年7月,因“计划东三省之革命”,原编辑长傅立鱼、副编辑长沈紫暾被殖民当局拘捕。[13]8月,傅立鱼被逐离连,沈紫暾去向不明。
1928年前后,陆续有李笛晨、陈涛(化名陈达民)、吴晓天等中共党员潜入《泰东日报》从事地下工作。由于陈涛很快获得日人社主信任,对编辑局用人亦有很大权限,他除介绍曾任中共北满地委委员、团北满地委书记的吴晓天进入《泰东日报》,还曾介绍盖仲人(从苏联归国党员)、周东郊(自吉林出狱党员)等到《泰东日报》任编辑。[14]此外,国民党大连地方党部负责人李仲刚约在1929年前后入社担任记者,致使社内中国报人成分及相互间关系愈形复杂。
1930年底至1931年初,吴晓天、陈涛或是被迫逃离,或是被殖民当局逮捕,至1931年三四月间,关内报人已从《泰东日报》流散殆尽,继续留下的多为关东州或其他东北地区“土著”报人。他们即便对日本殖民统治持不认同甚至抵抗态度,却无法或不愿离开故土,甘愿作为雇佣者在《泰东日报》工作。此后不久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使中日关系大变,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报人在报社中的“传统地位”,他们不再对报纸言论和采编活动拥有控制权。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为统一舆论,《泰东日报》依殖民当局指示将大连另外两家中文报纸《关东报》、《满洲报》合并,同时加入伪满洲国弘报协会。与社务的空前发展相比,《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进一步边缘化和傀儡化。尤其1940年后,在百余人的社员构成中,各部门日人数量遽然增加,“9名采访记者中4名是日人”。[15]在中国报人的安排与使用上,日人社主可以不顾及其意愿随意支配。[17]另如同时期“宗主国”日本国内的各大报纸一样,战时《泰东日报》采编人员被定位为“报道战士”。[18]报社内部时常举行“祈祷皇军武运长久”、“协同沙场战士共同灭敌”、“完成吾等东亚民族之共荣圈”等各类培养中国报人效忠精神的活动。此外,报社还数次主办“大东亚战与州民觉悟座谈会”、“州人教育昂扬大会”及“昂扬战意、增强战力讲演会”等活动,协力日本殖民侵略。在这些活动中,中国报人被要求积极发言或作演讲,动员州内“满人”协力战争。[19]本次研究共“发掘”出101位《泰东日报》大连本社社员。这101人中,入社最早的中国报人出生于1869年(清同治三年),最小的则生于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籍贯分布上,关东州本土最多,占19%,以下依次为奉天8%,安徽5%,江苏、直隶、北京各2%,广东、山东、浙江各1%,其他目前尚难考证。从受教育情况看,早期的李在旃为进士,曲模亭、傅立鱼为秀才,接受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教育。因废除科举等原因,此后入社的中国报人不再拥有功名,但大多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且有留日经历。统计中,留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庆应义塾等日本名校的占10%。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国立法政学校等是关内报人曾经求学的主要机构。关东州本土报人则主要毕业于金州公学堂、旅顺第二中学校、大连商业学堂、旅顺师范学堂等日本殖民教育机构。
另需说明的是,在可资查证的《泰东日报》上,每期报头均署“编辑人”姓名,先后为张复生、李子民、陈达民(即陈涛)、蒋模庵、李永蕃、赵忠忱、刘士忱。但除张复生、陈达民外,他们对报纸采编活动没有什么话语权。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担任此职务的李永蕃、赵忠忱、刘士忱,他们虽名为编辑人,却“不管什么事”。[21]较之于编辑人,编辑长或编辑局长是《泰东日报》采编群体的核心角色,此职务不仅控制整个采编体系,也有用人、选人权限。“九·一八”事变前,该职务均由中国人担任。据已掌握的史料,傅立鱼、毕乾一、马冠标、陈涛曾先后担任过此职务。陈涛以后,该职务均由日本人担任。[22]
二、报纸业务实践与报人职业认知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关东州先后出版报纸41种,其中日文37种,中文3种,英文1种。[23]另据1935年出版的《中国报纸指南》一书,当时租借地中心城市大连每日报纸发行总量达12万份,排在江苏(含上海)、河北(含北平、天津)、香港、广东、山东之后,居第6位。若按每万人拥有报纸数量计算,则仅次于香港。[24]关东州报纸虽然种类多、发行量大,却全为日人创办和经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即是在这样的报业异态时空中开展新闻业务实践并逐步形成报人职业认知的。
(一)异态时空中新闻业务实践
戈公振先生曾在《英京读书记》一文中指出,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因国势强盛,其新闻事业“一跃而与欧美并驾齐驱”。[25]在被日本强占并视为“领土外延”[26]的关东州,活跃着大量专业日本报人(包括《泰东日报》内部)。这些人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新闻业务实践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示范,加之大多数中国报人相当勤勉,从而使各时期的《泰东日报》表现出较高的业务水准。
作为一份综合性大报,社论、时评、短评等各类言论是《泰东日报》的核心内容。在该报出版史上,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极少数言论由日人所写外,其他均由中国报人完成。[27]其中,傅立鱼、张复生、安怀音、沈紫暾、沈止民、吕仪文、侯小飞、毕乾一、刘憪躬、尹仙阁、赵恂九、杨华亭以及尚难确知真实姓名的“甦生”、“狮儿”、“从权”、“振”、“逸民”、“凝安”等人,是该报历史上主要言论作者。暂不论他们所写的万余篇言论政治立场如何,仅就写作技巧而言,大多立意高远,用典巧妙,承续了中国文人以匡扶时世为己任的精神传统,读之有铿锵之感。一些报人如傅立鱼、尹仙阁、赵恂九等,常常连日撰写社论不辍,下笔多在千言以上。对于言论写作质量,中国报人自我要求也较严格,“狮儿”曾在日记中提及,某日“作短评约计合五万余言,同事某君云太略,遂揉碎弗刊”。[28]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报人在言论方面虽然高产,但明显已有受日人操控的迹象,成为日人奴化国人的工具,典型的如“勉”的《抗日误国中国国民当任其咎》(1937年11月11日)、尹仙阁的《吃饭与爱国》(1938年2月11日)、赵恂九的《汪精卫氏之和平宣言》(1940年3月14日)等。
新闻采写方面,《泰东日报》创刊初期访员长期捉襟见肘,不得不向社会上的“士农工商”征稿。[29]1913年,有办报经验的傅立鱼入社后,经其多方网罗,采编队伍才渐成体系并初步职业化。1920年后,随着《关东报》和《满洲报》问世,弹丸之地的关东州新闻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却也推动了《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新闻业务水平提升。自此开始,王兰、李仲刚、张兴五、吕仪文、王昨非、李永蕃等人已有相对明确的“条线”领域,如王兰负责体育、李永蕃负责经济、张兴五负责社会新闻等。对于州外重大时事,中国报人也已具备相当强的机动反应能力,如1928年吕仪文赴奉天采访张作霖被炸事件,[30]1929年李仲刚赴山东采访国民党接防济南、赴南京采访孙中山奉安大典[31]等。
1931年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新闻采写活动进入受权力操控的“殖民话语”和“他者叙事”模式,[32]其稿件写作与编排均需经过重重审核,这从一些新闻报道和新闻图片后印有的“阅讫”字样可得印证。即便如此,他们在具体新闻业务领域仍有一定进步。如在不必刻意展示与“宗主国”日本“亲和性”的社会新闻采编活动中,中国报人表现出良好的新闻敏感性和文字驾驭能力。采访与写作迅捷、灵动,写作风格、语言文字、表现手法等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学表现手法的痕迹,但大多能够保证稿件真实性,向壁虚构的情况甚少发生。一些较大型的报道如《庒淑玉主演“彩凤离鸦”喜剧》[33]、《汽车乘客豹变 途中劫司机》[34]、《饭馆被歹人觊觎 强抢未遂竟杀人》[35]等,负责采写的“外勤记者”均能接触多个信息源,对新闻事实进行反复核证。
至于“内勤记者”(即编辑)日常工作状态,一直工作到1945年报纸停刊的老报人周静庵在1934年的一篇短文中有生动描述:
(编辑工作)终朝伏案,薪劳栗碌,唯日不遑……逐日被纷如雪片之稿件包围,兼收并蓄,临时集中,整理排比,随时发出。迨及开付即毕,一日之工作方告完成,一日之光阴已成过去。日日如是,陈陈相因,俄而星期,俄而满月,光景恍如昨日,岁华又是一年。[36]与大多数中国近代综合性大报相类似,副刊是《泰东日报》版面上与新闻、政论并驾齐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相对“隐蔽”的天地中,中国报人可较为自由地编排栏目、组织约稿和发排稿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16年左右文艺消闲性内容从“游刊”发展到固定的“艺文部”后,《泰东日报》上先后出现的有固定刊头的副刊逾30种。其间涌现出多名精于副刊编辑的报人,典型的有刘憪躬、李笛晨、吴晓天、毕殿元、魏秉文、王丙炎、董文侠等。个别报人甚至同时编辑多种副刊,如1930年代文艺部主任毕殿元,就曾同时编辑《儿童》、《体育双周》和《文艺》三大副刊。一些生活实用性副刊也编辑得有声有色,如副刊《家庭》等。《家庭》由董文侠负责编辑,其“家庭问题问答”栏目颇受读者欢迎,1940年初结集出版,[37]当下国内古旧书市场仍可见该书。
就以上言论、新闻、副刊等报纸核心业务,本研究曾对不同时期的《泰东日报》进行简单抽样,并将之与同时期的《申报》与《大公报》等进行粗略比对。从结果看,无论是大小言论、内容编排、版式设计、标题制作,还是对新闻资源的深挖能力、新闻采访的扎实度与专业度,均看不出各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与《申报》、《大公报》中的那些名记者、名编辑有多大差距,个别之处,甚至有所超越。
(二)报人职业认知的形成与扭曲
1908年《泰东日报》创刊时,中国已进入第二次办报高潮,甚至出现以汪康年为代表的以办报为职志的“第一代报业家”。[38]但在关东州,人们对新闻记者仍持鄙夷态度,“往往群聚一室,谈笑正欢,或有新闻记者至,谈笑顿时终止,遇有向之探问,虽极普通之事,亦不肯据实直告,敬鬼神而远之”。[39]正因如此,创刊初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对自身的职业身份似乎并不看重。有举人功名的李在旃干脆常年义务劳动,不支薪水,即有旧文人不愿降志辱身背负“报人”声名之嫌。
在《泰东日报》发展史的中前期,不少中国报人虽全身心办报却志不在报。典型的如傅立鱼,他在入职《泰东日报》后仍热衷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称帝,闻此消息,主持报纸笔政两年多的傅立鱼“投笔而起,走津沪齐鲁”,[40]袁死后方返任编辑长。5年后,他又组织发起近代大连著名爱国进步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安怀音、毕乾一、沈止民、沈紫暾 、汪小村等多位《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亦在该会兼任职务。
除参与中华青年会活动外,《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还曾发起组织其他各类社会团体,如安淮阴等成立大连人道维持会,[41]汪小村发起中华文艺社,[42]沈紫暾等创立微光学术研究社[43]等。在这些社团组织中,他们以人权领袖、社会教育家、戏曲艺术家、学术权威等身份活跃于各种社会公共空间。此外,刘憪躬和李仲刚为国民党党员,后者一度是大连国民党组织负责人;陈涛、李笛晨、吴晓天、盖仲人、周东郊等则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大连秘密党组织的核心成员。部分中国报人也曾尝试参与关东州殖民事务,傅立鱼、王子衡、李仲刚等曾参与大连市会议员竞选。[44]此类非新闻职业行为分散了他们从事新闻采编活动的精力,对其新闻报道与言论客观性、公正性造成减损。
虽然热衷参与各类社外活动,但随着报人职业社会地位的整体提升,《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对职业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早在1913年,一位中国报人在题为《本报访员达黄县大同阅报所之质问书》的文章中即清晰表达了自己对所从事职业的认知:“报馆为监督政府、辅助社会之机关,访员有搜讨□密褒贬善恶之责任,有闻必录为全球报刊所公许,除奸烛隐犹系同人应尽之义务。” [45]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二次常会在广州举行,其间提出筹设新闻大学的建议,记者沈止民热情回应称:“至于新闻大学,我今握笔为文,书此四字,尚觉怦然□动,果有开办确讯,吾将屏除一切,决然入学。” [46]1928年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生存环境愈形恶化,但大部分人仍能坚持新闻记者职业的操守与品格。是年初冬,记者王兰被大陆浪人小日向白朗设计殴伤,众多读者投信报社表示慰问。王兰则在回信中说:
自我从业记者的那天,我便未有记得我的职责是记者(原文如此——笔者注),忠实于记者的职责。那便是我唯一的服务了。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利诱与威迫,我从来连想都没有想到……假如我还能活着的一天,怕于我职责的本身,便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47]在关东州人文闭塞的情况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职业意识的形成和他们与各类报界团体及业内同人的交往有一定关系。1913-1914年间,东三省曾连续举办三届“中日记者大会”,《泰东日报》中国报人金梅五、张复生、刘仁山及分社记者多人均先后赴会。[48]此后东三省各类大型报界团体活动,均有《泰东日报》中国报人身影。其首次参加全国性报界活动是编辑长傅立鱼1921年赴北京参加中国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49]此时参与报刊言论工作的安怀音指出:“报界人物,胥为国家之优秀分子,似此次交欢一堂,沟通意见,互换智识,其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又岂浅鲜哉。” [50]亲身参会的傅立鱼则认为,“报纸乃是社会的导师,国家的干城,最关紧要”,全国报纸记者“集在一堂,讨论国家大计,也算是一种快心之事”。[51]身处被日本视为“领土外延”的关东州,《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与日本报界向来交往密切。1923年5月在大连召开的“日本全国新闻记者协会大会”再次为中日报人间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该会议“出席者日本内地方面一百二十八名,大连方面参加者三十六名”,沈紫暾、吕仪文二人则作为《泰东日报》代表出席。[52]勿论其参与的各类报界同业活动性质如何,客观上,与行业同人之交往有利于《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形成职业群体意识,增强职业身份认同。与新闻业相对发达的日本报界的广泛接触,对他们形成较先进的职业理念、提升业务能力也有帮助。
“九·一八”事变后,在无法逃离故土、只能继续寄人篱下的情况下,关东州本土报人较前辈同人更加专注于报人职业,将清谈送日的耕砚生涯作为一种颇有颜面的文人生计。倒数第二任编辑人赵恂九就曾在他的小说《流动》中对当时报人在关东州的社会地位有所描述。该小说男主人公是一位有着赵恂九影子的报纸编辑,赵恂九借助小说人物之口称他是个“上层社会的人”。[53]总体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报人虽委身日人报纸,却不全为稻粱谋,而是对报人职业持崇敬和认同的态度。只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报社中的日本人加强对中国人的控制后,“本是书生面目,尊为无冕之王”、“手执秃笔一枝,足抵三千毛瑟” [54]所带来的成就感变得无从谈起,只能化作中国报人内心的挣扎与愤懑。在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下,他们的职业信仰不得不折腰于殖民霸权。
三、在殖民话语生产中的角色与作用
“殖民话语”由萨义德借自福柯,用以“描述一种在其中产生着广泛殖民活动的实践体系”。[55]作为租借地殖民话语生产主体之一的《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其报刊活动必然对关东州国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精神和心理影响。也应注意到,因环境和时局不同,他们在较长时期内实则充当着殖民话语解构者的角色。
(一)作为殖民话语生产者
作为日人文化机构中的雇佣者,《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从一开始就陷入金子雪斋“大乘的民族主义”[56]的宽容性陷阱。一些中国报人即便为华人权益呼喊,但其生活方式却已不自觉地日本化。当看到故土在日人治下发展成极为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时,他们内心怀着复杂情感。1921年的一个秋夜,时任编辑长毕乾一“披和衣,着木屐”漫步在繁华的大连浪速町一带,感叹道:
晚间披和衣,着木屐,往来跸□于浪速町一带,见游人如鲫,商贩麇集。日人之名媛闺秀衣香髻影,结袂翩飜,明媚电光照地作淡绿色,街中车声隆隆……街头摊卖尽是日用之资,商场罗列无非辉煌之品。如此繁华境地,怡我之心,悦我之目……若当二十年前,此地不过以荒野之区耳,焉有街平如镜、楼高如云。[57]具有爱国意识、出身中国传统诗书世家的毕乾一尚且如此,[58]接受日本殖民教育成长起来的赵恂九等人更是对殖民现代性示以拥抱。在赵恂九的作品中,“高楼大厦在栉比着”的大连被称为小巴黎,[59]这里有极为摩登的现代都市生活,男女主人公相识于穿行城市的电车,穿的是洋装洋服……缺少批判和反思的殖民话语生产,反映出作者对殖民现代性和殖民文化的接受。
“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对“宗主国”日本进行了全盘美化,这在多位中国报人的赴日游记中有鲜明体现。1924年记者吕仪文访日时,其行记对日本的评价相对中立,并无太多“谄媚”或刻意美化成分。[60]1934年后李永蕃、毕殿元、张洪运、赵恂九、刘士忱、侯立常、魏秉文、张仁术、张孟仁等人的访日行记中,让人看到的却是一组互文性铸成的“完美日本”形象:日本风景“是世界有名的”,[61]工厂“规模之大东洋第一,世界闻名”、[62]人民“每一个都有责任心,绝不像不长进民族那样马马虎虎”。[63]这些行记借着真实的名义,使一个过度美化的日本形象不断被互文性地生产,最终畅通无阻地进入关东州和东北国人的社会集体想象。
伪满洲国成立之际,《泰东日报》也不断向东北国人灌输所谓的“王道”思想,宣扬新“国家”是“除去种族之别,国际之争,王道乐土”。[64] “王道”观念不仅蛊惑了成年人,也毒化了青少年心灵。毕殿元编辑的副刊《儿童》和《少年》即刊登不少宣扬“日满一体”、伪满洲国是“王道乐土”之类的文章,对正处于民族国家观念形成期的东北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1934年7月8日的《儿童》上,一名小学生的文章写道:
(伪满洲国)建国之宗旨,以顺天安民为主,对外门户开放,对内广施王道……故吾等青年,宜共同努力,发展教育,开拓利源,使吾满洲有日新月异之气象,变为东亚乐园,亦无愧于新国民建设矣,此王道之目的与使命也。[65]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尹仙阁、惠东、张兴五等人开始传播实用主义“节义观”,劝中国人早降。尹仙阁曾写《吃饭与爱国》一文,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乃是“饱闷之后,被饭塞住心窍”而发出的“一屁不通之论”。[66]在另一篇题为《历史覆辙(续)》的文章中,他虽认为中国人爱国无错,但却“昧于理势”,不知危急之际可不必计较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类传统节义观。[67]一些中国报人甚至不惜为冯道、秦桧等失节者正名,认为“痛诋冯道为无耻、秦桧为媚敌者”实属“简单之主观”。[68]日本在关东州推行奴化教育以普及日语为初始。[69]对殖民后出生的一代关东州人来说,日文几乎是一种自然习得的语言文字。在情感和理智上,他们已不再将日语视为对民族文化的巨大威胁而加以抗拒。《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某些作品,无疑提醒了国人需“自觉”学习日语。仍以赵恂九为例:他公开发表的14部小说中,有9部小说男主人公精通日语,其中6位留学日本。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如会日语,都将获得某种生活上的便利,就如《他的忏悔》中男主人公对他的学生所说的:
现在住在这个地方,日本话是很要紧的。你想,我们每一出门,都要遇着日本人的,同时你们若是毕业后,还得在日本机关里做事,若是不会日本语,哪能行呢?而且自己家中,若遇着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若是自己能说日本语,更是方便的。[70]《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也是“东亚共荣”话语的重要生产者和传播者。在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之前的1938年,“论说委员”尹仙阁即构想出一个“将来之远东大帝国”,这一大帝国由日本为盟主,“团结黄种民族,同跻于共存共荣之域”。[71]1940年3月,赴日参加东亚操觚者大会归来的“整理部次长”侯立常在大连西岗子公学堂面对二千余名华人同胞讲述了自己对“东亚新秩序”的理解:建设东亚新秩序“不是排外,也不是利己”,“其最终之目的乃在全世界的和平”。[72]若能注意到部分《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确有“东亚共荣”之类的欲念与幻想,其激切的助日言论便可得到进一步理解。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他们的办报活动最终陷入殖民权力的话语当中。
(二)不应忽视的反殖与解殖作用
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处境,供职《泰东日报》时,中国报人未在公开场合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利用有限的自由空间,他们也进行了大量反殖和解殖性话语生产,尤其是在报纸创刊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13年间。
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那里,中国传统文化是其藉以解殖和反殖最常使用的话语资源。“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报人可较为自由地在租借地内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引导国人坚守固有的文化认同。1919年的一篇社论映射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豪与自信:
记者常聆听某国人(指日人——笔者注)语,谓吾人每见中国文化之发达,不胜惊叹……试案史册而察三千有余年来,中国文化之隆替则大有遨游百花缭乱之乐园之慨,岂非大可炫耀者乎。某国之骇目惊叹者,亦可谓得其宜也。[73]对日本欺侮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和行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曾直接予以回击。刘憪躬就曾提醒国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74]对于日人以“支那”侮称中国,傅立鱼表示殊为不解,“甚愿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一为顾及,改支那二字之旧称,易以中华民国之名”。[75]在《泰东日报》发展史上,对“五卅惨案”的报道最充分、最直接地体现了该报中国报人群体难能可贵的反帝爱国气节。在毕乾一、沈紫暾等主持下,《泰东日报》曾极力声援沪上。毕乾一在长篇社论《沪上暴动风潮暨外人有以自觉》中指出,“五卅惨案”是“深耻大辱,不得不雪”。这种“激烈”举动最终遭到殖民当局“禁卖”报纸一日的处罚。[76]值此家国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相逼荐臻之候。……沪人非尽愚痴者流,抑亦有不得已者存焉。……试问公共租界何人土地,非我中华民国土地耶……而实痛心夫列强之得陇望蜀,宰割日甚,压迫我民族,虐待我同胞,深耻大辱,不能不雪。[77]对于州内华人同胞所受不公正对待,《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也挺身维护其基本权益,多次公开指责殖民当局施政不当,希望将“待遇华人种种不善之处彻底改良”,[78]告诫当局保证华人就学之权利,[79]同时要求日人对大连华人苦力予以尊重。[80]如一位不知名的中国报人所采写的《满铁首脑之不顾大局 石炭之高贵垄断 苦我华人》一文,指责满铁垄断煤炭价格,“苦我华人太甚”,号召“吾华人对于满铁此种暴举应讲求对抗之策”。[81]该中国报人还去到满铁大连本社,当面质询满铁副社长。[82]《泰东日报》各类文艺副刊是中国报人平衡和解构殖民话语的重要园地。无论是早期的游刊,还是中期的《泰东杂俎》、《泰东日报·副张》和《艺苑》,均以摛藻扬芬、英雄儿女、雪泥鸿爪、零缣断锦、照世明镜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栏目为主,充当着关东州华人保持与祖国文化亲缘关系的重要媒介。1920年代末,李笛晨、吴晓天等中共地下党人先后接手《泰东日报》副刊。他们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通过《泰东日报》副刊宣传普罗文学。[83]尽管最终失败,但客观上推动了州内和东北文学青年的个性解放,促使他们关注黑暗的社会现实。
社会主义学说是反抗殖民统治和推动民族解放的重要理论资源。“五四运动”至1920年代中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曾编发郑振铎的《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1919年1月25日)、鹃魂的《六个月间的李[列]宁》(1919年12月2日)、瞿秋白的《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1919年12月11日)、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1920年1月14日)、倪洪文的《社会主义的解释》(1920年10月26日)等多篇介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章,使《泰东日报》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东北地区传播的重要基地。
《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也是近代东北文坛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他们常在采编工作之余进行文学生产活动。除言情小说作家赵恂九外,毕乾一、安怀音、刘憪躬、魏秉文、王丙炎等人也曾创作大量不同类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并不一定具有多高文学造诣,但“常常在不经意处与殖民统治意识形态宣传相左,具有消解、溶解、拆解殖民文化、殖民统治的意味和作用”。[84]
四、家国情感与身份认同
在近代中国大陆地区,家国情感与身份认同之间张力最大的地区莫过于关东州租借地。四十年间,因日人信息严密封锁及全面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战败前有不少关东州国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知道自己就是中国人”。[85] “何为祖国”以及“我们是谁”的问题拷问着《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内心,影响了他们的职业行为。
(一)中国即“吾国”
在报纸发展史的中前期,《泰东日报》未将“中国”作为殖民权力话语表述的“他者”,而是以“日人报纸”之身将中国视为“自我”,在相对本真的层面称中国为“吾国”。实际上,这种“中国认同”即是报社中中国报人国家认同的体现——他们虽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但与生俱来的中华血脉和民族情感使其一直将中国视为精神与文化上的“原乡”。
此一时期,来自关内地区的报人是《泰东日报》人员主体,无论是担任编辑长的傅立鱼,还是承担过社论写作工作的甦生、张复生、沈紫暾、安怀音、沈止民等人均来自关内。这些“侨寓”在日本租借地的华人,常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诉诸笔端,如1919年“双十节”甦生所写的纪念感言: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在今天这个隆重的双十节,凡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不拘老幼男女,农商工官,自然要为一致的欢欣鼓舞……在下及本社同人说,虽然侨寓此间,那衷心的喜悦,与其希望,也是非言可喻。[86]不仅关内报人,此时东北本土报人也保持着较明确的“中国认同”。李在旃来自关东州内的金州,为清光绪十五年举人,为近代大连著名爱国诗人;同样来自金州的毕乾一, 父亲为清末秀才,本人担任《泰东日报》编辑长期间曾写作大量反帝民族主义的社论。又如1920-1924年间的重要评论作者和副刊编辑刘憪躬来自铁岭,也是近代东北较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87]后来附敌分别担任伪滨江省省长、伪通化省省长的记者王子衡和吕仪文彼时言论中亲日立场也不明显,如吕仪文在1924年的一篇短评中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批评日本为“忘本”之国家:“日本自先东亚民族为世界的强国后,自忘为东亚民族中之一国。” [88]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关东州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关内地区,大多是只身“闯关东”至此,其亲族仍留在关内。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使他们保持着对祖国和家人的牵挂。金子雪斋去世前,州内第一代在日本统治下出生的中国人刚满20岁,尚未成为影响社会意识的主流知识分子群体。此外,因《泰东日报》从未质疑日本殖民关东州的合法性,认同中国、肆言中国政局也无伤日本殖民统治。
无论是来自关内,还是关外的东北(包括关东州本土),前中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们承续了中国知识人群体爱国爱乡的精神传统,展现出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明确认同。身处关东州租借地,被歧视、被凌辱的处境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中国人”意识。他们在颇具社会威望的社长金子雪斋允许和“庇护”下,有着借助《泰东日报》呈现并塑造州内华人同胞“中国认同”的欲望与冲动。
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短时期内,《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仍坚持认同中国为“吾国”,对国家遭遇的“未曾有之艰难”感到悲切。如在1931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第20个“双十节”,中国报人哀叹国是日艰,却笃信中国“必有富强之一日”:
每届国庆纪念日,吾人輙疾首蹙额,相顾而发深痛之慨叹者……环顾举国之中,竟无一片乐土,且外交日非,国难方殷,此际纵欲忍痛言欢,亦有不可得者矣……夫以今日之国情言,内外交迫,所遇皆未曾有之艰难,是则锻炼我国人也。国人经此锻炼,苟奋发图强,将来国势,必有富强之一日。[89](二)“我们是谁?”
中国、伪满洲国和“宗主国”日本三者之中,何为真正意义上的“祖国”?直到1944年,关东州华人仍不甚明了。
我关东州在日本皇道精神之下,施政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以地区而论,以为关东州是个特殊地带,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住在州内的人,身份既无明确之判定,名称也很为复杂。因之有时称现在的州人为满人,或中国人的,一直到本年四月二十日,公布了关东州人教育令以后,这才确定了州人的称呼。[90]上述引文中所提及的《关东州人教育令》是1944年4月20日日本为在关东州地区推行“皇民化”运动而施行的一项法令,要求关东州华人宣称自己是“天皇陛下之御民”。[91]时至今日,已难准确考察在中国、伪满洲国和日本之间,到底哪一个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所真正认同的“祖国”,他们当年的自我表述也是相互矛盾的。编辑王丙炎在战后的一份自述中说:“我永远没有忘掉我是中国人,我也衷心期待着日本鬼子失败、中国的胜利。” [92]由此可见,王丙炎所认同的应该还是那个传统的中国。但在“论说委员”尹仙阁那里,“中国人”仅仅是自己过去的政治身份:“吾人与中国之民,昔为同胞,今为善邻”。[93]伪满洲国建立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也曾将之视作新的“祖国”。一位中国报人宣称,伪满洲国“完全为独立国家,非供人傀儡可比”,而自己作为“满籍之民”,则应“努力爱国,以应付非常时代”。[94]对于日本在关东州地区推行“皇民化”运动,《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也表示拥护,“特报部次长”孙世瀚在一次题为《澈悟州人教育令精神》的演讲中,“力论州人教育令之精神与州人皇民化之必然性”,希望“一百六十万州人理宜澈悟其旨意,发挥八紘肇国精神,协助大和民族共负建设共荣圈光荣责任”。[95]1938年5月,伪满洲国“国家总动员法”在关东州施行。[96]在总动员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无法回避来自日人社主和殖民当局的压力。作为“次日本人”或“准日本人”的他们,处于愈发尴尬的地位。在无路可逃、既受日本人排斥又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下,受战争胁迫而被绑到日本人同一条船上的他们,确乎表现出认同于日本的趋势。但即便如此,孙世瀚等中国报人诉诸笔端或在公开演讲中所表现出的“皇国认同”是否出自本意,如今已难以确证。
当中国报人不被要求协力战争而退回传统中国的语境时,报章文字或讲演中畅言的“东亚政治”话题或所谓的“皇民身份”便不屑于提及,“假意恭维所谓日本文明或日本国力如何雄厚”已经没有必要。[97]如魏秉文、王丙炎等在新闻采编活动之外所创作的大量小说作品中,在人物角色的设定上也基本是清一色的华人面孔,故事呈现与人物命运安排也基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框架。在《故乡之春》、《风雨之夜》等作品中,读不出“国”为何国,而“家”则明显是以中国道德伦理关系建构的中华之“家”。一些来自关外的中国报人,即便在高度日本化的大连生活多年,对传统中国的回忆依然挥之不去。1944年春节,家乡“远在大别山的南面”的副刊编辑董文侠深情写道:“离开故乡将近十五年了,现在故乡变到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然而儿时的梦游之地,每一忆及,无不历历在目。” [98]复杂的家国情感和不断拷问内心的认同挣扎,导致日本统治后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出现各种“怪异”行为。譬如,赵恂九曾对本职工作颇不用心,而专注于言情小说创作,小说作品则又和他的报章言论有着绝大分野:在报章言论中,他曾对“大东亚战争”不遗余力地鼓噪,但其小说作品却刻意淡化政治意味。这固然有迎合沦陷区言情小说市场趣味的考虑,但考虑到“报人出身的小说家往往对政治有自己的敏感”,[99]作为《泰东日报》编辑人和“论说委员”的赵恂九却视政治为畏途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五、日本战败后的抉择与命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重获新生的《泰东日报》中国报人欣喜于回归祖国母亲怀抱,在尚未被勒令停刊的报纸上,呼吁被殖民统治了四十年的大连市民把“非驴非马、中日参半的言语”来个根本清算,“一切殖民地的态度表情,自亦当及时廓清”,[100]但又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因往日与侵略者的“合作”经历而遭惩罚。
在长达四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关东州国人受制于信息封锁,对国内政治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在抗战中的贡献知之甚少,绝大多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奉国民党政权为“正朔”。[101]因此,日本投降后,中国报人急于与国民党方面寻求接触。约9月底,杨华亭、刘士忱、李长春、陶云甫四人组成的报社“管理委员会”商议决定,派人携带《泰东日报》管理委员会名单赴长春,“问问(国民党)何日来接收”。[102]在多数中国报人将国民党判断为战后中国政局主导者的同时,白全武、刘汉、洛鹏等极少数人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日本尚未投降之际,他们便已与党的外围情报组织建立秘密联系。苏联向日本宣战后,白全武等人立即着手搜集日本在连驻军情报并拟派人送赴党的地下组织。[103]另据刘汉老人回忆,日本投降后的一周,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写大标语上街贴,如‘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等;另一工作是白全武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小册子,大家上街散发”,甚至准备“持枪”接管报社。[104]洛鹏此时则按照党的指示继续隐蔽。
1945年10月,《泰东日报》被苏军勒令停刊。日本报人被陆续遣返,中国报人则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成为1945年10月30日创刊的大连市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的人员班底,此部分人大多持亲国民党倾向;二是白全武、刘汉等共产党背景报人受中共大连地方党委委派,于11月1日创办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人民呼声》。
《新生时报》的场所、设备等均来自《泰东日报》,编辑部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亦为《泰东日报》原班人马。[105]但受旧观念、旧传统等影响,他们在新岗位上的工作没有得到党和苏军认可,其所编辑出版的报纸流露出对新政权的“敌对”态度。[106]1946年2月,最后一任编辑人刘士忱不辞而别,出走他乡。曾任外勤部副部长、社会部长等职务的张兴五,对旅大特殊解放区政权组织形式持有异见。1946年3月采访报道大连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107] 期间,他在会议现场对大会选举程序公开质疑。据洛鹏回忆:“这位老兄由于和我们政见不合,在二届临参会闭幕不久就辞职不干,跑到国统区去了。” [108]在此前后,极富办报经验的老报人周静庵、郭瑞堂也先后离职。
1947年5月,出版仅1年半的《新生时报》停刊,改组为关东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又部分转入该报工作。在留存至今的一份职员名单中,仍可看到洛鹏、文安禄、韩建堂、杨华亭、于永志、韩冈矿等人的名字。[109]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们有的选择坚守,有的选择逃离,也曾不断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
部分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后来“不知所踪”,除政见不同等因素外,也与战后中国政府着手处置汉奸有一定关联。1945年11月,民国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明确将“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列为“汉奸”。[110]作为供职于日人报纸《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他们无疑具备“汉奸”罪名成立的条件。对此,刘士忱曾有清晰认识,他“既庆幸祖国胜利,又顾虑汉奸将被惩处”。[111]刘士忱此后是否被以汉奸罪论处,笔者尚未查知,但其前任赵恂九确曾以相关罪名被判处15年徒刑,在黑龙江某劳改农场走完曲折悲惨的一生。[112]据原大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于景生老人口述,至20世纪50年代,仍有文安禄等五六名原《泰东日报》报人在《大连日报》从事采编等工作,但在“反右”运动开始前后,陆续不知去向。[113]除极个别人外,《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大多悲惨,一些人隐姓埋名,一些人锒铛入狱,成为连自己子女都长时间不愿提及甚至耻于提及的一代文人。
结语
在殖民地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是关东州地区中国报人的主体。与国人报纸中的中国文人相比,备受压抑的他们并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如欲从事报纸采编活动,只能委身于日人报纸,因此具有比较明显的“依附性”,这也是本文称关东州日人报纸中的中国报人为“寄居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体上,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较长时期内,中国报人在《泰东日报》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有决定这份日人报纸“报格”的能力与权限,基本做到了大节不亏,甚至在报章文字中公开“排日”。这在近代日人在华所经营的报刊中并不多见,甚至可算孤例。也说明,委身于日本关东州租借地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拥有一定的政治自由空间,也能果敢地利用自己的职业平台和职业资源声张民族气节,传递民族精神。“九·一八”事变发生、伪满洲国建立后,日人加紧了对中国报人的控制。在此情形下,他们或为稻粱谋,或基于其他利益考虑,选择与日人妥协或“合作”,生产着大量美化日本侵略、协力殖民战争的新闻和言论,对东北国人的精神和心理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是不容置喙的事实。但若抛却复杂的民族情感和历史纠葛而仅从技术与业务层面考察,这个群体有着较高的专业素养,其所从事的报刊活动对推动近现代东北地区新闻业的现代化有重要贡献。
另值得注意的是,《泰东日报》(1908-1945)几与关东州租借地(1905-1945)同龄,几代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租借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在日人离开大连时焚毁大量档案资料、[114]苏方接管大连后又私藏密运大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115]《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留下的大量报章文字成为研究关东州租借地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他们的记录与日后相对程式化的史述相比,展示了更为鲜活、复杂的租借地国人生存状态。通过他们留下的文字,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从同化或合作到抵抗和反叛,他们的行为遵循着不同的逻辑,精神世界异常复杂,远非简单的道德或政治评判所能评价和衡量。
概而言之,在关东州租借地,“合作”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只有当“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时,[116]我们对《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才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研究也将更加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①《泰东日报》终刊于1945年,但因本文涉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命运抉择问题,因此,将研究时段的终点延伸至1947年。
②1898年,沙俄强租旅顺、大连,设立“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代替沙俄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并沿用“关东州”的叫法。历史上,“关东州”之名从未被清朝及其后各个中国当局承认,本文仅为使用史料方便,行文中不再对“关东州”一词加引号。
③历史上,关东州先后出现三份中文报纸,先后为1908年创刊的《泰东日报》、1920年创刊的《关东报》和1922年创刊的《满洲报》,后两份报纸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被《泰东日报》兼并。
④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修订版)》第1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宫胁襄二与井口陆造更替时的《泰东日报》佚失,尚难确定二人更替的具体日期。
⑥模亭:《本报诞生追记》,《泰东日报》1934年9月1日
⑦《吊李在旃氏》,《泰东日报》1928年8月14日
⑧参阅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编:《东北新闻史》第2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张枫:「大連における泰東日報の経営動向と新聞論調:中國人社會との関系を中心に」,[日]加瀬和俊:《戦間期日本の新聞産業: 経営事情と社論を中心に》第168页,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11年版
⑩傅立鱼:《呜呼金子雪斋先生 逝世忽一周年矣(三)》,《泰东日报》1926年8月28日
[11]《毕乾一氏送别会》,《泰东日报》1928年5月26日
[12]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大连图书馆编:《典籍文化研究》第46页,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
[13]《运动东省革命化者被关东厅派警拘捕》,《泰东日报》1928年7月25日(为专心于自己所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事务,傅立鱼于1921年10月15日即宣布退出《泰东日报》。)
[14]大连地方党史编辑室:《中共大连地方党史资料汇辑》第216页,1983年编印
[15]张仁术:《〈泰东日报〉的史料回忆》,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296页,1989年编印
[16]该名单依据1940年1月1日第17版《〈泰东日报〉之历史与现状》一文绘制。名单中“支配人”处尚有刘仙洲、郭习楷、张本政、曲模亭,“监察役”处有邵慎亭,均为当时大连“商界巨头”,但在《泰东日报》仅是兼职。
[17]刘淳:《我和〈泰东日报〉》,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314页,1989年编印
[18]参阅《本报全社员祈祷战胜》,《泰东日报》1941年12月13日(乙)
[19]参见1942年2月13日第5版《大东亚战与州民觉悟座谈会》;1942年5月21日(乙)第5版《本报主办:大东亚战争照片展昨假貔会盛大举开》);1944年6月15日(乙)第3版《本报主办:欢欣鼓舞祝不世荣光 州人教育昂扬大会定期举行》;1945年4月18日第3版《昂扬战意 增强战力 大连地区讲演会十九日举行》。
[20]图片中文字应为“事变第二周年纪念日”,疑排印有误。
[21]刘淳:《我和〈泰东日报〉》,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309页,1989年编印
[22]据不完全统计,此后担任此编辑局长一职的日本人是桥川浚、西冈泰吉、大西秀治、佐藤四郎及岛屋进治。
[23]《大连解放前报纸简况》,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166页,1989年编印
[24]相关数据转引自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其他报纸当年发行量情况,1935年大连报纸日发行总量12万份具有较高可信度。)
[25]戈公振:《英京读书记》,《国闻周报》1928年第5卷第10期
[26]郭铁桩等:《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上册)》第10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7]此时期一些未署名社论因选词用语有日文语法痕迹,疑为社内日本报人所写。另有一些稿件署名“左腾”,应为时任编辑局长佐藤四郎。
[28]狮儿:《狮儿日记》,《泰东日报》1918年11月15日
[29]《本社启事》,《泰东日报》1913年1月9日
[30]参阅《张作霖发丧犹有待 张学良就任尚未正式通告》(1928年6月22日)等。
[31]参阅《本报特派专员调查山东接收情形》(1929年5月8日)、《本报特派专员参列奉安大典》(1929年5月26日)等。
[32]参阅梁德学:《近代日本人在华中文报纸的殖民话语与“他者”叙事》,《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33]《一度轰动连滨沪两江队健将庒淑玉主演“彩凤离鸦”喜剧》,《泰东日报》1931年7月5日
[34]《汽车乘客豹变 途中劫司机》,《泰东日报》1935年4月11日
[35]《饭馆被歹人觊觎 强抢未遂竟杀人》,《泰东日报》1936年3月28日
[36]恨人:《编余回顾琐记》,《泰东日报》1934年1月1日
[37]董文侠:《家庭问题解答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0年版
[38]参阅樊亚平《中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认同研究 1815-192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9]周恨人:《社会与新闻之进步》,《泰东日报》1934年9月1日
[40][日]加藤清风、深谷松涛:『东三省官绅史』第224页,东三省官绅史发行局1917年版
[41]《大连人道维持会》,《泰东日报》1922年7月6日
[42]《中华文艺社消息 戏曲研究部成立》,《泰东日报》1923年3月16日
[43]《微光学社宣言》,《泰东日报》1923年10月18日
[44]《议员假选第八次披露》,《泰东日报》1921年12月13日
[45]《本报访员达黄县大同阅报所之质问书》,《泰东日报》1913年2月5日(史料中辨识不清的文字以“□”代替,下同。)
[46]指鸣:《广东报界议案之感言》,《泰东日报》1920年7月2日
[47]王兰:《答》,《泰东日报》1928年12月8日
[48]参阅《中日记者预备会纪事》(1913年1月26日《泰东日报》)、《东三省中日记者第二次大会预志》(1913年8月29日《盛京时报》)、《第三次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出席名表》(1914年10月16日《盛京时报》)。
[49]《全国报界大会之盛况》,《泰东日报》1921年5月20日
[50]淮阴:《我所望于报界联合会者》,《泰东日报》1921年5月7日
[51]西河:《京华回忆录·序言》,《泰东日报》1921年6月15日
[52]《新闻协会大会出席 大连侧三十六名》,《泰东日报》1923年4月29日
[53]赵恂九:《流动》(原书页码不详),泰东日报社出版部1935年版
[54]恨人:《编余回顾琐记》,《泰东日报》1934年1月1日
[55]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Helen Tiffin:《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p66-57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9
[56]金子雪斋是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大乘的民族主义”一派的理论创建者。该种“民族主义”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反对日本在关东州推行强硬殖民政策。
[57]大拙:《落英缤纷》,《泰东日报》1918年9月7日
[58]毕乾一之父毕序昭为金州名儒,字宗武,号蔗农,清末秀才。
[59]赵恂九:《风雨之夜》(原书页码不详),大连启东书社1943年版
[60]参阅1924年3月24日至4月16日吕仪文向报社发回的《赴日视察团消息》15篇、《赴日视察感想追录》12篇。
[61]毕殿元:《日本之一般社会情况及感想》,《泰东日报》1935年4月28日
[62]李永蕃:《本报视察团视察记(二十九)》,《泰东日报》1934年5月24日
[63]毕殿元:《满洲国记者团在日所得印象》,《泰东日报》1935年5月8日
[64]《满洲国执政宣言》,《泰东日报》1932年3月11日
[65]孟祥福:《满洲国王道主义之使命》,《泰东日报》1934年7月8日
[66]仙:《吃饭与爱国》,《泰东日报》,1938年2月11日(B)
[67]仙:《历史覆辙(续)》,《泰东日报》,1937年10月17日(B)
[68]勉:《抗日误国中国国民当任其咎》,《泰东日报》1937年11月11日(A)
[69]参阅李延坤:《“关东州”的殖民文化研究——以日语教育为中心》,《东北亚论坛》 2012年第2期
[70]赵恂九:《他的忏悔》第49页,大连实业洋行出版部1935年版
[71]仙:《将来之远东大帝国》,《泰东日报》1938年2月18日(B)
[72]侯立常:《建设东亚新秩序与日本国民精神》,《泰东日报》1940年3月8日(乙)
[73]《中国文明今昔观》,《泰东日报》1919年8月27日
[74]憪躬:《临案通牒后对于友邦国人之忠告》,《泰东日报》1923年8月14日
[75]西河:《日本对于中国应改支那之旧称》,《泰东日报》1919年3月13日
[76]《本报禁止发卖一日》,《泰东日报》,1925年6月7日
[77]大拙:《沪上暴动风潮暨外人有以自觉》,《泰东日报》1925年6月6日
[78]西河:《笞刑废止乃当然之事也》,《泰东日报》1919年8月9日
[79]西河:《第二公学堂之设定》,《泰东日报》1920年8月11日
[80]西河:《呜呼苦力》,《泰东日报》1920年7月30日
[81]《满铁首脑之不顾大局 石炭之高贵垄断 苦我华人》,《泰东日报》1921年2月17日
[82]《关于煤炭问题 本社记者满铁干部访问记》,《泰东日报》1921年2月22日
[83]洛鹏:《我地下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在〈泰东日报〉的革命活动》,《大连党史》1990年第3期
[84]刘晓丽:《解殖性内在于殖民地文学》,《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
[85]口述人朱毅,1934年生。引自齐红深编:《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第780页,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含有大量相关访谈可供参考。)
[86]甦生:《国庆纪念感言》,《泰东日报》1919年10月10日
[87]冯玉贤:《早期在大连从事革命活动的铁岭人——记刘憪躬、石三一夫妇》,政协铁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铁岭文史资料汇编 第5辑》第1-15页,1986年编印
[88]仪文:《忘本》,《泰东日报》1924年11月28日
[89]《今岁国庆日之感怀》,《泰东日报》1931年10月10日
[90]钟济生:《皇民化与惟神大道》,《泰东日报》1944年10月1日(乙)
[91]《关东州人皇民化运动于此机会将盛大展开》,《泰东日报》1944年4月21日(乙)
[92]王丙炎:《新旧社会两重天》,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298页,1989年编印
[93]仙:《中国缺乏需要人物》,《泰东日报》1937年10月20日(B)
[94]《谨祝治外法权撤废签字》,《泰东日报》1937年11月6日(A)(文章未署名,但正文中出现“我满籍之民”字样,可知其作者为中国人。)
[95]《昂扬战意增强战力 大连地区讲演会十九日举行》,《泰东日报》1944年4月18日
[96]伪满洲国方面在1938年5月11日已开始施行该法。
[97]刘淳:《我和〈泰东日报〉》,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312页,1989年编印
[98]文侠:《谈谈故乡新年》,《泰东日报》1944年1月3日
[99]袁进:《鸳鸯蝴蝶派》第17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100]《中国同胞须认识党国 国歌及遗嘱尤应家喻户晓》,《泰东日报》1945年9月5日
[101]2017年7月8日对原《泰东日报》编辑部职员刘汉老人访谈。
[102]杨华亭:《我的新闻生涯》,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305页,1989年编印
[103]《六人情报小组》,《大连晚报》2011年8月21日
[104]2017年7月8日对原《泰东日报》编辑部职员刘汉老人访谈。
[105]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33页,1989年编印
[106]姜毅:《回忆我在大连从事新闻工作的情况》,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249页,1989年编印
[107]顾明义等编:《大连近百年史》第167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8]洛鹏:《一次难忘的采访活动》,大连日报社:《大连日报史料集》第186页,1985年编印
[109]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44—45页,1989年编印
[110]《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国民政府令,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11]刘淳:《我和泰东日报》,大连日报社:《大连报史资料》第316页,1989年编印
[112]2016年10月对赵恂九之子李振铎先生访谈。
[113]2017年8月对原大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于景生老人访谈。
[114][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第56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5]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苏军进入大连后,没收了大连图书馆和满铁调查部资料室的全部藏书和资料,并用卡车拉走了保存在营城子高尔夫球场地下室的大量调查文献。接管大连图书馆的多年间,苏军禁止任何中国人入馆(包括保洁人员),私藏密运历史文献的数量至今难以确知。
[116]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第285页,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梁德学系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感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蒋蕾教授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细致、中肯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