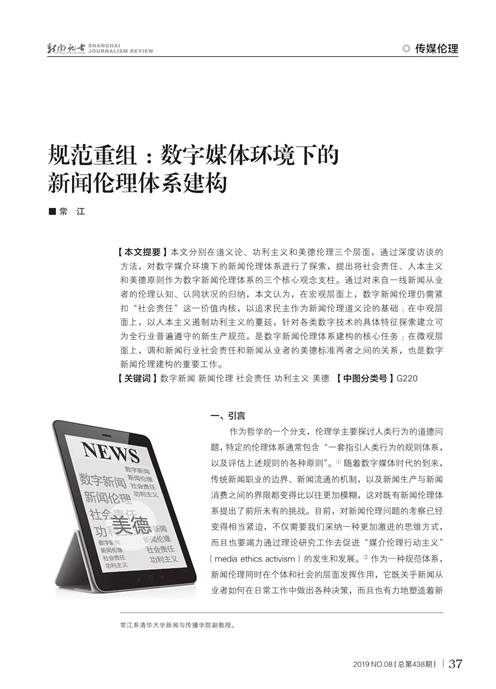规范重组: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建构
■常江
【本文提要】本文分别在道义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三个层面,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数字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进行了探索,提出将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和美德原则作为数字新闻伦理体系的三个核心观念支柱。通过对来自一线新闻从业者的伦理认知、认同状况的归纳,本文认为,在宏观层面上,数字新闻伦理仍需紧扣“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内核,以追求民主作为新闻伦理道义论的基础;在中观层面上,以人本主义遏制功利主义的蔓延,针对各类数字技术的具体特征探索建立可为全行业普遍遵守的新生产规范,是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在微观层面上,调和新闻行业社会责任和新闻从业者的美德标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数字新闻伦理建构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数字新闻 新闻伦理 社会责任 功利主义 美德
【中图分类号】G220
一、引言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主要探讨人类行为的道德问题,特定的伦理体系通常包含“一套指引人类行为的规则体系,以及评估上述规则的各种原则”。①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新闻职业的边界、新闻流通的机制,以及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之间的界限都变得比以往更加模糊,这对既有新闻伦理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对新闻伦理问题的考察已经变得相当紧迫,不仅需要我们采纳一种更加激进的思维方式,而且也要竭力通过理论研究工作去促进“媒介伦理行动主义”(media ethics activism)的发生和发展。②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新闻伦理同时在个体和社会的层面发挥作用,它既关乎新闻从业者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做出各种决策,而且也有力地塑造着新闻从业者群体与既定社会规则之间的关系。③简而言之,“新闻伦理不但指引着新闻从业者做出个人选择,而且也界定着新闻职业的身份……它设定边界,区分新闻业的局内人和局外人,并鼓励新闻从业者与非专业人士和实践保持距离”。④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的冲击对传统新闻伦理产生的影响,以及新闻从业者对这一过程做出的反应展开了探索性的研究。早在1998年,Cooper就提出了新媒体给新闻业带来的40个伦理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较多集中在比较表浅的层面(如文字剽窃和图片篡改现象)。⑤在2000年展开的一项调查中,两位学者严肃审视了媒介融合可能导致的“机构利益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会对新闻生产的道德标准产生的影响。⑥在比较的维度上,有研究者认为,传统新闻伦理体系对新闻的公正性以及新闻源核查的强调,正在转化为对用户协作、生产过程透明性以及后期纠错(postpublication correction)机制的强调,因此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新闻伦理体系提出了几乎是颠覆性的修正要求。⑦在认知或行为层面,有研究指出,数字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普遍对这一变化体现出了抵制(resist)或抗拒(reject)的情绪,“他们以前会将伦理作为一种合法性考量的基本原则,今天却只会将伦理当作一种(适应技术环境的)工具”。⑧在新伦理体系建构方面,有多位学者展开过深入的讨论。如Ward和Wasserman曾提出建立互联网媒体的“开放伦理”(open ethics),即在全球话语体系下,允许不同的文化与专业思维参与新新闻伦理的建构;⑨Singer更加细致地设计了这一新体系的建构路径,包括“对公共服务的强调,对信息准确性的承诺,对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的抵制,以及独立于经济压力的业务体系”;⑩
Fourie则提出应当超越新闻伦理或媒介伦理的概念界限,而致力于建立“合乎伦理的传播系统”(ethical communication)这一价值体系,进而为数字媒体时代设定新的规范理论。[11]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未就“数字新闻伦理”(digital journalism ethics)这一概念的内涵达成共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主导新闻业发展转型的数字技术进化速度太快,这一现状使大部分相关研究都“不得不”紧扣某一种特定的技术在新闻业内制造的伦理困境,如大数据的检索和来源问题、[12]算法的客观性和透明性问题,[13]等等。但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那就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凸显出探索建立新的伦理体系,乃至新的新闻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的紧迫性,研究者必须在数字新闻研究中重视对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探索,从而不断明确和锚定新闻从业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14]本文主要采用Ananny提出的分析框架,回归经典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分别从道义论(deontology)、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三个维度,对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进行探索性的建构;而在分析中,这三个维度又分别对应着我们理解新闻伦理问题的三个层面:宏观的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中观的新闻机构及日常新闻生产机制,以及微观的新闻从业者对自身的约束。[15]这一框架有两个显著的优势:第一,它使研究者得以超脱于具体的技术形式,将“数字化”视为当代新闻业所拥有的一种总体性生态加以理解,以形成稳定的、规律性的认识;第二,它兼顾伦理分析的基本框架和新闻业所拥有的独特的结构,使得我们对规范理论的探讨得以更加紧密地与新闻业自身的特征及发展需求相结合。
在方法论方面,本项研究采纳与经典媒介社会学研究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文化研究的视角,这种视角将新闻业内的生产实践、身份认同和专业主义视为特定人群(新闻从业者)的特定生活方式,并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获取一手的质化经验资料。具体而言,笔者在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之间,针对不同的研究议题,对美国、英国和瑞士三个国家共106位一线新闻从业者和数字新闻用户进行了半结构或无结构的深度访谈,尝试通过一手的质化经验资料,勾勒出数字时代的全景式的“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16]这些受访者分别来自17家新闻机构,其中既有ProPublica、Slate、美国在线等数字新闻机构,也有《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瑞士法语广播电视公司(RTS)等正在进行数字转型的传统新闻机构(见表1)。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一部分访谈是通过Skype等即时通讯软件和电子邮件书面采访完成的。绝大部分访谈用英语完成,一小部分访谈通过法语的电子邮件通信完成。
本文认为,既然新闻学存在的合法性几乎完全来源于它与新闻业之间的辅车相依的关联,那么新闻理论的经验基础必然是也只能是一线新闻从业者对行业的认知、态度和判断。文化研究要求研究者“穿上他人的鞋子走路”,本土地、自觉地完成对生活经验的理论化,这种视角以往甚少为新闻理论研究人士所借鉴。笔者期望通过这项研究,将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的价值注入新闻理论的发展路径。本文即从上述质化的经验资料出发,对一线新闻从业者对数字时代伦理问题的认知和反思进行呈现和挖掘,尝试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本文认为,一线新闻从业者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日常生产实践中对伦理问题形成的种种思考,可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清晰的认知地图,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数字新闻伦理体系的建构。
具体而言,本文分别从道义论/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功利主义/新闻机构及其日常生产,以及美德伦理/新闻从业者的自我约束三个方面,对访谈资料进行结构性整理。在结论中,也将紧扣这三个方面完成理论化工作。
二、数字新闻的道义论
道义论缘起于康德的哲学思想,强调“道德的基础是人类交流行为中的职责和义务”。[17]在新闻伦理范畴,道义论的话语常见于对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的讨论之中。在传统新闻伦理体系中,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被视为个体自由和制度民主的重要保障,一如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中所强调的:如果人民要想在拥有自由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就必须确保他们拥有接近真实信息的权利,而且这些信息必须能够公正呈现每天发生的重要事务,以及这些事务对普通人的影响。[18]对于传统新闻伦理为新闻业设定的这一“宏大”责任,受访的新闻从业者呈现出观点的分化。其中,大部分受访者坚持新闻业在传统时代被赋予的这种社会责任,并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某些偏向的批评,来强调新的伦理体系绝不可放弃对社会责任的坚守。例如,一位来自美国某新闻网站的编辑称:“我其实从来都对算法所声称的‘中立性’不以为然。对于某一条报道来说,大数据是有用的,也是高效的,但在总体的图景上,算法只会利用已有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社会永远是有限的。新闻要想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克服这种‘绝对客观’的话语,要看到数据并不是万能的。”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受访者则干脆认为,大数据往往是被操纵的,她反问:“究竟人类生活的哪些领域的数据能够被收纳进所谓的‘大数据’?又是哪些机构和人有资格对这些数据的质量和用处进行分类、分级?如果整个行业都把选择和判断的权力交给大数据和机器人,那么这个行业还能称自己为新闻业吗?我们还有资格称自己为新闻从业者吗?”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新闻的“社会责任论”不但在数字时代的新闻从业者群体中有着深厚的认知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理解和探讨其他层面的伦理问题(比如机构层面、个体层面)的前提。很多新闻从业者用社会责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话语(如公共服务),来抵御或至少延缓数字技术给自己造成的心理冲击。
不过,也有一些受访者认为,数字技术本身其实并不存在破坏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偏向,恰恰相反,对于数字技术的正确使用也许可以令新闻业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例如,一位瑞士的受访者称:“我们不得不承认,算法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关注到了以往不会去关注的东西,为我们看待某些事务打开了眼界,让我们能够理解一些社会现象的潜在意义,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好的指引。”但持有这样观点的受访者往往也会同时强调“人”的因素不可或缺,即人对于技术的全面掌控是技术的发展能够服务于新闻业的“终极伦理”的保障,一如一位来自美国某报纸的受访者所说的:“比起威胁来,我更愿意将数字技术的潮流看作是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机遇,只要从业者对技术保持清醒,坚持新闻业的公共服务精神,那么整个行业有比过去更大的可能去克服责任和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构成更加符合民主的精神。”当然,也不难发现,持有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大多来自“数字化”成色更足的新闻机构,比如新闻网站。在这些机构,新闻生产的技术和新闻分发的渠道已完全是数字化的,其从业者对技术的态度也更加温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Willnat等人在2013-2014年间展开的一项调查的结果:传统新闻媒体(电视和报纸)的从业者比其他新闻媒体从业者更重视新闻业的传播者(disseminator)角色,进而也拥有更加强烈的公共性理念。[19]当然,也有少数受访者对“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从始至终都是权力结构操纵的结果。如一位英国的受访者所言:“在新闻业的社会责任中,很少包括对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注;追求‘多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一种更加基础的、本质性的偏见,而数字时代到来以后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过,持这样观点的受访者很少,其对支配欧美新闻业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的分析,也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范畴。
总体而言,无论如何看待传播技术在新闻业的社会责任中扮演的角色,受访者皆普遍认同“社会责任”是新闻业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立足和发展的基本道义,这一点并未因为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出现显著的变化。这也表明,至少在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责任论”在数字新闻伦理体系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它既被新闻从业者用来规划自己在行业中的长远价值目标,也被运用于遏制数字化的新闻业可能出现的反民主倾向。不过,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还需要从业者和学界展开全面的反思和探讨。正像Glasser所指出的那样:新闻业不能在高扬民主大旗的同时,又以一种独断专行的立场去理解伦理问题……这样的新闻业不过是“披着民主外衣的独裁机构”而已。[20]
三、功利主义视角下的数字新闻伦理
功利主义的新闻伦理观主要源于边沁的古典功利主义理论,这种伦理观的核心在于探索和追求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令最大数量的人受益。[21]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功利主义通常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幸福)作为评判制度“善”与“恶”的标准,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为一种缺乏人性考量的、绝对化的理性。正如博克斯所指出的:“功利主义往往通过对导致未来特定后果的现实行为的强调,来批判甚至否定一切感官化的生活……包括个体化的情感与动物本能。” [22]功利主义忽视情感和个体的(偏离集体趋势的)价值选择的倾向,往往很容易跟各种形式的社会进化论结合,甚至,在当代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进化论功利主义”(evolutionary utilitarianism),其主要的修辞就体现在“功利主义者应当遵守哪些能够让人类幸福最大化的道德准则”。[23]在某种程度上,数字技术在新闻业内的迅猛发展与功利主义伦理观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对数字技术的引入和使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行业效率,以更低的成本完成新闻的流通并令更大范围的用户“受益”,因此即使在传统新闻伦理体系内,也往往存在着支持和鼓励技术的倾向。在新闻从业者的日常生产实践中,追求“效率”和“受益”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是新闻从业者采纳、理解和反思数字新闻生产技术的重要的认知依据。
然而,在访谈中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持有较为强烈的批判态度,并将对这一观点的批评作为其反思数字技术的话语基础。其中,数字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时效性”需求,成为其批判的重点。比如,一位来自瑞士的受访者称:“当下新闻业的道德问题,几乎就是由新闻机构过分追求时效造成的,每一个新闻机构都想抢在同行之前提供信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不可避免导致新闻中存在比以往更多的错误,这种错误正在一点一点将新闻变成一个可笑的东西。”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受访者也表示:“对速度的追求,迫使记者和编辑不得不与用户合作以获得一手信息,也迫使新闻机构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去解决纠错的问题。如果为了速度连基本的准确性都不要了,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公众相信新闻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呢?”当然,甚少受访者会明确将日常新闻生产中这种为竞争而牺牲准确性的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数字技术环境”联系起来,他们更多是在批评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具体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出了新闻从业者对于自己“在新闻生产中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做出的反应——他们感觉自己是在“被迫”做出过于功利主义的选择。
在具体的技术应用层面上,受访者的批评和反思主要集中在大数据和算法两个领域。
针对大数据,受访者大多强调其可能导致的两类伦理问题:一是隐私权问题,二是数据操纵问题。例如,一位来自英国的受访者指出:“记者被要求使用数据来完成报道,但却无法确定数据的来源,比如,这些数据是不是用非法的手段收集来的?拥有这些数据的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证数据的合法和透明?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在被记者和编辑使用之前,是不是存在被篡改的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新闻机构或许还能知悉一些,但记者完全是一头雾水的。”而一位来自美国的受访者也称:“必须要警惕数据对私人空间的侵袭,尤其是……当这些数据被用于新闻报道,它所产生的破坏力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很多受访者认为,尽管与数据来源相关的很多问题都是法律问题,但新闻机构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却不得不在道德和效率之间做出选择。一些受访者失望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机构往往会选择后者,做出这一选择则多半是迫于生存压力。
至于算法,受访者的意见较为集中:多针对算法的透明性问题。很多受访者表示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足以对自动化报道生成的整个过程进行必要的干预,因而产生了一种失控感。一位来自英国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保护新闻源是全行业一个不言自明的准则。但是,当算法代替记者和编辑做了绝大部分工作,我认为新闻源也相应地不应该继续是一个秘密。”还有一些受访者表示,算法的不透明有可能导致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信息的准确性。一位美国受访者提到,美联社曾在一篇商业报道中,因算法的编码过程出了问题而生成了错误的内容,将某公司过去一年的经营情况完全弄反了。用这位受访者的话来说:“如果算法的编码过程没做好,那么软件完全有可能自动生成错误的报道。更糟糕的是,对于编辑来说,这个过程是完全无法介入的,我们只能在报道发布之后,再去纠错。我想,这严重地损害了新闻的公共价值。”此外,还有受访者提出,基于算法的自动化报道或许不应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而应该有专门的生产规范和伦理规则。
总体而言,在较为中观的层面,本文的受访者普遍表示了对数字技术冲击下的新闻机构过分追求效率、收益和影响力的功利主义态度的批判。大多数人认为,应当强化“人性”在新闻生产机制中的重要性以制衡日趋失控的功利主义倾向。至于如何在日常生产实践中体现“人性”的存在和影响,大多数受访者并未达成共识。但无论如何,受访者均在如下问题上持有高度相似的观点,那就是新闻机构应当对于数据的来源、编码的质量以及经算法生成的报道可能具有的潜在法律及道德风险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同时也应当在盈利和新闻报道质量之间做好平衡。在数字媒体时代,显然新闻从业者对新闻机构的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机构而言,平衡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humanitarianism)之间的关系或许将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伦理难题。
四、新闻从业者对自身的美德要求
在伦理学体系中,美德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对自身的道德要求。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对于“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思考和回答。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对美德问题的认识不可避免要受到新闻业的行业规范和从业者的主流身份认同的影响。因此,新闻从业者的美德是人性美德与职业美德相融合的产物。传统新闻伦理体系下的美德标准较为多元,但这些标准可被大致归结为三方面的要求:性质(character)先于结果(consequences)、“善”(good)先于“对”(right),以及主体相涉(agent-relative)价值与主体中立(agent-neutral)价值并重。[24]在新闻从业者的个体认知中,上述三方面的要求往往具体化为一系列行为原则,包括关切(care)公众及弱势群体的利益、避免对无辜的人构成冒犯或伤害、尽量以客观的方式呈现与自身所在社区或群体利益相关的冲突、努力追求报道过程的程序合法及正义,等等。[25]这些行为原则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自身与行业、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对于传统新闻伦理的各项美德原则,本文的受访者均保持着较为强烈的认同。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新闻从业者应当具有一种源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善”,尽管在日常工作中要遵从理性和客观的要求,但“善”应当是理性和客观的基础。正如一位瑞士的受访者所说的:“要想成为一名好新闻记者,你首先要是一个好人……当然,这不是指你要同情心泛滥,或者时时刻刻想要做拯救地球的英雄。善良是贯穿在日常新闻工作中的,如同一种世界观,它的存在确保你的新闻报道并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事实和不关己事的冷漠。”还有一位美国的受访者提出,“善良与否”主要体现在新闻从业者对待公权力和对待公民个体的态度的差异上——在很多时候,对公权力的审视越是严苛和冷酷,反而表明了从业者的行为越是合乎善的法则。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对个人美德层面的“善”的追求,并没有因新闻生产的技术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尽管如此,受访者还是对于数字技术可能对从业者的总体美德水平构成的侵蚀表示担忧。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数字技术给记者和编辑群体带来了太多的“诱惑”,而新闻从业者要想抵御这些“诱惑”,就必须对技术的负面效应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比如,一位英国的受访者认为,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诱使”从业者将自己变成业务上的多面手,其结果则是新闻生产的结果导向。他说:“我认为应该将那种需要时时刻刻盯着最新的信息流、留意其他媒体报道的标题、关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的职位,和那种需要人潜下心来寻找有价值的选题、撰写有深度的文章、追求专精于某一领域的职位区分开来。将生产调查性报道的人和只知道在推特及Facebook上发帖子的人混为一谈,是十分可笑的。”而在另一位瑞士的受访者看来,数字技术对时效性的过分强调仍然是最值得警惕的伦理危机:“在数字化之前,编辑部门已经是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了。数字化完成后,情况变得更加荒唐可笑,很多编辑甚至会因为偶尔离开了自己的办公桌而产生愧疚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我们常说假新闻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新闻从业者在时间的压力下不可避免会犯的错误。”
很多受访者认为,新闻从业者的美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们生产的新闻不止揭示事实本身,而且也能够让新闻符合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性。例如,一位美国的受访者即表示算法在新闻生产中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人的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他说:“算法只会执行程序的命令,而不会对选题和表述做出合乎人情的判断。我很担心一种情况发生,那就是当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是由程序自动生成的,记者们会渐渐习惯于这种过于冷静,甚至过于‘客观’的新闻。这样一来,新闻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就被忽视了,那就是让读者能够知道自己究竟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做出正确的选择。”也有受访者指出,数字技术其实并不必然带来负面的影响,它对“协同性生产”(participatory production)的强调或许会令新闻从业者更多地理解和吸纳普通用户的观点,从而使其观念和行为更加符合“善”的标准。当然,持这一观点的受访者大多供职于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新闻机构。如美国某新闻网站的一位受访者称:“数字新闻记者其实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伦理)标准,而这套标准其实是在从业者和公众的协同关系中被制定出来的。由于读者在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因此记者的行为也就要受到更多力量的制衡。”
但无论持有何种观点,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对新闻从业者的美德给予很高的重视。一些受访者甚至认为个体美德水准的重要性要高于整个行业所设定的共同的价值标准,正像一位瑞士受访者所说的:“当行业的规则与自己内心的选择发生冲突时,应当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这实际上体现出了传统新闻伦理体系在从业者个体认知和情感层面的稳定性。这一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García-Avilés的观点:新闻从业者对自身的美德要求并未因新闻机构的类型(传统或数字)差异而有本质的变化,作为“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的新闻从业者“有能力很好地应对当下的种种伦理挑战”。[26]
五、建构中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
本文采用成熟的分析框架,分别在道义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三个层面,以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数字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进行了探索。通过对来自一线新闻从业者的伦理认知、认同状况的归纳,本文认为,对于数字新闻伦理体系的建构工作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和挑战,也有不同的目标。
在宏观(新闻行业)层面上,传统的社会责任话语始终在一线新闻从业者的认知中占据核心地位。尽管人们对于数字技术和新闻业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理解,但这并未动摇“社会责任”本身作为现代新闻业的道义基石这一事实。新闻业以民主为价值宗旨,通过生产和传播基于事实的信息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点并未因数字时代的到来而有所改变。在我们对数字新闻伦理体系进行建构时,仍需紧扣“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内核,以追求民主作为新闻伦理道义论的基础。
在中观(新闻机构)层面上,本文发现,数字技术的介入无节制地放大了传统新闻伦理中的功利主义面向,从而在日常生产实践中制造了功利导向的伦理危机。数字新闻机构存在盲目追求效率、价值虚无以及技术崇拜的倾向,“人”的存在和价值则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这凸显出了在我们“将计算机伦理移植到新闻场域时”,[27]积极而有效地引入人本主义观念的重要性。因此,在日常生产和机构运作层面,以人本主义遏制功利主义的蔓延,强调人相对于数据和算法的价值主体地位,并针对各类数字技术的具体特征探索建立可为全行业普遍遵守的新生产规范,是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
在微观(新闻从业者个体)层面上,不难发现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美德原则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其“权重”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超越了整个新闻业的社会责任。数字技术的普及显然在从业者和行业、机构之间制造了矛盾,记者和编辑不再充分信赖行业和机构能够“代表”自身,在面对伦理挑战的时候做出“善”的选择。因此,与传统新闻伦理体系不同,数字新闻伦理中的个体美德和全行业的社会责任不再基于逻辑上的一致性。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会以一种更加自我、更加个人化的标准,在遭遇伦理困境时做出符合美德标准的选择。如何在技术哲学的框架内,调和新闻行业社会责任和新闻从业者的美德标准两者之间的关系,透过两者表面的冲突,建立起一种具有内在连续性的观念体系,也是数字新闻伦理建构的重要工作。
因此,我们不妨将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和美德原则作为数字新闻伦理体系的三个核心观念支柱。而对于未来的新闻伦理研究来说,如何弥补抽象而宏大的“社会责任”与人本主义、美德原则等嵌入具体新闻生产实践和个人选择的伦理原则之间的逻辑裂缝,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①TAVANIH. H. Ethics and Technology: ControversiesQuestionsand Strategies for Ethical Computing [M]. New Jersey: Wiley2011p. 36.
②WARDS. Radical media ethic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42 (4)p. 469.
③WARDS. Global Journalism Ethics [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10.
④LEWIS, S. C and WESTLUND, O. Big data and journalism: epistemology, expertiseeconomicsand ethic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53 (3)p. 459.
⑤COOPERT. W. New technology effects inventory: forty leading ethical issues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99813 (2)pp. 71-92.
⑥DAVIS, C. and CRAFTS. New media synergy: emergence of institution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0015 (4)pp. 219-231.
⑦ESS, C. Digital Media Ethics [M].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2009.
⑧SINGERJ. Getting past the future: journalism ethics, innovation, and a call for “flexible first” [J]. Communica??o e Sociedade201425p. 67.
⑨WARDS. and WASSERMANH. Towards an open ethics: implication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for global ethics discourse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1025 (4)pp. 275-292.
⑩SINGERJ. Partnerships and public service: normative issues for journalists in converged newsrooms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0621 (1)p. 30.
[11]FOURIEP. J. Normative media theory in the digital media landscape: from media ethics to ethical communication [J]. Communicatio, 201743 (2)pp. 109-127.
[12]BRADSHAWP. Data journalism [C]. In L. Zion and D. Craig (eds). Ethics for Digital Journalists: Emerging Bet Practices. New York: Routledge2014pp. 202-219.
[13]GILLESPIE, T.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 [C]. In T. Gillespieet al. (eds). Media Technologies: Paths Forward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MIT Press2014pp. 167-194. MCBRIDEK. and ROSENTIELT. New guiding principles for a new era of journalism [C]. In K. McBride and T. Rosentiel (eds). The New Ethics of Journalism. Thousand Oaks, CA: CQ Press2014pp. 1-6.
[14]CULVERK. B. Disengaged ethics: code development and journalism’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711 (4)pp. 477-492.
[15]ANANNYToward an ethics of algorithms: conveningobservationprobabilityand timeliness [J]. Science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201541 (1)pp. 93-117.
[16]ANDERSONC. W. News ecosystem [C]. In T. Witschge,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6p. 410.
[17]DORRK. N. and HOLLNBUCHNER, K. Ethical challenges of algorithmic journalis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75 (4)pp. 404-419.
[18]HUTCHINS COMMISSION.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Chicago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7.
[19]WILLNAT, L.WEAVER, D. H. and WILHOITC.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age: how journalists and the public think about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ism Studies201920 (3)pp. 423-441.
[20]GLASSER, T. The privatization of press ethics [J]. Journalism Studies201415 (6)p. 699.
[21]BENTHAM, J. The Rationale of Reward [M]. London: Forgotten Books2015.
[22]BIRKS, T. R. Modern Utilitarianism, or the System of PaleyBenthamand Mill Examined and Compared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74p. 159.
[23]MULGANT. Understanding Utilitarianism [M]. New York: Routledge2007p. 47.
[24]QUINN, A. Moral virtues for journalists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0722 (2-3)pp. 168-186.
[25]STEINER, L. and OKRUSCHC. M. Care as a virtue for journalists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0721 (2-3)pp. 102-122.
[26]GARCIA-AVILESJ. A. Online newsrooms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exploring digital journalists’ applied ethics [J].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01429 (4)p. 269.
[27]SPINELLOR. A. Cyberethics: Morality and Law in Cyberspace [M]. Sudbury: Jones & Barlett2011p. 11.
常江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