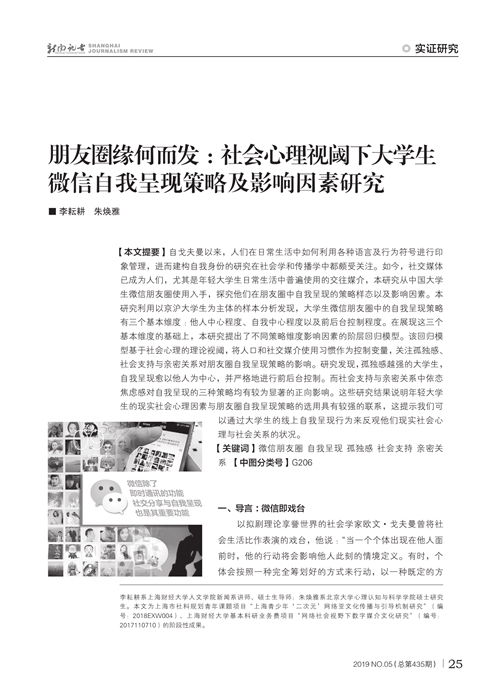朋友圈缘何而发:社会心理视阈下大学生微信自我呈现策略及影响因素研究
■李耘耕 朱焕雅
【本文提要】自戈夫曼以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利用各种语言及行为符号进行印象管理,进而建构自我身份的研究在社会学和传播学中都颇受关注。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交往媒介,本研究从中国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使用入手,探究他们在朋友圈中自我呈现的策略样态以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利用以京沪大学生为主体的样本分析发现,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策略有三个基本维度:他人中心程度、自我中心程度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在展现这三个基本维度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不同策略维度影响因素的阶层回归模型。该回归模型基于社会心理的理论视阈,将人口和社交媒介使用习惯作为控制变量,关注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对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孤独感越强的大学生,自我呈现愈以他人为中心,并严格地进行前后台控制。而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中依恋焦虑感对自我呈现的三种策略均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年轻大学生的现实社会心理因素与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选用具有较强的联系,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大学生的线上自我呈现行为来反观他们现实社会心理与社会关系的状况。
【关键词】微信朋友圈 自我呈现 孤独感 社会支持 亲密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导言:微信即戏台
以拟剧理论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将社会生活比作表演的戏台,他说:“当一个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他的行动将会影响他人此刻的情境定义。有时,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 ①戈夫曼将此种行为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在大多数情境下,这样有目的有策略的自我呈现需要借助媒介完成。时至今日,随着互联网和手机智能终端的出现,人们前所未有地被联系在一起,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原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变成了社交媒体中一场盛大的展示。②
“惯常的恰当行为在已经变化了的交往场景中不再‘恰当’,这就迫使角色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 以及自我呈现的策略。③在中国,微信是眼下最为普遍的社交媒体。随着手机等移动媒体的普及,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受众都可以注册并使用微信。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报道,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微信的用户达到了10.4亿,并占据了国内网民 23.8%的上网时间。④正因有此体量的用户及可观的使用时间,有学者直言微信在中国当前社会状况中,成为了人们的“在世存有”。⑤
对年轻人来说,微信除了即时通讯的功能,社交分享与自我呈现也是其重要功能。社交平台自身的特点,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呈现策略。微信的自我呈现多集中在朋友圈的功能之中。相比于其他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具有更强的实名性、隐私性和封闭性,它既像是现实社交网络的线上复刻,又在印象管理技术上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微信朋友圈具有屏蔽、设置分组可见、设置三天可见等管理和控制的功能。这些功能使得用户可以更加主动地经营自己的呈现形象,进而管理他人眼中的自我印象。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拟剧论在社交媒体上演化出的新特点。因此,研究社交媒体上中国年轻人的日常自我呈现,微信朋友圈是最好的样本。
自我呈现的样态与策略同哪些因素有关、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如何影响社交媒体,一直是新媒体研究学者关注的议题。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西方语境。他们关注由计算机中介(computer-mediated)的社交媒体呈现及沟通行为与线下面对面呈现及沟通行为的比较。但在中国语境下,类似的实证研究付诸阙如。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实证方法从社会心理的理论视阈切入,探究大学生社会心理因素(以孤独感、社会支持和亲密关系为三个衡量指标)对其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形式与策略的影响。
二、社会心理视阈下的线上自我呈现
(一)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与策略选择
拟剧理论将人们在他人面前的行为界定为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既受到观看表演的特定观众的影响,又反过来会对这些观众施加影响。同时,表演又是一个持续存在的过程,个体可以在该过程中调整行为并选择性地表现细节。此外,戈夫曼认为这种表演在时空上是有界限的,是发生在特定有限的环境中。在戈夫曼的理论中,这样的情境限定主要以物理空间为划分依据,比如前台与后台的区分。而这一点在梅罗维茨的理论中有所修正,他认为情境的区分应该以信息的流动为界限,情境应是媒介形成的信息环境。在其著作《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梅罗维茨将戈夫曼的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理论相融合,阐述了在电子媒介时代,变化了的时空感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其中,他最引人注目的论述莫过于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地点中相互联系的成分被撕开了。无论一个人现在在哪里——在家、在工作,或者在汽车里——他都被接触着和接触着别人”。⑥由此,戈夫曼意义上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前台和后台之间开始界限模糊,从而出现了被电子媒介中介的中台。这就便于我们理解为何用戈夫曼的理论来研究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是可行的。虽然使用社交媒体的个体,在线上自我呈现的那一时刻,其周围可能并无实际存在的“观众”,但社交媒体所塑造出的信息环境,对个体进行自我呈现时的影响依然有效。
然而如何用线下人际传播的理论评估由计算机中介的线上自我呈现是一个新媒体研究的焦点议题。社会再现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⑦、社会信息处理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⑧以及超个人理论(hyperpersonal theory)⑨是研究当代线上自我呈现和自我披露的经典理论。社会再现指的是互动者感知到的一种传播媒介将其形象再现的程度。这些感知到的再现程度包括亲密度、即时度以及在媒介中言语或非言语的语境线索的丰富度。⑩尽管这些再现程度都是媒介使用者的主观感受,但是有研究表明感知到的媒介再现程度越高,使用者自我披露意愿就越强。[11]这一理论提示我们,社交媒体使用者的自我呈现意愿及策略,与他们的心理感受和对媒介的认知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则进一步指出,由于非语言线索(如表情、肢体语言、社会环境等)在计算机中介沟通中的匮乏,所以在电子媒介上的沟通与呈现需要更多自我信息的披露。这样,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沟通可以获得比面对面沟通更好的人际效果。[12]但新近的研究也同时表明,此种电子媒介的自我披露依然远远低于面对面沟通的披露程度。[13]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原有理论假设可能存在的缺陷,但更有可能的是在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的社交媒介已经远远不是之前那样缺乏非语言线索的媒介形式了。以微信为例,在传播和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各种表情包、图片甚至视频、多媒体都可以弥补文字语言的不足。所以社交媒体甚至可能比面对面传播更多非语言的线索。社会再现理论和社会信息处理理论都较为关注媒介形式本身或被感知到的变化所带来的自我呈现及披露样态的不同。而超个人理论则更关注媒介使用者和媒介形式之间的结合所带来的自我呈现样态和策略的变化。换句话说,在超个人理论中,更重要的是人怎样使用媒介而非媒介怎样规定人。超个人传播有几个重要特征:其一,因为非语言线索的缺乏,使得个人会更加自觉并有策略地进行自我呈现;其二,接收者会给予呈现者有限的反馈以建构呈现者的形象;其三,用以传播信息的媒介为此过程提供支持,因为电子媒介常允许人们在发送信息之前不断地修改与重建;最后,反馈机制鼓励正面评价而非负面评价,这些正面评价又反过来强化呈现者的正面形象。[14]超个人传播把握了现代社交媒介语境下,以社交沟通为目的的自我呈现的一个重要特质,即人对自己形象的主动建构以及通过他人评价来不断修正和控制自我形象的策略性实践。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即电子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印象管理”。[15]在戈夫曼那里,对自我呈现的印象管理是一整套日常交往的符号和行为控制的策略及技术。有学者引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的“人性游乐场”概念,认为在“互联网中,人们真实、复杂的一面被缩小了,完美、精致的一面则被放大了。在分享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己被重视、被认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还会渐渐对自己产生一种自带光环的幻觉”。[16]这种幻觉正是由于他人所给予的正面评价带来的。因此,为了维持这种幻觉,人们必须围绕他人的评价来施行自我呈现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看重评论、在发布每个朋友圈的时候都字斟句酌并反复修改、对点赞和快速回复有所期待、事先考虑朋友圈发出后的结果以及精挑细选要发布的照片图片等。在本研究中,这一系列的策略被我们认为是以他人为中心的呈现策略。
国外对社交媒介自我呈现的研究多借鉴戈夫曼的理论,而研究对象多以Facebook为主。Mendelson和Papacharissi证明了社交网站上的图片和传统印象管理标准的一致性。[17]Rueda-Ortiz和Giraldo用戈夫曼的理论来分析Facebook个人资料中的图片所表达的个体需求和描绘现代社会生活的身份探寻,以此来说明在Facebook上自我呈现的方式。[18]有研究证明线上自我呈现和青年时期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发展存在一定关系。Weber和Mitchell通过量化研究发现,线上自我呈现会引起个体的自我反省,进而促进青年身份认同的发展。[19]Michikyan等人则发现刚成年的年轻人会在社交网站上呈现出多种自我形象,并认为青年的自我认同和其在社交网站上的自我呈现有一定联系。[20]在微信语境下,黄华和张旭东认为朋友圈是青少年主观感受到“自我”在网络中的延伸,从而表现出“真实的理想自我”。[21]这些研究都说明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固然会围绕他人评价展开。然而,相当一部分的自我呈现,目的却是自我表达和社会生活身份的再确认。从这一点来看,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可能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呈现策略。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之命名为自我中心程度。这一维度的呈现策略包括常在朋友圈表达喜怒哀乐、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我反思以及常发自己的照片等。
反观国内社交网络上自我呈现的文献,则主要从呈现策略和内容两方面的研究入手。具体到微信语境下的自我呈现,李华伟将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策略分为“自我审查”、“隔离观众”、“销声匿迹”等。自我审查的审查内容包括发布动态的时机、内容、呈现方式、频率等。“隔离观众”是通过设置朋友圈权限,并将圈内好友分成不同组,各组可以看到的内容各不相同。“销声匿迹”主要体现为删除或隐藏朋友圈动态,是对之前所做的表演进行的补救。[22]这些策略都说明人们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会主动地通过技术设置控制前后台的呈现方式。因此,本研究中,我们在以他人为中心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之外提出前后台控制程度作为另一个可能的策略维度,针对这一维度,我们所测量的策略项包括屏蔽朋友圈、设置分组可见、设置三天可见以及删除朋友圈动态等。
综上,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即:
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策略是否存在他人中心程度、自我中心程度以及前后台控制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包含了怎样的具体呈现策略。
(二)孤独感、社会关系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策略
当代社交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人类借助工具克服时空传播障碍的技术表征。对于社交的渴望首先来自于人类自身对于孤独感的克服。孤独感通常产生于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数量和质量低于他的期望之时。[23]孤独感可以看作是衡量人际关系的一种情感性因素。Shaw 和 Gant的一个历时性研究揭示,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地降低孤独感、抑郁情绪,并极大地提高使用者的自尊感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24]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假设孤独感和互联网的积极使用也存在着密切关系。Hughes 等人的研究就旨在说明人格特征与社交媒介信息和社交媒介使用之间的分别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理论中神经质(neuroticism,一种经历消极情绪状态的持久倾向)的人格特征与Facebook使用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Facebook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将Facebook视作缓解孤独情绪的工具。[25]谭海燕的研究发现,朋友圈自我表露中的情感状况、兴趣爱好和孤独感分别呈正相关、负相关。[26]如果说孤独感高者需要通过更加理想的自我呈现来弥补自己的社交匮乏,那么有理由假设其自我呈现时存在较高的他人取向,但是却较低地以自我为中心,并呈现有较高的前后台控制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一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a:孤独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他人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1b:孤独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自我中心程度越低。
研究假设1c:孤独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前后台控制程度越高。
然而,也有研究同时指出,孤独感和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是“虚假”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孤独感越高的人似乎更愿意使用互联网,是社交焦虑而非孤独感在起作用。[27]Correa及同事的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和使用者的个性的关系,他们发现,越是外向、情感稳定以及开放个性的人越会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28]尽管互联网使用与以社交、展现或分享为目的的社交媒介呈现有本质不同,本研究依然从两个方面反思了这一研究假设:首先,在微信这样一个强社交属性的媒介上,验证孤独感和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其次,在孤独感之外,我们同时将与社交焦虑相关的社会关系因素纳入考量,这两个社会关系因素分别是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以此弥补孤独感或社交焦虑忽视社会关系宏观变量的缺憾。
林南及其同事将社会支持定义为“由社区,社会网络或亲密伴侣感知到或实际的工具性及/或表达性给予”。[29]据此,社会支持是在个体面临困难或威胁时可以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这一定义强调从他人处得到帮助以解决困难或问题。基于此,社会支持可以被理解为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个体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可以作为反映该个体人际关系好坏情况的指标。Shaw 及 Grant的研究揭示了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使用者感知到的社会支持。[30]换言之,现实中的社会支持也会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产生影响。而具体就社交媒介来说,谢笑春等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微信使用强度和积极应对的关系中起正向中介作用。[31]这说明,社会支持越高的个体,越能感受到社会关系和支持对自己影响的重要性,也越需要通过主动的自我呈现策略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a: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他人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2b: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自我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2c: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前后台程度越高。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支持,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另一个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亲密关系。对于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往往在异地独立生活,远离熟悉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大学生正处于刚刚成年阶段,对于爱情的追求是重要的社交动机,爱情也是其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Hazan及Shaver将此种基于浪漫爱情的亲密关系概念化为依恋过程(attachment process)。[32]依恋的研究最早始于婴儿对母亲的依恋。Ainsworth等人通过在实验室中观察婴儿与母亲分离所表现出的反应,将婴儿依恋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型。[33]Hazan 和Shaver的研究证明这三种依恋类型也可以应用于成人的恋爱过程中。[34]Brenna等人收集了14个已有的成人依恋量表,选出323个题目,施测后进行因素分析,抽取出两个因素。根据题目内容,把这两个因素命名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35]依恋焦虑主要是指对被他人拒绝或抛弃的恐惧,从而产生对伴侣的过度依赖感。而依恋回避指出于对依附和亲密关系的恐惧而产生的自我封闭和回避感。关于亲密关系与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目前比较缺乏,但是学者曾经考察过手机使用与亲密关系与依恋的研究,研究发现在亲密关系中的人更频繁地使用手机,并且手机使用与依恋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36]更细致的研究揭示了在年轻大学生中,依恋回避会导致较少频率的手机和短信使用;而可以被视作社交媒体前身的社会网络媒体(social network site)使用则对依恋焦虑的人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支持。[37]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就预测朋友圈呈现策略来说,亲密关系可以作为预测不同策略的重要变量。而为了测量的方便与准确,本研究对亲密关系的界定使用依恋理论的类型区分。因此,依恋焦虑感越强,个体更可能在自我呈现中采用他人中心和前后台控制的策略;而依恋回避感较强的个体则更可能采取自我中心的策略进而保持与亲密对象的距离感,但同时又能够维持一种较高满意度的亲密关系。综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a:依恋焦虑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他人中心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3b:依恋焦虑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前后台控制程度越高。
研究假设3c:依恋回避感越高的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的自我中心程度越高。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测量
人口变量。研究调查的人口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当前的恋爱情况。
除了研究所关注的孤独感、社会支持与亲密关系作为主要的自变量,该研究还加入社交媒介使用频率作为辅助的控制变量。研究调查了受访者使用国内主流的三个社交媒体的频率,分别为:微信、微博、QQ,设置从“从不使用”到“每天使用”的五级量表。
孤独感变量的测量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该量表是孤独感心理测量的经典量表。Hays和DiMatteo修订了该量表,将其简化为8个项目的ULS-8量表。他们的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近似原版量表,并且比原版更为简洁。[38]周亮测量了ULS-8量表在中文语境下的信效度,发现反向计分条目3和条目6会影响量表的因子结构。在去除两个反向计分条目后,新形成的ULS-6除了信效度良好外,还更加符合原量表的理论构想。[39]本研究根据前测的因子分析结果,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因此最终的施测量表去除了反向计分条目,保留6个项目(ULS-6)。对于本次样本采集,此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7。
社会支持变量的测量采用叶悦妹等编制的大学生社会支持量表。[40]为方便施测,实际采用的版本对量表中的题目进行了筛选。原量表有17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考虑到题目长度的问题,筛选时每个维度都只保留了三个条目,因此最终施测版本采用了9个条目。但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只发现了两个因子,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社会支持的变量,所有9个条目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0。
亲密关系变量的测量采用学界广泛使用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简版(ECR),该量表共有36个条目。本研究采用经Wei等人修订的该量表简版,共有12个条目,选项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采用七级量表。[41]中文版参考李同归等对原始量表的翻译和修订。[42]简版量表与原量表一致,分为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各6个条目。在本研究前测的因子分析中提取出的2个主成分因子及对应条目均和原量表一致。其中,依恋回避因子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4,而依恋焦虑因子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均具有较高信度。
根据文献回顾和理论推演,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策略变量的测量使用自编量表(具体内容及分析结果见研究结果部分)。量表整体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3。选项从不符合到符合,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二)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通过问卷星编制问卷并生成在线链接发放。主要传播方式为高校学生间的人际传播,具体方式不限于直接分享链接给符合条件的朋友,朋友圈、微信群、QQ空间以及 QQ群链接分享等。从2018年3月到8月,问卷发放时间持续5个月,回收样本总计785份。问卷设计时所有题目均为必答题,填答无漏选后问卷才可提交成功。因此回收的785份问卷均无数据缺失现象。从媒介使用频率上来看,有2人从不使用微信,因此将此份问卷标记为无效问卷。即回收有效样本783份,样本有效率为99.7%。
在有效问卷中,男性问卷388份,女性问卷395份,男女比为0.98:1。链接分享时明确说明对象为在校大学生,本科生占91.6%。问卷填答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在18-23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占本次样本总量的91.2%。问卷填答对象的大学所在省份(直辖市)分布如下:上海52.4%,北京10.3%,陕西9.2%,四川3.2%。其余省份和其他国家(总计)样本所占比例均低于2%。可见该样本主要以北京、上海高校的大学生样本为主。
四、研究结果与假设检验
(一)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因子分析
首先,本研究将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以解决第一个研究问题。KMO(KMO = .85)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Chi-Square = 2821.03df = 78p < .001)结果显示该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利用正交旋转法对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问卷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对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的因子分析表示,有三种不同的因子呈现出来。它们共同解释了自我呈现策略52.21%的变异量。根据问题的分类,将这三个因子分为:他人中心程度(eigenvalue = 4.37crobach’s alpha = .81)、自我中心程度(eigenvalue = 1.58crobach’s alpha = .70)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eigenvalue = 1.17crobach’s alpha = .65)。
他人中心程度主要描述个体可能会考虑到他人对自己评价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以此来反映个体对在微信朋友圈中自我呈现时以他人为中心的策略程度。自我中心程度用来描述个体表达与自身相关信息意愿的程度。前后台控制维度主要描述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为控制表演的前后台可能产生行为的程度。每个策略维度下所包含的具体策略可见(表1 表1见本期第31页)。
(二)社会心理视阈下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多阶层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阶层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的方法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将人口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媒介使用频率、孤独感、社会支持、亲密关系作为自变量,分别预测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的三种策略,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2 表2见本期第32页)。
总体回归模型可以解释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时他人中心程度19%的变异量,自我中心程度11%的变异量,前后台控制程度13%的变异量。就他人中心程度而言,社会支持(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6)和亲密关系(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6)都有较强的预测力,接下来依次是孤独感(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3)、社交媒介使用频率(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和人口变量(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就自我中心程度而言,社会支持有最强的预测力(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6),接下来依次是社交媒介使用频率(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人口变量(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和亲密关系(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1)。孤独感(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0)基本没有预测力;而在前后台控制程度上,人口变量有最强的预测力(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4),接下来依次是亲密关系(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3)、社交媒介使用频率(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孤独感(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以及社会支持(adjusted incremental R平方 = .02)。
就更细致的各层次变量来看,人口变量中,性别在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5p < .001)、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9p < .001)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上(standardized beta = .19p < .001)均表现出强预测力。这提示我们女性在自我呈现时比男性更倾向于进行自我呈现形象的主动建构。年龄在预测三种呈现策略时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我们调查的大学生群体年龄相仿。而恋爱情况对他人中心的策略无显著影响。但有恋爱经历的人更容易在呈现时表现出自我中心倾向(standardized beta = .08p < .05),并对自我呈现较多地进行前后台控制(standardized beta = .08p < .05)。不同社交媒介使用对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呈现不同效果,微信使用频率对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1p < .01)与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08p < .05)有正向影响,但对自我中心程度无显著影响;微博使用频率则对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0p < .05)与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2p < .01)有正向影响,但对他人中心程度无显著影响;QQ使用频率对自我中心程度有正向影响(standardized beta = .09p < .01),但却对前后台控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standardized beta = -.09p < .01),对他人中心程度无明显影响。这些说明,微信、微博、QQ虽然都是社交媒体,但却对使用者来说意义迥异。微信更加是向他人展现自己的社交平台,而微博则更关注自我表达,QQ则是更加私密或是更少主动控制和建构的社交工具。可见,不同的媒介平台对于使用者的自我呈现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
再次,就假设验证结果来看,孤独感对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9p < .001)和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5p < .001)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中心程度无显著影响。研究假设1a、1c得到支持,虽然研究假设1b不被支持,但也同时说明孤独感越高,朋友圈中自我呈现的他人中心程度和前后台控制程度越高;而自我中心的程度却不受此变量影响。
就社会支持的影响来看,社会支持对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28p < .001)、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28p < .001)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7p < .001)均有较强的正向预测作用。研究假设2a、2b、2c均得到支持。总体看来,现实的社会支持越高,大学生对自我形象的主动控制行为越明显。这说明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支持越高的年轻人,越意识到社交工具对于自我在社会联结中的重要性,从而愈加主动地建构自己的呈现形象。
从亲密关系这一层来看,依恋焦虑对自我呈现的他人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28p < .001)、自我中心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1p < .001)以及前后台控制程度(standardized beta = .17p < .001)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而依恋回避对因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提示我们,依恋焦虑越高的个体,越需要通过朋友圈向外界展现一个更理想的自我以获得他人关注,进而降低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焦虑感。同时个体可能也意识到这种缓解自身焦虑的表演方式并不适用于朋友圈中的所有观众,因此会通过加强前后台控制来避免表演崩溃。研究假设3a、3b均得到支持。而研究假设3c和研究结果有所出入的原因,可能是具有依恋回避倾向的年轻人并无较高的线上自我表达的需求;反而是在恋爱关系中有更多焦虑感的人对线上自我中心的表达需求更加强烈。
五、结论与讨论
微信朋友圈作为信息时代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介,其塑造的媒介环境也在重塑着人们的行为。区别于其他匿名性较强的社交网络平台,微信可以被看作多数人真实生活中社交圈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不同于一般的即时通讯工具,朋友圈的功能扩展了微信的社交想象力,使其成为一个类似虚拟社区的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实际上成为戈夫曼意义上的线上“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个体通过自己对环境的判断来不断调整和修饰自己的行为,管理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不管是自我呈现中的他人中心还是前后台控制,这些有意识的表演行为的发生,都是为了在社交场域中呈现一个理想而未必“真实”的自我。本研究的发现首先确证了年轻大学生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策略及样态与其现实的社会心理状况有着较强的联结。
首先,与社会信息处理与超个人理论相呼应,孤独感、社会支持以及亲密关系中依恋焦虑与朋友圈自我呈现的主动控制策略之间的显著联系表明,社交媒体正在成为现实之外最重要的维持人际关系,进而影响年轻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交往中介。Walther 等人的经典研究也说明,在电脑中介的环境下非语言线索的丰富甚至会抑制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43]在社交媒介环境下,非语言线索(如图片、音频、视频以及表情包)的可供性变得更加丰富,为了获得最佳的人际关系效果,自我呈现中的主动控制成为必要且重要的手段。本研究中孤独感和依恋焦虑感愈强的人在朋友圈中采取更加他人中心及更强的前后台控制正可能是超个人理论带来的效应,即为了规避非语言线索对人际关系的抑制效应,呈现者必须时刻他者化自我呈现的样态并对非语言线索的前后台实施积极控制。
其次,社会支持对三种呈现策略一致的正向作用说明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正在使我们摆脱“大多数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年轻人都是缺乏良好现实社会联结或人际关系的问题少年”这一刻板印象。微信等社交媒介的出现显著地打破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隔断,越来越变成现实社会关系的补充工具。社会支持愈高的年轻人,就愈会主动运用社交媒介工具构建自我形象,从而进一步优化其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社交媒介成为自我的“后台”与呈现的“前台”之间的混合区域。正如梅罗维茨观察到的那样:“当场景融合时,火辣辣的脸红和冰冷的凝视混合成了中区的‘冷静’”。[44]这是媒介环境学者在电子媒介时代做出的论断,但在社交媒介时代,“中台”才变得更加真实可见。
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介中的自我呈现也展现出了一些复杂性。自我中心这一维度的发现,似乎和自我呈现定义中的受到他人评价影响这一限定相背离;但这一维度却和孤独感与依恋焦虑无显著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在进行自我中心的呈现时,并不是为了缓解其孤独感或依恋焦虑感,而且社会支持越高的人也同时自我表达愈充分。这一结果在提示我们处在次级社会化过渡阶段的年轻大学生的社会心理与自我呈现的复杂性。[45]一方面,他们把社交媒介作为提升现实社会人际关系和缓解心理情绪的一种工具;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将社交媒介认可为一种自我表达的和个性彰显的舞台。 当然,由于控制功能和技术的存在,社交媒介的这两种功用并不矛盾,但是这一结果也说明社交媒介的自我呈现同时容纳了年轻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成为其社会身份认同建构的核心舞台之一,而这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样本上,由于作者所在地域和滚雪球抽样的局限,地域的样本来源并非均匀分布。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问卷的编制虽然参考了相关文献,总体信度显示良好,但前后台控制维度的信度结果偏低,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优化设计。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日后更深入的研究来探明。■
①[美]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5页,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Hogan, B.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30(6)377–386.
③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第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年中国微信登陆人数、微信公众号数量及微信小程序数量统计,2018年5月30日,链接自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5/645403.html
⑤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⑥[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298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Short, J.Williams, E.& Christie, B. (197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⑧Walther, J. B. (1992).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1)52–90.
⑨Walther, J. B. (199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mpersonal, interpersonaland 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1)3–43.
⑩RuppelE. K.GrossC.StollA.Peck, B. S.AllenM.& KimS. Y. (2017). Reflecting on Connecting: Meta-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uter-Mediated and Face-to-Face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2(1)18–34. 9
[11]Sproull, L.SubramaniM.KieslerS.Walker, J.& Waters, K. (1996). When the Interface Is a Fac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11(2)97–124.
[12]Walther, J. B. (1992).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1)52–90.
[13]RuppelE. K.GrossC.StollA.Peck, B. S.AllenM.& KimS. Y. (2017). Reflecting on Connecting: Meta-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uter-Mediated and Face-to-Face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2(1)18–34. 9
[14]Walther, J. B. (1992).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1)52–90.;RuppelE. K.GrossC.StollA.Peck, B. S.AllenM.& KimS. Y. (2017). Reflecting on Connecting: Meta-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uter-Mediated and Face-to-Face Self-Disclosur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2(1)18–34. 9.
[15][美]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董晨宇、丁依然:《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
[17]Mendelson, A.& Papacharissi, Z. (2010). Look at us: Collective narcissism in college student Facebook photo galleries. In Z. Papacharissi (Ed.)The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pp. 251-273).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18]Rueda-Ortiz R.Giraldo D. (2016) Profile Image: Ways of Self-(re-)presentation on the Facebook Social Network. In: Walrave M.Ponnet K.Vanderhoven E.Haers J.Segaert B. (eds) Youth 2.0: Social Media and Adolescence. Springer, Cham.
[19]Weber, S.& Mitchell, C. (2008). Imagingkeyboardingand posting identities: Young people and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D. Buckingham (Ed.)Youth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 (pp.25–47). CambridgeMA: MIT Press.
[20]Michikyan, M.Dennis, J.& Subrahmanyam, K. (2015). Can you guess who I am? Real, idealand false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among emerging adults. Emerging Adulthood3(1)55–64.
[21]黄华、张旭东:《朋友圈里的“我”:青少年的经验》,《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
[22]李华伟:《青年群体在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青年记者》2017年第23期
[23]Ernst, J. M.& Cacioppo, J. T. (1999). Lonely hearts: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oneliness. Applied and Preventive Psychology, 8(1)1–22.
[24]ShawL. H.& Gant, L. M. (2002). In defense of the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depression, loneliness, self-esteem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2)157–171.
[25]HughesD. J.Rowe, M.BateyM.& LeeA. (2012). A tale of two sites: Twitter vs. Facebook and the personality predictors of social media usag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2)561–569.
[26]谭海燕:《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传播力研究》2017年第4期
[27]CaplanS. E. (2007). Relations among loneliness, social anxietyan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2)234–242.
[28]CorreaT.HinsleyA. W.& Zuniga, H. G. de. (2010). Who interacts on the Web?: The intersection of us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edia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247–253.
[29]Lin, N.Dean, A.& M.Ensel, W. (1986). Social support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OrlandoFlorida: Academic Press.
[30]ShawL. H.& Gant, L. M. (2002). In defense of the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depression, loneliness, self-esteem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2)157–171.
[31]谢笑春、雷雳:《大学生微信使用强度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友谊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心理研究》2016年第5期
[32]Hazan, C.&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3)511–524.
[33]Ainsworth, M. D. S. (1989). Attachments beyond infan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4)709–716.
[34]Hazan CShaver P. Conceptualizing romantic love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52 (3):511 ~ 524.
[35]Brennan K AClark C LShaver P R (1998). Self-report measure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overview. In SimpsonJ. A.& Rholes, W. S. E (Ed.).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pp.46-7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36]Jin, B.& Pena, J. F. (2010).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mobile phone userelational uncertaintylove, commitment, and attachment styles. Communication Reports23(1)39–51.
[37]Morey, J. N.Gentzler, A. L.Creasy, B.Oberhauser, A. M.& WestermanD. (2013). Young adults’use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ithin their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associations with attachment sty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4)1771–1778.
[38]HaysR. D.& DiMatteo, M. R. (1987). A short-form measure of lonel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1(1)69–81.
[39]周亮、黎芝、胡宓、肖水源:《ULS-8孤独感量表信效度检验及其应用》,《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年第11期
[40]叶悦妹、戴晓阳:《大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8年第5期
[41]Wei, M.RussellD. W.Mallinckrodt, B.VogelD. L.WeiM.RussellD. W.… VogelD. L. (2007). The 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 scale (ECR)-short form: Reliabilityvalidity,and factor struc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8(2)187–204.
[42]李同归、加藤和生:《成人依恋的测量: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中文版》,《心理学报》2006年第3期
[43]Walther, J. B.Slovacek, C. L.& TidwellL. C. (2001). Is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Photographic images in long-term and short-term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1)105–134.
[44][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第301页,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5]根据伯格和卢克曼(2009),他们将社会化定义为“一种将个体广泛地和持续不断地导入社会或其部分客观世界的过程”。 初级社会化通常是在童年完成的,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初次旅程,次级社会化却是“已经社会化的个体进入其所在社会客观世界中新的部分的过程”。详细参见[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第109页,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李耘耕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讲师、硕士生导师;朱焕雅系北京大学心理认知与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项目“上海青少年‘二次元’网络亚文化传播与引导机制研究”(编号:2018EXW004)、上海财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网络社会视野下数字媒介文化研究”(编号:20171107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