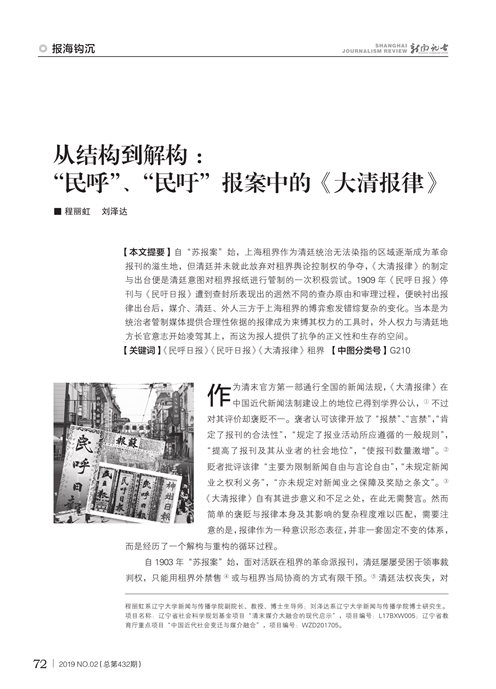从结构到解构:“民呼”、“民吁”报案中的《大清报律》
■程丽虹 刘泽达
【本文提要】自“苏报案”始,上海租界作为清廷统治无法染指的区域逐渐成为革命报刊的滋生地,但清廷并未就此放弃对租界舆论控制权的争夺,《大清报律》的制定与出台便是清廷意图对租界报纸进行管制的一次积极尝试。1909年《民呼日报》停刊与《民吁日报》遭到查封所表现出的迥然不同的查办原由和审理过程,便映衬出报律出台后,媒介、清廷、外人三方于上海租界的博弈愈发错综复杂的变化。当本是为统治者管制媒体提供合理性依据的报律成为束缚其权力的工具时,外人权力与清廷地方长官意志开始凌驾其上,而这为报人提供了抗争的正义性和生存的空间。
【关键词】《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大清报律》租界
【中图分类号】G210
作为清末官方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新闻法规,《大清报律》在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上的地位已得到学界公认,①不过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褒者认可该律开放了“报禁”、“言禁”,“肯定了报刊的合法性”,“规定了报业活动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提高了报刊及其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使报刊数量激增”。②
贬者批评该律“主要为限制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未规定新闻业之权利义务”,“亦未规定对新闻业之保障及奖励之条文”。③
《大清报律》自有其进步意义和不足之处,在此无需赘言。然而简单的褒贬与报律本身及其影响的复杂程度难以匹配,需要注意的是,报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征,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体系,而是经历了一个解构与重构的循环过程。
自1903年“苏报案”始,面对活跃在租界的革命派报刊,清廷屡屡受困于领事裁判权,只能用租界外禁售④或与租界当局协商的方式有限干预。⑤清廷法权丧失,对此,当时参与修订新律的沈家本曾奏言:“夫西国首重法权,随一国之疆域为界限,甲国之人侨寓乙国,即受乙国之裁制,乃独于中国不受裁制,转予我不仁之名,此亟当幡然变计者也。” ⑥1902年签订的中英《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也曾规定:“中国深欲整顿律例,期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断案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实,皆臻妥善,英国允弃其领事裁判权。” ⑦因而,制定一部为外人所认可的新闻法律,成为清廷参与租界报刊管理的一次积极尝试。1908年3月《大清报律》正式出台前曾经过多次修订,军机处尤“饬外部与各公使力商”,⑧甚至“另订租界报律” ⑨送予各国领事商办。然而外人不会轻易让渡租界权益,声称报律“所拟各条,实与立宪政体反对,各国向无此等报律推行,租界一层实难承认云”。⑩《字林西报》甚至断言,“中国新订报律四十二条,其意非欲改良中国之新闻事业,乃欲钳制主笔访员之口耳”。[11]法制化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是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进的基础。本文不以《大清报律》的条文内容为主要观测点,而通过对1909年发生于租界的“《民呼日报》案”和“《民吁日报》案”,关注《大清报律》给清末新闻事业乃至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民呼日报》因上海道台诉讼压力被迫停刊,《民吁日报》则缘于日本领事施压未审先封,由原告不同所导致的迥然有异的立案及审理过程,凸显了人治大于法治的现实,但当被告的律师引证《大清报律》进行辩护时,这一行为本身及其引发的“非意图性后果”便构建了解构清廷乃至租界统治根基的强力因子。“结构总是处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在历史上特定的某个时点上所进行的传播实践塑造了或重新塑造了这些结构”。[12]换言之,《大清报律》是一系列报案的结果,也是一系列报案的开始,而近代中国正是在媒介与权力的冲突中走上现代化的旅程。
一、报律为凭:报人与地方长官的较量
《民呼日报》创刊于1909年5月15日,是于右任退出《神州日报》后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第二份报纸,于右任自任社长,陈非(飞)卿任总主笔,编辑成员有李梦符、王无生、汪允中、谈善吾、杨千里、范鸿仙等。[13]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不受官款,不收外股”,[14]宣称“以巩人民之藩篱,使官吏无所施其伎俩者,其道匪一,而要以舆论为之先驱”。“更发呓语,以此报出现之日,即私人机关报消灭之期。凡向其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皆将于是乎昌昌大言之”。[15]然而理想归理想,鉴于此前《苏报》和《警钟日报》之遭际,该报稍事收敛,不再直言“革命排满”,但“既曰为民请命,所以对于贪官污吏的攻击,不遗余力”,[16]因而广受欢迎,“出世以来,为时仅阅三月,销行已逾万纸”。[17]《民呼日报》“专以攻击官场为事”,[18]尤关注路矿权益和民间疾苦,立意“通过揭发官吏虐政和水旱灾荒,隐晦地宣传改朝换代的变天思想,为革命思想开拓道路”。[19]呼吁路矿权益可博取绅商之同情,报道民生则赢得底层民众的支持。所以该报创刊号即聚焦安徽铜官山矿废约事,并对清廷与英商交涉的事态发展予以追踪报道,附以社说、评论等营造舆论,宣扬皖绅众志成城的同时,讥刺清廷“袒人抑己”,“不敢自伸斯意,屡屡强压忠于卫国之绅民,以行其曲顺外人之意”。[20]《民呼日报》不仅追踪最新动态,还开展深度调查挖掘背景材料,客观呈现英商福公司勾结洋买办盗取特权经营怀庆煤矿的经过,大胆揭露外人谋夺矿产的手段和清廷官员的腐败。
有关“路权”报道,《民呼日报》直指时任邮传部左侍郎的汪大燮,斥其“全国人所共詈为卖路贼者也”,“苟真立宪,必首先籍没汪大燮卖路而得之家产,抵偿沪杭甬借款之亏累,以快全国人民之心”。[21]此后“汪大燮”成了“卖路贼”的代名词,凡出卖路权的官员皆被冠以“汪大燮第×”。其中,尤对“汪大燮第四”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集中火力,穷追猛打,除谴责李贪贿卖路之外,更揭秘其发家史,言李氏“以某监故,得随使出洋,以学生而得随员之重薪优保”,[22]是以借之抨击清廷内监外臣交相勾结,以民脂民膏中饱私囊。
古人笃信天象示警,灾患疫情负载王朝衰败、帝王失德之隐喻,因之《民呼日报》格外注重灾荒报道,在援助灾民,获取声名的同时,借机暗示清廷末路已至。时值甘肃大旱,于右任作为陕人,感同身受。一方面抨击甘督升允玩忽职守,三年匿灾不报,坐视甘民受灾,怒斥“以是知官民相较,千人之生命,不能抵其一红顶。万人之生命,不能抵其一花翎。虽至全省糜烂,而不能损其总督之毫末也”。[23]另一方面及时报道甘民受灾惨状,并应甘肃筹赈会所请,于报馆设筹赈公所,特辟赈灾专栏,另言“需赈银四十万,已有半数,现得透雨,又无子种,尚望提倡以救灾黎”。[24]公所初时“一日所收者仅有一两宗”,“后数日收者日多”。[25]眼见声势日隆,却为早已心怀怨恨的甘肃护督嗅到了报复的机会,饬令上海道究查所谓侵吞赈款事件,[26]拉开了《民呼日报》被迫停刊的序幕。
《民呼日报》放论敢言,为受其抨击之各省当局所嫉恨;影响日盛,又为热衷操纵舆论的上海道台蔡乃煌所忌惮。因而甘督发难后,不仅蔡氏积极响应,札饬租界公廨提审于右任追缴欠款,且有朱云锦、陈德龙、蔡国桢三人控告《民呼日报》毁人名誉。[27]租界公廨审理“报案”此前已有先例,“《警钟日报》案”循“《苏报》案”流程,仅用十三天即告结案。而“《民呼日报》案”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自于右任被关押至释放,历时一月零七天,先后开庭审理九次,原告人数较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大清报律》的作用更为关键,它成了报人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以致在于右任被关押后,《民呼日报》仍然坚持出版并报道审讯事态,上海道只能于租界外禁售、焚报,[28]却始终无法通过法律程序封报,最后只能用关押于右任的手段逼迫《民呼日报》屈服停刊。
“《民呼日报》案”由护理陕甘督宪毛庆蕃致上海道电谕而起,谕中称,访知设在民呼报馆内的甘肃筹赈公所“在沪募收赈款数已三万余金,人言啧啧,多谓其敛钱肥己,意图渔利,实与甘省赈务大有关碍”。[29]沪道蔡乃煌随即转札租界公廨,谳员宝颐派差协探,于1909年8月3日晚将于右任、陈非卿传至捕房。[30]此外,尚有皖路公司协理朱云锦、已故上海道台蔡钧之子蔡国桢与新军协统陈德龙三人分别控告该报毁坏名誉。[31]是以“《民呼日报》案”由四案组成,罪名可分为“侵吞赈款”和“毁人名誉”两类,实际关涉的是我国近代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报人自律意识欠缺与新闻失实两个问题。
首先在“侵吞赈款”案中,筹赈公所本由刘廷荣主持,借用民呼报馆房屋,与该报主笔并无关系,但两者账目确有钱款往来且账目有误。在审案过程中,谳员宝颐调取筹赈公所、民呼报馆及负责收汇款的两家票号各项账册和收条根薄,查得“民呼流水簿内逐日有付筹赈公所买物零星之款,公所账簿内又有于右任携去铜洋二十三元一款,公所账簿内又有两次付民呼报兑换铜板钱二十五千一款,十七日账尾又有收还民呼报钱二十五千一款”。随后又复查“该公所总计簿结存大洋两千八百三十七元,刘廷荣(负责筹赈公所之人)所呈收支清折结存大洋三千六百六十四元,两相悬殊,其余小洋、铜洋存数亦均不相同”,正如宝颐所质问:“倘该报馆与筹赈公所果系两事各不相谋,何以赈捐之款由民呼账房取付,何以收捐之条由民呼之主笔账房填发耶?” [32]对此,于右任所聘律师只能以“司账员系学界中人,未明账情所致,且排字人亦有讹排之处” [33]应对。
显然,在“侵吞赈款”案中,《民呼日报》尽管是被“欲加之罪”,但罪名却并非“莫须有”。正如宝谳员在结案词中所称:“经公堂调查账册,弊混丛生,现虽据悉数呈缴,然非经此番彻查,将公款归其私蚀,律以挪移,百喙难辞”。[34]民呼报馆侵吞赈款虽查无实据,但账目弊混,确为事实。报馆报道灾情、号召赈灾无可厚非,但参与赈灾筹款,一则有失自身的独立性,二则妨碍舆论监督的超然地位。况且账务本为敏感之处,赈灾账目因钱粮出自公众更受瞩目,民呼报馆于账目上与筹赈公所未能泾渭分明,实为报人自律意识欠缺,对财务问题缺乏警惕性的恶果。
而三起“毁人名誉”案中,皖省铁路协理朱云锦控告《民呼日报》七月二十日所载《营私者能招股即可留乎》一文称其“飞扬跋扈”,“以包工为发财之目的”,[35]不仅言论多为不实,还“加评语任意谤毁,与路政前途大有障碍”。此书虽为投函,但“报馆来函一门须查明事实方可登载”,[36]况且朱氏见报后即拟稿送请该馆更正,却被置之不理;已故上海道台蔡钧之子蔡国桢则控告该报毁谤其父生前名誉,言“故父自怀退志,恳请开缺,并无革职情事”,然“该报任意谤毁,应请彻究”;[37]新军协统陈德龙亦控诉该报毁其名誉,称报中登载其“捐官一层尤属可笑”,其所聘律师强调“原告现为协统,系属逐级推升,不能捐取”,[38]进而指责该报“专事骂人,居心险恶”,且上纲上线:“毁坏军官名誉,设一旦军心不服,为祸尤大”。[39]针对上述指控,被告方所延律师依据《大清报律》为于、陈二人辩护,声称查“中国报律乃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由民政部奏准,并非草律,自然遵行”。[40]并举证朱案中投函者为有顾问之权的铁路股东,且有投函见证三人到堂担承责任,投函后所加评语亦属公论。至于未登更正稿件一事,究其实乃朱氏“更正之底稿较原文长有五倍,查照第八条报律所载,应交告白之费,而朱吝惜,故未登录”。[41]蔡案中《民呼日报》所载蔡钧事宜悉照来函,并无添改,被革职业经核实,“京报与上海各日报均于八月十五日登出”,“蔡钧系先朝佞臣,煌煌上谕著交地方官严加看管,所登各节并非毁坏名誉”。至于陈案,情形相同,“有投函人担其责任”,且“与报馆有闻必录并无不合”,况“陈事他报亦曾登载请察”。[42]查照《大清报律》第八条明文规定:“报纸记载失实,经本人或关系人声请更正,或送登辨误书函,应即于次号照登。如辨误字数过原文二倍以上者,准照该报普通告白例计字收费。更正及辩误书函,如措词有背法律或未书姓名、住址者,毋庸照登。”第九条则有:“记载失实事项,由他报转钞而来者,如见该报自行更正或登有辩误书函时,应于本报次号照登,不得收费。” [43]可见所谓的《民呼日报》“毁人名誉”案皆属合法操作。然而其秉行的“有闻必录”作为报馆“应付社会纠纷的护身符”,[44]虽然适宜于当时新闻业技术条件落后、专业人才匮乏的现实,也客观上推动了新闻自由观念的发展,但必定存在较大局限,正如徐宝璜先生所言:“若信一二人之传说,而不详加调查,证其确否,径视为事实而登载之,将致常登以讹传讹之消息,且有时于不知不觉成为他人播谣之机械,此亦为以伪乱真。” [45]《民呼日报》侵吞赈款查无实据,毁人名誉无违报律,最终会审公廨谳员宝颐唯有以“公所账房系民呼报馆所派”,账册“弊混丛生”,“报载诸多失实” [46]为由宣布结案。无论租界如何抗拒《大清报律》,此案中它成为辩护的主要依据,并影响断案结果,却是既成事实。此前,于右任未获保释,炎天酷暑,身陷幽囚,报馆同人“宁使民呼报先于君而死,不愿于君先民呼报而死”,[47]宣布停刊。加之舆论纷纷声援于右任,挞伐蔡道摧折报馆,[48]迫于压力,最后会审公廨从轻议结,“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49]不想,二十天后于右任便卷土重来,接盘民呼报馆原有机器生财,化“大声疾呼”为“长吁短叹”。
二、有律难行:凌驾报律的外人势力
《民吁日报》于1909年10月3日在法租界登记创刊,因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遂由原民呼报馆成员朱少屏出面任发行人,范鸿仙任主笔,于右任虽然撰写了《民吁日报》宣言书,但该报出版期间他身在日本,“实际工作已非于在主持,而是由之前来沪营救于右任的同盟会成员景耀月负责”。[50]《民吁日报》在版式上与《民呼日报》几乎如出一辙,标榜“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唯求“庶看白日之再中,稍尽寸心,犹望狂澜之可挽”。[51]而若欲力挽中国于濒亡之局,则“在修明言权,尤在主持始终一贯之国民主义”。[52]相较“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此宗旨略显内敛,但在随后的新闻实践中,该报的革命性却日渐凸显,愈发浓厚。
《民吁日报》认为民气不振源于“内逼于政府之压力,外摄于列强之恐吓”,[53]是以其革命色彩主要体现在对清廷立宪的抨击和对日本侵略野心的揭露,内外相合,将清廷的腐败无能展露无遗。首先针对当时国内喧喧嚷嚷的立宪热潮,该报极力讽刺清廷不过是“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不为党人所煽惑”,而“所谓的改革者”,也大多是“无钱捐官”、“无资格出洋”或“无科举进身者”的投机分子借立宪之名以谋私利。[54]正如《江苏咨议开会记》一文所揭:“百余议员中大率趾高气扬欣欣自得,其有深远之思,忧劳之色者,殆十不得二三人。是日无所议,唯读会长及各当道之颂词而已,遂散会”。[55]清廷立宪荒诞颓唐之象,跃然纸上。
宣传“反日”是《民吁日报》的重心所在,亦是其遭查封的主因。戈公振评价此报“专事攻击日本”,[56]虽不够全面,却足见其给时人所留“反日”的深刻印象。1909年8月,日本擅自动工修筑安奉铁路,意图将日俄战争期间修筑的安奉轻便军用铁道改筑为商业铁路,从而搭建连接沈阳与丹东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运输线。当时身陷诉讼风波的《民呼日报》,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告诫国人“日本政府对待安奉铁路交涉,欲用强逼手段”。[57]《民吁日报》创刊后面对东三省事态日急,自然逐渐把报道重心放在对日本侵略野心的揭露上,持续追踪安奉铁路事件,全文刊载《中日安奉铁路协约》,并评论此约“非双方同意之协约,乃一方强迫,一方被强迫,不得已而成之协约”,是“日本宣布自由行动,中国恐惧惊骇无可奈何,忍气吞声任所欲为,而惟命是从之协约也”,“不惟老大帝国腐败政府被弄诸掌股之上”。[58]该报对日本侵略行径在国内引发的反应也予以关注,尤注重对抵制日货运动的报道,极尽鼓动之能事,如“日本以区区三岛主国,土地小缺”,“能为次等之工业,投吾人利用之间,而恃我为其顾客也”,因而“日本之资赖我者实不啻婴儿之待乳,颇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之势”。[59]面对日本政府的抗议,则声言“抵制日货,乃民人人能力所能办到之事,人各不买,自尽天职,禁无可禁,强不可强”,[60]鼓动民众坚持抵制。
《民吁日报》的“反日”宣传,在伊藤博文哈尔滨遇刺前后达到了顶峰。伊藤抵达中国之前,该报便密切关注,提醒国人“此怪物一行,将来必有重大问题发现,居心真不可测也”,[61]其目的可能在于“调查中国内情,监督中国财政”,[62]且此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为中国之必将瓜分而思有以固日本之地位而立进取之基也”。[63]伊藤遇刺后,该报言论愈发激烈,歌颂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壮矣哉韩国之民也”,亦关注伊藤死后形势,指出伊藤实属缓进派,而激进派上台后,怕是“且复益逼愈急之势者也”,[64]并警醒民众“向所谓中国同种同文,唇齿友邦必兄弟相依,维持东亚和平之说,皆彼国政治家欺人之语,未足信也”,甚至直言“最不欲吾国之强者惟某国,最努力妨害我国之强者惟某国,且首欲亡吾中国者惟某国”。[65]如此直戳日人狼子野心,日人自也无需再粉饰其伪善的面具。1909年11月19日,驻沪日本总领事以“民呼日报登一论说有关日本国全体名誉,并伤中日两国邦交” [66]为由,照会沪道蔡乃煌请饬租界公廨查封该报,并升特别公堂传主笔范鸿仙讯究。实际上,《民吁日报》宣传“反日”已近一月之久,日人除掉该报之心也早已有之,之所以拖延些许时日,是因该报在法租界注册过,日领事需先与法领事商议将其挂号注销,方能查封。然而未经审讯先行查封,任何国家皆无此等法律。因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虽然日领事与上海道台以威权凌驾法律,但被告律师始终据理力争,以公理对强权,以致审讯前后绵延一个多月,纵然日方派遣陪审员并施用突击审讯等手段,[67]却仍无法改变其在法理上的非正义性。
在该案中,被告律师指出不合法律之处共计有五。其一,“中西法律均无未经讯明,先行发封之例”,且“该报所登论说究与政事有无关系” [68]尚不确定,言下之意应先确定违规后封禁方属合法。其二,被告律师“请将公牍及报载关于邦交各条给看”,日方拖延不给,“仅令被告交保,延宕不讯,核与公堂法律亦有不合”;[69]其三,“此案原告查系日本领事,应以刑事论,归早堂[70]讯判,毋庸会讯。此前被告到案时未照行,尤难索解”。[71]其四,“前堂被告到案,亦系英领堂期”,而到此案“乃竟由日领事会讯”。[72]因而该案升特别公堂审讯且由日领事担任陪审官不合法。其五,“日本政府不愿日领事出为原告,则此案系属捕房寻常案件,应归英美德三国领事会讯,此系公堂定例”。[73]不过最终谳员宝颐与出任陪审员的日本中畑、三穗两副领事仍以“有违报律”结案,称“查该报并未注册挂号,已属有违报律,乃所载论说多系臆测造谣,实于中日邦交有损,迨经传讯,复不稍自悛敛,尤敢有意挑衅,实为不合”。[74]其中“论说造谣”、“有碍邦交”于报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但“注册挂号”确有所依。据《大清报律》第一条规定:“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开具下列各款,于发行二十日以前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历及住址;四、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地址。” [75]因而《民吁日报》在法租界注册,未曾到上海地方官衙门登记,确实于报律不合。上海道台蔡乃煌在该报被封后曾出牌示,亦称“该报本托法商出面挂号,交法国书信馆及日本邮便局递寄各埠销售,本未到道请领执照”,更有“乞怜于外人,以图抵制中国” [76]之语,足见蔡氏对该报敌意之深。
然而违此条款所对应之惩处却绝非封报。据《大清报律》第十六条:“凡未照第一条呈报逾行发报者,该发行人处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 [77]但宝谳员与日领事却判决:“将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由该被告切实具结领取可也。” [78]《字林西报》对此案评曰:“无论何国,不能无故贸然要求他国政府封禁其报馆,或停止出版权,诚以此等办法,既不合公正之裁判,且亦中国报律之所无也。” [79]《北华捷报》则曰此案“足以显明华官全在日本人权力支配之下”。[80]因而,单方面的强词结案表明报律条文在此案中已成为租界公廨与日领事任意取弃,肆意阐释的工具,法治沦落为人治的附庸。但从民间的舆论反应来看,《大清报律》作为由包含着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条款搭建而成的意识形态表征,在面对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人或群体时,解构出了丰富多样、甚至彼此冲突的意义。
三、报律改进:报案与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前文述及的两起报案中,与清廷和租界的压迫力量相对抗的是来自社会各界的舆论,尤其是来自报界同行的声援,是影响审判结果的重要砝码。而这些声援所倚仗的,正是原本为束缚其行为而制定出来的《大清报律》。在拥有能动性的主体面前,“具有压迫力量的结构也有可能转变成一种通向自由的方式”。[81]《大清报律》所蕴含的民主、立宪、法治、新闻自由等现代元素,在报人们的阐释下成为质疑,乃至对抗清廷与租界当局的依据,并为之提供了合法性和正义性。
当于右任被收押后,《民呼日报》能坚持出版,且在报上自鸣其冤,皆因依报律,上海道台蔡乃煌无权将其查封,唯有另寻它案施压。法理上无法条可依,道义上无正义可言,蔡氏将自己推向了舆论的众矢之的,其解释扣押于右任情由的电文被改成《蔡乃煌瞒昧报界之电文》,各报纷纷转载,文中讽刺蔡氏自述是“借以恫吓报界,冀免清议,其心可诛”。[82]中外各报还对会审公廨审案结果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尤以《神州日报》、《时报》、《东方杂志》为激昂”,其中《时报》评论称:“民呼日报案为赈款也,曰赈款未侵吞,是《民呼日报》无罪也。《民呼日报》案,为朱蔡陈控毁名誉也,控毁名誉仅曰不为无因,是《民呼日报》未定罪也。”并且感慨:“上海各报时有凭空诋毁是非之事,岂以一民呼报为未足,又欲尽上海各报而一网尽之耶?” [83]因而报界声援《民呼日报》,不仅是不平则鸣,更是在保护自己,报律这一本带有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在此被解构为维护报人合法权益的依据。
《民吁日报》未审先封,日领事无视报律,与蔡乃煌以威权凌驾法律,依凭长官意志审案,看似取得了胜利;但压迫愈甚,抵抗力愈强,被告律师在终审的陈词便代表现代法治精神向威权发出了挑战:“似此办法,殊难申辩,盖因公堂定例,历久奉行,断非一二国人意见所能更易。今已违章,本律师不能服从,惟有申请领事公会提议此案之办法是否合宜,再请订期会讯。” [84]而此前英领事早已特意回避此案,于案件初次审讯时“竟未到场”。[85]因而虽然日领事打通种种关节,且对上海道等清廷官员如臂使指,但其在法律和道义上是孤立无援的。《北华捷报》就此写道:“如果日本总领事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场争论的强行判决,就彻底颠覆了所有的公正原则。一个纯粹的中国法庭如此行事,无人觉得惊讶;但现代日本可信赖的外交代表的行为,却令外人社会有资格刨根问底。” [86]因此,虽然《大清报律》出台后并不被租界当局认可,亦被租界报刊所无视,但在上述两案的审讯过程中,该律不仅给予了被告法理上的依据,也为社会舆论的反抗提供了正义的道德光环。两起案件中,《大清报律》从权力压迫舆论的工具转化成为舆论反抗权力的武器,映射出了报律这一由主体的知识与理解形成的规则,与报案——即新闻实践活动之间的结构与解构的相互作用。其中,主体在知识与理解上的有限性与社会实践无限变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因而“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循环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87]清廷为规范报刊经营、消除革命宣传、插手租界报刊管理而制定报律,是以先有报案而后有报律,乃汇清廷于各类报案之经验教训而成;报人则以报律为依据维护自身权益,扩大生存空间,对不合理之处据理力争,[88]是以有报律后报案不减反增,且据其中之新问题与新闻事业之新发展而成新报律。相较《大清报律》,1911年出台的《钦定报律》不仅降低了注册报纸的保押费,删掉了“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与“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挟嫌诬蔑、损人名誉”两项,而且缩小降低了处罚的范围和程度,除登载“冒渎乘舆之语、淆乱政体之语”会被处以监禁附加罚金外,余者若违皆无监禁之惩。此外,对报纸登载错误事项的更正规定更为详细,并对因“专为公益、不涉阴私”而损人名誉的报道免除了惩罚。但其中“外交、陆海军事件及其他事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登载”一项中的“其他”指代不明,为清廷预留限制报纸内容的操作空间。[89]从“《苏报》案”、“《警钟日报》案”到“民呼”、“民吁”报案,清末的新闻法制建设经历了从结构化到解构和走向重构的过程,其中《大清报律》的出台是清廷立意管控报业的一次努力,也是时机最佳的一次尝试。在“民呼”和“民吁”报案中,《大清报律》虽然束缚了蔡乃煌的手脚,令日领事受到正义的谴责,但并没有改变两份报纸停刊和被查封的命运,报律在清廷、日领事和报人三方各自的解构下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报律重构迫在眉睫,然而清廷昏聩颟顸,当重构的进度无法与新闻事业发展的速度相匹配时,舆论的全面失控自然难以避免,1911年姗姗来迟的《钦定报律》已无力回天。
四、结语
《大清报律》作为清末立宪修律活动的产物,凸显了清廷对新闻报刊的重视和规制言论的决心。然而清廷中央式微,地方权重,中枢行政命令受地方长官个人意志影响日甚。外人租界各项法条渐趋完备,独立王国之势难逆,清廷政令纵使服膺西法,亦绝难通行。同时国人为西潮涤荡日久,立宪、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思想渐为知识阶层所接受。因而《大清报律》对内施行其落后内容受报人诘责、舆论反对,其进步之处又为地方官所抵制;对外推行不被外人承认,甚至在强权面前威严扫地。在“民呼”、“民吁”两起报案中,清廷地方长官、租界当局与报人三方博弈中的冲突与妥协凸显了后者利用前两者的冲突矛盾图生求存的艰难处境,清廷尝试收回租界舆论管控权而出台的报律恰为报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占据绝对强势的租界和人治尚自大于法治的清廷面前,报律虽然未能改变两报被查封的命运,但有律难行这一事实本身便意味权力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遭到消解。对此,清廷的应对被动而迟缓,以致对言论的管控走向失控,而其200多年的统治亦在失控中走向解体。■
①清末管制新闻及言论的独立法规“最初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之《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及《报章应守规则》,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始正式颁布《大清报律》。是为名实相符之新闻法规。”参见于衡:《大清报律之研究》第1页,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版。“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的创制与颁行,特别是《大清报律》等一批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在封建统治的末年初步建成。”参见黄瑚:《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第9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大清报律》“在形式上基本具有了西方现代法律条令的‘条’‘款’体例,一改前面《报章应守规则》和《报馆暂行条规》中以‘一’到底的传统法规形式,以‘律’中分‘条’、‘条’下列‘款’的形式表述内容,基本上达到了形式简洁、行文规范的法律文书要求。”参见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法制发展史》第308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大清报律》“涉及报刊创办手续、编辑、稿件审查、出版、发行、禁载、违禁处罚、职业道德等方面。是中国第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报刊法。”参见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第59-6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大清报律》是按照当时的形势,建立的具有近代性质,较为完整、系统的一部法律制度。它的制定为以后新闻法律法规的制定建立了一种模式,此后历届政府在内容、形式上对此多有承袭。”参见殷莉《清末民初新闻出版立法研究》第52页,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②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01期
③于衡:《大清报律之研究》第2页,台湾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严禁国民报示》,《申报》,1903年10月27日,第10964号
⑤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7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沈家本:《寄簃文存》第2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⑦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光绪条约》第2113页,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⑧专电,《申报》,1908年1月7日,第12554号
⑨⑩《外部编订租界报律》,《申报》,1908年3月6日,第12606号
[11]《中国报律之实行》,《申报》,1908年3月6日,第12606号
[12]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第38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8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本社启事》,《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第1号
[15]《民呼日报宣言书》,《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第1号
[16]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第19页,台湾商务印书1981年版
[17]《民呼日报辞世之言》,《民呼日报》,1909年8月14日,第92号
[1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9]赵凯主编:《王中文集》第1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卖国罪案之一端》,《民呼日报》,1909年5月26日,第12号
[21]《论汪大燮不宜任邮部事》,《民呼日报》,1909年5月21日,第7号
[22]《汪大燮第四李德顺之历史》,《民呼日报》,1909年6月17日,第34号
[23]《论最近之政局与最近之民命》,《民呼日报》,1909年7月10日,第57号
[24]《甘肃旱灾》,《民呼日报》,1909年7月23日,第70号
[25]《筹赈公所与民呼报之命运》,《民呼日报》,1909年8月6日,第84号
[26]《附毛护督原电》,《申报》,1909年8月4日,第13110号
[27]《民呼日报馆之讼案》,《申报》,1909年8月5日,第13111号
[28]《甘肃筹赈公所与民呼日报》,《夏声》,1909年第9期,第41页
[29]《沪道札公共公廨宝谳员文》(附毛护督原电),《申报》,1909年8月4日,第13110号
[30]《民呼日报之讼案》,《申报》,1909年8月5日,第13111号
[31]许有成、徐晓彬:《于右任传》第7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宝谳员禀沪道文》,《申报》,1909年8月10日,第13116号
[33]《民呼日报馆讼案七志》,《申报》,1909年8月19日,第13125号
[34]《宣布民呼报讼案堂谕》,《申报》,1909年9月9日,第13146号
[35]《营私者能招股即可留乎》,《民呼日报》,1909年7月20日,第67号
[36]《民呼报控案四志》,《申报》,1909年8月10日,第13116号
[37]《民呼日报讼案十志》,《申报》,1909年8月26日,第13132号
[38]《七志民呼报涉讼案》,《大公报》,1909年9月3日,第2558号
[39]《民呼日报讼案十一志》,《申报》,1909年8月28日,第1314号
[40]《民呼日报控案五志》,《申报》,1909年8月11日,第13117号
[41]《民呼报控案四志》,《申报》,1909年8月10日,第13116号
[42]《民呼日报讼案十一志》,《申报》,1909年8月28日,第1314号
[43]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第35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44]宁树藩:《“有闻必录”考》,《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
[45]徐宝璜:《新闻学》第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6][49]《宣布民呼报讼案堂谕》,《申报》,1909年9月9日,第13146号
[47]《民呼日报辞世之言》,《民呼日报》,1909年8月14日,第92号
[4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0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50]刘延涛编:《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第19页,台湾商务印书1981年版
[51]《〈民吁日报〉宣言书》,《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第1号
[52][53]《本报四大宗旨》,《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第1号
[54]《中国改革谈》,《民吁日报》,1909年10月6日,第4号
[55]《江苏咨议开会记》,《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7日,第15号
[5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57]《日人强筑安奉铁路》,《民呼日报》,1909年8月8日,第86号
[58]《论日本对满洲外交之痛险》,《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9日,第27号
[59]《论中日贸易之关切》,《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8日,第26号
[60]《解除抵制日货之善后》,《民吁日报》,1909年10月8日,第6号
[61]《伊藤怪物之行踪》,《民吁日报》,1909年10月16日,第14号
[62]《政治的旅行之疑问》,《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2日,第20号
[63]《伊藤满洲旅行之阴谋》,《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6日,第24号
[64]《中国外交危机之愈迫》,《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1日,第29号
[65]《外交思痛论》,《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8日,第47号
[66]《审讯民吁报馆讼案》,《申报》,1909年11月21日,第13219号
[67]“敝律师等均于今日临讯时,始知所有应辩各节,均未预备,无从对付。”参见《会审民吁报封闭案志详》,《申报》,1909年12月21日,第13249号
[68][69]《催讯民吁日报馆讼案》,《申报》,1909年12月9日,第13237号
[70]会审公堂分早堂、会堂和晚堂。早堂专审刑事,会堂审理外人为原告之民事案件,晚堂审理纯粹华人间民事案件。
[71]《催讯民吁日报馆讼案》,《申报》,1909年12月9日,第13237号
[72]《民吁报案讯结无期》,《大公报》,1909年12月16日,第2662号
[73][74][84]《宣布民吁报讼案之堂判》,《申报》,1909年12月30日,第13258号
[7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76]《关于民吁报讼案之牌示》,《申报》,1909年11月28日,第13226号
[77]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78]《民吁讼案如此了结》,《大公报》,1910年1月9日,第2685号
[79]《记上海民吁日报被封事》,《东方杂志》第413页,1909年第6卷第12期
[8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1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81]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从解构到主体》第81页,黎明文化2010年版
[82]《蔡乃煌瞒昧报界之电文》,《大公报》,1909年8月15日,第2539号
[8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30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85]《续志民吁报馆被封事》,《大公报》,1909年12月3日,第2649号
[86]郭泰纳夫著,朱华译:《上海会审公堂与工部局》第18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
[87]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第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8]朱传誉:《先秦唐宋元明清传播事业论集》第437-4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89]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三卷、第十卷)第35-38页、第312-316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程丽虹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达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项目名称: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清末媒介大融合的现代启示”,项目编号:L17BXW005;辽宁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与媒介融合”,项目编号:WZD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