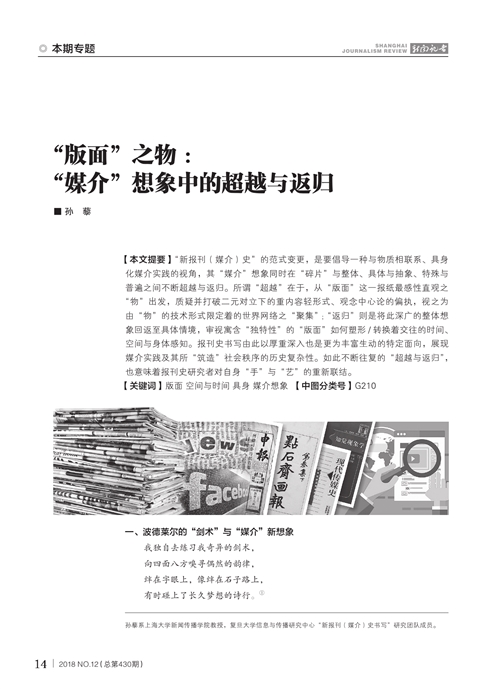“版面”之物:“媒介”想象中的超越与返归
<副题>=
■孙藜
【本文提要】“新报刊(媒介)史”的范式变更,是要倡导一种与物质相联系、具身化媒介实践的视角,其“媒介”想象同时在“碎片”与整体、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之间不断超越与返归。所谓“超越”在于,从“版面”这一报纸最感性直观之“物”出发,质疑并打破二元对立下的重内容轻形式、观念中心论的偏执,视之为由“物”的技术形式限定着的世界网络之“聚集”;“返归”则是将此深广的整体想象回返至具体情境,审视寓含“独特性”的“版面”如何塑形/转换着交往的时间、空间与身体感知。报刊史书写由此以厚重深入也是更为丰富生动的特定面向,展现媒介实践及其所“筑造”社会秩序的历史复杂性。如此不断往复的“超越与返归”,也意味着报刊史研究者对自身“手”与“艺”的重新联结。
【关键词】版面 空间与时间 具身 媒介想象
【中图分类号】G210
一、波德莱尔的“剑术”与“媒介”新想象
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
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
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
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①
借助诗人苦练“奇异剑术”的自我描绘,本雅明点明了波德莱尔也是“每一位艺术家”进行创作时的一个隐喻:剑客。“每一位艺术家都要面临一种决斗”,万籁俱寂之际,他“俯身在他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审视着一张纸,就像他白天观察周围的对象;他是如何用细毛笔、鹅毛笔和粗毛笔左右劈杀,把杯子里的水溅到天花板上,在他的衬衣上试用鹅毛笔;他是如何急速而紧张地从事着他的动作,仿佛担心影像会逃脱掉;因此即便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也是斗志昂扬,而且要避开自己的打击”。②
这实际上是本雅明转述的波德莱尔对另一位艺术家的描绘,不难看出,本雅明对这个意象心怀激赏。在一篇未完成的方法论导言中,本雅明用他的方式对之进行了描述:研究者的出发点,面对的“是被谬误、猜测所遮蔽而令人迷惑的客体”,“唯物主义方法始终是泾渭分明的,因此一开始就进行区分。它所做的区分是对这种高度混合的客体内部的区分。它不可能让这个客体呈现为混合的或未经充分批判的形态”。③再联系本雅明对现代性“碎片和瓦砾”的迷恋,在“区分”和“批判”过程中还有对碎片的提取与拼凑——
真正的历史知识只可能作为幻觉的超越。但是,这个超越不应意味着物的发散和现实,而是,作为物的一部分呈现一种迅速想象的建构。这种迅速的小的想象与科学的从容相对照。迅速想象的建构与对事物中的“当前”提出自己的质疑相一致。④
“新报刊(媒介)史”的书写者,理应从这里借鉴学习、修炼锻造自己的“剑术”。他可以像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从“物”入手,对各种历史话语中事物的“当前”、也就是那些用来“遮蔽而令人迷惑”的“谬误”与“猜测”,提出自己的质疑,在对“幻觉的超越”中,建构一种“作为物的一部分”的想象。这种想象往往从正统科学叙事所忽视的“碎片”切入,但又“意识到碎片本身是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特殊总体”,由此将收集的碎片“与其他碎片一起被重新装配”,“它们的独特性必须被认识、被拯救”。⑤
“新报刊史书写”由此为自身提出了一种新的技艺期待。从“碎片”到“总体”,并非是一个单向的搜集与装配过程,它同时亦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特殊总体”中“认识”、“拯救”碎片自身之“独特性”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媒介”想象要在“超越与返归”间不断往复:所谓“超越”,是在质疑“事物中的‘当前’”(或“幻觉”)的过程中,一方面对“高度混合的客体”进行充分批判的“内部区分”,以对媒介特定的概念化理解形成对“客体”的把握视角,另一方面此视角同时又会从“碎片”自身更为宽广地延展开去,将眼前在场之“物”与不在场者“聚集”成想象性联结;所谓“返归”则意味着,将此飞扬的媒介想象再次置于特定历史场景的“筑造”之中,审视寓含“独特性”的“碎片”如何在此间具体生成,并同时塑形/转换着交往的时间、空间与身体感知。
“超越”与“返归”的关系,简洁地说,一方面两者很难“抽刀断水”、截然分离,且它们也都与特定的研究问题“视域”密切关联;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在前者的广阔联系中把捉特定媒介“是何”的想象,同时在后者的具体情境中体察媒介“如何是其所是”。由此,“新报刊史书写”或能以厚重深入也是更为丰富生动的特定面向,展现媒介实践及其所“筑造”社会秩序的历史复杂性。
二、“版面”之聚集:“物”中介着“网络”与“秩序”
就让我们从现代报纸最直观的“物”开始。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说,“版面”,都是人们手握、目视、嗅寻和想象首先要迎面的“物”。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是特定尺寸与材质的纸张、或许气味已经飘散的油墨,还是大小形状不一的字号字体、抑或作为分区和分栏编排标志的空白或线条?大概似是而非。说“不是”是因为“内容像一块滋味鲜美的肉,涣散了看门狗的注意力”。——麦克卢汉的揶揄,针对的不仅仅是普通人。也如唐·伊德所说,当人们习惯了戴着眼镜看事物之后,眼镜就在意识中退缩到了“边缘地位”,换言之,“随着我们学会了将技术具身在我们熟悉的行动上,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得意忘形”的我们偶尔——比如在眼镜蒙尘之际——才会被意识到“形”的存在。⑥即是说,上述种种“物”或“形式”,就是报纸让人们看世界的“眼镜”;即便不被观察者忽略,也往往退缩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
对物质“技术”与“形式”的漠视、忽视或轻视,一方面使物质“技术”似乎退隐成“透明”形态,另一方面又往往联系着“观念中心论”,这种“使世界服从于主体”的“形而上学的自我中心主义”,“它几乎和我们一样持久”。⑦“媒介”就此被视为人使用的工具、服务于满足主体的观念或需求。这种与生活常识颇为契合的想象方式,在学术研究中也很常见,“很多社会科学都以主体的或系统的目的和目标的成功实现为其前提条件”。⑧由此而生,“媒介”成了被“主体的或系统的目的和目标”所决定、脱离于情境的抽象存在,失去或至少模糊了其“事物本身”的面目。
因而,超越性的媒介想象,就面临着双重任务:首先,要把本雅明的“质疑”演化为一种“转换能力”,“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一种倒置的眼光”,⑨但“倒置”不是“抛弃”,也不是从对一端的固执走向另一端。这种“倒置”要“让事物说话”,一旦“眼镜”被从边缘聚焦到中心,它们就可能自动“说”出所富含的信息,促动、激发着观察者在聆听中把捉到新的想象。其次,要将媒介从各种“抽象存在”尤其是“反映/再现”模式中解放出来,或者用海德格尔更一般性的表达,要从西方思想“自古以来”就“过于贫乏地估计物的本质”的习惯桎楛下挣脱出来,将“那已经包含着这一物的聚集着的本质中的一切”显现出来。⑩这种显现,自然也会从“版面”的感性向着“媒介”中介做抽象,但此种“抽象”朝向广阔世界敞开,从而告别了“过于贫乏”的理性认知或观念投射。
练习“剑术”中的波德莱尔,就是超越性想象的一个很好例子。为了能幸运地碰到“长久梦想的诗行”,他游荡于“城市和郊野”,遭遇着“破房”、“百叶窗”、“毒辣的太阳”、“屋顶和麦田”。诗人“向四面八方嗅寻”,同时也是让事物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里,诗人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心灵与自我的敞开,一次对“不在场之物”虔敬而辛劳的呼唤,一场投身于周遭情境之中对“灵光”偶然乍现的探险式采汲。
由此观之,“物”不是简单的与“我”两分的物质,作为“实体物”或“对象物的‘物’”,在与人的意向遭逢与交融之中,“毋宁说它已不是一物,而是一个‘东-西’,一个召唤、邀请、聚集于上下四方,各路神灵来此显山露水,伸展手脚,现身出场的‘中空之域’”。[11]有学者用媒介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了上述海德格尔对“物”的存在论理解:任何存在者或存在物,都具有成为媒介的先天质素或潜能,与其说媒介是一个中介物,还不如说是一个“媒-介”活动,在其“召唤、谋合、聚集、容纳、赋形、建构”中,“任何一个被‘媒-介’着的存在者也有可能成为另一媒介而‘媒-介’着其他更多存在者”,“以此类推,整个世界就成为相互‘媒-介’着的网络了”。[12]简单点儿说,这个“网络”,就是由“物”中介着的实践与交往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就为此媒介想象展示了绝好的范本,只要去感受一下他对一把“壶”的描画中所展现出的惊人想象力。[13]“版面”,正是让报刊史研究者迎向这一世界的“聚集”之物。麦克卢汉对“观念中心论”者另有揶揄说,他们在品尝“乌龟肉”美味的同时,却看不到对象(连同观察者自己身上也生出的)“美丽的背甲”。[14]这在中国语境下更富意味,正是龟背和其上刻写下的古老文字,比起现在所有的媒介,都更为直观地显现着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物之聚集”:天、地、神、人。就形式而言,“龟背”就是一种古老的“版面”材质,它坚硬、粗糙,要在风吹日晒之后才能迎来刻刀的书写,相比竹简打磨着漆后的平滑与齐整,它们各自为书写提供、塑形着不同的空间、技能,也决定着“在空间中传播与在时间中保存的”知识的类型。这就是英尼斯为报刊史准备的基本“理论武器”:媒介载体联系着知识的时空偏向。甲骨比竹帛偏向时间,但又比青铜偏向空间。[15]然而,无论这哪一种,又都绝非一块自然之物。剥离或刨光,就像削尖一块石头或一根树枝,“即便是一点点的细微的人工行为,它也会超出偶然的潜在功能性”,人与物的这种“最原始、最基本”的交互,“早已将智能融入材料中,将精神融入细微的行为中”。[16]即是说,“眼镜与肉眼”、“智能与材料”、“精神与行动”乃至人与媒介,在历史与现实中早已是交融于一体。
新闻学奠基人李普曼明白这一道理。他关注“内容的形式”,“到达读者受众时,每份报纸都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这些选择包括印什么新闻、印在什么位置、每条应占多大面积、各自的重点是什么等等”;由此他也得出了一个关于“形式的内容”的结论:报纸报告的,只能是“秧苗破土”而不是“种子生长”。[17] “版面”的体积大小、方向重量,以及整个布局,带来了波兹曼眼中的世界的生成:“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18]李普曼启发了后来的“框架”理论。换做海德格尔的表述——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这也就是“边界”,“边界不是某物停滞的地方”,“边界是某物赖以开始其本质的那个东西”。[19]由此延展开去,超越性的媒介想象,并非将“版面”之聚集,视为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平行汇聚,而是于此间设定着具有边界与等级的特定秩序。福柯将视野投向“词与物”的网络,由此审度人类知识构型“秩序”的历史变化:
没有比在物中确立一个秩序的过程更具探索性、更具经验性(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更需要一双锋利的眼睛或一种较为确信的抑扬顿挫的语言;更坚决地要求一个人要允许自己被性质和形式的激增所摆布。[20]这种“物”的“知识考古”的形象,很适合“新报刊史”书写。它意味着借“一双锋利的眼睛”把想象引向“性质和形式的激增”,这些“激增”出现在“版面”聚集的“媒介域”之中,需要研究者投身其中并在其中“确立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只是在这一网络的空格,秩序才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默默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时刻”。[21]事实上,福柯这里所讲的,与本雅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很相通:“秩序”,“作为幻觉的超越”的“真正历史知识”,既是“物的一部分”,又是“想象”建构的产物。
这也正是“新报刊史”媒介想象的超越性所在。以此观照“词与物”的双重网络:“版面”的物质材料、形式内容,与他物“相互间遭遇”的“隐蔽网络”;以及,围绕着“版面”的目光注视、故事讲述、知识逻辑等等,“新报刊史”能够借此从这一碎片,考掘出一个人类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史的“特殊总体”。比如说,“版面”的英文表述之一是page,“书页”的“页”。以书之“页”命名报之“版”,中西都很一致。在中文字源中,“版”也意味着雕刻、刊印用的木板,那正是形塑“圣贤之书”的物质。单单从“命名”这一最基本的话语实践出发,那个隐藏的“秩序”就已显露、提示着如下问题:
作为历史的“总体”,“版面”如何穿行于那个波谲的行程——从雕版到活字、从毕昇到谷腾堡,还有那激动人心的——“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作为独具的“特殊”,报纸之“版面”,究竟与书页、与APP的屏幕有何不同,这种不同何以可能,与意义建构、信息传播、知识构型以及不同群体的经验感知,存在何种联系,又意味着什么。当然,“版”与page的不同,也同时标定着这些问题的不同历史时空。
三、“版面”之筑造:具身关系的“独特”生成
“新报刊史”在实践与交往的生活世界中探究这一追问。这就是新“媒介”想象中的“返归”。返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从抽象到具体”,尤其不是简化了的“理论烛照经验”,它也不是在狭窄的意识或认知领域中进行所谓“还原”。返归的意义或价值在于,要把超越性想象中的那个“世界网络”(或福柯所说的“秩序”)置于特定情境下,让“媒介”的独特性在生成演化之中清晰地呈现出来。事实上这也即考察,特定的媒介实践如何塑形着融普遍与特殊于一体的具身关系。就“版面”而言,“版”的另一个字源含义是“打土墙用的夹板”,把它动词化,就是用“泥土”和“木头”来筑造一面“墙”。“筑造”是“新报刊史”工具箱中的另一个重要意象,简单地说,“筑造”就是让“聚集”独特地显现出来。[22]“返归”让研究者切近如下这种体察, “版”(“报纸”)从来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明晰“面目”的“物”,它也从来不是一旦成型就被人们纳入同样早已成型且固定清晰的“政治”“经济”之中;相反,正如飞架于河流之上的“桥”,“它不只是把已经现成的河岸连接起来”,而恰是“在桥的横越中”,“河岸才作为河岸而出现”。[23]在“版”的筑造中,用来印刷书页的字钉以新的规则排着序,记者们以人皆默会、却难以明言的不同于书的规则,加工处理着“知识”。[24]而如此“版面”之成型,也就是那个“新闻生产”的组织过程的每日显现;而每日发生的活生生的“现实”,也在被拣选裁剪、改头换面之后,涌入“版面”的某个位置,然后——遥远的“现实”就这样发生了,它嵌入生活世界,迎面人们、邀请通达。如果说“版面”的“两岸”,就是“组织的生产”与“读者的消费”,那么它们就是以此为媒介,彼此横越与相遇,并筑造了“两岸”“四周的风景”。或者,说它是一个权力的“秩序”。
也正是在这里,“返归”的媒介想象遇到了最为复杂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何审视经由“碎片”之组合装配而来的那个“总体”本身的独特性。对此难题的追索,自然离不开超越性想象中所建立起的宽广联系,这为发掘媒介实践的特殊性提供了可能。例如,本雅明联系着“讲故事的人”来打量新闻,德里达映照着语音来审度书写。实际上,这种参照也正是对于“碎片”本身之独特性的认识和“拯救”,特定媒介自身的差异,诸如其物质技术与形式、媒介之间关联带来的重组,必然也同时展现于时间、空间与媒介场景生成的特定意蕴之中。差异,而不是同一,是“返归”想象的着力所在。
首先来看一下空间。“版面”另有一个英文表述——space。“版面/空间”既实在有形,又像“视窗”一样,邀请人们进入虚拟无形中想象与漫游。而这种想象与漫游,终究也无法脱离具体的实体空间的彼此“搭桥”(articulate),并为此“勾连”赋予意义。在这种复杂的空间交往中,“版面”的纸张油墨,占据着一个拥有特定体积与重量的实实在在的“位置”,色彩线条则在其上勾勒出区分与联结的布局;伴随着机器的轰鸣、轮子的摩擦和报童的吆喝,“版面”进入到了城市街道、家庭餐桌、咖啡馆吧台、弄堂天井,和张贴过“告示”的墙壁,也就进入了生活世界中的私人或公共“空间”。
“版面”流动于这个“相互‘媒-介’着的网络”中,“新报刊史”追随它的位移,仔细探查每个空间的独特性,是如何与同样独特的媒介实践发生着关联的。或许,它会飘落在20世纪早期印尼爪哇岛城市某条“长长的藤制躺椅上”,一位年轻人在“一页页翻着”中“看得入神了”。“我们的年轻人”,实际上正在参与一种仪式,由“版面”筑造出来的“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共同体的想象”;而像他一样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25]这种仪式与想象,与各地教堂里的“早祷”很相似,不过,早在1806年,黑格尔就把家庭中看报纸的行为,视为市民阶层“早晨的礼拜”,就如同他从进入耶拿城的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这种与启蒙现代性紧密相联的“版面”,在后来的尼采眼里,却成了“早晨的呕吐”。[26]又或许,它飘落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某辆“时髦”的城市公交车或机车上,在那些“眼睛、双手都空闲下来”的人那里,“版面”成了新的风景,并因之也改变着自身:“缩小了纸张尺码,加大了标题字号,大量运用图片,还发展了‘导语’段落”。[27]部分因为这种景观,人们能够打发西美尔所说的那种“从未置身过的处境”,即在19世纪公共汽车、铁路和电车“完全建立起来”之后,乘坐者可以“数分钟甚至数小时之久地互相盯视却彼此一言不发”。[28]宗教与世俗、工作与旅行,换言之,所有人类社会的交往形式和意义建构,韦伯的“组织”、涂尔干的“教堂”和马克思的“商品”,以及滕尼斯的“社区”、芒福德的“城市”,当然还有哈贝马斯的“咖啡馆”,所有这些实体的、想象的或制度的“空间”,都会因“版面”的连接而生成着新的面貌。“版面”筑造其间,即是“新社会”也是各种权力“秩序”之生成,而这些空间中“版面”实践的面貌,彼此之间也可谓千差万别。19世纪晚期投身《申报》的士人,与他们的读者发生了一场争论,“京报”究竟该在“版面”中占据何种位置,报首还是附张?[29]他们争论的,某种意义上就是彼此眼中“国家”与“城市”的关系。换作《时务报》,这或许就不是一个问题。
在“返归”的媒介想象中,“版面”自始就保留着其字源的一个“原始”意象:身体之“(脸)面”。“版面”就是一个“身体”,有报头、报眼与报耳,它“瞭望”、“交谈”与“布道”,它展示各种人、事、物的“形象”,甚至被视作国家之“脸面”。身体总是活动于 “地方”与“场景”之中,并且也总是在其中形成或短或长的记忆、或显或潜的意识。如此就将时间与空间扭结在了一起,而时空本就是“单一经验的不同方面”,它们“互相结合、互相定义”。[30] “人类时间像人体一样是不对称的,一个人的背部通向过去,而脸部朝向未来”。“版面”也是如此。它将“过去”置于当前,又将当前引向“未来”。如果说,“生活就是要求永远向前朝着光明迈进,放弃自己身后无法看到的黑暗与过去”,[31]那么,与“版面”互相嵌入着的“生活”,也就有着独特的“过去”与“未来”。报纸的时间,不同于书,它塑造着不同的感知、记忆与回忆。
麦克卢汉将报纸视为“集体独白”,区别于书籍的“个人独白”,他还在与“爵士乐、切分乐、立体主义”的联系中体味“报纸头版”,因而,报纸的时空感知既与书籍相异,又与现代艺术形式有相类之处:
报纸新闻的爵士乐、切分乐那样的非连续性与其他现代艺术形式有关系吗?为了报道的范围包括从中国到秘鲁的广阔地区,同时又实现焦点集中的同步性,你能够想象比报纸头版的立体主义更加有效的方式吗?你是否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版面的新闻像是一幅印象派的风景画?[32]在麦氏那里,“电报式报纸”对时空的重组,对“广阔空间”“实现焦点集中的同步性”,引发了人的兴趣与群体成员的广泛参与;他的学生波兹曼则与之不同,波兹曼将报纸置于与摄影术、电报的杂交之中,解读出特定的时空转换:“(印刷)阐释时代”即将逝去,一个“美丽新世界”由此诞生:“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世界”。[3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是从报纸与小说的联系中,重新阐释那种“同时性”: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在那时间内部,‘世界’强健地向前奔驰而去”。[34]同样,当报纸在晚清开始抢占书籍的风头,人们也感受到了新的时间:正如初创时期《申报》广告的自我表白,“每晨发一张,风雨不改”,那不也正是一种向着未来坚定直奔的热切宣告吗?《点石斋画报》像所有定期出版的报刊一样,近乎“风雨不改”地连续着,然而它的每期编号却既有“甲一”、“甲二”,又有“天干”这样古老的“非线性”标识;也像它的版面,一页一页翻过去,不连续的图像又会连续起来。读者在一种连续的“理性生产机制”中发现,“一种稳定的视角很难保持不变”,研究者称之为“连续的不连续性”。[35]在差异与同一间不断返归的媒介想象中,所谓“连续”或“断裂”,并不存在于历史本身,只能存在于对历史的建构中。“新报刊史”与其说要展现“连续的不连续性”,抑或发掘“断裂与连续”的变奏,毋宁是要让历史展现出一种独特面目,即本雅明眼中的“暧昧”——“恰恰是现代性总是在召唤悠远的古代性。这种情况是通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产物所特有的暧昧性而发生的”。[36]而这篇短文已经显示,蕴含着“特有的暧昧性”的那些“社会关系和产物”,总是与特定的媒介技术、媒介感知和媒介时空紧密缠绕在一起。
“版”与“面”在当下“这个时代”的组合,也呈现着这种媒介史的暧昧。Facebook或“脸书”,这个值得玩味的名称,囊括了从身体、印刷到数字化的融合。Face是“脸”也是“界面”,Facebook既是人们打交道的对象,也是借之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界面。这个界面融合、改造了所有的身体空间与想象空间,又把face的气息、book的痕迹保留在了新的筑造之中。书页之前,“版面”是以羊皮卷或竹简的方式在手中徐徐展开;计算机之后,“版面”是以下拉“菜单”的方式伴随手指平滑移动。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将一种网络最基本的界面工具Explore,翻译为“浏览器”而不是“探索器”,可谓无意间切中了媒介史的核心问题。
四、“手”与“艺”的双重联结
本雅明认同于这样一个判断:“在波德莱尔那里,诗歌创作像一种体力劳动。” [37]在万籁俱寂抑或阳光明媚之际,波德莱尔的“决斗”中确乎留存着“体力劳动”的印迹:“俯身在他的桌子上”“左右劈杀”,“在衬衣上试用鹅毛笔”,“把杯子里的水溅到天花板上”;在“毒辣的太阳下”,“绊在字眼上”,“也绊在石子路上”。他有时会“惊恐地尖叫”,为了捕捉“会逃掉的影像”,他的“手”一定与他的“心”一样,“急速而紧张”地活动着。
本雅明的认同有着很深的缘由。因为“经验”的成型,联系着人将活生生的“身体”感知与已有记忆(往往体现为“传统”)融贯起来,而那些现代城市中来自外部世界巨大能量的“震惊”,就有可能无法被经验吸收而造成“创伤性休克”。当然,本雅明同时也对“震惊”保持着敞开的一面。在多数表述中,他对“版面”的洞察与波兹曼有相近之处:“新闻信息的原则所起的作用”——这些原则包括“新鲜、简短、易懂,尤其是各条新闻之间没有联系”,如麦氏所说的那种“印象派绘画”——“与版面编排和报纸风格一样大”。这样一种同时并置的“不连续性”和“转瞬即逝性”,在本雅明眼中给感知带来了“创伤”,因为信息不能纳入传统,“版面”脱离了“经验”。与之相对,作为“最古老的传播方式之一”,“讲故事就带有讲故事人的印记,正如陶器上带有制陶人的手印一样”。[38]如果“新报刊史书写”所期待的“技艺”,指的是art而非technique或technology,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遵从本雅明的启迪,将这一“技艺”称作“手艺”,一种同时也是“体力劳动”的精神劳作,一种从当下跃动着的“身体”经验出发,不断分离又不断返回的再反思与再理解。[39]就像“制陶人”在故事中留下“手印”一样,这一手艺,是“手”对“泥土”的拨弄与捏塑,是对“物”之聚集与筑造的敞开;是对“地层”的层层考掘与拂拭,是让某种“秩序”图景小心翼翼地在“手”中破土而出、清晰绽放。这也就意味着,新报刊史将媒介想象的“超越与返归”同时运用于自身,它信奉米尔斯所言,“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地把握了他生活的时代的思想”,[40]反过来,也正是迎面当下媒介剧变所生发出的困扰,激发它同时走进历史与未来,同时质疑与超越各种“幻象”。一个“秩序”,就像波德莱尔冀求的“偶然的韵律”,或许就在此间呼之欲出。
对“手印”的关注,提醒着德布雷去辨别“arts”一词的分裂,以及其中所展现的“阶级分别和价值分别”:原本art包含着“除了天生以外,后天获得的所有东西”,后来却分裂为“技术”与“文化”的“分别”:“关系到体力生活的手工活动和材料活动归于‘技术’一词”,而将“精心雕琢、精心设计”保留在“文化”之中。[41]这与威廉斯对“文化”和“大众”概念史的反思,意气相投。这不由也让人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去追问:那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名的报刊史书写,在某个面向上却偏执于“内容”与“观念”而不能自拔,是否也是那种古老的“君子不器”、“道器观”的折射?德布雷就有这样的反思:对技术的轻视“尤其是在基督教的拉丁文化国家”,要比新教国家更为严重。[42]因而,在相当意义上,“新报刊史书写”之“新”,就在于对“手”与“艺”的重新联结。这种重新联结是对自身的丰富,也是对“对象”的尊重。基特勒批评2500年以来的西方哲学史“都完全忽视了其自身的技术媒介”,倡导建立“媒介本体论”,从他称之为“硬件”的“物”出发,以“物”的储存、处理与传输为轴心,重构整个文化史;[43]梅洛-庞蒂也为历史建立起一种新形象:“我们不必关心历史的‘头脑’和‘脚’,但要关心历史的身体。” [44]直白地说,“新报刊史”尊重不同视角和进路的各自价值,但它既不醉心于单纯地描绘“思想的战场”,也不沉陷于排列遗失了意义和理解的“脚的行动”。它让自己的“关心”落在“历史的身体”上,这或许就意味着,要“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45]最后,将“手”与“艺”的重新联结,意味着“新报刊史”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平实的目标:它的确会考掘出某种“秩序”,但那不是一切,也不会取代一切;它的确可能做到了某种对“幻觉的超越”,但那“不是去发现另一种真理的基础”,而毋宁是——“有勇气和力量与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一起生活”。[46]如果一定要说及“真理”,那么它宁愿欣赏乔治·巴塔耶所说,“要紧的事情从来不是肯定”,“严肃、死亡和痛苦奠定了迟钝的真理”。[47]■
①[法]波德莱尔:《太阳》,载《恶之花》第209页,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③[36][37][38][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第138、184、21、195-196、198-199页,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④[德]本雅明:《拱廊街计划》,转引自:[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第284页,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⑤[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第288页,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⑥[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第49-50页,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⑦[法]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第184页,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⑧[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第17页,李冠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16][41][42][法]德布雷:《媒介学引论》第23-24页,刘文玲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德]海德格尔:《筑·居·思》,《演讲与论文集》第161-162页,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本文看来,媒介学家对“媒介”的概念化理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做“聚集”观,例如将媒介视为一个场景中“组合内容”的方式、一种“接收/形成体验”的空间、一种“组织”或“社会制度”等。
[11]王庆节:《道之为物: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12]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第41-42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德]海德格尔:《物》,《演讲与论文集》第172-195页,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13]此处牵涉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即当媒介想象从有限“在场之物”拓展联结到广阔无限的“不在场之物”时,如何处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以及“无限”的边界问题。这值得专文讨论,此处仅借助美国学者卡斯滕·哈里斯的“视角原理”(principle of perspective)稍加提示,“要把一个视角理解成视角,把视角显现理解成视角显现,那么至少在思想中就已经超越了这些视角的限制”,“把有限当作有限来思考,就已经对无限有了某种认识”。[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第156页,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第一部分已指出,所谓“超越与返归”都与特定“视角”息息相关。
[14][32][加]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第1页,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董琨先生指出,青铜作为礼器多用于祭祀,用途隆重,相应其上铭文就需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甲骨文虽也是宫廷乃至商王亲自使用,但时效短,多“一次性使用”,其书写就不免讲求便捷。由此也出现了汉字正体的变体。董琨:《汉字的源流》第111-112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7][美]李普曼:《公众舆论》第280页,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种子”比喻见该书第270页。
[18][33][美]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第11、70页,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9][22][23][德]海德格尔:《筑·居·思》,《演讲与论文集》第162、154-159、160页,孙周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
[20][21][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7页,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4][美]塔奇曼:《做新闻》第4页,麻争旗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美]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第8-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34-35页,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6][日]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第8页,诸葛蔚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美]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第92页,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第103页;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指出,这主要是中上阶层的体验,对下层阶级来说,“他们是在铁路出现之后才加入旅行者的行列”,“愉快的交谈和笑声”会回响在“坐得满满当当的”三、四等车厢里。[德]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第125页,金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9]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第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0][31][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第100、105、106、108页,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4][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33页,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5][美]包卫红:《全景世界观:探求〈点石斋画报〉的视觉性》,李迟译,《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4期
[39]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40][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179页,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43][德]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菊兰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4][45][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6页,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6][英]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第23页,廖鸿飞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7][法]巴塔耶:《内在体验》第261、264页,尉光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孙藜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