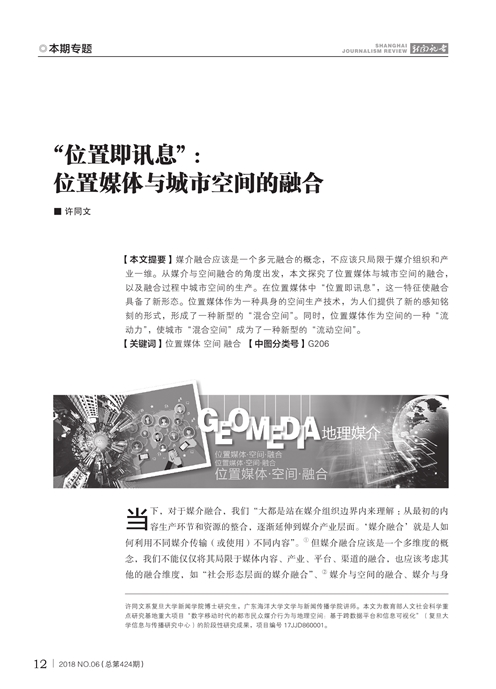“位置即讯息”: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
■许同文
【本文提要】媒介融合应该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概念,不应该只局限于媒介组织和产业一维。从媒介与空间融合的角度出发,本文探究了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融合过程中城市空间的生产。在位置媒体中“位置即讯息”,这一特征使融合具备了新形态。位置媒体作为一种具身的空间生产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感知铭刻的形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混合空间”。同时,位置媒体作为空间的一种“流动力”,使城市“混合空间”成为了一种新型的“流动空间”。
【关键词】位置媒体 空间 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当下,对于媒介融合,我们“大都是站在媒介组织边界内来理解:从最初的内容生产环节和资源的整合,逐渐延伸到媒介产业层面。‘媒介融合’就是人如何利用不同媒介传输(或使用)不同内容”。①但媒介融合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局限于媒体内容、产业、平台、渠道的融合,也应该考虑其他的融合维度,如“社会形态层面的媒介融合”、②媒介与空间的融合、媒介与身体的融合等。本文关注媒介与空间的融合。这种媒介与地理空间的融合,产生了一种“地理媒介(Geomedia)”其意味着“媒介技术中的几个关键性转变,这些传播技术上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媒介与城市空间的关系”。③
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使当代城市成为“媒体-建筑复合体”,产生了一种“媒体城市”。“媒体城市这一术语旨在凸显媒体技术在当代城市空间的动态生产中的作用。” ④位置媒体(Locative Media)充分体现了这种技术与空间的融合,成为“由媒介到地理媒介”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对于位置媒体而言,其与空间的融合也重新定义了空间。⑥本文以位置媒体为个案,试图分析这种媒介实践如何体现了媒介技术与空间的融合,这种融合有何特征,这种融合形成了怎样的城市空间。
一、“位置即讯息”:位置媒体与空间融合的表现与意义
位置媒体是具有位置感知功能的媒体,其主要通过GPS定位设备感知用户的物理位置,据此提供此地及周边环境的相关信息,也被称作是“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⑦2003年,由Kalnins、Tuters组织的“‘位置媒体’国际工作坊”第一次提出“位置媒体”这一概念。⑧位置媒体可以被视为现代数字技术的第三次浪潮。⑨国内外现有的位置媒体种类繁多,如Foursquare、谷歌地图、美团、陌陌、咕咚等。人们可以使用位置媒体进行导航、记录移动轨迹、签到、制作地理标签、社交、购物等。位置媒体对于人们创造及维持社交关系、传播信息、形塑地方具有重要意义。⑩位置媒体的可供性激发、创造了新的社会实践。“无定位,不场景”,位置媒体可以说是一种“新生的革命性的场景软件应用程序”。[11]对于位置媒体来说,“移动设备所在的地方使我们成其所是”。[12](一)“位置决定信息”:融合的表现
在位置媒体中,位置是信息的先决条件,位置媒体区别于其他移动媒体最大的特点是物理位置与网络间的关系,位置媒体“把互联网带回到了地球”。[13]可以说,位置不同,人们在位置媒体中接收到的信息也不同。数字网络和物理空间融合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Eric Gordon和Adriana de Souza Ee Silva所言:“物理位置成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设备所在的位置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留下的数字踪迹构成了我们的物理世界”。[1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位置即讯息”。
读书、听音乐、通过移动电话和朋友交谈其实都是一种将信息附加于物理空间的一种行为。但是在这些情况中,物理空间对信息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和在另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在内容上并无差别。但位置媒体就截然不同,人们在使用位置媒体时接触到的信息是与他们所在的位置有关的。[15]人们接收到什么样的信息,依据的是他们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人们在不同的城市中的不同的街道通过位置媒体所接收到的信息是不同的”。[16]在这一方面,位置媒体与空间的融合不同于其他媒体,其不是一种简单的叠加。在位置媒体与空间的融合中,一方面位置决定信息,另一方面这种信息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位置的感知。“随着基于位置的搜索在百度和谷歌之类的主流引擎上日益普遍,我们所在的位置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帮助我们组织我们接触到的媒体内容”。[17](二)“网络位置”:融合的意义
这种网络与物理位置的融合,改变了网络与物理空间的传统二分逻辑。据此,Eric Gordon和 Adriana de Souza Ee Silva将这种网络与物理位置的融合称之为“网络位置”(Net Locality)。[18]这一概念意在表达虚拟的网络信息被位置化了,地理位置成为网络的组织逻辑。我们在位置媒体中看到的节点是一种“锚定的节点”,即数字网络与数字设备所在的物理空间成为紧密的整体,而非卡斯特所强调的在网络社会中“漂浮的节点”。
电子媒介的兴起曾让人们断言地理就此终结。梅罗维茨认为电视使“有形的空间结构大大降低了其社会重要程度”。[19]卡斯特面对互联网的崛起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20]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节点的关系,节点与物理空间的位置则关联不大,我们可以将这种节点称之为“漂浮的节点”。尼葛洛庞帝认为:“作为信息的DNA,‘比特’迅速取代‘原子’,现行社会已形成一个以‘比特’为思考基础的新格局。” [21]Ling认为移动通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减少了物理距离的重要性。[22]但正如de Souza e Silva和Jordan Frith所言,卡斯特、Ling等人关于移动技术的研究忽略了物理位置的问题。[23]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革新,空间被视为一种或多或少被克服了的障碍,其重要性在传播过程中被隐去了。在这些论述中,研究者显然更多地强调了数字信息的重要性。其虽然并未明确否定物理空间的价值,但是物理空间和数字信息的二分却是显而易见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地理终结”的论断被逆转,“移动性持续增强,地理非但没有加速终结的命运,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24]如在位置媒体中,物理空间的重要性就被凸显出来,信息基于空间被生产,空间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首要因素,物理空间与数字信息在这一媒体形态中被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Jordan Frith将这一新的位置与空间的融合形式称为“从原子到比特又回到原子”的过程。[25]
二、“混合空间”:融合过程中空间的具身生产
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实践论引入到空间研究的领域,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完成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转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始了一场“空间转向”。在传播学领域这种表现的代表是“传播地理学”。Paul C. Adams与André Jansson认为:“空间是‘通过’、‘为了’、‘在’中介化的传播创造的。” [26]André Jansson与Jesper Falkheimer认为:“地理与传播之间的联系在于所有形式的传播都是在空间中进行的,所有的空间都是通过传播来表征的。换句话说,空间生产理论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传播和中介化的理论。” [27]在传播地理学看来,传播是空间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有什么样的传播就会有什么样的空间生产。进而,遵循“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媒介有不同的空间生产能力。从空间与媒介融合的角度来看,在传播地理学的视野中,媒介的因素始终是与空间相关联的,不同的媒介(即不同的传播和中介化过程)与空间相融合的表现,以及这种融合所对应的空间生产也是不相同的。媒介与空间融合的重要体现便是媒介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具体到位置媒体与空间的融合中,我们认为这种融合过程中的空间生产是一种新式的具身生产,其生产结果是一种新型的“混合空间”。
(一)位置媒体与空间的具身生产
位置媒体作为一种新的具身技术,对空间进行了再生产。“在研究新技术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空间和具身的关联。空间的观念和具身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28]具体到位置媒体的研究,Leighton Evans和Michael Saker认为在研究LBSN(Location-based social media networking)的影响时,如果不考虑位置和技术使用中的具身问题,这种研究是不充分的。[29]梅洛-庞蒂关于具身的核心观点是具身是通过感知实现的,“具身的理论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感觉的理论”。[30]基于梅洛-庞蒂的具身观念,Farman将后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感知铭刻”(sensory-inscribed)的概念。这一概念认为影响感知(即具身)的因素,既包括身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包括数字化、物质化的媒介因素。空间中的身体是“感知铭刻的身体”(sensory-inscribed body),具身成为一种空间化的实践。在Farman看来,传播技术是感知铭刻的重要形式其较为强调空间的具身生产,这种具身是一种以数字界面为中介的感知铭刻。在这一意义上,身体、媒介、空间融合成为一个整体。[31] “每一种人类-技术的关系都是一种身体-工具的关系,每一种身体-工具的关系都能够产生某种类型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以及不同的了解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方式”。[32]不同的技术对应不同的“感知铭刻”,不同的具身实践所产生的空间经验也是不同的。位置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感知铭刻”的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具身形式,以及“一种新的空间生产的渠道”。[33]Dodge和Kitchin认为软件(或者编码)对于空间理解的影响持续地改变着空间。[34]承接Dodge的“编码/空间”理论,Evans将LBSN等位置媒体的使用看作是一种编码实践,认为其创造了新的空间性。于是,位置媒体成为一种“具身的代理人(embodied agent)”,其通过物理的或数字中介化的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35](二)作为混合空间生产方式的位置媒体
作为新的感知铭刻技术,位置媒体重新定义了空间。“界面的每一次改变都将会重新定义由其中介的社会关系及空间。移动设备创造了人们和互联网之间更加生动的关系,其嵌入了人们的户外活动和日常生活,我们再也不能够严格区分开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界限”。[36]基于此,Silva提出了“混合空间”(hybrid space)的概念,“混合空间是一种流动的空间,在移动的过程中用户和因特网及其他用户之间建立了一种持续的关联”。“这种城市空间中移动过程中的持续关联是通过将遥远它处的环境叠加在身体所处的当下环境而实现的”。“手机中的位置功能较好地印证了这种混合空间”。“互联网和位置功能的叠加,使用户和网络及物理空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关系。我们空间经验的改变既意味着一种新的交往形式,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生活的空间”。[37]混合空间这一概念并不仅仅强调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一种简单叠加,其更为强调在移动过程中的叠加。这就凸显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空间生产的独特性,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在移动的过程中融合,而位置媒体则具备了Silva所谓的混合空间的特征,且呈现出新的特征。
Jordan Frith认为混合空间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位置媒体及其社会影响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混合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受基于地理位置的移动网络影响的空间,其同时也是一种展示了物理空间如何形塑移动网络意义的空间。在混合空间中,物理位置决定了接收者所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就像基于地理位置的信息影响人们如何在地理空间中移动一样。依靠接触到的空间信息,移动屏幕中介了人们的空间经验以及移动”。[38]Jordan Frith认为社会交往、数字信息和物理空间三个元素之间的联合构成了混合空间,“混合空间中人们接触到的数字信息不是外在于物理空间的,其对于用户来说本身就是物理空间的一部分”。[39]也就是说,在位置媒体所生成的混合空间,不仅仅具备一般移动技术所生成的混合空间的特征,即数字空间中的信息对于物理空间的影响。其独特性在于突出了物理空间对于数字空间的影响。位置媒体所生成的混合空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叠加或嵌入,而是一种“交互生成”,即以位置媒体为界面,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互相影响。位置媒体所生产的空间是混合空间的一个独特案例,这种独特性源自位置媒体与空间的独特关系,即“锚定的节点”,其更加突出了物理空间对于数字空间的影响,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位置即讯息”。
三、“流动空间”:融合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
混合空间是一种以流动技术为支撑的流动空间。作为一种新的感知铭刻形式和空间的具身生产形式,位置媒体与空间的融合所产生的“混合空间”,促进了城市空间中的流动性。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流动性”转向,这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空间转向”相关联,其关注于物理的、虚拟的、物质的等各种形式的流动,打破了交通运输和社会研究的区隔。移动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40]这种“流动性转向”强调了技术在流动性经验以及空间生产中的重要角色。这种移动技术包括火车等运输技术,也包括媒介技术,特别是移动媒介技术。基于Urry等人的流动性范式,我们认为现代都市是一种“流动空间”,新流动技术的出现会促发新的流动空间。这种流动空间是技术与空间融合的重要体现。位置媒体是当下社会流动技术的代表,其与城市空间融合,使城市空间成为一种新型的流动空间。这种新型的流动空间是上述混合空间的重要体现,也是“混合”的结果之一。
作为一种流动技术,位置媒体是城市空间的一种“流动力(motility)”。“流动力”是指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决定和控制自身和他人流动性的一种资本和能力。[41]位置媒体作为都市流动空间的一种流动力,有助于人、信息、物品在空间中的流动。这具体表现在:位置媒体增加了流动空间的“可读性”,从而使都市“陌生”空间“熟悉化”;移动路线的“灵活校准”,从而改变人们在流动空间中的流动计划;社会交往的丰富性,从而使人的流动更加多元化。位置媒体的这三重“流动力”,共同成为普适计算时代城市流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陌生”空间的“熟悉”化
John Montgomery将“可读性”(legibility)定义为城市的各种要素(如路线、边缘、分区、节点、地标等)被组织成一个清楚的、可识别的模式”。[42]数字技术以新的方式提供了日常世界的可读性,使物理空间中隐蔽的东西可视化。[43]位置感知技术便是这样一种新的数字技术形式,其使这些因素更为可见。[44] “提供了空间信息的新的呈现模式,因为它呈现了关于空间的新的信息、知识”。[45]在位置媒体中呈现的,不仅包括地理位置的信息,还包括空间中物与人的信息:物的信息,如商业类位置媒体中共享单车、出租车、附近商家的信息等;人的信息,如Foursquare、微信、Blued等应用中的用户位置信息。地理位置标签(geotagging)也是一种新的空间书写形式,会影响人们的空间经验。[46]用户将空间的个人感受上传至位置媒体,这种文本嵌入了物理空间,其他用户在使用位置媒体进行位置搜索时,可能接触到这些信息,从而影响他们在空间中的活动。[47]这种地理位置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空间的“可读性”。
当前社会,人们的流动性空前加剧,地方的陌生性是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种陌生性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不熟悉,还包括空间内信息的不可见。导航类、社交类、商业类等位置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这种陌生性,以及由这种陌生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不可见的空间及空间内部的信息清晰化。Humphreys研究发现,Dodgeball形塑了人们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位置信息的创造、分享、交换”,公共空间中的用户在朋友的群体当中产生了一种“共同感(Commonality)”,使人们在不熟悉的公共环境中产生了一种熟悉感。[48](二)移动路线“灵活的校准”
导航类位置媒体最大的功能便是为用户的移动路线提供参考和规划。除此之外,位置媒体中的地理标签、打卡、游戏等功能,也会影响用户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路线。位置媒体大都具有用户生产内容的特征,这些信息会影响其他用户对这一地点的感受及决策。在Jordan Frith看来,位置媒体中的移动地图,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灵活的校准(Flexible alignment)”。“灵活的校准”指手机上的信息检索行为能够改变人们的计划。位置媒体中的移动地图像手机短信、电话一样能够影响人们的协调实践。[49]位置媒体的打卡功能及社交平台上的位置分享功能也会影响人们行走路线的选择。Humphrey发现,用户受Dodgeball的影响,经常改变他们在城市中的行走路线,人们如果通过LBSN发现他们的朋友在附近,就会调整其路线。位置媒体的游戏功能也会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及移动路线。[50]Jordan Frith认为,Foursquare等位置媒体的游戏元素使物理空间游戏化,将“生活变成游戏”,改变了参与者的移动轨迹。[51]Michael Saker和Leighton Evans也认为,Foursquare的游戏因素影响了人们在空间中的流动(如行走路线的选择)和空间关系(如“市长”这一游戏机制的设置)。[52](三)社会交往的丰富性
位置媒体具有社交的属性,尤其是LBSN,既能促进熟人间的社会交往,也能促进陌生人间的社会交往。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位置媒体促进了空间中人员的流动。在人员流动的过程中,促发了丰富的社会交往活动。
位置媒体中,有一些是专门针对熟人社交的应用,如,Dodgeball、微信的位置共享等,Dodgeball将个人的位置、移动进行编目和存档的实践,能够促进朋友间的亲密关系。[53]同时,Dodgeball创建了家和工作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third palaces),导致了一种社会分子化,使活跃的Dodgeball成员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在城市中穿行。[54]微信朋友圈打卡、位置共享、发送实时位置等,都可以促进朋友间的交往和互动。
还有一些专门针对陌生人间的社交应用,如陌陌、身边、探探、Blued等。这类陌生人的社交软件使具有特殊社交需求的群体,发现“附近的人”,进行“地缘实时社交”。这为都市人群的社会交往及线下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Blued这款同志社交软件,基于地理位置信息实现“多维度匹配,他在你身边”,还可以通过“群组”发现附近的各种群体组织。
结语
媒介融合应该从单一的媒介组织和产业的融合,走向多元的融合。媒介技术与空间的融合,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观察媒介融合的视野。从媒介与空间融合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在将我们从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成为空间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方式”。[55]数字技术与空间的融合所生成的“地理媒介”具有重要意义。其“构成了公共空间生产的新环境,影响我们‘城市权力’的占有与实施,影响我们的社会交往,影响我们日常经验中远与近,出席与缺席的关系”。[56]在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中,位置成为关键性的因素,决定了信息的内容。作为一种新感知铭刻的技术形式,位置媒体带来的空间具身生产的经验,生成了一种新的混合空间。这种混合空间中网络与物理位置的特殊关系,增强了城市空间的流动性。从中国经验来看,都市人群的移动性问题、商业模式再造问题、熟人或陌生人间的社交问题、个体的自我量化问题都和位置媒体与空间的融合有巨大的关联度。位置媒体的个案对于我们理解媒介技术与空间的融合有重要价值和意义,需要加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获取丰富的经验材料的支撑。■
①②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③⑤[17]斯科特·麦奎尔:《网络化公共空间》,《中国传播学评论》2017年第七辑
④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⑥⑨[13]Collis, C.& Nitins, T. (2009). Bringing the internet down to earth : emerging spaces of locative media. Record of the Communications Policy & Research Forum.
⑦[15][25][38][39][44][46][49]Jordan Frith(2015),Smartphones as Locative Media,Polity Press.
⑧Mark BilandzicMarcus Foth(2012),A review of locative mediamobile and embodied spatial interaction,Int. J. Human-Computer Studies 70 (2012) 66–71
⑩Evans, L. (2015). Locative social media:place in the digital age. Palgrave.
[11]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
[12][14][18]Gordon, E.& SilvaA. D. S. E. (2011). Net Locality: Why Location Matters in a Networked World. Wiley-Blackwel
[16]de Souza e SilvaA.and SutkoD.(2011).Theorizing locative technologies through philosophies of the virtual.Communication Theory,2011:23-42
[1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版
[21]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版
[22]LingR. (2008).New Tech, New Ties: How Mobile Communication Is Resha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MIT Press.
[23]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Jordan Frith. (2010). Locative mobile social networks: mapping communication and location in urban spaces.Mobilities5(4)485-505.
[24]孙玮:《城市传播:地理媒介、时空重组与社会生活》,《中国传播学评论》2017年第七辑
[26]Adams, P. C.& JanssonA. (2012). Communication geography: a bridge between disciplin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2(3)299–318.
[27]André Jansson & Jesper Falkheimer.(2006)Geography of Communication:The Spatial Turn of Media Studies.Livrena AB,Kungalv,Sweden.
[28][30][31]Farman, J. (2012). Mobile Interface Theory: Embodied Space and Locative Media. Routledge.
[29][32][33][35]EvansL.& SakerM. (2017). Location-Based Social Media.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34]Kitchin, R.& DodgeM. (2011). Code/Space:Software and Everyday Life. The MIT Press.
[36][37]SilvaA. D. S. E. (2006). From cyber to hybrid mobile technologies as interfaces of hybrid spaces. Space & Culture9(3)261-278.
[40]Sheller, M.& Urry, J. (2012).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 Planning A38(2)207-226.
[41]KaufmannV.BergmanM. M.& Joye, D. (2010). Motility: mobility as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8(4)745-756.
[42]John Montgomery. (1998). Making a city: urbanity, vitality and urban design.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3(1)93-116.
[43]BellG.& DourishP. (2011). Divining a Digital Future. MIT Press.
[45]BrewerJoanna, & DourishPaul. (2008). Storied spaces: Cultural accounts of mobilit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know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66(12)963–976
[47][53]HumphreysLee& Liao, Tony. (2011). Mobile geotagging: Reexamining our interactions with Urban Space.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16407–423.
[48][50]HumphreysL.(2010)Mobile social networks and urban public space. New Media & Society12(5)763-778.
[51]Jordan Frith , (2013)Turning life into a game: Foursquare, gamification, and personal mobility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1(2) 248–262
[52]Saker, M.& EvansL. (2016). Locative media and identity: accumulativ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Sage Open, 6(3).
[54]Humphreys, L. (2007). Mobile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dodgeball.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3(1)341-360.
[55][56]McQuireScott.(2016). Geomedia: Networked City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许同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民众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基于跨数据平台和信息可视化”(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JJD86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