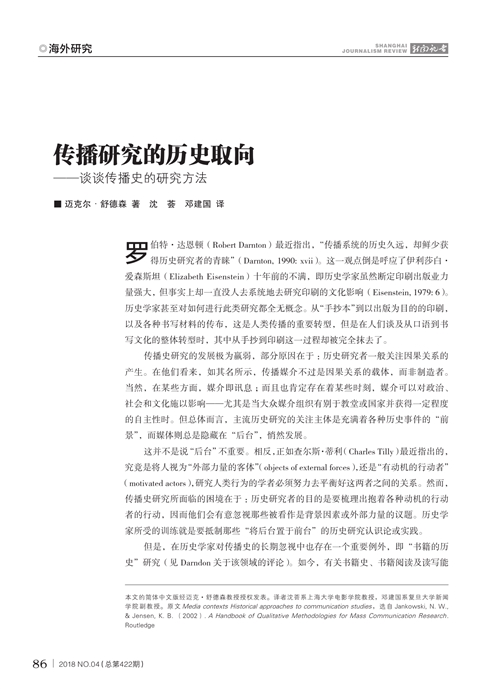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向
——谈谈传播史的研究方法
■迈克尔·舒德森 著 沈荟 邓建国译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最近指出,“传播系统的历史久远,却鲜少获得历史研究者的青睐”(Darnton, 1990: xvii)。这一观点倒是呼应了伊利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十年前的不满,即历史学家虽然断定印刷出版业力量强大,但事实上却一直没人去系统地去研究印刷的文化影响(Eisenstein1979: 6)。历史学家甚至对如何进行此类研究都全无概念。从“手抄本”到以出版为目的的印刷,以及各种书写材料的传布,这是人类传播的重要转型,但是在人们谈及从口语到书写文化的整体转型时,其中从手抄到印刷这一过程却被完全抹去了。
传播史研究的发展极为羸弱,部分原因在于:历史研究者一般关注因果关系的产生。在他们看来,如其名所示,传播媒介不过是因果关系的载体,而非制造者。当然,在某些方面,媒介即讯息;而且也肯定存在着某些时刻,媒介可以对政治、社会和文化施以影响——尤其是当大众媒介组织有别于教堂或国家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时。但总体而言,主流历史研究的关注主体是充满着各种历史事件的“前景”,而媒体则总是隐藏在“后台”,悄然发展。
这并不是说“后台”不重要。相反,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最近指出的,究竟是将人视为“外部力量的客体”(objects of external forces),还是“有动机的行动者”(motivated actors),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必须努力去平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传播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历史研究者的目的是要梳理出抱着各种动机的行动者的行动,因而他们会有意忽视那些被看作是背景因素或外部力量的议题。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就是要抵制那些“将后台置于前台”的历史研究认识论或实践。
但是,在历史学家对传播史的长期忽视中也存在一个重要例外,即“书籍的历史”研究(见Darndon关于该领域的评论)。如今,有关书籍史、书籍阅读及读写能力历史的研究文献,已相当丰富而深入。对自现代早期以来,尤其是西欧阅读公众(the reading public)的历史研究也很丰富(见Graff 1987)。但除书籍史外,历史学不曾对传播史的其他领域有过丝毫的“有组织的”兴趣,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传播史研究中,也没有其他任何领域曾像书籍史研究那样系统地去搜集各种档案材料,并充分受益于书目编纂者和藏书家的工作;传播史中的任何其他领域的学者们也不曾如书籍史研究者那样彼此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进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学术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书籍史的研究者也充分意识到“受众”(audience)研究或“接收”(reception)研究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们将传播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即分析信息的生产、诠释信息或文本的内容,以及考察受众对信息的接收,那么到目前为止“接收”是三个部分中最难以捉摸的。书籍史学者至少是做到了充分承认受众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它的困难性。鉴于这些特点,书籍史研究可以说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其已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次学科(subdiscipline),但这一成功却仍然缺乏一种更加大胆的传播史视野。相比之下,文化、文学及人类学研究者的传播史视域要大胆得多。
一般说来,传播史研究分为三类。我称其为:宏观传播史研究(macro-history)、本体传播史研究(history proper)和组织传播史研究(institutional history)。这里我将聚焦于已有的传播史研究使用的整体理论框架(其中有许多研究可能被认为是定性的)。我会探讨一些特定方法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传播史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方法,而在理念视野上。
一、已有的传播史研究
在已有的传播史研究三大分支中,宏观传播史研究最广为人知。它研究的是媒介与人类进化的关系,提出的是“传播历史如何说明人类本性”这一问题。在传播学取得研究领域合法性上,宏观传播史研究贡献巨大。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加拿大思想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他们留下了许多奇妙而复杂的思想遗产。一方面他们的开阔视野激发了人们对传播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宏阔的论断也引发了人们对传播史研究严肃性的怀疑。虽然两位思想家受到一些人的尊崇,但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对英尼斯的评价是相当尖刻的,而麦克卢汉则已遭到猛烈攻击——更不用说冷嘲热讽了。
实际上,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从口头到书写文化的转变——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并不孤单。杰克·古蒂(Jack Goody)和伊恩·瓦特(Ian Watt)、沃尔特·翁(Walter Ong)以及艾瑞克·哈维诺(Eric Havelock)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其他人最近也采取一些百科全书式的撰写方式对整个传播史进行了梳理和组织。唐纳德·劳氏(Donald Lowe)曾经写了一篇《中产阶级感知的历史》的文章,詹姆斯·贝尼格(James Beniger)开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调查,认为20世纪以信息为基础的控制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一样深远。尽管讨论这些视野广阔的研究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但它们都是该领域的卓越代表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
本体传播史研究,依我看来则是以上三者中发展最为羸弱的。它研究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或者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的社会变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传播领域的变化”。宏观传播史研究仅仅着眼于通过传播看其他事物(something else)——如人性、“进步”、“现代化”等。本体传播史研究则想要告诉我们如何通过传播看社会,或通过社会看传播,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在其恢宏的笔触中,伊利莎白·爱森斯坦的研究便是一个案例。她的研究重点是:从手抄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型,以及这一转型对政治、科学和社会思想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钱德拉·穆可伊(Chandra Mukerji)的研究。他将印刷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具与推动力,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滞后的结果体现在上层建筑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分析了传播在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崛起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研究同样具有代表性。
在以上三个例子中,爱森斯坦关注印刷对人类思想特色和品质的影响,比较偏向宏观历史,另外两个研究则紧密关注传播模式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及文化制度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研究也类似。例如,我关于美国新闻“客观性”这一理念的研究,试图根据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所发生的变化来解释这一职业意识形态(Schudson1978)。我的研究不同于流传极广的美国新闻的标准历史(例如埃默里父子所写的美国新闻史1988)。我认为只有将新闻业置于更广泛的社会中,我们才能将新闻业内部的重要变化解释清楚。
爱森斯坦在研究印刷史时所采取的一个策略,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她所关注的是印刷业对社会精英而不是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这一策略使得研究者在证明“受众接收”的情况时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但是在最近流行的历史研究中却往往被忽视——现在流行做法是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试图通过发掘“读者史”来发掘新读者。然而,例如电视-政治史,它既是电视对观众(政治家讨好的对象)的影响的历史,也是电视对政客影响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电视对政治人物思想的影响,以及电视对普通民众与政治之关系的影响,我认为证据表明前者更大。在广告的影响问题上,我也有类似的观点:广告对投资者、销售人员及零售商的影响较大,对消费者的影响反而较小(Schudson1986: XIV)。
传播史研究的第三类是组织传播史。它研究媒介本身的发展史,主要从媒体组织角度,但也从语言的历史、特定题材(如小说)的历史或电影(如神经质喜剧)的历史来考量。组织传播史研究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或那个)大众传播组织是如何发展的。”至于外部因素,研究者只对那些对他们所研究的传媒组织和产业产生了影响的社会力量感兴趣;另一方面,研究者认为传媒组织或产业对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需要他们去额外调查确定。传播组织史的范围显然是巨大的。历史上存在成百上千个报社、杂志和出版公司,几十个公营私营广播电视公司和电影公司,它们的历史都可以研究。有一些非常杰出的成果,比如亚撒·布里格斯(Asa Briggs, 1961-79)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研究,或埃里克·巴尔诺(Erik Barnouw 1966-70)对美国广播电视的研究。还有数以百计的记者、编辑、出版商、企业家、广告代理商、电影制片人、诗人、小说家、演员出版的回忆录和自传。这些都是传播史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材料本身通常并不能对传播在人类经验和社会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提炼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因此,我在这里对这些研究搁置不提。
在这里我想要阐述的是组织传播史的某些典型优缺点,以及它们对传播史方法论具有的总体上的启示。组织史研究,不管好还是不好,往往要依赖于商业和政府机构的记录和档案。传播组织史研究因此会利用这些资料,强调媒介生产者的内部视角以及组织成长和变化背后的动机以及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然而,机构记录可能很少能揭示媒介对于个人意识或政府与社会结构的广泛影响。这导致媒介组织史往往沦为组织领导人的个性展示和组织内部不断调整重组的历史。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生产书籍和电影的机构和生产滚珠轴承或消声器的工厂固然不同,但如果按照以上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史,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差异了。
对以上任何一类传播史研究来说,试图确证媒介组织对文化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并非易事,因为调查数据匮乏(甚至即使能获得数据,它们也不完整)。就拿最基础的问题为例:谁(who)在过去读了什么(what)?历史学家经常不得不仔细研究各种文学作品。例如,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阅读便士报的人都是谁?关于这一点,彼时的社会学调查无法给我们任何提示。当时的便士报编辑们宣称,他们知道谁在读他们的报纸,但这些话里有营销的成分,我们只能对之半信半疑。而另一些竞争性报纸的编辑们则另有说法,我们对之当然也不能全信。我们能找到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的日记(1889),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纽约人,记录了很多他所在城市的日常生活,这给研究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也能收集到其他来源中的零星记录,比如P.T.巴纳姆(P.T. Barnum 1871: 67)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他最初来纽约时是通过《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的分类广告找工作的。还有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他的小说《归途》(Homeward Bound1838)及《重归故里》(Home As Found1938)中都虚构了报纸编辑的角色,这名编辑还发表了反报纸的言论(Cooper1838/ 1969)。尽管如此,对“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阅读便士报的人都是谁”这个问题还是无法做出一个全面丰富的回答。
最近,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时期的阅读公众时取得了一些方法上的进步。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1989)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一书中着眼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一小部分美国人的阅读生活史。布朗从这些读者那里获得了大量信息,包括详细的日记。这些日记和相关文件中的片段展现出日记主人的阅读生活史以及他们对这些阅读的评价(当然这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评价信息也不多)。威廉·吉尔默(William Gilmore1989)的关注对象则不是个体,而是一个地理区域——佛蒙特的一个乡村地区。他尽量全面地搜集了1770-1830年期间这个地区个人家庭图书馆的藏书、报刊订阅和书店为各个小镇(地理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和家庭(财富水平不一)提供的图书目录。然而,对他来说,追踪报纸的使用情况比详细介绍书籍的使用情况要难得多,因为报纸会被传阅或者被扔掉,而书籍则被保存下来,并在家庭的财产目录和遗嘱中得到说明。大卫·诺德(David Nord, 1986)关注更晚的一个时期。他通过1891年美国劳工处所做的社会调查得出的个人家庭数据,了解到当时工薪阶层读者的一些情况。他发现,阅读行为与阅读者的地理区域、民族和收入都有关,秉承法理制度(Gesellschaft)的家庭的阅读量比秉承礼俗制度(Gemeinschaft)的家庭要大。也可以发掘出一些其他的证据,例如书籍史研究者也分析了绘画和其他艺术作品对人们的阅读行为的描绘(Darnton 1990: 167-8),但研究者同时也反思了这些证据的价值和局限性。
传播组织史研究或者任何传播史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其基本研究材料的“易逝性”(evanescence)。在美国,1968年范德比尔大学建立了电视档案库,对每晚电视新闻予以录制保存,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全国电视新闻资料可供研究。即使如此,想要从范德比尔大学获得资料,不仅所费不赀,而且手续繁琐。如果研究者想要讨巧,则可以使用20世纪60至80年代中期CBS电视新闻文字打印稿缩微胶卷,但对于其他电视网则不存在这样的档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通俗小说、流行唱片、电影或小镇报纸,很多这类记录已难觅踪影。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1984:174)对1850至1950年英帝国通过媒介进行宣传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发现之一就是过去学校的各种教科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影片也正在世界各地破损解体——历史记录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Kaufmann,1990)。
二、传播史研究方法和案例
现在让我谈谈具体的、方法运用得当的本体传播史个案。这种历史让我们注意到传播(它以不同的形式和维度所展现出来)在人类经验中的地位。它从宏观传播史研究中获得灵感,提出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人类学问题:“传播媒介是如何塑造人的性格的?”但是本体传播史研究进而将这个哲学人类学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媒介变化(不仅是其从一种介质到另一种介质的具体变化,而且包括特定介质内部发生的组织、意识形态、经济关系或是政治赞助上的诸种变化)是如何同人类经验的变化相联系的?”宏观传播史研究主要思考媒介如何形塑人的心灵,而我这里所描述的本体传播史研究思考的则是媒介(media)怎样与其使用者、时间和空间体验、公众之观念、政府与社会之观念和实践,以及语言(语言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等因素之间相互建构。
迈克尔·麦格尔(Michael McGerr, 1986)关于19世纪晚期美国政治选战宣传(campaigning)变革的研究堪称经典,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仔细考察了媒介与政治这人类实践领域之一)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次,他对“媒介”的理解没有局限在通常所说的三种类型(口头、书写和电子媒介)上。麦格尔感兴趣的传播媒介是政治选战宣传——它既包括口头的和参与性仪式传播,又包括演讲词印刷稿的传播以及政党所组织的各种大众景观。这非常有意思,政治选战宣传是一种能体现美国整体文化的符号特征的媒介。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笔下的菲利亚·福克(Phileas Fogg)在旧金山下船时,他对美国的初次体验就是被街道上参加竞选集会的人群挤来挤去。
麦格尔的意图是想要解释,“(过去政治宣战那么火爆)为什么今天的政治宣传却不再能使美国人兴奋了”。他认为,美国在19世纪中期有过一段非常活跃的政治生活,其特点是形象生动而有时又显凶猛的政党宣传;公民对政党表现出炽热的忠诚;以及大量公民参与的“壮观的”政治活动。他发现,到20世纪20年代(需要提醒的是,这是在电视出现很久以前)左右,这种“大众政治”已被“一种狭隘的公共生活所取代,这与我们今天很相似”(Michael, 1986: VII)。
对19世纪90年代后美国投票率和政治参与度下降这一现象,不少人试图作出解释。麦格尔是其中之一,但他的解释颇有新意。他强调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对选举活动应该采用何种传播方式有所限定,这催生了各种新的竞选实践。此前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城市自由主义改革者发现,强大的政党系统和公民对政党的狂热忠诚存在不少弊端。于是他们发起了与政党决裂的独立运动,建立党外组织,比如“好政府俱乐部”及市政改革组织等。他们推动选票改革和公共服务,开创出一种“另类政治风格”(Michael,1986: 66)。他们在政治竞选中不再将资金耗费在游行时的服装和手电筒上,而是用在对选民有广泛教育意义的宣传手册上。在他们所倡导的模式中,政治运动是室内活动,是以阅读为中心的,而不是一个户外的嘉年华。1888年,一位威斯康星州民主党领袖承诺“舍弃激情演讲这样的竞选方式,尽力去教育或说服公民,诉诸其智慧”(Michael, 198687)。《纽约时报》称赞候选人格罗夫·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在其竞选宣传中将重心放在关税问题上,因为“它并不诉诸选民的情绪”(Michael, 1986: 89)。当竞选宣传方式从游行转向散发小册子时,当时人们所贴切地称为“政治新教”的政治宣传就开始了。
麦格尔的研究对传播学很有启发性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麦格尔所提供的历史视角,迫使我们对历史生活有更为丰富的理解,例如,他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因为电视和电视竞选的出现才使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开始下滑。第二,麦格尔对政治传播的考察并没有局限在诸多媒介史研究都存在的(传播)组织狭隘性里。也就是说,在他的研究中,新闻业尽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他所描绘出的引人入胜的剧目中,真正的重头戏则是由政党领导者担纲的。在麦格尔的研究中,政治党派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媒介。如果我们将传播媒介定义为将信息从一个人或群体传递给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中介物,那么政党(以及其他众多类似物)也无疑是一种传播媒介(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例子也很容易找到:1990年时,相较于新闻媒体,政治党派是更强的议程设置者,甚至在美国衰弱的传统政党系统中也是如此)。第三,在传播学领域,普遍认为传播的传递观(transmission models of communication)和仪式观(ritual models of communication)存在差异,但麦格尔没有受到这一区分的限制。他在审视政治竞选时,明显地注意到这两种模式都在起作用。他所记载的竞选宣传变革,我们可以总结其特点,即从开始的一个公共仪式般的竞选——“一个公共的自我启示的过程”——转向一个信息传递式的竞选。或者,用麦格尔(1986: 149)的话说,后者是一个具有“教育性”和“广告性”,而非“景观性”的竞选。这就将两种传播模式归为一个谱系。在麦格尔这里,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生动。麦格尔的研究对传播学很有启发性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研究路径将传播媒介融入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中。
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一直在研究“作为传播的剧院”问题,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莱文考察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戏剧在美国的接收情况。他发现,在19世纪早期莎士比亚还是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单独满足那些有一定教育水平的群体的品位。但到19世纪晚期,莎士比亚已经被拔高为“高雅文化”,被捧为一般大众智力水平无法企及的文化。同时,观看戏剧成为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公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娱乐同政治一样,经由一个焦虑的、防御性上层阶级的指导后都经历了新教式改革。
麦克尔或莱文的研究都扎根于美国政治和文化历史的独立传统,虽然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是受哈贝马斯的影响,但他们研究的大体框架是来源于哈贝马斯的。1989年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被翻译成英文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尽管英美学者在早些时候从《新德国批判主义》(New German Critique, Habermas, 1974)的大纲和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 1976)的译文中已经得到了这本书的概要。在此书中,哈贝马斯将媒介置于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框架中,从而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单一解释模式。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传播新媒介的增长必然是促进人类自由的推动力。哈贝马斯则另辟蹊径,对“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的出现和衰落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人类若要有效地组织其社会,就需要所有人参与决策,而有效的决策必然需要信息沟通尽可能得自由、充分和公平。因此,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的建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大众化新闻媒体、代议制民主、对政府机密诉讼予以限制的出现,便成为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
哈贝马斯(1989)追溯了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及其19世纪中期开始的衰落。在较早时期,受公共理性讨论和言论自由信念的刺激,中产阶级抨击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国家权力。在新的资产阶级秩序中,报纸和公众讨论出现在咖啡馆和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种公共领域。也就是说,当时在国家及其代理机构和私人的企业及家庭生活之间出现了一个有形的话语空间,即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
但是后来,政治官僚化和媒介商业化都压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前景(当然,这种解放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一开始它仅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公众舆论一旦动态地、真实地进入公共场所,就容易被官僚、广告商和宣传人员操控。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 1977)写过一篇关于资本如何控制英国媒体的重要论文,详细地说明了即使在废除了国家对媒介的直接控制之后,19世纪末的资本扩张都在对激进表达予以压制。这与哈贝马斯论述的立场相一致,尽管在最近的研究中,柯伦尖锐地批评了哈贝马斯,认为他早期的公共领域概念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当时各种激进报刊的重要性和正面效果。(Curran即将出版)。
哈贝马斯的著作没有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其黄金时期(于哈贝马斯而言)的局限性。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驻足民主的伦敦咖啡馆,阅读报纸,与意见领袖讨论,这种熠熠生辉的景象很难与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很小的公众投票参与率、恭敬选举传统以及相对保密的政府决策方式相协调。支持哈贝马斯的历史证据实在太少了,“至今,历史研究者常使用哈贝马斯模型讨论公共新闻,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哈氏何所指毫无了解”。(Dooley1990: 473)此外,如约翰·基恩(John Keane1984)所注意到的,哈贝马斯对当代文化的描绘也太苍白,显得反驳与抵制在这个被精心操控的社会中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即便如此,哈贝马斯仍为传播历史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述(中层研究范本)。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研究传播组织而研究传播组织——这种动机早已经过时了——那么这种理由根本不充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整个传播历史作为人性的核心构成因素去研究(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合理的科学动机),但是又会因为研究对象无所不包而导致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的实际研究。另外,研究对象过于宏大也会导致我们对具体媒介之间的差异研究微不足道。而我认为,这些差异——例如,一个相对自由和相对封闭的新闻业之间的差异——正是值得我们讨论和争论的内容。
三、传播史研究的视角
传播史研究一直有一个未明言的内在结构,它与加思·乔维特(Garth Jowett, 1975: 36)15年前评论中所指出的问题十分接近:“传播(communications)史学家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在一种新的传播媒介被引入社会时将会发生什么。”我认为,现在这不应该再被当作是传播史研究的唯一的核心问题。如果这样规定,那就会将研究指向多种多样的技术。我们现在积累了足够的知识让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取向的合理性。特别是如果我们将“技术”宽泛地定义为口述、印刷和电子通讯技术,传播史研究就会深陷困境。爱森斯坦(Eisenstein1979)将注意力放在两种书写传播模式——手抄模式和印刷模式——的区别上。她的这种研究操作应该是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将之盖棺论定了。
但是即使我们对技术有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比如,书写(如手写和字母系统),由于其是在迥异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被使用,导致书写作为一种技术对不同社会、政治或认知造成的共性影响微乎其微。在我看来,杰克·古蒂(Jack Goody)、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西尔维娅·斯科莱布诺(Sylvia Scribner)有关北非和西非文化中读写能力的人类学研究,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了重要教益(参见古蒂Goody, 1987;斯科莱布和科尔Scribner and Cole, 1981)。我们只能将传播媒介视为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s)和文化供给性(affordances),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74)在他论述电视的书中清楚地区分了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和作为一种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的电视。但这种区分也很容易让人误解,让人以为我们可以将技术和蕴含该技术的文化形式区别开来。在任何时候,新的文化形式的演化-影响与新技术的演化-影响一样重要,也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也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研究,例如,伊恩·瓦特(Ian Watt, 1957)研究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小说的历史;我研究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倒金字塔”式新闻报道的历史(Schudson1982);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即将出版)和奇库·阿达多(Kiku Adatoo, 1990)调查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正在变化的电视内容编辑实践,阿达多将之定性为一种新文学时尚或风格,哈林则将之看作是电视媒体人对专业主义力量的再次确认。
更宽泛地说,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传播史研究的结构所依据的是技术被发明的顺序,这导致传播史研究更青睐某种技术决定论。诚然,在建构传播史时,研究者很难避免不对新技术新发明出现的重要时刻另眼相待。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楚这种以技术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局限性。仅举一例,雷蒙德·威廉姆斯(1983a: 20)研究发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技术的出现使得“一种新的可移动的动态组合”成为可能,于此同时,在艺术界中,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则正在创作一种新型的舞台剧,其中有快速的场景转换、连续的影像,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镜头“叠化”。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斯特林堡影响了早期的电影工作者,亦或说早期电影技术上的新实验影响了斯特林堡。事实是,两者都是当时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运动的体现,也是电影界和戏剧界对这一文化运动做出的回应。
正如宏观历史学家坚持的,传播与一个社会所隐含的时空(time and space)结构有关。研究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人认为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观念)的传播史是非常复杂的。传播实践既是基础性的(我们甚至可能会说是根本性的),也是上层建筑的主要塑造者和载体。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马克思(Marx)和韦伯(Weber)的遗产与涂尔干的人类学遗产(Durkheim1915-1965)联系起来。涂尔干指出,人类不同文化中时空概念都与其社会结构相关。同样,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播历史同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整合起来。我们可以将铁路视为如电报一样的传播媒介(尽管它既承载货物也传输信息);汽车类似于广播,飞机则像电视。
例如,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1977)指出,19世纪美国铁路的发展迫使并且提供了条件促使新的管理模式、新的消费习惯,以及最终新的人们存在方式的出现,这不仅是因为铁路淡化了距离对人际互动的影响,还因为铁路能通过新的协调方式可预测地减少了距离的影响。社会在改变,不仅是因为你可以更快地从A移动到B,还因为大量的商品开始从A向B移动,而且新的协调和传播模式的发展能够对这种突然增加的大规模物体快速流动进行控制。如果传播和运输技术革新为密集的人际互动提供了机会(驱动城市化的就是人类“传播”上的变革),那么这些互动实际上是通过各种日益复杂的人类组织这一中介实现的。因此,传播史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历史(它减弱了时空隔阂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也是社会组织变革的历史(它使时空间的协调变得更加可行和更便于管理)。詹姆斯·凯瑞(1967)早先在批评麦克卢汉时也指出,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其说影响力了人们的“认知”或“心智”,不如说影响了那些管理人们“认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协调模式。“认知”本身不是个人属性,而是一个社会(不只是技术)建构现象。如果传播史研究能够少一些行为主义,多一些维果茨基主义(Vygotskyan1962),它将取得长足进步。
“时间”和“空间”不仅被技术化地和概念化地重新组织,而且也被政治化和语言化地重新组织。如果说传播史研究中有一本著作被很不公平地忽视了,它可能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民族主义问题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安德森对此不足提出了直接挑战。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其实在经典社会理论中,民族主义问题老早就几乎被完全忽视了——韦伯和涂尔干都没有提出比马克思更深刻的观点。安德森(1983: 15)的论证虽然还不够全面完整,但却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洞见——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对于安德森来说,民族国家就是一种富有想象的行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文化载体是小说和报纸。安德森(1983: 39)借鉴黑格尔的理论,将日常报纸的阅读形容为一个大众仪式,是现代人对中世纪晨祷的替代。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相互融合,叠加在人类语言多种性之上,组成了一个新型想象共同体的基础,这个新型的想象共同体就是民族国家。
如果安德森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一个领域(field)的传播就是包含有一个历史性主题的。对此,其他学科一直倾向于忽视,整个传播研究本身则几乎对之完全视而不见。这个历史性主题就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系统的出现是当代大部分社会科学理所当然的背景假设,更不用说是20世纪大部分恐怖事件的主要来源。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1987)最近呼吁传播学者关注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大部分“传播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都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文化及民族国家认同视为理所当然的和毫无疑异的术语。他建议我们抛弃此种认识,而“应当从民族认同如何被建构入手,并将传播与文化放置在这一问题框架中”(Schlesinger, 1987: 259)。
最后,我应当提示行文至此已经很明显的一点:在一篇意图讨论研究方法的论文中,我却几乎没谈研究方法。传播史研究的困境不在于它缺乏或者滥用研究方法,而在于(a)很少有历史论著将传播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或学术问题(problematic);(b)在有关传播史的论著中,很少能承认技术和文化形式的不可分离性;(c)大多数历史研究者都不清楚如何才能将对传播媒介的理解与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变迁的核心议题相融合(大部分历史研究都关注这些核心议题)。背离传播史研究的不是错误的方法而是理念过于粗糙。目前最令人不满意的是:传播史研究游移不定,要么滑向追求刺激而又抽象的宏大叙述,要么沦为狭隘构想的组织史,中层传播史研究还远远不够。至于哈贝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我并不是将他们看作示范性的方法论者,而是视他们为思想者。他们的思想引人入胜,我们可以据之提出传播史研究的新议程。受益于哈贝马斯思想的各种新研究已经涌现于包括历史、社会和传播在内的各领域。而对安德森思想的探索,我认为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
无论如何,历史研究都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更多理论观点,并与其他历史研究的分支——例如与本体历史研究——建立更多的联系。各种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成员都会使用传播技术,我们在分析传播时必须参照这些技术使用背后的特定历史情境;技术本身必须被看作是社会与文化实践,这从传播的生产者和接受者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如果文化产物(objects)的生产过程中包含了一些预设(例如,人们如何制造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信息和如何接受信息等),那么文化产物的接收也应如此。正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90: 171)所言,“阅读不单纯是一种技能(skill),而且是一种制造意义的方式,并且它一定会因文化不同而各异”。我认为,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才可能朝着“将传播史研究发展为一个内部协调自洽的研究领域”这一目标迈得更近。■
①AdattoK. (1990) “Sound bite democracy: network evening news presidential campaign coverage, 1968 and 1988” paperCambridgeMA: 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②Anderson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③Barnouw, E. (1966–70) A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3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BarnumP.T. (1871) Struggles and Triumphs: or, Forty Years’ Recollections of P.T.BarnumNew York: American News.
⑤Beniger, J. (1986) The Control Revolution,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⑥Beniger, J. (1988)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new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2:198–218.
⑦BriggsA. (1961–79) 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4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Brown, R. (1989) Knowledge is Pow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⑨Carey, J.W. (1967) “Harold Innis and Marshall McLuhan” Antioch Review 27:5–37.
⑩ChandlerA. (1977)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CooperJ.F. (1838/1969) The American Democrat, Baltimore: Penguin.
[12]CurranJ. (1977)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J. Curran, M.Gurevitch, and J.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Beverly HillsCA: Sage.
[13]CurranJ. (forthcoming) “Rethinking the media as a public sphere,” in P. Dahlgren and C.Sparks (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London: Routledge.
[14]Darnton, R. (1990) The Kiss of Lamourette, New York: W.W.Norton.
[15]DooleyB. (1990)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to systems theory in early modern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1:461–86.
[16]DurkheimE. (1915/196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7]EisensteinE.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Emery, M. and EmeryE. (1988) The Press and America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Gilmore, W. (1989) Reading Becomes a Necessity of Lif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Goody, J. and Watt, I. (1963)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304–45. Reprinted in J.Goody (ed.)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GouldnerA.W. (1976) 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Seabury.
[22]Graff, H. (1987) The Labyrinths of Literacy, London: Falmer.
[23]HabermasJ. (1974)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49–55.
[24]Habermas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MA: MIT Press.
[25]Habermas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MA: MIT Press.
[26]HallinD.C. (1991) “The rise of the ten second sound bit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
[27]HavelockE. (1986)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8]HoneP. (1889) The Diary of Philip Hone, New York: Dodd, Mead.
[29]Innis, H.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0]Innis, H. (1972)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1]JowettG. (1975) “Toward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History 2:34–7.
[32]KaufmannS. (1990) “Stanley Kaufmann on film: crisis,” The New Republic, 23 July: 26–7.
[33]Keane, J. (1984)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LevineL. (1988) Highbrow/Lowbrow,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5]LoweD. (1982) History of Bourgeois Per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6]MacKenzie, J. (1984) Propaganda and Empi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7]MarvinC. (1983) “Space, time, and captive communications history” in M.Mander (ed.) Communication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Praeger.
[38]McGerrM. (1986) 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9]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40]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New York: McGraw-Hill.
[41]Mukerji, C. (1983) From Graven Ima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2]NordD. (1986) “Working-class readers: family, communityand reading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 156–81.
[43]Ong, W.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Methuen.
[44]Schlesinger, P. (1987) “On national identity: some conceptions and misconceptions criticiz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6:219–64.
[45]Schudson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46]SchudsonM. (1982) “The politics of narrative form: the emergence of news conventions in print and television,” Daedalus 111:97–112.
[47]SchudsonM. (1986) “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in M.Schudson Advertisingthe Uneasy Persua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48]ScribnerS. and Cole, M. (1981)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c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9]VygotskyL. (1962)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MA: MIT Press.
[50]WattI. (1957) The Rise of the NovelLondon: Penguin; repr. 1961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1]Williams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本文的简体中文版经迈克·舒德森教授授权发表。译者沈荟系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邓建国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原文Media contexts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选自Jankowski, N. W.& Jensen, K. B. (2002).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