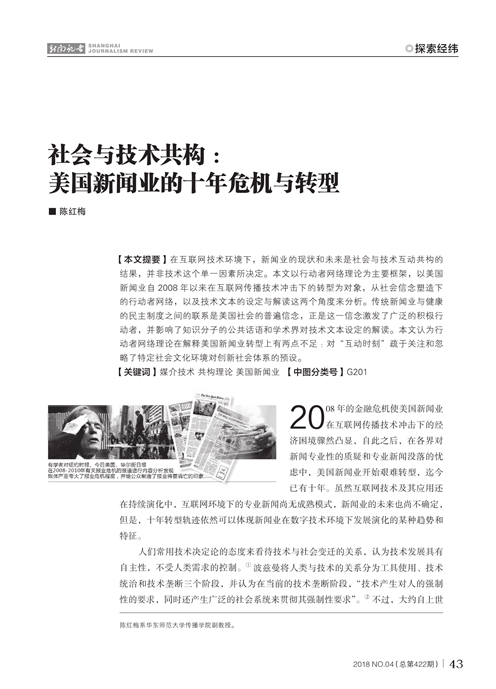社会与技术共构:美国新闻业的十年危机与转型
■陈红梅
【本文提要】在互联网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现状和未来是社会与技术互动共构的结果,并非技术这个单一因素所决定。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主要框架,以美国新闻业自2008年以来在互联网传播技术冲击下的转型为对象,从社会信念塑造下的行动者网络,以及技术文本的设定与解读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传统新闻业与健康的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是美国社会的普遍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激发了广泛的积极行动者,并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和学术界对技术文本设定的解读。本文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解释美国新闻业转型上有两点不足:对“互动时刻”疏于关注和忽略了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创新社会体系的预设。
【关键词】媒介技术 共构理论 美国新闻业
【中图分类号】G201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新闻业在互联网传播技术冲击下的经济困境骤然凸显,自此之后,在各界对新闻专业性的质疑和专业新闻没落的忧虑中,美国新闻业开始艰难转型,迄今已有十年。虽然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还在持续演化中,互联网环境下的专业新闻尚无成熟模式,新闻业的未来也尚不确定,但是,十年转型轨迹依然可以体现新闻业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发展演化的某种趋势和特征。
人们常用技术决定论的态度来看待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技术发展具有自主性,不受人类需求的控制。①波兹曼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分为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并认为在当前的技术垄断阶段,“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的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②不过,大约自上世纪80年代始,技术决定论受到广泛批评。技术史研究者发现,技术虽然不是可用可不用的纯粹工具,但也不能决定生活方式、价值制度等社会诸多方面。③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越来越多的科技史研究者认为,科学事实和技术产品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④技术产品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共同塑造了特定技术的共享框架。⑤
就互联网传播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美国学界和业界最初的反应都体现出某种技术决定论的悲观。曾有学者对《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2008-2010年有关报业危机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媒体严重夸大了报业危机程度,并给公众制造了报业将要消亡的印象。⑥学界对新闻业危机虽有更为多元的考察,但在骤然升级的经济压力面前,也难免产生悲观情绪,这从一系列著作的标题可见其一斑,如《正在消失的报纸》、⑦《失去新闻》、⑧《最后一名记者将熄灯?》⑨等。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在新闻业变迁中只是一个“放大器和增速器”,“技术既不是变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可以完全复制的媒介,它是正在出现的影响到记者工作的各种趋势和发展的增压器”。⑩直到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认为“危机”深植于每个组织的内在结构中,是面向未来的基础,新闻业其实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存在于基于技术、社会、政治、经济、职业道德、法律环境的一系列选择中。[11]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认为,社会事实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结果,在互联网技术环境下,新闻业对自身的期许、文化环境、社会群体,乃至作为技术使用者和应用设计者的个体都参与到对于未来的塑造中。每一个因素的不同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想象力。因此,本文以社会和技术共构作为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基本假设,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基本框架,对美国新闻业近十年发展演变的经历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分析出行动者要素,以及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借以拓展中国新闻业在面对危机时刻的想象空间。
一、共构理论与社会-技术共构
1.共构理论与媒介技术研究
共构(co-construction)理论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传统。其一是语言学研究,认为所有语言活动和现象皆是参与者共同构建的结果。“共构存在于一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上的社会互动的建构和阐释中”,作为一种隐晦的创造性的合作活动,是“一种关于形式、阐释、立场、活动、动作、认同、制度、技能、意识形态、情绪或其他具有文化意义的现实的联合创造”。[12]其二是科学技术史研究,特别是采取相对主义立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研究。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科学知识与其被看成对纯粹事实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有一定限制的意义、信念和活动”。[13]如此,传统上被视为真实、公正,没有曲解和偏见的科学知识也丧失其确定的特殊地位,成为需要依赖一定情境背景来进行分析的社会事实,是随机的社会阐释的结果。稍后,激进的技术史研究者认为,科学知识和其技术应用之间并非确定对应的关系,一些成功的技术应用的科学理论基础往往是错误或部分错误的,这说明技术和科学一样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14]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并没有将“共构”列入其核心概念,但“共构”是潜隐于其关于技术史叙事中的核心理解。Bijker认为:“技术产品或技术系统的涵义并不存在于技术本身,必须要研究技术是怎样在异质的社会互动环境中被塑造和获得其涵义的。”Bijker提出“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一词,认为“社会不是由技术决定的,技术也不是由社会决定的,两者都是在人造物(artifacts)、社会事实(facts)和相关社会群体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技术硬币的两面”。[15]将上述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参照,能为理解技术发展带来新的启发。实际上,技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取向即是将技术视作文本,强调技术文本的阐释灵活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16]语言学的共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构成对技术发展的隐喻,技术和语言一样,既不能脱离使用者而独立存在,其意义也不是预存在某种固定结构中,而总是在使用中被建构出来。语言的意义阐释在社会互动中实现,技术的内涵和影响也同样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呈现。值得关注的是用怎样的方式和机制来进行社会互动和意义阐释。
新闻传播学上对于技术的关注相对来说更多受技术决定论影响,大多数时候技术被视为一个有巨大权力的独立影响因素。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如Ornebring所说,技术在新闻业日常工作中具有很高的整合性,一个新的内容管理系统被引进新闻编辑室,新闻人的工作习惯和管理制度都不得不因之而改变,这种直观的感受很容易造成技术决定的印象。[17]另一个原因则是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技术决定论的进步乐观主义倾向,凯瑞(Carey)将其称为“电子乌托邦理想”和“电子至上论”。[18]不少新闻传播学者在关注互联网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时,虽然抛弃了乐观主义,但仍然有意无意地保留了决定论立场,认为电脑和软件的使用需要记者有更熟练的技术能力,从而导致媒介生产中的新的依赖性,这有可能损害记者的自主性,给编辑以更大的权力。[19]即使凯瑞本人在考察电报技术对新闻业乃至全社会的影响时,也采取了决定论的态度,认为“电报改变了书面语言的性质,最后改变了意识本身的性质”,“电报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带来了信息的选择性控制与传递”。[20]本世纪以来,更多传播学者注意到技术影响的复杂性。Ornebring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对新闻史进行考察,认为新闻业虽然被技术形塑,但是“技术并非一种自足的力量,它总是根据植根于文化、社会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存价值系统进行调整和补充”。[21]欧洲学者Fickers的媒介史研究深受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影响,他梳理了从电报、无线电广播、电视到直播技术的社会接受脉络,认为技术作为非中立的“行动者(actant)”形塑了特定的叙事方式,也影响到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但不能决定我们的体验及与世界的互动,“技术及其使用者在共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协商信息流动的方式和意义”,“我们应在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纬度中来阐释技术及其实践的角色、功能和影响”。[22]2.本文思路
建构主义的技术社会学研究内部主要有三个流派:系统论研究、行动者网络研究(ANT)和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SCOT),[23]每个流派都形成一些有特色的分析角度和概念范畴,其共同点则在于都十分重视从历史和社会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技术是怎样在社会互动的环境中被塑造和获得其涵义的。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框架,同时结合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和语言学共构研究的一些概念范畴,来分析美国新闻业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在互联网传播技术冲击下的发展历程。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由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针对传统的解释性社会学观念而提出。传统社会学划定了一种稳定的事件状态和一系列关系,各种社会现象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拉图尔认为,社会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或领域,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基本原则,社会规则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所有异质的因素都可以在特定的事态中被重新组合起来,每当一种新事物(疫苗、工作、政治运动、星系发现、灾难等)出现,之前的社会定义失效,“我们就必须对那些原先联结在一起的观念进行重新洗牌”。“在科学实践中,所有行动者共同产生作用,发生联系形成网络。沿着各种联系,每一个行动者通过相连的其他行动者而获得意义”。[24]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特别价值主要在于:1.充分强调了物(非人)的能动性,物不再是不参与意义过程的简单的承载工具,而是有可能修改、扭曲、转变意义的翻译者;2.行动者的意义不是结构性先在的,只有在与其他行动者联结时才获得,且联结随时在重新组合。
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SCOT)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和技术相互形塑的双向过程,[25]相对来说将技术和人的因素进行了区分,以技术和技术使用为核心发展出一系列概念来分析社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从技术对行动者以及行动者关系进行限定的角度主要涉及两个概念:设定(configuring)和脚本(script)。所谓“设定”指技术设计者“定义推定用户的身份,并对他们可能的未来行为设置约束的过程”。[26]所谓“脚本”指技术创新者和设计者对技术客体与其相关行动者关系的技术实现。就像电影剧本限定了演员的表演一样,技术脚本预定了行动者的动作框架和活动空间,但潜在使用者也可能拒绝设计者的设计,所以,两者也会进行协商沟通从而确定技术形式。[27]可以看出,技术背后真正的行动者仍然是人,是技术产品的创新者和技术企业的各类相关人群。
从使用者的角度,SCOT研究提出使用者常常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来使用新技术,因此技术产品并不能自我说明,而是需要被阐释,技术产品因为相关社会群体的接纳而有用。最初,不同社会群体会用不同方式来阐释技术产品的意义,也就是技术具有“阐释灵活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但是,当某个社会群体所赋予的意义和使用方式在所有相关群体中获得主导性的地位后,技术的“阐释灵活性”关闭(closure)。[28] “相关社会群体”包括机构、组织、有组织或无组织的人群,“一个社会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共享同一套意义,跟同一个产品有关”,界定相关群体的关键在于,看技术产品对该群体是否有意义,“使用者”固然是相关社会群体,“反对使用者”也是。[29]综合起来,设计者和使用者共同塑造了技术框架,他们其实都是技术产品的“相关社会群体”。
语言学共构理论强调特定的“互动时刻”(interactional moment)的重要性,“每一个互动时刻都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将对后续的互动做进一步的反应”。“互动时刻”是形成共构的重要场景,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实时、同速响应互动时刻的丰富信息流;也是当下时刻和历史文化情境的交汇点,既对当下的互动作出响应,又是个人和集体在既往时间里所经验到的历史对话和互动的复杂产物。互动时刻挑战现存的社会规则,并且在对话者之间进行社会规则的再生产和再设定。[30]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互联网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是一个社会和技术共构的过程,互联网传播技术特征并不能单方面决定新闻报道的业务特征或新闻业的未来走向,各相关社会群体和个体作为行动者,彼此联结、互动,协商沟通,共同塑造了互联网传播技术本身及其应用特征,并最终塑造了新闻业的未来。在这个前提之下,在传统新闻业转型这个场域之中,有待厘清的问题是:1.在行动者这个范畴里,有哪些显在的和潜在的相关社会群体,或者说有哪些可能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之间是怎样联结和互动的?由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当下时刻的互动,还会卷入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因素,那么是怎样的因素参与到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并塑造了互动结果?2.就技术文本的“设定”和“解读”而言,互联网传播技术及其应用设定了怎样的新闻传播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是怎样被相关社会群体解读和使用,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解读?3.既往的技术社会学研究虽然高度关注互动关系,但是并没有重点聚焦于“互动时刻”,那么语言学共构研究中的“互动时刻”在传统新闻业转型的场域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会是怎样的因素,这个特定时刻对行动者及其互动的影响是什么?
本文截取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迄今的十年时间段,观察美国传统新闻业在互联网传播技术冲击下的转型发展状况,[31]将从社会对技术驯化的行动者网络、知识分子对新技术的诠释,以及学术界对技术文本设定的解读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与技术共构的过程,总结在美国传统新闻业转型这个场域中的行动者要素及其互动关系,以及其对新闻业现状和未来的塑造,并对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框架应用于新技术影响下的新闻业转型场域进行反思。
二、社会信念塑造下的行动者网络
2008年金融危机及紧随而来的报纸破产、媒介机构裁员的消息,媒体各种关于新闻业危机处境的报道,以及调研机构所发布的关于新闻报道品质退化的报告,引发了全社会对于新闻业境况的极大关注和担忧。支持这个关注的背后是传统新闻业所代表的专业价值体系与民主社会之间的关联,“没有新闻业的世界并非没有政治信息,而是将追求自身利益的宣传包装成为新闻,其中一些是惊人的诡辩,一些是尚武的言论,但是绝大部分价值可疑,这个环境将催生出犬儒主义、无知冷漠和道德败坏”。[32]传统新闻作为一种“公有物”(public goods),从政治的角度,它使公众能够监督政府和其他机构为其行为负责,从而使社会能够良性运转,[33]而互联网新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公民新闻”并不能担当此任,因为新闻系统要能发挥作用,需要一批全职工作的记者来报道社区、国家和世界,还要有严格的事实核查制度和专业的新闻机构。[34]因此,许多学者、媒介人士,乃至政府官员都呼吁,新闻业危机需要社会干预。
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和公共利益,传统新闻业的命运不能听任自然主义的技术发展的结果,应该说,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愿景和假想,因为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传统新闻业和民主社会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但是,这并不影响传统新闻业的公共价值成为一种社会信念,因为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巴恩斯所言,“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制度化的信念体系虽然近乎“幻觉”或“梦想”,但它“默认了实在和对人性的制约作用”。[35]文化范畴有着建构事实的作用,美国新闻业的十年危机和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信念前提下,各类行动者各自行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普通技术在社会接受过程的特征,也体现出自身特色。
从相关社会群体的角度来看,新闻场域中的新技术变革激发了三个圈层的行动者。第一圈层是新技术和新闻业的直接相关群体,包括传统新闻机构、新技术研发和应用企业、新闻机构和新技术的使用者。第二圈层是与新闻业有各种关联的机构和人群,主要包括公益机构、大学新闻系和具有积极行动力的个人(如慈善家、记者、编辑、议员、政府官员等)。第三圈层是传统上来说与新闻业和新技术变革并无特别关联,但是在本次新闻业危机中被调动而活跃起来的机构和群体,包括学术群体、民调机构和政府机构。三个圈层的行动者构成一个复杂多元的行动网络。
总体上,第一圈层行动者的表现与其他技术革新场景中的行动者表现并没有太大差异。传统新闻机构吸纳新技术推出网上新闻、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合作;新技术研发和应用不断整合使用者的反馈和互联网的互动分享的文化基因而推陈出新;使用者通过对新技术应用的创造性使用而体现“阐释灵活性”。行动者的各自行动也在彼此之间产生作用,如使用者的阐释灵活性改变和促进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功能,并对传统新闻机构形成挑战,传统新闻机构应对受众流失和商业模式的危机等。如果行动者仅限于此圈层,那么,在使用者的阐释灵活性关闭,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功能稳定后的场景则是:新技术应用取得优势社会地位,传统新闻业消失或转向其他利基市场。但是,对传统新闻业的社会信念激活了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的行动者,改变了行动者网络状况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使美国新闻场域的社会和技术共构体现了一些新鲜的特征。
1.互动时刻:社会共识的动员和达成
“互动时刻”是语言学共构理论提出的概念,强调即时互动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创造力和重塑社会规则的能力。在美国新技术与新闻业的场域中,因为传统新闻业的紧急危机状态,叠加美国社会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的普遍信念,十分反常地激发了各类行动者的密集行动和话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形成蔚然可观的社会现象,本文借用语言学概念将此亦称为“互动时刻”。
2009年“互动时刻”以年初接连的报纸停刊和申请破产保护事件为起始。2月27日有着150年历史的《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关闭,3月17日《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关闭,此外还有著名地区性大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申请破产保护。调查型报道项目受经济威胁而停止运转,媒体没有足够的人手报道政府,以致有记者声称,未来的10到15年将是地方腐败和腐败官员的好时光。[36]在美国学术界和业界都有重要影响力的皮尤媒体年度报告将此称为“危险的接近自由落体的状态”。[37]这种状况引起了新闻学术界的极大担忧,知名学者在精英报刊撰文分析新闻业危机,探求化解危机的可能路径,[38]或者直接呼吁政府补贴作为公共服务的新闻业。[39]媒体自身对于新闻业危机的报道也是不遗余力。2009年3月4日,著名的精英杂志《新共和》推出一组有关“报业危机”的封面专题报道,主报道的标题触目惊心《报业终结:民主失去最好的朋友》(The end of the press: democracy loses its best friends)。《落基山新闻》终刊的消息登上美国各大主流报纸的头版,《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落基山新闻谢幕,也带走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可以反映媒体对报业衰落的普遍心态。[40]尽管2010年的皮尤媒体年度报告认为,2009年并没有出现报纸倒闭潮,全年只有6家报纸停刊或缩刊,且大多数是所在城市的第二份报纸,[41]但是2009年的媒体报道、学者撰文和各种来源的统计数据报告已经将“报业危机”建构成为重要而紧急的公共话题,并推动了立法机构、政府决策机构和政府要员的关注。
2009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小组委员会”举行主题为“未来新闻业”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参议员John Kerry表示,“美国人民怎样获取信息,跟我们所有人都紧密相关,因为这是民主的基础,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新闻业是第四种权力或曰政府的第四部门这个观念,那么我们需要审视数字信息时代里新闻业的未来,及其对共和制和对民主的涵义”。[42]资深媒体人David Simon在听证会上批评了短视的华尔街资本逻辑和媒体人自身的虚荣对新闻业的伤害,但他同样强调了公民新闻不能替代训练有素的专业报道,同时呼吁政府要采取税收激励措施来发展新闻的非营利组织,国会应考虑放宽针对报业的某些反垄断禁令。[43]这次听证会在政府政策立法上没有取得进展,当立法者询问线上新闻是否可以提供深度报道和解释时,报纸发行人认为不可以;当问及非营利机构能否填补空缺时,基金经理说不可以,但是各方达成的共识是,必须以某种形式来保存深度报道和提供高品质的新闻。[44]同年5月,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启动项目研究互联网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挑战。一年后,项目组提出草案描述了报业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状况,以及当前新闻业的各种创新实验。由于新闻业发展趋向不明朗,草案认为政府当下应采取“观望”的态度,因为很难确认各种政策的短期、长期和非预期效果。[45]2009年9月,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也举行听证会,主题是“未来报纸:对经济和民主的影响”,不过,对于政府是否需要启动对报业的紧急援助,听证会同样充满争议。[46]听证会只是再次确认了报业危机状况和挽救传统新闻价值的意义。
总体而言,2009年“互动时刻”虽然没有在政策层面产生直接影响,但还是形成了一些大体一致的结论,即新闻业未来可能不会产生新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需要创新和探索新的收入方式,如订阅、基金和慈善捐助、提供其他类型服务等。听证会和调研报告也深入探讨了政府通过版权、税收、反垄断和直接资助等各种干预方法的利弊,以及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可能状况。这些材料、数据和分析影响了美国社会的认知,并在政府干预之外推动了潜在的行动者。
2.积极行动者的创造性
这里使用“积极行动者”一词主要是用以区分行动者在社会信念影响下的行为与自然主义的行为之间的差别。在技术创新的场景中,普通行动者通常是新技术的使用者,尽管使用者也可以通过“阐释灵活性”来创造性“使用”,但是“积极行动者”则是超越使用者身份而参与到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规则设定和重塑,进而改变技术发展的自然主义进程。在美国新闻业场域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积极行动者,因为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抱有强烈的信念,而采取积极行动来挽救濒临险境的媒体或资助创设新的替代性媒体,他们从不同角度塑造了美国新闻业的现状。
在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场域中,面对新技术压力,传统新闻业持续探索新的生存发展模式,且迄今并无成功,因此,这个场域中没有英雄式的创造性叙事,而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因为强烈的社会信念而成为新闻场域中的积极行动者。依照社会身份,这些积极行动者大概有五个群体:记者编辑、慈善基金、政府官员、专业机构和学术机构、身份莫辨的一般公众。
传统新闻从业者是新闻业危机的直接感受者,也是新闻业寻求变革和实验新路径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同时因为谙熟新闻采写制作和推广的路径,也是新技术的富有创造性的使用者。本文将忽略新闻从业者在制度规范内的职业创新行为,如设立付费墙、发展原生广告等,也忽略其对新技术的创造性使用,如创办新闻博客网站等,本文关注的是在新闻业危机时刻以传统新闻价值体系为依归的新闻从业者的行动,特别是一线记者和编辑为保存传统新闻价值所作的努力。
几乎在每一个濒危报纸的背后都有一些记者编辑个体化努力的故事,有些在各种因素的支持下取得成功,更多的努力只能维持较短时间,但是不论成败,这些行动汇聚成一股力量塑造着美国新闻业的转型面貌。McChesney & Nichols讲述了美国中西部大报《托莱多刀锋报》(The Toledo Blade)记者凯特的经历,堪称此种新闻从业者行动的一个典型。[47]凯特是刀锋报一名优秀的深度调查报道记者,2008年9月在报业危机中被裁员,因为想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顺从历史”,2009年初她和同时被裁员的另一位同事一起创办网站“rustwire.com”,致力于报道“锈带城市”(Rust Belt cities)的经济和创新问题,其专业性和生动性一度超过大多数报纸网站,但是终因不能创造足够的收入而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凯特所代表的新闻精神并未熄灭,它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许多主流媒体从业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追求。
一些得到创业投资或慈善捐助的由记者编辑创建和维持的新闻网站较长期地存在,甚至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影响力。这当中最有名的是致力于调查性报道并曾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ProPublica。该网站创办于2008年,因得到慈善家桑德勒夫妇每年1000万美元的多年资助承诺而启动,后来又得到其他公益基金资助。[48]自报业危机以来,慈善资金对新闻业的扶持力度也增加。2010年度皮尤媒体报告称,自2005年以来,美国有1.41亿美元的公益资金用以资助除公共广播之外的新媒体事业发展。2013年皮尤调查发现,全美除了9个州以外,其他州至少有一家非营利的新闻机构,大多数是在专业的新闻领域工作,21%聚焦于调查性报道,17%侧重于政府报道。[49]对于慈善捐助和公益基金能否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维持高品质的新闻报道,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一是基金资助的可持续性问题,不少基金只是资助创业机构,且维持的时间有限,因此,受资助的新闻机构仍然必须找到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二是基金资助的偏向性问题,不少基金资助某一方面问题的报道,带来新闻报道的不平衡,并有可能带来新闻报道的党派偏向性。[50]另外,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基金会本身的权力控制问题,基金会通过会议、讨论和建议对其资助的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基金会的利益倾向和新闻事业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具批判性的思考,社会需要对慈善基金有更多的警惕。[51]但是在危机中,非营利新闻机构填补了一些主流媒体留下的新闻空缺,目前一些主流大报也在发展非营利部门以支持特殊领域报道,如《纽约时报》在2017年9月宣布建立非营利部门来支持其地方新闻报道,[52]非营利新闻机构已经成为维系美国传统新闻价值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官员因倡议立法或组织专题听证会而成为报业危机中的积极行动者,尽管因美国传统上对政府介入媒体的任何举动都有高度的警惕,这些立法倡议和听证会讨论最后都没有真正形成公共救助方案,但是这些活动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报业危机的关注,如参议员Benjamin Cardin在2009年3月提出的《报纸复兴法案》(The Newspaper Revitalization Act),建议给予报业非营利机构地位以减轻其经济负担,激发政府、学界和业界的深入讨论。[53]政府官员的行动也微妙地和其他行动者形成互动,并影响到整个行动者网络。例如,2011年在纽约召开的一个由基金发起人出席的会议宣称,由于缺少商业和政府支持,基金将要承担起为新闻业危机寻找解决方案的重要公民责任。[54]某种程度上,公益基金的这种态度和自我意识可以看作是对其他行动者的回应。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政府官员是作为普通的媒体使用者因个人体验而成为积极行动者,如麻省参议员John Kerry发起参议院关于“未来新闻业”听证会,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有感于家乡大报《波士顿环球报》面临倒闭的威胁。[55]大学新闻系和一些专业机构也是报业危机中的积极行动者。大学新闻系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学生优势在所在的州、城市和社区报道上发挥作用。一些大学新闻系师生所办的报纸电视和网站成为当地的重要媒体,密苏里新闻学院在此方面有悠久传统,现在创办媒体在其他大学新闻系也蔚然成风,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纽约社区的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对旧金山社区的报道。一些大学和非营利调查性新闻机构合作,在地方传统媒体遭遇危机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地方新闻的空缺,如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看门狗研究所”(The Watchdog Institute)、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的“威斯康星调查新闻中心”等。[56]奈特基金会、波因特(Poynter)新闻研究院、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等也都是积极行动者,每年发布报告调查新闻业现状和探求解决方案,影响到公众认知和行动。
一般民众是不易被察知的积极行动者,在美国新闻场域中,有两个细节可以说明其作为积极行动者的存在。其一是对新兴数字化非营利新闻机构的小额捐款。据奈特基金会2015年发布的对20个地方性数字新闻机构的调查,个人捐款和会员费占这些机构收入约20%,在2012至2013年间,所有机构的个人捐助者数量增加了18%,捐款数额增加了近一倍,而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小额捐款驱动的,2013年所有捐款中97%的数额低于1000美元。[57]其二是因特朗普总统竞选带来的所谓“特朗普突起”(Trump Bump)现象。从2016年第四季度起到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多家精英日报订阅量和网页浏览量骤增,特别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家有线电视(CNN、FOX、MSNBC)收视率也同期剧增。[58]路透研究院在2017年2月的调查中发现,“特朗普突起”中全美数字付费订阅量从9%增加至16%,对新闻业的捐款增加三倍,增长主要来自左翼人士和年轻人;在问卷调查中,29%的美国人声称其为新闻付费的主要原因在于“想要资助新闻业”。[59]从这两个现象中可知,尽管公众习惯免费的互联网内容,但是美国一般民众对传统新闻价值有较高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驱使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资助和支持新闻业。
迄今,美国传统新闻业仍在困境之中,但是积极行动者仍然深刻塑造了美国新闻业的现状。这集中体现在两点:首先是非营利新闻机构的发展。自2008年以来美国非营利新闻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带动了美国新闻体系多元化的发展,[60]并形成新的媒体生态环境。[61]2009年20家非营利新闻机构联合建立“调查新闻网络”(INN),到2013年其成员即增加到80多家,这些团体致力于“重建社区信任”,通过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来“重新联结市民”,试图在信息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中来建立一种新的互相理解的“记者-受众”关系。[62]其次是美国新闻业在重重危机中仍然通过各种办法维持甚或发展了报道规模和影响力。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2016年报纸全行业广告收入180亿美元,而发行订阅收入110亿美元,发行收入的增长使一些出版商开始追求“发行第一”的发展模式。[63]许多地方性大报遭遇了比全国性媒体更为严峻的危机,也更集中展现了在数字技术冲击下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种因素互动对新闻业的重塑。《费城问询报》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家诞生于1829年的报纸是美国第三古老的报纸,也是20个普利策新闻奖的得主,和同在费城的《每日新闻》、Philly.com网站一起每月有800多万读者。[64]在经济危机中,《费城问询报》和另外两家媒体几度裁员和转让所有权,最终在2009年2月申请破产重组,管理层欲保留资产控制权未果,2010年下半年,这组费城最重要的新闻资产终为银行和对冲基金所有。“在工业时代看似坚固的机构在互联网的数字海啸下冰消雪化”,不过,数字技术给了市民“成为媒介”的机会,也给了报纸“线上再生”的机会。[65]2012年《费城问询报》因财务危机几近停刊,2014年费城慈善家Lenfest买下《费城问询报》等三家机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保存这一地区独立编辑的声音”,并于两年后将其捐赠给费城基金会所属的非营利的新媒体新闻研究院,《费城问询报》因而成为非营利新闻机构。[66]在这个个案中,慈善家个体、慈善基金、媒体研究机构和新闻公司“创造性合作”,共同塑造了费城新闻业的现状和未来。
三、挪用技术:公共话语的诠释
美国新闻场域的新技术转型还卷入大量的公共话语生产,这些话语界定新闻业危机,分析危机形成的原因和解决路径,呼吁公共政策和全社会的关注,划定新技术和传统新闻业之间的关系,对新技术和未来新闻业进行构想,松散而弥漫的话语整合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重新塑造了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影响了新闻业和技术本身的发展走向。本文将各种人士和社会机构关于技术及其影响的话语称为“挪用技术”(appropriating technology),“挪用技术”集中体现了社会的文化层面与科学技术的共构关系。
学者采用“挪用”(appropriation)概念来分析“非专业人士”对已经在社会中取得稳定地位的技术的“再阐释”(reinterpret)和“再创造”(reinvent)现象,认为“挪用”有可能带来糅合了本地知识的专业技术创新,而后进入再一轮的挪用。“超越技术的假定功能而发现新的可能性所需要的创造力是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技术挪用映射了社会权力的流动,有可能遭到政府或技术企业的抑制,但也“开启了文化和科学关系的新的可能性”。[67]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场域中主要的话语生产者有三类,一是传统主流媒体(主要是报纸)所发布的各种媒介危机讯息,在提供动态的同时也提供相关背景材料和分析;二是新闻传播相关学者、作家、评论员所发表的分析评论以及所出版的著作研究,通常有对新闻业危机分析、历史脉络的阐述,以及化解危机的策略建议;三是非营利研究机构(智库)和民调机构,通常是发布调查报告,分析统计数据,提供对于趋势的预测和判断。
传统主流媒体主要提供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话语。据学者研究,2008-2010年间报纸关于报业危机的报道基调整体而言是负面的,超过四分之一的报道都包含一些“死亡”意象,报道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历史视角和全球报业状况,主要关注媒体经济数据的短期大幅度下滑,因此实际上是夸大报业危机的规模。[68]由于记者对报业衰退亲身感受的情感因素,以及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深受记者个人风格影响,报业危机报道的偏向性十分明显,但是这些报道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新闻业危机的认知,在2010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中,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传统媒体将在十年内消失。[69]实际上,一般评论和学者著述中关于报业危机的描述,大多也以报纸缩版停刊裁员、报业公司申请破产的案例作为主要依据,若干大报破产和停刊的信息被反复引用。[70]可见媒体关于报业危机的话语影响甚深。
媒体通常将报业危机简单归因于广告流失和读者迁移,也就是归因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71]新闻传播学者梳理历史的路径在这里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文化从根本上制造了新闻业危机。这种观点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奉为新闻业的“黄金时代”,认为在随后的垄断商业文化中,新闻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惜牺牲新闻报道的专业品质,公众对新闻业的信心下降,独立新闻业长期以来处于衰落中。[7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传统新闻业体系。美国报业曾经长期依赖政治补贴,只是在上世纪因为广告的交叉补贴而成为高利润行业,进而能够服务公共利益,互联网消解了报业的商业模式,却不能承担起报业的社会功能。美国历史上主要城市的报纸不仅是新闻生产的中心,而且是大都市人们的生活重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趋近的不是报纸的终结,而是报纸时代的终结”。[73]但是不论哪种归因,学者们一致认同的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对传统新闻业商业模式的颠覆是不可逆转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报纸这种形式或可放弃,但是报纸所代表的自由独立、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不可或缺,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方式来“重建新闻业”。[74]至于如何重建,普林斯顿大学的斯塔尔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唐尼等分别在《新共和》杂志和《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上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斯塔尔认为新闻业作为“公有物”(public goods),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补贴都会带来政治操控的风险,将新闻业转为非营利机构和慈善基金的支持虽可以促进发展公共服务的新闻,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并不可与传统的新闻力量相提并论。[75]唐尼等为重建新闻业提供了六条建议,认为政府、新闻界、慈善事业、高等教育和社会其他领域各种力量进行创造性合作,“才能确保独立新闻报道的未来”。[76]事实上,这样的话语是将重建新闻业的责任置于每一个社会机构和个体肩上。
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除了慈善基金以更大的力度投入对新闻业的经济支持外,互联网技术公司和新闻聚合引擎也被迫直接或间接投入到对传统新闻事业的支持中,“否则将没有新闻可供售卖、聚合、广告、分析或讽刺”。[77]2015年,有140亿用户的Facebook和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数家新闻媒体商谈合作,希望能直接呈现新闻内容,而不是仅仅向用户提供导向各媒体网站的链接,为此Facebook将向各媒体支付不菲的广告费。[78]另外,互联网技术企业还通过成立公益基金来发展传统新闻事业。《赫芬顿邮报》2009年与非营利调查报道机构“美国新闻计划”(American News Project)合作,建立“赫芬顿邮报调查报道基金”,聘请前《华盛顿邮报》知名调查记者为主编,聘有12名调查记者,以独立和非党派立场从事全国性主题报道,内容提供给《赫芬顿邮报》和其他新闻媒体。[79]2017年3月在线分类广告公司Craigslist设立的基金会向非营利新闻机构Pro Publica捐赠100万美元,公司创始人称,“值得信赖的媒体是民主的免疫系统”,自己有责任支持新闻工作,该基金会还在2016年捐款数百万美元资助媒体相关组织。[80]数量众多的非营利研究机构也构成新闻转型场域中非常重要的话语资源。这类机构一般依托慈善基金或大学部门而建立,定期或不定期发布各种研究报告,提供对新闻业发展现状、数字媒体发展状况的调查和分析,以及未来发展战略建议等。一些机构的年度报告已经成为全社会判断新闻业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如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发布的“美国媒体发展状况报告”。路透研究院从2012年开始每年发布“数字新闻报告”,调查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媒体发展状况,影响力也渐增。其他重要机构有波因特研究院、奈特基金会,以及依托大学部门建立的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的“创业新闻中心”等。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一直是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它既非完全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其研究是一种话语工具,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一个看似不带偏见的方式,使他们对于未来的愿景成为现实”。[81]就皮尤研究中心媒体年度报告和路透研究院的多项报告而言,除了对媒体发展现状的统计描述外,其高度关注的现象和议题在于:1.新出现的商业模式,如非营利新闻、众筹新闻、受众为新闻付费的意愿等;2.公众对当前新闻报道的信心状况,以及媒体业者对未来新闻业的信心;3.新闻报道质量和受众接收的相关议题,如路透研究院多年专题调查新闻报道的客观性问题,以及受众对传统新闻业的态度;4.传统新闻业和新技术的关系议题,在2008-2009年的悲观论调之后,近年对新技术的积极面有更多肯定,相关议题往往被涵盖在“创新”、“合作”的主题里。
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说,研究机构总是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出发,将某个特定的现象纳入考虑和进行解释,而研究报告则通过将世界秩序化来指导行动者在时间、金钱和行动上的投入。[82]在美国新闻场域中,可以看到非营利研究机构的关注点和现实行动者的行动之间的关联性。学者对2009-2016年间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发布的50多篇报告进行分析,[83]认为将技术变革与文化创新相结合的“创业乐观主义”(entrepreneurial optimism)是这些研究报告的基调,创新为变迁中的新闻业在商业哲学、编辑策略和新闻认同等方面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创新的初衷在于创造一个“真正的知情社区”,因此,创新领域应该面向无数参与者开放,倡议其以自己的干预来更好地服务于公众。这些研究报告也因为各种问题而遭到批评,如将创新目标窄化成“为了收入、技术进步和新闻质量”,导致以市场为导向的关于新闻业未来的愿景,忽视了数字媒体所固有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因目标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而带来新闻生产与流通问题。但是,新闻业的价值追求有可能被忽视,却始终高踞于市场目标之上,并为追求新闻业的未来提供合法性。
四、技术文本设定的解读
荷兰学者Broersma & Peters曾将互联网新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概括为两点:信息生产的去工业化和新闻消费的去仪式化。[84]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带来复杂的后果,并进而影响到新闻业与民主社会的关系。从生产的角度,如同其他工业时代的生产逻辑,新闻业的初衷在于面向大量的受众(mass audience)提供大众化的产品(mass production),关注产品的标准化和建立起规模经济。在工业时代,新闻业因为垄断信息生产和流通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商品,也是丰富的知识来源,因此成为培养见多识广的公民并为民主社会提供动力的重要机构。新技术颠覆了新闻业在信息领域的垄断地位,使新闻业和新闻本身都面临基础性的变革,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商业模式、新闻生产过程、新闻实践规范及其社会功能。从消费的角度而言,看电视新闻和读报曾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仪式化的行为,而在新技术环境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各种方式来接触新闻,新闻消费的个人化和特殊化使新闻业一直以来的假想破灭,即公众有规律地接触新闻,熟悉各种议题,进而可以履行一个“好公民”的义务。现代技术增加了人们彼此连接的机会和可能性,但并不必然增加稳固的社会关系。相反,很多观察者认为,社会的凝聚度下降,公众日益分裂和碎片化,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社会连接与社会冲突和动乱紧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崛起的最重要的后果在于“自主性(autonomy)”的迁移,从公众稳定的媒介消费习惯转变为新闻业需要使自己习惯于弹性的时空。
本文将新技术的文本设定理解为新技术给新闻业的基本面带来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如新闻业的经济基础、专业性、内容生产等。那么,从上述关于新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来看,新技术文本设定的特征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新技术颠覆了传统新闻业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基础,制造了所谓的“新闻业危机”;2.新技术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实践规范并进而影响到其社会角色和功能;3.新技术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以及新闻业和受众的关系。学术界对这三个特征的解读则重新界定了新闻业的专业性及其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1.对新闻业信任危机的反思
尽管学术界对互联网技术导致传统新闻业商业模式的衰落没有争议,但是对新闻业危机的定义和归因却有多个层面。经济和技术压力之下的新闻体系基础结构的变迁被认为是本轮新闻业危机的起因,而危机则表现于三个不同的层面:经济危机,即新闻业的收入方式的变迁;专业危机,即新闻业划定自身边界并区分于其他的能力受到挑战;信任危机,即新闻与其声称所服务的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变迁。[85]在这三种危机中,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被整合进技术创新的话语中,相关研究致力于分析新闻业的收入新模式,并和积极行动者的行动互为呼应。专业危机关注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在新技术环境中的被偏离和被破坏,由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通常和更广义的民主话语紧密相关,因此,相关研究致力于整合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闻实践,并重新确认新闻专业的边界。信任危机是美国新闻业存在已久的问题,相关讨论时断时续,经济危机再度激活关于信任危机的讨论,并且信任危机被认为是加剧经济危机破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86]因此,学术界对新闻业危机的讨论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对信任危机的反思和话语建构。
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美国新闻业信任危机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只是以往被新闻业良好的经济效益所遮盖。根据盖洛普调查数据,1990年美国人对报纸“很信任”的比率为39%,1993年报纸信任度为31%,电视新闻为46%,而到2008年这两个数据均下跌为24%。[87]导致信任度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媒介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新闻品质下降,新闻业对公关宣传材料的接纳也是原因之一。上世纪90年代是报业利润丰厚的年代,统计数据却表明在1992-2002年间,广播和报纸编辑部工作岗位减少了6000个,2001年的一项研究认为,报纸日益成为广告主和金融市场的代言人。[88]面对新闻质量下降及其所带来的信任危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新闻作为公有物不再能够通过商业化的方式来获取”,因此需要公共补贴和开明政策的支持。[89]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高质量的报道带来受众信任,进而带来媒体影响力和可持续的盈利,因此,信任危机和受众下滑会倒逼媒介所有者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报道是挽救新闻业颓势的路径。[90]历史学者则通过对美国近代新闻史的考察认为,当前美国新闻业危机是半个世纪前新闻业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工人阶级受众的结果。在讨论新闻系统巨变时,人们假设大众从传统新闻媒介迁移到互联网,但实际上大众(尤其是其中工人阶级部分)并没有迁移到其他新闻来源,而仅仅是在被传统媒介抛弃之后也失去了对新闻的兴趣而已。“这是一个巨大的未被开发的新闻市场”,在包括通讯公司在内的所有行业都设法从穷人身上赚钱时,拯救新闻业危机的路径是重新获得工人阶级受众。[91]由于传统中对政府介入的高度不信任,因此,综合起来,面对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业信任危机,学术界解读和反思的结果是新闻业需要提供高品质的新闻和关注报道普通大众议题及利益以重新赢得工人阶级的接纳。但是,怎样才是高品质的新闻,它跟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标准关系如何?重新赢得工人阶级的具体涵义和路径是什么?前者与新技术环境中对新闻基本规范的再确认息息相关,后者则需要与新技术环境中新闻业与受众关系的重构一同考虑。
2.对新闻专业基本规范的再确认
新闻专业主义有漫长的历史,但仅仅到上世纪60年代因为传播渠道稀缺与公众问责制兴起的偶然巧合而成为新闻业规范。[92]尽管历史学者认为新闻业“看门狗”的作用被高估,专业主义的一组信念仍然被认为维系着独立的公共领域。新闻业被认为有独立的文化权力(cultural power),专业危机也就意味着文化层面的重新建构,而正确的理论话语将“为经验研究设定不同的研究框架”,使“当前危机的因果情况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而正在进行的组织修复也将得到应有的重视”,[93]因此,整合新技术变革而确认新闻专业边界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议题。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业出现媒体分化现象以来,[94]学术界开始对新闻专业性、新闻业社会功能、与民主社会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一些学者认为,六七十年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当时所谓“高现代主义”的政治、经济环境所成就,随着政治共识的崩溃和经济竞争的加剧,记者角色和新闻报道的特征已然改变,记者应该放弃其作为政治权威和普通大众的中介人角色的观念,回归“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95]更为激进的观点则认为,记者工作并不具有专业性,记者通过非正式社交网络协商、讨论形成“阐释性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通过共享阐释而建立不被传统新闻观所重视的实践权威”。[96]不过,总体而言,学术界在新闻业对民主和公民参与(civil engagement)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存有共识。[97]不确定的是怎样从理论上整合新技术变革和解读变化的传播环境。
首先是新技术传播对客观性规范的冲击。客观性被视为美国式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规范之一,作为一套具体的惯例习俗,它是新闻业建立大众信任和避免报道主观性指责的工具。[98]互联网的出现使公共空间充满各种“用户生产”的普通人的个人性情感故事,一些主流日报也开始刊登此类私人情感经历,并不惜付费获得独家报道权,著名的精英报纸聘请个人风格鲜明的记者和评论员。[99]这种基于个人经历和观点的情绪化的表达,通常被新闻业视为对公共领域理想的“偏离”(deviance),并被贬低为”小报风格”(tabloidisation)但是“技术变迁不仅影响了记者和受众关于新闻价值的观念,而且影响了新闻职业及其实践和认识论”,一些媒介学者开始关注和承认情绪在公共话语中的位置,将这种表达“个人声音”的新闻称为“主观新闻学”(subjective journalism),认为这是记者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在冲突和灾难事件报道中通过对受难故事的富有同情心的报道可以促进世界团结(cosmopolitan solidarity)。[100]新闻的客观性理想代表的是一种精英专家式的“知识论”,认为“新闻媒体应当给公民提供公正而全面的信息”,“提供条理分明的框架来帮助公民理解复杂的政治世界”,这样公民才能作出合理的决定。尽管心理学、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并没有客观的知识,可能也没有理性、明智而见多识广的公众,但是民主的目标仍然是对新闻实践“极好的指导”,新闻媒体需要“精神分裂”,“把古典主义民主作为触手可及的东西,同时要抱着大量见多识广的、热忱参与的选民不可能存在的态度工作”。[101]因此,面对新技术给新闻传播范式和认识论带来的挑战,学者们承认情绪话语的公共价值,其实是对被渗透和侵蚀的专业边界的修补和重新划定,新闻专业技术的重要性仍然被高度强调,记者通过专业技术将受众提供的业余的粗糙的素材转变成真正可用的新闻内容。这种将公众的情绪话语与新闻的客观性理想进行并置(juxtaposition)的处理,是对新闻工作专业性和客观性的一种防卫,保护了记者作为“知识和真相生产者”的优先地位(privileged status)。[102]其次是对高品质新闻(quality journalism)的重新界定。“高品质新闻”一词经常被使用,但很少有清晰界定,大多数时候人们将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些规范要求套入使用。2005年Deuze整理多位学者的零散表述,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价值观概括为五点:公共服务、客观性、自主性、时效性、伦理性(指记者要有伦理感,注重报道有效性和合法性),[103]这大致可以代表传统上对高品质新闻的理解。互联网传播的发展挑战了记者在公共领域信息报道上的垄断性,“质量”成为区分专业记者工作和公民记者劳动并维护新闻专业边界的关键词。那么,记者的专业工作能为新闻报道添加怎样的价值?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得到各式各样的回答。
有学者认为,记者遵从个人良知,独立于消息来源,提供中立的信息使各方有可能折衷和解,这些专业主义规范“不仅创造新闻,而且贡献于道德话语,使社会团结成为可能”,“新闻是一项市民艺术”。[104]还有学者借用照相和绘画艺术之间的隐喻关系认为,当受众可以借助博客、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布和接收第一手的报道后,也就意味着一直保持写实主义(realism)的新闻业应该像其他科学艺术一样转向后现代主义,新闻的定义里不仅要有准确(exactitude)和精确(precise),还要包括“对新闻的解释和评论”,高品质的新闻在于要做“智慧新闻”(wisdom journalism),也就是“能增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新闻”。[105]另外,传统新闻报道所强调的“客观平衡”屡被公众和学者指责为不能真正提供有效的公共议题报道,两个著名的失败案例是伊拉克战争报道和气候变化政策讨论报道,[106]因此,有学者主张“公然有偏向的报道”(declaredly biased journalism)应该被视为没有道德争议的高质量报道,只是报道应该建立在严格缜密的消息来源和证据的基础上,还要进行严格的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107]在诸多界定和描述中,加拿大学者Shapiro所提出的一个包含五项基本业务能力的新闻质量评估框架值得一提。这个框架虽然比较复杂和多层次,但是相对整合进学者们关于新闻质量的多种意见,并充分考虑了互联网传播环境特征和实践状况。五项新闻业务能力分别为:发现(决定报道什么)、整理(规划表达结构)、风格(选择正确的词汇)、记忆(memorization)和传递(delivery)。在这五项能力的基础上,高质量新闻的标准是:独立、准确、开放评估(open to appraisal)、可编辑(edited)、未经审查(uncensored);最佳新闻的标准是:有抱负(ambitious)、无畏(undaunted)、情境化(contextual)、参与性(engaging)、原创性。[108]综合上述可见,互联网传播实践冲击到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专业传播和公民传播之间的界限,但是通过再解释和再限定,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价值仍然是确定和不可替代的,因为专业新闻不仅是信息,更是一种话语,提供解释和建立道德合法性。原创、客观、独立、公共服务等作为基本价值维护着新闻的专业性边界,同时互联网传播带来的受众参与因素也被整合进专业传播体系之中。
3.新闻业和受众关系的重构
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新技术传播带来的最重要变迁是用户参与内容生产和流通,在重大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中,用户借助社交平台传播的内容备受关注。在早期的极端化判断之后,学者通过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发现,公民记者通常要与主流媒体合作才能提高个人叙事的可见性(visibility),同时主流媒体内部结构也非单一固化,主流媒体和公民记者的相互依赖使新闻所描画的世界图景更趋复杂。[109]互联网使新闻传播权力再分配,但这种分配总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并非所有的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都能被赋权,互联网传播的互动参与给新社会运动和边缘群体提供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但主流媒体在大多数场景中仍是主要行动者。[110]社会激进分子(activist)借助社交媒体推动了主流媒体新闻实践的变革,传统上主要依赖精英消息来源的主流媒体在消息来源上变得更加多元和非精英化。[111]综合而言,实证研究显示,替代性新闻(alternative news)和公民新闻虽然值得关注,但主流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取代。
传统新闻业和社交平台参与式的公民传播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可能性:竞争、补充和整合。[112]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公民新闻在新闻价值、客观性、可信度等方面均存在缺失,因此不能替代传统新闻业。Zelizer认为,公众在新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促进更为民主和平等的新闻环境,以及公众对于多元化社区的认知,在最坏的情况下,则“给那些质量不佳的观点、议题和事件提供传播平台”,从长远来说,势必激发专业新闻的参与。[113]补充关系意味着专业新闻和公民传播作为不同的实体彼此影响,如专业新闻利用公民传播所提供的故事,公民传播借用专业新闻的话题等。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用户的参与性还表现在对传统新闻业产品的评论上,他们跟踪监督记者和新闻报道中的错误,交流新闻观看和阅读体验,这些评论和交流形成对媒体行为的监督和规范,相比于传统新闻业对新闻报道质量的自我规制(self- regulation),被称为“参与式媒介规制”,即“依赖群众的智慧来区分什么是好新闻什么是坏新闻”。[114]在传统新闻业屡有道德逾越的情况下,一些学者认为“参与式媒介规制”对媒介的自我规制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整合关系意味着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使用社交工具和其他互动参与的传播形式,鼓励受众参与和吸纳用户生产的内容,将新技术传播手段整合进主流的传播体系。
从实践来说,主流媒体对新技术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的整合使用一直在进行,只是这个过程并非传统媒体对互联网技术文化的完全接纳,也非简单的传统媒体对公民新闻实践的吸收,相反,它体现的是传统媒体自身的惯例规范、专业期许以及社会愿景与互联网技术文化互动交流的结果。学者Anderson对费城2009-2012年间媒体生态圈的观察生动展示了这个过程。[115]由公民中的积极分子所开设的博客和推出的新闻项目致力于社区参与,主要用于社群对话和信息综合等“文化实践”。而当传统媒体采纳这些公民参与性的传播方式后也一并将其带入媒体日常工作惯例,由专业记者撰写的博客更加强调原创性,通常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突发新闻的一部分;其多媒体项目也主要是刊登媒体报道,而很少有媒体外资源的链接。此种策略主要源于传统媒体对自身专业性的维护和对公民作为统一整体的想象,因为原创性被传统媒体视为建立自身专业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根据。
总体而言,学者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新闻报道基础范式的变迁,社交网络、移动媒体和数据新闻的发展合流使专业新闻报道从过去封闭的高度控制的模式转向更加开放、合作和公民参与的新闻报道模式。[116]在一些类型的新闻报道中,受众参与和社交媒体具有特别的价值,受众和主流新闻业的合作十分重要,如突发事件中普通公民对现场的报道,数据新闻中受众所添加的故事等。不过,互联网仍然是个等级社会,少数有影响者获得巨大关注,大多数写作者几乎不被注意,因此新闻业要“促进用户参与”,“给普通公民以被听见的机会”,“新闻业要成为公共话语的仲裁人”。[117]多年来的受众调查显示,社交媒体不可能对传统新闻业构成竞争关系,人们主要使用社交媒体娱乐、交流和培养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优先选择专业新闻,源于其对传统新闻品质的信心。因此,学者认为,将受众和传统新闻业置于平等合作的地位是不合适的,互联网动摇了传统新闻业的经济基础,但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用户参与的增加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中,专业媒介必须承担起更为重大的责任,不仅要生产新闻,还要承担起公共领域的导航和调节稳定的责任,要通过更高品质和更为独家的内容来赢得潜在受众的信任。[118]
五、结语
传统新闻业与健康的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是美国社会普遍的信念,这个信念激发了广泛的积极行动者,深刻影响了美国新闻业在互联网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转型过程。虽然有学术界和公众舆论的呼吁,并且美国政府机构几度介入调查研讨,但是根深蒂固的对于政府介入的警惕和被舒德森称为“民主商业社会”的特征使美国新闻业并没有走上公共补贴等政府干预路径。被强烈的社会信念所激发的积极行动者在深厚的慈善和公益基金传统的支持下,使非营利新闻机构的发展成为美国新闻业转型过程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现象,这是美国新闻业转型中的一个创新。
知识分子对新闻业危机的解读、阐释,以及民调机构、非营利研究机构的报告和调查数据相互援引和支撑,使“重建新闻业”和“知情社区”的目标成为美国新闻转型场域中最突出的话语符号,而这些话语动员了潜在的行动者,并使技术型企业和传统新闻业的挑战者也加入到重建新闻业和知情社区的努力中。尽管技术演变的走向和新闻业的未来形势均不明朗,知识分子和知识机构的话语所重申的新闻业核心价值规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从业者乃至社会公众对专业新闻和新闻业未来的信心。
学术界话语对美国新闻业的转型发展一直有深刻影响。面对互联网传播新技术的文本设定,学术界对新闻的专业性以及新闻业与受众的关系有一些激进的表达,比如“主观新闻学”的出现和对公民新闻影响的极端化评价等,但是现实境况的参差复杂给了学术界多元解读的空间,而关于新闻业对民主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性的认识则使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规范和新闻业所应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话语凸显出来。互联网技术的互动参与特征被整合进对新闻专业基本规范的再确认和对新闻业与受众关系的重构中,但是传统新闻业的社会功能和专业要求并没有因此被削弱,相反,新闻业要以高品质的报道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传播环境中担当起稳定和导航公共领域的责任,吸引鼓励受众参与和为社区服务成为新闻专业规范的新要素。
在一个创新社会中,传统规范解体,新技术似乎拥有决定性的权力,而拉图尔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包括技术在内的多元行动者的行动及其相互作用塑造了创新社会的面貌,流动的社会观破除了技术决定论的神话。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观察互联网新技术环境下传统新闻业的变迁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视角,使我们可以在社会与技术共构的视野里观察和设想新闻业的现状和未来。但是,审视美国新闻业十年转型的过程,也显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科学技术社会学的概念体系在解释媒介技术与新闻业变迁上的不足,这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对“互动时刻”疏于关注。就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场域来说,新技术进入社会所引发的危机状态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产生大量的相关话语以及话语和行为层面的互动,这些话语和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社会仪式,其一是聚焦全社会的关注,其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凝聚社会共识,这个仪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显在和潜在的行动者,因而值得特别关注。二是“行动者网络”概念的局限性,忽略了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对创新社会体系的预设。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在创新社会中,旧的社会网络解体,行动者重新组合为新的网络,这对解释“流动的社会”状态非常有利,但是,这个概念完全剥离了行动者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承载。实际上,行动者总是受到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每个行动者都是在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框限下行动,那么,这个特定社会中一般意识形态其实织成了一张更高层次的无形的网络,而这个网络并不是随着每一次创新而被随时打破和重组的。就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场域来说,如果忽略了这个更高层次的社会一般意识形态网络,那么,不管是行动者的行动,还是学术界对技术文本设定的主流解读,都将很难得到充分解释。■
①Ellul J.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Y: Alfred A. KnopfInc.
②[美]尼尔·波兹曼著:《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60页,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Kranzberg, M. (1986). “Technology and Histo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7(3): 544-560.
④Pinch, T. & Bijker, W. (198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 399-441.
⑤Oudshoorn, N. & PinchT. (2004). “Introduction: How Users and Non-Users Matter”. In Oudshoorn & Pinch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MA: MIT Press.
⑥ChyiHsiang, Seth Lewisand Nan Zheng. (2012).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Examining How Newspapers Covered the Newspaper ‘Crisis’.” Journalism Studies 13 (3): 305–324.
⑦Meyer, P. (2009).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lumbia :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⑧Jones, A. (2009). Losing the News: The Future of the News that Feeds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⑨McChesney, R. & PickardV. (2011).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The Collapse of Journalism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Fix I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⑩Deuze, M. (2009). “Techn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Journalists: Agency beyond imitation and Change”. In ZelizerB. (ed.) The Changing Face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New York: Routledge. P.82.
[11]Zelizer, B. (2015). “Terms of Choice: UncertaintyJournalism, and Cri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5:888–908.
[12]JacobyS. & Ochs, E. (1995). “Co-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28(3):171-183.
[13][英]巴里·巴恩斯著:《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138页,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4]MulkayM. (1979). “Knowledge and Ut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9(1):63-80.
[15]BijkerW.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p.6、274.
[16]Woolgar, S. (1991). “The Turn to Technology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6(1): 20-50.
[17]Ornebring, H.(2010).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as-labou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ism, 11(1):57-74.
[18][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91、95页,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9]PavlikJ. (2000).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2):229-237.
[20][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167、170页,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1]Ornebring, H.(2010).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as-labou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ism, 11(1):57-74.
[22]Fickers, A. (2014). “’Neither good, nor bad; nor neutral’: the Historical Dispositif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NY: Campus Verlag GmbH, Frankfurt-on-Main. Pp.45、48.
[23]BijkerW.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6.
[24]吴莹、卢雨霞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5]BijkerW.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p.3、273.
[26]Oudshoorn, N. & PinchT. (2004). “Introduction: How Users and Non-Users Matter”. In Oudshoorn & Pinch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 CambridgeMA: MIT Press. p.8.
[27]AkrichM. (1992). “The De-Scrip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in Bijker, W. & LawJ. (Eds.) Shaping Technology / Building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P.208.
[28]BijkerW.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p.270-271.
[29]Pinch, T. & Bijker, W. (198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399-441.
[30]JacobyS. & Ochs, E. (1995). “Co-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28(3):171-183.
[31]本文使用“传统新闻业”/“新闻业”一词指以报纸为代表、以新闻专业主义规范为基本价值体系的新闻体系,不必然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形态,传统媒体的互联网传播形式和互联网原生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本规范的媒体形式皆被视为“传统新闻业”/“新闻业”。
[32]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p. X.
[33]Starr, P. (2009). “Goodbye to the Age of Newspapers: Hello to a New Era of Corruption”. The New Republic, March 4th :28-35.
[34]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pp. 81-82.
[35][英]巴里·巴恩斯著《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4页,鲁旭东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36]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Pp. 21-27.
[37]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09).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9”. P. 174.
[38]Starr, P. (2009). “Goodbye to the Age of Newspapers: Hello to a New Era of Corruption”. The New Republic, March 4th :28-35.
[39]Bollinger, L. (2010). “Journalism Needs Government Hel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14th.
[40]Johnson, K. (2009). “The Rocky Says GoodbyeTaking a Part of Its City’s Past With It”. The New York TimesFeb. 28p. A11.
[41]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2010).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0”. P. 10.
[42]ReynoldsA. (2014).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How Changes in Journalism, Technology and Public Life Impact Each Other”. In Miller, A. & Reynolds, A. (eds.). News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The Future of Print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p.15.
[43]Simon, D. (2009). “Death of the Newspaperman”.回溯日期:2017/12/10,
[44]Barnhurst, K. (2014).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News”.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NY: Campus Verlag GmbH, Frankfurt-on-Main. p.111.
[45]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10) ‘‘Potenti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upport the Reinvention of Journalism’’Staff Discussion DraftWashington, D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46]“THE FUTURE OF NEWSPAPERS: THE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DEMOCRACY”,回溯日期:2017/12/10,https://www. gpo. gov/fdsys/pkg/CHRG-111shrg55622/html/CHRG -111shrg55622.htm
[47]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pp.23-24、54-56.
[48]MitchellA. & HolcombJ. (2014). “Personal Wealth, Capital Investmentsand Philanthropy”,Pew研究中心,2014年度媒体报告,回溯日期2017/12/10,http://www.journalism.org/2014/03/26/personal-wealth-capital-investments-and-philanthropy/
[49]MitchellA.JurkowitzM.etc. (2013). “Nonprofit Journalism: A Growing but Fragile Part of the U.S. News System”. 回溯日期2017/12/10,http://www.journalism.org/2013/06/10/nonprofit-journalism/
[50]BensonR. (2017). “Can foundations solve the journalism crisis?” Journalism, Aug. 31. Online First.
[51]BrowneH. (2010). “Foundation-Funded Journalism: Reasons to be Wary of Charitable Support”. Journalism Studies11(6): 889-903.
[52]Bonazzo, J. (2017). “NY Times Launches Philanthropy Initiative to Get Outside Funding for Journalism”Observer, Sep. 1. http://observer.com/2017/09/new-york-times-philanthropy-nonprofit-journalism/
[53]DuBordS. (2009). “The Newspaper Revitalization Act Bailout”. 回溯日期:2017/12/15,https://www.thenewamerican.com/usnews/congress/item/2224-the-newspaper-revitalization-act-bailout
[54]BensonR. (2017). “Can foundations solve the journalism crisis?” Journalism, Aug. 31. Online First.
[55]A.P. (2009). “US newspapers are an endangered speciessays Senator John Kerry”6 May回溯日期2017/12/15,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09/may/06/usa-newspapers-john-kerry-senate
[56]DownieL.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ct. 20http://archives.cjr.org/reconstruction/the_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
[57]Pew研究中心:《2016年度媒体报告》第60页,回溯日期2017/12/10,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16/06/30143308/state-of-the-news-media-report-2016-final.pdf[58]“Traditional media firms are enjoying a Trump bump:Making America’s august news groups great again”. The EconomistFeb. 16th 2017.
[59]NewmanN.Fletcher, R.etc. (2017). “Reuters Institute?Digital News Report 2017”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Pp.9、23.
[60]Stearns, J. (2011). “Non-profit journalism and the need for policy solutions”. Freepress.net. 回溯日期2017/12/16http://www.freepress.net/blog/11/12/05/nonprofit-journalism-and-need-policy-solutions
[61]Levis, C. (2010). “New journalism ecosystem thrives”.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orkshop, Oct. 29回溯日期2017/12/16,http://investigativereportingworkshop.org/ilab/story/ecosystem/
[62]Konieczna, M. & Robinson, S. (2014). “Emerging news non-profits: A case study for rebuilding community trust?” Journalism, 15(8): 968-986.
[63]Barthel, M. (2017). “Despite subscription surges for largest U.S. newspapers, circulation and revenue fall for industry overall”.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
[64]Barbash, F. (2016). “Struggling Philadelphia Inquirer is donated to nonprofit in groundbreaking deal”.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12.
[65]AndersonC. (2013). Rebuilding the News: Metropolitan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 149-150.
[66]Barbash, F. (2016). “Struggling Philadelphia Inquirer is donated to nonprofit in groundbreaking deal”.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12.
[67]EglashR. (2004). “Appropriating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Eglash, R.etc. (eds.) Appropriating Technology: Vernacular Science and Social Pow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8]ChyiHsiang, Seth Lewisand Nan Zheng. (2012).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Examining How Newspapers Covered the Newspaper ‘Crisis’.” Journalism Studies 13 (3): 305–324.
[69]Sturgis, I. (ed.)(2012). Are Traditional Media Dead? Can Journalism Survive in the Digital World? NY: IDEBATE Press. P.1.
[70]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71]ChyiHsiang, Seth Lewisand Nan Zheng. (2012).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Examining How Newspapers Covered the Newspaper ‘Crisis’.” Journalism Studies 13 (3): 305–324.
[72]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73]Starr, P. (2009). “Goodbye to the Age of Newspapers: Hello to a New Era of Corruption”. The New Republic, March 4th : 28-35.
[74]DownieL.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ct. 20http://archives.cjr.org/reconstruction/the_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
[75]Starr, P. (2009). “Goodbye to the Age of Newspapers: Hello to a New Era of Corruption”. The New Republic, March 4th : 28-35.
[76]DownieL.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ct. 20http://archives.cjr.org/reconstruction/the_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
[77]Alexander, J. (2016).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democratic cultureand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In AlexanderJ.Breese, E. & Luengo, M. (eds.).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7.
[78]Somaiya, R.IsaacM. & Goel, V. (2015). “Facebook May Host News Sites’ Content”. New York TimesMarch 24B1.
[79]罗世宏、胡元辉编:《新闻业的危机与重建:全球经验与台湾反思》第153页,先驱媒体社会企业2010年版
[80]HaA. (2017). “Craigslist founder donates $1M to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onprofit ProPublica”. Techcrunch, Mar.1. https://techcrunch.com/2017/03/01/craig-newmark-propublica/
[81]CreechB. & Nadler, A. (2017). “Post-industrial fog: Reconsidering innovation in visions of journalism’s future”. Journalism, Jan. 28Online First.
[82]CreechB. & Nadler, A. (2017). “Post-industrial fog: Reconsidering innovation in visions of journalism’s future”. Journalism, Jan. 28Online First.
[83]CreechB. & Nadler, A. (2017). “Post-industrial fog: Reconsidering innovation in visions of journalism’s future”. Journalism, Jan. 28Online First.
[84]BroersmaM. & Peters, C. (2013).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Journalism: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 Public Good”. In Peters, C. & Broersma, M. (eds.) Rethinking Journalism: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transformed news landscape. NY: Routledge. pp. 1-12.
[85]Nielsen, R. (2016). “The many crises of Western journ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crises, professional crises, and crises of confidence”. In AlexanderJ.Breese, E. & Luengo, M. (eds.).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7.
[86]Meyer, P. (2009).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87]MoraleL. (2011). “Americans Regain Some Confidence in Newspapers , TV News”. Gallup, Jun. 27. http://www.gallup.com/poll/148250/Americans-Regain-Confidence- Newspapers-News.aspx
[88]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P. 34.
[89]McChesney, R. & NicholsJ. (2010). 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hiladelphia: Nation Books. P. 4.
[90]Meyer, P. (2009).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P.2.
[91]NeroneJ. (2013). “Why Journalism History Matters to Journalism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ism, 30(1): 15-28.
[92]NeroneJ. (2013). “Why Journalism History Matters to Journalism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ism, 30(1): 15-28.
[93]Alexander, J. (2016).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democratic cultureand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In AlexanderJ.Breese, E. & Luengo, M. (eds.).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
[94][美]达洛尔·韦斯特著:《美国传媒体制的兴衰》,董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5]HallinD. (1992). “The Passing of the ‘High Modernism’ of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3): 14-25.
[96]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 219-237.
[97]PetersC. & Broersma, M. (eds.) Rethinking Journalism: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transformed news landscape. NY: Routledge. p.2.
[98][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69页,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9]CowardR. (2013). Speaking Personally: The Rise of Subjective and Confessional Journalism. NY: Palgrave Macmillan. P.6.
[100]Wahl-Jorgensen, K. (2014). “Changing Technologies, Changing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ies: Public ParticipationEmotionality and the Challenge to Objectivity”.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p. 279、265-266.
[101][美]迈克尔·舒德森著:《新闻的力量》第28、201页,刘艺聘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102]Wahl-Jorgensen, K. (2014). “Changing Technologies, Changing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ies: Public ParticipationEmotionality and the Challenge to Objectivity”.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p. 279.
[103]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 442-464.
[104]Alexander, J. (2016). “Introduction: Journalism, Democratic Cultureand Creative Reconstruction ”. In AlexanderJ.Breese, E. & Luengo, M. (eds.).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
[105]Stephens, M. (2014). “Quality in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The Limits of Realism”.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p. 238-240.
[106]NeroneJ. (2013). “Why Journalism History Matters to Journalism Studies”. American Journalism, 30(1): 15-28.
[107]AndersonP. (2014). “Defining and Measuring Quality News Journalism”. In Anderson, P.OgolaG. & Williams, M. (eds.). The Future of Quality Journalism: A Cross-Continental Analysis. NY: Routledge. P.9.
[108]Shapiro, I. (2010). “Evaluating Journalism: Towards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4(2): 143-162.
[109]PalmerL. (2014). “CNN’s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 The Ambivalent Labor of iReporting”. In ThorsenE. & AllanS. (eds.). Citizen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P.36.
[110] Valle, F. (2014). “Getting into the Mainstream: the Digital Media Strategies of a Feminist Coalition in Puerto Rico”. In ThorsenE. & AllanS. (eds.). Citizen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NY: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P.221.
[111]Kamel, Y. (2014). “Reporting a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When Activists Drive the News Coverage”. In ThorsenE. & AllanS. (eds.). Citizen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NY: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P.238.
[112]Neuberger, C. (2014). “User Participation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on the Interne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246.
[113]Zelizer, B. (2017). 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21.
[114]EberweinT. (2014). “Journalistic Quality as Crowd Wisdom? What Journalists Think about Criticism on the Social Web”.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206.
[115]AndersonC. (2016). “Assembling PublicsAssembling Routines, Assembling Values: Journalistic Self-conception and the Crisis in Journalism”. In AlexanderJ.Breese, E. & Luengo, M. (eds.).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Reconsidered: Democratic CultureProfessional CodesDigital Futur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53-169.
[116]PavlikJ. (2014). “MobileNetworked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tic Work”.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187.
[117]Neuberger, C. (2014). “User Participation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on the Interne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247.
[118]Neuberger, C. (2014). “User Participation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on the Internet: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SchreiberM. & Zimmermann, C. (eds.) Journalism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ontemporary Trends.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p.248-260.
陈红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