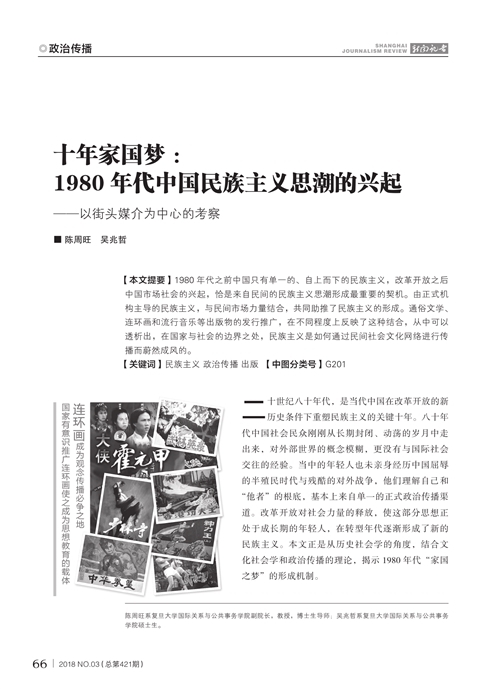十年家国梦:198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以街头媒介为中心的考察
■陈周旺 吴兆哲
【本文提要】1980年代之前中国只有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兴起,恰是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最重要的契机。由正式机构主导的民族主义,与民间市场力量结合,共同助推了民族主义的形成。通俗文学、连环画和流行音乐等出版物的发行推广,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结合,从中可以透析出,在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之处,民族主义是如何通过民间社会文化网络进行传播而蔚然成风的。
【关键词】民族主义 政治传播 出版
【中图分类号】G20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重塑民族主义的关键十年。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民众刚刚从长期封闭、动荡的岁月中走出来,对外部世界的概念模糊,更没有与国际社会交往的经验。当中的年轻人也未亲身经历中国屈辱的半殖民时代与残酷的对外战争,他们理解自己和“他者”的根底,基本上来自单一的正式政治传播渠道。改革开放对社会力量的释放,使这部分思想正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人,在转型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主义。本文正是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结合文化社会学和政治传播的理论,揭示1980年代“家国之梦”的形成机制。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
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建构的产物。早期民族理论深受赫尔德理论传统之影响,坚持民族认同来自自然历史的传承,是文化传统深沉积淀的结果。①赫尔德的自然主义从霍布斯鲍姆开始,逐渐被一种历史—社会—经济的解释所取代,这种解释首先强调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时期即现代化之产物;其次则主张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取决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即是说,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对于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②
后一种解释最终导致了本·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政权有意识建构的结果,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为了凝聚其领土上的人口,通过一系列政治传播机制向后者灌输“同文同种”的观念,使地缘上遥远的陌生人彼此想象为“同胞”,亦为现代国家披上民族代表的外衣,成为其权力合法性的论证。因此,在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统治者有意无意的政治传播扮演了关键角色。③诚如霍布斯鲍姆之言,所谓“传统”,并非全然自发的,甚至很有可能是被政治精英“发明”出来的。④
基于对民族主义“历史性”的理解,霍布斯鲍姆区分了“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⑤其意绝非做“历史性”与“自然性”之断然二分。“官方民族主义”更多是统治精英为其政治之目的塑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借以巩固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亦为统治的正当性提供解释。“民间民族主义”的形成,当然不能排除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政治传播的作用,但明显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波折,也主要体现在民间民族主义身上,因为影响后者的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事实上,“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两者基本不是同步发展,霍布斯鲍姆的这个区分在此就显得特别有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不是没有“共同体意识”,甚至如秦晖所言,已经有清楚的“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之分。⑥但林林总总亦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共同体”的意识,⑦与对“虚幻的共同体”的观念相去较远。帝国与帝国边疆的冲突古已有之,满蒙时代更臣服于游牧敌国,及至晚清,中华帝国的臣民,对于外族“他者”,不说麻木迟钝,至少也无强烈之异己排斥之感。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显著的民族主义思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何伟亚的研究指出,马嘎尔尼访华引发的中西礼仪之争,并非缘自天朝的封闭、保守,而是中国另有一套平行的世界体系理念,⑧不管这套理念被称为“朝贡体系”还是“天下体系”,彼时相较西方的主权体系观念,显得更为包容、和平。
茅海建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战败后中英谈判前夕,从道光皇帝到各级官员,都仍然把英国人当作传统的游牧敌国来对待,以为通过“和亲”政策可以安抚之。⑨在当时人眼中,《南京条约》绝非主权平等国家之缔约,而只是一贯“怀柔远人”的和亲举措。是故,恩格斯从记者见闻得知中国鸦片战争发生之事,便这样评论道:“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 ⑩
转折点发生于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大清皇帝退守热河。情急之下,以奕为首的士大夫群体不得不诉诸当时在帝国精英内部流传的《万国公法》,要求英法联军撤出北京,这无形中等于接受了主权体系,承认中国只是与西方诸强主权地位平等的林立民族国家中之一员。其结果众所周知:英法撤军,东交民巷划设使馆区。嗣后《万国公法》洛阳纸贵,官方民族主义终成定局。[11]与“官方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的“民间民族主义”来得稍晚些。后者是在中西交流的漫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结果。按照何伟亚的研究,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处心积虑,足足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彻底瓦解了中华帝国传统的权威观念,首当其冲的就是君权的神圣性,随之自然是传统的大共同体意识、天下观念等一系列配套的思想体系。[12]顾德曼以上海为例,指出上海市井之民经历与包括外国商客、租界管治者在内的“他者”长期互动抗争之后,至民国时代,所谓“中国市民的民族主义”方才成熟定型。[13]与之相较,所谓“中国农民民族主义”则更晚,查默斯·约翰逊把时间点挪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农民向来都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乡村经济在西方冲击下破产,也未能提升农民对“他者”的认知。约翰逊认为,正是日本侵略者深入到中国乡村地区的烧杀抢掠,才充分激发了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14]此时已经距鸦片战争官方民族主义形成近一百年。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基于对“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同,确实是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经过百年激荡扎根于中国民众心中的民族主义观念,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民间民族主义随着社会力量的发展,强度呈现不同的起伏。
二、重塑民族主义:为什么是1980年代?
由于具备强固的国家能力,新中国政权有足够的能力来引导民众思想的发展,形塑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这对于凝聚国家共识、促进社会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么,在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中,1980年代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应把它视为家国之梦的“关键十年”?
首先,在对外关系上,1980年代对于中国与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被定为基本政策,意味着中国社会重新融入世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中国社会就是完全封闭的。无论是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还是发起不结盟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对外援助,等等,都显示中国较为主动的外交姿态。中国与英国、日本、美国等国也陆续恢复邦交,这些其实正是1980年代得以推行开放政策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时期,国家也在不断塑造各种“他者”,如通过“赶英超美”,以及炮击金门、中苏交恶等事件之后对美、苏帝国主义侵略者形象的建构,等等,都是十分典型的、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用以保持人民团结一致、热爱祖国的重要策略。不过,在这个阶段,民族主义多是来自国家主导的单一声音,民间社会与外国接触的机会有限,缺乏对“他者”的真切体会。
这种局面,在198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借实行开放政策的契机,中国社会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开始了政治、经济和体育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交流,尽管在当时条件下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西方作家的译作开始在新华书店上架公开发行;国外制造的电子产品开始进入指定的外贸商场,市民可以通过外汇券进行购买;电影院、电视开始播放海外的影视作品;普罗大众可以通过实况录像收看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队参加的奥林匹克赛事;南方率先开放的大城市街头开始出现蓝眼金发的外国人身影。对于中国普通的大众而言,国际社会这个“他者”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想象,而是真实的存在。至少在1980年代,公开接触、拥抱各种外国产品不再是禁忌,有市民们开始比较中外产品的优劣。由于社会上存在一些过分吹捧国外文化优越性的人,1980年代中叶掀起了持续的关于“崇洋媚外”言行的宽松而平和的争论,同时也凸显民间社会在遭遇“他者”初期的自觉。
其次,1980年代中国同时开启思想启蒙和经济改革。这个进程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市场力量和民间社会的复苏,为民间民族主义的发轫提供载体和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将全面计划经济体制改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合法性,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以及个体经营兴起,配以稳步推进的价格体制改革,被管制的“牌价”与市场放开的“议价”一度并存,后者通常针对市场上紧俏的商品。[15]中国的市场力量就此重新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之下,中国思想界、文艺界和学术界也走出了传统思想的藩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于为中国的思想启蒙确立了一条具有开放性的准则。诚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脱胎于之前的体制,依然不乏陈旧的话语、符号,但是已经为吸收、消化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提供了可能性。思想启蒙加上经济管制的放松,使各种半官方、半市场的机构,成为民间社会传播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1980年代起,中国的消费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历了一场所谓的“城市消费革命”,其结果是“打破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垄断”。[16]与之前受到严格拘束的生活方式不同,198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消费向多元化、丰富化扩展,尤其是大规模公共传媒技术开始投入民间应用,广播、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们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还是广播、报纸和电影,以至于类似于自卫反击战、血丝虫病防治、科普等宣传,都是通过观看电影来完成的。八十年代初,黑白电视进入城市小康家庭。1980年中国拥有电视机902万台,电视人口覆盖率达45%,1985年中国电视机社会拥有量已经达到6965万台,[17]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69.4%,[18]在中国城市基本普及,中央电视台乃至部分地方电视台的节目库也逐渐丰富起来,能够支持整个晚上至少六个小时左右的节目时间,[19]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就从报纸转到了电视,使电视取代电影、广播等传统媒体,成为民族主义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公共传媒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尽管从性质上是党的“喉舌”,依靠公共财政支持,但却在政策上被允许走商业化路线,从一开始就依靠商业广告来维持运营,即所谓“走自己的路”。[20]因此他们刻意迎合消费社会的需求,力求让电视节目更加多元化、娱乐化,软化了政府机构的刻板形象,而在传播效果上则更容易深入人心。[21]这就是1980年代为中国民族主义型塑提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那一代年轻的爱国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甚至毫不夸张地说,1980年代开放之初的民族主义,对于后来中国将国家战略重点转向民族国家建设、坚持走中国民族自强道路,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这正是观念变迁渐积所致。
由于1980年代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框架与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家国情怀交互作用的结果,即是说,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由民间或半民间机构推波助澜,而达到潜移默化之效果。因此,对1980年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应更多着眼于这个年代社会的集体记忆,[22]而这正是这十年间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经验弥足珍贵之处。
换一种说法,可以认为是主流意识形态有意识地或巧妙地渗透进了社会文化消费网络,对这一代人的思想进行了形塑。这一过程,正是迈克尔·曼所描述的“基础性权力”的运作。[23]事实上也只有当市场商业网络、公共传媒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基础性权力”才能变得游刃有余,意识形态的操作也就更偏重于循“基础性”途径,而更少诉诸更直接的维度。那么,这一思想形塑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一追问迫使我们不得不将着眼点放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相互塑造的边界领域,去探寻民族主义的形成。本文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物作为这个边界领域的代表,重点考察当时由政府机构和民间共同推动的出版物如何被用来来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三、街头巷尾的民族主义
显然,正式教育是官方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的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制度化工具,国家首先是通过教科书体系的训导,向年轻学生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民族情感,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一种“教科书史观”。不过,这种史观的真正形成,并不完全是在课堂上,其实是借助了民间社会力量的推波助澜,来自街头巷尾的民族主义。
与初中教科书遥相呼应的,是1980年代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各种出版物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情结。这些流行的出版物随着中国逐渐开放的市场而生,包括了书刊、流行音乐以及作为街头儿童读物的各色各样连环画。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社会上散布的出版物固然都存在程度不一的限制,但在当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口号下,迎合中国消费社会的发展,它们获得了较大的市场空间,以更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方式,深入地影响了那一代成长中的青年的头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报纸和杂志仍然受政府部门严格管制,也不存在竞争压力,并不刻意迎合市场,故很难称其具“民间性”。竞争性初露端倪的是书籍出版领域,在普通日常民众的生活中流传更广的当数文学类书籍。按照一般的文学史分类,中国的文学作品分为“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前者流行于市井之中,为正式教育体系所不喜、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多为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24]区分的标准不全在写作手法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话语”,[25]而通常取决于是否由政府控制的出版机构所出版,或是否由拥有正式编制作家所撰写。“通俗文学”的作者群体多为我国港台地区的作家,包括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亦舒等,或者是一些从事所谓“传奇文学”创作的无名民间作者。出版方亦多为半官方半民间性质,是从正式出版机构衍生出来、专门用以创收牟利的部门。“通俗文学”书籍的出版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不特以传播意识形态为旨归,但为了取得合法性,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弘扬民族情感、在作品中融入民族主义元素,正是“通俗文学”最重要的市场策略。如此一来,这些书籍便成为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结合的渠道。
正式的“严肃文学”的出版、销售渠道被严格管控,读者群十分有限,一般民众难以企及,更与广大中小学生格格不入。“通俗文学”便趁虚而入,反而成为那一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主要读物。尽管在学校正式教育体系中,对这些出版物予以严格取缔和禁止,但仍不影响学生群体在“课外”以之为主要读物。学生群体的价值观是在“教科书史观”和“课外读物史观”的冲突中形成的,但这些相互冲撞的观念,却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当然,这些书籍的影响力不可高估。首先,作为正式渠道之外的出版物,其流通本身存在诸般限制,受众群体十分有限。对这些书籍的阅读本身也常常被视为禁忌,“禁忌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压抑意识生成。其次,就作品本身的内容而言,以武侠、言情为主线的描写,往往会遮蔽、淡化作品中蕴含的民族主义元素。以金庸、梁羽生等香港作家的武侠小说为例,这些作品每每将个人情感嵌入宏大历史背景之中,本可以成为弘扬民族情感的绝佳素材,却往往执著于“夷夏之辨”判正邪,反而冲淡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因此,在民族主义思想传播中更值得重视的,是由正式出版机构迎合市场需求发行的出版物。在出版史和传播史中常常被轻视、作为草根出版物的连环画,正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连环画起源于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后迎来春天,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连环画走向市场化、创作趋于多元化的巅峰时期,出版量剧增,尤其在1982年,达到8.6亿册,占全国图书出版总量的三分之一,1983年、1984年两年更达到15亿册。[26]连环画图文并茂,价格便宜,流通渠道多元便利,容易获得。这些便利条件使之成为1980年代青少年广泛流传的读物,也是这一代少年成长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
于是,连环画成为观念传播必争之地,国家有意识推广连环画使之成为思想教育的载体。[27]民间民族主义的教化,主要来自武术题材连环画。香港电视系列剧《霍元甲》在内地播出,以及电影《少林寺》及其系列的风靡,以岭南美术出版社开风气之先,推动了一批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武术连环画的创作和发行,包括有《香港功夫王》(1981)、《两打镇华台》(1982)、《武林志》 (1983)、《激战双鹰峰》(1983)、《铁臂扫群奸》(1983)、《小龙云怒打洋力士》(1983)、《霍元甲摆擂台》 (1983)、《武林英豪》(1984)、《古河英魂》(1984)、《南北大侠》(1984)、《神力王》(1984)、《神州擂》(1985)、《神腿扫奸》 (1985)、《中华拳星》(1985)、《雌雄剑恩仇记》 (1985)等等,不一而足。从中也不难发现,武术连环画出版的高峰是在1980年代上半叶,1986年之后随着整个连环画市场遭遇多重竞争渐趋不景气而退潮。[28]它们的故事都比较雷同:中国武术家与外国拳师比武。这种叙事模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外武术家“比武”的故事设计,是以“敌我斗争”模式来设定中外关系,在“武术”这个特定场域的投射。中国武术家儒雅忠厚,武术招式凌厉却有节制,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儒家形象。相反,外国武士无不高大彪悍、穷凶极恶,招式阴险毒辣,毫不留情,完全靠“力”争胜。
在这些武术连环画中,外国拳师主要来自两个国家:俄国与日本。尽管传说中霍元甲的主要对手是美国拳师奥皮音,各种出版物中却刻意被改为俄国拳师波索夫。跟风的各种武术连环画,纷纷将矛头指向俄国,比如《武林志》中国武术家东方旭的对手就是俄国大力士“达得洛夫”;《神州擂》东方一杰的对手则是俄国大力士“马洛托夫”;连环画《神力王》出身义和团的武师王斌在擂台上力克各国武士,当中便有俄国的“克劳斯夫”。不可否认,这些带“夫”、生搬硬造的俄国人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是当时中苏关系的投射。其时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他者”并非欧美国家,而恰恰是苏俄。在近代史教育,以及大众传媒的宣传中,俄国如何趁大清帝国积弱而鲸吞北方领土的故事,不断被强调、重复。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连环画《神腿扫奸》,甚至从第一页就将故事背景放在沙俄特使鲍里斯借向大清皇帝贺寿伺机侵占中国领土上。
武术连环画对于1980年代民族主义建构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在其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身体政治”。在这些作品中,“东亚病夫”这一刺眼的称号,几乎成为八十年代人最深重的创伤烙印。“东亚病夫”一说,据说最早来自《字西林报》一篇英国作者的文章。[29]当它藉由一个“脱亚入欧”、军事实力后来凌驾于中国之上的东亚“蕞尔小国”之口讲出,则具有别样的刺激和挑衅意味。
“东亚病夫”的蔑称,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耻辱的身体政治。一方面,“病夫”的说法是指那些吸食鸦片之后被摧残的中国人身体,这很容易跟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半殖民历史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东亚病夫”代表了中国人种族在身体力量上与西方种族的差距,容易激发起中国人深层的自卑感。瘦弱、病恹恹的男性身体,是近代以来整个民族苦难状态的缩影。在“中外比武模式”的武术连环画中,那些外国武士口中不断轻蔑地喊出“东亚病夫”,刺激着中国观众的民族主义神经,而对这些代表列强的大力士反戈一击,以及对中华武术高超技术的渲染,反过来在更高程度上激发起民族的自豪感。诸多武术连环画正是透过“武术”这种身体语言来传递民族自强、“落后就要挨打”的信念,须知“武术”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来的,民族主义在身体上的隐喻。
这种“身体民族主义”,在中国代表团参加美国洛杉矶举办的1984年奥运会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许海峰在射击比赛中拿下第一枚奥运会金牌,被称为“零的突破”。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和奖牌总数第4名,官方传媒反复声称,中国从此不再是“东亚病夫”。[30]电视的普及、卫星通讯技术的投入使用,这些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众多的中国平民大众,生平第一次通过卫星直播,坐在电视机前,参与了这场一雪前耻的盛会,使这一届奥运会具有了深远的意义。
武术连环画退潮之后,接续连环画承担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出版物,便是1985年前后开始在街头巷尾传唱的音像制品。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不乏在普罗大众当中流行的“革命歌曲”,但刻意避免用真嗓演绎的“通俗歌曲”,遑论创作、生产、包装、营销一体化的流行音乐市场。八十年代之初,李谷一、朱逢博等学院派歌唱家开了通俗唱法的先河,加上台湾甜美歌后邓丽君横空出世,使流行音乐在短短几年内取代“革命歌曲”成为中国音乐市场的主流。八十年代中叶,以程琳、朱晓琳、王洁实、谢莉斯组合等为代表的校园民谣在中小学生群体中风靡一时,这些都是港台流行音乐风格的蔓延,他们演唱的歌曲大多都是台湾地区原创,在两岸未能“三通”的条件下,只能靠大陆歌手翻唱而为消费者所熟谙。[31]当时虽仍有《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革命歌曲”力作推出,但总体创作乏力,渐渐无法与流行歌曲争锋。将主流意识形态巧妙嵌入流行音乐之中,成为一种现实、合理的选择。
典型例子是香港歌手张明敏的异军突起。这位在香港并不入流的歌手,却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他能够用普通话演唱。张明敏虽然不能做到字正腔圆,却成为联通两岸三地流行音乐的绝好中介。他大量翻唱台湾原创的流行歌曲,使之被大陆听众所熟悉。让张明敏在八十年代民族主义建构中独领风骚的,是一首由香港文人黄霑创作的《我的中国心》。时值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年,作为香港人的张明敏获邀参加当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这首《我的中国心》,以迎接中国即将收回香港主权的历史时刻。“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朗朗上口的歌词、慷慨激昂的旋律,极易引发共鸣,唤起普罗大众的民族自豪感,可谓一时无两。
此后,张明敏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以演唱爱国歌曲为业,演绎了多首由台湾音乐人创作的《中华民族》、《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长城谣》、《青海青》等爱国歌曲。这些流行歌曲情绪高昂,有别于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靡靡之音,遂为官方所认可并有意识推波助澜。传播“四海一心”的民族认同情感,由此便成为海外流行文化进入内地市场的正当化理由。
与之相应的一个重要变化,是1980年代初盒式录音带在市场上的普及,打破了以出版黑胶唱片为业的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垄断地位。大量出版盒式录音带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公司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等开始进入市场竞争,在推动流行歌曲的发展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32]在革命歌曲后劲不足、爱情歌曲难登大雅之堂的八十年代中叶,容易传唱、旋律优美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爱国歌曲”,参照裴宜理“文化置位、操控” [33]的术语,因正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文化重置”边界,便成为滋养那一代年轻人心灵的主要养料,使民族主义在这些人心中扎根。
结论
中国的民族主义,扎根于两种历史记忆,一是中国两千年不绝如缕、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此乃中华民族形成血脉相连的“共同体想象”、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源泉;一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半殖民的屈辱近代史,构建了中国对西方世界“他者”的想象,通过苦难忧思激发民族自强的信念。这两种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其实是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适逢改革开放之初,消费社会逐渐形成、传播技术突飞猛进,上述两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社会进行广泛传播和弥散的条件日臻成熟。借助市场力量,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民间思潮,成为主要的民族主义传播模式。八十年代民族主义,无疑是正式教育体系与民间市场力量相互契合推动的产物。■
①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⑤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1页
⑥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⑦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⑧何伟亚:《怀柔远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⑩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0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申剑敏:《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
[12]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3]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5]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16]慧思、卢汉龙等:《中国城市消费革命》第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7]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583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8]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第49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19]赵化勇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第11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20]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第16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21]麦康勉:《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的变迁》,《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七十七期
[22]康納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3]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mechanisms and results”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Vol. 251984.
[24]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5]吴秉杰:《两种不同的文学话语》,《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26]魏华:《新中国连环画艺术简史》第117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7]苗田:《民间文化的非民间运动》,《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7期
[28]范生福:《中国连环画的百年兴衰》,《史林》2012年增刊第11期;宛少军:《20世纪中国连环画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
[29]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
[30]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http://www.olympic.cn/games/summer/china/2004-03-25/120254.html
[31]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第141-14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32]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第62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33]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陈周旺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兆哲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