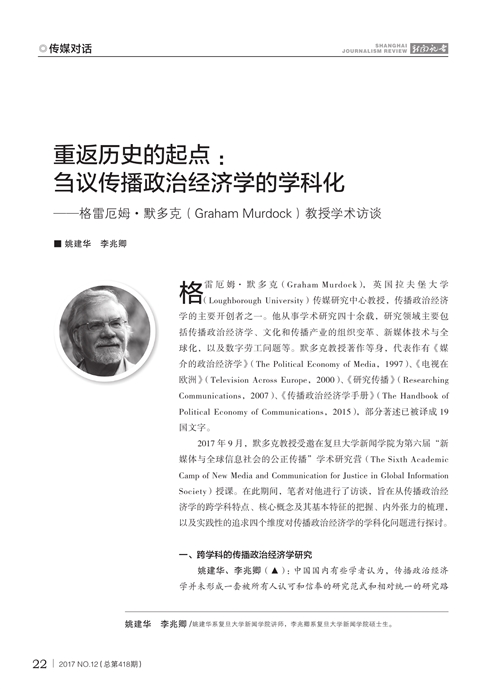重返历史的起点:刍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化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学术访谈
■姚建华 李兆卿
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传媒研究中心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从事学术研究四十余载,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和传播产业的组织变革、新媒体技术与全球化,以及数字劳工问题等。默多克教授著作等身,代表作有《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1997)、《电视在欧洲》(Television Across Europe,2000)、《研究传播》(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2007)、《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2015),部分著述已被译成19国文字。
2017年9月,默多克教授受邀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第六届“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The Sixth Academic Camp of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for Justice in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授课。在此期间,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特点、核心概念及其基本特征的把握、内外张力的梳理,以及实践性的追求四个维度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跨学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姚建华、李兆卿(▲):中国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未形成一套被所有人认可和信奉的研究范式和相对统一的研究路径,因此很难被称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您如何看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化问题?
默多克(●):传播政治经济学并非一门学科,也不应该成为一门学科,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母体的政治经济学的起源中去。政治经济学于18世纪中期在欧洲兴起,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特别关注三方面的变革过程及其联系,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政府管控与社会控制。具体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帝国扩张的过程是相互构连的,这种构连使社会政治系统内部也发生了诸多变革,比如封建制度的废除、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在美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不再是君主或现代帝国所宰制的对象,而成为具有政治自决权的“公民”(citizen)——他们有权去选择、塑造自愿在其统治/管理之下的政府的形态。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的变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由于资本的急速扩张,大量移民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使得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因此,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试图去理解经济力量和上述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自诩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希望能够重新拥抱这种整体观(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盛行促使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反思和重塑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议题、范式和方法——笔者注)。
19世纪末随着现代大学的出现,不同的研究领域被彻底专业化、学科化和边界化。经济学彻底抛弃了社会分析的方法,仅仅研究由供给关系决定的市场中个体的理性选择;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只局限于国家和政府;而社会学也仅仅关注社会的发展问题。学科之间的区隔加剧了研究者对政府和社会变革进行整体性把握的难度。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重回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起点,是因为将这些研究领域重新糅合在一起,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如果经济学家仅仅将经济学视为一个边界分明的学科领域,截然隔绝与其他学科的任何联系,这样他们只能在自身狭仄的学科系统内固步自封,而事实并非如此。回归历史的起点,就意味着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个研究领域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为其研究起点,寻根朔源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检视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效应以及社会、文化机制所带来的整体性影响。因此,脱胎于政治经济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产生伊始,就带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的印记。作为不同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永远也不能被学科化,因为一旦被学科化,就意味着它将失去蓬勃的生命力。
二、传播政治经学的核心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一年前,当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在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被问及他所理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时,他强调了社会的不平等。那么在您看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三个核心概念,即不平等(inequality)、权力(power)以及危机(crises)。首先,是对不平等的关注。还是让我们回到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的起点之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强调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一种以交换为主的系统,关注市场和交易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在斯密看来,市场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平衡的系统,也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系统。人们各自讨价还价,最终使双方获得相对平等的收益。但马克思对此持批判的态度,而这也正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开端。批判就意味着要解构市场的正统地位,其中关键点就是承认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并非是市场机制,而是资源的分配,是关于财产的所有权和非所有权问题。这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为何如此关心公司产权的因由所在。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不平等的权力系统,造成了阶级、性别、种族的不断分化。现代资本主义根据人们与新的生产系统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阶级分化。它同时改变了不同性别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经济的关联性,“家庭”的概念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和帝国扩张紧密相连,因此种族分化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就以美国社会为例,奴隶制的“遗风”至今尚存——在经济上,黑人工人阶级孩子的生活境遇远远落后于白人工人阶级的小孩。但问题是,这些分化是如何将人们的机会结构化的,比如如何获得更好的自我发展、自我表达的机会?如何获取更多自身所需信息的权利?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声张自己的权利?这些问题对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言至关重要。
最后,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思考。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系可以自我修正,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周而复始地产生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经济危机的历史,比如2008年的经济危机彻底破坏了资本主义日常的运作机制,让特权阶级、利益集团趁此机会攫取大量的利益而赚得“盆满钵盈”。我同意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的表述,从1945-1975年的这30年间,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机会是相对比较平等的;但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社会机会出现了严重的极化,因此不平等、权力、危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概念。
▲:以不平等、权力和危机为研究起点的跨学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政治、经济和历史变革进程的研究。它以欧洲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为切入点,研究民主、新形式政府的出现及其与经济变革之间的勾连关系。而这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它是一个关于政治、经济变革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领域。与这些变革相伴随的是,社会中也出现了大量其他的革新,传播政治经济学旨在对社会中出现的这些基础性的结构变迁进行系统性的分析。
其次,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其诞生之初,就与道德哲学紧密联系,且不停地追问: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是“善治”的社会?如何去建构“善治”的社会?这些追问与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诉求高度一致,即追求个体性、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但问题是,如何平衡这三种不同的诉求,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经济秩序来满足这些诉求,而不是去破坏它?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一系列道德哲学的问题,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将对道德哲学的思考重新引入对社会生活和进行道德评判的研究之中。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如果对什么是“善治”的社会,现行的经济结构如何实现或阻碍“善治”社会的形成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存有疑惑,那么研究者就有责任进一步介入到这些变革的进程之中,审视各种制度所引发的变化,其中哪些制度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平等与团结,同时更有利于个体的创造和表达。所以说,马克思强调的实践观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并非意味着单纯的理论分析研究,而是对自己的研究承担起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并将自己投入政治的角斗场,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智慧,成为自身理论“忠实”的履践者。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内外张力
▲:1977年,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揭开了20世纪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争的序幕。您如何看待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张力的呢?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实际上取决于不同的研究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转型、这种转型如何重构传播系统,这些系统性的重构又如何改变个人资源的分配方式以及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环境等等。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对各种转型进行结构性的分析。但与此同时,传播也是一个由象征符号构成的系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也是人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文化研究的优势在于分析这些由象征符号构成的世界的组织形式,分析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图像、声音来生产和创造意义,大量的民族志研究分析了这些象征符号如何参与并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并非是竞争性的关系,而是在不同层面针对不同研究议题所进行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整体的过程,它定义了文化生产和社会行为发生的环境,是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能揭示出这样的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或者人们对此做出何种反应。例如在对迪斯尼的公司战略进行结构性的研究过程中,理解这些战略对文化生产方式决定性的影响,并不能帮助我们准确地预测出迪斯尼下一部具体作品的名称。后者涉及文化生产过程中大量的协商,而这恰恰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领域。总之,如果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的是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结构性的整体分析,那么文化研究学者更多地聚焦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两者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只是研究议题不同罢了。
▲:作为西方学术界两次大规模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争的亲历者,您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作为亲历者,我还写了很多论文来阐述我之前所谈到的观点,即没有必要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区别扩大并极化,因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研究过程。我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争论时期的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注),不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在大学中都是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就拿文化研究举例,那时候,文化研究学者还正在努力让文化研究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竭尽所能使之学科化,进而区别于已有的文学、语言学、电影学研究。要做到学科化就必须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最后,文化研究赢得了这场学科化的战役,但究其实质,这场战役并非是一场关于建制新的学科的战役,而是一场对大学教育资源的争夺战。文化研究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学科,这个结果对其研究是富有积极成效的,但代价却使文化研究通过缩紧学科边界与其他研究领域彻底“分道扬镳”,文化研究学者不再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学研究学者进行交流。
新兴研究领域在大学中建立自己的学科和院系的需求,在那一时期达到了顶峰。诚如这次争论的主将之一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所言,在那个迫切的需要学科化、制度化的时期,大辩论实际上是围绕着大学资源的分配而进行的对话语权的争夺。我个人一直致力于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导致了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关系,但我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并非文化研究的敌人,恰恰相反,它为文化研究在洞察人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语境。
在英国,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了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危机使英国政府被迫从公共财政中拿出大量的资金来支持银行系统,如此一来,政府就没有钱投入到像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这种非商业性的公共事业之中。政府的这种“紧缩政策”(austerity policy)极大地加速了英国文化产业的商业化进程,并对普通民众文化资源的近用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者要了解英国文化,首先就得了解那次经济危机以及其他通过文化和经济系统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作为文化研究学者,同样需要关注经济及其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们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很多文化研究学者开始将上述准则付诸实践,因为经济因素的作用太过明显,以至于无法忽视。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敌对”时期似乎也早就过去,因为文化研究已经确立了其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如此便可适当放宽自己的边界,从而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的对话。
▲:如果我们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争视为存在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外的张力的话,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内部是否也存在着一种二元张力,即北美研究路径和欧洲研究路径之间的差异性?
●:这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北美研究路径强调宪法规定政府不能以任何法律形式限制个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在没有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由市场的充分竞争,因为市场才是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观点在美国影响颇深,直到18-19世纪,国家才对出版进行部分的审查和控制。在新媒体盛行的时代,由于传播通信在民主生活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且提供了个体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所必需的所有信息,因而同样需要政府相应的管制(regulation)。总体而言,北美研究路径凸显了市场的重要性,而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
在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政府在资助非商业性的传播事业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传播。政府通过税收支持公共传播事业,使其相对独立于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为民众提供公共广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以卫星为基础的有线电视的出现才发生改变。欧洲的传统是,国家不仅仅要对资本市场进行管制,同时还需要利用税收为非商业性的公共传播事业提供资金的扶持,如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公共广播等。这些公共事业对文化多样性而言异常重要,在批判学者看来,这更是一种有效地抵制商业化的机制。在英国,所有的公共广播,比如BBC国内频道是不允许播放任何广告的,因为在商业化广播机构看来,受众是商品,传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激发受众的购买行为;但公共广播却将受众视为公民,当作有责任且为社会作贡献的一员来看待,所以这两者道德哲学的基础是迥然相异的。其中心便是,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关注公共机构的社会角色,而北美则更加注重市场机制以及政府对市场实行有限的管制。
四、作为实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套理论、是一组方法,更是一种开放的学术实践。大多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既是研究人员又是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媒介民主化、传播的发展、独立媒体及其全球覆盖等,如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的“自由新闻界”(亦被翻译成“自由媒体”,Free Press)和“网络中立化”(network neutrality)运动。您是如何理解作为实践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
●:就像我之前论述的,政治经济学与道德哲学联系甚密,比如亚当·斯密,他其实是哲学教授,而非政治经济学教授。所以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来说,经验事实和道德评判其实是无法彻底分离的。如果在经验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发现在信息的供给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那么他们就有道德责任去介入这个情境,并尽力纠正问题。这几乎是所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同的行为准则,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必须跟随自己分析的逻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举三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关于全世界媒介改革中对调查性新闻的保护。在美国,报纸岌岌可危,尤其是地方性报纸,几乎每天都在消失。对于剩下尚且存活的报纸,如何维持它们的新闻生产成了一个难题。而调查性新闻又是所有新闻形式中成本最高的一种,因为它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这让报纸中调查性新闻的数量与日俱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窘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麦克切斯尼主张,专注于调查和监督权力滥用的调查性新闻是一种“公共产品”,从本质上来说,它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就可以由公共预算来支持和维系它的生产。这是学者介入如何使用公共预算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二个实例是目前在互联网上非常流行的一种经济,我把它称之为“礼物经济”(gift economy)。这种经济常常是由一群人聚在网上进行创作,其成果为大家免费共享,比如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却又纯粹是通过人们的志愿性劳动创建起来的。比如,我编写了一些知识在网络上进行分享,希望这些知识能对他人有所帮助;但与此同时,我也将他人定位于“潜在贡献者”的角色,即希望他们也能编写一些他们熟知的内容从而使我或者他人受益,这就是所谓的“互惠性”——礼物经济最根本的特征。礼物经济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对开源期刊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
第三个实例是众筹在出版方面的一些有趣的尝试。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倡议下,新西兰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为低收入家庭儿童众筹图书的运动。他们鼓励民众纷纷捐款,并用这些钱款印制一些专门的教科书,免费发放给贫困的孩子。这些都是人们希望在商业化系统之外进行资源再配置的有益尝试。
▲:目前有大量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关注阶级、社会性别、劳工问题等议题。对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如制造产业中流水线上的操作女工)的人文关怀,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实践性的具体表现呢?
●:是的,学者们会朝着自己最感兴趣并擅长的方向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对特定阶级、性别、族裔人群的研究,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广泛关注,并在实践中,为他们谋求实质性的改善而奔波劳碌、栉风沐雨。我个人比较关注传播的物质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近些年来互联网的新发展——物联网所带来的,比如无人驾驶汽车以及通过传感器将物品联系起来的技术手段等等。在目前复杂的传播系统中,这种“交流性机器”(communicative machines)相比过去,其作用愈加重要。那么它们的物质性又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沿着生产链进行回溯,就像马克思曾对斯密做过一个伟大的批判——我们应该远离市场中随处可见的东西,去找寻那些隐藏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可见因素。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物联网产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这些产品从哪来,用什么材料制成——只有回到工厂,甚至回到矿场,才能对上述问题“正本清源”。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愈加恶化的气候条件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而高科技产品对环境的实际破坏力是不容小觑的。很显然,我们曾经认为自然是取之不竭的想法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生态议题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中。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仅是对劳工剥削的历史,同样也是对自然剥削的历史。因此,仅仅关注个体性、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研究环境的可持续性,因为一个“善治”的社会势必是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问题是我最关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议题,可能也是未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除了阶级、社会性别、劳工问题等议题之外新的学科增长点。与此同时,我也将为环保事业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先行者,您是否可以寄语中国年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中国目前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实验室”,因为中国正在引入强大经济发展动能的同时,却保持着强有力的国家导向,这是之前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壮阔景观。所以对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土壤上有着大量独特而有趣的案例可以进行研究。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很可能带有预设和偏见,我认为西方学者应该把中国问题留给中国学者自己去分析和研究,他们定会给我们带来启示与惊喜。■
姚建华 李兆卿/姚建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李兆卿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