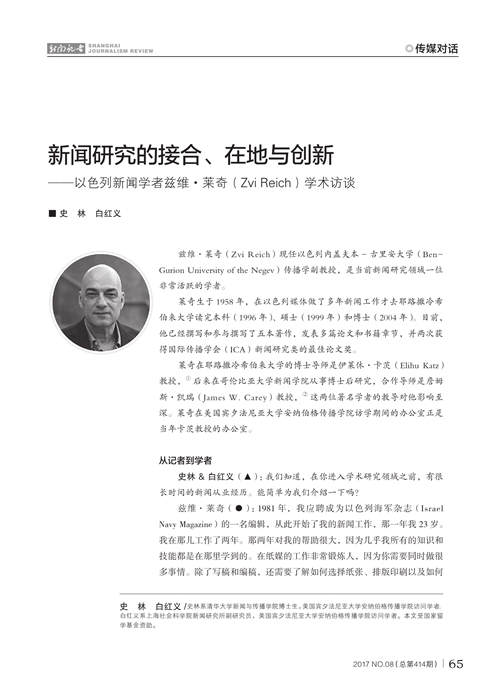新闻研究的接合、在地与创新
——以色列新闻学者兹维·莱奇(Zvi Reich)学术访谈
■史林 白红义
兹维·莱奇(Zvi Reich)现任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Ben-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传播学副教授,是当前新闻研究领域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
莱奇生于1958年,在以色列媒体做了多年新闻工作才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读完本科(1996年)、硕士(1999年)和博士(2004年)。目前,他已经撰写和参与撰写了五本著作,发表多篇论文和书籍章节,并两次获得国际传播学会(ICA)新闻研究类的最佳论文奖。
莱奇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博士导师是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教授,①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教授,②这两位著名学者的教导对他影响至深。莱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学期间的办公室正是当年卡茨教授的办公室。
从记者到学者
史林 & 白红义(▲):我们知道,在你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前,有很长时间的新闻从业经历。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兹维·莱奇(●):1981年,我应聘成为以色列海军杂志(Israel Navy Magazine)的一名编辑,从此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那一年我23岁。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那两年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几乎我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是在那里学到的。在纸媒的工作非常锻炼人,因为你需要同时做很多事情。除了写稿和编稿,还需要了解如何选择纸张、排版印刷以及如何做经营发行。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不能把新闻实务最根本的技能丢掉,于是我跟着杂志社里很有资历的老记者学习新闻摄影、如何写头条、如何起标题等,我的新闻采写能力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两年后,机缘巧合下我被业内同行推荐到《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h)工作,成为一名资深编辑。自20世纪70年代后,《以色列新消息报》成为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被称为以色列“第一大报”。我在那里工作了整整15年(1983-1998年)。其间,每两到三年会轮换到不同的岗位,也因此得以了解不同新闻类别的写作风格。
从事新闻工作的十多年间,我一直视自己为学生,因为我知道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而且你还要适应瞬息万变的媒介环境。我所习得的摄影、排版印刷、出版发行等技能让我颇为受益。直到现在教授新闻采写课程时,我都会告诫学生们,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保持一颗求知若渴的上进心十分必要。
▲:是什么原因驱使你在从事多年新闻工作后转而攻读学位?
●:故事发生在我35岁那年。有一天,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我,我已经在报社工作了12年,却一直没休假。我被告知有一整年的假期。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之余还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新闻学。我想,何不用一年的时间专心学习,完成我的学业呢?于是我用接下来的时间修完了学分,获得了本科学位。我渐渐发现,我很享受在学校里读书思考的时光,于是在本科毕业后接着申请攻读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硕士学位。其间我被任命担任报社的一个重要职位。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兴趣已经转向学术研究,我决定放弃工作全身心投入学习。在我38岁时,我从工作了15年的报社辞职了。
技术、实证与治学
▲:你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消息来源的,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研究?它的创新之处或者说贡献是什么?③
●:一直以来我对新闻业的技术使用问题很感兴趣,具体来说,我想考察新媒介技术是如何介入记者与信源之间的关系的。我记得197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记者十分倚赖电话与信源联系,但不同领域的记者拨打和接听电话的侧重是不同的。研究提到,从事政治新闻报道的记者更多地向外拨打电话,而从事社会新闻报道的记者更多地接听电话。这个研究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我从事新闻工作的1980年代正是新技术在新闻业的萌芽时期。技术对新闻编辑室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个改变是传真机的应用,这在当时的以色列非常普遍。记者们不必在报社工作,他们可以在家写完稿子用传真机传到报社,新闻编辑室一下子空空荡荡很是冷清。还有一个现象是传呼机(pagers)的普及,有时候一个记者拥有好几个传呼机,便于和不同的信源联系获取新闻线索。
人们对新技术的到来津津乐道,特别是对技术对记者劳动力的解放大加赞赏。当时最直观的感受是,互联网、电子邮件等新技术越来越多地被新闻编辑室采用,如此一来记者们不必像从前那样直接赶到事件发生地就可以获取足够的消息来源。现实情况果真如此吗?但那时候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来解答这个问题。鉴于此,我在研究消息来源与媒介技术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归纳出一种量化的研究方法,并在之后的研究中被反复使用和验证。④近几年,这一研究方法逐渐被学界认可,很多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士、瑞典等)的高校邀请我去做讲座或开办工作坊,教授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及研究员的培训。
▲: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研究和其中有意思的发现吗?
●:我在2006-2007年间做了一项关于传播技术对记者获取信源的效果研究。⑤选取了以色列包括报纸、广播和在线新闻网站在内的9家媒体机构,分别从中抽取一定数量的记者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为了确保访谈的成功率,通常我会找一个中间人帮我联系访谈对象,如此一来,90%的记者接受了我的采访,为我节省了相当多时间。
在访谈前需要完成的工作:第一,在所有新闻报道领域中随机挑选10类。第二,收集访谈对象的新闻作品,最好选取其近一段时间内的作品,以保证访谈内容的准确性。第三,每个访谈对象随机抽取10部作品。
在传播技术的选择上,主要考察直接渠道(包括身处新闻事件发生地和面对面采访)、口头渠道(包括使用电话和手机)和文本中介渠道(包括使用互联网、邮件、传呼机、传真机、邮寄、文件、短信和档案)这三种方式在记者新闻发现和新闻采集两个阶段的使用情况。访谈期间,我给每一个访谈对象展示我所选取的新闻作品,针对每一篇报道询问他们当时获取信源采用的不同渠道。
有意思的是,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观感知并不一致。研究发现,报纸、广播和网站在使用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的差别并不显著。媒介技术的确在记者进行远程新闻报道(distant coverage)获取信源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基本上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先通过口头渠道获得,然后再借助其他技术手段加以补充。但是,尽管记者已经普遍使用互联网来收集信息,他们却极少将互联网上的信息视作消息来源,甚至连网站记者也是如此。因此,媒介技术的使用与消息来源的获取之间并非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你的博士导师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教授是著名的传播学家,但你的论文偏向于新闻研究,他对你的指导和帮助主要在哪些方面?
●:虽然我的研究兴趣与卡茨的领域不尽相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我记得第一次与他交流博士论文选题时,他并没有多做点评,而是给我列了一个阅读书目。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之前认为的好的想法早已被别人研究过了,甚至比我的想法还要全面和深入。第二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把新的想法告诉他,他多了几分兴趣,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这样,我的选题在与他反复沟通和一问一答中不断完善。我想这就是卡茨培养年轻学者的方式:他会通过发问让你知道什么是好的想法,什么是不好的、不够新颖的,并教导你如何独立思考。
我对卡茨的钦佩之处还在于他的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修改我的博士论文时,会把每个章节都打印出来,逐行逐句修改。在数据分析的章节,他甚至在纸上勾勾画画,把我的数据结果重新计算一遍,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直至今日,卡茨对我的指导让我依然受用。
▲:能跟我们谈谈你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的经历吗?
●:2004年博士毕业之后,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欣然接受。院长和同事们都鼓励我出国深造,我便着手寻找机会。2005年,我独自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开展博士后研究项目。哥大的教学资源十分丰富,我尽量多地去上课、参加讲座和研讨会。其间,我结识了罗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⑦克里斯·安德森(Christopher W. Anderson)、⑧卢卡斯·格雷夫斯(Lucas Graves)⑨等一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学者。当时我们几个人每周二从哥大坐地铁到纽约大学旁听社会学和新闻学的课程。新闻学院十分注重学界和业界的互动,经常邀请美国(特别是纽约当地)新闻媒体机构的从业人员举办讲座,因此可以了解美国新闻业最前沿的变革。除此之外,我还选修了其他学院的课程,如商学院的媒介管理学等。我在哥大的时光忙碌而充实,知识体系也不断丰满,它给我更多的启发在于,学术研究要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
新闻的实践、知识和专业性
▲:目前你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哪几个领域?
●:一直以来我都在关注新闻生产的问题。新闻何以成为新闻?新闻内容生产过程中,消息来源、技术和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另外,我的兴趣还在新闻的作者和署名问题(authorship and byline)上。⑩近几年,算法新闻成为新闻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它是指运用算法对数据自动加工生成完整新闻报道的计算机程序。这些机器人新闻写手的出现,为新闻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我更关心其中的新闻伦理和法规问题。[11]一篇算法新闻如何署名?谁将授权给新闻机构进行数据抓取?倘若一篇算法新闻引发争端,谁来承担具体的法律责任?当我们拥抱新技术为新闻业带来的改变时,研究者需要思考更深层的问题。
除了上述两个方向,我目前更关注新闻业的知识性(knowledge)和专业性(expertise)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新闻业一直遭人诟病,公众认为新闻写作是单纯的事实记录,无所谓“专业性”。但我认为,新闻业也有其专门的知识,从碎片化的事实材料到完整的新闻报道,其生产逻辑也是一门知识和学问。记者在写作任何一篇新闻时他都要思考,究竟怎样的事实组合和材料拼接才能让一篇新闻被公众认可。好比餐厅里的服务员,在他从厨师手中接过新鲜出炉的饭菜时,他就变成了顾客和饭菜之间的传播者,他的任务是如何让顾客接受并喜欢这道菜。记者正如服务员一样,是“互动的专家”(interactive expert)。[12]目前我的研究侧重于如何发掘新闻业中的专业性和知识,进而采用何种方式去测量。
▲:提及新闻专业性的问题,你在去年提出了一个“新闻专业性的辩证模型” [13](图1 图1见本期第69页)。能阐释一下你对当下新闻业或新闻工作者专业性的认识吗?
●:新闻专业性这个提法在学界的认知中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记者在报道某一领域时对该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其二是之于新闻实践而言的新闻专业主义。我更关注第一个层面的专业性,因为它最终塑造了记者和新闻受众之间的知识传递。
新闻专业性一直是专业知识和新闻专业主义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还受到多方力量的制约(行业内主要受记者自身、编辑、上司和同行的制约,行业外则受到其他组织机构、行业专家和受众的制约)。据此我将形塑新闻专业性的力量归纳为五个独立的连续统,每个连续统都有其内在的张力,都在强专业性与弱专业性的抗衡中实现辩证统一。这五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分别是:(1)组织层面,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对立;(2)议题层面,专业领域与一般领域的对立;(3)互动层面,专家与受众的对立;(4)认知层面,专业性与责任感的对立;(5)知识层面,本质的专业性与附属的专业性之间的对立。
整体来看,近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组织等方面的变迁,新闻专业性朝着更少的专业性、更多的形象维护方向转变。在可预见的未来,记者的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对抗会一直持续下去,与其哀叹行业的衰退,不如思索应对非专业性趋势的策略。
新闻研究的未来
▲:在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业界认为学界的研究对他们没有帮助,指责很多新闻学院的老师缺少从业经验,有时候没有与他们形成共同体。学界则认为业界的很多事情做得不好。以色列的情况是怎样的?你怎么看待新闻研究和新闻实践之间的关系?
●: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沟通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以色列也不例外。例如,学界认为新闻的本质是建构现实而非还原现实,但新闻从业者显然不以为然,因为这与他们所坚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学界与业界的冲突在于,他们经常划分出明确的边界以显示各自的专业性。有时候,学者们会使用一些晦涩的学术语言去评判新闻业界的变化,这更不利于学界和业界的沟通。我们应该看到,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是反哺共生的关系,新闻研究总在新闻实践之后。近年来,新闻行业受到公关、广告的冲击,整体呈现衰退的趋势,而这也导致新闻研究产生了低谷。最直观的感受是,各大高校的传播学院里,与新闻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少。
就我个人而言,新闻实践与新闻研究的关系就像是“带线的风筝”。一方面,它将你与现实相连,让你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思考问题能否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你的放飞,阻碍了你在学术思考中的理论想象力。
▲:你对新闻业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
●:未来的一年将是新闻业的危机年。毋庸置疑,新闻业对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公众的质疑。一方面,广告公关宣传近几年大行其道,他们用大量的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使得新闻业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新闻实践中无法避免的报道失实,使得新闻业整体的形象大打折扣。这在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中可见一斑。在美国总统辩论阶段,希拉里呼吁媒体在对特朗普的报道中进行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让人觉得事实核查只是民主党的事,与共和党无关。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被右翼媒体予以回击,这样一来,反而提高了右翼党派的媒体曝光度,却同时降低了自身的可信性,被人们戏谑为“特朗普的免费广告”。公众质疑媒体的真实性,令新闻业的处境堪忧。
而另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业也展现出其多样性。这主要表现在计算机算法的使用和可视化的呈现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模式。未来的新闻生产应该朝着提供更持续的而非片段式的、更私人定制化的、更能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的信息方向发展。
但是,无论新闻业如何变迁,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而言,在进行新闻报道时要尽力做到客观公正。我在2016年出版的小册子《新闻室中的怀疑论者》[14]中提到,记者在写作时要持有怀疑精神,扪心自问四个问题:我收集到的信息是准确的吗?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吗?数据、研究方法和结论是真实有效的吗?我的写作是合乎规范的吗?
▲:在当下从事新闻研究,你在方法、理论等方面有何建议?
●:与传播学研究相比,新闻学研究还很年轻。国际传播学会(ICA)中成立新闻研究分会(Journalism Studies Division)仅有十几年的时间。近几年,新生代学者层出不穷,为新闻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大部分是获得博士学位后直接进入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因而缺少一定的从业经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但他们理论知识扎实且广博,能将其他领域的知识输入到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他们有很强烈的自省意识,勤于思考,这对学者而言至关重要。值得警惕的是,和其他学科一样,新闻研究也存在美国一家独大的问题,这受制于英语语言的主导性地位。对非英语国家的新闻业、新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学者们也应予以关注。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最普遍的是内容分析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最直观有效地对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未来的内容分析方法将会朝着更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操作发展。比如以往是搜集传统媒体上的新闻进行分析,如今则越来越多的从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抓取数据来分析。在类目建构上,借助大数据分析方法,如社会网分析和语义网分析等,能够发现更多更有意思的变量。■
①⑥Elihu Katz(1926-),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
②James W. Carey(1934-200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③这篇博士论文已出版,参见Reich, Z. (2009). Sourcing the news: key issues in journalism--an innovative study of the Israeli press. Hampton Pr。自从1973年Sigal的《记者与官员》(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出版以来,关于消息来源的研究一直是新闻社会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在笔者看来,Sourcing the news是近年来这个领域较有新意的一本著作,另一本是Matt Carlson关于匿名消息来源的研究,参见Carlson, M. (2011).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Unnamed sources and the battle for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④这一方法最早在莱奇的专著Sourcing the news中使用,他在2016年出版的《数字新闻手册》中发表了一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的文章。参见Reich, Z.& Barnoy, A. (2016). Reconstructing production practices through interviewing. In T. Witschge, C. W. Anderson, D. Domingo& A. Hermida (Eds.)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pp.477-493). London: Sage.
⑤有关这一研究的具体内容,请参考原文:Reich, Z. (2008). The role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obtaining news: Staying close to distant sourc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5(3)625-646.
⑦Rodney Benson,现为纽约大学教授,著有Shaping immigration news: A French-American compari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他与艾瑞克·内维尔(Erik Neveu)合编的《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2017年3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⑧Christopher W. Anderson,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现为纽约城市大学副教授,2017年秋季将转任英国利兹大学教授。著有Rebuilding the news: Metropolitan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age. Temple University(2013)。
⑨Lucas Graves,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现为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著有Deciding what's true: Fact-checking journalism and the new ecology of news. Columbia University(2013)。
⑩Reich, Z. (2010). Constrained authors: Bylines and authorship in news reporting. Journalism, 11(6)707-725.
[11]MontalT.& ReichZ. (2016). IRobot. YouJournalist. Who is the Author? Authorship, bylines and full disclosure in automated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1080/21670811.2016.1209083.
[12]Reich, Z. (2012). Journalism as bipolar interactional expertise. Communication Theory, 22(4)339-358.
[13]Reich, Z.& Godler, Y. (2016). The disruption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 In C. Peters & M. Broersma (Eds.)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pp.64-81). London: Routledge.
[14]Reich, Z & Godler, Y. (2016). The Skeptic in the Newsroom: Tools for Coping with a Deceptive World.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 and Am Oved (Hebrew).
史林 白红义/史林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白红义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