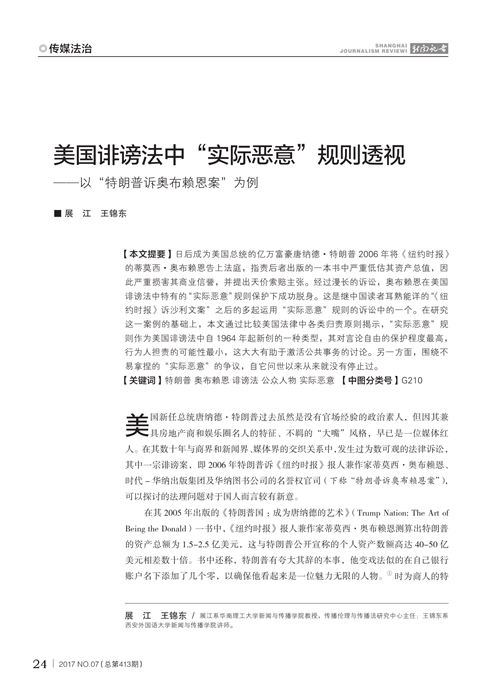美国诽谤法中“实际恶意”规则透视
——以“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为例
■展江 王锦东
【本文提要】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亿万富豪唐纳德·特朗普2006年将《纽约时报》的蒂莫西·奥布赖恩告上法庭,指责后者出版的一本书中严重低估其资产总值,因此严重损害其商业信誉,并提出天价索赔主张。经过漫长的诉讼,奥布赖恩在美国诽谤法中特有的“实际恶意”规则保护下成功脱身。这是继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后的多起运用“实际恶意”规则的诉讼中的一个。在研究这一案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比较美国法律中各类归责原则揭示,“实际恶意”规则作为美国诽谤法中自1964年起新创的一种类型,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最高,行为人担责的可能性最小,这大大有助于激活公共事务的讨论。另一方面,围绕不易拿捏的“实际恶意”的争议,自它问世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关键词】特朗普 奥布赖恩 诽谤法 公众人物 实际恶意 【中图分类号】G210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过去虽然是没有官场经验的政治素人,但因其兼具房地产商和娱乐圈名人的特征、不羁的“大嘴”风格,早已是一位媒体红人。在其数十年与商界和新闻界、媒体界的交织关系中,发生过为数可观的法律诉讼,其中一宗诽谤案,即2006年特朗普诉《纽约时报》报人兼作家蒂莫西·奥布赖恩、时代-华纳出版集团及华纳图书公司的名誉权官司(下称“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可以探讨的法理问题对于国人而言较有新意。
在其2005年出版的《特朗普国:成为唐纳德的艺术》(Trump Nation: The Art of Being the Donald)一书中,《纽约时报》报人兼作家蒂莫西·奥布赖恩测算出特朗普的资产总额为1.5-2.5亿美元,这与特朗普公开宣称的个人资产数额高达40-50亿美元相差数十倍。书中还称,特朗普有夸大其辞的本事,他变戏法似的在自己银行账户名下添加了几个零,以确保他看起来是一位魅力无限的人物。①时为商人的特朗普认为,奥布赖恩故意将其资产数额缩水,由此带来个人声誉和品牌价值的降低,其生意也因此而受到了拖累。于是在2006年以诽谤为由将奥布赖恩告上法庭,提出索赔50亿美元的天价损害赔偿金。
向一位工薪族索赔50亿美元,这足以让一般被告和看客吓出一身冷汗。我们知道,美国法律中基本排除了刑事诽谤,表达信息和观点的人不用担心因诽谤他人而有牢狱之灾。加上《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美国人经常自诩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在高度保护商业的美国,涉及商誉的诽谤很可能引发天价诉讼,这是事情的另一面。被告一旦败诉,就可能倾家荡产。退一步说,即便最终没有败诉,高昂的律师费等开支和没完没了的时间消耗也让一般人惊悸不已。那么被告有没有救济途径呢?
了解美国法的人都知道,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新的诽谤法规则,即若原告被法院认定为“公共官员”,则必须由其来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方可胜诉并可能获得赔偿。1967年,范围更广的“公众人物”取代了“公共官员”,同样适用“实际恶意”规则。
毫无疑问,媒体红人兼地产巨头特朗普属于“公众人物”,因而,该案讼争焦点为被告是否具有“实际恶意”。诉讼过程中,特朗普也主要抓住奥布赖恩在采访中使用了匿名消息来源,以此作为主张其具有“实际恶意”的主要依据。②2009年7月15日,新泽西州高等法院女法官米歇尔·M.福克斯在即决审判(summary judgment)③中判定,原告特朗普无法证明被告具有“实际恶意”,驳回了特朗普的请求。特朗普不服即决判决,向新泽西州上诉法院上诉,州上诉法院法官经审理后认为初审法院的裁定正确,2011年9月7日驳回特朗普的上诉。
作为一种过错标准,“实际恶意”究竟有何内在的涵义?本案中的被告使用消息来源构成“实际恶意”吗?特朗普的诽谤案又向人们展示出“实际恶意”规则的哪些特点?本文带着这样的疑问,尝试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案情和判决
被告奥布赖恩(1961-)毕业于乔治城大学文学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新闻学和MBA三个硕士学位。其新闻生涯起步于《国家地理》杂志,后转入《纽约时报》。作为多能记者,他的报道领域和对象包括:华尔街、俄罗斯、曼哈顿艺术世界、网络犯罪和身份盗窃、巴菲特、地缘政治、国际金融、数字媒体、好莱坞、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财源、洗钱、赌博和白领欺诈。2006年任《纽约时报》商业组主编。2011年转任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的执行主编。现任评论网站彭博视界(Bloomberg View)的发行人和编委。④
奥布赖恩对特朗普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在1992年当过特朗普传记作家韦恩·巴雷特的研究助理,1998年撰写过美国赌博业的材料,2004年为《纽约时报》报道过特朗普公司的财务危机,其中谈到估算特朗普财产很有难度。在当年8月与人合作的报道中,他提到特朗普自称其资产总额为20-50亿美元。但奥布赖恩也写道:根据知情的3个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特朗普继承的资产比重较大,如果不考虑高额债务,资产总额应为2-3亿美元。这与亿万富翁俱乐部的身价虽有差距,但在普通人眼里已经是巨资了。⑤
2004年12月,奥布赖恩与时代-华纳出版集团签订了出版《特朗普国》的合同,其中包括对特朗普本人及其法务、财务人员等的访谈内容,并再次采访那3个匿名消息来源,后者再次降低了对特朗普资产数额的评估,认为特朗普的资产为1.2-2亿美元。2005年10月3日,奥布赖恩将对3名匿名消息来源的采访报道刊出。其中,奥布赖恩详细报道了特朗普不断变化的财富,也道出了他试图搞清楚特朗普究竟有多少净资产时遇到的困惑。
奥布赖恩引用《华盛顿邮报》2004年9月9日的一篇文章称:事实上,我们很难准确知道特朗普在赌场生意中所持有的股份,因为特朗普的大部分投资组合是在那些不对外公示其所得的私人公司里。他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亿万富翁”,但是谁知道呢?有些怀疑者认为特朗普最多只有3亿美元。而众所周知的是,他喜欢炒作自己。更早之前,2000年4月3日刊登于《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写道:特朗普在那些精心设计的骗局里玩得不亦乐乎,他极其顽固地热衷于质疑或颠覆别人对某人真实财富调查评估的认真努力。他曾对采访者说:“将事情做得滴水不漏、难以捉摸是极好的,因为这样就没人能真正搞懂内幕。” ⑥
《特朗普国》中描述,特朗普的职业生涯初始阶段结束时负债9亿美元,与银行交易时调整了这笔债务。然后描述了特朗普的露面和消失,以及再次露面是作为全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之一登上了福布斯年度榜,并称他不择手段登上榜单。文中说估计2004年特朗普有26亿美元,居第189位。
事实上,特朗普本人及其工作人员对其资产总额的说法也扑朔迷离。在奥布赖恩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特朗普称他有40-50亿美元。那天晚些时候,特朗普说,他的赌场约占他财产的2%,这部分的净值为17亿美元。而在特朗普公司的宣传小册子里称,特朗普的财产是95亿美元。特朗普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艾伦·魏塞尔伯格告诉奥布赖恩,特朗普的资产有60亿美元。他随后又说,财产清单中有不属于特朗普的部分,可能有50亿美元,还承认有些资产难以找到证据支撑。⑦
尽管奥布赖恩获得了所谓“史无前例”的特权,即特朗普给奥布赖恩提供了较多了解其财产数额的机会,但实际上仅仅是特朗普圈定好的内容。那些特朗普自称提供给奥布赖恩的资料是不完整且未经审计的,而且也不包含特朗普个人当时及未来财产、债务、收益的准确信息。特朗普则表示:奥布赖恩明知他拥有曼哈顿西区的数处房产,却在《特朗普国》中谎称他并不拥有这些资产。但是,证据显然表明,特朗普是与来自香港的普通合伙人共同拥有这些资产的,尽管他在证词中极力夸大这个数字,而他只持有30%的股份。因此,所有存在的实际争议不过是就“所有权”而玩的文字游戏。
另外,奥布赖恩从一份已公开的记录中得知,在特朗普与香港商人合作的项目中,后者对这份资产的售卖有绝对处置权。在港商以17.6亿美元将其售卖之后,特朗普入禀法院,对他们提起了诉讼,称由于他们对此房地产价值的低估而损害了他的收益。其实特朗普的实际收益也是不明的,因为他并未对外公布这些资产负债情况。
一边是奥布莱恩意欲调查清楚特朗普的确切资产数目,一边是特朗普巧舌如簧、闪烁其辞的惊人本领。当特朗普说他持有广场酒店10%的股份时,其实际意义是:如果饭店被卖掉,他能获得10%的收益。当他说他正在联合国大厦旁建造一座90层的高楼时,其实他盖的是一座有超高楼顶的72层的建筑。
在此情况下,奥布赖恩四处寻找答案,其中三个匿名消息来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三人已为特朗普工作多年。他们透露了在奥布赖恩看来较为真实的信息。于是在形成的文字中推算特朗普的资产应为1.5-2亿美元。文章的这部分也提到,特朗普对这个数据予以否认。
另一争议是:奥布赖恩是否在2005年4月21日与特朗普手下一起参加的会议中做了记录?特朗普的两位手下都否认有会议记录,他们说,他们没有回忆起有关会议记录的事情。法院认为,退一步讲,即便这个疑义确实存在,也不能成为特朗普指控奥布赖恩存在“实际恶意”的支持证据。
特朗普说,奥布赖恩曾声称他对特朗普的工作人员汇编的他的财务资料并无兴趣,因为奥布赖恩的书已经完稿了。特朗普还就奥布赖恩的调查助理约瑟夫·普兰贝克的言论做了补充,说约瑟夫自称只是调查了特朗普的某个项目,而奥布赖恩则称约瑟夫对特朗普房地产价值做了充分、大量的调查。特朗普认为二者的话是矛盾的和有误的,也坚信奥布赖恩的调查是不充分的。
特朗普称,奥布赖恩曾承认他那远远超过“可口”和“百事”的特朗普大名是无形财富的论断是不正确的。经法院核实这句话其实出自特朗普本人之口,见于《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的某篇报道。
特朗普反对奥布赖恩对于即决判决的提议。他说,他有足够直接且详尽的证据证明,奥布赖恩明知其消息来源所提供的关于其净资产报告的信息是错误的,可他却全然不顾这些情况,这明显不能作为支持陪审团裁决的证据,也不足以为即决判决提供参考。他称奥布赖恩故意避开了能说明其真正净资产的证据,且奥布赖恩的出发点存在恶意。
特朗普认为,奥布赖恩不当地忽略“特朗普”这一大名鼎鼎的名誉资产。法院驳回此说。因为特朗普的会计师们在2004年的资产情况报表中承认:根据普遍接受的财会准则,“名誉资产”并不包括在个人净资产之内。
特朗普还提出,就在《特朗普国》出版前三天,奥布赖恩曾在一篇文章中承认特朗普名下的赌场出现(收益)反弹。可是这种论断本身并不能证明“实际恶意”的存在。而且,很难要求在一本已经付梓、即将发行的书中写进资金状况较之前更可观这一说法,或者说将该书部分内容重新修改。
特朗普补充说明称,在拿到《特朗普国》预售本之后,他与律师曾警示过《纽约时报》商业组主编,此书有明显的不实之处,而主编也与奥布赖恩讨论了此事。尽管如此,该书还是照旧出版了。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该书是否存在不实之处,而是该书作者是否带有“实际恶意”的诽谤言论。特朗普写给《纽约时报》商业组主编的那些信中并没有特意明确指出奥布赖恩言论的错误或问题。
法官认定:涉案的内容不存在与匿名消息来源明显不符的情况,与那些被认定为“可靠”的信息也不矛盾,这为判定是否为“实际恶意”提供了依据。上诉法院查明,奥布赖恩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的严重失实程度,或者他严重怀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很明显,特朗普的论断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奥布赖恩追踪调查报道他已经很多年了。因此,即便他发表的东西中确实有错误不实之处,奥布赖恩的“错误”最多只能被认定为疏忽大意,而不能判定为“实际恶意”,所以对被告的控告不成立,判决同样适用于其他被告即图书出版商。⑧
二、何为“实际恶意”
1964年里程碑式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了“实际恶意”规则,改写了美国诽谤审理中的归责原则。执笔“《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意见的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将“实际恶意”定义为“明知其言虚假或罔顾其言是否虚假”(with knowledge that it was false or 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的心理状态。⑨拆分开来看,“明知其言虚假”是指被告明知发表的内容不真实却依然发布,相当于说谎;“罔顾其言是否虚假”是说,行为人发布信息时,“很大程度上意识到该材料可能是虚假的”,或者“很大程度上怀疑材料的真实性”。⑩作为一项诽谤法中全新的规则,美国联邦法院以一系列的判决形成了以原告身份类型为主和议题类型为辅的审理方式,体现了言论自由优先的价值选择,适用于诽谤法领域。[11]“实际恶意”规则除了实体上增加了“明知其言虚假或罔顾其言是否虚假”这一要件,从程序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被告证明真实转变为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陈述的虚假事实具有“实际恶意”,而且证据需要达到明确的和有说服力的程度。这种改变使得“公众人物”原告在诽谤官司中极难胜诉,显著拓展了言论自由的空间。由于此番革新援引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恶意”规则又被称之为一项宪法特权,即实现了“诽谤法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defamation law)。[12]然而,这一规则的内涵及其边界并不那么清晰易懂。“实际恶意”规则包含的“明知其言虚假”意义相对明确,即只要原告能证明被告说谎,就可被确认存在“实际恶意”,真正难以判断的是“罔顾其言是否虚假”。事实上,自“实际恶意”规则确立以来,在学理和实务上,对“罔顾其言是否虚假”的内涵及具体运用,还有一定的模糊和争议之处。最初,这项重要规则实体上的意义就是这样简单表述的。美国法作为判例法,只能通过“《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后的审理逐渐加以清晰,外界对该规则的理解也随这些个案不断深入。
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实际恶意”规则的内涵第一次解释,该案判决中关于“实际恶意”规则大体包含的要旨有:(1)“实际恶意”系关于被告的心理状态;(2)单纯未加查证并不足以证明具有“实际恶意”;(3)被告相信所言为真的理由如“合理”,可帮助判断不构成“实际恶意”。[13]“实际恶意”规则意味着,法律保护诚实的错误。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被告《纽约时报》刊登的涉案广告内容存在失实之处,包括:学生们在议会厅前唱的是国歌《星条旗永不落》,而不是《我的国也是你的国》;警方确实在校园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但并未“包围”学生、试图以饥饿威胁学生就范;马丁·路德·金曾经4次被逮捕,而不是涉案言论中的6次,等等。[14]而在新闻报道和著述中,记者、媒体和作者对消息来源的倚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考察被告具体如何使用消息来源,往往是判断是否存有“实际恶意”的重要依据。在“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中,被告使用匿名消息来源是否具有“实际恶意”成为法院审理中的焦点所在。
在美国诽谤法史上,第一宗被判定存有“实际恶意”的案例是1971年的“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该案原告沃利·巴茨(1905-1973年)为前橄榄球球员,佐治亚大学主教练(1939-1960年),1942年率领佐治亚大学斗牛犬队夺得全国橄榄球冠军,还4次获得东南大会冠军。巴茨被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一致认定为“公众人物”。法院认为,被告公司旗下的《星期六晚邮报》使用了明显可疑的消息来源(正在服缓刑的诈骗犯),而对其他能轻易核实相关内容真实性的重要证据(比赛录像)没有做出简单的查对,也没有采访其他容易采访到的知情者。甚至有证据表明,两位主编已意识到该报道需要仔细核实,这种情形下被告媒体却没有做出以上任何应该查对的措施,从而被法院认定为存有“实际恶意”。[15]而在“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中,特朗普认为奥布赖恩应有充分理由怀疑信息的准确性和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审理中奥布莱恩证实,他在发布由3名匿名消息来源估计的财产之前对他们进行了回访,并记录了2004年和2005年两次会面的情形。在这个重要的记录中,有这3人对特朗普净资产的相似估计,还就发布时的具体数字提出了建议。参与汇编2004年特朗普资产报表的会计师杰拉尔德·罗森布鲁姆出庭作证说,他至今都搞不清楚特朗普的资产负债情况。
奥布莱恩在证词中称:他有理由相信这些消息来源提供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也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他们作为消息来源的资质与品格。奥布莱恩曾证实过由秘密消息源提供的大多数信息。事实上,奥布莱恩虽与特朗普在后者资产数额上相对立,但他并没有完全采用匿名消息源所提供的对于特朗普净资产低估价的资料。
针对特朗普根据奥布莱恩拒绝在庭审中供出秘密消息来源作为后者具有“实际恶意”的主张,法院认为:拒绝提供消息来源信息并不能推断为不存在此消息来源。同时,因为这些秘密消息来源提供的报告并不自相矛盾也没有被那些所谓可靠的消息所反驳否定,所以,根据“实际恶意”的判定标准,没有什么让奥布赖恩主观上怀疑其信源的虚假不真实或质疑信息的不准确。[16]在美国大多数州,媒体受到盾法(shield law)的保护,在诽谤法等诉讼中被告享有不透露秘密消息来源的法定权利。基于这个原因,“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的被告未向法院透露匿名消息来源的真实身份。
为了证明奥布赖恩依赖他的秘密消息来源是恰当的,被告引用了2007年的“斯普雷维尔诉纽约邮报控股公司案”(Sprewell v. NYP Holdings, Inc.)的判决。在该案中,NBA劲旅纽约尼克斯队的球员拉特雷尔·斯普雷维尔声称他被《纽约邮报》记者马克·伯尔曼(Marc Berman)诽谤,后者文章就是基于秘密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记者在报道中也称该球员否认相关事实,法院同样也未认定报道存在“实际恶意”。[17]审理该案的法院认定:事实上,记者面对不同消息来源之间的不同说法时,即便没有做进一步查证,也不能据此认定其报道存在“实际恶意”。记者在不同消息来源之间选择其中一个的说法,也不能认定为存在“实际恶意”。[18]而“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的判决进一步确认了:即便被告使用了匿名消息来源,也不能作为其具有“实际恶意”的证据。
三、“实际恶意”规则与美国法其他规则的比较
传统上,美国侵权法继受自英国,其归责原则类型可分为故意、过失及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19]在诽谤法领域,其归责原则更为丰富、复杂。除以上归责原则外,还有改写了美国诽谤法的“实际恶意”规则,及介于“实际恶意”和过失(negligence)之间的严重过失(gross negligence),按照美国权威法学家的看法,这反映了诸种归责原则的过错层级,即“实际恶意”高于严重过失,严重过失高于一般过失。[20]比较这些规则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实际恶意”的特殊意义,并了解美国诽谤侵权法领域适用规则的全貌。
自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后,一系列的判决逐渐形成了针对原告身份类别及言论内容类别的差别化的诽谤诉讼规则体系,在1974年的“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公司案”(Gertz v. Robert WelchInc.)后,基本形成了沿用至今的较为明晰的法律体系。其中,针对“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原告并涉及公共事务的言论的诽谤纠纷,适用“实际恶意”规则;针对普通人原告,以过失责任为起点。[21]针对原告为普通人的诽谤案,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标准是一般过失;而在少数州,则要求被告的过错达到严重过失的程度。[22]在“格茨诉罗伯特·韦尔奇公司案”中,联邦最高院宣布禁止各州在诽谤诉讼中适用严格责任。[23]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严格责任下,无论被告有没有尽到该尽的注意义务,有没有过错,都需要担责。这虽然最大限度地防止了错误报道的发生,但也大大抑制了传播本身。[24]普通法上的过失侵权须具备的条件是,注意义务(duty of care)的存在、(注意)义务的违反(breach of the duty)及损害(damage)的发生。[25]在诽谤诉讼中,是否存在过失以是否尽到合理查证义务为基本判断的依据。需要考虑的因素一般包括:侵害名誉权之性质的严重程度、受侵害者澄清及恢复名誉的成本、言论的社会价值及查证事实的成本。[26]在判断诽谤诉讼中被告过失与否的标准上,一般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被告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发布的内容真实,二是被告是否就相关内容做过合理的查证。[27]实务中,可证明记者未能尽到合理谨慎义务的依据有:依赖不可靠的消息来源,不阅读相关文献或误读相关文献,未能求证于显而易见的消息来源(包括原告),在编辑和处理新闻时粗心大意等。[28]而若论行为人是否尽到查证义务,这反而偏离了发布者的心理状态,无助于判断其是否具有“实际恶意”。[29]例如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被告媒体未对涉案内容进行查证,而未加查证的原因在于《纽约时报》认为言论内容并无具体的批评对象,也在于信赖某位社会声望人士对涉案内容可靠性的证明。[30]据此,可以认为媒体有过失,而不能证明其“明知其言虚假或罔顾其言是否虚假”的心理状态,也就是不能认定“实际恶意”。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中,法院认为即便被告奥布赖恩对原告财产数字调查有误,充其量也只证明被告存在过失。事实上被告记者主观上是相信知情人的信息的,部分内部描述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因而不能证明其有“实际恶意”。[31]但在判断是否存有“实际恶意”时,也可以以媒体的操作流程作为重要依据,依据其行为来判断其心理状态(state of mind)。1979年的“赫伯特诉兰多案”(Herbert v. Lando)确立了5条可资原告查证被告编辑过程的规则:
记者、编辑在调查中,关于对某采访对象继续采访还是停止采访持有怎样的结论;
记者、编辑在调查中,关于采访对象对其事实陈述的真实性的内心状态有怎样的结论;
对采访中的人或事的真实性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新闻工作者和同行或其他人对新闻材料获取、处理及刊出的交流过程,尤其是有关这些材料取舍的讨论;
这些材料取舍决定时表现出的目的。[32]需要明了的是,对媒体操作流程的检视也只是为了判断“实际恶意”所聚焦的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即通过这个流程的了解来证明媒体在操作过程中是否存有“明知其言虚假或罔顾其言是否虚假”,而不是证明其是否尽到了查证的注意义务进而确立是否有过失。
严重过失责任是一种高于一般过失的责任,是指行为人在极不合理的程度上疏忽了交往中应有的谨慎,未采取任何人在特定情形下都会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严重的不以为然。[33]在美国的诽谤法领域,联邦最高法院在“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中将严重过失表述为“高度不合理的行为,极端违反一般负责任的出版者所遵守之调查与报道标准”。[34]可见,严重过失和一般过失一样,采取的是客观化的衡量标准,其指向了行为的合理程度,意味着严重过错迥异于“实际恶意”。
相比之下,“实际恶意”只关乎被告在发布信息时的状态,即他在发布时相信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同样情境下的一般理性人会做出什么样的查证行为。[35]甚至在以往的判例中,即使报道者“编造”了受访者的引语,也未被认定为“实际恶意”。[36]事实上疏于查证也只是判断构成“实际恶意”的一个因素。
从与美国侵权法中的故意的比较看,故意包括行为人追求特定后果的发生(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引发特定后果,即便他没有追求这种后果(间接故意)。从中可见,故意包含了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有国内学者因此认为,“实际恶意”可大致视同于我国法律中的故意责任标准,[37]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实际恶意”只涉及行为人对信息真假的认知,并不包含故意所蕴含的意志因素。因此,“实际恶意”不能简单等同于故意。
事实上,在我国法中故意的内涵不但在刑法和民法上基本相同,与美国法也没有明显差别。而自美国法中的“实际恶意”规则出现以来,因其难以拿捏而一直争议不休,试想如果它真的等同于“故意”,应该没有必要另外创设这一令人捉摸不定的新规则。
“实际恶意”也完全不同于普通法中的“明显恶意”或“恶意”。不良动机本身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实际恶意”的充分条件;一个人极有可能出于不怀好意或报复说谎,也有可能基于同样的动机说出真话。但不良动机可能与其他条件总和成为判断是否存在“实际恶意”的因素。[38]一般意义上的恶意,指不良意图或坏的念头,“实际恶意”只是一种认知状态。[39]按照“《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对“实际恶意”的认定,二者区别明显。[40]特朗普声称,奥布赖恩受到坏念头(ill will)的激发而对外发布有关信息,但是即便情况果真如此,“坏念头”也并不等同于“实际恶意”。
再从与已在美国诽谤诉讼中被禁止使用的严格责任比较看,可以说两种归责体系恰恰位于天平的两端。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前的民事诽谤诉讼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无论被告在发表言论时多么谨慎地核查事实,一旦被控诽谤,则只要存在不实之处或不能以真实进行抗辩,从而需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41]严格责任意味着给行为人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也限制了传播自身;与之旨趣迥异的“实际恶意”则是说,只要行为人传播关于公共官员或公众人物的内容不是撒谎或完全不顾及其真假而发布,都可以受到宪法的保护而不必承担责任。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说,“实际恶意”作为美国诽谤法中新创的一种类型,其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最高,行为人担责的可能性最小,这极大地为激活公共事务的讨论排除障碍。回到本文所讨论的诽谤案,法院在分析了各种证据后确认,被告奥布赖恩最多存有疏忽,而根本不具备“实际恶意”,因而予以免责。
“特朗普诉奥布赖恩案”的判决援引了联邦最高法院以往涉及“实际恶意”规则判例中的观点并认为:“实际恶意”并不仅仅取决于发布内容的性质,也非被告发布者未能找到独立的核查事实的消息。[42]实际上当各种不合理的因素综合起来,就有可能被证明“实际恶意”成立。例如,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疏于查证本身不能被证明是“实际恶意”,但刻意回避真相就构成了“实际恶意”。[43]
四、“实际恶意”规则的影响简析
布伦南大法官在他主持撰写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书里称:我国曾对一项原则做过深远承诺,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44]这一划时代的宣告,是对“实际恶意”规则得以确立之法理上的有力阐释。至于该规则出台的具体考量,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都是自愿将自己暴露于更严格的公众审视之下,而且他们拥有更多的运用大众媒介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反驳诽谤性指控。而普通人没有同样的机会,因此需要得到诽谤法的更多帮助。[45]美国的影响力及由“实际恶意”规则创设后其在世界范围内相对较高的表达自由度,引起了许多国家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各国毕竟有自己不同于美国的制度背景、法律文化,因而真正全面引入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见。正如王泽鉴教授认为的,“实际恶意”规则的创设有美国特定时期的法制和时代背景,例如种族冲突严重,普通法上的诽谤沿用严格责任,以及巨额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有赖言论市场发挥其追求真理的作用。[46]可能的唯一例外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某些判决中有积极的借鉴,如在“台上字第1979号判决书”中称:倘行为人所提证据资料,可认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纵事后证明其言论内容与事实不符,亦不能令负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责任,庶几与“实际恶意”原则所揭橥之旨趣无悖。[47]而在日本,类似公共官员的名誉权案件仍适用于一般人的“真实性、相当性”法理,并未给予此类言论以明显的保障。[48]其他欧美国家,如施行普通法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大陆法的德国等,也没有在本国法中接纳或借鉴“实际恶意”规则。
即便在美国,对“实际恶意”规则也褒贬不一。首先是该规则自创设以来,其界限并不容易掌握,以至于布莱克大法官对“实际恶意”规则不以为然,认为“恶意”是一个难以琢磨、非常抽象的概念,很难通过证据证实。[49]更重要的是,理论上,“实际恶意”规则有利于媒体被告,实际上,新闻媒体仍然屡受诽谤诉讼威胁。[50]有利于被告的依据是,自“《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后,从1982年-1988年间,美国新闻媒体作为被告的614件诽谤案件中,只有10%的原告获得胜诉,33个原告获得金钱赔偿;其中由公共官员和公众人物提起的诽谤诉讼共381件,只有19件原告获得胜诉。[51]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甚至不乏误解的规则,极大改变了美国诽谤法中的被告一方,尤其令新闻媒体在对权势人物开展的舆论监督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呼吸空间”。其中的重要启示在于,“实际恶意”规则的运用使得美国媒体对政要、名流的监督得到很大的保障。试想,如果奥布赖恩是在不采纳“公众人物”和“实际恶意”原则的英国成为特朗普一类富豪的被告,会不会败诉呢?■
①②⑤⑥⑦⑧[16] [31] [42]DONALD TRUMP v. TIMOTHY L. O’BRIEN, see http://law.justia.com/cases/new-jersey/appellate-division-published/2011/a6141-08-opn.html.
③大约相当于我国法中的简易审判。即对于涉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采取的审理方式,此类案件应当在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④参见http://timothylobrien.c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othy_L._O%27Brien。
⑨[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88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97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王泽鉴:《人格权法》第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23]吴永乾:《美国诽谤法所称“真正恶意”法则之研究》,《中正法学集刊》第15期,2004年1月
[13][26][27][30][34] 许家馨:“美国诽谤法侵权法归责体系初探——以归责内涵及查证义务为中心”,《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14][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第38页,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91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DONALD TRUMP v. TIMOTHY L. O’BRIEN.
[18][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19]王泽鉴主编:《英美法导论》第1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84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肯尼斯·S·亚伯拉罕、阿尔伯特·C·奈特:《侵权法重述——纲要》第191页,许传玺、石宏等译,许传玺审校,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2][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84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刘文杰:《论新闻侵权的归责原则》,《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4期
[25]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第5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8][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95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9][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95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美]T·巴顿·卡特、朱丽叶·L·迪伊、哈维·朱克曼:《大众传播法(第五版)》第115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3][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侵权行为法》(上卷)第319—320页,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5][45][美]约翰·D·泽莱兹尼著:《传播法:自由、限制与现代媒介》第131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Masson v. New Yorker Magazine, Inc. (89-1799)501 U.S. 513 (1991).
[37]邹利伟:《论故意的认识因素》,《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2期;张金玺:《美国公共诽谤法研究》第2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8][美]Vencent R. Johnson:《美国侵权法》(注释本)第261页,赵秀文、徐琳、刘克毅注,赵秀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9][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第196页,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0][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95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第十三版)第160页,张金玺、赵刚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张金玺:《美国公共诽谤法研究》第24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4][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第181页,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6]王泽鉴:《人格权法》第3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7]王泽鉴:《人格权法》第3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8][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第100页,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9][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第192页,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0]王泽鉴:《人格权法》第3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1]魏永征:《从证明真实到证明确信真实》,(香港)《时代传媒》2002年第6期
展江 王锦东/展江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传播伦理与传播法研究中心主任;王锦东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