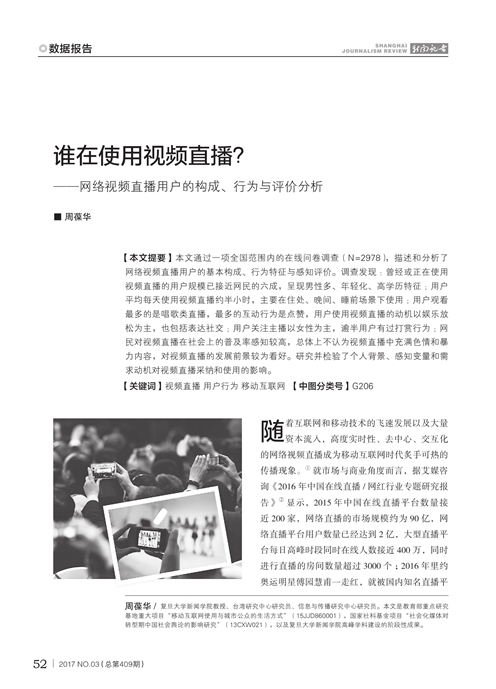谁在使用视频直播?
——网络视频直播用户的构成、行为与评价分析
■周葆华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在线问卷调查(N=2978),描述和分析了网络视频直播用户的基本构成、行为特征与感知评价。调查发现:曾经或正在使用视频直播的用户规模已接近网民的六成,呈现男性多、年轻化、高学历特征;用户平均每天使用视频直播约半小时,主要在住处、晚间、睡前场景下使用;用户观看最多的是唱歌类直播,最多的互动行为是点赞,用户使用视频直播的动机以娱乐放松为主,也包括表达社交;用户关注主播以女性为主,逾半用户有过打赏行为;网民对视频直播在社会上的普及率感知较高,总体上不认为视频直播中充满色情和暴力内容,对视频直播的发展前景较为看好。研究并检验了个人背景、感知变量和需求动机对视频直播采纳和使用的影响。
【关键词】视频直播 用户行为 移动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206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大量资本流入,高度实时性、去中心、交互化的网络视频直播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炙手可热的传播现象。①就市场与商业角度而言,据艾媒咨询《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网红行业专题研究报告》②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家,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约为90亿,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个;2016年里约奥运明星傅园慧甫一走红,就被国内知名直播平台抢邀在线直播,赢得万千瞩目;不仅如此,视频直播作为新媒介应用形态,也影响着传统媒体的转型实践与模式创新(如湖南卫视于2016年暑期推出的娱乐真人秀《夏日甜心》,就以视频直播为主打内容),并成为社会的热点关注话题,其内容质量、社会心理、文化导向等均成为传媒报道的焦点。
但在业界实践与媒体关注如火如荼的同时,有关视频直播严谨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的用户实证研究尚付阙如。目前视频直播用户达到多大规模?观看视频直播的用户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有怎样的使用行为特征?使用直播平台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又如何看待视频直播及其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目前视频直播用户的基本特征,对整个视频直播行业发展也有极强的借鉴意义;而且对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用户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基于此,本课题组于2016年7-8月展开了一项针对全国网民的在线问卷调查,以系统地分析视频直播用户的构成、行为与评价。③本次调查的数据由移动调查公司(“点点赚”)协助收集,该调查平台由一家专业的调研公司设立,拥有覆盖全国除港澳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50多万个样本库,在具体执行中,调查平台根据中国网民的地区分布基础数据进行配额抽样,被抽中的样本打开在线问卷即可开始回答,经统计响应率(即接触到问卷的样本中回答完整的比例)达到98%,最终共成功访问到3000名网民。即便如此,由于样本库的基础构成、推送比例及应答者特征等因素,网络调查并非一个完全随机的样本,因此在数据清理过程中,除了对数据的可靠性进行核查、去除极端值等步骤外,还运用从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调查所获得的网民性别、年龄和城乡三维交叉分布比例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以使本次调查样本的构成尽可能地与中国网民的分布一致,加权后的有效样本为N=2978。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1.8周岁,男性占比57.3%,城镇居民占73.5%,分布于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我们将报告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视频直播用户的比例与构成
根据创新扩散的基本理论(如Rogers2010;DuttonRogers, & Jun1987④),用户对新媒体的采纳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本研究超越简单的“使用与否”的二元区分,根据被访者与视频直播平台的关系,将之划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目前正在使用视频直播的“现用户”,近半年曾经使用但目前已不再使用的“前用户”(以上两类在本研究中合并为“用户”),知道视频直播但未使用过的“非用户”,以及“不知道什么是视频直播平台”的“非知晓者”。结果表明:曾经或正在使用视频直播的用户占到网民群体的57.8%(根据CNNIC2016年7月发布的调查数据,大致相当于全体居民中的29.9%),其中现用户占比44.3%,⑤前用户占比13.5%,而非用户和非知晓者分别占到34.3%和7.9%。
就视频直播用户的构成来看以男性居多(占比60.4%),平均年龄为29.72岁,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占73.9%。可以大致认为,一个比较“典型”的视频直播用户是一个30岁左右、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男性。如果将四类被访者的人口学基本特征进行比较,会发现(见表1):视频直播用户(包括现用户和前用户)中的男性比例显著高于非用户,平均年龄显著更低,学历水平显著更高,平均月收入显著更高,未婚比例显著更高,以及更多居住在城镇地区。
进一步,为控制人口学变量的相互影响,多元逻辑斯迪克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显示:⑥第一,在以非用户为参考组,进行“用户vs.非用户”以及“非知晓者vs.非用户”比较时,相比于非用户,男性(B=.284p<.01)、年龄(B=-.039p<.001)、教育(B=.201p<.001)、收入(B=.229p<.001)和未婚(B=.517p<.001),对成为视频直播用户的概率仍然具有显著影响;而相较于非用户,非知晓者更多为女性(B=.630p<.001)、年龄显著更大(B=.045p<.001)、教育(B=-.233p<.01)显著更低、收入(B=.231p<.001)显著更高、更多居住于农村(B=1.108p<.001)。第二,相对于流失的前用户,现用户的年龄显著更大(B=.036p<.001)、收入显著更高(B=.101p<.01)、更多未婚(B=.392p<.05)。
同时,调查中询问所有被访者对“未来一段时间我(还)会使用视频直播类平台”这一说法的赞同程度(采用五级量表衡量,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结果显示:现用户、前用户、非用户和非知晓者的回答均值分别为3.52(标准差S.D.=1.18)、3.18(S.D.=.98)、2.79(S.D.=1.15)与2.96(S.D.=1.40),如将回答“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的比例合并提取出来,则前用户、非用户和非知晓者的(重新)采纳可能性分别为38.3%、26.1%和41.1%,即前用户和非知晓者的采纳意愿要超过非用户。
视频直播用户的行为特征
1.使用时长、时空与情境
调查采用两个问题——“平均每周有几天使用视频直播平台”和“在使用视频直播平台的那些天,平均每天大概使用多少分钟”,来测量用户使用视频直播的时间。将这两道题的回答结果相乘处理后发现:用户每周使用视频直播平台的时长平均为219.8分钟(S.D.=309.4),约相当于平均每天使用半小时左右(31.4分钟)。其中,男性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长(232.5分钟)显著高于女性用户(200.3分钟)(p<.001),城镇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长(242.5分钟)显著高于农村用户(132.6分钟)(p<.001)。OLS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在用户个人特征变量相互控制后,性别(男性,β=.068p<.01)和城乡(城镇,β=.139p<.001)因素仍然对视频直播的使用时长有显著的独立影响,而年龄、教育、收入、婚否等其他变量则缺乏显著影响。
从用户使用视频直播平台的时间分布来看,无论是平时还是周末,主要集中于晚上8-11点之间,大约有近六成的用户会在这一时段使用视频直播平台;其次是傍晚5-8点,约有近三成的用户使用;排在第三的时段工作日与双休日有所区别——平时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约15%的用户使用),而周末则是下午的2-5点(约25%的用户使用)。总的来看,除了傍晚到晚上的“黄金时段”和夜间的“睡眠时段”外,在其他时段,特别是上午8-11点、下午2-5点,以及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三个时段,周末都比平时的使用率有明显增长。(图1 图1见本期第55页)
用户使用视频直播平台最主要的地点是住处(占用户比例87.2%),其次是工作单位或学校(占比25.1%),第三是其他室内公共场所(占比18.1%),而在交通工具上使用的比例为13.0%,在其他室外场所使用的比例为9.7%。
调查显示:用户使用视频直播平台最主要的情境是“睡觉前”(选择比例为58.4%),其次是“其他空闲时候”(56.8%),第三是“吃饭时”(20.5%);另有18.8%的用户表示会在“所关注的主播上线/更新时”使用视频直播平台,而选择“通勤或外出路上”“起床前”“工作或学习时”的比例相对较少,分别为7.8%、7.4%和6.6%。
用户使用视频直播平台时的网络环境主要是无线网(Wi-Fi),选择比例高达93.6%,只有1.0%选择“手机流量”,另有5.3%表示“两者差不多”。
2.使用内容
从接触比例来看,用户收看视频直播的主要类型是唱歌(选择比例为91.9%),其次是其他才艺(87.4%),第三是美食(85.8%),随后依次包括脱口秀(85.6%)、大型活动(82.1%)、其他日常生活记录(81.7%)等。如按照使用频率量表赋值计算后,排序稍有变化:唱歌类直播仍是用户最青睐的类型,其次是脱口秀与美食类直播。(表2 表2见本期第55页)
表2同时显示了男女用户在收看直播类型上的差异:女性用户在唱歌、美食、其他日常生活记录、跳舞和美妆上的收看频率都显著高于男性,而男性用户对游戏类直播的收看频率则显著高于女性。由此也造成在整体排序上的差异:与女性用户最多收看唱歌类直播不同,男性用户收看最多的是脱口秀类直播。
进一步,本研究经主成分斜交因子分析后发现:用户收看的视频直播内容可以区分为三个因子——第一个是由唱歌和跳舞组合而成的“歌舞”类内容(两者相关系数r=.485p<.001),第二个是“生活才艺”,包括脱口秀、其他才艺、美食、美妆、大型活动和其他日常生活记录(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786),最后一个是独立的“游戏”。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用户最经常收看的视频直播内容是“歌舞”,其次是“生活才艺”,最后是“游戏”(两两差异均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
3.互动行为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用户行为远远超出了被动的“观看”范畴,而包含更多的互动与参与行为,⑦这也是网络视频直播区别于传统电视直播的重要内涵。调查发现:针对本研究所考察的用户在视频直播平台上所从事的八项活动,仅有四分之一左右(25.7%)的用户未从事任何一项,其余74.3%的用户至少有过一种互动参与行为。其中,比例最高的行为是“点赞”(63.3%),其次是“点按钮关注主播”(57.9%),位居第三的是“发弹幕”(54.2%)。随后依次是“发其他留言/评论”“分享至其他平台”等。(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25.1%的用户曾经在视频直播平台上“自己做主播”,从而将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身份转化为较具严格意义的“传者”。⑧
进一步,我们可以根据互动参与需投入的成本将上述行为从概念上分为两类——第一类互动行为较为简单,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较低,如点赞、点按钮关注主播等;第二类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如送礼物、发红包,乃至自己做主播等。经因子分析后发现:经验数据的确验证了这一假设,剔除个别双重负载的题项外,七个条目区分为两个负载清晰的因子,分别命名为“基本型互动”和“成本型互动”——前者包括“点赞”“点按钮关注主播”和“发弹幕”三种行为(Cronbach's alpha=.847),后者包括“分享至其他平台”“送礼物”“发红包”和“自己做主播”四种行为(Cronbach's alpha=.861)。在对各因子组成条目加总取均值后发现:“基本型互动”的频率均值为2.21(S.D.=1.07),“成本型互动”的频率均值为1.72(S.D.=.86),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两者差异达到显著程度(p<.001)。
4.需求动机
调查发现:用户使用视频直播平台的需求按重要程度排序(采用五级量表衡量,1=不重要,5=非常重要)列首位的是“消遣娱乐放松”(M=3.01S.D.=1.34),其次是“打发时间”(M=2.82S.D.=1.25),第三是“学习知识、技能”(M=2.73S.D.=1.31),随后依次是“看美女、帅哥”(M=2.70S.D.=1.32)、“满足好奇心”(M=2.62S.D.=1.26)、“认识更多朋友”(M=2.61S.D.=1.30)、“获得共鸣”(M=2.60S.D.=1.28)、“表达自我”(M=2.40S.D.=1.24)、“获得成就感”(M=2.38S.D.=1.23)等。(图2 图2见本期第57页)
因子分析显示:这九个动机可以组合成两个负载清晰的因子——第一个因子代表“娱乐放松需求”,由“消遣娱乐放松”“打发时间”“看美女、帅哥”和“满足好奇心” 四个题项组合而成(Cronbach’s alpha=.881);第二个因子是“表达社交需求”,包括“学习知识、技能”“认知更多朋友”“获得共鸣”“表达自我”和“获得成就感”五个条目(Cronbach’s alpha=.914)。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用户使用视频直播平台的“娱乐放松需求”(M=2.79S.D.=1.11)显著高于“表达社交需求”(M=2.54S.D.=1.10)(p<.001)。
就群体比较而言,One-Way ANOVA分析发现:男性用户与女性用户在“娱乐放松需求”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女性用户的“表达社交需求”(M=2.66S.D.=1.07)要显著高于男性用户(M=2.47S.D.=1.11)(p<.001),这可以解释不少女性用户从视频直播中学习美妆、时尚等实用技能;而城镇用户在两类需求上都要显著高于农村用户。
视频直播用户与主播的关系
网络视频直播与传统电视直播、以及Web1.0中心化形态的传统网络直播的重要区别除了直播的载体从电视转向网络,特别是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受关系的巨大变化。传统直播形态以组织化的传媒机构(包括网站机构)精心组织和准备直播内容为核心,用户缺少反馈和参与,其中虽有“主持人”,但主持人的角色主要服务于直播的内容需要起到串联功能,很少成为直播节目的中心,也很少超出“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⑨的层面与用户互动,观众更无法转化为直播的主体。但本研究所分析的“网络视频直播”全面重构了传受关系:直播主体不再仅是传媒机构,也不仅限于原本接受专业训练的职业主持人,而是人人皆可为“主播”,主播具有强烈的个性化、对用户具有较强的吸附性与影响力,用户与主播之间可以通过点赞、评论、打赏等方式展开实时互动,观众自身也可以成为主播。正因如此,本研究特别调查了有关用户与主播关系的内容。
首先,调查发现:95.2%的用户至少在视频直播平台上关注了一位主播,其中69.1%关注的主播数量在1-10位之间(47.4%关注了1-5位,21.7%关注了6-10位),19.4%关注了11-20位主播(9.8%关注了11-15位,9.6%关注了16-20位),还有6.5%关注的主播数在21位以上(3.1%关注了21-30位,3.4%关注了31位以上)。OLS回归分析显示:男性(β=.100p<.001)、越年轻(β=.069p<.05)、收入越高(β=.121p<.001)、居住在城镇(β=.094p<.001),以及每周使用直播平台的时间越长(β=.134p<.001),其所关注的主播数越多。
第二,就用户所关注的主播性别来看,超过一半(50.8%)的用户表示主要关注女主播,34.2%表示“两者差不多”,14.9%表示主要关注男主播。将用户性别与关注主播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后可见:57.6%的男性用户所关注的主播主要为女性,而女性用户关注女主播的比例则下降为40.5%,卡方检验显示两者差异达到显著程度(p<.001)。
第三,打赏情况。调查发现:50.3%的用户在视频直播平台上有过赠送礼物或金钱的打赏行为。其中,39.8%的用户平均每次打赏金额在10元以内(28.6%为0.1-5元,11.2%为6-10元),9.1%的用户每次打赏在11-100元之间(6.8%为11-50元,2.3%为51-100元),只有1.4%的用户每次打赏超过101元。OLS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越年轻(β=.157p<.001)、收入越高(β=.300p<.001)、居住在城镇(β=.118p<.001),每周使用直播平台的时间越长(β=.072p<.01),以及所关注的主播数越多(β=.153p<.001),该用户每次观看视频直播时打赏的金额也显著越高。
第四,与主播的联系和认同。本调查通过一组八个问题询问视频直播用户与主播的联系与认同情况。结果发现:用户认同程度最高的表述是“我会反驳不利于我喜爱的主播的言论”(M=2.74S.D.=1.15),其次是“我会想了解主播的日常生活,和他/她更亲近”(M=2.74S.D.=1.20),第三是“我能接受主播打广告的行为”(M=2.70S.D.=1.02)。(见表4)
经因子分析后发现,以上八个陈述区分为负载明晰的两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由“我能接受主播打广告的行为”和“我会尝试购买或使用主播推荐的产品/服务”组成(r=.552p<.001),代表“广告追随”;第二个因子则包括其余六个陈述,代表“粉丝追随”(Cronbach’s alpha=.884)。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用户对自己喜欢的主播的“粉丝追随”程度(M=2.68S.D.=.87)显著高于“广告追随”(M=2.55S.D.=.89)(p<.001)。OLS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用户越年轻、收入越高、已婚、居住在城镇,每周使用直播平台的时间越长,以及所关注的主播数越多,其对所关注主播的“粉丝追随”(以上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在.105~.231之间)和“广告追随”(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在.071~.202之间)程度也越高(均在.01或.001的水平上显著)。
视频直播用户对直播的感知与评价
首先,本研究调查了网民对视频直播的“感知流行性”(perceived popularity)。具体测量方式为请被访者根据了解或估计的情况分别回答视频直播平台在“家人”“朋友”“同学/同事”,以及“社会总体人群”中的使用分别有多普遍(均采用五级量表衡量,1=不普遍,5=非常普遍)。结果显示:被访者感知视频直播在“社会总体人群”中使用最为普遍(M=3.39S.D.=1.12),其次是在同学/同事中(M=3.11S.D.=1.12),随后是在朋友(M=3.00S.D.=1.11)和家人(M=2.08S.D.=1.08)中。由于这四个条目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我们将之组合为一个变量,代表对视频直播的总体“感知流行性”(Cronbach's alpha=.812),其均值为2.90(S.D.=.89)。
其次,针对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所关注的视频直播平台发展中出现的内容质量与导向问题,本研究询问被访者对“视频直播上充满了色情内容”和“视频直播上充满了暴力内容”两个说法的赞同程度(采用五级量表衡量,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结果显示:网民对“视频直播上充满了色情内容”的赞同程度均值为2.62(S.D.=1.23),对“视频直播上充满了暴力内容”的赞同程度均值为2.37(S.D.=1.09),两者都显著低于五级量表的中值3(p<.001),即倾向于不赞同。如果将视频直播用户与非用户对此问题的判断相比较,后者对直播中充满色情(均值2.79vs.2.58)与暴力(均值2.50vs.2.32)的赞同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前者(p<.001)。由于被访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具有较高的相关性(r=.725p<.001),我们将之组合为一个新变量“感知负面形象”用于后续分析(M=2.48S.D.=1.07)。
第三,根据业界分析和媒体报道,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那么它会火多久呢?调查结果显示:对“视频直播会火相当长时间”这一说法,26.0%的用户表示“非常不赞同”或“不大赞同”,36.5%表示“一般”,37.5%表示“比较赞同”或“非常赞同”。其均值为3.15(S.D.=1.09),显著高于五级量表的中值3(p<.001),即倾向于赞同,说明网民总体上对视频直播的生命力较为看好。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基于“创新扩散”和“使用与满足”等经典理论的指引,将视频直播应用作为新媒体采纳与使用的“第二层”问题,[11]探究个体特征、感知流行,以及需求动机等因素,对视频直播采纳与使用的影响。在自变量方面,除去上述三个维度外,本研究还纳入“感知负面形象”(即感知色情与暴力内容的程度)以及“感知生命力”(代表对视频直播未来发展的信心)两个因素加以分析。而在因变量方面,对视频直播采纳的考察将基于本研究所划分的四种类型(现用户、前用户、非用户、非知晓者)进行比较,并预测前三类群体的“(重新/继续)采纳意愿”;而对视频直播的“使用”则包括使用内容与互动行为两个维度。
(表5 表5见本期第59页)呈现了视频直播采纳的影响因素。
第一,对四个类别(以现用户为基准)的多元逻辑斯迪克回归(MLR)分析发现:女性、年长、教育程度低的网民更容易是视频直播的非用户或非知晓者,农村网民更有可能是非知晓者,收入低、已婚的网民更容易是非用户,而相较于现用户,流失的前用户年龄更低、收入更低、更多已婚;与此同时,感知流行对视频直播的采纳有显著影响——越认为视频直播普及,越可能是用户;相较于现用户,非用户对视频直播的形象感知更趋负面;另一方面,相较于非用户或非知晓者,现用户反而不认为视频直播可以火很久。
第二,OLS回归分析显示:对视频直播的“感知流行”和“感知生命力”两个因素对三类群体的采纳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β在.220~.371之间(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对视频直播的负面形象感知会抑制非用户的采纳意愿,却与现用户的继续采纳意愿正相关;除娱乐放松需求可以正向影响现用户的继续采纳意愿外,需求动机对视频直播的采纳意愿影响不大。
(表6 表6见本期第60页)呈现了视频直播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OLS回归分析结果。
首先,人口学变量中,女性网民更偏爱歌舞类和生活才艺类直播,而男性更多观看游戏类直播,且更多基本型互动行为(点赞、点击按钮关注主播、发弹幕等),收入水平对三类直播的收看程度和两种互动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对收看生活才艺类直播及基本型互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收看游戏类直播则呈负相关,城镇网民相比于农村网民更多收看歌舞类直播,更少基本型互动,但更多成本型互动(如分享、送礼物、自己做主播等);
其次,感知流行与除了“基本型互动”外的其余五个使用变量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感知生命力可以正向影响歌舞类和游戏类直播的使用,感知负面形象与歌舞类直播的收看和成本型互动频率正相关;
第三,需求动机对视频直播的使用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表达社交”需求,对除了歌舞类直播的其余五个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娱乐放松”需求可以正向影响歌舞类直播观看和基本型互动行为,却与生活才艺类直播的收看负相关。
总体上,在人口学变量之外,对视频直播的感知和需求动机对视频直播使用变异的解释力提高了5.5%~29.3%。
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一项针对网络视频直播用户的实证调查研究,本文对当前视频直播用户的构成、行为及评价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描述性分析,对视频直播的使用内容、互动行为、需求动机、与主播关系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内部结构的区分,并运用“创新扩散”和“使用与满足”的基本理论对视频直播采纳和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解释。本文的主要发现可概括如下:
第一,规模与构成: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项新型应用,网络视频直播目前已的确赢得了较大的用户市场,总体上有近六成(57.8%)网民曾经或正在使用视频直播平台(其中44.3%在调查时仍在使用)。其构成特征表现为以男性用户居多,年轻化,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多居住在城镇地区,但农村地区网民中视频直播用户的比例也已超过四成。
第二,使用行为特征:用户平均每天使用视频直播的时间约为半小时,主要使用时段是晚上8-11点和傍晚5-8点,使用的地点主要是住处,主要情境是入睡前;唱歌类直播是用户最青睐的类型,其次是脱口秀与美食类等;女性用户对歌舞、美食等类型直播的收看频率都显著高于男性,而男性用户对游戏类直播的收看频率显著高于女性;3/4左右的用户在视频直播平台上至少有过一种互动参与行为,其中最普遍的是“点赞”(63.3%),另有1/4的用户曾经在直播平台上自己做主播;用户使用直播主要是为了满足娱乐放松需求(如消遣娱乐放松、打发时间、看美女帅哥等),但学习知识、技能,认识更多朋友,表达自我等“表达社交”需求也占有一定比重。
第三,与主播的关系:95.2%的用户至少在视频直播平台上关注了一位主播,其中大部分人关注的主播数量在10位以下,且以女主播为主;逾半(50.3%)用户在视频直播平台上有过打赏行为,其中大部分每次打赏金额平均在10元以内,用户越年轻、收入越高、居住在城镇、每周使用直播平台的时间越长,以及所关注的主播数越多,其打赏金额也显著越高;用户与自己喜爱的主播形成了粉丝追随关系,这种关系也影响其对主播广告行为的接受。
第四,感知与评价:网民对视频直播在社会上的普及率感知较高,总体上并不认为视频直播中充满了色情和暴力内容,对视频直播的发展前景较为看好。这些对视频直播的感知与评价对视频直播的采纳和使用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感知流行性被证明无论对视频直播的采纳,还是对具体使用和互动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生命力也与对视频直播的采纳意愿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尽管不能有效地预测采纳,但需求动机、尤其是“表达社交”方面的需求越强烈,用户对视频直播的使用程度和互动行为也越活跃。
尽管本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呈现视频直播用户的基本特征,但在如下两方面也具有理论发展的潜力:第一,本文简要阐释并区分了用户互动行为的两个维度(“基本型互动”与“成本型互动”),不仅提供了在新媒体环境下分析“使用”行为的具体方式,而且发现了它们与其他变量之间的不同联系(如“娱乐放松”动机可以影响“基本型互动”,却无法影响“成本型互动”);第二,本研究分析视频直播采纳和使用的影响因素,不仅验证了以往研究所发现的感知流行、需求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提出并检验了感知生命力、感知形象等新变量的影响。同时,就对业界的参考意义而言:首先,本文既显示视频直播有了相当大的用户市场规模,提示运用这一新形态展开传播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又反映出其用户群体并未稳定——既有用户流失,也有潜在用户加入,在目前“创新扩散”的动态过程中,视频直播依靠怎样的服务和特色吸引用户,就成为这一新型应用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其次,从用户需求角度看,相比于“娱乐放松”需求,“表达社交”需求更能促进对视频直播的使用与互动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报道与业界讨论所构建的视频直播“娱乐”形象似乎并不足以保证其长远发展,视频直播能否满足用户在“表达社交”乃至“个人提升”方面的多样需求,可能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在追踪中不断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①本文考察的“网络视频直播”特指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所产生的新型直播形态,它区别于传统“直播”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传播平台并非以电视台或Web1.0形态的网站为主导,而是以新兴移动互联网平台为主导,如映客、花椒、斗鱼等;第二、传播主体并非传媒机构,而是去中心化的机构、小团队或个体,“主播”的个性化特征明显;第三、直播内容超越传统的大型活动或公共事件,包含从娱乐、游戏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广泛内容;第四、传受关系改变单一的观看模式,呈现高度交互化、参与性的特征,用户自己也可以成为主播。本文第三部分对此也有分析。
②艾媒咨询《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网红行业专题研究报告》,取自网络:http://www.imxdata.com/archives/7699,2016年6月1日
③上海南康网络公司(“调查宝·点点赚”)协助执行了问卷调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新媒体硕士班同学参与了问卷初稿设计的讨论,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了最新的网民分组构成比例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④RogersE. M. (2010).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Dutton, W. H.Rogers, E. M.& JunS. H. (1987). Diffusion and social impacts of personal compute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2)219-250.
⑤根据CNNIC(2016年7月)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比例占网民总体的45.8%,与本研究“现用户”比例高度吻合,但CNNIC调查并未包含对视频直播用户行为和评价的具体分析。
⑥这两个多元逻辑斯迪克回归模型包含的自变量均为: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婚否以及城乡,模型的虚拟McFadden R2分别为11.0%和8.9%,限于篇幅,表格未附。
⑦NapoliP. M. (2011). Audience evolution: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audie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⑧这里的“严格意义”,是指“传者”实际上可以是个具有宽泛意义的概念,例如在视频直播平台上从事点赞、发弹幕、留言/评论、乃至转发等“微生产”活动,都具有传播、分发内容的“传者”意义,但“自己做主播”则更为集中地体现“传者”概念所强调的“生产”含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本研究所考察的这些行为,也可被视为具有不同主动生产程度的“传者阶梯”。
⑨HortonD.& Richard Wohl, R. (1956).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 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 Psychiatry, 19(3)215-229.
⑩如吴晋娜、张紫璇、李政葳:《七个“关键词”改变2016年传媒生态》,取自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1231/c1013-28991130.html,2016年12月31日
[11]周葆华:《Web2.0知情与表达:以上海网民为例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公众的生活方式”(15JJD860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化媒体对转型期中国社会舆论的影响研究”(13CXW021),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高峰学科建设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