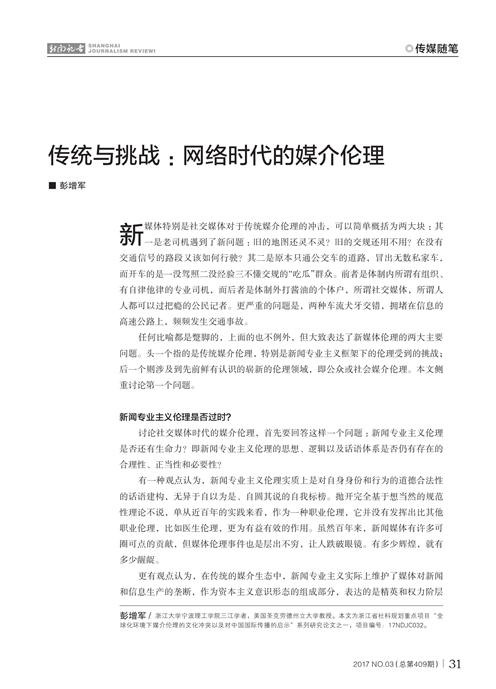传统与挑战: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
■彭增军
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对于传统媒介伦理的冲击,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大块:其一是老司机遇到了新问题:旧的地图还灵不灵?旧的交规还用不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路段又该如何行驶?其二是原本只通公交车的道路,冒出无数私家车,而开车的是一没驾照二没经验三不懂交规的“吃瓜”群众。前者是体制内所谓有组织、有自律他律的专业司机,而后者是体制外打酱油的个体户,所谓社交媒体,所谓人人都可以过把瘾的公民记者。更严重的问题是,两种车流犬牙交错,拥堵在信息的高速公路上,频频发生交通事故。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上面的也不例外,但大致表达了新媒体伦理的两大主要问题。头一个指的是传统媒介伦理,特别是新闻专业主义框架下的伦理受到的挑战;后一个则涉及到先前鲜有认识的崭新的伦理领域,即公众或社会媒介伦理。本文侧重讨论第一个问题。
新闻专业主义伦理是否过时?
讨论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伦理是否还有生命力?即新闻专业主义伦理的思想、逻辑以及话语体系是否仍有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伦理实质上是对自身身份和行为的道德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无异于自以为是、自圆其说的自我标榜。抛开完全基于想当然的规范性理论不说,单从近百年的实践来看,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它并没有发挥出比其他职业伦理,比如医生伦理,更为有益有效的作用。虽然百年来,新闻媒体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但媒体伦理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让人跌破眼镜。有多少辉煌,就有多少龌龊。
更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的媒介生态中,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维护了媒体对新闻和信息生产的垄断,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表达的是精英和权力阶层的意志,观念市场的多样性越来越差,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权得不到维护。即使退一步讲, 如果说在信息稀缺的媒介生态下,新闻媒体作为唯一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其专业主义伦理有其客观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新媒体革命以后,信息不再是短缺资源,垄断被打破,人人都可以加入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当中,新闻媒体自然失去了以往作为单一信源的重要地位,新闻媒体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所以,媒体无需自我神圣化。
再者,新闻自由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公众的表达自由,新闻媒体公共性在于代表公众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由此才有所谓的第四权力说。那么,当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屡创历史新低的时候,媒体的代表性如何实现?失去了公众代表性,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又从何谈起?
以上观点的要害是说可以存在一个没有新闻专业主义的新闻界,其理论支撑点是古典的观念市场理论,即让各种观念在市场上充分竞争,善赢恶败,优胜劣汰。但是,这样的观念市场的前提是,各种观念都有平等的表达和传播机会。可惜在权力和阶层社会中,在基本人权都不平等的情况下,观念的市场更可能是一个丛林社会而非自由平等竞争。从现实看,网络社会发展二十多年来,数字鸿沟不但没有缩小,相反越来越大,社会非但没有共识,相反越来越分裂。而新闻媒体社会信任度的下降,恰恰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更彰显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与紧迫。
言论自由实现的保证是传播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给了普通民众更多的传播自由,从而为言论自由至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但是,言论自由本身不是目的,是手段,是为了寻求真相,表达意见,由此形成舆论,参与和影响政治。所以,没有专业主义的伦理,谎言和偏见往往遮蔽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所谓正义也许会迟到,却永不会缺席,只能作为鼓舞人们坚持寻求真相的呐喊。迟到的正义,往往是无法挽回的悲剧。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虽说媒体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媒体依然是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流媒体。尽管有60%的用户从脸书等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但是社交媒体的新闻,其大部分来源仍然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依然生产着70%的原创新闻。虽然人们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只有32%, 但是相对社交媒体来讲,依然高得不是一点半点。根据BuzzFeed News 2017年1月的调查,只有18%的人相信脸书上的信息。
由此看来,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依然有生命力。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新闻视点和新闻技巧,任何时候都不可只讲镜头,不讲镜头前面和后面的人。新闻媒体经营模式的衰落并不等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死亡。
传统与挑战
传统新闻伦理是围绕专业主义的理念建构的,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由行业组织制定,通过自律和同行评议来监督执行的伦理守则。行业协会,顾名思义,是封闭的、排外的,在某种程度上同江湖帮会并无二致。如果说新闻行业协会是“帮会”的话,那么伦理守则无非就是“帮规”。“帮规”首先要确定的是身份认同和行为规则,要界定的问题包括“我们是谁,我们坚持什么,我们干什么、不干什么”。 “帮规”可以为君子协定也可以是小人联盟。俗话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许多情形下,君子更以“有所不为”在江湖安身立命,一如张季鸾《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相比之下,小人则无所不为。新闻“帮会”“帮规”是君子协定,为什么?因为其公共性,以及对社会的道义担当。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凯瑞 (James Carey)直截了当说新闻专业主义的全部价值与存在意义在于其公共性。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从上个世纪初逐步建立的伦理守则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新闻媒体垄断了新闻生产,是新闻的把关人。虽然表明公共服务为其宗旨,但其制定和实施却一点也不“公共”,普通民众除了通过读者来信或者听众来电表达一点意见外,公众对于媒体伦理没有话语权。
那么,究竟什么打破了这种垄断?是新的媒介吗?
在以往的媒介进化过程中,由报纸发展起来的新闻专业主义伦理并没有由于媒介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广播和电视时代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媒介本身并不是关键,不是新的媒介必然需要新的媒介伦理。
我们经常问新媒体到底新在哪里?数字化?非线性?交互性?是也不是。因为这些都是特性,却不是本质。本质是媒介革命带来的新闻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改变。一百多年来,新闻信息的生产一直是封闭与垄断的,其本质就是消费者同生产资料和传播渠道的脱离,普通民众没有能力拥有媒体生产所需的资本和渠道。网络的出现,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人人成为新闻记者、成为出版商变为现实,从而由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生产者,况且在传播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无论怎样优秀的新闻稿,没有受众的分享,等于白做。新的生产方式导致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而伦理就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新的社会关系必然会挑战传统的媒体伦理体系。传统的新闻生产是垄断的、封闭的、固定的,因此其专业主义的新闻伦理也是垄断的、封闭的、固定的;而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是共享的、开放流动的,因而要求伦理也是共享的、开放的流动的。
新的媒体生态影响到媒体伦理的方方面面,显而易见的有下列种种:
1.事实与求真
“真”是普世价值,即使骗子也不乐意别人对他说谎。新闻伦理的第一原则是求真。求真不是对真相的承诺,而是为接近真相诚实的努力。新闻伦理的认识论是科学和实证的,因此,真实、客观、公正、独立等就成为新闻伦理探求真相的途径和行为的准则。
但是,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下,新闻生产是共享、开放和参与的,不再是由职业媒体人把关的固态,而是流动的,犹如液体般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力量都会加入,每个加入者都有着自己的目的,而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为了真相。在我们说真理越辩越明的时候,也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水越搅越浑,而真相往往淹没在事实与谎言的纠缠当中。
网络传播特点同传统新闻生产理念和方式也有许多冲突。比如,求真的第一步是呈现事实,而事实要求准确,但准确这一原则,就同网络的即时性相矛盾。保证事实准确的最为重要的方法是什么?是验证。验证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当前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对于传统的生产流程进行了压缩简化。比如说,验证和校对是传统媒体质量监控的最为关键有效的一环,所有传统新闻编辑部都设有专门的校验部(Copy Desk)。但是,由于经营压力,在部门调整和人员压缩上,校验部往往是最先挨刀。即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标杆前不久也宣布要裁撤校验部。从专业的角度讲,裁撤校验部几乎等于宣布放弃产品质量,因为缺少验证,出错是必然的。甘乃特报业集团旗下的地方大报《辛辛那提问询报》,2014年 11月取消校验部后,频频出错,在 2015年2月8日的周日刊上,居然出现了13处错误,连头版头条的图片说明都写错了。媒体伦理的第一要义是寻求和报道真相,如果新闻媒体连基本的事实准确都不能保证,还奢谈什么真相。
2.客观与公正
为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需要遵循的重要伦理原则首先是独立。传统上,新闻记者一般不参加政治社团和社交活动,就是为了保持职业的独立性。但是,在网络社会,这样的独立性往往很难做到。网络社会的本质就是联络,而社交媒体的本质无外乎社交。新闻记者再也不是以往的“孤独的狼”,单打独斗;新闻生产本身已经社会化,记者使用社交网络不仅仅是个人喜好,而是工作的需要,这样不可避免就产生两种身份的冲突。比如说,媒体人在社交网络上成为大V或者网红,该如何维护自己记者身份的独立性?当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表明立场以后,又如何来为自己所做新闻节目的客观公正辩护?可信度又有多少?记者在社交媒体或者自己的公众号转发和分享某条新闻或者文章又意味着什么?
3.数据与隐私
如果说隐私权是指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信息的权利和能力,那么在数码时代,隐私被侵犯的概率以及善后的难度成倍增加,一旦遭受伤害,无法补救,即使你删除了原文,无数影像文件依然存在。
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毫无隐私可言,个人信息无时无刻都在被搜集。这些有关我的数据的所有权属于谁? 我对于关于自己的数据有没有知情权和使用权?可悲的是,即使你有这些权利,你也无法主张,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搜集了哪些隐私,搜集者又是谁?
那么,作为主动方的媒体,该如何尊重、保护用户和受众的知情权和隐私权?而作为记者或者编辑,又如何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注意这个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记者是否需要表明身份、征得同意才能使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的发言或信息?
4.责任与边界
网络时代的新闻信息生产是开放的和分享的,普通人在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和传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不再是新闻媒体的垄断产品,而是媒体与公众的共同创造。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媒体的责任边界在哪里?要不要对参与到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民众的言行——比如发表的信息和评论负责,又该如何负责? 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是否适用于公民新闻? 依据又是什么?又该如何落实?对于违反了专业新闻伦理的帖子或者评论是否删除?如果删除,是否侵犯了发表人的言论自由?对文章里的链接又该如何负责?链接到的内容是否应该符合我们的伦理标准?即使认真审核了链接的内容,又如何保证链接到的第三方的内容没有变动?
以上讨论局限于文章开首所谈到的第一大块,即:专业主义伦理所遇到的挑战。另外一块,即公众或者社会媒介伦理,学界和业界讨论不多却非常重要。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吃人事件的视频传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社交媒体使用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媒介伦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途径又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更是急迫的现实问题。■
彭增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全球化环境下媒介伦理的文化冲突以及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系列研究论文之一,项目编号:17NDJC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