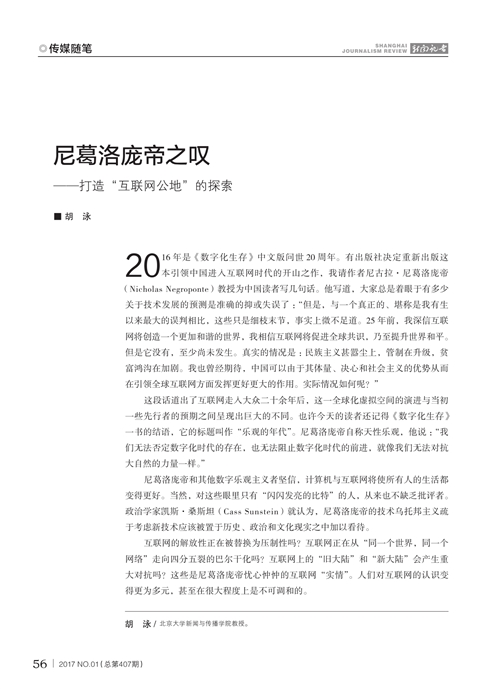尼葛洛庞帝之叹
——打造“互联网公地”的探索
■胡泳
2016年是《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周年。有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这本引领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开山之作,我请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他写道,大家总是着眼于有多少关于技术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抑或失误了:“但是,与一个真正的、堪称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相比,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事实上微不足道。25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
这段话道出了互联网走入大众二十余年后,这一全球化虚拟空间的演进与当初一些先行者的预期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不同。也许今天的读者还记得《数字化生存》一书的结语,它的标题叫作“乐观的年代”。尼葛洛庞帝自称天性乐观,他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
尼葛洛庞帝和其他数字乐观主义者坚信,计算机与互联网将使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好。当然,对这些眼里只有“闪闪发亮的比特”的人,从来也不缺乏批评者。政治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认为,尼葛洛庞帝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疏于考虑新技术应该被置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现实之中加以看待。
互联网的解放性正在被替换为压制性吗?互联网正在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走向四分五裂的巴尔干化吗?互联网上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会产生重大对抗吗?这些是尼葛洛庞帝忧心忡忡的互联网“实情”。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变得更为多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调和的。
互联网一度被宣扬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充分参与者;同时,人们也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互联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经由新技术极大地增强“老大哥”的监控能力。公民的权利不仅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剥夺,也被大企业侵害。很多人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不确定是否该允许“一切照常”抑或是拥抱更多的规制。例如,言论自由和隐私,就是人们矛盾心理体现得极为明显的两个领域。
出于历史的原因,现有的互联网规制和治理如同中国人常说的“九龙治水”,来源多样,彼此重叠,甚而冲突。民族国家的“尺寸”在跨越地域的互联网上显得奇怪,然而它们坚持自己地域内的管辖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通过用户协议规范用户的网络行为,而技术的开发者又不无“代码即法律”的傲慢。用户机会与全球性的网络生态就这样被多股力量所塑造。令人惊异的是,在一个高唱“消费者至上”“用户为本”的时代,用户不仅失语,而且备感无力。
互联网上的三股力量
政府、市场和公众构成了互联网上的三股力量。他们也带来了互联网的三种治理模式:以政府为中心的模式,可以称之为“新威权模式”,或者叫作“网络威权主义”,它维持适度的市场竞争,但强调网络设施为国家所有,推动国家支持的互联网产业,并通过宣传、监控、审查极大地限制个人自由。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具有强烈的技术乌托邦色彩,有人命名为“加州意识形态”,夹杂了控制论、自由市场思想和反文化的自由意志论。以公众为中心的模式,我称之为“公地模式”,它的比较极端的表述,可以称之为“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三股力量奇特地搅在一起,彼此生成,又互相缠斗。
“加州意识形态”从宏观层面塑造了美国加州今日自由开放的硅谷,从技术角度影响了此后的半导体产业、PC产业和互联网。虽然标榜自由市场,它也催生了如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国家行为。奇特的是,“加州意识形态”还衍生出了赛博文化,其要旨是通过技术项目达至技术乌托邦。通过用技术系统来表达设计者的梦想,互联网被视为解放和民主的催化剂。在这种对互联网的历史性解释中,互联网生来就是要打破政府的桎梏,典型的表达是约翰·巴娄(John Barlow)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今天我们都知道,赛博空间根本无法独立,“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敌不过新威权模式和大企业的操控。就连巴娄的“互联网主权”概念也被完全挪作相反的用途。斯诺登事件不过是这种现状的最经典的反映。仍然对互联网心怀理想的人为此发出“夺回互联网”的呼吁,比如有名的密码学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就严厉抨击说,政府和产业背叛了互联网。经由把互联网变成巨大的监控平台,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契约,而大公司也是不可信任的互联网管家。
施奈尔给出的行动建议是:揭露你所知道的监控现实,重新设计互联网,以及影响互联网治理。在重新打造的“互联网公地”中,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理应依赖崭新的、以全球网络社区为中心的体系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
互联网为每个人赋予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创造、学习和共享资源。它不受个别机构、个人或政府操控。所以,各国政府不应该单独决定互联网的前途。全球数以十亿计使用互联网的人,才最有发言权。最好的方式是让国家政府退后一步,以便协调和整合各自的不同,积极促进公民社会和企业在全球治理、合作与沟通中发挥作用。而对中国而言,如果要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国际玩家,一定要认识到光成为经济大国是不够的,而是要努力创造一个自由想象、自由沟通的环境,让个体更有力量。
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
至于说到企业,它们既需要关注经济上的“公地”环境——例如,对基础设施或是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否不足,也需要更多考量政治上的“公地”环境——只要想想在一个民主而公正的社会中做生意会有多么顺畅,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今天企业赖以运行的环境,本身就是政治决策的产物。法治和产权对一种稳定的经济系统的作用,历史上的例证历历在目。就像良好的治理是企业高绩效的必要前提一样,善治也是高绩效国家的必要前提,一个国家拥有健康的民主文化,也是完全符合国家自身的利益的。
在互联网发展的最近10年,技术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不论是工具还是平台,也不论人们对这些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和理解,都显示出一种明确无误的演进: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我们将面临一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正是为此,围绕互联网的公共讨论和学术话语正在发生一场“从强调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开放度到把风险、冲突、弱点、常规化、稳定性和控制看作当务之急”的迁移。
我所说的这场冲突,构成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性挑战:它并不仅仅关乎信息自由,而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之中。
正如英国的贵族们在1215年制订“大宪章”来约束不受欢迎的国王约翰的权力,今天在“大宪章”颁布800年之际,网民应组织起来遏制政府和企业的权力。
互联网的“宪章时刻”存在三个突出的主题:一是自由与控制的关系,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安全。不少国家以强调安全之名牺牲公民自由与隐私,此一安全与自由之争在网络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见。数字社会的复杂性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与安全的概念。个体公民更加关心自己的数据为何人所掌握,政府则看到电脑犯罪、黑客活动、恐怖袭击等占据国家安全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有可能同时在网上获得自由与安全吗?
二是如何建立数字信任。无所不在的互联网要求我们重新界定信任的边界,并在数字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用户现在可以方便、灵活地收发各种信息,这给网络法与网络规范造成了空前挑战。后者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总是落后于技术的发展。网络行为如何在规制与规范下得以发生和展开?信息的完整性与可靠性如何保证?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否能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当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数字信任?这种线上的信任又是怎样同线下的责任感、透明度等关联在一起?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三是如何填平数字鸿沟与提高网络素养。网络接入权与网民素养是网络社会的基石所在,个人因此而赋权,知识借此而撒播,从而确保不会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进的互联网列车。在这里,数字鸿沟不仅意味着网络接入权的泛化与网络普及率的提高,还包括上网设备的成本、用户的技能、应用ICT技术的时间与机会以及用户使用的目的和影响等多个参数。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例如,年轻的技术精英掌握编程技巧,熟稔代码,颠覆了传统精英的位置,致使整个社会弥漫“后喻”文化。然而数字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养以及新的伦理,特别是在年长者对年轻人引领的网络规范充满狐疑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决定了数字时代的连接是否最终会导向赋权,以及赋权的对象为何。
为了回应这些主题,我们集合全国的一批有志于从各个方面探讨互联网未来的优秀学者,通过开展独创性的研究,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面向全球互联网发言。我们将把这些研究成果汇集为年度的“公地”文丛。
我们的研究中,反对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将其看作一种时有不同的技术、平台、行为和话语的集合,它们与社会互相激荡,共同演变。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从历史延伸至当代,以使人们了解和挑战对互联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理解和假设。我们研究涵盖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文明变迁,财富历程,认同与主体性,政治与民主,技术、知识与媒介,产业与管理,数字权利与网络治理,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