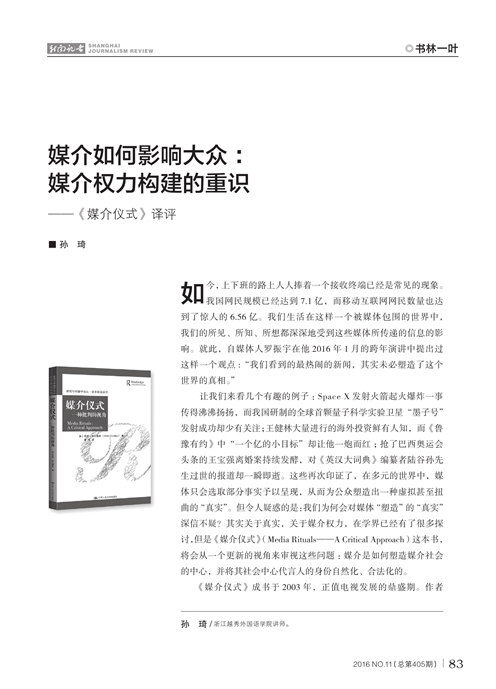媒介如何影响大众:媒介权力构建的重识
——《媒介仪式》译评
■孙琦
如今,上下班的路上人人捧着一个接收终端已经是常见的现象。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1亿,而移动互联网网民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6.56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媒体包围的世界中,我们的所见、所知、所想都深深地受到这些媒体所传递的信息的影响。就此,自媒体人罗振宇在他2016年1月的跨年演讲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看到的最热闹的新闻,其实未必塑造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让我们来看几个有趣的例子:Space X发射火箭起火爆炸一事传得沸沸扬扬,而我国研制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成功却少有关注;王健林大量进行的海外投资鲜有人知,而《鲁豫有约》中“一个亿的小目标”却让他一炮而红;抢了巴西奥运会头条的王宝强离婚案持续发酵,对《英汉大词典》编纂者陆谷孙先生过世的报道却一瞬即逝。这些再次印证了,在多元的世界中,媒体只会选取部分事实予以呈现,从而为公众塑造出一种虚拟甚至扭曲的“真实”。但令人疑惑的是:我们为何会对媒体“塑造”的“真实”深信不疑?其实关于真实,关于媒介权力,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探讨,但是《媒介仪式》(Media Rituals——A Critical Approach)这本书,将会从一个更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媒介是如何塑造媒介社会的中心,并将其社会中心代言人的身份自然化、合法化的。
《媒介仪式》成书于2003年,正值电视发展的鼎盛期。作者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笔者曾译为尼克·寇德瑞)敏锐洞悉了电视媒介权力背后的神秘力量。而在电视传媒逐渐衰落,移动互联网全面改变着社会传播结构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启示,它所提供的探究媒介权力变化本质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媒体产业研究和发展趋势分析有着另一番借鉴意义。
一、尼克·库尔德里的仪式观
仪式理论研究起源于19世纪,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在该领域的研究过程中,此前的学者提出了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事件等概念。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尼克·库尔德里提出了“媒介仪式”这个概念,并阐明其核心观点:现代社会是被媒介系统所渗透和制约的“媒介化”社会,媒介通过对“社会中心”的塑造和表达,构建起其“社会中心”代言人的地位,而权力构建过程则通过媒介仪式变得隐蔽化和合法化。库尔德里的论述解答了媒介在建立日常生活秩序、塑造社会结构方面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媒介作为社会存在如何与人们的生活实践产生紧密关联等问题。
在对“仪式”的认识上,库尔德里颠覆了长久以来涂尔干主义的研究路径,他在书中明确提出:“要解释媒介仪式性的一面,必须颠覆涂尔干的解读……关键的不是‘仪式’一词所昭示的什么古代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质的东西:即权力和社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中化。”这一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高维的分析方法,对传播活动和仪式活动进行抽象:传播活动和仪式活动的本质是“权力和社会组织大规模的集中化”的问题,也就是“符号资源”和“社会调和”的问题。“符号资源”问题关注传播活动的主动性、内容观念和影响场域问题,而“社会调和”则侧重于从传播结果的角度进行分析。
库尔德里关注到了媒介仪式背后的权力和控制问题,在肯定了媒介在社会调和方面作用的同时,把关注点投向了媒介对符号资源的控制和媒介作用场域的分析上。不但为我们指出了构建媒介权力的资源和媒介权力的作用场域,同时也阐明了媒介是如何通过媒介仪式将自身的权力合法化、自然化的。
这些研究视角,很好地解释了电视时代关于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构建的问题。那么对于现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研究又有何价值呢?
二、媒介仪式透视下的网络时代
媒介仪式理论的关注重点,是媒介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对于媒介社会中心的构建,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符号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正是利用对这些符号资源的垄断,使得媒介可以实现意识、观念的灌输。在新媒体时代,伴随着社会化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播的社会连接结构从传统的树状连接,向更为复杂的网状连接转化,传统媒体原本垄断的符号资源被极大地稀释。首先,由于信源本身的多样化,使得信息所构建的受众意识形态变得不可预测;其次,不同信源内容的冲突加剧了当前媒介权威性和中心化的瓦解。
传统媒介权威性的瓦解,也从反面证明了媒介仪式理论的正确性。一方面“媒介社会中心”的构建并不依赖于“社会中心”的实际存在,而是通过符号资源和媒介仪式活动在受众心中构建起来一种共同“认知”。由于这种“认知”的虚构性,在受到其他符号资源冲击的时候,就会变得脆弱。另一方面,媒介符号资源的稀释和社会传播结构的网状化,使得媒介难以利用“垄断、稀缺的符号资源”通过具有排他性的“传播仪式”,构建起“媒介社会中心”。
尽管在社会整体宏观层面上,“媒介社会中心现象”被一定程度地弱化了,但媒介仪式理论本身在帮助我们分析、理解社会传播现象时,仍然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尽管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带来了传播结构的网络化,但在社会整体的不同维度空间内,仍然会以共同的目的或属性构建起为数众多的“社群”,媒介仪式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透析每个微观层次的“社群”的“中心”是如何构建和维护的。
媒介仪式理论当中,构建媒介社会中心的基础就是符号资源。在笔者看来,新媒体语境下的“符号资源”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信息资源,二是连接资源。所谓信息资源,可理解为媒介本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社群中心”的代言人,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够多大程度上为其成员提供信息价值。而连接资源,是指媒介传播信息所能达到的广泛程度。媒介如何将自己构建成为所处社群的中心,其核心就是如何不断地增强信息资源能力和连接资源能力。这为我们提供了两种途径,一种是摊煎饼式的构建,即依托优质的信息资源,通过二次传播,不断扩展连接范围和影响面,不断吸引有资源需求的受众与媒介相连接,在成为社群中心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圈子的范围。另一种则是盖楼式的构建,即依托已有的连接资源,在新的维度上构建一个新的社群。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互联网推广模式都可以用这两种构建方式来解读。例如豆瓣,作为一个读书、电影、文化交流的平台,它最先经营的是社群的中心媒介地位,在成功构建其“媒介中心”地位后,通过对平台的宣传和推广,实现了社群范围的扩大。而腾讯公司的媒介中心构建则采用第二种方式,它依托即时通讯的巨大的用户群,可以快速推送新的平台信息到所有用户,在新的维度上构建了媒介中心。
显然,尼克·库尔德里仪式观为我们审视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诸多媒介权力现象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同时,限于时代背景,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了符号资源、仪式活动对构建媒介中心的作用,而对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移动互联时代所带来的改变,其中一点即为公众不再仅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们需要表达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思想和意志。新时代下,专业的新闻媒体在“媒介中心”构建的过程中,不但要注重从正面强化符号资源的力量,同时也要应对来自受众的反馈。而有时,这种反馈可能是破坏性的,这种破坏性来源于受众本身在网络社会中所拥有的符号资源。“媒介中心”所拥有的连接资源并不具有垄断性,受众的网络化连接结构可能使其具有与“媒介中心”同样量级的连接资源。这一现象,导致了媒介中心与受众的互动,以及媒介权力的再分配问题。
三、关于《媒介仪式》中译本
前些年,国内传播学者对仪式理论产生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与国外译著的引进有关。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得益于崔玺所译《媒介仪式》在中国的面世,国内的学者将更多地了解尼克·库尔德里及其媒介仪式理论,并可能再一次激发相关领域研究的热潮。
学术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学术著作语言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极强,要准确地表达原文作者的思想,不但需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更需要有深厚的专业积淀。只有两者兼具,方能流畅、准确地传递出原著作者的思想。这部《媒介仪式》中译本,用专业的语言将媒介仪式的核心理论呈现出来,这为国内的学者认识、研究这一领域打开了便利之门,扫除了语言障碍,减少了大量的初期翻译工作。尤其是译者在对原著作者核心观点的把握方面,体现出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然而,这部中译本仍有些可改进之处。一是直译方式导致的语言表达晦涩、生硬,二是某些词汇的翻译值得商榷。
目前,逐字逐句地直译原文是国内部分专业译著采用的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是对原著的充分尊重,但也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会导致语言表达晦涩、生硬,不便于读者理解。这类译著可以帮助读者大致了解作者的思想,但细部和概念性的问题,则必须回到英文原著中寻求答案。直译方式难于理解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英文的语言表达习惯不同,在英文学术著作中往往存在大量定语结构和从句结构,采用直译方式会使表意发生中断或跳跃,有时甚至难以提炼出语句或段落主干;二是部分原著作者的行文习惯倾向非结构化和口语化,直译会使读者不知所云(例如,在使用形容词时没有具体、明确的形容对象)。《媒介仪式》也未能避免以上问题,在书中一些直译之处,存在语句难以读懂的现象。
另外,在某些词汇的翻译上,笔者希望能与译者进行探讨,例如对于“myth”一词的翻译。尽管此词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著作中,而且多被翻译为“神话”“迷思”。但笔者认为,在《媒介仪式》一书中,译者采用音译的方式将其翻译成“迷思”,这会给读者理解库尔德里要表达的原意带来困难。“Myth”主要出现在“Myth of Social Center”以及“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er”的章节中。“迷思”的翻译方式,给读者最直接的感受是一种“不确定的、令人迷惑的思想”,然而,原著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虚构的或令人捉摸不透的现象或存在”。因此,此处如果翻译为“幻象”也许更贴合原意,如“社会中心幻象”和“媒介中心幻象”,这将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去理解“媒介构建出来的一个虚拟的或者是不存在的、而受众却认为其真实存在的社会中心”这一核心概念。
在《媒介仪式》一书的前言中,尼克·库尔德里写道:“对于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些现象非常的奇怪,甚至不可思议……人们只知道自己对电视越来越熟悉,对电视呈现给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熟悉。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当媒介存在的时候,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变化,又是如何带来这些影响和变化的。想要理解媒介,首先需要产生好奇。”带着这样的好奇,尼克·库尔德里逐次为我们解开了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来源的问题。他的探索,让我们看到媒介仪式背后,媒介对符号资源和空间场域的控制,使我们有方法了解媒介如何给受众植入“媒介代表社会的中心”这一理念。这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无论是对媒介权力在传统媒体时代集中化的解读,还是对其在新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的探讨,都能够提供帮助和启发。笔者深切希望这本译著,能够为中国传播学界认识尼克·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理论打开一扇大门。■
孙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