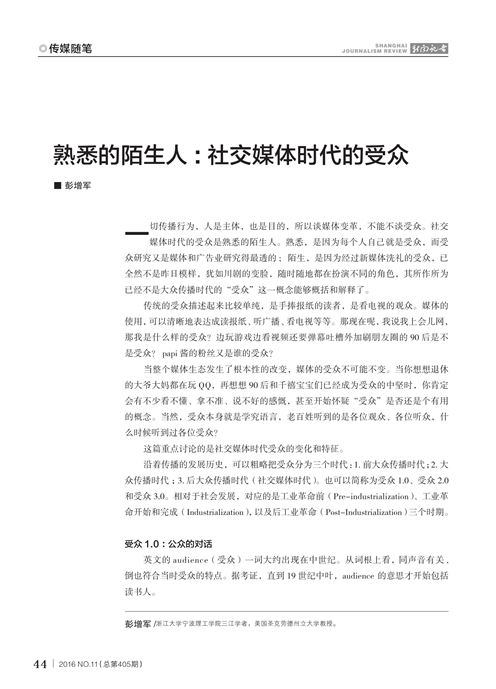熟悉的陌生人:社交媒体时代的受众
■彭增军
一切传播行为,人是主体,也是目的,所以谈媒体变革,不能不谈受众。社交媒体时代的受众是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每个人自己就是受众,而受众研究又是媒体和广告业研究得最透的; 陌生,是因为经过新媒体洗礼的受众,已全然不是昨日模样,犹如川剧的变脸,随时随地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其所作所为已经不是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这一概念能够概括和解释了。
传统的受众描述起来比较单纯,是手捧报纸的读者,是看电视的观众。媒体的使用,可以清晰地表达成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等等。那现在呢,我说我上会儿网,那我是什么样的受众?边玩游戏边看视频还要弹幕吐槽外加刷朋友圈的90后是不是受众? papi酱的粉丝又是谁的受众?
当整个媒体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媒体的受众不可能不变。当你想想退休的大爷大妈都在玩QQ,再想想90后和千禧宝宝们已经成为受众的中坚时,你肯定会有不少看不懂、拿不准、说不好的感慨,甚至开始怀疑“受众”是否还是个有用的概念。当然,受众本身就是学究语言,老百姓听到的是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什么时候听到过各位受众?
这篇重点讨论的是社交媒体时代受众的变化和特征。
沿着传播的发展历史,可以粗略把受众分为三个时代:1.前大众传播时代;2.大众传播时代;3.后大众传播时代(社交媒体时代)。也可以简称为受众1.0、受众2.0 和受众3.0。相对于社会发展,对应的是工业革命前(Pre-industrialization)、工业革命开始和完成(Industrialization),以及后工业革命(Post-Industrialization)三个时期。
受众1.0:公众的对话
英文的audience(受众)一词大约出现在中世纪。从词根上看,同声音有关 倒也符合当时受众的特点。据考证,直到19世纪中叶,audience 的意思才开始包括读书人。
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意义就宽泛多了,几乎囊括了一切使用大众媒介获取信息的人,书报有读者,电台有听众,电视、电影有观众。
“受众”这一中文对应词的出现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传播学传入大陆以后。受众这个中文翻译相当形象、准确:“受”可引申为被动的接受,而人多为“众”。
这个时期的受众特点在于“众”,公众的众,即英文的Public。往前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罗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理想国时代。这个阶段的“受众”简单明了,是听众和观众,是即时的、现场的,是对话和交流;它的内容是政治,社会、文化等公共事物;它的形式是演讲,是戏剧;它的发生地是广场,是剧场;它是面对面、非媒介的;它是小众的。当然,对于那个时期的受众的性质也不能理想化,因为它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公众对话。一如传播学者罗塞里(David Kawalko Roselli)所说,在古希腊和罗马,公众并不是全部,别忘了还有阶级,还有奴隶。自此两千多年,王朝兴亡,沧海桑田,传播的媒介与时俱进,但是,传播的形态和“受众”的基本特性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受众2.0:注意力商品
1440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书籍成为大众消费品,人类社会开始走进大众传播时代。随后五百年间,特别是近一百多年,传播科技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飞跃,电子模拟技术达到顶峰。印刷技术、摄影、电报、电话、电影、电视等媒介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改变了人本身。
前面说过,1.0时代,“受众”的本质是公众的对话,那么,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最重要的特点或者本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任何一本大众传播学教科书都可以洋洋洒洒地讲一两个章节,不外乎说受众是线性传播模式中被动的大多数,在政治生活中是被忽悠的对象,在经济生活中是消费者等。传播学几乎所有的理论,比如宣传理论、涵养理论、议程设置、批判理论等都是以此为基本前提的。所谓受众就是信息传播的对象和接收者,是被影响者。
这些理论取向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点到大众传播时代受众性质的穴位。接收信息其实并不是受众的本质,更不是媒体组织的终极目标。受众是消费者不假,但不是媒体内容的消费者,而是工业商品的消费者。注意力经济模式下,广告商才是媒体的客户,而受众不过是媒体用来同广告商交换的商品,所以,刻薄一点讲,媒体生产的不是内容,而是受众,受众的本质是商品。
所以,粗暴简单的结论是,大众传播的过程就是把1.0的公众变成受众的过程,把公民的对话(conversation)变成媒体单方的训话(lecture)。
即使标榜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体,也总是沉浸在把关人的傲慢之中,从未真的降下身段,同受众进行平等的对话。曾有《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的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在回复读者的邮件里这样教训道:“你不赞同我的观点或者感觉被我的言论侮辱,这个实在不重要,至少对我来说。这不是对话,而是上课。你要么洗耳恭听,要么走人,而不是站起来嚷嚷。”
也许有人要问,大众传播时代受众的本质是商品,这样的结论是不是过于武断、片面?是不是太不厚道?毕竟新闻媒体特别是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在苦撑着新闻专业主义,我们不是还有调查新闻,还有普利策奖吗?
问的有道理。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上限;另一条是资本、市场、商业的底线。新闻专业主义相对的是培育公众(public),而资本的底线,就是要把受众变现。这两条线重合是例外,分离是常态。顺便提一句,新闻学院不是既有新闻专业,还有广告和公关专业吗?正是这两条线的相互作用,看似分裂,其实和谐。
两条线的较量中,毕竟资本是底线。把受众变成整天盯着电视的所谓沙发土豆(couch potato)符合电视台作为企业的根本利益。遥控器不是为了方便,而是鼓励懒惰。所谓媒体忠诚度,无非就是“葛优瘫”。
受众3.0:熟悉的陌生人
二十世纪的百年间,媒介科技发展可谓风起云涌,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必然威胁到旧有体制以及既得利益集团,新旧力量冲突激烈。仔细观察一下冲突过程和结局,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既有媒介体系在一遍遍的“狼来了”之后,不但化险为夷,而且还能因祸得福。电台的出现并没有颠覆报纸,电视也没能让电影公司倒闭。媒体帝国犹如独裁政权,对于任何挑战,首先是扼杀在摇篮、赶尽杀绝,如果不能奏效,便会招安、利用和改编。
好莱坞对于录像机的抵制,诉讼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要求法院对录像机全面封杀。报纸也曾经严禁电台广播自己的内容。电影业曾经死活不向电视台出售电影的播映权,不管你出多大价钱,就是不卖,就是要饿死你。而三板斧过后,如果实在顶不住,就会去拉拢、招安和利用。比如报纸会买下电台,电影公司会经营自己的音像出租网络等等。
实际上,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传统媒体采取的也是这个套路。先是因为傲慢而蔑视,觉得网络这东西成不了气候,后来被忽悠,免费提供内容上网,等醒悟过来,马上又开始封杀,同时建立自己网站,搞媒体融合。
可惜这一次这些威逼利诱的招数统统不灵了。为什么?因为被从未防范过的闯入者搅了局。而这闯入者不是别人,正是被纽约大学罗森教授(Jay Rosen)称作“原来被叫做受众的人”(PWFKA,people who wer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罗森是在2006年的一篇博客里提出这个名称和观点的。这篇经典博客可以说是受众起义的宣言书,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三句话:我们“受“够了,我们要发言!我们要参与!我们要自己玩!
这些“原来被叫做受众的人”说话的底气为什么这么足呢?因为此时的受众已经武装起来,拥有了媒体生产工具和手段。传统媒体生产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消费者同生产资料的脱离。媒体生产同其他工业生产一样,是资本行为,普通受众很难有足够的资本去打破垄断、进入这个行业。你也许可以咬牙跺脚自己出钱去采访,去写作,去制造内容,但你再咬牙恐怕也咬不出一个发行渠道的钱。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但使一般的内容制造成本降低,而且使出版和发行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和出版商。由此,媒体生产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学者希尔斯(Doc Searls)早在2001年就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媒体生产一大特征是,内容生产是围绕生产机器的远近来组织的。也就是说编辑部犹如一个车间,码字工(新闻工作者)必须同机器靠近才能生产。新媒体革命改变了这一生产方式,一部爱疯(iPhone)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的生产流程。而更可怕的是,这些闯入者不仅全副“武装”,而且全世界的闯入者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他们不但闯入传统媒体的世袭领地,而且还开辟领地,自己嗨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媒体大佬对于这些网民的喧哗并不在意,比如web 1.0 阶段的博客和BBS。为什么,因为BBS 无非是一群闲散的“盲流”在打嘴仗,缺乏公信力,吸引不了广告商,而博客大部分还得依靠传统媒体平台来获得流量。直到有一天,线上分类广告(craglist)出现,使媒体大佬们的三观尽毁:居然可以没有内容直接玩广告!媒体这才紧张起来,感觉自己被掏空,彻底失控了。
受众与用户,控制与自由
传统媒体的盈利模式是通过对资源和渠道的垄断来控制受众,从而控制广告商。传媒业从这种控制中赢得了垄断利润。而互联网把这种商业模式打乱了,媒体上百年的好日子终于到头。
新媒体最大的功德是它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解放了的受众可以不再被毫无选择、毫无抵抗地卖给广告商。曾几何时,媒体犹如一个专制的君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它说发生了什么就是什么,版本不容置疑,正如美国著名新闻主持人克朗凯特(Cronkite)的经典结束语:“就是这么回事(That’s way it is)!”虽然说美国宪法规定人人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如《纽约客》著名撰稿人赖博宁(A.J. Liebling)所说:“出版自由只属于那些拥有出版社的人。”
媒体控制的丧失至少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受众的分化;二是受众的独立。分化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包括内容的分化和信息平台渠道的多样。如果媒体的控制力还在的话,无论如何分化,肉再碎还是烂在锅里。电视台多开一个频道又有什么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连电视都不看了,纵然有一万个频道又有什么用?人们可以去Youtube,可以去看网红直播,兴致来了干脆自己直播。以前的受众,好比是有户口的老街坊,跑不了。而现在的受众都是由着性子来,捉摸不定,因为他们不再依附于媒体,可以独立自主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来进行媒体消费,而且可以直接加入到信息的采集和生产中,时刻提醒、挑战媒体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显然,此“受众”已经完全不是彼“受众”,同时可以有多个名头:读者、观众、听众、网民、消费者、用户、参与者、业余记者、出版商、自媒体等等。
面对如此复杂的熟悉的陌生人,媒体从经营模式上又该如何考虑呢?从过去十多年的实践来看,无外乎两种模式:一种沿袭了注意力经济的套路,想尽一切办法来吸引、抓住受众。一只手死命抓住传统媒体受众,毕竟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依然是大头,即使知道没有明天,但今天的钱总是要赚的;另一只手在网络上招揽、培养受众,浏览量、点击量是关键词。这种模式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把用户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
另外一种模式把受众作为用户或者客户,报社和电视台的付费墙就是这个模式。这一模式说白了,就是要受众赎身,花钱来买不被卖掉的自由,即不看广告的自由。当然,任何媒体都不会采取单一模式,而是两种模式并行并存,一是因为这两种模式都还比较有效,二是因为媒体变革转型,一切都很难说。如果只认准一棵树,难保不被吊死得很难看。
其实在这两种模式之下,有一个更大、更深层的经营模式,细思极恐,那就是大数据。无论是受众也好,用户也好,你留下的最值钱的不是你的眼球或者你的订阅费,而是关于你的信息。一个透明的你会更值钱,更好卖。■
彭增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