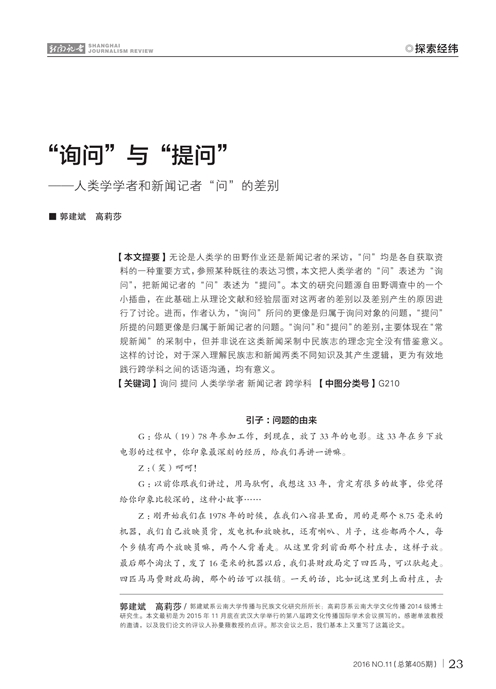“询问”与“提问”
——人类学学者和新闻记者“问”的差别
■郭建斌 高莉莎
【本文提要】无论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还是新闻记者的采访,“问”均是各自获取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参照某种既往的表达习惯,本文把人类学者的“问”表述为“询问”,把新闻记者的“问”表述为“提问”。本文的研究问题源自田野调查中的一个小插曲,在此基础上从理论文献和经验层面对这两者的差别以及差别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进而,作者认为,“询问”所问的更像是归属于询问对象的问题,“提问”所提的问题更像是归属于新闻记者的问题。“询问”和“提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常规新闻”的采制中,但并非说在这类新闻采制中民族志的理念完全没有借鉴意义。这样的讨论,对于深入理解民族志和新闻两类不同知识及其产生逻辑,更为有效地践行跨学科之间的话语沟通,均有意义。
【关键词】询问 提问 人类学学者 新闻记者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G210
引子:问题的由来
G:你从(19)78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放了33年的电影。这33年在乡下放电影的过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经历,给我们再讲一讲嘛。
Z:(笑)呵呵!
G:以前你跟我们讲过,用马驮啊,我想这33年,肯定有很多的故事,你觉得给你印象比较深的,这种小故事……
Z:刚开始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在我们八宿县里面,用的是那个8.75毫米的机器,我们自己放映员背,发电机和放映机,还有喇叭、片子,这些都两个人,每个乡镇有两个放映员嘛,两个人背着走。从这里背到前面那个村庄去,这样子放。最后那个淘汰了,发了16毫米的机器以后,我们县财政局定了四匹马,可以驮起走。四匹马马费财政局掏,那个的话可以报销。一天的话,比如说这里到上面村庄,去一天的话,是五块钱一匹马,(四匹马)二十块钱,那个的话可以报。就这个样子。
G:就是说在这三十几年的放电影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
Z:有,说不完!哎呀!说不完!
G:你挑一两个你记得的故事给我们讲讲。
CH:挑一点精彩的。
Z:挑不出来啥精彩的嘛,呵呵!
CH:比如说有时候你们去放的时候,突然马跑掉啦,找马,或者是下大雨,下大雪,或者是怎么冷,之类的,你就想想,当年给你的一些记忆。
G:像上次你给我们讲的,去那个卡瓦白庆乡,是要用马驮的,是不是?
Z:对。
……
以上对话,是本文作者之一(即对话中的G)和其他课题组成员①2011年8月在西藏昌都地区②八宿县邦达镇对一个电影放映员所做的访谈中的一段。这个访谈是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得以较为完整地重现当时的情景。在后期整理这些视频资料时,无数次地观看这段视频,每次均有这样的感觉:这样对话更像是新闻采访,而不是人类学的访谈。
自2010年6月起,本文作者之一就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区从事与流动电影相关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简单说来,就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这项研究前后持续了5年多。在调查中,除了参与观察之外,访谈也是获取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
这些年的调查中,在具体的资料收集方式上,除了用笔记录,还使用了录音、录像等方式(自然是首先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在拍摄视频资料时,课题组希望日后能从这些视频素材中剪出一些片子,因此也就希望访谈对象在面对镜头时能讲出一些“精彩”的故事。正是出于要得到一些“精彩”故事的考虑,当访问者觉得访谈对象讲述的内容不够“精彩”时,便迫不及待地进行追问,甚至是“诱逼”。因此才有了上面那段听起来更像是新闻采访的谈话。
由此,引发了我们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做的是田野调查,为什么通过视频资料重现当时的工作情景时会有像新闻采访的感觉?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受过新闻学训练的人做的有些田野调查,也会被有些人类学学者认为更像是新闻采访?是否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研究,它靠得住么?进而言之,人类学者的“问”和新闻记者的“问”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个边界是否能够跨越?何以跨越?
这样一些研究问题,直接来自田野研究的实践。本文的两个作者,最初接受的均是新闻学的训练,一个目前还从事与新闻采访相关的教学,另一个在媒体做过记者。在目前的研究实践中,两位作者主要采用的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跨界”经历,以上这样一些问题不时会让我们感到惴惴不安,当遭遇人类学者的“质疑”时,我们更加诚惶诚恐。这倒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处于这样一种学科边缘、力图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寻求某种合法性的焦虑,而是自己身处其中,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感受或许会比“局外人”要更真切一些,并且也觉得某些问题有进一步辨识与澄清的必要。此外,在中国大陆近十余年来新闻传播研究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但是这些相关成果,也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引来了一些争议。③以上种种“质疑”或“争议”,除了同样可能存在的学科偏见、甚至是知识的缺乏之外,也意味着这两个有交叉但同时也有区别的学科或是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的值得深究的“问题空间”。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有些学生和年轻学者也尝试着借鉴人类学的方法来指导新闻传播的业务实践和学术研究,但若对两者之间的界限或联系没有清楚的认识,或许又会引出一些新的麻烦。由于新闻学和人类学的异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问题,本文只想沿着我们此前提出的研究问题来做一个具体的讨论。并且,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想谈区别。谈区别并非是要刻意划清界限,而是在某个层面上厘清这两者的关系。
一、通过文献探寻解答
关于这方面问题,包括本文作者之一的国内学者,也曾做过一些讨论,④但是那些讨论主要讲的是民族志与新闻可能存在的联系。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感觉到,在强调联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差别。如果只讲联系,不讲差别,或者说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利于讲清问题。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侧重来谈两者的差别。其他问题,另做文章再去讨论。
1985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格林德尔主持召开过一个讨论会,探讨人类学的研究技巧在对现代文明的认知和报道中所起的作用。参加会议的有佛罗里达州的一些新闻记者,另有两位人类学学者、三位新闻学教授、两位写作系教授和几位学生。⑤会后,格林德尔与罗宾·罗兹写了《论新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点》,发表在美国《新闻教育家》杂志1987年冬季号上。此文后来经孙向辉、王建刚编译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1989年第1期。这篇短文分了三个小标题,其中一个小标题是“人种论和新闻学”,译者这里所翻的“人种论”,应该就是现在更为通行的译法——民族志。在文章的这一部分里,格林德尔等对民族志与新闻学的“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进行了反思。简而言之,在格林德尔等人看来,民族志更接近于真理,而新闻更主要是对支离破碎的事件的描写。因此他们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和敏锐思想注入新闻,会改进新闻报道的真理性价值”。⑥格林德尔等的说法,稍做简化,或许可以表述为:民族志关注的是“理”⑦(至于这里所说的理到底是真理还是理论,暂时按下不表),新闻关注的是“事”。在我们看来,这一点的确是触及了民族志和新闻的重要区别,但是对于他们认为的“人类学的知识和敏锐思想注入新闻,会改进新闻报道的真理性价值”的观点,或许适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新闻报道(如深度报道等),但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或是常规新闻)而言,格林德尔等人的建议或许很难奏效。正如格林德尔等人自己所写的:“新闻报道是迅速而不连续的,这种性质使它对原事件的报道不全面,甚至经常不准确。新闻报道本身的性质,促使人们对事件抱不偏不倚的观点,而且不介入事件。” ⑧因此,格林德尔对于民族志与新闻的区别,虽然讲到了某些重要之点,至少在这篇短文中,并未把相关问题讲得很透彻。
如前所说,格林德尔等人只看到了“理”和“事”的区别,虽然这也是民族志和新闻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仅仅止步于此,是不够的。
格林德尔等人在1980年代中期举办这样一次研讨会,和美国人类学界始于1960年代末期,并于1970年代形成高潮的一个议题——即如何利用媒体扩大美国民众对人类学知识的认知密切相关,关于这方面问题,本文作者之一在相关的文章中也有所提及,⑨不再赘述。
在我们所见到的关于新闻与民族志之间的异同的言说中,大卫·费特曼(David M.Fetterman)的说法是最精彩且明白易懂的,他首先这样写道:
(做民族志)这份工作非常类似于好研究的记者所干的活:会见相关的人们,查看记录,在矛盾的观点之间辨别它们的可信性,寻找特定的利益集团与组织之间的联系,然后为关心此事的大众和职业同事们撰写一个故事。⑩
接着,费特曼又写道:
然而,善于调查的记者与民族志学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记者意图发现不寻常之事——凶杀、飞机失事或银行抢劫,而民族志学者则描述人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11]费特曼是在讲如何做民族志时讲这一番话的,接下来,费特曼并未对做民族志和做新闻的联系和区别做进一步的辨析,而是转向了如何做民族志。对此,吴飞等人认为费特曼的这一说法是“以偏概全”,[12]在文章中,吴飞等人提供的证据是19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亲近性新闻”(Intimate Journalism)。但是这样一种新闻中的特殊形态是否能够完全否定费特曼的判断呢?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还有待商榷。
正如吴飞等人所说的,虽然费特曼的讨论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费特曼对于“善于调查的记者与民族志学者之间的关键区别”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一针见血的。的确,就吴飞等人所说的“亲近性新闻”而言,与费特曼的标准不一定完全吻合,但“亲近性新闻”毕竟是新闻中的一种特定形态。吴飞等人在这里所说的“亲近性新闻”,属于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的范畴,关于这方面问题,在人类学家的讨论中也提及过,正如人类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批评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所写的:
对于民族志或历史叙述中虚构手法的运用这一问题,已经有过一些讨论,不过最为精致的讨论是在新闻学当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在(19)60年代有关新派新闻学(New Journalism)的讨论中产生出来的。[13]就“新新闻学”而言,它只是新闻中的一种特定类型,甚至在新闻学中还是一种饱受争议的新闻类型。[14]因此,若要以此来否定费特曼的说法,证据显然也是不足的。
在我们看来,既往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在有些方面说不清、道不明,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并未对人类学学者的最终产品——民族志和新闻记者的“最终”产品——新闻这两者的具体含义做出明晰的界定。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想对相关问题进行一点必要的说明。
二、什么样的民族志?什么样的新闻?
就民族志而言,借用有的学者的最通俗的表述,即“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15]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表述,用在早期的民族志,即有些学者所说的“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即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的)是基本适用的,在这个阶段或时代,民族志和同一时期的新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民族志的“科学性”时代之后,以及此后民族志学者对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反思,进而开启了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之后,上述说法就过于宽泛了。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逐步确立了一种“专业化”标准,其和新闻的交集也渐渐缩小。相较于民族志,新闻在最近一百多年来也经历了一个逐渐专业化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的具体呈现形态也不断丰富,同时,因为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新闻时效性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并且伴随着专业的媒体生产行业的日益壮大,民族志和新闻之间的区隔越来越明显。在此过程中,如同前一部分里我们讲到过的出现于1960年代美国的“新新闻学”,这类文本是新闻、文学和民族志的一种杂交品种,就这一类“混合文本”而言,民族志和新闻之间是几乎没有明显的界限的。此外,新闻中的某些深度报道,[16]或者是伊丽莎白·博德[17]所说的“文化新闻”(cultural journalism),在采制时间、工作方式上,也和民族志有类似之处。除此以外的绝大多数新闻,和民族志渐行渐远。
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中近年来对美国芝加哥早期社会学派讲得比较多,其中的代表人物杜威、帕克等人对于新闻的理解,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的讨论。但是他们对于新闻的理解,其实也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这种差别,和我们这里所讲的民族志和新闻有点关系,因此可以简单说一说。
有学者把杜威对于新闻的理解称为“有机知识”,并且认为:“作为杜威传播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知识’新闻观首要的是一种将‘新闻’视为应用科学探究精神、解决社会问题、建构共同体的新闻功能观。” [18]此后,曾经和杜威一起参与过《思想新闻》创办的杜威的学生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也对新闻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问题进行过讨论。依照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知识的分类[19],帕克把新闻划归“感知”(acquaintance with)知识的范畴[20]。“在帕克看来,‘理解’的知识是从对世界的系统调查而来,它基于我们对世界所提出的特定问题,特别是与科学研究所创造的那些正式的和逻辑的探究方法(formal and logical apparatus)关联,而‘感知’知识则基于个人经验的积累”。[21]在帕克对于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的新闻的讨论中,他倒是未直接提到新闻和民族志的关系,但是在后来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直接把这个问题的源头找到了帕克那里。[22]在我们看来,帕克对于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的新闻的讨论中,更多强调的是作为“感知”知识的新闻和其他“理解”知识的区别。帕克对于新闻的理解,与杜威等人并不相同,正如孙藜所说:“‘新闻’在杜威和福特的眼中,不能像帕克后来的理解那样,只满足于关注孤立的、变动的事件,而是要揭示这些事件对人们共同生活、甚至上升到‘人类生活’的意义上来。” [23]因此,在我们看来,帕克对于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的新闻的讨论,更多的是强调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类型新闻的特殊性,虽然从帕克的个人经历以及学术实践来看他应该比杜威等更加理解民族志,但是他对于新闻的理解,似乎比杜威更“专业”。反之,再看杜威的那种“有机知识”的新闻观,似乎与民族志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上文引用过的“揭示这些事件对人们共同生活、甚至上升到‘人类生活’的意义上来”的观点,这和民族志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帕克对于新闻的理解,更加接近于“专业”的标准,并且和新闻专业实践更加吻合;而杜威对于新闻的理解,更加抽象化、学术化,甚至和前文中所讲到的格林德尔等人讨论民族志时所说的“民族志更加接近于真理”有几分相似。
回到前面所讨论的问题,在两类不同的知识生产日益专业化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专业标准被确立,姑且不论那些具体的专业标准,在我们看来,前文引述过的大卫·费特曼所说的善于调查的记者和民族志学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是有道理的,即前者意图发现不寻常之事,后者则描述人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这样一种区别,也决定了新闻记者和民族志学者不同的问题导向。在新闻的诸多类型中,即便有少数新闻生产并非如此,但也不能由此否定在一般意义上这正是两者之间的关键差别。
在我们看来,就吴飞等人所说“亲近性新闻”或是更为宽泛的“新新闻学”而言,它们和民族志之间的确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在除此以外的“常规新闻”中,新闻和民族志之间,的确存在着费特曼所说的那种关键区别。因此在讨论新闻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明确新闻的具体含义,因为较之民族志,新闻的具体形态更加复杂,很难概而言之。在既往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的某些语义混乱,部分是由于未对新闻做出明确的界定。本文所说的新闻,指的是排除了那些交叉性题材,如“近亲性新闻”、“新新闻学”作品、报告文学、文化报道等交叉性题材之外的“常规新闻”。参照大卫·费特曼的说法,是对人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的描述,也不涉及那些与“新新闻学”相类似的及“实验民族志”等类型。
三、“询问”与“提问”:实践层面的差别
毫无疑问,无论是做民族志还是做新闻,人类学者和新闻记者均要通过问来获得相关的素材。参照既往相关的表达习惯,本文把人类学者的“问”称为“询问”,把新闻记者的“问”称为“提问”。前者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所编的著名手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中的“询问”(query)具有相同意义,后者则是新闻采访中的一种常用表达。正如有记者说的:“一个好记者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自己讲得如何,而在于如何让别人‘说’得精彩,因此‘提问’便是采访最先决、最重要的前提。” [24]在中国新闻业界,甚至有“提问是记者的天职” [25]的说法。因此,“询问”和“提问”,是我们对人类学者和新闻记者“问”的表述。这样一种区别对待,并非完全是词义上的区别,即便有人类学者也难免要“提问”,新闻记者也会“询问”,但是因为两者毕竟存在差别,因此在表述上我们也如此区别对待。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讲的“询问”和“提问”,它们既涉及具体提出的“问题”层面,还涉及这样一些具体问题背后的问题取向,即那些具体提出的问题(如何问),以及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问)。这样的说明,旨在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在这里把人类学者和新闻记者的“问”以两个不同的词语来指代。
如果读者接受了我们这样一种表述上的差别对待,接下来,我们想对两类不同的“问”的具体含义做出说明。
我们在上面说过,这样一种表述上的差别对待,不仅仅是词义层面的差别,因此,这必须结合具体的工作实践进行考察。
在这里,我们引用前面提到的“手册”中的一组问题来具体说明:
不管是偶尔收养还是故意送养的风俗习惯,都要调查以下几个方面:养父母的地位是等同还是低于生父母的地位?养父母与生父母是亲戚、氏族关系还是其他何种社会群体的普通成员关系?孩子在几岁离开养父母,离开后是否与养父母及他们的子女保持一定的社会关系?(例如:报血仇的义务或假的亲属关系)是否有报酬?如果有,要给养父母什么报酬?一个家庭的所有孩子是送给相同的养父母还是分送给不同的养父母?孩子通常在几岁离开他们的生父母,并在什么时候回到生父母身边?他们是否可以继承养父母?养父母对这些孩子有多大程度的社会、经济责任?什么原因导致当地出现抚育风俗?[26]以上问题是“手册”中讲到在调查“抚养风俗”时所列举的具体问题。通过这样一组问题,基本上可以得到对这种风俗习惯的较为完整的认识。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人类学者的“询问”的具体的问题样式。
当面对这样一种风俗习惯时,新闻记者通常不会按照人类学者“询问”的思路来“提问”,因为这样一种风俗习惯,它还不足以成为新闻。新闻记者可能会问的是:新闻在哪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新闻记者通常不会对此进行“提问”。若此,人类学者或许会留下来对此风俗习惯进行仔细“询问”,新闻记者则是继续去找其他的“新闻”,这样,两种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在田野调查中就分道扬镳了。
如果新闻记者在这样一种风俗习惯中“发现”了“新闻”,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该地区这样的“抚养风俗”十分盛行,并且超出了新闻记者的既往知识和经验,或者说是与新闻记者所理解的“常态”悬殊巨大。若此,新闻记者或许会进行“提问”。即便如此,新闻记者的“提问”也会和人类学者的“询问”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没有直接相关的案例可以引用,我们在此只能按照新闻记者通常的“提问”逻辑做出如下“模拟”:
该地区“抚养”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多少家庭中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家庭在该地区家庭总数中占比多少?在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的一般情况又是如何?进而,新闻记者或许也会做这样的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地区出现这样一种“特殊”现象?
从以上“提问”示例中可以看出,新闻记者“提问”的前提是这个现象与众不同,如果此类现象和新闻记者基于常识(或专业知识)的判断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没有差别,记者通常不会“提问”。
就本文开头我们讲到的例子而言,我们之所以要“诱逼”访谈对象给我们讲一些精彩的故事,并非为了获得某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而是在此之前在没有摄像机在场的情况下,访谈对象在一种较为轻松的交流状态下的确给我们讲过一些“精彩的故事”,或许是因为摄像机的在场,让他有些紧张,讲得有些平淡,因此我们才采取这样的“提问”。[27]或许是新闻采访中的“采访”二字,使得新闻的表达,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往往出现“采访”的情景(似乎这样会显得更加“客观”),而在人类学的影视作品中,即便进行了访谈,访谈者通常不出现在最终的作品中,看起来更像是“当地人”自己的讲述。关于这方面问题,还可以另外进行讨论,暂不多说。
如上所述,既然我们是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来从事研究,即便我们在某些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看起来更像新闻采访,也不能以此推断我们是在做新闻采访。因为人类学者“询问”和新闻记者“提问”的价值导向不同,关注点各异,“问”的方式自然不同,仅仅基于新闻记者的“提问”所得到的资料,的确很难形成合格的民族志文本。但是就本文开头提到的“困惑”而言,在某个特定的局部,的确暴露了我们这些学新闻的人的“本性”,但是就整个研究而言,我们的取向,是一种民族志式的,也即意欲去描述人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因此,对于某些人类学者的“指责”,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基于以上对“询问”和“提问”的说明与示例,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对本文开头处所讲到的困惑得以释怀。但是,以上回答还未完全达到我们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我们还想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
四、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
首先,我们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做简单的回答,那就是人类学者和新闻记者本来就是从事不同的工作。这样的回答,在我们看来,虽然结论不错,但缺乏必要的理,难以服人。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既要说明这两者有何不同,也要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前文中讲到过的大卫·费特曼的观点,即“善于调查的记者与民族志学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记者意图发现不寻常之事,而民族志学者则描述人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这样一种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它是成立的。这是在讨论“询问”与“提问”的差别的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因这个问题我们在前文中讲述过,不再赘述。
在我们对本文进行修改过程中,中南民族大学的陆敏女士2015年底在武汉大学听过我们这篇文章的原稿的报告,她发邮件就我们那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谈了一些想法,陆敏女士的想法很有启发。她从目的、方式、状态、结果等方面叙说了人类学(纪录片)访谈和新闻记者采访的差别,在“结果”一条中,她这样写道:
人类学(纪录片)的访谈结果更易于呈现一个开放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时空中,受访者的主体性得到尊重和发挥,随之而来即是其所承载的文化有了充分表达的可能。而这也是人类学者更愿意看到的。反之,新闻采访中,呈现出来的更可能是一个局限而封闭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受限的时空中,只来得及允许简明观点和简洁描述的表达,无法呈现更多丰富的细节和细腻的情感。[28]陆敏女士的这番话,让我们马上想到了潘忠党先生在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开篇的一句话:“传媒是局促的历史舞台。” [29]因为潘忠党这篇文章所考察的是我国传媒对香港回归的报道,因此,以上表述改为“新闻是局促的历史舞台”,似乎也并无不妥。在这里,我们倒不是要讨论新闻和历史的关系,而是想说陆敏所说的新闻采访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受限的时空”,和我们改写潘忠党的说法之后得的表述——“新闻是局促的历史舞台”,这两者之间,在理路上完全是相通的。
有记者曾这样说道:“人类学者是拥有两年截稿期的新闻记者。” [30]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却很好地说出了民族志和新闻在时效方面的差别。一个人类学者花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撰写出一个民族志文本,这对“时效就是生命”的新闻记者来说,几乎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当新闻事件一发生,记者就要采访,去“问”,挖掘材料、写出新闻并尽快刊播。在民族志研究中,首先强调的是“参与观察”,然后才是问、访谈,提问应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之上。人类学家Jean Lave讲述的一段经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参与观察与提问的关系:
当我首次去巴西时,行驶2000英里到巴西的中北部的一个小镇,我听说确实有印第安人住在那个小镇上。我还记得我当时难以置信的兴奋感。我飞奔出去,到镇上到处找,直到我发现这个印第安部落,我直接走向他们——然后,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想问:“你们有部族系统吗?”(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那样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一种了解他们是否有部族系统的提问方式。[31]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出,人类学者的“询问”需建立在参与观察之上,在研究对象所生活的环境中待上一段时间,在对当地的语言、日常、权力结构、社区道德政治等有一定理解和感受的基础上来提出问题,并对受访者所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长期的参与观察,很多“问题”已不言自明无须再问。而在某些情况下,记者为了保证信息来源的“有据可查”而明知故问,目的只是通过采访对象表达出记者想到的信息或观点,以示客观。在新闻记者的采访中,虽然也强调观察,特别是对细节的捕捉方面,但迫于文本生产时间压力,记者最便捷的方式便是采用直截了当的“问”来获取信息。
正是源于时效(或文本生产周期)方面的差别,人类学者的“询问”可以“慢条斯理”,新闻记者的“提问”则显得“局促”。人类学者可以较长时间地和访谈对象生活在一起,在“闲聊”中得到素材,新闻记者则通常很难这样,必须找个“正式”的地点,正儿八经地坐下来谈,尤其是在影像报道中。即便是无法坐下来谈,也需要记者紧扣所关注的问题对采访对象“穷追不舍”,甚至用上“诱逼”及其他“提问技巧”。
正因如此,与人类学者最终的产品“深描”相比,新闻记者的最终产品,更像是“浅描”。由于篇幅所限,这方面问题在这里也不做展开。
五、“询问”与“提问”:问题的归属
在前面追问的基础上,我们还想做这样的追问:从问题的归属来看,人类学者的“询问”和新闻记者的“提问”,到底是谁的问题?
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有读者会觉得奇怪。但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同样是讨论人类学者的“询问”和新闻记者的“提问”差别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32]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或许是我们这篇文章存在的一个最大争议,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收到某种“抛砖引玉”的效果,激发更多的讨论。
在我们看来,人类学的“询问”,更像是一种“学习者”的姿态,并且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因此所“询问”的问题,更像是研究对象自身的问题。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很多时候类似于“侦探”,这也就决定了他/她们所提出的问题,更像是记者的问题。[33]无论是人类学者的“询问”,还是新闻记者的“提问”,问题本身均由人类学者和新闻记者提出,并且均与研究对象和采访对象相关,但是这样一些问题经由不同的提问主体“问”出来,其问题的归属,就发生了变化。就人类学者的“询问”而言,其目的在于获得对“当地人”的文化的“理解”,因此其“询问”的问题指向,通常是朝着如何去理解这样一种文化的方向来“问”,这样的问题归属,更像是研究对象自身的问题;就新闻记者的“提问”而言,新闻记者基于某种价值标准(或新闻价值)对事实进行判断,进而进行“提问”,其目的在于得到“新闻”并把它在更大的范围传播,因此这样的问题归属,更像是新闻记者的问题。
人类学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问题,正如斯丹娜·苛费尔和斯文·布林克曼两位学者所说的:
我想要用你的观点来了解世界。我想以你了解事物的方式,知道你所了解的事物。我想了解你亲身体验到的意义,穿着你的鞋子散步,以你感受事物的方式来感受它们,以你解释事物的方式去解释它们。[34]因此人类学者在“询问”时,运用的各种所谓技巧也好、方法也罢,最终的目的是理解当地人的文化,寻找到某种规律,或是对当地人的文化做出阐释。这样的一种视角(或站位),在新闻采访中并非完全没有,如肯·梅茨认为的采访,首先是以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思想和信息的交换来促进较高程度的知晓,以达到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达到的知晓程度,其次才是在采访中追求人性化和戏剧化的成分。[35]在这一对采访的理解中,记者和采访对象是平等的,无主次,通过双方的交谈达到彼此信息的增量。这样的观点,其实在后现代民族志中,也有学者讨论过。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谈到他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对田野作业图景的理解时,把人类学者和研究对象的核心关系界定为“共谋”(complicity),用来代替既往的“亲密关系”。[36]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归属上的差别,主要对其进行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并无意对问题归属进行价值判断。同时,如同以往的相关讨论中时常被提及的,在新闻和民族志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新闻记者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是事实层面的报道,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也可能写出不错的民族志文本,甚至从新闻记者变成人类学学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转向”一旦发生,同时伴随着发生的是从“提问”到“询问”的转变。反之,人类学学者的某些传奇经历或奇风异俗,写出来之后,同样也具有新闻的意义。
六、有限的借鉴意义:民族志之于“常规新闻”
在前面部分,我们呈现了“询问”与“提问”的区别,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追问。我们在前面也做出过说明,这样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常规新闻”的采制中。即便如此,并非是说在“常规新闻”的生产中民族志的一些理念对于做新闻来说,完全没有借鉴意义。
在我们写作这篇文章期间,恰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2015年9月15日晚,中新网刊发了题为《云南最原始的傈僳族部落 烟酒不离手》的图片报道[37]。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发了国内一些从事傈僳族研究的学者的不满,并发表了回应(图1 图1见本期第32页)。
2015年9月24日,中国新闻社云南分社采编这组图片报道的记者和编辑公开发表了致歉信,承认了几点“重大失误”:
1.以“烟酒不离手”为视角观察报道少数民族同胞确实不妥,有猎奇的倾向,在报道导向上出现严重偏差;2.由于采访不深入,将剥青核桃导致的手黑误作抽烟所致,犯了严重的事实性错误;3.整组稿件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引起了外界对傈僳族的误读;4.由于把关不严,缺乏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政治敏锐性不强,特别是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学习不够,导致了稿件的轻率播发。[38]在我们看来,这篇报道主要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实性出入,即记者和编辑所承认的“将剥青核桃导致的手黑误作抽烟所致”;二是记者的“站位”(或视角)。后一点,记者和编辑似乎并未意识到。
在人类学中有一句几乎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是并未被很多“外人”所理解的话,那就是“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也就是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所说的“当地人的视角”(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就上述新闻报道来说,还谈不上“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来思考”,如果能够真正地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而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或许就不会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如果记者再多一点点人类学方面的知识,或许也不会在图片的文字说明中使用“原始”这样的字眼。多年前某电视台曾有一期“民生新闻”节目,讲的是城管执法(执法对象是路边摊贩),但是从电视新闻的画面来看,摄像机的角度,与城管的角度完全是一致的。而这样的新闻,还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新闻。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对于研究者的视角(或站位),有“主位”“客位”之说,[39]所谓“主位”,简单地说,就是“当地人的视角”;所谓“客位”,即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就上述这篇新闻而言,“主位”视角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否可以称其为“客位”,尚存疑问。[40]据我们的观察,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民族”的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由于篇幅的原因,这个问题也不在这里展开讨论。只想做三点简要说明:第一,并非是说在新闻报道中“客位”视角一定是不可取的,一定要从“主位”的视角来进行报道。但是新闻报道中的不少“偏见”,往往是“主位”视角的缺失而导致的。第二,新闻报道强调客观,这与人类学中所说的“客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客位”并非“客观”,“主位”并非“主观”。[41]第三,任何由记者呈现出来的“新闻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只有在记者、采访对象、受众之间搭建一个共享的意义体系才能有效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客位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意义理解的偏差。
结语
本文是源于作者在研究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所做的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或许也困扰着那些和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或体验的人。早期的那些“准人类学者”,怀着探寻远方的“文化之谜”的冲动,进入了各种“异文化”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那是最早的“民族志”,也是新闻。那时,没有现在所说的人类学,也没有新闻学。在过去百余年中,人类学、新闻学等均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确立了各自的种种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和新闻学虽然还有交叉,但渐行渐远。从当下两类知识生产的逻辑来看,至少在现有的“常规科学”阶段,人类学和新闻学是异大于同。由此,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问”问题的方式和逻辑。这只是当下的情况,未来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做出预测。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也有人类学者意识到了自身工作可能面临的危机,正如人类学家乔治·E.马库斯所说的:“今天任何人类学所关注的主题事实上都不可能没有被当代新闻界首先关注过,或者说新闻界已经更快且常常同样有效地承担起经典民族志的描述任务。” [42]马库斯这样的说法,或许会令某些新闻记者感到欢欣鼓舞。如果这样,或许我们就真的中了马库斯的“圈套”。新闻业界乃至新闻学界,对于新闻生产的反思,远远不及人类学者及人类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学者就指出,“现时代,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包含的内容远比传统的社会科学广泛)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人文学科面临着一种“表述危机”。[43]这样一种应该也包含新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似乎并未被新闻界(或是从事新闻学研究)的大多数人意识到。即便有人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相关的反思也明显不够。
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即便在“常规新闻”的采制中,虽然民族志和新闻存在很多难以调和的区别,但这并非是说民族志对于新闻完全没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涉及民族(或族群、种族)或文化等方面的报道中,人类学中所说的“当地人视角”,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关于这方面,在国内外新闻报道中,血的教训,并不鲜见。
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借鉴,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是合理的借鉴是建立在对相关知识系统、深入梳理基础上的。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我们方能知道哪些能借鉴,哪些不能借鉴,以及如何借鉴。“问”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思考方式,人世间的“问”也千差万别,在本文中,我们仅仅是聚焦于两种特定的“问”,对其进行了一种尝试性的讨论。想法和观点错谬之处,也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①在那次调查中,云南大学新闻系陈宇、李元昭及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展参与了访谈,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②2014年10月20日,昌都地区撤地设市获国务院批复,原昌都地区更名为昌都市。因访谈时并未更名,因此沿用原来的地区名。
③最近两年的相关争议,主要是围绕两篇硕士论文展开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云南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蒋易澄的《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2014),另一篇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次仁群宗的《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2014)。相关讨论在网络上均可查到,在此不再赘述。
④参见郭建斌、晋群:《新闻采访写作基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春霞:《民族志与新闻》,见郭建斌主编:《文化适应与传播》第120-13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⑥[30]布鲁斯T.格林德尔、罗宾·罗兹:《论新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点》,孙向辉、王建刚编译,《国际新闻界》1989年第1期
⑦从格林德尔等的表述来看,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科学民族志”阶段,这方面问题,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⑧布鲁斯T.格林德尔、罗宾·罗兹:《论新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点》,孙向辉、王建刚编译,《国际新闻界》1989年第1期
⑨郭建斌,《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0期
⑩[11]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第1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吴飞、卢艳:《亲近性新闻”:公民化转型中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
[13]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11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4]楼坚:《新新闻主义的复活》,《新闻大学》1995年第4期;芮必峰:《论新新闻学》,《潍坊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罗以澄,胡亚平,《挑战现实理性构建浪漫真实——解读新新闻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叙事结构》,《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
[15]这是高丙中在为《写文化》一书所写的代译序,标题为“《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见《写文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页。本文这部分里所讲的民族志的三个时代的相关资料,也引自该文。
[16]虽然深度报道这个词在新闻学中也是一个意义模糊的词,限于篇幅的原因,暂不展开讨论。
[17]S.Elizabeth Bird(2005).The Journalist as Ethnographer? How Anthropology Can Enrich Journalistic Practice.
[18][21][23]孙藜:《作为“有机知识”的新闻:杜威和“夭折”的〈思想新闻〉》,《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
[19]詹姆斯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感知”(acquaintance with),另一类是“理解”(knowledge about)
[20]ParkRobert E.(1940)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0Vol.5pp.669-686.
[22]S.Elizabeth Bird(2005).The Journalist as Ethnographer? How Anthropology Can Enrich Journalistic Practice.
[24]长江:《“提问”在采访中的作用》,《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
[25]王尔山所著的一本与英美报刊主编对话的书,就直接用这句话作为书名(王尔山:《提问是记者的天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6]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周云水等译:《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27]我很难去猜测访谈对象在有摄像机和没有摄像机的情况下心理上的变化,但是,我自己心理上的变化,是可以简单讲一点的。在摄像机的“监视”下我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问题和问题之间不敢有太多的停顿,有时,或许两个问题之间的停顿并不太长,但是因为有摄像机的“在场”,我自己担心问题之间的停顿是不是太长了;第二,因为想用所拍的访谈资料剪出一个片子来,因此,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希望访谈对象能够给我们讲一些“精彩”的故事,如果访谈资料仅仅是一种干巴巴的介绍,这样在后期剪辑片子时,也会比较为难。这也是任何一个做过片子的人均能体会的。
[28]2016年5月14日陆敏的邮件。
[29]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见《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31][34] [丹麦] 斯丹娜·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著,范立恒译:《质性研究访谈》第116、13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32]在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博士论文是如何磨成的”学术沙龙中,我们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简单的讨论,也引起了一些青年学者们的共鸣,这也正是激发我们去写作本文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起点。但是那时似乎并未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因此想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讨论。同时也感谢当时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各位。
[33]2015年11月底,我们在武汉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初次报告了这篇文章,评议人台湾政治大学的孙曼蘋教授认为这种说法不妥,认为新闻记者的问题归属是社会公共问题。对此,我们坚持原来的观点,若从这样一个宽泛的层面来讲,人类学者的问题同样是一种社会公共性问题,正如人类学家马库斯所说的“人类学从来都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维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2006:14)因此,在这样一个维度上看不到两者的差别。并且,如果把新闻记者的问题归为社会公共性问题,把新闻记者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主要的表达者,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35]肯·梅茨勒著,李丽颖译:《创造性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6][43]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2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37]由于此后“中新网”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原初报道可见:http://www.tibet.cn/news/roll/1442375528197.shtml。
[38]资料来源:http://www.yn.chinanews.com/news/2015/0925/8309.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报道和编辑这篇新闻的两位记者均是我所在的系的毕业生(本科),事情发生后,我也把这个案例在本科生的课堂上讲过。对于学者们的回应,同样也只是讲到了事实性“失实”的方面,缺少应有的学理方面的内容,并且也带有较为强烈的情绪。
[39]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概念最初是肯尼斯·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从语言学的术语——“音位的”(phonemic)和“音素的”(phonetic)中提出来的,后来经认知人类学引申到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见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40]更为妥当的表述或许是“记者中心主义”。
[41]ames W. Lett曾对人类学者和新闻记者对客观的不同理解进行过讨论,他认为:对于人类学者来说,客观意味着公正;而对新闻记者来说,客观意味着对每个报道中涉及的人的公平,后者即通常所说的“平衡”。转引自S.Elizabeth Bird(2005).The Journalist as Ethnographer? How Anthropology Can Enrich Journalistic Practice.
[42]J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著,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郭建斌 高莉莎/郭建斌系云南大学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高莉莎系云南大学文化传播2014级博士研究生。本文最初是为2015年11月底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第八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撰写的,感谢单波教授的邀请,以及我们论文的评议人孙曼蘋教授的点评。那次会议之后,我们基本上又重写了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