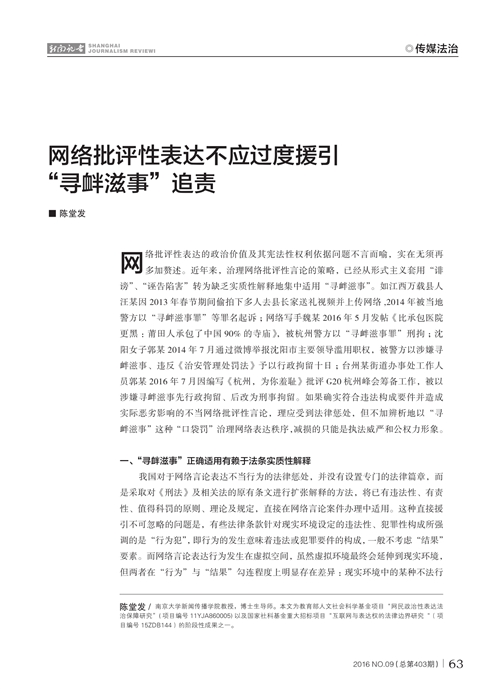网络批评性表达不应过度援引“寻衅滋事”追责
■陈堂发
网络批评性表达的政治价值及其宪法性权利依据问题不言而喻,实在无须再多加赘述。近年来,治理网络批评性言论的策略,已经从形式主义套用“诽谤”、“诬告陷害”转为缺乏实质性解释地集中适用“寻衅滋事”。如江西万载县人汪某因2013年春节期间偷拍下多人去县长家送礼视频并上传网络2014年被当地警方以“寻衅滋事罪”等罪名起诉;网络写手魏某2016年5月发帖《比承包医院更黑:莆田人承包了中国90%的寺庙》,被杭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沈阳女子郭某2014年7月通过微博举报沈阳市主要领导滥用职权,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拘留十日;台州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郭某2016年7月因编写《杭州,为你羞耻》批评G20杭州峰会筹备工作,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先行政拘留、后改为刑事拘留。如果确实符合违法构成要件并造成实际恶劣影响的不当网络批评性言论,理应受到法律惩处,但不加辨析地以“寻衅滋事”这种“口袋罚”治理网络表达秩序,减损的只能是执法威严和公权力形象。
一、“寻衅滋事”正确适用有赖于法条实质性解释
我国对于网络言论表达不当行为的法律惩处,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法律篇章,而是采取对《刑法》及相关法的原有条文进行扩张解释的方法,将已有违法性、有责性、值得科罚的原则、理论及规定,直接在网络言论案件办理中适用。这种直接援引不可忽略的问题是,有些法律条款针对现实环境设定的违法性、犯罪性构成所强调的是“行为犯”,即行为的发生意味着违法或犯罪要件的构成,一般不考虑“结果”要素。而网络言论表达行为发生在虚拟空间,虽然虚拟环境最终会延伸到现实环境,但两者在“行为”与“结果”勾连程度上明显存在差异:现实环境中的某种不法行为,其所产生的事实性后果与当然性推测结果基本一致。而网络表达行为所处的环境“虚拟性”,使得“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与当然性推测结果之间往往出现“断裂”,明显失当的网络言论可能会促成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但这种错误认识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以法益衡量为核心的法条实质性解释,才是弥补“断裂”、正确适用法律的有效手段。就此而言,对于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施加行政责任的“寻衅滋事”还是科处刑事责任的“寻衅滋事”,都必须基于合理的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寻衅滋事”行为的追责均有规定,但执法实践中,由于缺少适用精确限制原则,办案人员采取限缩或扩张性解释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网民对其行为后果所应承担何种责任存在不确定性。
《刑法》第293条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无事生非随意殴打、辱骂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有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从法条字面规定看,该犯罪行为具体表现有:随意殴打人,情节恶劣的行为;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行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必须出于故意并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犯罪结果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罪与非罪的界限方面,寻衅滋事罪的结果是行为恶劣或严重地扰乱社会秩序,没有达到恶劣程度或严重程度,或过失行为,均不构成犯罪。①网络批评性言论被禁止,显然只有可能与该条“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侵害法益有关。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则对“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为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其他公共场所”不应该包含网络空间,因为该条已经列出的“公共场所”都是现实环境空间,作为对象未穷尽的表述方式“其他公共场所”,在空间属性上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应该单列一条款规定,以示场所物理属性的区别。此外,从该解释第五条后半部分的规定“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可以间接推定,寻衅滋事的场所应该认定为现实空间环境,因为这些衡量要素的描述都强调了行为主体的行为所造成后果的即时性与在场性。这是刑法形式解释论的判断。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寻衅滋事”的行政责任追究,在是否构成违法性要件上应持同一判定标准。
实质解释论则主张,对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考虑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及程度,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出扩大解释,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对违法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行为的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②与形式解释相区别的是,实质性解释强调如果社会危害性是客观危害与主观恶性的统一,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使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形式解释则要求,如果构成要件只是违法类型,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就必须使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性。③现代刑法基本上都是既充分考虑保护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也会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在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本质就是有效地控制国家公权力的现代价值观面前,优先保障包含言论批评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和个人利益,是现代刑法理念的核心价值。地方权力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司法完全可以借用“法益”概念对法律进行不适当的扩张性解释。但网络表达使“法益”的内涵从物质利益、人身利益转向精神自由与政治价值时,司法不应当过分强调向超个人法益的国家利益、社会秩序、公共秩序挺进,因为这明显损害了刑法对个人权利与利益的保障机能。如果一味推崇个体利益对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让步,当“法益”成为国家刑罚权扩张的理论依据时,许多本不该纳入刑法控制范围的情形就顺理成章地被犯罪化。放弃了公民个人权利保护的核心价值,就会出现国家“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全面化,这与依宪法治背道而驰。“一个在刑事政策上有拘束力的法益概念,只能产生于我们在基本法中载明的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法治国家的任务。……法益是在一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者目标设定。” ④个体才是社会利益的真正主体和享受者,国家和社会只是为了更好实现公民个人的权利,因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必须能够和最终需要还原成为公民个人的利益,这才应该成为刑法真正保护的对象。
禁止寻衅滋事行为所保护的法益是抽象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修复程度主要取决于被批评的公权力主体对真实信息的公开与事件真相的澄清,执法实践中对言论导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则更多地出于缺少事实根据的主观认定。网络批评性言论的法益衡量标准之一是言论本身的法律价值。有些类型的言论表达权应该获得优先地位,比如刑法不禁止且宪法所保护的言论。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的核心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公民通过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言论,批评政治公众人物的言论以及正当行使宪法权利的其他言论,是落实宪法的行为。此外,宪法未明确保护但刑法未禁止的言论以及需要具体判断宪法是否保护及刑法是否禁止的言论,⑤对这些言论的限制亦应以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为前提,不应轻易科以罚责。只有宪法不保护且刑法所禁止的言论,如煽动分裂国家的言论、煽动恐怖主义言论,显著破坏宪法秩序的言论,才被追究刑事责任。法益衡量的另一重要标准是政治目标价值追求,民主政权应该设立充分容纳民众善意但并非正确的批评言论的机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此也一直强调与重申,如邓小平曾强调:“人民群众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⑥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指出:“对广大网民,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让互联网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二、“刑事优先”应当慎重介入网络批评性言论
执法实践中,被当作治理对象的网络言论总是先被执法主体界定为“谣言”,以散布谣言、寻衅滋事,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社会秩序作为刑事惩治优先介入的依据。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我们对于谣言的认知判断均采取否定性态度,倾向于将谣言本质界定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故意捏造的消息,无中生有,造谣者具有主观的恶意。实际上,对于复杂的谣言现象,这种认知、判断难免过于简单化。谣言作为个体认识与应对外在客观世界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其本质表述更具价值评估上的中立性:“虚假并非谣言的界定标准、谣言可真可假。其根本特征是区别于精确性的不可知性。” ⑦如美国心理学者奥尔伯特强调,谣言是未经证实性的信息:“谣言仅在缺乏‘证据的可靠标准’时盛行,该标准使谣言区别于新闻和科学”。⑧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对谣言的认知,则在“未经证实”之外加上了“非官方性”特征:“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 ⑨美国社会学者特·希布塔尼对谣言更持有积极的态度:谣言是一群人议论过程中产生的即兴新闻。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又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⑩因此,在未深入调查事实、仅以主观界定为“谣言”,就以寻衅滋事罪实施刑事惩处优先的措施,虽执法效力显著,但执法指导思想值得商榷。
在地方权力调控网络言论方面,执法实践中刑事优先倾向比较突出,作为“最后手段”的刑法,有时作为“优先手段”、“第一手段”使用。对不当、违法网络言论的治理,本该有多种手段和方式,道德的、纪律的、民事经济的和行政的,刑事治理方法只能是“托底”,只有在其他制裁性手段都确实无效时才不得已使用的措施。在犯罪认定和刑事介入问题上,应该摒弃“刑事优先”观念,倡导刑法的谦抑性。刑事优先意味着以威慑的方式表明言论自由是不能说错话的权利,但言论自由的本质就是允许并保障说错话的权利。谁也不会禁止“正确的”言论,保障“说正确的话”权利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承认只能有“说正确的话”权利,就需要一个人来判断正确与否,这个人当然是政府。说正确话的自由就变成了说与政府一致话的自由,而言论自由也包含了公民批评政府的宪法权利,这就违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刑法是具有保障法地位的特殊法,凡是为其他法律如宪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都可以成为刑法保护的内容,凡是为其他他法所不容的违法行为,都有可能进入到刑法的视野。而已经进入刑法规定中的犯罪正是行为人侵犯了为其他法律所保护的社会权益而其他法律又无法或无力处置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程度上的最高体现。可以不需要刑法介入的,刑惩手段必须谨慎使用。
履行起诉必要性审查对于网络言论案件阻却“刑事优先”、摒弃“有罪必诉”“有罪必罚”“轻保护,重打击”等错误观念具有实质性意义。起诉必要性审查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通过综合考量犯罪具体情形、国家利益、社会危害性、诉讼效益等因素,确定该案是否有提起诉讼或终止刑事程序的必要和价值。由于法律将相对不起诉范围限制在“犯罪情节轻微”且“依法无需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内,故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应将诉讼效益、国家公共利益、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等因素作为网络批评性言论案件的起诉必要性的审查要素,纵观该类案件的具体案情,多数案件都符合相对不起诉的条件。根据有关法律精神,以下具有违法性的网络批评性言论案件,经起诉必要性审查后,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或终止刑事程序的决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刑罚的案件,若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给予其刑事处罚的意义不大;过失类犯罪案件,若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疏忽大意过失,如网络转帖行为;预判刑罚为非监禁刑的案件,情节轻微,危害性不明显;无须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案件,无实质性危害后果。对该类案件采取起诉便宜主义,更有利于彰显法益。刑事诉讼的公理性原则之一即是比例原则、或适度原则,刑事追究措施,特别是侵犯基本权利的措施在其种类、轻重上,必须要与所追究的不法行为相适应。[11]对于轻微的犯罪,在适当、适度方面不采取苛重追究措施。执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仅仅以实现其目的为限度,对公民的惩罚必须控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内。刑事程序设计和运作必须注意刑事司法手段的节制性,避免损及公民人权。严厉的追究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活动。实行起诉便宜主义,要求检察官在审查决定是否起诉时,权衡罪行的轻重,对于轻微的犯罪,可以对被告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抑制“刑事优先”的另一种考虑则是确立有效的刑事检察听证环节。刑事检察听证是指检察机关在依据刑事诉讼法行使特定检察权并作出相应决定之前,就相关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听取诉讼参与人、利害关系人以及其他特定社会公众意见的司法监督安排,它是从程序正义立场出发实施的一项有利于保证公正行使检察权的程序,防止刑事政策的滥用。这对遏制地方公权力作为控告方的网络批评性案件的公正处理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实体规范的立法更多地适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条款,比如刑拘条件之一“社会危险性”,不起诉条件“情节显著轻微”、“情节轻微”等等。检察听证的公开性和参与人员的广泛性,能够促使检察机关谨慎思维,理性决策,有助于实现自由裁量权的制衡。在检察听证中,社会公众通过向检察机关陈述有关事实,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检察机关掌握事实真相,进而做出正确的司法行为。合目的的刑事检察听证必须遵循如下原则:其一,公开性。该原则强调听证的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外,刑事检察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参加听证人员除了案件当事人及利害相关人,还应该包括公众、法学理论与实务工作者以及新闻媒体记者;其二,合法性。听证制度的组织方应当是人民检察院,方案内容及程序实施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规范;其三,公正性。检察机关作出对被告人不利决定时,需要在听证场合给予利益相关人辩护或陈述理由机会,无偏袒见地听取反对方意见,衡量有无减轻处罚的事实及理由。■
注释:
①周其华:《中国刑法罪名释考》第406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②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③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④[德]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第15页,法律出版社2005年
⑤张明楷:《划定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检察日报》2013年9月10日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册)》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⑦卡斯·R·桑斯坦著,张楠迪扬译:《谣言》第9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⑧奥尔伯特著,刘水平等译:《谣言心理学》第10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⑨[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著,郑若麟译:《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⑩奥尔伯特著,刘水平等译:《谣言心理学》第10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彼得·斯坦著,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第37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陈堂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民政治性表达法治保障研究”(项目编号11YJA860005)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互联网与表达权的法律边界研究“(项目编号15ZDB14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