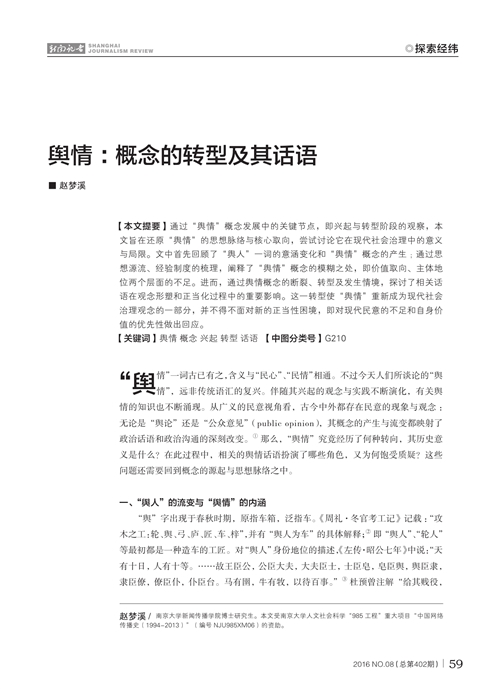舆情:概念的转型及其话语
■赵梦溪
【本文提要】通过“舆情”概念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即兴起与转型阶段的观察,本文旨在还原“舆情”的思想脉络与核心取向,尝试讨论它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意义与局限。文中首先回顾了“舆人”一词的意涵变化和“舆情”概念的产生;通过思想源流、经验制度的梳理,阐释了“舆情”概念的模糊之处,即价值取向、主体地位两个层面的不足。进而,通过舆情概念的断裂、转型及发生情境,探讨了相关话语在观念形塑和正当化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这一转型使“舆情”重新成为现代社会治理观念的一部分,并不得不面对新的正当性困境,即对现代民意的不足和自身价值的优先性做出回应。
【关键词】舆情 概念 兴起 转型 话语
【中图分类号】G210
“舆情”一词古已有之,含义与“民心”、“民情”相通。不过今天人们所谈论的“舆情”,远非传统语汇的复兴。伴随其兴起的观念与实践不断演化,有关舆情的知识也不断涌现。从广义的民意视角看,古今中外都存在民意的现象与观念:无论是“舆论”还是“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其概念的产生与流变都映射了政治话语和政治沟通的深刻改变。①那么,“舆情”究竟经历了何种转向,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在此过程中,相关的舆情话语扮演了哪些角色,又为何饱受质疑?这些问题还需要回到概念的源起与思想脉络之中。
一、“舆人”的流变与“舆情”的内涵
“舆”字出现于春秋时期,原指车箱,泛指车。《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并有“舆人为车”的具体解释;②即“舆人”、“轮人”等最初都是一种造车的工匠。对“舆人”身份地位的描述,《左传·昭公七年》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③杜预曾注解“给其贱役,从皂至牧” ④。因此“舆人”属于职位低微的吏卒,但不同于布衣百姓或奴隶。
“舆”的早期使用,常与军队士卒联系在一起。《周礼·夏官司马》列举了军中政官之属,从大司马、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至旅、府、史、胥、徒,共十等。⑤根据《辞源》,舆司马、舆帅、舆尉等都是掌兵车之官,⑥可见是从“舆”的本意“车”衍生而来。《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听“舆人之谋”、“舆人之诵”,被今天的研究者视为民众意愿的表达而广泛引用。但需要指出,这些词汇的使用都出于诸国纷争、军队相伐的语境,如“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⑦此时“舆人”可以理解为军中众人,但仍不能泛化地等同于平民百姓。⑧这种早期含义使“舆人”与“国人”、“庶人”等概念区别开来(虽然逐渐都可以泛指平民)。
进入汉代,“舆人”的内涵出现了变化。对前文《周礼》中的“舆司马”一词,郑玄注“舆,众也”,⑨这一理解被此后的许多著述所引用。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类似观点已十分盛行。《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舆,众也,佐皂举众事也”;⑩对僖公二十八年“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宋代林尧叟则注有:“晋文公患其摇动军心,听众人之计谋,顺众心也。” [11]通过后人的注疏可以看出,“舆”字早期带有的低微色彩被淡化,众、多之意进一步突出。
“舆情”一词的正式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末。《旧唐书·崔慎由列传》记载,唐昭宗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的诏书中,写有:“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 [12]此句意在彰显皇帝德行,能听取众人意见、体察民情。此外根据《旧五代史·末帝本纪下》,节度使石敬瑭因与后唐末帝不和,在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上章:“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舆情,宜推令辟。” [13]奏章指责皇帝身为养子继位不正,不能符合民意,应该让位。在早期的语境中,“舆情”泛指民情民意,是天子善治的重要体现;但具体内涵十分模糊,表达形式也不够明确。
到了宋朝,在包拯《致君·七事》一文的论述中,“舆情”的范畴有所明确。这篇文章主张对获罪流放的官员有所复用,指出当下:“罪罟实繁,刑网太密,甚伤清议,大郁舆情。昔匹妇含怨,三年亢阳;匹夫怀愤,六月飞霜。近岁窜逐之人,讵止匹夫匹妇之伦也,得不逆和气召灾沴乎!” [14]包拯认为,罪网过密会损伤清议,也使舆情郁积,并用“含怨”、[15] “怀愤”等情感强烈的词语作比。该文为认知“舆情”的主体和形态,提供了两层启示:首先是“清议”在唐宋时期更多是指在朝知识分子的议政现象,[16]而“舆情”的主体显然在精英群体之外;其次,“议”或“论”偏重显性、明确的意见表达,“舆情”则指向态度或情感层面,形成了更加明显的差异。现代民意研究中,意见一般认为是直观可察的,可以通过语言,或者投票、示威、罢工等行为表现出来;态度更加隐蔽,多是情感的本能反应而非理性认知。[17]如果处于意见环境或社会情境的压力下,意见与态度的偏离往往更为明显,“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典型的写照。
总体而言,“舆情”的内涵更接近民情或民声,与“清议”或“舆论”的差异较为显著;此外它可以涵盖百姓称颂,也可以代表民生疾苦,比“民隐”、“民瘼”等词义更加宽泛。在《辞海》中,“舆情”被解释为“众人的意愿和态度”,[18]体现了相同的理解。从唐至清,“舆情”的基本含义得以延续,没有明显的变化;随之产生的舆情观念,也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二、“舆情”的思想源流与价值取向
在“舆人”出现后,“舆诵”、“舆情”、“舆论”等表达随之产生。这些词语用来反映平民众人的心声,其核心可以回溯到西周兴起的民本思想。先秦诸子曾用丰富的著述来推崇民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19]汉武帝以降儒学定于一尊,民本思想更加具有正当性、甚至排他性。[20] 虽然民本强调“保民”、“重民”,甚至有约束君主专制的主张,但同时复合着“使民”、“牧民”的思想。从“载舟覆舟”到“防川”之论,某种程度反映了民本为用、君本为体的实质。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看,皇权既来自“天命”,又来自“民心”,形成了模糊的二元合法性。[21]这种合法性为“民心”或“舆情”赋予了正当地位,但民众的怨恨或爱戴,却不能使天子的统治丧失效力或合法化。统治者为了彰显自己受命于天、重视民心向背,还需要士绅精英的支持。在此关系框架下,士大夫以谏诤制度表达民情、直言天子过失;或者在皇权体制的内外进行清议、舆论活动。士绅阶层固然是“天子”与“民”的重要沟通渠道,但其意见表达不免是精英取向的。在这种民意基础上,“舆情”既是君主对百姓的安抚,又是士大夫们约束皇权的手段。
但是,无论士绅还是平民,对统治者的制衡都是相当有限的。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维系了社会控制与社会服从的延续;但这种平衡缺少制度性的保障,主要依赖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道德契约:只有统治者是道德楷模的时候,臣民才会顺从。[22]纵观历史,士绅不乏以悲壮扼腕之举对抗皇权:当礼义说教或天道制约被悬空之后,士大夫们甚至会走向极端,以死相谏。[23]对于皇权和民间舆论的博弈,林语堂认为共有三次高潮,即汉朝的公众批判和党锢事件,南宋的太学生爱国学潮,以及明代的东林党运动;他以现代民主政治思想肯定了舆论力量的存在,但不得不承认,在屡次对抗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民间舆论不堪一击。[24]与此同时,在崇尚“仁政”、“德政”的儒家政治思想中,作为个体的平民的利益也由统治者所定义,难以得到保障。历史的经验积累,内化成“敢怒不敢言”或“勿谈国事”的社会心理。由此可见,“民心”、“舆情”更多停留于抽象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没能进一步经验化(落实到个体层面);它缺少直接、及时的机制去约束昏庸暴虐,直至发展到用极端形式(如起义)喷涌出来。
基于上述思想,如何将“舆情”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同样十分关键。魏源通过《默觚·治篇》一文,把相诤之臣比作股肱喉舌、庶人为鼻息。为说明贤明帝王皆与庶人息息相通,他总结了历史中下情上达的多种形式:“至于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士传言,遒人木铎以徇于路,登其歌谣,审其诅祝,察其谤议,于以明目达聪。” [25]《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将舆情的传播制度归纳为四类:一是“采风制度”,古代通过采集民谣民歌了解民情,滥觞于夏商周;二是“谏诤制度”,臣子劝谏君主、为民请命;三是“巡查制度”,天子或官员出巡、访百姓疾苦;最后是“朝觐制度”,官员朝见皇帝,陈述地方民情与施政情况。[26]这些制度或方式,具有两个明显的共性:首先是“被动性”,即突显了统治者对舆情的主动收集或问询,产生舆情的主体——百姓庶人却沦为被动;其次是“间接性”,即舆情往往要经过士绅这一“中介”才能上达。以上方式还可能面临残酷、专横的言禁,根源如前所述,臣与民的说话权利最终归结于君主的道德修养,而非制度的保障。
由上可见,“舆情”并不是十分完善或清晰的概念。从思想源起看,“民心”或“舆情”虽得到正当性的辩护,但始终不能脱离“天命”的终极价值;在经验制度上,作为主体的普通百姓被弱化甚至替代,使舆情本身被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来表述。可以认为,“舆情”的核心取向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没有超出驭民之术的观念。
三、“舆情”的转型与话语建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浙江代表在递呈国会的请愿书中写道:“呈为图存济变,系命于立宪,而根据于国会,联名签请从速饬议实行,以定国是而顺舆情,仰祈代奏事。”并在文尾呼吁:“凡为中国臣民,咸盼国会迅速成立,以保皇室之万世一系,而人民亦得一日为立宪之国民。”?文中出现了三种“舆情”主体的表述,从“臣民”、“人民”到“国民”,折射出近代新旧观念的交织与碰撞——随着西式民主制度和价值的输入以及新民的培养,“舆情”失去了传统的思想土壤和主体,一度转入沉寂。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民意测验为代表的现代民意实践在中国起步。由于政治气候,此后的民调活动几经曲折、停滞,民主话语受到压抑,一度成为禁忌。到90年代,在学术或官方性机构之外,出现了商业化运作的调查研究企业;至此民意调查与研究的多元格局才得以形成。随着社情民意的高涨以及国家、社会的日趋重视,“舆情”作为一个“新鲜”概念走入公众的视野。新世纪初,互联网空间的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加速了它的流行与消费,并促生了大量舆情实践:从监测与分析技术、专业机构到舆情产业,甚至一种舆情体制。
在此情境下,想通过“舆情”的概念或观念来观察舆情现象,却发现困难重重:人们对它的理解已迥异于历史,又尚未对新的认知达成共识。
一方面,舆情现象的快速兴起主要源于政府决策观念与政治回应方式的改变。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部分指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2003年开始,中央与地方领导人逐步上网、对网络民意做出公开回应;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制度之一,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也在各级政府中建立起来。由此,“舆情”从历史中走出,开始指向一种现代的民意现象;其主体也从“舆人”变为具有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的“公众”。
另一方面,人们对“新”概念的定义仍存在许多分歧。早期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中,王来华将“舆情”定义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以突出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含义。[28]丁柏铨认为舆情即是民意,包括公开或未公开表达的意见与议论,但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囿于社会政治态度的范畴。[29]张克生的界定最为宽泛,认为“舆情”是客观的社会情况与主观的民众意愿的综合,即社情民意。[30]从现有文献看,“情”的含义实际覆盖了多个维度,包括情感或情绪(sentiment)、意愿(will),以及情况或情势(circumstance)等。
概念层面的争议,与舆情话语的复杂多变密切相关。舆情话语是对客观舆情现象的社会建构,包括人们对舆情的定义、讨论与评价,以及使用的话语结构。它关注“舆情”的能指、所指如何在某种情境中结合起来;不同话语的竞争和对抗,导致了“舆情”本身的不确定性。
在当下的概念或观念中,可以发现多种显著的话语:较早出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一种政策话语,旨在通过舆情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致力于政策服务。科学话语主张科学客观地还原舆情历史,与西方民意研究加以比较,寻找跨越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分析框架。民主话语则针对“舆情”内在的民主诉求,讨论其在政治沟通中的功能或局限。这些话语的界限不断变化,相互渗透与竞争,形成了话语的互文性。如果从主体角度来划分,又至少可以归纳出四种舆情话语,如政府话语、学术话语、专业话语及日常话语。这些话语内部同样存在分歧,如政府话语中,基层的行政逻辑与顶层的政治考量往往存在偏离;在以媒介为代表的专业话语中,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分化也导致了分歧加剧。
这些关键的话语,共同形塑了今天的舆情观念。在此过程中,舆情话语既要适应当下的中国情境,又需要向历史寻求资源,面临着时间维度的张力。同时,“舆情”的建构是本土民意观念与西方的一次碰撞融合;近代中国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争论,自然也渗入舆论、舆情等研究领域。如何借鉴西方民意理论,并作出本土的回应?这或许构成更为重要的张力,即空间维度的对话与抵抗。
四、结语:舆情、话语和现代性
今天的“舆情”历经断裂和转型,已从古老中国的统治术变成现代社会治理观念的一部分。舆情话语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舆情”的看法,还在生产特殊的知识,为其正当性加以辩护。
将“舆情”与“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比较来看,黄旦评价认为:“public opinion”源于民主理论,属于民主机制的构成部分;舆情分析是了解民情的技术手段,是统治学的辅助或从属部分,至多属于效率而非民主。[31]值得指出,“公众意见”自诞生后,逐渐与许多理想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包括“充分讨论”、“多数原则”等重要含义(分别来自启蒙运动与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遗产)。[32]但长久以来,“公众意见”也遭遇许多难题,如易受宣传的影响,可能导致多数暴政,易受制于少数的精英群体等。类似的问题同样困扰着“舆情”:随着互联网对民意的释放,网络舆情成为现实政治和社会矛盾的重要载体,线上表达与线下行动的结合更加紧密;“舆情”开始与无序、风险、危机联系起来,成为需要引导、治理的对象。
从实践来看,政府的舆情治理方式更加复合,在运动式治理或危机管理之外,也依赖于政府服务和常态化的吸纳机制。其中,网络舆情的治理日趋技术化、精细化,管控特征重新加强。在一些政府话语中,舆情主体往往成为不稳定的制造者,讨价还价的博弈者,或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某种意义上这更加契合最狭义的舆情定义,即突出了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为正当化的过程带来了更深的危机:舆情话语既要为现代民意的共性缺陷寻找出路,又要对当下的治理逻辑作出回应。因此“舆情”不仅是当下社会情境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产物。
在价值取向上,“新”概念被赋予了更多民主的理性价值,又带有社会治理术的工具价值。两种价值的竞争,即人们对二者优先性的考量,可以视为“舆情”的核心矛盾。从社会控制的演进看,以精心计算的信息传播来操纵大众行为,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33]在西方民意研究中,人们对此也始终保持着警惕:虽然“公众意见”概念具有不容置疑的民主基础,但日常政治决策中的民主基础却相差甚远;依赖公众意见的决策需要经过公开与传播,但传播也可能沦为劝服和意见操纵的工具。[34]可以认为,由于对政治传播的秩序与效率的追求,宣传、舆论引导、公共关系等实践就不会停止。在这种意义上,“舆情”概念的正当性就悬在表达自由与治理效率之间。这一问题在舆情观念中较为模糊,也是当下舆情话语饱受争议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本文从最广泛意义上使用民意的概念,即整个社会普遍意志和意识的集中展现,参见童兵:《“民意中国”的破题——兼议民意及其特征》,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为避免语义混淆,本文将西方民意研究中的核心概念“public opinion”直译为“公众意见”;同时“舆论”、“民意”等词在特指时,均指发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概念。
②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46《冬官考工记》第1529、15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③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44《昭公七年》第7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春秋左传正义》卷34《襄公二十一年》第590页
⑤《周礼注疏》卷33《夏官司马》第1073页
⑥见《辞源》第3033页“舆司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⑦《春秋左传正义》卷16《僖公二十八年》第273页
⑧杨伯峻在《僖公二十五年》中注有“舆人,众人也。或为士兵,或为役卒。”(《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此外,汉代许慎对司马、尉、侯、司空、舆五种官级有详细注解,其中“舆,众也。候领舆众在军之后者。”(《淮南鸿烈集解》卷15《兵略训》,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均可作为参考。
⑨《周礼注疏》卷33《夏官司马》第1073页
⑩《春秋左传正义》卷44《昭公七年》第759页
[11]林尧叟:《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卷15《僖公二十八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18册第4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2]见《旧唐书》卷177《崔慎由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4584~4585页。有研究者认为此诏书出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但根据该卷记载,唐昭宗于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被挟,次年收到朱全忠的一封上表才下此诏书。此外,《唐大诏令集》卷58《大臣宰相·贬降下》(中华书局,2008年)也记载了此诏书,时间为“天复二年十一月”。
[13]《旧五代史》卷48《唐书·末帝本纪下》第415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14][15]张田编:《包拯集》卷1《致君·七事》第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6]“清议”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体结构不尽相同(如有在朝、在野的划分)。参见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41~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倪琳:《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第69~72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参见Allport, F. H. (1937). Toward a science of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7-23.
[18]见《辞海》(第六版)第2791页“舆情”,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
[19]分别见《国语·周语上》、《书经·多士》、《管子·牧民》。
[20]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第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1]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载于《史林》,2003年第2期。
[22][美]唐(TangT. F.):《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第4页,胡赣栋、张东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倪琳:《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第67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4]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61页,王海、何洪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十二》第67~6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26]参见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第12~14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7]汤寿潜:《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载于《浙江档案》,1991年第1期
[28]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第32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9]见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格局与舆情研判》,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丁柏铨:《论网络舆情》,载于《新闻记者》2010年第3期
[30]张克生:《国家决策:机制与舆倩》绪论第17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31]来自黄旦在“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学术论坛(2014)的主旨发言:《民主和效率:舆情分析与中国社会治理》。
[32]参见普赖斯:《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第147~148页,邵志择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导言第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
[34]普赖斯:《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第243~244页,邵志择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赵梦溪/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985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网络传播史(1994-2013)”(编号NJU985XM06)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