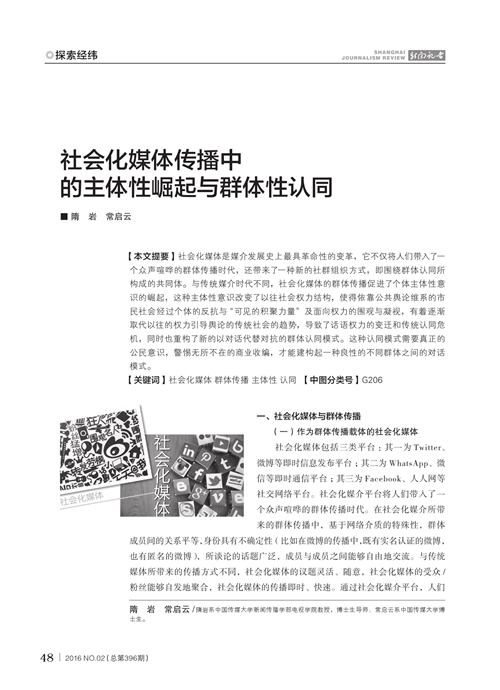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主体性崛起与群体性认同
■隋岩 常启云
【本文提要】社会化媒体是媒介发展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群体传播时代,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群组织方式,即围绕群体认同所构成的共同体。与传统媒介时代不同,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促进了个体主体性意识的崛起,这种主体性意识改变了以往社会权力结构,使得依靠公共舆论维系的市民社会经过个体的反抗与“可见的积聚力量”及面向权力的围观与凝视,有着逐渐取代以往的权力引导舆论的传统社会的趋势,导致了话语权力的变迁和传统认同危机,同时也重构了新的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群体认同模式。这种认同模式需要真正的公民意识,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收编,才能建构起一种良性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模式。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 群体传播 主体性 认同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社会化媒体与群体传播
(一)作为群体传播载体的社会化媒体
社会化媒体包括三类平台:其一为Twitter、微博等即时信息发布平台;其二为WhatsApp、微信等即时通信平台;其三为Facebook、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平台。社会化媒介平台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群体传播时代。在社会化媒介所带来的群体传播中,基于网络介质的特殊性,群体成员间的关系平等,身份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在微博的传播中,既有实名认证的微博,也有匿名的微博),所谈论的话题广泛,成员与成员之间能够自由地交流。与传统媒体所带来的传播方式不同,社会化媒体的议题灵活、随意,社会化媒体的受众/粉丝能够自发地聚合,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即时、快速。通过社会化媒介平台,人们能够亲自参与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实现对历史事件的现场直播。有了社会化媒介平台,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和个人拥有的价值逐渐被重视,个体的主体性问题和围绕个体所形成的认同问题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二)作为共同体形式的社会化媒体传播
社会化媒介平台的广泛应用是媒介发展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群体传播正推动着媒介传播方式、互联网商业模式,乃至人类生存模式的新一轮发展和变革”。①但是,社会化媒体所带来的还远非简单意义上的群体传播,它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群组织方式,即围绕认同所构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式不同于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它是虚拟的,流动的,但却能够时刻在网络上得到直观的展示。
此时,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形式不仅仅是获得了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也对人类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交往行为方式的赋权改变了社会的权力结构,也改变了建立在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个体的价值开始得到关注,个体建构主体性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开始崛起,个体获得了设置和影响议程的可能性,个体与个体间的认同形成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又一种力量。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个体的主体性崛起
(一)传统媒介时代被忽略的主体
在传统媒介时代,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往往被忽视。这是因为,一方面,工业社会需要个体“异化”为物才能参与资本生产,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制度本身对个体即是一种压制;另一方面,主体的存在受制于政治、教育、宗教、家庭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存在与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而意识形态通过“召唤”机制把个体建构为主体,个体的存在离不开这些物质存在,因此个体对意识形态的“召唤”也无从逃避。在此情形下,很多人悲观地感觉到,组成社会的个人在白天承受无思想的“伺服机器”的活动,而晚上则浸淫在娱乐之中,分享着制造出来的“共识”,放弃了思考、批判与反抗。
在传统媒介时代,批评者也往往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召唤和建构作用,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到的主体对个体的建构作用,意识形态提供一种“经济高度发达的、做好本职工作的、言行合乎道德的、履行公民职责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和不关心政治的意识”。②个体被这种意识形态“召唤”为主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以延续,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劳动技能的再生产”,也表现为“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是“工人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③此外,葛兰西提到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霸权”,乔姆斯基提到的“共识的制造”或福柯提到的权力从惩罚走向规训等理论,也都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主体形成时所受到的压制和建构。在传统媒介时代,个体没有获得媒介的赋权,个体的声音弱于媒介的声音,因此个体的主体性在传统媒介时代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但是,微博、微信等社会媒介体系的广泛应用为个体的主体性崛起提供了条件。
(二)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崛起的主体
在讨论主体性问题时,观点被引用最多的学者大部分生活在传统媒介时代,因此笔者认为,传统媒介时代的学者提出的理论也同样需要在新的媒介体系下进行再思考。比如,阿尔都塞谈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形成”的“召唤”作用,但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典型代表的媒介在当今社会发生了变化,因此其理论也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在社会化媒体所带来的群体传播时代,社会的权力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民社会的崛起
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作为具体的一个个“群体”,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整个市民社会的崛起。而有关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 ④恩格斯也总结说:“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⑤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则直接将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所以谁掌握了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谁就控制了市民社会,控制了意识形态。” ⑥
但是,市民社会是靠公共舆论来维系的。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各种观点也都一目了然地展现在网络上,论辩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论辩所带来的调节和群体极化一起存在。权力引导舆论的效果和以往相比有所减弱,市民的言论在社会化媒体上直观而快捷地展现出来,“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通过社会化媒体的赋权与社会化媒体背后所带来的群体性的支持,个人的主体意识正在崛起,通过社会化媒体影响舆论乃至影响公共议程的意识也正在萌芽。
2.话语权力的变迁
话语背后体现着权力,“既定的话语总是先于个人而存在,在这些话语中各种主体性已经得到表述,比如有关阶级、性别、国家、种族、年龄、家庭与个性的话语。我们‘栖居’于许多这类话语性主体性中,由此确立和经验我们自己的个性”。⑦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个体不仅仅有了话语权力,还通过创造自我的符号系统来抵抗话语权力。比如在网络语言中,更加平等意味的“Ta”代替了“他”或“她”,调和了男权与女权之间的关系,逃避“敏感词”的各种拆字技巧也形成了新的话语与符号,QQ签名中的火星文标示了一个和传统话语不同的个性解放。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召唤”受到影响,因为社会化媒体的形式赋予了个体以空前的表达权和近用权,这使得个体对“召唤”模式的反叛和解构能够快速传播,比如在微博、微信上有很多解构宣传话语的段子,而通过这些段子的传播,持有共同看法的人聚在一起并最终建立新的群体认同。而在人人网上,各种认同更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直观的聚合。
(三)社会化媒体时代个体主体性崛起的表现
主体性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作为政治学理论中的主体,即主体对于他/她所受制的权力而言缺乏行动的自由。其二为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主体。其三为语法中的主体,话语或文本的主体”。⑧主体性的崛起也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在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个体主体性的崛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的反抗与“可见的积聚力量”
个体的反抗一直存在,斯图亚特·霍尔和约翰·菲斯克都曾经提到个体的反抗。在霍尔看来,个体可以通过“解码”和“编码”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而在菲斯克的视域中,个体也可以通过解构文化工业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但是,传统媒介形式下的反抗并未获得与社会化媒介时代这种“认同的群体”和网络表达这种“可见的积聚力量”。囿于对社会孤立的恐惧,个体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往往会预测一下意见气候,一旦发现可能的舆论于己不利,则容易沉默,而最终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在网络时代,个体是匿名的、异质的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意见气候不需要猜测,在社会化媒体所体现的意见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而且在社会化媒体群体传播中还存在着一个“捅窗户纸效应”,平日一些大家都认可的观点,一经微博、微信等申明,便能立刻传播开来,这样,个体的反抗很容易找到共鸣,⑨这些“弱者抵抗”⑩最终变成了影响舆论的强有力的声音。
2.面向权力的围观与凝视
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一书中,把凝视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某种镜像关系,因此凝视并非长久而专注地看或被看,而是被他人的视野所影响”。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以往“看”与“被看”的权力格局,传统媒体时代,个体往往处于被看和被监视的地位,社会结构如福柯所言是一个巨大的“敞闭式监狱”,个体受到他人的监视和他人视野的影响,个体接受权力的规训。而在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个体不仅解构权力,还可以围观权力,可以通过“凝视”这种权力机制对权力施加反作用,过去“凝视”别人的人成为被“凝视”的对象,受到更多的规制和影响。例如,陕西“表哥”事件出来之后,很多官员害怕受到社会化媒体(比如微博)的监督,于是不再戴表;民间有很多微博、微信也监督着公车私用的问题,使得很多官员再也不敢开着公车去做私人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被社会化媒体所“凝视”的结果。而且,这种对权力的围观与凝视给更多的民众以自信,公民意识正在进一步崛起,公民共享新闻也逐渐改变着传媒的生态。
三、个体主体性崛起带来的传统认同危机及其重构
(一)个体主体性崛起之下的传统认同危机
“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 [11]认同也是维系一个群体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认同的形式也有不同的变化。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强调对“王道”和“族群”的认同,这是一种文化领导权;进入现代社会,领导者强调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进入网络社会,认同的形式有了反抗现代性的特征,宏大叙事的认同情结开始消解,认同开始走向了多元化。
现代社会带来了功能与意义的结构性分裂,“当人们不能在承担社会功能的劳作中寻找意义时,便把目光投向了网络”,于是一个工人,白天可能在“伺服机器”的过程中糊口,而晚上却在网络社会的虚拟社群里寻找认同。而且在网络社会这样一个“充斥着组织崩溃、制度丧失正当性、主要的社会运动消失无踪,以及文化表现朝生暮死的历史时期里,认同便成为是最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意义来源”。[12]社会化媒体的广泛应用为认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域,人们按照自己所从属的群体来重构主体,随着主体性的崛起,影响认同产生的支配性的社会权力受到挑战和解构,传统的围绕支配性权力所形成的宏大的认同模式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也面临着危机。
(二)社会化媒体时代新的认同重构:超越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走向规划性认同
曼纽尔·卡斯特主张把“建构认同的形式分为三种类型,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与规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抗拒性认同导致共同体的形成,而规划性认同产生了主体”。[13]这里的主体如阿兰·图海纳所说:“主体成为一个个体的愿望,它创造了个人历史,赋予了个人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以意义。”
主体由被压抑到反抗再到被建构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对合法性的抵抗由武力的抵抗转为舆论的抵抗,而舆论一旦获得社会化媒体中这种可以积聚的可见力量,主体性的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就更加显著——“一旦主体被建构起来,就不再以公民社会为基础,而是共同体抗拒的进一步延伸”。[14]在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有着各种共同体的存在,他们或解构或抵抗着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当“春晚”逐渐发挥意识形态的“召唤”功能时,微博上也有另外一个群体一边看“春晚”,一边“吐槽”各种关于春晚的段子;当《舌尖上的中国》自豪地阐释中国的美食文化时,微博、微信上也有《舌尖上的另一个中国》,关注食品安全问题。而在社会化媒体的传播中,还有一些群体,通过相似的认同,寻找到与传统社会相对立的意义。例如,LGBT运动的兴起,对弱势群体如抑郁症关注的运动兴起,和NGO运动越来越活跃,体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认同力量。
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正是在超越了合法性认同与抗拒性认同之后走向了规划性认同,个人化的时代或者“我的”时代到来,个体通过对自身意义的规划建构主体,通过个体主体性的崛起实现了个体的解放。
四、社会化媒体时代如何形塑新的认同:超越功能主义的批判
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规划性认同产生了主体,而这种认同模式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主体性的崛起肯定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一个声音,一个世界”的模式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众声喧哗,多个世界”。在这个网络社会中,人的价值重新得到肯定,这对防止独裁与专政,建设人性化的社会带来了福音。但同时,新的认同模式下主体的崛起也消解了传统以国家和民族为代表的认同模式,恐怖主义、邪教组织等极端认同形式成为人类的公敌。
社会化媒体具有其技术上所偏向的公共性。但是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社会的“美丽新世界”,依然需要付出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既包括建立不同共同体间的对话机制,也包括对构成社会的个人所进行的“公民教育”,以及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收编。
1.以对话代替对抗
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带来了社会调和的可能,同时也带来了群体极化的隐忧,经常能看见不同观点,经过微博、微信上的争吵之后变得更加极端。此时,倡导对话及建立健康的对话机制成为协调不同认同的有效路径。[15]而对话指的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交流,是交流的理想状态,只是在社会步入现代化之后,对话变得着实不易,各种“交流的无奈”充斥着现代社会。对话不仅能进行社会的调和,也能在冲破现代性对交往的设置的障碍之后重拾每个人的价值。
“人们一直主张,把作为对话的交流用做治疗(现代性)痼疾的药方”。[16]尽管在20世纪,一些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认为对话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现阶段,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为不同利益阶层、不同意义归属的团体创造了最大限度的对话可能。个人主体性的崛起与认同的范式转移必将带来深刻的社会革命,在未来社会,协商与对话会逐渐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常态。
2.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
不同的媒介形态需要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个体主体性的崛起,也带来了新的认同模式,个人有了影响议程的可能性与力量。但是在这种变迁之后,媒介素养教育也应该超越“保护主义”范式走向公民教育,培养一种普遍的公民意识,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会用新媒体、善用新媒体,有效行使自己的表达权,构建一种良性而健康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对话模式。
3.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收编
在公民教育之后,还应该警惕个体主体性的崛起有被商业所收编的可能性,因为当个体的反叛仅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对严肃社会问题的讨论变成一场娱乐时,所谓的网络文化就真正走进了荒漠。这既需要用户的自省,也需要传播学者以其专业化的视角投身于正在发生的社会活动,以社会公共性的视角尽力避免商业化收编。
综上所述,当下,以Twitter、微博为代表的即时信息发布平台,以WhatsApp、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平台和以Facebook、人人网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共同组成了社会化媒体的传播环境。这种传播环境为数以万计的人们营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群体传播时代,各种共同体从想象走向可见可闻、可触可感,传统社会中支配性的社会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解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召唤”机制遭遇了主体的多样化反抗,个体的主体性受到关注。这种被传统媒体时代所忽略了的主体,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借助群体传播的力量,实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崛起,而这种主体性的崛起在对权力的围观与凝视中彰显着“可见的积聚力量”,带来了市民社会崛起的曙光,同时也促进了群体认同从以往的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走向了规划性认同。而要实现这种规划性的认同,需要培养起网民真正的公民意识,以对话代替对抗,并高度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收编。■
隋岩 常启云/隋岩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启云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注释:
①隋岩、曹飞:《群体传播时代的莅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②吴小丽:《影视理论文献导读电影分册》第327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路易·阿尔都塞著,李迅译:《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于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第685~7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第250~25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张国良:《E社会传播: 创新、合作与责任》第3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⑧约翰·菲斯克著,李彬译:《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84~85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⑨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通用词汇编》第114~11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⑩徐海波:《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第11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13][14]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第5、8、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2]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第3~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5]邓力:《传媒研究中的公共性概念辨析》,《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9期
[16]约翰·达勒姆·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第216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