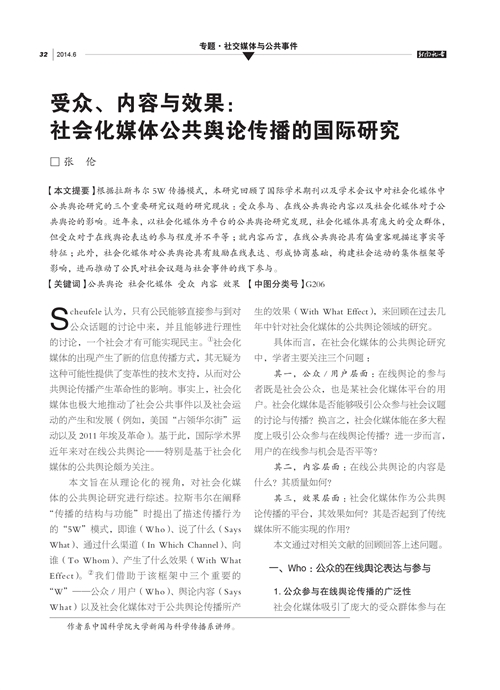受众、内容与效果:社会化媒体公共舆论传播的国际研究
□张伦
【本文提要】 根据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本研究回顾了国际学术期刊以及学术会议中对社会化媒体中公共舆论研究的三个重要研究议题的研究现状:受众参与、在线公共舆论内容以及社会化媒体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近年来,以社会化媒体为平台的公共舆论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具有庞大的受众群体,但受众对于在线舆论表达的参与程度并不平等;就内容而言,在线公共舆论具有偏重客观描述事实等特征;此外,社会化媒体对公共舆论具有鼓励在线表达、形成协商基础,构建社会运动的集体框架等影响,进而推动了公民对社会议题与社会事件的线下参与。
【关键词】 公共舆论 社会化媒体 受众 内容 效果
【中图分类号】 G206
Scheufele认为,只有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到对公众话题的讨论中来,并且能够进行理性的讨论,一个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民主。①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产生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其无疑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变革性的技术支持,从而对公共舆论传播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事实上,社会化媒体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公共事件以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1年埃及革命)。基于此,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对在线公共舆论——特别是基于社会化媒体的公共舆论颇为关注。
本文旨在从理论化的视角,对社会化媒体的公共舆论研究进行综述。拉斯韦尔在阐释“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时提出了描述传播行为的“5W”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向谁(To Whom)、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②我们借助于该框架中三个重要的“W”——公众/用户(Who)、舆论内容(Says What)以及社会化媒体对于公共舆论传播所产生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来回顾在过去几年中针对社会化媒体的公共舆论领域的研究。
具体而言,在社会化媒体的公共舆论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其一,公众/用户层面:在线舆论的参与者既是社会公众,也是某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用户。社会化媒体是否能够吸引公众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与传播?换言之,社会化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公众参与在线舆论传播?进一步而言,用户的在线参与机会是否平等?
其二,内容层面:在线公共舆论的内容是什么?其质量如何?
其三,效果层面:社会化媒体作为公共舆论传播的平台,其效果如何?其是否起到了传统媒体所不能实现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回答上述问题。
一、Who:公众的在线舆论表达与参与
1.公众参与在线舆论传播的广泛性
社会化媒体吸引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参与在线公共舆论传播。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参与人数众多。一个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样本研究发现,在美国使用过在线聊天等在线讨论区的用户中,约有10%的人参与过政治论坛的讨论。③ 2005年,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经常参与在线讨论,10%的用户参与了2004年关于总统选举的在线讨论。④2011年的埃及革命至少吸纳了17万名Facebook用户成为运动参与者,并得到了140万名用户的支持。⑤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13.1万用户加入了Facebook一个名为“一起占领(Occupy Together)”的专页。更为重要的是,在Facebook中,该运动的参与者共建立了400多个独立页面,且美国本土每个州至少建立了一个页面。大部分新的运动专页在9月23日~10月5日号建立。仅10月11日一天,Facebook中关于该运动的帖子和评论为7.4万个。到了10月22日,Facebook中运动专页的帖子数已经有117万个。⑥
第二,受众群体多样化。一项对“占领华尔街”初期Twitter中相关内容历时性分析的研究发现,在参与讨论的最活跃的200个人中,新闻媒体所占的比例最大,为39%;社会活动家(Activist)其次,为23%;娱乐业(Entertainment/Recreation)为10%;其他参与者还有大学教师(2%)、非政府组织(2%)和IT人士(1%)等。⑦对美国20多个在线新闻组的研究发现,在线内容有60%来自传统的大众媒体(例如,电视、报纸等),15%来自在线新闻,其他的新闻来源还有个人博客(8%)、政府和NGO组织(6%)等。⑧
2.公众参与在线公共舆论传播的不平等性
以往的研究发现,虽然互联网存在接入成本低等特点,但就一个社会整体而言,不同种族、性别和年龄的群体之间其互联网的采纳率和采纳效能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构成了社会群体之间对互联网使用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⑨对于社会化媒体的公众参与而言,这种不平等是否依然存在?更进一步,即使社会化媒体能够覆盖大部分社会公众,但公众的在线参与程度是否也存在不平等?
Himelboim对6年中35个在线新闻组的20万用户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在线参与以及其他用户对话题的注意力服从幂律分布。且这种幂律分布的系数随着网络人数的增长而增大。⑩这说明,用户的在线参与程度非常不平等,且在线社区的规模越大,这种不平等越显著。与此类似,另一项研究抓取了Twitter中以“占领华尔街”为主题的帖子,分析了该主题的内容特点历时性变化。[11]该研究发现,用户对“占领华尔街”相关的内容贡献极不平均,其发帖量也呈幂律分布。很小一部分用户贡献了绝大部分内容,而大部分用户只贡献了少部分内容。该发现与社会化媒体之前的在线舆论研究类似。[12]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线公共舆论参与与传统的线下舆论参与并无区别:一小部分人向大部分被动的受众传播观点。
这种不平等或许与用户的媒介使用技术等原因有关。例如,Shen等人分析了中国网民的互联网使用与在线表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例如,即时通讯软件、在线聊天室、BBS等)的使用频率促进了用户的在线表达。[13]公众对公共舆论的参与程度不仅在个体层面上表现出不平等,在地区水平上,信息的贡献程度也不平均。Twitter的数据显示,与“埃及革命”有关的信息转发帖子数最多的地区为纽约,此外,加州、哥伦比亚特区、麻省、伊利诺伊等几个州的用户转帖量也比较大。但是不同州的转帖量分布非常不平均。此外,该研究还分析了Twitter不同州的用户之间转发 “占领华尔街”事件相关帖子的情况。研究发现,“占领华尔街”事件的网络流量关系图呈现出非常高的中心度。来自纽约、华盛顿和加州的帖子流量占到了全部帖子流量的50%,而非中心地区之间彼此的连接度不高。[14]
二、What:在线舆论的质量评估
Scheufele认为,公共舆论的内容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探讨: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与情感维度(Affective Dimension)。[15]前者强调对于事实的阐述,后者强调参与者的情感倾向以及态度倾向。
从认知维度而言,在线公共舆论更倾向于对事实进行客观化描述。由于新媒介与面对面沟通相比缺少在场感,因此在线舆论的参与者更倾向于进行理性沟通。[16]与此类似,Wang等人发现,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活跃的200名Twitter用户所发布的帖子更偏重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感性用词则较少。[17]此外,在线舆论提高了公共议题的时效性,从而引发受众对该议题的关注。例如,Papacharissi和Oliveira基于Twitter中关于2011年“埃及革命”的帖子对比了社会化媒体中的舆论内容与传统新闻的差别。研究发现,Twitter帖子和传统新闻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例如,二者都强调公众对事件的广泛参与、地理接近性、信息的即时性、相关性、个人化和重要性等。[18]但与此同时,Twitter的帖子还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时性。Twitter的帖子发布与事件发生时间几乎没有时间差。这使得传统媒体在报道事实上丧失了优势。该研究甚至认为,社会化媒体对社会新闻的报道挑战了学界对于“新闻”的定义。第二,“众包的权威”(Crowdsourcing of Elite):在Twitter中,意见领袖是因为被其他用户对其帖子的转发而产生的,这类人比较活跃、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比较深入;而传统新闻中的权威则是媒体所赋予的。[19]在线公共舆论研究分别从态度倾向和情感倾向两方面对舆论的情感维度进行了经验性研究。例如,Wu & Huberman考察了受众如何通过评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相关议题的态度。[20]该研究分析了受众对亚马逊和IMDB电影数据库中的书籍、电影评论的意见的演化趋势。该研究发现,后期的评论者与前期的评论者对书籍和电影的评论得分差异很大,这种不同扭转了舆论向极端方向发展。更有意思的是,用户的意见具有明显的向均值“回归”的现象。即起初打分较低的书籍和电影在后期的打分会比较高;相反,起初打分较高的书籍、电影在后期的打分会偏低。“选举者困境(Voter's paradox)”或许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人们都倾向于使自己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全局。因此,当用户看到其评价对象当前的平均得分时,其往往会给出一个与平均分差距较大的得分,从而尽最大可能左右全局。
三、With What Effect:社会化媒体作为在线公共舆论平台的效果
Thorson等人认为,社会化媒体的内容在社会运动中具有以下功能:为线下的社会运动提供信息资源(informational resources),为用户参与社会运动提供协商资源(deliberative resources),形成和发展用于构建集体身份认同的归属资源(affiliation Resources)以及动员社会实体资源(例如,资金支持、物资支持等),从而推动公众线下对公共议题的参与。[21]例如,Wojcieszak通过经验性分析一个新纳粹主义和激进环境主义的在线论坛与其用户线下社会运动的参与情况发现,在线论坛的参与程度高的用户(例如,在线论坛的使用时间等)对线下运动更为支持。[22] Price 和 Cappella也发现,在线论坛的参与促使用户参与线下的政治活动与社区活动。[23]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回顾,社会化媒体的公共舆论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励用户线上意见表达。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是否表达意愿取决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看法。当人们认为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中自身的观点可能会得到主流人群的赞同,则其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相反,如果人们认为其处于非主流人群中,由于害怕可能出现的被其他成员孤立的情况,其一般不倾向于表达自身的观点。[24]通过对在线公共舆论的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推动了用户在线上的意见表达,这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沉默的螺旋理论。例如,Price等人认为,社会化媒体鼓励构建在线社区的规范性意见气候(Opinion Climate),以及鼓励成员分享信息。[25]具体而言,Price等人将在线社区中群体对个体用户的影响分为“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和“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前者指个体希望自身满足其他人的期望,从而获得奖励(例如,获得自尊、或者来自他人承认),避免来自群体的惩罚(例如,被孤立或逐出群体)。Price等人认为,规范性社会影响是“沉默的螺旋”得以成立的条件。而“信息性社会影响”指个体认为来自他者的信息、意见等是构成事实的重要部分。[26]该研究收集了60个讨论关于2000年美国两个总统候选人的税收政策的在线社区数据。研究将用户的所有言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关于意见或偏好的表达,一类为支持某类观点的原因或论据。前者创造了在线社区规范性意见气候;而后者是构成群体内成员间信息性价值的重要基础。该研究发现,该在线社区对个体在线表达的规范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皆存在,即在线群体构建了规范性意见气候,并分享了其意见形成的论据。
Woong等人还考察了人们对于在线及线下意见气候对人们在线表达的影响。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在线论坛中,由于媒体的匿名化特点,人们在表达意见时主要考虑在线意见气候,而并不考虑该话题的线下意见气候是否与用户自身想表达的意见一致。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线用户在表达意见时并不存在在线隔离恐惧(Fear of Isolation),即表达意见的用户的隔离恐惧程度与没有表达意见的用户的隔离恐惧程度相比无统计显著性差异。[27]第二,形成协商基础,构建社会运动的集体叙述框架。在一项社会运动中,参与方往往来自多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目的的群体。因此,社会化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传递信息、鼓励用户的意见表达。更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产生关于某个社会议题的协商基础的平台,使得参与者在复杂的集体行动中对组织模式以及对组织议程形成反馈。[28]对社会化媒体公众舆论的内容分析印证了该研究的上述观点。Himelboim 等人对Twitter的一项研究发现,用户往往关注那些与他们政治意见一致的其他人,而很少能接触到与其政治态度意见相左的信息。因此,社会化媒体可能促使人们在某些问题上与意见相似的人进行沟通,达到意见融合,甚至达成共识。[29]一项针对2012年美国大选的在线论谈的研究发现,在政治论坛中用户虽然不能够形成对某议题完全一致的意见,但用户能够形成讨论该议题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共享的政治知识以及对议题的解读。[30] Conover等人分析了全国范围内Twitter用户中关于“占领华尔街”事件的关键词,他发现,在跨州传播的帖子中被强调的信息主要涉及该运动的核心框架以及新闻报道主题(例如,wall,nyc,street,news,99%,bank,peaceful)。这说明,Twitter在集体叙事框架的构建(Develop Narrative Frames)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1]第三,动员线下社会资源。社会化媒体作为公共舆论平台,其并非仅仅停留在线上的意见表达,社会化媒体还被用作征集运动资源(例如,用于社会运动的医疗设施)的平台,而且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线下的社会运动。以“占领华尔街”事件为例,Conover等人分析了Twitter在动员本地社会资源的作用。该研究发现,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关的帖子传播是高度本地化的。40%的帖子在本地产生,并只被本州参与者转发。特别有意思的是,研究还发现,州内的帖子内容被强调较多的主要是具体的事件、行动以及地理位置(例如,citytonightmarchjoin, solidarity, daysquare, please, part, now)。[32]这说明,Twitter在本地被主要用于社会资源的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而全国性或者跨州的传播行为则更侧重于推进该运动集体框架的进程。此外,Thorson等人发现,在被Twitter转发的关于“占领华尔街”的YouTube视频中,大部分(63%)视频是在发布两天之内被转发的。这说明,YouTube视频能够被参与者在社会事件发生后用作快速社会动员。[33]第四,形成和发展集体身份认同。在线参与者通过展示其在线意见表达的团结和一致,帮助事件参与者构建了在公共事件中的集体身份认同与归属感。Papacharissi和Oliveira考察了Twitter中关于2011年“埃及革命”的帖子的内容。他发现,参与者会倾向于用相同的词汇描述该次运动。例如,Twitter的帖子中对这次社会运动的描述多用“革命(revolution)”而非“抗议(protest)”。而通过“转发”、“提及”等信息传播方式,这种用词的一致性又被大大强化了。此外,社会化媒体还能够大量转发相同内容的信息,烘托集体行动的气氛 (Ambience)。例如,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的消息,在Twitter中被重复转发,尽管该信息已经被多次且广泛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发帖子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运动。用户转发帖子的目的不再是传播信息,而在于营造和烘托一种“新闻正在进行的气氛(always-on news environment)”。[34]
四、结语
本文从受众、内容和影响三个方面回顾了社会化媒体中的公共舆论研究。从受众参与的角度而言,社会化媒体具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参与在线舆论表达,但参与程度并不平等;从在线公共舆论的内容特征而言,在线公共舆论具有偏重客观描述事实等特征;就社会化媒体对于公共舆论传播的影响来说,在线公共舆论有激励用户线上意见表达、形成协商基础,构建社会运动的集体叙述框架、动员线下社会资源、形成和发展集体身份认同等影响,从而推动了线下社会运动的公民参与。
社会化媒体或许会对舆论传播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用户的舆论表达机会较传统媒体平台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因此研究者能够更为全面地获取公众的意见信息。原因之二,社会化媒体的数据采集数量与传统的调查等数据获取方式相比呈指数倍上升。这使得研究者有机会从非抽样的数据中挖掘公众舆论的某些新的规律和特征。因此,针对社会化媒体平台,有效并精确挖掘海量数据中的公众舆论内容,是舆论传播研究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
注释
①[15] ScheufeleD. A. (1999). Deliberation or dispute? An exploratory study examining dimensions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1(1)25-58.
②LasswellH.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37.
③WojcieszakM. E.& Mutz, D. C. (2009).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Do online discussion spaces facilitate exposure to political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9(1)40-56.
④Pew. (2005). Trends 2005.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⑤⑥CarenN.& Gaby, S. (2011). Occupy online: Facebook and the spread of Occupy Wall Street.Unpublished manuscript.
⑦[11] [16] Wang, C.-J.& Wang, P.-P. (2011). Discussing Occupying Wall Street on Twitter: Longitudinal Network Analysis of Equality, Emotionand Stability of Public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World Associa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
⑧Himelboim, I.Gleave, E.& SmithM. (2009). Discussion catalyst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 Content importers and conversation starters. Journal of Computer ediated Communication14(4)771-789.
⑨DiMaggioP.& HargittaiE. (2001). From the digital divide to digital inequality? Studying Internet use as penetration increa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al Policy Studies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15.
⑩Himelboim, I. (2011). Civil Society and Online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Unrestricted Discuss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5)634-659.
[12][17] Albrecht, S. (2006). Whose voice is heard in online deliberation?: A study of particip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al debates o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Community and Society9(1)62-82.
[13]Shen, F.Wang, N.GuoZ.& GuoL. (2009). Online network size, efficacy, and opinion expression: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Internet us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1(4)451-476.
[14][31][32]ConoverM. D.DavisC.FerraraE.McKelvey, K.MenczerF.& Flammini, A. (2013). The geo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 social movement communication network. PloS one8(3)e55957.
[18][19][34]Papacharissi, Z.& de Fatima Oliveira, M. (2012). Affective news and networked publics: The rhythms of news storytelling on# Egyp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2(2)266-282.
[20]WuF.& Huberman, B. A. (2010). Opinion formation under costly expression.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TIST)1(1)5.
[21][33]ThorsonK.Driscoll, K.Ekdale, B.EdgerlyS.Thompson, L. G.SchrockA.et al. (2013). YouTubeTwitter and the Occupy Movement: Connecting content and circul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6(3)421-451.
[22]WojcieszakM. (2009). "Carrying Online Participation Offline"--Mobilization by Radical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ly Dissimilar Offline T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9(3)564-586.
[23]Price, V.& Cappella, J. N. (2002). Online delibe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The electronic dialogue project in campaign 2000. IT & Society1(1)303-329.
[24]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4(2)43-51.
[25][26]PriceV.NirL.& Cappella, J. N. (2006).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influence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16(1)47-74.
[27]Woong YunG.& Park, S. Y. (2011). Selective posting: Willingness to post a message online.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16(2)201-227.
[28]Segerberg, A.& BennettW. L. (2011).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3)197-215.
[29]Himelboim, I.McCreery, S.& SmithM. (2013). Birds of a Feather Tweet Together: Integrating Network and Content Analyses to Examine Cross deology Exposure on Twitter.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30]Liang, H. (in press). Coevolution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common ground in web discussion forum.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与科学传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