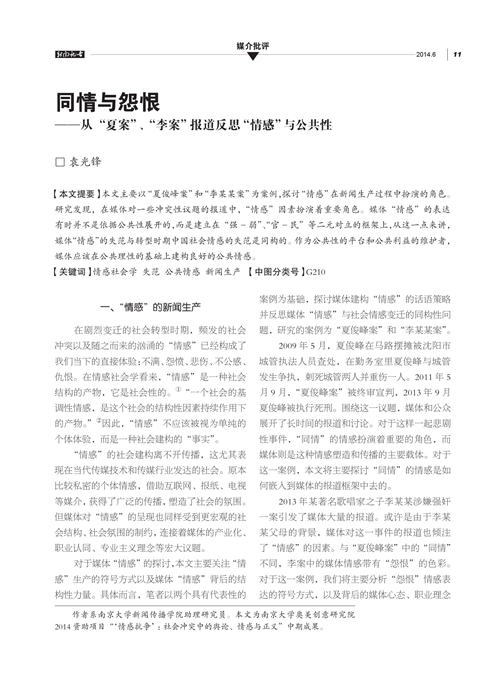同情与怨恨
从“夏案”、“李案”报道反思“情感”与公共性
□袁光锋
【本文提要】 本文主要以“夏俊峰案”和“李某某案”为案例,探讨“情感”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在媒体对一些冲突性议题的报道中,“情感”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体“情感”的表达有时并不是依据公共性展开的,而是建立在“强-弱”、“官-民”等二元对立的框架上,从这一点来讲,媒体“情感”的失范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情感的失范是同构的。作为公共性的平台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媒体应该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建构良好的公共情感。
【关键词】 情感社会学 失范 公共情感 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 G210
一、“情感”的新闻生产
在剧烈变迁的社会转型时期,频发的社会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汹涌的“情感”已经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直接体验:不满、怨愤、悲伤、不公感、仇恨。在情感社会学看来,“情感”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它是社会性的。①“一个社会的基调性情感,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持续作用下的产物。”②因此,“情感”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个体体验,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
“情感”的社会建构离不开传播,这尤其表现在当代传媒技术和传媒行业发达的社会。原本比较私密的个体情感,借助互联网、报纸、电视等媒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塑造了社会的氛围。但媒体对“情感”的呈现也同样受到更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氛围的制约,连接着媒体的产业化、职业认同、专业主义理念等宏大议题。
对于媒体“情感”的探讨,本文主要关注“情感”生产的符号方式以及媒体“情感”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具体而言,笔者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为基础,探讨媒体建构“情感”的话语策略并反思媒体“情感”与社会情感变迁的同构性问题,研究的案例为“夏俊峰案”和“李某某案”。
2009年5月,夏俊峰在马路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在勤务室里夏俊峰与城管发生争执,刺死城管两人并重伤一人。2011年5月9月,“夏俊峰案”被终审宣判,2013年9月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围绕这一议题,媒体和公众展开了长时间的报道和讨论。对于这样一起悲剧性事件,“同情”的情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媒体则是这种情感塑造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对于这一案例,本文将主要探讨“同情”的情感是如何嵌入到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去的。
2013年某著名歌唱家之子李某某涉嫌强奸一案引发了媒体大量的报道。或许是由于李某某父母的背景,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也倾注了“情感”的因素。与“夏俊峰案”中的“同情”不同,李案中的媒体情感带有“怨恨”的色彩。对于这一案例,我们将主要分析“怨恨”情感表达的符号方式,以及背后的媒体心态、职业理念等问题。
二、“夏案”报道中的“同情”
“夏俊峰案”发生在2009年,但通过“读秀”报纸数据库的查询,我们发现最初媒体并没有大规模地报道,这或许是因为类似的事情比较多,新闻价值不够高。最初的报道也多是把这一事件当做普通的刑事案件,情感的色彩很淡薄,比如《凶犯夏俊峰被判死刑》之类的报道。夏俊峰的妻子张晶认为,最初一些媒体把夏俊峰描述成故意杀人的罪犯,这并不符合她经历的事实。自2011年起,媒体的报道显著增多,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张晶寻找网络推手、联系媒体的努力取得了效果。③不仅是数量的增多,媒体的报道偏向也转移到夏俊峰及其妻子上。报道的内容除了关注司法判决之外,还关注夏俊峰的家庭命运、苦难,夏俊峰之子的生活状态。比如《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记者手记《一个弱女子如何拯救夏俊峰》,“弱女子”既指身体上的弱——“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过于瘦弱的东北女子,言辞谨慎而谦卑”;也包括地位上的弱势。作者描述了夏俊峰案对张晶家庭的影响:
2009年的圣诞节,她一个人带着儿子去沈阳街头看夜景,满目尽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儿子要买一个8块钱的玩具,她没舍得……言及此,张晶泪下。满座皆寂静。
……
张晶的努力逐渐见效,通过她之口讲述的小贩生活,让每一个辛勤耕耘的底层国人心生同情。精英阶层显然也已被城管制度之恶彻底激怒,导演陆川给张晶捐了1万块,并来电话声援;作家郑渊洁向自己的粉丝喊话,希望网友能用关注张晶微博的方式,表明对夏俊峰的声援。④
这一文本通过对张晶个人的描绘以及对夏案发生后张晶家庭的描述,建构了公众的“同情”感。
还有一些类似的媒体文本,例如在《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获死刑背后:妻儿命运受关注》的报道中,开篇即这样叙述:
两年前,“小贩夏俊峰持刀刺死城管”一案震惊世人。两年中,夏俊峰先后迎来一审、二审两次“死刑”的判决。对于夏俊峰的命运,无论有着怎样的争议,最终还是应该由法律裁定。但是,夏俊峰身后那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他的妻子、儿子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篇文章紧接着叙述了夏俊峰事件发生之后对张晶、儿子的影响:“我们依然想要写出来,真实还原一个底层家庭过往的生活,以及经历‘事件’后的无能为力。”⑤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同情”是如何被嵌入到媒体的报道中去的。
坎迪斯·克拉克将“同情”界定为“为他人感到悲伤和怜悯”。⑥悲伤和怜悯情感的唤起与对事件的界定、当事人的身份建构有关,就像克拉克所指出的,同情感的加工和生成受到信念、价值、规则、逻辑、符号等元素的制约,“同情总是包括正义、公平和价值等文化观念的唤醒”。易言之,“同情”感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人对正义、公平等价值的判断有关,人们更容易同情受到不公平对待者。克拉克对决定什么样的困难是不幸的、处于这个范畴中的成员是值得同情的,增加了一系列规则,其中有两条值得我们关注。一条是“特殊的剥夺规则”,它“强调因剥夺使个体处于正常生活之外”;另外一条规则是命运公平规则,这是指“那些享受到好的运气和奢侈生活的人(如名人、富人、有权人)与普通人或不幸的人相比,受到的同情较少”。⑦
在对“夏俊峰案”的报道中,媒体传播的“同情”也大致遵循了这样两条规则。首先,不少报道特别提出夏俊峰一家的底层身份,他们是为了生存的压力而不得不出去摆摊,这样的底层是被不公正的制度剥夺的,受到了制度的不公平对待,因此,这一群体的“不幸”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对“底层”身份的强调是媒体唤起“同情”的重要话语策略。“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归类是与作为符号的“城管”作对比的。虽然也有一些报道指出,被刺死的城管也是底层群体。但无论媒体还是公众都似乎更关注“城管”背后的符号意义,即“城管”象征着强权、暴力执法、不公正的制度。显然,在这种对比的框架中,夏俊峰家庭更容易获得媒体的报道和同情。
为了追求“同情感”更好的传播效果,有网民发现,有媒体在报道夏俊峰案时用错了照片,将北京小贩崔英杰的庭审照片当作夏俊峰的照片使用,甚至连夏俊峰的妻子在转发微博时也“误将崔英杰当作夏俊峰”。⑧崔英杰是2006年一起商贩刺死城管案件的当事人。至于为什么媒体会错用了崔英杰的照片,有网友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崔英杰在庭审上擦眼泪的表情可为夏俊峰增加同情分。⑨
当然,媒体的“同情”并不仅仅是指向夏俊峰及其家庭,尤其是到了后期,“同情”也越来越多地指向夏俊峰与被刺死城管的家庭。不少媒体的报道都将夏俊峰案视为“三个家庭的悲剧”,比如以下两篇报道:
9月25日,沈阳小贩夏俊峰被处死,从通知家属到行刑不足6小时。从此,母亲没了儿子、妻子没了丈夫、孩子没了爸爸。但是,遇害城管孙旭东,比夏家更穷;另一遇害城管申凯,四代单传。3个人,3个家庭,全是可悲的牺牲品!一个人被执行死刑,两个人被杀,三个破碎的家庭永远无法复原。⑩
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使三个原本没有交集的家庭各自坠入谷底。虽然案件从法律程序上画上了句号,但对三家人而言,走出伤痛,面对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1]同情的产生与人们对同情对象困境产生的归因分析有关,如果把事情归因于个体层面,一般就不会产生同情感,如果归因于社会层面就容易引起同情感。[12]在夏俊峰案中,媒体显然倾向于把问题归因于社会层面。当归因于城管的暴力执法时,夏俊峰及其家庭获得了媒体的同情,而当归因于城管制度甚至更高层次制度的时候,夏俊峰家庭及被刺死城管的家庭都获得了媒体的同情。同情的背后是对制度的批判,比如《东方早报》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指出:“悲剧一起又一起,令人错愕而黯然,原因究竟在哪?针对夏俊峰一案,在沈阳市沈河区当了24年人大代表的中科院教授冯有为感叹,‘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品’。这是执法者权力无限度扩张,老百姓的权利却没有得到保障的失衡下的恶果。” [13]这就使得媒体的“同情”带有了批判性的意义。
三、作为传播的“怨恨”
“李某某案”所引起的舆论风波已经无需过多叙述,但有必要对一些报道呈现出的“情感”进行分析。
它首先涉及传媒的伦理。《环球时报》曾报道指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对近期5起报刊刊载虚假低俗内容的调查处理情况予以通报,涉及刊载低俗标题、低俗广告、失实报道、虚假新闻等行为。其中,山东《聊城晚报》题为《李某某(原文为真名)他妈的要求高,律师不干了》的报道以及上海《新民周刊》题为《李某某他妈的舆论战》的报道,都因标题粗俗而受罚。” [14] “2013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课题组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认为,“新闻语言粗鄙化的现象,不仅是传媒文化低俗的表现,也显示了以刺激性、情绪化的语言表达,迎合社会情绪,甚至扩张社会戾气的某些传媒人的心态。” [15]除了语言的粗鄙化之外,一些媒体关于李某某案件的报道也违背了司法正义。魏永征指出:“这是一件双重的依法不公开审理的罪案:未成年人罪案和强奸罪(涉及受害人私隐)案,但是它的信息公开和传播却远远超过了那些公开审理的案件。”在事件过程中,“无论是警方还是这些中央级媒体,似乎都没有想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有权威媒体带头,众多媒体无所顾忌地开展了一场挖掘涉案人李某某信息的大竞赛,他的家世、学校、孩提时代的优裕生活、留学时打架的劣迹、宝马车的时新改装,当然还免不了重提上一年打人而被劳教的‘旧科’,继而波及他的父母的各自身世、恋爱结婚史、成名经过,一概暴露无遗”。[16]语言的粗鄙化与违背司法正义都与媒体的伦理失范有关,已经有不少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我们关注的是这起事件传播过程中的媒体情感。不同于“夏案”中的媒体“同情”,在“李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怨恨”感。根据舍勒的研究:“无力对他者施及的伤害即刻还手却又饱含复仇意识的情绪体验,便是‘怨恨’。” [17]此种情感在转型时期的情感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与社会转型的本质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转型是体制改革、平权观念兴起、社会结构变迁、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其间,平权观念和平等的诉求促使个体进行舍勒所说的生存比较,[18]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产生对不平等现状的不满以及改变阶层身份的强烈愿望,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促使阶层之间的日益分化,[19]当前阶层之间的流动也日益固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缺乏公正的分配制度,再加上制度性表达渠道的匮乏,种种因素导致处于弱势的普通公众和社会底层对自己的生活有较高的期待,却又缺乏实现的手段,产生一种无力感。而在尼采的笔下,正是这种无力感促使了怨恨感的产生。[20]“怨恨”的情感也常常见之于媒体的报道中,尤其是在阶层冲突(比如富二代、官二代)、官民冲突的议题上。虽然关于媒体上“怨恨”情感的传播效果还没有精确的测量,但它的确有可能扩大社会的怨恨情绪。公众的“怨恨”一部分与现实中的自身体验有关,另一部分则来自媒体的报道及塑造的氛围。人们是把事件、人物进行“符号化”的处理,体验的并不一定是具体的事件(或人物)的伤害,而是“符号”的伤害。在夏案中,“同情”的背后也含有对“城管”的“怨恨”,但“怨恨”的对象并不是被刺死的两位城管,而是作为执法群体的“城管”和城管制度。在“李案”中,公众“怨恨”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李本人,而是象征的阶层。
四、情感与媒体的公共性
我们分析了“同情”和“怨恨”两种情感是如何被媒体呈现的。当然,情感社会学研究的“情感”类型有许多种,但可以说,“同情”、“怨恨”这两种情感在当前中国的大众媒体上更为常见和显著。但媒体的情感结构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受到社会情感本身的塑造,可以说,媒体的“情感”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基调性情感带有很强的同质性。
在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与社会变迁同步的是社会情感结构的变迁。一些类型的情感逐渐淡薄,而另一些类型的情感则日益凸显,比如“怨恨”与“同情”。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怨恨”情感往往盛行于现代化转型时期。如有学者指出:“尽管怨恨心理及其助推的报复行动见于任何时代,但相形之下,平权观念制导的普遍性生存比较与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层落差相对撞,则特别容易酿成怨恨的群体性积聚。” [21]平等的承诺与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是怨恨感流行的主要原因。经由各种媒介的传播,“怨恨”感弥漫在公共空间中。
而“同情”的情感虽然自古有之,但在转型期的中国,同情感与人们的正义观、弱势群体的界定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情”是对“弱者”的同情,而对“弱者”的身份界定则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比如富人与穷人、官与民。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弱者”和“强者”的范畴也具有流动性,人们并没有固守某种教条式的区分,而是在具体的事件、具体的情境中区分“强弱”,同情“弱者”,怨恨“强者”。同情感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怨恨感。就如同在夏俊峰案件中,最初人们建立了“小贩=弱者”、“城管=强者”的心理框架,之后,又把小贩和城管都视为“弱者”,而此时的“强者”则是制度。
对目前中国社会情感现状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情”和“怨恨”的存在自有其原因,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如果太多的负面情感弥漫在社会中时,我们就可以称其为“社会情感失范”。有学者把“社会情感失范”界定为“社会的情感规范和价值观念遭遇反抗或处于相对脆弱、阙如的社会状况”。[22] “当前公共情感的失范,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23]比如,“在相对自主的赛博空间,我们也不难发现公共情感的严重失范状态。随便在哪个论坛,网民们似乎都是怒气冲天,对于政府官员和富人充满了讥讽和怨恨。官员的贪婪和缺乏基本的操守,富人的嚣张和狂妄,经常成为公共情感宣泄的狂欢对象”。[24]这种失范在“李某某案”和“夏俊峰案”中都有所表现。但对此的检讨不是本文的目的。
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媒体报道中的“情感”问题。在不少社会冲突议题上,媒体的报道已经成为一种“情感的仪式”,带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吸引公众对事件的参与。“情感”的话语策略有助于倒逼事件的真相。在中国的语境中,社会冲突性议题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媒体通过“情感”的话语策略,有助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急速扩大传播的范围,冲破地方政府的控制,迫使政府对事件做出回应,一步步地揭示出真相,最终促成事件的解决。因此,“情感”具有“倒逼”真相的功能。“情感”也有助于调动道德的资源,这也可以倒逼政府做出回应。在一些议题上,“情感”的策略类似于社会抗争中的“闹大”。有学者指出:“通过戏剧化的抗争剧目,“闹大”引发民意的爆炸性释放,并以此吸引外界的关注、帮助和支持。” [25]媒体的情感可以调动公众的情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情感”也影响到媒体的报道框架,我们所分析的两个案例表明了这一点。媒体对于“情感”的建构往往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的,也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贫富、官民等对立框架。媒体秉持一种“弱者的正义”,而“情感”则被视为对正义的呼唤。虽然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中立、客观不符,但由于“情感”的正义性也就被正当化了。当然,这背后不仅仅与正义的想象有关,有时还与媒体的商业追求、炒作需求有关。
媒体这样的“情感”有可能会产生失范的问题。在关于“李案”的某些报道中,“怨恨”情感宣泄的背后是对新闻专业主义操守的违背,而在“夏案”中,仅仅对夏俊峰及其家庭表达同情,也并没有实现媒体的公共性。抛开我们讨论的案例不论,在不少议题上,媒体的“这种缺乏宽容和理性的情感宣泄,这种怨恨式批判,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倒可能加深社会隔阂和断裂”。[26]须知,媒体是一种公共性的平台。媒体的情感失范则是指媒体呈现或传播的情感基调没有吻合公共性平台的角色。
在当前阶层分化严重、阶层冲突频发的时代,媒体更应该扮演好公共性的角色。我们并不是说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是由媒体造成的。阶层冲突的问题有着复杂的原因,前文已经述及。但媒体的报道有时候也会推波助澜。不论是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还是后来的新闻框架理论都证明,媒体的报道框架、叙事策略、原因归因显然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当媒体采取“二元对立”的框架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有可能会加剧阶层之间的对立态势。
若要扮演好自身公共性的角色,媒体需要走向公共理性。我们借用了罗尔斯的这一概念。“公共理性”要求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不能从当事人的身份、所处阶层等因素进行选择性的、带有偏向性的报道,而应该努力还原事件的真相,扮演公共平台的角色,并以“公共理性”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超越个体身份的。易言之,我们所说的“公共理性”并不是某一群体的“理性”。以夏俊峰案为例,公共理性要求媒体的报道不能根据“小贩=弱者=正义”、“城管=强者=非正义”的逻辑,不应根据当事人的身份进行事实的选择,而应该将议题引入公共性的维度。公共理性并没有排除情感的价值,新闻报道是由具体的新闻人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感”的色彩。公共理性会产生良好的公共情感,它在不同的议题上有不同的呈现。比如在灾难面前,它表现为悲悯,而不是娱乐,表现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而不是追求冲击力和煽情。其实在夏俊峰案中,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有良好的“情感”表现,媒体同情的对象从夏俊峰这方转移到夏俊峰与被刺小贩,三个家庭都被视为“制度的悲剧”,媒体上被刺死小贩申凯父亲的声音也让人动容。这样一来,媒体就开始超越带有身份色彩和偏向性的“弱者正义”,重塑了自己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性,并建构了自己对制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
上文主要考察了媒体在进行冲突性议题报道时的“情感”策略。但“情感”政治可以说影响到整个公共舆论系统,包括媒体、意见领袖、网民等多元主体,这些主体的“情感”及互动塑造了当前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情感”是如何嵌入到公共舆论中去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王宁:《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②成伯清:《“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人民论坛》2011年第18期
③上文关于“夏俊峰案”及张晶的叙述,来自于杨璐:《从小贩妻子到沈阳张晶》,《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10月25日
④刘水:《一个弱女子如何拯救夏俊峰》,《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5日
⑤李瑾:《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获死刑背后:妻儿命运受关注》,《工人日报》2011年8月13日
⑥⑦[美]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第47、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平之:《夏俊峰案再反思:我们不该沦为乌合之众》,http://opinion.cntv.cn/2013/10/08/ARTI1381226140674753.shtml。
⑨《网友称夏俊峰妻子张晶错认老公 将崔英杰流泪照片当作夏俊峰》,
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Media/2013_10_07_176749.shtml
⑩《夏俊峰案落幕 三个破碎家庭却无法复原》,《东南早报》2013年9月26日。
[11]《小贩夏俊峰家仅吃了10分钟 城管申凯父亲车棚里吃泡面》,《深圳晚报》2014年2月7日。
[12][22]郭景萍:《情感社会学》第378、11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3]王石川:《“夏俊峰案”拷问城管制度》,《东方早报》2011年5月10日
[14]王传宝:《别让“他妈的”弄脏媒体的脸》,《环球时报》2014年1月4日
[15]“2013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课题组:《2013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
[16]魏永征:《薄案与李案:怎样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17][18][19][21]张凤阳:《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怨恨》,《学海》2014年第2期
[20]李亚妤:《怨恨、互联网与社会抗争》,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3][24][26]成伯清:《从同情到尊敬:中国政治文化与公共情感的变迁》,《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9期
[25]韩志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为南京大学奥美创意研究院2014资助项目“‘情感抗争’:社会冲突中的舆论、情感与正义”中期成果。